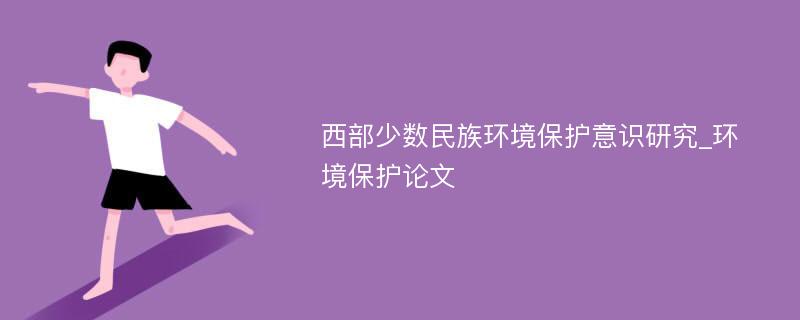
西部少数民族环境保护意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保护意识论文,西部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056—04
1.研究意义
随着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环境科学及其基础理论——环境伦理学在我国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颇丰。当今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伦理学和西方伦理学(含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历来注重“天人合一”,环境伦理思想在先秦诸子学说中已经相当普遍,并为后世不断扬弃[1]。注重“人与自然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新文化”运动至今,中国传统文化屡遭劫难、衣钵无继。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环境问题解决的可贵品质被西方学者逐渐发现了,从而重新受到国人的重视。再看西方,16世纪以来,工业生产一日千里,环境破坏日益严峻,学者们为了避免世界环境遭到致命破坏,创设了“西方环境伦理学”,强调自然界的固有价值,倡导人类敬畏自然、珍视环境[2]。马克思主义环境伦理学属于其分支。中国传统伦理学是随着农业社会而产生的,西方环境伦理学是应对工业化所引起的环境恶化而运生的。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环境保护意识是在人们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经验中自发形成的。
古代的西部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绿色生机的西部。今天的西部是生态面临极大威胁的西部,在西部开发中如果忽视了环境意识文明建设,后果不堪设想。国家能够认识到在开发中将环境保护和治理提到首位[3],意义重大!环境意识是环境治理的基础,西部少数民族环保意识在西部开发中的环境治理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中国传统环境伦理学和西方伦理学都不能代替它的地位,因为西部少数民族环境意识有着自己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1.1鲜活性和实践性
西部少数民族环境保护意识不是历史上的而是鲜活的存在着的;不是书本上的而是在生活中的正在被实践着的。如果国家将之上升为强制性规则,人们不会有“猝然加之”之感。而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出现断层,重新恢复,尚待时日。西方环境伦理学仅仅是学者们的一种理论学说,立即实践,亦非易事。优劣明显,无须赘言。
1.2广泛性和权威性
其他两种生态伦理学都是学者们的思想,影响仅及于一部分知识分子,真正的深入研究者实为有限,而真正的实践者寥若晨星,他们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少数民族环保意识,一般在本族群众是通行的文化意识和行为规则,自幼儿以至耋老无人不知,而且所有人都自觉践履,其影响的广泛性为余者不可比。权威性一方面表现为其意识和相应规则贯穿于生产生活的过程中的各种习惯和禁忌,另一方面表现在强制性文件中的禁止性规则和惩罚,比如《阿拉坦汗法典》曾经列出禁杀野畜的规定[4],又如《三旗法典》中规定:“不准乱砍树木,违者没收家产”。
1.3自发性和宗教性
西部少数民族生活地区大多是传统的农牧区,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息息相关。人们从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自然养育了人类,人类必须服从自然。这种意识自发地形成了若干有利于环保和生态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一般是零散、没有逻辑性体系化的朴素规则。正因为这种朴素直观的规则群还缺乏归纳总结能力,从而使其经常和图腾、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保护山水的原因是对山水神的敬畏,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环保行为,更不可能上升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1.4自然习惯性和主动认同性
少数民族环保意识已经深深的渗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了,自孩提时便生活在这样的族群中,人们都是自然而然地习得。其他生态伦理学,作为知识学问,没有较深的文化积累和长时间的研究是难于掌握的。也正是因为自然习得的过程没有外界强力,人们将这种思想已经内化为个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并且时刻地会体现在自己的日常行为中,所以也就产生了主体对环保意识的主动认同性。至于其他环境伦理学,学习者很难将之内化为自身的意识。
1.5规范性和属人性
所谓规范性是指少数民族的环保意识并非以抽象的哲学或学术理论体系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各种不同的规范形式存在,如宗教戒律、谚语、禁忌、习惯、传统、风俗、节日等形式。正因为这些意识是以某种具体的规则形态而不是周详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那么其效力一般仅及于本民族成员或者本宗教教徒,具有明显的属人性。
以上探讨并没有穷尽少数民族环保意识和其他两种生态伦理学的区别之处。但是通过总结可知:西部少数民族环保意识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要想实现西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该地区固有的环境保护意识,为我国环境立法提供借鉴之资,十分重要。
2.西部少数民族环境保护意识的主要表现形式
如上所述,民族地区环保意识是零散的,并无科学严谨之思想体系,至于其环保意识,我们只能通过人们生活生产中的一系列具体规则来加以认识和研究。
2.1环境保护方面的表现
2.1.1对山的保护。在藏族人的心目中,山不单纯是一个挺拔威武的自然存在,而且是神的象征。在藏族文化中存在着众多的个性鲜明的神,对神的崇敬还表现在各地存在的众多“拉泽”和“俄博”,二者分别是藏语和蒙古语,意指祭祀山神的场地,一般设在山巅。四川德格部落规定:不准在神山上打猎、采药、开垦;不准在神山、泉水、神湖处便溺。侵犯神山、神树者,要被脱光衣服,施以鞭打,并用烧红铁器在额头上烙十字印,戴上低帽,以驱鬼法逐其出境[5]。
2.1.2对土地的保护。对于牧民而言,大地是其衣食之源,因此形成了对土地神的敬畏。由于对土地神的敬奉,蒙古族宗教禁忌中有不少有关限制乱挖洞,乱动土的禁忌。在萨满教祭山、祭地、祭敖包等祭祠中充满了对故土的赞美和爱护之情。古代蒙古族中还有不少禁止破坏草场的宗教禁忌。宋朝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记载:“其禁草生而创地者,遗火而焚草者,诛其家。”古代蒙古人还忌讳把“奶或任何饮料或食物倒在地上”,“在搬迁时把垃圾扫干净,把自家的地面打扫干净,掘的草皮埋好,把羊毛、碎羊皮、羊骨头等都打扫干净。”这些习俗对净化草原环境无疑是非常有利的。藏族出于对土地的珍惜,又有另外的禁忌,动土须先祈求土地神;随意挖掘土地是禁止的,而且要保持土地的纯洁性。
2.1.3对水的保护。水孕育了生命,没有水,人类社会一刻也不能存在,如果水源遭到破坏,则所有的人都要受到损害,这是人类生存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所以对水源的保护,各少数民族习惯中都可以见到。
藏族对水源和河流的保护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将河流、湖泊神化。在藏族人的观念中,水是神圣的,主宰水之神是“鲁”即龙。青海湖及西藏的纳木错湖都是全藏区的神湖,而且环湖藏族祭湖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二是严禁污染水流。按照藏族的习俗,青苗出土至收割结束前,不准在河里洗澡洗衣服,以防因污染河水而触怒神灵招致天罚;在藏族的丧葬方式中,虽然也有水葬一说,但其适用地域不是很广,原因在于藏族人认为水葬会污染河流。因此多采用火葬和天葬,普遍认为只有火葬和天葬才是最洁净和神圣的。
对于蒙古族这样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来说,水是人畜的命根。在“逐水草而居”这一游动性意识形态中包含了许多关于防止水面污染和水源干涸的宗教观念和禁忌规范。古代蒙古人忌讳春、夏两季河中洗手,他们认为水是极为纯洁的,严禁以任何方式污染它。在古代蒙古族萨满教禁忌中,严禁在水里大小便,夏季在河水中脱衣服、洗衣服,甚至用手汲水,这些都被认为是对水的污染。
新疆自古就干旱,特别在近代更加干旱的情况下使维族人民推崇水、珍惜保护水的来源的信仰更加强烈。在此信仰的推动下维吾尔民间形成了“向饮用水里倒垃圾、污染水是一种恶行”的看法。维吾尔族人千古以来一直信奉着“在饮用水源里解手是最严重的罪恶,水是生命的来源,对流水小便的人就会小便失禁或尿道疼痛;水能满足万物的渴望,若水被污染,土地和农作物都会被污染”等观点。
2.2对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2.2.1对动植物的保护
西部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农牧业阶段,与大自然中的动植物朝夕相处,而且动植物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的吃穿住行都与动植物息息相关,因此,人们十分重视保护动植物。早在吐蕃王朝时期,藏区有了以佛教“十善法”为基础的法律,其中规定要信因果报应,杜绝杀生等恶行。其中对藏区生态环境保护也有规定。一份噶厦关于禁止打猎之命令(无发布时间)明确指出:“……为了使鸟兽、鱼、水獭等水中与陆地栖息的大小生物的生命得到保护,日喀则、仁孜、南木林、拉布、甲错、领嘎等地方,‘年厄’依法禁止打猎,要继续加强管理……违犯无论轻重,不偏不倚,立即抓起,进行惩罚,并将情况上报。”[6] 理塘木拉地区不准砍神树,也不准到其他头人辖区内砍柴,对上山砍柴者罚藏洋12~30元,越界砍柴者除罚藏洋10元外,还得退出所砍的柴,并没收砍柴工具[7]。理塘毛垭地区土司规定:不能打猎。不准伤害有生命的东西,否则罚款。打死一只公鹿罚藏洋100元,母鹿罚50元,藏羊或岩羊罚10元,獐子或狐狸罚30元,水獭罚20元。
在古代蒙古族的萨满教观念中树神往往和灵魂观、生命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普兰尼·加宾尼的记载:“现今皇帝的父亲窝阔台汗遗留下一片小树林,让它生长,为他的灵魂祝福。他命令说,任何人不得在那里砍伐树木。我们亲眼看到,任何人,只要在那里砍下一根小树枝,就被鞭打,剥光衣服和受虐待。”[18] 这种“神林”观念具有一定的环境保护作用。蒙古人对树木的崇拜和供祭,在《蒙古秘史》等典籍以及萨满的祭仪中均有明显表现与记载。如供独棵树、繁茂树、“萨满树”、桦树、落叶松等习俗的产生,从根源上说,无不与树木图腾观念有关。这种树木崇拜观念在蒙古族中至今仍有影响,对树木起到保护的作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鄂温克人当中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嘎勒布勒”,汉译为“根子”之意,即图腾。每一个氏族是以图腾为标志,例如“那乌那基尔”氏族的图腾是一种叫“奥腾”的鸟,“我乌特巴亚基尔”氏族的图腾是天鹅[9]。这种对图腾动物不能伤害的观念和实际行为中的禁打、禁杀等禁止行为起到了保护图腾动物的作用。
《新疆青年》(维文)1982年第11期发表的《新疆出土了我国最早的森林法》有这样的内容:从南疆的昆仑山北麓的古国——鄯鄯(现叫楼兰)王国古地出土了在公元三世纪的用当时的国语卢文记载的森林法,其中规定“不论是谁都严禁随意砍伐树木。对于砍伐有根的树木者,罚一匹马;森林在生长期禁止砍伐,违者罚一头牛”。有关保护森林、重视造林、造园的谚语在维吾尔民族里是很多的。例如:“有园林的人,就是有靠山的人”,“没有树林、果园的农民和富人,不算是真正的农民和富人”等等。维吾尔民族在哪里安家落户,首先要在那里周围植树造林,甚至在墓地上也种树养花,祝愿亡者的灵魂像树一样常青。没有特殊的情况,他们不砍折生长着的树木,也不让动物破坏,因而维吾尔民族建造的绿洲植被特别茂密。维吾尔民族的自然观点把有关的动物看作图腾,因此维吾尔族不论为消费或为取得经济利益,从来不随心所欲地大量捕猎动物,对自己的牲畜也不使其肚子挨饿或鞭打折磨。维吾尔族人一般也不会毫无根据地憎恨猛兽禽和无益的动物,因为他们知道猛兽吃病老的动物,改良其品种,提高其素质。总之,维吾尔族人认为人类和动物之间从来有密切关系,降临到动物身上的任何危险和灾难,同样会落到人类头上;假如全体动物死光,那时人类在精神方面就会感到非常孤独。所以,他们将关心和保护动物的习俗提升到民族传统意识[10]。
西南少数民族是非常重视对鸟类和各种动物的保护。在云南鹤庆县西山一带的白族中,流传着一个“祭鸟节”。每年清明前后,人们身着盛装,吹着唢呐集中到山野草坪,先由一位长者在乐器伴奏下唱歌,赞颂鸟类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接着人们踏歌而行,边行边把食物撤在草坪上供鸟类抢食。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也同蒙古族一样,在古代就有禁止猎取和食用他们所崇拜的作为图腾的动物的习俗。
2.2.2水资源利用
西南地区虽然多为山区,但在许多地方,人们有一种充满自豪感的说法“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哈尼族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山坡上修筑梯田,从山脚到山顶,上下可以垒叠数百层。这么高的地方水从哪里来?哈尼族通过千百年来的实践,以他们特有的方法将高山密林中凹潭和溪流的水引入盘山而下的水沟,水沟迂回曲折流经层层梯田。每块梯田根据其面积规定的用水量,然后通过一个木槽,十分巧妙地将水引入田中。正因为有了梯田和水,才把大片的山区变成了盛产谷米的良田。凡到过哈尼族山寨的人,都会为哈尼族人民的这一独特创造赞赏不已[11]。
2.2.3轮休制度
自然资源是人们的生存之本,为了保持自己和后代人的生存基础,西南少数民族在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合理利用资源的方法。其中典型的是轮耕制度和牧草轮休制度。一般观念认为“刀耕火种”是破坏环境资源的落后的耕作方式,但是有的学者经过细致的考察,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发现了有利于资源合理利用的轮休制度:他们的“刀耕火种”也并非某些人想像的那样是一种破坏性行为。凡进行“刀耕火种”的地方,都要将其土地划为若干片(一般是1~20片),在这些分为片的土地上,有的是耕种一年后即让该片土地轮歇;有的是耕种2~3年但轮种不同的作物后让该片土地轮歇。而在轮歇抛荒的土地上,人们又种上速生树木或经济林木。这样做的结果,有利于土地资源的良性循环,也有利于森林植被的恢复生长。由此可以看出,“刀耕火种”并不是没有节制地将山林砍光烧光,也不是没有止境地向大自然掠夺索取,其中包含着人们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冷静理智[12]。
西南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的调整,寻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其中积累了不少经验。首先是对牧草的利用和保护。在实践中,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总结出根据季节的变化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做法。例如居住在云南红河沿岸的哈尼族、傣族,有的村寨分为上村和下村两个部分。许多人家上村有一个家,下村也有一个家。夏季,他们把牲畜赶到海拔高的上村放牧;冬季,则回到海拔低的下村放牧。这样做,一方面解决了牲畜的饲料问题,另一方面轮歇放牧有利于牧草的再生。以上所属各少数民族的利于环境保护的传统习惯具有实践性、鲜活性、习惯法等,使我们加强西部环境保护过程中丰富的思想源泉和制度储备。
3.研究西部少数民族环境保护意识的价值
3.1研究西部少数民族环境保护意识是文明发展的需要
人类历史一再表明,一个文明的兴起必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每一个文明的衰落和消亡,也必然缘起于生态环境的过度破坏。世界上文明古国的盛衰即为明证。中华文明独存于世,与其统治者思想中的宏深的生态智慧紧密相关。我国西部民族聚居区,大多自成一个文化体系,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少,即使与中央王朝世代联系的藏族同胞也不例外。因为西部少数民族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一直践履其生存智慧,所以保证了其自身的生存环境免罹危困之灾,尽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西部民族区域自古是一个自满自洽的自然—人文体系,近代以来屡遭破坏,这也是西方工业文明传入中国后对西部的影响之一,因为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持,而资源的储备地又首推西部地区。
历史学家研究表明古代文明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破坏森林、过度使用土地从而导致良田变成了荒地,自然失去支持人类生存的能力。“文明曾经跨越过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人类的某些文明之所以灭亡是由于“人类践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一旦环境迅速恶化,人类文明也就随之衰落了[13]。如果没有谨慎的态度去对待工业文明的发展,其最终结果似难逃厄运,西部开发的目的是“西部经济上有所进步”,如果因为经济发展而牺牲了环境、毁了生态,则得不偿失。因此,西部开发,环境先行!但是,西部独特的背景和社会特点决定了在这个地区积极发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环境保护意识是其他的环境生态思想不可比拟的。综上,保护和发扬西部少数民族环境保护意识是促进发展西部经济、维持西部文明的必然要求。
3.2发扬优良意识,为环境立法提供借鉴
西方生态伦理学和中国传统生态伦理学都是以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圣贤学者感天人之交际,织经纶之伟思。此种学者书本上的理论是否能能够解决西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尚待明证。少数民族环境保护意识却是西部土地上自然生发的,与各族人民有着深厚的亲缘性,人们生于斯、长于斯,传统的意识已经深深地刻烙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只要国家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尊重其传统并且给予物质上、制度上的相应保障,人们会自然接受的。在这个问题上,国家法和民族固有法之间的龃龉必可消弭无间,因为“传统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遗产,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14]
所谓的“逻辑严谨、论旨宏远”的生态伦理学具有超然性、普适性,而少数民族环境保护意识的根基本身就在西部,千百年来存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也最适合解决西部问题。发展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也是民族生态文化系统的调适和重建。当前,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部大开发不仅仅是经济的开发与发展,也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更是环境资源保护的改善与实现。“要对付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15]。我们在西部开发中不断地发掘和保护这些思想就已有很强的社会价值和实践可能性,其立法借鉴意义亦在于此即文化自身的优点。
结语
人与自然本为一体,互生共存,先民即有所知。古代智者深有所感,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此思想具有重要的生态伦理学价值[16]。反而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了之后,人类得意忘本,开始破坏自然,恶果又非人类所能受领。西部少数民族环境保护意识在长时间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在西部开发中我们必须努力发掘、大力保护,在未来环境立法中吸收有价值的养分,为构建一个生活富裕、生态平衡、社会和谐的新西部而奋斗!
[收稿日期]2006—1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干旱地区雨水集蓄利用法律问题研究”项目(06xfx007)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西部缺水地区雨水资源利用法律问题研究”项目(05JA820012)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