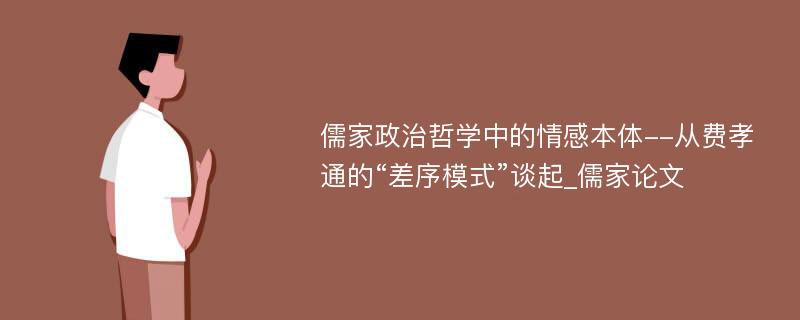
儒家政治哲学当中的“情之本体”——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本体论文,格局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政治哲学的经验论基础是一种以广义的“情”为本体的私域经验,这种经验模式是儒家思想与文化所独具的,它解决的是个人与共同体是如何达到和谐的问题。西方政治理论往往把握到了个人与共同体的两端,却忽略了从个人的经验究竟如何推广到社会的和谐的动态过程,尽管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注意到了“同情心”作为道德的动力,但是儒家却将这种以“同情心”为核心的“仁”看作是情感与生命的本源,具有“与天地参”的本体性质。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意味着,儒家政治哲学的起点是每个个体的修为或“文化化”的道德修养,然后进入到家庭价值领域,进而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最后则是整个世界的大同或者“永久和平”。这种内在的次序恰恰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架构。
一 “同心圆”隐喻:如何理解“差序格局”?
儒家政治哲学的架构,在表面上呈现为“身—家—国—天下”的等级次序。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这里面,以“隐喻性的思维”所言说的,就是一种由近及远的“以己度人”的推广方法。这种格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所谓的“差序格局”,这是社会学家费孝通研究中国“乡土社会”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它也基本适用于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的解析,因为“乡土社会”在中国农耕社会当中构成了基础的社会单元。
然而,费孝通却始终没有给出“差序格局”以学术上的界定,这四个字本身就可以让中国人“望文生义”,但是究竟什么是“差序格局”的明确内涵呢?费孝通与哲学家们试图明晰界定概念不同,而是给出了一个著名的“同心圆”的隐喻,试图来描述他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在1948年初版的《乡土中国》里对其描述主要在于如下三点:
(1)“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①
(2)“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②
(3)“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③
从这种列举可以得见,(1)所言说的是“己”乃中国人的社会同心圆的核心,由这个核心来拓展出整个的社会关系,正如水波的扩散后有远近和薄厚一样,近则“亲”,远则“疏”。这恰恰是儒家的社会建制。这是因为,在原始儒家那里就已经奠定了这样的思想:一方面,爱是有“等差”的,爱是因亲疏而有别,墨子的“兼爱”在儒家看来则是一潭死水;但另一方面,极远的关系也是可以由“己”推导出关系来的,从“身”到“天下”是一脉贯通的,每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有差别的社会责任。
既然已经确定了同心圆的“圆心”和“圆圈”的基本格局,那么,从圆心到各个逐渐扩大的圆圈,其间所维系的最基本的关系是什么呢?(2)回答了这个问题。按照费孝通的意见,居于最内核地位的就是“亲属关系”,换言之,最小的同心圆和趋近于最小的同心圆,其基本关系都是亲属。当然,这种亲属关系既有上传下承的纵向的“血缘关联”(在费孝通看来其核心就是“生育”),又有相互结合的横向的“婚姻关联”,由此构成了纵横交错的社会网络,儒家思想和制度就置嵌在这个社会网络之中。
中国这样的“同心圆”的社会结构,显然是同西方相对而出的,(3)恰恰在言说这样的社会结构的比较事实。西方社会的格局被比喻为捆柴,几束成一扎,几扎成一捆,几捆一挑,同扎、同捆、同挑的柴是不会弄乱的,这被用以比喻西方由社会团体组成的社会结构。比较而言,中国社会则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同心圆,这种附带在每个人身上的社会关系具有流动而非相对固定的性质,随着时空的转变而产生微妙的变化,而不像西方那样就连同一团体内的等级与组别都似乎是先规定好的。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精妙的解析似乎缺少了什么,它的确把握住了中国传统社会静态结构的特质,但是却失去了对于社会内在关系的动态分析。我们由此继续深入来解析,(1)对于同心圆的格局的解析固然没错,从社会结构来说,“己”也是绝对的核心。“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大学》。)但是,问题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已”或者“身”是逻辑起点吗?似乎儒家所论述的“性”、“心”之类都在“身”之前,或者说,费孝通关注的只是“身”与“身外”及其关系的问题,却没有考虑到“身内”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儒家看来才是缘起性的问题。这个缘起性的问题,在我看来就密切关乎“情”。
在费孝通那里,(2)也的确抓住了同心圆居于中心区域的层面,特别是生育与婚姻,确实把握住了中国社会关联的血缘与非血缘的两个核心要素。但是我们要问,在这些居于中心区域的层面之外,这个同心圆究竟是如何拓展和扩充下去的呢?难道是将亲属关系简单地套用到非亲属上面去吗?为何在某种语境下的为了非亲属去“舍生取义”而不是为了亲属呢?还有,“亲亲相隐”之类的现实冲突问题如何解决(为了维系亲属关系可以逍遥法外吗)?在此,亲属关系似乎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因为,必定对于其他社会成员不可能都以亲属关系待之,那么,一种泛化了的“大情”,而非囿于血亲和婚姻关系的“小情”,在居于非中心区域的层面,就开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越到同心圆的边缘,“小情”就越不起作用,而“大情”的作用则往往相反。
从中西社会比较的角度看,(3)也确实洞见到了西方社会的个体存在的“原子主义”的事实,但是,似乎矛盾在于,为何费孝通指出了“差序格局”当中的个体也好比是圆心,这不就好像主张中国式的一种自我主义吗?然而,必须从哲学的角度看到,“中国人关心自己时,其重心并不在于自我(ego)而更多在于自身(the self),即以身体为单位的自己,因此也许更好的说法是‘自身主义’,即以身体为单位的自己。”④ 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即使是最为极端的杨朱的“重己”的主张,那种“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氾论训》)的观点,实际上也是一种在中国思想中最为极端的自身主义,而非以人为万物尺度的主体性的张扬。这种解析无疑是正确的,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中的个体差异。许多汉学家和中国学者都由衷地赞美中国的“人本主义”和“个体思想”,其实是用西化的话语模式来阐释中国本土的思想。我还要继续追问一句,在同心圆心的传统这个人,究竟统同西方社会内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如果他或者她既然是出于关注亲属关系的圈子内的个人,同时也是将情感关系扩大化到同心圆边缘的个人的话,那么,“情”的要素在中国传统个人的“身内”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总之,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理论,所言说的更多是“差”和“序”,也就是等级的不同与次序的分殊,但是却相对忽略了“和”的另一面,而维系这种有差别的统合(亦即“和”)而非无差别的统合(亦即“同”)的关键要素。在我看来,就在于往往被忽略了的“情”,“人之常情”之“情”。
二 从“身内”到“身外”:“情”不可推吗?
在“同心圆”的隐喻当中,一个最重要的难题,这同时也是儒家政治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推爱”的问题——如何将在接近圆心部分还浓重的“情”推展到远离圆心的部分?对于这个难题的解答,自孟子时代就已经开始,所以孟子继续发展出“性善论”来为这种推爱提供理论基石,并以其所发现的“善端”为同心圆寻求真正的心理起点或者根源,从圆心到诸多圆圈的边缘就需要形成一种“推善”的过程。
但是,由此很容易产生的置疑就是,这种蕴涵在社会关系当中的、近“亲”而远“疏”的“情”,是可推的吗?是不是在接近圆心的部分这种推爱才有其“有效性”,而其根本就“推不远”,甚至会出现“推不动”抑或“推不成”的情形?这种置疑的观点已经开始出现:“推爱问题更是儒家的关键所在。亲亲是自明的(这是事实),但亲亲显然不够,还必须能够推爱及众,才能够构造出普遍有效的伦理。……当以亲亲原则进行推爱,就形成了后来被费孝通描述为‘同心圆’结构的伦理体系,所谓层层外推而达到爱众。推爱及众的严重困难是推爱推不出多远,恩义就非常稀薄了,最后完全消失在变得疏远的关系中,推不远所以推不成。这个困难的另一面是:天下有无数家,任意一家与另一家之间同样存在着与个人之间一样的矛盾和冲突。这说明亲亲模式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个充分的伦理基础,它对解决社会冲突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由家伦理推不出社会伦理,由爱亲人推不出爱他人,这是儒家的致命困难。”⑤
这类具有典型性的观点,其实是建立在两种假定基础上的。其一,就是它虚构了一种“陌生人理论”,似乎在“熟人”之外都是陌生人了,并从哲学的角度认为定:陌生人才是典型的他者,不能解释陌生人就等于不能解释他者。这种阐释显然是提出了这样的难题,边缘化的他者能否为“私”情所动?显然,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是以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为基础的,假如超出了血缘和地缘之外,如何推爱到陌生人就成了问题。依此逻辑,熟人之外,莫非陌生人。这种假设很容易被事实所击溃,因为它忽视了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以中国的汶川大地震为例,当受灾深重的时候,为何那么多的人(不仅是中国人)都奉献出了如此巨大的同情呢?为何同情者的“情”推及到千里之外的陌生人那里呢?如果“陌生人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大多数的中国人就应当对地震灾情无动于衷了,但事实恰恰并非如此。
其二,这种观点的另一个理论假设,则是一种“节情理论”。如果说“陌生人理论”是显在的,那么,这种“节情理论”则是更为隐在的。为何推不远,推不到陌生人,既具有客观化的原因,也有“节情”的主观化的理由。所以,儒家强调了情的自然天赋和本能使然的一面,“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记·礼运》。)但另一面却因此一定强调“治人七情”,(《礼记·礼运》。)一个“治”字就将政治化的意味赋予到了“节情”上面。所以孔颖达注疏说:“七情好恶不定,故云治。”被公认的观点是,儒家思想的主流就是“以理节情”,但是这种主流的形成,无疑是同后来宋明理学的位居主导是相关的(甚至走向了理性化的极端而灭情灭欲)。其实先秦的“原始儒家”在先秦时代曾有“主情”的主张,这在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当中已经透露这种信息。那么,为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越到晚期就越容易出现“节情”的主张呢?更深层地说,这里面的前提就是人情无非就是人欲,所以要“节”要“治”。但是,这种理解显然就是对“情”给予了狭隘的理解,人的情毕竟是丰富的,并非仅仅与生理欲望相关,还有日常生活当中的许多非本能和有意识的规定。无疑,在儒家那里,以“礼”治“心”就是要“节人之情”,但是,这种“节”在儒家那里始终是有“度”的,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最为理想的状态。
三 儒家政治哲学之“情”的基本规定
更深层地看,儒家政治哲学的“软性”的内核之一,其实乃是“情”,它构成了儒家政治思想的经验论的基础。这种以“情”为“本”的政治哲学,是通过如下的途径得以实现的:
首先,儒家私域的起点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这是一种内在的和谐。通过“以己推人”的同情,所谓“心同此感,情同此受”,从而将个人经验置于“主体间性”的换位思考的视角当中,从居于圆心的个人直到产生相应关联的陌生人,内在的中介环节就是“推情”,尽管必须承认“推”的多寡还是有差别的。比较而言,康德的伦理学和美学所强调的“共同感”,⑥ 则更多强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种理想化的取向显然不同于中国“主情”的感性化路数,而且其先验的设定也同中国的“主体间性”有异。
其次,这种实现的一种重要方法是通过艺术,或者说通过一种审美化的情感教育实现的,所谓“游于艺”与“成于乐”就是既注重审美的陶冶又关注道德的提升,二者是统一的。无论是诗歌使得社会人群达到“群”的功能,还是音乐使得“血气平和”与“天下皆宁”的作用,(《荀子·乐论》)都说明了“情”如何在塑造自我当中起到作用。这种规定除了与古希腊城邦文明那里有类似之处之外,在世界上似乎很少文化赋予了音乐以如此高的政治作用。
再次,在这种感性化的“共通感”的基础上,儒家伦理的“小系统”就是家庭伦理范围内的和谐。所谓家庭价值在这里面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不同于西方的“原子主义”取向的家庭系统。只有从这种“小系统”的和谐,才能达到“大系统”的和谐。按照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的说法,“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⑦
最后,儒家政治哲学的超越指向了一种“准宗教性道德”,这种道德不同于“社会性道德”那种公域化,而指向了一种内在超越的“私领道德”。所谓“曾点之学”与“孔颜乐处”,都是指向了这种具有某种审美取向的内在超越的宗教—道德的维度,审美、宗教和道德是内在统一的。这种体验其实也就是冯友兰所谓的“天地境界”和李泽厚所说的“审美境界”,其实中国的思想家们很容易把握到这层境界。
综上所述,“情”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同心圆”当中不仅是可推的,而且也构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经验论的基石,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情之本体”,它更深层地显现出中国古典的“情哲学”作为本土思想的重要基石的构成功能。
然而,当我们使用“ontology”这个词的时候就难免落入西化语言的窠臼,但是我们又不得不使用之。不过必须指出,我所使用的“本体”并不是在西方的ontology意义上使用的,而在“体用”的意义上使用其中的“体”的意义,这个“体”更接近于original substance。“本”“体”这个合并词,并不是作为“存在”(being)的本体,而是作为“生成”(becoming)的本体。为了表示我们所用的“ontology”并不是欧洲哲学语境内的作为“存在”的本体,必须将之替换为“生成”(becoming)这个规定词,称之为情的生成本体(the becoming ontology),⑧ 这正是由于“情”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说我所用的“情”作为本体,既指“情本”又指“情体”,而且是二者的合一,那么,它力主的并不是深受西方形而上学影响而孳生出来的“仁本主义”,而是一种反对过度以西释中的、立足于本土思想的“情本主义”。
那么,“情”究竟具有哪些本质性的规定呢?我们在此拟从“性情之辩”与“儒墨之分”两个角度来简要地厘定“情”的主要属性。⑨
四 从“性情之辩”到“儒墨之分”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性”与“情”往往是连缀在一起的,二者结合起来称为“性情说”,所谓“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庄子·马蹄》)1994年上海博物馆收集的战国竹简中就有关于“性情”论的集中论述,但是,“性”与“情”之间还存在着微妙的差异。
随着“郭店楚简”被发掘之后,其中的《性自命出》一篇对于“情”的独特强调被广为关注(前后共出现了20次之多),儒家重“情”的思想取向被重新彰显了出来。但是对于“情”究为何义,却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性自命出》最著名的提法就是:“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按照这种宇宙模式,儒家的这个支派就形成了“天—命—性—情—道”的生成图式和发展逻辑。但是,作为连通“性”与“道”的中介环节,“情”的意义往往被解释为“实情”,因为先秦时代的情多是指“实情”,这是汉学家葛瑞汉很早就提出的观点。⑩ 的确,在孔子与孟子的文本里的“情”更多是就实情而言的,但是到了荀子那里许多“情”的含义似乎更多是就人之情而言的,所以有论者更多认为《性自命出》可能是更晚的荀子学派的产物。
但是,根据《性自命出》的其他提法,如“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这些语境当中的“情”当然指的就是人之“常情”。另外,在论述“性”与“情”的关系时,还有更为重要的一句:“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这就是说,信是致情之方,只有如此,“情”才能出自于自然本性之性。当然,“性”与“情”仍是非常接近的,比如在《大戴礼记》中“性”就是指“喜怒欲惧忧”之“性”,(《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直到唐代的李翱也认为“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李翱:《复性书》)但是,“性”与“情”毕竟不同,“性”是指自然人性,“情”是发自“性”的“常情”,只是其中有“真情”亦有不真之情。而《性自命出》又说,“凡人情为可悦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凡人情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只要真实就好,即使过度也可以,所以说“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这都说明“情”真才能崭露出“性”,“情”更多是人们基本的悲喜好恶哀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七情六欲。所谓“欲生于性”、“恶生于性”、“喜生于性”都是此意。(《郭店楚简·语丛二》)先秦时代,“情”与“欲”是难分的,实际上前者是包含后者的,后者是前者更底层的部分,但是后来的儒家似乎更愿意将“情”狭隘地理解为“欲”,这也为“节情”诸论提供了某种前提。
因而,这种“主情”的说法及“性情”诸论,更多是暗伏在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深层而潜在发展的,它们更多被表面的“理性化”的主导思想所压抑。在宋明理学那里更是如此,最早在张载语录那里出现了“心统性情”的说法,后来被朱熹大加阐发。按照朱熹的看法,“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朱熹:《朱文公文集·元亨利贞说》卷67)但是,朱熹所理解的“性”与“情”都为“德化之性”和“伦理之情”,其基本范围显然被加以狭隘的理解了。而更重要的是,“性”与“情”,前者为理,后者为用,而且皆为心之理与心之用,“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朱熹:《朱子语类》卷20)所以说,“心统性情,统犹兼也”,(朱熹:《朱子语类》卷98)“心”在朱熹那里成了一种德性无疑占先和为主的意识活动的总体。历史的发展也恰恰顺应了这种趋势,在宋明理学的推动之下,“情”与“性”皆被儒学思想的主流压制下来,不仅“情”被歪曲理解,而且“以心统情”甚至走向灭“情”灭“欲”的极端。然而,理论上的压制并不等于现实当中的无存,儒家思想在社会实践当中,“情”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泯灭的。
通常说来,为人所属的“情”往往是与“实”相对而出的,当然,这里的“情”绝不是指客观化的“实情”。但是,对于“情”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实用化的理解与非实用化的理解,这也正是墨家与儒家的分殊所在。
墨子的政治哲学其实是最接近于现代观念的,也就是说,它以一种实用主义眼光和现实主义的考虑来看待政治问题。所以,孔、墨同尊三代圣人之道,但是,他们的选择却迥然不同:孔子“从周”而遵循礼乐教化,而墨子则“厚禹”而关注实际效用。所以,尽管墨子道明了“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的事实,(《墨子·三辩》)但是,与孔子要以变通的形式“复之”的取向不同,墨子则走向了“乐非所以治天下也”的极端。(《墨子·三辩》)这就是“圣人不为乐”的“非乐”论。这种非乐,实际上就是“非情”。当然,在看待情感的问题上,墨子以著名的“兼爱”而与孔子的“亲亲”不同。所谓“爱无厚薄”,(《墨子·大取》)这就是孟子所尖锐指责的“爱无等差”,(《孟子·滕文公上》)如此的泛爱其实就是无爱,泛情就是滥情,“所谓墨子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
而儒家的“泛爱众”则无疑是有等差的,所以才能构成“环环相套的”同心圆的结构;而墨子的“兼爱”就像一个规范而单一的圆一样,圆心到圆圈的各个半径都是一样。所谓“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视人身若其身”、“视人室若其室”,“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在墨子那里也形成了“身—室—家—国”的环节。但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圆一样(道家所谓的“大圆若缺”或“大成若缺”),这种考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与儒家比较,在墨子那里并没有“天下”的观念,而多了一个“室”的环节,这恰恰说明墨子并不关注“家”的那种亲缘关联,而是关注诸如“室”的实际方面。而且墨子对儒家批判的所谓“繁饰礼乐以淫人”,(《墨子·非儒》)“行不在服”,(《墨子·公孟》)也只是看到了“礼”的表面化的一面,而未深入到礼所承载的内容方面,从而以注重实际的践行为根本出发点。
因此,儒家对于墨家的批判(这实际上这也是对于法家的批判)及其思想差异,可以为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以法家为例,它完全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这是一种更为极端的看法,根本没有哪怕一点的情感要素参与其中,使得中国第一次大一统的秦国就是按照这种观念来强国。但是,强国不等于能治国,所以秦始皇之后不过一代就覆灭了,这也是历史的事实。
五 重思“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
以“情”为本的儒家政治哲学,究竟该如何参与到当代政治理论和实践当中呢?其实,儒家的价值在当代政治哲学论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当中,儒家的视角是非常独特的,它倾向于社群主义但又不同于社群主义。
首先,从表面上看,儒家政治哲学恰恰站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反面,因为后者是以一种“对原子主义”为理论起点的,但是儒家的所谓“己”却始终是处于共同体之内的个体,或者说是置身于同心圆内的个体,这在表面上同社群主义也是接近的。其次,许多论者都认为儒家政治哲学与社群主义是极为接近的,但是,从儒家政治哲学的本义看来,这只是表面上的接近,因为社群主义是一种“无情”的干瘪的政治思想,这恰恰是儒家政治哲学最远离社群主义的部分,也是当代美国的社群主义在实践当中根本无法建设的部分,因为其社会现实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基础的。最后,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都是建基在一种“二元论”的基础上的,也就是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共同体的分立的基础上的。如果从儒家政治哲学的那种“私域的公域化”同时也是“公域的私域化”的角度来看,这两端恰恰是本然未分的,不能采取那种“执其两端”的视角来处理这种关系。
当代学者马廷迈认为,西方学者往往从“整体主义”来理解孔子思想是不够的,因为孔子本人并没有使用个人与社会之间极性之类的概念,而是从“人和人的活动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如果发生冲突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而非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11) 这种回归到个人主义来论述的观点,的确不能完全令人认同,因为儒家哲学当中的个人本身就是社会化的个人,而儒家哲学当中的社会则是由“己”推演出来的。
但是,从活动论的角度来看个人与社会关系,反对两极区分却无疑是符合儒家思想真义的。然而,马廷迈却没有看到,这种活动就是一种浸渍了“情”的活动。所以,返回到以“情”为本质规定的人的活动,才是理解儒家政治哲学的独特精髓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缺失的关键所在。在这点上,安乐哲强调的“审美秩序”在儒家社群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就显露出“情”的活动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所扮演的“居间者”的角色。(12) 这正是儒家政治哲学对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主流的启示所在。
本文之所以凸现中国本土之“情”的地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原因,就在于要应对我们当前国内外研究“儒家政治哲学”的主流趋向。目前的儒家政治哲学研究受到了美国政治哲学主流特别是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太深的影响,他晚期《政治自由主义》的“薄版本”自由主义更不用说早期《正义论》“厚版本”的自由主义,对于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影响尤甚。然而,我们现在做中国本土政治哲学研究的时候,往往套用“硬性的”西式框架来对中国政治哲学加以规定。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视角看到,两千年来所谓“孔氏中国”的政治运作当中的“软实力”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推动儒家政治哲学的那种软性而非硬化的根本要素到底是什么?这就要回到中国古典的“情本主义”来加以探索,也许这才是“中国化”的政治哲学研究的真正理路。
注释: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6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6页。
④ 赵汀阳:《身与身外——儒家的一个未决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⑤ 赵汀阳:《儒家政治的伦理学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内刊版),2007年第4期。
⑥ 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Judgment,Translated by Werner S.Pluhar,Hackett Publishing Co.,1957,p.89.
⑦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⑧ 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杜威的“经验哲学”的确是同中国思想较为接近的。参见Alfred North Whitehead,Process and Reality,New York:Macmilian Company,1929; J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New York: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1934.
⑨ 在本文最全的版本中,笔者曾从关联的角度对“情”的主要属性进行了历史与理论的解析。该四重关系具体包括:1.情与巫:从“巫史传统”到“化巫入情”;2.情与礼:从“礼乐相济”到“礼作于情”;3.情与性:从“情出于性”到“心统性情”;4.情与实:“泛爱众”的有情对“兼相爱”的无情。其中,对于“礼作于情”与“情出于性”的阐释都来自于“郭店楚简”的启示。
⑩ A.C.Graham,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pp.59-65.A.C.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La Salle,Illinois:Open Court,1989,p.98.
(11) Michael R.Martin,“On the Confucius' Mentality”,in Chinese Philosophy,1990,XVII.
(12) David L.Hall and Roger T.Ames.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Dewey,Confucius,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Chicago:Open Court,1999,chapter 8.
标签:儒家论文; 社群主义论文; 费孝通论文; 差序格局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乡土中国论文; 国学论文; 墨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