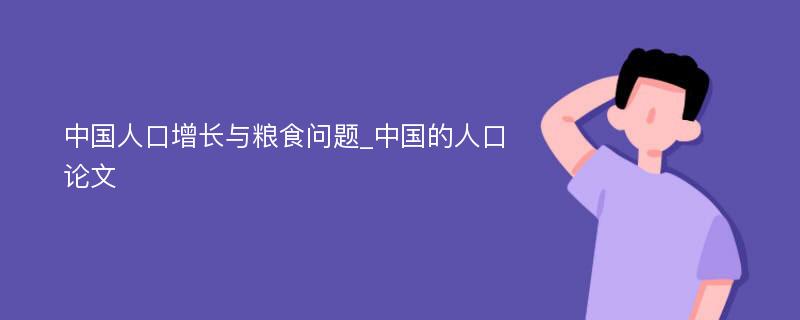
中国的人口增长和粮食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粮食论文,人口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自古以来,“吃饭问题”在中国这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泱泱大国就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古人说得好:“民以食为天”,而现代的认识则是:“无粮不稳、无农不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论在人口控制还是在农业生产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卓越成绩。但中国目前尚有6500万绝对贫困人口(我国1995年农村人口绝对贫困线为530 元——参见《经济日报》1996年3月20日),吃饭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还在于,人口增长势必会带来粮食消费的增加,因为人口是天然的消费力的存在,这该是无异议的。
我们常常听说一种说法:中国大陆以占全球7%的耕地, 养活了占全球22%的人口。这可以说是一种成就,但也同时给了我们一个信号——中国迄今仍处在温饱略有余的初级发展阶段。应当说,粮食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而问题的严重性又恰恰无法使我们掉以轻心。中国现在粮食供需紧张,粮价持续上升问题已开始为传媒所关注,与此同时,我们要提醒一下读者:眼下,“粮食短缺”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关心国事的读者一定可以从各路媒介获得这么一个信息:粮食问题是目前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例如,1996年4月8日出刊的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粮食生产要抓得紧而又紧”。《光明时报》于1996年4月18 日第五版也发表了令人瞩目的专论:“中国人民能够解决吃饭问题”。《中国农村经济》杂志在1996年第1 期专辟有“粮食问题专题”,详论中国粮食生产的潜力与前景。无独有偶,以展望未来为己任的《未来与发展》大型杂志也于1996年第1 期发表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一篇力作:“中国粮食的短缺与出路”。毫无疑问,如果粮食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势必影响我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及其发展,继而必然损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国民素质的改善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难怪最高决策层要说,粮食问题是最大的政治问题了。
我们举办本期论坛还有这样的背景:中国人口增长的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逆转的,而耕地的锐减问题日前也极令人关注。这种人增地减的情势会不会因此而演化出“粮紧”的问题,不能不有所讨论。二年前,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先生(Lester R.Broan)撰文认为:到21世纪前期,中国人口的增加将吃空世界粮食,2030年左右时中国严重的粮食短缺将招致全球性的饥荒,此言一出,即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各界人士各执一词,讨论热烈。布朗的预测会是真的吗?中国的人口增长和粮食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为此请几位学者参予了本期笔谈活动。胡鞍钢博士是对布朗的观点第一个作出反应的中国学者。尊重他的意见,我们全文转发了他最早刊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言论版(1994年10月31日)的一篇文章。蔡昉博士则与布朗博士曾在北京(1995)晤面讨论过“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其他三位学者也是很有见地的人士。现将他们的观点按姓氏笔划一并刊出,以飨读者。中国能够实现粮食自给的目标 胡鞍钢(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
最近,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Lester R·Broan )在《国际论坛先驱报》撰文:“2030年:谁能养活中国?”在国际上引起不小的反响。他预言中国将出现严重的粮荒,并对全球粮食市场构成严重影响。他说:“从1990年到2030年,中国总人口不断增长,但是粮食总产量至少减少20%,中国将进口约3.54亿吨粮食,而80年代以来,世界粮食出口总量每年1230亿吨。这将导致世界粮价迅速上升。摆在世界各国领导人面前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这种潜在的粮食赤字(grain deficit)迅速扩大。到那时,谁能供养十几亿中国人?”这是一种历史悲剧论。
1 中国比美国养活更多人口
对中国粮食问题,历史上曾一度流行过悲观论。早在45年前,中国大陆只有5亿多人口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曾讲过, 这是一种“不甚负担的压力。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他相信共产党的政府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人的面粉,才有出路。”
45年过去了,中国总人口惊人地翻了一番,由当时的5.4亿人口,增长至1993年的11.85亿人口,同期粮食总产量由1.13亿吨增长至4.56亿吨,跃居世界首位。当今世界上有资格、有能力供养十几亿人口吃饭的国家只有中国和美国,而中国用了只相当于美国50%的耕地,生产了相当美国总数的114%的谷物(1992年数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季报》1993年第1季度)供养了相当于美国总人口额的4.58 亿人口(1991年年中人口额,联合国《统计月报》,1993年3月)。
上述数据清楚地表明,尽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耕地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经济发展水平低,农业生产尚未现代化与机械化,但是中国人在过去的45年中却养活了比美国多三、四倍的人口。
2 粮食增长推测缺乏依据
布朗先生在文中推测,到2030年,如果中国大陆与人均粮食消费量达到目前台湾省人均水平400公斤的话,那时中国粮食总需求将达到6.51亿吨(按16.3亿人口额计算)。而粮食总产量为2.67亿吨,粮食短缺高达3.84亿吨。由此计算,中国粮食自给率只有41%。
当中国由低收入水平进入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人均粮食消费量随之不断提高,在未来时期,人均粮食消费400 公斤还是个较低的消费水平,这是一个与中国居民膳食习惯及膳食结构相适应的消费水平。或比较同意布朗先生对中国粮食总需求量的估计额,既使有些差异,也只是因对那时总人口额的预测不同,粮食总需求量额有所不同而已。
但是布朗先生对中国粮食总产量,增长趋势的估计缺乏科学性。他估计2030年,中国粮食生产量约267亿元吨。这是中国21 年前(指1973年)的粮食总产量。从那时起,中国粮食总产量已增长了72.2%,1993年达到4.564亿吨。
8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总产量净增长量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属于世界上粮食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统计,以1979—81年人均食物生产平均指数为100,1988—90年中国这一指数为133,增加了33个百分点,而同期低收入国家(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只提高了5 个百分点,中等收入国家只提高了2个百分点。高收入国家则无增长, 全世界平均提高了12个百分点,中国大大超过上述类型的国家和世界水平。(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
总之,无论是中国国家统计问题数据,还是世界银行统计数据,都表明了中国粮食总产量在不断增长,尽管这一增长中存在着周期波动(作者没有专文分析),但布朗先生把1973年中国粮食产量水平当作2030年的粮食产量水平的预测,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需要指出的是,布朗先生把上述缺乏科学依据的预测作为依据,从而推断中国的粮荒将变成世界的粮荒。这一推断也是没有根据的。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粮食消费大国,目前中国净进口粮食只占总消费的2%左右,是一个粮食自给率相当高, 粮食外贸依存度相当低的国家。粮食基本自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中国参与世界粮食市场贸易,纯属粮食品种与相互调剂,既使中国能够大量进口粮食,除了沿海地区之外,中南部地区地广人众,交通不便,将进口粮食大规模运送各地,特别是道远山区,其交易费用也是相当可观,极不合算。因此,不仅全国粮食基本自给的政策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而且粮食区域平衡的政策也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不可能依赖于世界粮食市场,更谈不上引起世界粮荒。
3 三种不同观点
对中国粮食问题存在三种观点:一是历史悲观论;二是盲目乐观论;三是谨慎乐观论。
历史悲观论过分地夸大了影响中国粮食增产的不利因素:盲目乐观论又过分地夸大了影响中国粮食增产的有利因素,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分析这些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无论是发挥有利因素,还是克服不利因素,都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有条件的谨慎乐观论,也是我们区别于布朗先生历史悲观论的关键所在。耕地前景与人口增长 胡伟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
让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进入21世纪,其中未来人口增长与粮食的关系,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外国人发出了危言耸听的疑问,国内上下都很关心。有的官员和学者从粮食产量增长前景等方面已经加以说明。其实,粮食的载体是耕地。威廉·配第早就说过,土地的价值在于“这块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中国历代许多思想家都重视人口与土地的对比关系。本文从耕地与人口的发展前景谈几个问题。
其一,高度认识耕地的重要性和特征。什么是耕地?中国有960 万平方公里陆地,居世界第三位,可谓“地大”。但并不是所有土地都是耕地。耕地是一种特定的土地,它是经过人类开垦后用于种植粮食等农作物并经常耕耘的土地。中国只有10%左右陆地是耕地,现在人均耕地面积1.19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耕地有两方面的重要特点:一方面,耕地不同于矿产资源,它是一种可持续利用的资源,但是耕地的某些组成要素可以被破坏、被消耗掉;另一方面,耕地有很强的有限性和地域性,陆地面积有限性注定了耕地有限性,耕地总是在一定区位上的,那么侵占耕地和区位竞争,就会使耕地面积减少。犹如工厂要产出工业品,耕地上要产出粮食等农产品,民以食为天,粮以地为体。所以,人口与粮食的关系,要落实到人口与耕地的关系。
其二,人口增长需要保障耕地面积。中国耕地到底有多少?1989年农业部公布数为14.35亿亩,国家统计局以此为基数,1994年为14.24亿亩(9491万公顷)。可是我国实有耕地数比统计数要大。90年代初公布的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为19.88亿亩。 美国人造卫星遥测我国现有耕地为22.6亿亩,这不能作为依据。所以,中国是以占世界7 %(统计面积计算)或9.4%(普查面积计算)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 %的人口。
按照耕地与人口的上述对比关系,对于未来我国人口增长的粮食供给,过去人们是比较乐观的。可是,不能盲目乐观。现在预测,我国总人口增长最高要达到16亿,其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会更快。如果假定农村人口可以自己解决粮食问题。那么未来我国人口增长的粮食问题,主要是未来城市人口的粮食问题。
当前,我国用了多少耕地来养活城市人口呢?根据国家统计年鉴,1994年:我国耕地为14.24亿亩,占陆地总面积9.88%; 市镇人口34301万人,占总人口28.62%;粮食总产4451.01亿公斤,粮食亩产300公斤。假定市镇人口每人每年消费400公斤粮食。那么,1994年全部市镇人口用粮1372.04亿公斤,需用耕地45734.67万亩(每亩300公斤计算)。这占全国统计数14.24亿亩的32.12%,占全国普查数19.88亿亩的23.01%。这就是说,我国用32.12%或23.01%的耕地养活占全国28.62%的市镇人口。平均几乎是一比一。 如果最高人口为16亿,城市人口大致为50%,那么,总人口所需耕地不能再缩小,城市人口用粮所需耕地会更多。这是假定粮食亩产不变的分析。
建国以来耕地面积减少数目惊人,这种趋势难以有效控制。据估计,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大体要1.5亩土地,其中有不少是耕地。怎样保障耕地面积是个大问题。今后:城市发展规划,要以提高内涵利用率为主,严格限制占用耕地。农村小城镇建设,要以原村镇为依托,量力而行,尽量少占耕地。城乡住宅建设要尽量不占耕地,尽可能把住宅建在非耕地的土地上;甚至建在山坡上,风景气候宜人,也有利于建山上的地下交通。又据说,住在高处的人口生育率很低。现有500 多个商品粮基地还不够,还要扩大。加快完成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的落实。加强耕地开发,保障一人至少一亩耕地到2030年。
其三,人口发展需要大力提高土地利用率。中国历代许多思想家都强调要“地尽其力”。耕地面积为一定时,提高耕地使用效率,等于增加耕地。如果耕地面积在减少,人口增长所需粮食在增加,那么,耕地使用效率的提高必须大于耕地缩小条件下人口用粮的增加部分。
提高耕地利用效率,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提高复种指数。复种指数高低反映人类对耕地的利用程度。目前我国平均复种指数只有155%多一点。较低的复种指数, 意味着没有充分利用光、热、水和劳动力资源。要充分认识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对缓解耕地不足与人口增加的矛盾,以及增加粮食等农产品的重要意义。我国提高复种指数曾出现多次反复,从1952年到现在平均每亩年增加0.6个百分点。主要受耕作制度改革指导思想摇摆的影响,有的地方还搞强迫命令、一刀切等。据有关专家预算,到21世纪初耕地复种指数可望提高到171%,从而增加总播种面积27548.4万亩,增加粮食总播种面积20661.3万亩,按现在粮食亩产计算,可增产粮食508.27亿公斤, 是现有粮食总产的12.3%。
第二,改造中低产田。划分中低产田的标准是什么?目前多以作物单产(亩产)高中低为准。其实,应当是把影响农作物产量的土壤障碍因素和强度作为划分高中产田的主要依据。土壤障碍因素和强度有:造成水土流失的坡度,盐碱化强度,干旱缺水量,风沙因素,土壤缺营养元素,等等。按照这些因素和强度,我国耕地中约有78.5%是中低产田。改造中低产田,就是要去除或减弱土壤障碍因素和强度,提高地力的等级。改造中低产田比开垦荒地投入省,用工少,见效快,改造好了能长期见效益。据测,如果做好中低产田改造工作,到下世纪初,可增产粮食大约688亿公斤。这项增产潜力相当可观。
第三,防治耕地污染。造成土壤污染的因素很多,污染趋势在扩大,后果严重。导致土壤性质变坏,土地肥力下降;引起农作物减产;污染粮食等农产品,威胁人类生活和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受污染的水田、旱地约150多万亩,在矿区附近的矿毒田、矿毒旱地150多万亩,用污水灌溉的耕地有2000多万亩。防治土壤污染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首先要控制和切断污染源,合理布局粮食、蔬菜、果木、渔业等基地,乡镇企业要发展无污染、少污染行业。其次要采取各种综合措施治理污染。再次是切实执行耕地保护法。还要把防治污染与耕地产权制度建立结合起来。目标是建立生态农业。粮食增长能否高于人口增长 郭书田(农业部政法司司长)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或是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粮食生产的增长能否超过人口的增长,有气候因素,更重要的是政策因素。从1949—1978年,先后经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人民公社几个阶段,粮食生产的增长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在这28年中,除有5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误造成减产外, 其余年份都增产的。这个时期粮食播种面积增长10%(由1.09亿公顷增加到1.2亿公顷),每公顷产量增长145.9%(1027公斤增加到2527公斤),总产量增长169.6%(由1.132亿吨增加到3.047亿吨),也就是说,总产量的增加主要是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与同期世界粮食总产量的增长90%是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相吻合的。在这个时期,我国人口增长77.7%(由54167万人增加到96259万人),粮食产量的增长高于人口的增长,从而使人均粮食产量由204公斤上升为318公斤。同时期,全世界谷物产量(不包括豆类和薯类)增长134%(由1995年的6.23 亿吨上升为1978年的14.61亿吨),人均产量由248公斤上升为343公斤。 在这一时期,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制度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下取得的。
1979年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农村率先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推动了城市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改革。 其中1979 —1984年,农业生产全面高速增长,粮食生产大幅度增加,由3.047 亿吨上升为4.037亿吨,6年连续上了两个新台阶(一个台阶为500 亿公斤),增长32.49%,人均产量由318公斤上升为397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由于调整产业结构,粮食播种面积下降6.36%(12058万公顷减为11288万公顷,即减少1.15亿亩)总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完全是靠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每公顷产量增长42.74 %(由2527公斤上升为3607公斤)。同时期,我国人口增长7.05 %(由96259万人上升为103051万人), 粮食产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
但是在1985年以后,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缓慢,出现了人口增长超过粮食增长的严峻局面。纵观1985—1994的10年,粮食总产量增长9.1 %(由4.077亿吨增加到4.445亿吨),而人口增长16.3%(由103051万人上升为119850万人),人均产量由397公斤下降为368公斤。这自然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粮食产量增长缓慢或基本上处于俳徊状态的直接原因,一是播种面积由11288万公顷减为10933万公顷(即16.4亿亩,低于16.5亿亩的警戒线),下降3.1%;二是单位面积产量由每公顷3607 公斤上升为4035公斤,只增长11.8%。1995年,由于中央和地方加强了对农业的领导,在灾害频繁的情况下,粮食播种面积恢复到11000 万公顷(即16.5亿亩),每公顷产量达到4208公斤,比上年增长3.6%;总产量达到4.65亿吨,比上年增长4.5%,高于人口增长1.25%的幅度;人均产量上升到384公斤,但仍未达到1984年的最高水平。 由于停止粮食出口,增加进口,粮食供求矛盾有所缓和,市场粮价趋于平稳。
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议和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提出到2000年粮食产量达到4.9—5亿吨,也就是说低线为4.9亿吨, 高线为5亿吨。1995年人口为12.1亿,如按每年平均增加1200万人计算,到2000年人口达到12.7亿,低线的人均产量为386公斤, 高线的人均产量为394公斤,无论是低线或是高线,应该说不是很高的。 至于到2030年,国内外研究部门有各种预测,大体可以归纳为低方案和高方案两种,低方案人均400公斤,高方案人均450公斤。人口以16亿计,低方案的需求量为6.4亿吨,高方案的需求量为7.2亿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有两个保证条件,一是播种面积不低于16亿亩; 二是每亩产量达到400—450公斤。也就是说人口与播种面积大体相等, 粮食人均需求量与粮食亩产量大体相等。我国的一些农业专家研究测算,粮食产量最大值为8亿吨。我们同莱斯特·布朗的分歧,主要不在需求的预测上, 而是在对供给能力的估量上。他是以低于现在20%的产量作为依据计算供求缺口的,从而得出“中国人口增长将吃空世界粮仓”的错误结论。摆在我国面前的问题是在控制人口增加的同时,如何保证粮食的16亿亩播种面积和亩产量达到400—450公斤(1995年为250公斤)。 这就必须从现在起采取一系列的重大措施,付出巨大的投入。包括政策投入、资金投入、科技投入和物质投入。政策投入主要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解决种粮食效益低的问题,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种粮食和粮食产区的积极性。资金投入主要解决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多年来形成的“重工轻农”问题,使农业的基础地位真正落实,“口号农业”真正消失,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真正改善,农业发展后劲真正增强,农业抗灾能力和综合生产能力真正提高,农业新的资源得到真正开发。科技投入一方面主要解决科技服务体系不健全的问题,把现有的适用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提高增产中的科技含量;另一方面,解决科技后备不足的问题,在品种以及其他生物技术等方面要有新的重大突破。物质投入主要解决农用生产资料数量、品种、质量和价格等方面的问题,切实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人们担心的问题是这些投入得不到真正的切实有效的落实,因而目标难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在全党从上到下形成真想农业还是假想农业的共识,在农业上率先实现中央提出的两个根本转变。
“人口—粮食”均衡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追求 曹力群(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1 从特定意义上讲,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任何国家、 任何历史时期的所有社会问题的起点,而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归根到底落实在人口与食物的均衡上。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人口与粮食的均衡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被人们当作“新问题”而提及。
2
当一百多万年以前的第一次农业革命产生了农耕文化并带来剩余农产品以后,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就摆脱了纯自然性质,而人类所独有的特性则体现得越来越强,这种特性的极端表现就是一方面有大量的人口因饥饿而毙命,同时又有大量的耕地和食物被人为地荒废和遗弃。即使在科技、运输高度发达的今天,这样现象仍非罕见。因此,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饥饿成了始终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魔鬼。也正因为如此,从古到今,无数人为“粮食/人口→均衡”这一关系式所醉心,并得出了难以计数的“解”,并且还有无数未知解在等待人们去探索。
3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 每一次人口粮食发生严重失衡状况都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换句话说,每当“人口—粮食”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话题时,也就预示着有一场新的社会变革的到来。当农耕社会中人口与食物的低水平均衡恶性循环步入“马尔萨斯困境”时,新兴的工业革命突破了这一陷阱,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当人们苦于无可耕荒地开垦,饥饿将威胁人类时,“绿色革命”又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单位面积产量的大幅度提高;而当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再一次降临人间时,“可持续发展”的旗帜又将召唤人们去做出新一轮的更大努力。
4 随着社会发展内容的丰富, 人口与食物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从去年开始,一个很流行的话题——“谁来养活中国”将全球关注的热点聚到了中国的“人口——粮食”平衡问题上。众所周知,它起因于以全球研究闻名的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博士1994年末发表的一篇短文,文中提出了“下一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经过一年的争论(包括到中国考察和讨论),布朗博士1995年9月又著新书, 再谈中国的粮食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人口与粮食的平衡存在二方面的制约。从需求方面看,一是人口基数太大,并且还将继续增长一段时期,二是改革以来特别是近四年,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饮食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蛋、禽、肉、奶、酒的人均消费量剧增,这些食品消耗了大量的粮食。从供给方面看,一是工业化进程使耕地面积减少,二是水资源在许多地区几近枯竭,三是化肥用量达于饱和,单产增加很难维持以往的速度。由此,他预测,如果中国在工业化进程的同一阶段中更好地防止耕地丧失,把减少幅度缩小到日本的1/5,同时饮食结构改善不大,那么, 单纯的人口增长因素就会在2030年把每年的粮食进口量推升到2亿吨, 相当于目前全球出口量的总和。再进一步预测,如果中国的人均粮食年消费量从目前的约300公斤增加到2030年的400公斤,那么,届时将需进口3.69 亿吨粮食才能满足需求。这样一来,中国今后几十年间的粮食进口量将可能超过全球粮食的出口总量,而需要进口粮食的国家又多达100多个,买方之间的竞争会非常激烈,缺少外汇的落后国家将加剧贫困和饥饿。由于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对布朗的观点表示了反对或支持,见仁见智,因此本文不打算再做争论。但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这样短的一篇文章会引起全球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极大的关注。我想除了近几年受气候影响部分国家粮食减产,如日本、朝鲜等国,而引起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剧烈,加之布朗本人的声望和影响以及部分别有用心或不了解中国实情的人推波助澜外,对这件事更多地应该放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来分析。而当我们讨论清楚了这场围绕中国人口与粮食关系争论的社会经济背景后,实质上已经解答了“谁来养活中国”这一命题。
5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似,在中国的现代化启动时期, 人口压力阻碍着社会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步提高,有相当长的时期难以摆脱“低水平均衡陷井”的制约。就粮食而言,自农村改革以来农村经济出现了惊人的增长阶段,全国的粮食生产连迈二个台阶,1995年粮食产量达到4.65亿吨,比1978年增长了52.6%,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2%。然而,由于人口增长因素影响,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却在1986年达到最高点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当然,并非说人均粮食消费量越高越好,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最合理的标准,否则将是浪费)。更为严重的是这个现象背后的几个数据:a.全国人均占有农林牧用地仅0.4 公顷,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4,生产粮食的基本资源——耕地,1993 年人均只有0.08公顷,只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3;b.长期以来,农村人口比重始终在70%以上,而粮食的商品率也一直没有突破30%;c.1978—1994年,我国粮食净进口总量达9561万吨,虽然仅占同期国内粮食生产总量的1.4%,但耗去的外汇却是不容忽视的;d.每年所需化肥量近1/3靠进口补充,约在1300万吨左右;e.农村贫困人口虽然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6500万人,但是这部分人的脱贫难度却是极端困难的;f.由于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和农膜,部分地区的耕地土质中有机质和微生物含量下降,阻碍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使用;g.现有耕地每年都在减少,1987—1994年间平均每年减少约为14万公顷。这些因素将使人口—粮食的平衡在长时期内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并直接制约着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与质量。
6 当然,这并不说明中国要靠别人来养活,但是, 它让我们看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发展要比发达国家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沉重的代价。中国的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已经并准备继续付出这样的努力和代价。当前,我们首先应该做到:a.严格保护耕地,在稳定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粮食播种面积;b.改善农业生产结构,增强农产品的创汇能力,创造粮食供给的良性循环环境;c.促进科技成果向粮食生产的转化,如将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目前的35%提高到50%,将可以替代耕地减少的损失;d.提高农村教育文化水平,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切实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人口低增长目标,并带动人口的非农转移;e.建立合理的粮食流通体制,制定合理的价格和市场体系,增强粮食生产的内在动力;f.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活跃的世界粮食贸易是国际分工合理性的标志,不存在谁养活谁的问题,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更多地参与世界粮食贸易是必然的;g.改善饮食构成,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如果农村居民口粮消费达到1994年城镇居民102公斤/人的水平,每年每人会节约159公斤粮食,按粮肉转化率5:1计,可增加31.8 公斤的肉类消费;h.杜绝浪费和非生产环节的损失。一个违背历史和逻辑的神话 蔡fǎng(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博士)
布朗预测,中国到2030年,人口将增加到16亿,而由于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极高,食物结构的改变也将加快,今后中国人的粮食需求将大幅度提高。与此相对应的供给潜力则不乐观。由于经济发展,耕地和水资源越来越多地转为非农使用,靠扩大播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的机会很少,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是有限的。由此,布朗预测,从90年代开始,中国粮食产量将以每年0.5%的速度下降,到下个世纪30 年代,中国粮食缺口将为2.16—3.78亿吨。
布朗的预测还指出,面对中国如此巨大的粮食缺口,全世界都不能给予填补。以致他得出耸人听闻的结论:尖锐的食物短缺和伴之而来的政治不稳定,可能使中国的奇迹中途夭折。而一旦中国转而面向世界寻求食物供给,则中国的食物短缺将成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短缺;中国的耕地和水的短缺将成为世界的短缺。布朗先生的用心是良苦的。他希望通过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这样惊世骇俗的问题,警醒世人关注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但是,由于布朗所作出的预测是建立在不科学的方法论和不确切的事实基础上,可能会引起极大的误导,因而是不负责的。
首先,布朗的预言不能从历史得到任何印证。自从马尔萨斯出版了《人口原理》,作出食物供给将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从而人类将面临饥饿的预言后,关于食物供给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适应性,一直是人们所热衷讨论的主题。而马尔萨斯以后的人类进步已经否定了他的这个预言。就世界整体和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来说,新的耕地的开发,新的农业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以及对土地和对劳动者的投资,使“马尔萨斯交点”〔1〕并没有到来。
用1961—1992年世界食品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与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相比,作为食品增长对人口增长的领先系数。从计算结果可以发现,马尔萨斯所预见的人口增长快于食品增长的现象并未发生,全世界平均的这个领先系数为1.17,即使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来看,该系数也达到1.34。
其次,布朗的研究也不符合经济逻辑。摆脱开波利安娜与卡桑德拉之争〔2〕, 除了布朗的预测所使用的关于中国农业资源和技术潜力的资料有大量不实之处外,他实际上假设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人的能动作用。即面对食品需求的增长和资源压力的增强,中国农民、消费者和政府政策,以及贸易伙伴对此皆不作出反应。这显然不符合经济逻辑。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事实所表明的,任何经济情形的变化,都会表现为产品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对于后者,所有的经济当事人都会作出相应的反应。技术创新、贸易扩大等一系列因素都足以应付任何能出现的问题。例如,从美国人均资源的概念来看,中国农业发展早就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布朗所描述的中国农业的需求和供给特征,始终存在。然而,我们不仅在80年代创造了让世界震惊的农业奇迹,而且一直保持全世界最高的农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率。
无论是历史对于布朗前辈的预言所作出的回答,还是现实中人们的行为逻辑,都表明了农业发展的资源压力固然存在,但“增长的极限”却是一个神话。尽管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有形资源是有限的,也会出现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但资源的概念却是一直变化着的。例如,古典经济学家最看重的是土地,后来的增长理论更偏爱物质资本,而新增长经济学却强调人力资本。实践表明,对人本身投资的回报是永远不会递减的。人的能力的增强,可以突破任何有形资源的限制。
不容讳言,中国确实是一个人均耕地比较缺乏的国家,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农业比较优势也趋于下降。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食品需求,中国面临严峻的挑战。但压力越大,相对价格的刺激越强,人们越会作出积极的反应。在当今的中国的农业经济中,作为增长基本推动力的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的潜力,不仅没有枯竭,而且相当大。在农业中市场机制逐渐完善的条件下,有效的激励将会诱致出更多的制度与技术创新,已有技术的转化率也会提高。特别是,随着中国农民素质的提高,在有效的激励机制下,农民可以点石成金,从而打破布朗的神话。
收稿时间:1996—04
Population Growth and Food Supply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Two years ago,Mr.Lester R.Brown published an articlepointing to the severe food shortage in China that mightcause a global famine around 2030 as growing population ofChina would eat up the world barn by the early 21st century.His words has lead to worldwide concerns and discussions onfood problem in China.And this issue of "Population anddevelopment Forum"is thus devoted to the questions such aswhether Brown's words will come true and what is actually the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food problem in China.
While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both populationcontro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China at present has 65 millionpeople who are in absolute poverty ( per capita incomelower than 530 yuan),further more,population growth willresult in increase in food consumption,the problem of feeding ha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he fact that the tens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food has become ever stronger and food price is in ongoing rising has appeared in recent years to be a heated topic in China.Concerns and even alarms are frequently expressed in China's leading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by scholars as well as political leaders.Policy makers at the top level have explicitly conveyed that food problem in China is a top political problem for this is critical to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quality of life,and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in China.
Among the contributors,especially invited are Dr. HuAngang,who is the first Chinese scholar to respond toBrown'sview and whose article appeared in Singapore in 1994is reprinted here,and Dr.Cai Fang,who met Brown in Beijinglast year and discussed"Who will feed China in 21st century?"
注释:
〔1〕指人口增长率超过食物供给增长率的那一点。
〔2〕波利安娜是美国作家波特小说中的人物, 代指遇事过分乐观的人,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的悲观女神,传说为特洛依国王之女,能预知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