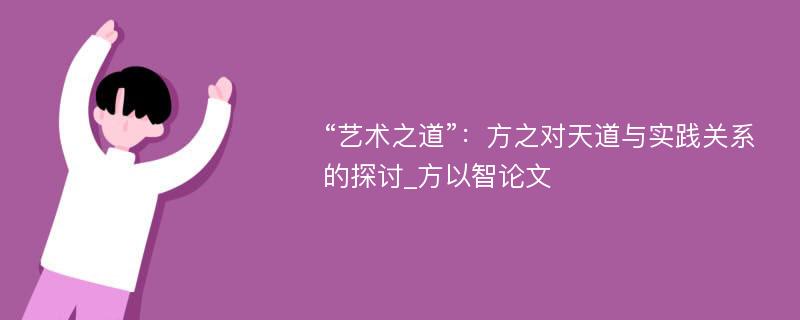
“道寓于艺”:方以智论天道与实学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学论文,天道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14)05-0045-08 “道寓于艺”是明末清初思想家方以智在中西文化激烈冲撞和宋明理学日渐式微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全新道器观,其中“艺”既泛指各种职业技艺,又特指当时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质测”之学。这种道器观将“实学”与对“天道”的虔诚,绾合为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在此统一体中,不仅职业技艺获得了理性的、具有目的取向的性质,而且中国传统儒家的“天道”观念亦挺立不坠。方以智提出“道寓于艺”,不单是出于博学治生以及会通中西文化的现实需求,亦体现了他对“於穆不已”之天道观念在明末清初衰微的焦虑。 道与器对举,首见于《易传·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按照《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和“形乃谓之器”的说法,“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乃圆融一体、显微无间。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孟子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这是先秦儒家道器(或曰道气)关系的原初表述。其中“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和“行与事”,皆为形下之器,“天”无形迹,然其“行焉”、“生焉”可示、可证。 降至北宋,理学家进一步阐扬孔孟所建道器关系之义理弘规,如伊川曰:“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①即是说,阴阳是形下之气,不是道;阴阳变化的背后根据,才是形上之道;没有离开阴阳的空悬之道,阴阳变化即是道之显。朱子亦曰:“性犹太极也,心犹阴阳也。太极只在阴阳之中,非能离阴阳也。”②朱子以为“心”如阴阳,这与阳明学不同,但他视性或太极等为形而上者,并认为道气不离,却是多数理学家的共同观点。另一方面,为了建立道德行为的价值之源,理学家们又不得不凸显“道”的至尊地位,刘蕺山评周濂溪《太极图说》曰:“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层以立至尊之位,故谓之太极;而实本无太极之可言,所谓‘无极而太极’也。”③也就是说,尽管“太极”与物无隔,但是必须立起来讲“太极”是化生万物之体,这样才能凸显其道德价值上的至尊地位(至善)。否则,如果视“太极”为一物,何足以言化生万物,“与道同体”又何以成为道德修养之目标? 如果将知识才力植于儒家道器关系中进行考量,那么,专业人才或职业技艺则为器。按照道器不二、理寓于气的原则,名物度数等经验知识理当受到醇儒的重视,求富的实践技能以及治国理政之才智乃是成圣所必须要求者。可实情并非如此,理学家们出于建体立极之需,他们视性命为精、形迹为粗,甚至黜气抑象,致使原有的道器、理气圆融关系,成了你死我活之争胜,如张载曰:“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④天理、人欲亦不例外,如朱子曰:“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⑤不仅如此,天下之“恶”亦尽归于后天之气。如此,其后果必然是贬智崇德、安贫乐道,如张载说:“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谓因身发智,贪天功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⑥此语强调“以性成身”之天道神功,却否定“因身发智”、“以身著性”之积极人为与担荷,此岂孔子所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理学家以为让天理做主,保住仁心而勿失,其意未尝不是。然不肯以此心通周万物、措之于天下之民,往往束身寡过,难语富有日新之大业。贬抑“因身发智”,妄废知识与人欲,何以保证父母饥有食、寒有衣、病有治?《易·系辞上》曰:“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先圣立体建极,旨在“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为天下利”,宋明诸儒却勤于涵养心性、立大本,外王理想反倒隐伏不彰。 方以智在《通雅》中说:“今谓宋儒与晋清谈同弊过矣。”⑦尽管此清谈非彼清谈,但忽视经验知识之弊,却是相同的。在他看来,理学家偏于求道,其表面精微,实为空谈无用之学,他说:“儒之弊也,迂而拘,华而荏……专主空悟,禁绝学问。”⑧此处“迂而拘”即指宋明儒者以拘紧的修养工夫,将天道与心性当作一空悬的物事来持守,其结果是疏于治物。这种“主空悟”、“绝学问”的迂阔之论,类于“神钱挂树,相绐取食”⑨。尽管宋儒学术有其不得已的时代使命⑩,但是,单就学术自身问题而言,确有方以智所指责的偏高遗物之失。 方以智并非事功主义者,他倡导“欲挽虚窃,必重实学”(11),以此对治理学家不切实用之弊,却没有因此妄废传统的道德形上学。 首先,他以《周易》为本,继承与发展其中关于道器(气)关系的论述,凸显原儒道器双显的思想精髓。他说:“阴阳即形下矣,而谓之道,岂非上藏于下而无上无下者乎?”(12)意即阴阳是形下之气,之所以“谓之道”,是在因为“上藏于下而无上无下”,道气原无上下分隔。当代新儒家刘述先先生将这种思维方式理解为一种“内在超越”,他说:“道既是形而上,非一物可见,故超越;但道又必须通过器表现出来,故内在,这样便是一种‘内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的型态。”(13)相对其他儒者,方以智特别强调道的这种“内在超越”性,既不能认气为道,又不可将道与气截成两片,此须借“上藏于下”来领悟二者的关系。他说:“太极非阴阳,而阴阳即太极。”(14)太极(道)是形而上者,其本身不是阴阳之气;阴阳亦不是太极,但离了阴阳却非道。其中“阴阳即太极”之“即”是圆融之即,非判断之即,这是就形下指形上者。时行物生,道无时不在眼前,《易·系辞下》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认得出,活泼泼地,自家原是自足之物;认不出,囚于桎梏,终无舒眉展目之日。在方以智的著作中,天道、命、性、心,同为一体,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如他说:“自古及今,无时不存,无处不有,即天也,即性也,即命也,即心也。”(15)同时,心或性即是仁,有创生之能,如他说:“仁,人心也,犹核中之仁,中央谓之心,未发之大荄也。”(16)此仁心“於穆不已”,上极乎天,他说:“心即是天,天休歇耶?自强不息,於穆不已。”(17)上述诸论主要本“一阴一阳之谓道”和“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易·系辞上》)等语而来,且能契合《论语》、《孟子》。此“道”即是《论语》的仁,又是《孟子》的心与性。诚如吴根友教授所说:“方以智所说‘三教归儒’之‘儒’,主要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包括孟子等人,并非秦汉后的儒者及其思想。而原始儒家则是方以智心目中理想型的儒家。”(18) 方以智常用“全树全仁”生动形象地诠释道气相即的原理,他说: 夫核仁入土而上芽生枝,下芽生根,其仁不可得矣。一树之根株花叶皆全仁也。……既知全树全仁矣,不必避树而求仁也,明甚。既知全树全仁矣,培根也,护干也,除虫也,收实也,条理灌输,日用不离也,明甚。(19) 其中“树”喻指后天可见的经验现象(气),它是仁之用,是末;“仁”则喻指超越的形上之道,它是体,是本。“全树全仁”形象地说明了既没有离树之“仁”,也没有无仁之“树”,仁(道)树(气)之间相即相融,离则双亡。“全树全仁”意即道不偏滞、活泼泼的周流万物。于人言之,乃是天命存于身,渊源无穷。“不必避树而求仁”意即道就在经验现象之中,求道不能贬黜形下之气。诸如培根、护干、除虫、收实等与知识才力相关的经验性劳作,除了求富,还有求道(仁)之目的。这种“全树全仁”的道器关系,可概括为:“一神于二,即器是道。”(20)此处“一”指道体,谓其绝对性与无对性;“二”指现象,谓其相对性与多样性;其中“神”则指道体的超越性与主宰性。如果仅强调“一神于二”,则偏于言超越之体,单显内圣,“一”则成为“影事”;如果仅重“即器是道”,则“道”的超越性有所减杀,易失为逐物之学,驰于外而昧其原。总之,在“全树全仁”的连续有机体中,体与用、价值与事实获得了深刻的统一。这种统一性最初源于“弥纶天地之道”的原始儒家对自我与自然相互关联的总体性意识及天人合一的情感体验。 其次,在阐发道器圆融关系的基础上,方以智结合发展“实学”的现实需求,提出“道寓于艺”的新型道器观。这是方以智祖述孔孟、宪章原典的历史意图。他说: 知道寓于艺者,艺外之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真智、内智,必用外智;性命、声音,人所本有;可自知也。寓(宇)内之方言称谓、动植物性、律历、古今之得失,必待学而后知……据实论之,赤子之饭与行必学而后知,谓赤子可以笔、可以书则然,责赤子不学持笔而能作书乎?欲离外以言内,则学道人当先从不许学饭始!而好玄溺深者语必讳学,即语学亦语偏上之学,直是畏难实学而踞好高之竿以自掩耳!(21) “道寓于艺”是以“全树全仁”所阐明的道器(气)关系为理论基础的,从根本上说,乃是推“一阴一阳之谓道”之义理而行之。此“艺”包括“宇内之方言称谓、动植物性、律历、古今之得失”等博识外学,它直接关乎百姓的吃饭穿衣与政治生活。这样一来,传统的“器”范畴就具体地落实为包括种种职业技艺在内的外王之学,道器关系就合乎逻辑地转化为更加明确、更具有时代特色的道艺之关系。“道寓于艺”须结合“艺外之无道”与“道外之无艺”二个方面来理解。“艺外之无道”意谓工夫即是本体,道德修养不能离开见闻之知、才艺之能,王阳明所言“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22)即是,此与在恍惚忘我的冥思、静坐中体验“天人合一”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艺外之无道”并不是说一技一艺即可成圣,而是说成圣离不开实践技艺。技艺(事实)与道德(价值)的内在关联,可以解除谋利之事无关德性的内心焦虑与不安。方以智说:“行于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23)在此语中,技能与道义、知识与德性,相互关联,融成一片。如此,不仅职业劳动具有了理性的、具有目的取向的性质,而且技艺的工具性、劳动的物性,亦因天道流行其中而具有绝对的意义。颜元亦曰:“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矣。”(24)在颜元看来,“艺”不仅是治生的工具,而且是“德成”的途径,此与“艺外之无道”所涵义蕴有相似之处。如果说“艺外之无道”是即用见体的话,那么“道外之无艺”就是承体起用。道者,生生之源,亦谓仁。功名事业皆是仁心之不容己地发用流行,利民厚生之事皆自仁心上来,否则,别有技艺,别有事功,则是与道不相干,陷入物欲,有用而无体。“艺外之无道”与“道外之无艺”要相互发明,才能理会“道寓于艺”所蕴含的有体有用、成己成物之意境。 在上文中,方以智因理学家“畏难实学”而斥之为“偏上之学”,可见,方以智的“实学”是相对于形上之道而言的,它泛指一切经世济民的博物之学、经验之知,因此,他并不严格区分“艺”与“实学”。如果从内外关系的角度来看,“艺”与“道”则分属外与内,“艺”是外物之学,属于见闻之知。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之“学”,即是指关于经验知识的学问,方以智所言“赤子之饭与行必学而后知”之“学”亦是这种外学。“道”是超越的“於穆不已”者,非感性认知的对象,知“道”属于穷神知化的德性之知。知“艺”需要“外智”,知“道”却需要“真智、内智”。方以智以为“真智、内智,必用外智”,是以其关联“道寓于艺”而言的。 根据“即器求道”之原则,舍形下之器、废知识才艺,道亦无从显立,方以智仍以“全树全仁”来说明博学多识之于道的必要性,他说: 道德、文章、事业,犹根必干、干必枝、枝必叶而花。言扫除者,无门吹橐之塘煨火也。若见花而恶之,见枝而削之,见干而斫之,其根几乎不死者!核烂而仁出,甲坼生根,而根下之仁已烂矣。世知枝为末而根为本耳,抑知枝叶之皆仁乎?则皆本乎一树之神,含于根而发于花。(25) 道德是立身之本,它与文章、事业之间,就如同仁与干、枝、花的关系,它们共同联结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根必干”是说道不自道,必起繁兴大用。有“根”而无枝叶,必属无用之根;有体而无用,必是顽空之体。“枝叶皆仁”是谓道体遍在、觌面相承。“言扫除者”高谈心性,殊不知心性非离身、家、国、天下与万物而独存。如果“见花而恶之,见枝而削之,见干而斫之”,则根亦死矣、仁亦亡矣!所以,仅就实学乃见道之必要条件而言,类于枯禅之静坐,因其远离职业技能这一点,就应该摒弃。博闻之学并非安于耳目形器而已,其中含有为“仁”而劳动的终极目的,“本乎一树之神”即是。这种具有目的取向的职业劳动,永远不仅仅是一系列的专门技艺。 以身言之,上文“根必干”即是张载所支持的“以性成身”,“枝叶皆仁”就是张载所反驳的“以身著性”。《孟子·尽心上》言“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即是这种“以身著性”。张载只强调“以性成身”,虽然天道等超越观念的意识加强了,却忽视了见闻之知的必要性。张载说:“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无不在也。”(26)他重视“天体物”与“仁体事”,却轻看了“物著天”、“事显仁”这一原儒传统。所以,他说:“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尔!”(27)既然视经验现象为“糟粕”,那么,他反对“因身发智”,就顺理成章了。方以智根据道气圆融关系,认为仁心与躯体皆不可或缺,他说:“爱一恶赜,胶柱已甚。人当独有一心,四官四支(肢)、三百六十骨节太多,何不废之?”(28)内在的仁心固然重要,躯体亦不可废,天理与人欲,相即不离。不能在合理的人欲之外寻求根源,不能离事业以皈仰天道。 如果细究方以智与宋明理学家在学脉上的亲疏关系,其“全树全仁”之喻与北宋程明道“观鸡雏,此可观仁”(29)之意境,最为切近,他们皆在指点生生之道与庶物不隔的道理。不执一家之说的方以智,在这个问题上,明确地赞成程明道的观点,他说:“信所谓识本心者,即程伯子之所谓识仁。……惟在识仁,万念皆融。”(30)可见,方以智十分熟悉且极力赞赏程明道的“识仁”之说。凡持体用不二者,皆教人随事精察力行,而不是悬空参悟,比如,程明道曰:“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31)其门人谢上蔡更明确地提出“须就事上做工夫”(32)的修养论。可惜程明道与谢上蔡没有就此问题充分展开。王阳明于道器、理欲关系看得明白,他说:“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33)也就是说,致良知的工夫就用在“声色货利上”,只要保任良知无蔽,声色货利之交即是天理,此意可简单地表述为“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34)。王阳明气魄大,却总担心人们“专求见闻之末”而失去了学问的“大头脑”,所以,他不得不强调说:“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35)他将知识与人欲、才力与天理对峙起来,结果又回到方以智所反驳的“偏上之学”。 如果将“道寓于艺”置于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语境下进行考量,它就合理地扩大为“质测即藏通几”。方以智早年好物理,又深谙泰西质测之学,他说:“太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36)又曰:“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37)他不单赞叹近代西方“质测”之精良,同时也为儒家文化的成德之教、“通几”之学之详备而感到自豪。学术界对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尤其是对他早年的《物理小识》和《通雅》等著作所取得的科学成就评价颇高。然而,方以智主要是作为一位思想家而不是科学家名垂于青史。如果以科学家视之,他远不如同时代的徐光启等人。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突出贡献,并不是“质测”之学本身,也不是其博采众长的宽容精神,而是他敏锐地觉察到儒家文化在近代西方文化激烈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脆弱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积极地、创造性地转化,从而使儒家义理能够有机地契接泰西“质测”之学的治学方法。 方以智不是依照实用的原则直接将“质测”之学机械地接受过来,而是积极地从文化之根上寻求能够合理嫁接西学之处。依据“上藏于下而无上无下”的道器关系,他认为西方“质测”之学与中国儒家“通几”之学是互融的,他说:“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38)在儒家天人合一、生命一体化的语境中,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通为一体,既不能单“显其宥密之神”,又不可“遗物”。《易·系辞上》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在先儒立说之初,有关人类进步的历史意识就已经出现,方以智将“质测”新学视“器”的做法,就是道器关系的“推而行之”,就是“举而错之天下之民”。“道寓于艺”或“质测即藏通几”既继承与维护了儒家自先秦以来的文化信念,又合理地将“质测”纳入儒家道德形上学体系。这种做法是内圣之学的“自救”,是方以智思想体系中彻头彻尾的近代性因素。 在方以智的著作中,“通几”就是“道”,如他说:“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39)其中,“几”可以“物物”、亦可“神神”,即寂即感,故亦可曰“深几”。显然,“几”不属于气,它是超越的道体,是绝对的“一”,如他又说:“圣门之几本一,而本不执一,其圆如珠。”(40)这两个“本”应训为“本来”之意,不是说“几”要以“一”为本,亦不是说本体不执一。圣门之“几”就是“一”,但又不执着于“一”。一方面,“几”具有超越义,它是无对之“一”;另一方面,“几”流行于万物之中,如仁之在树,此状难以表述,故曰“其圆如珠”。 方以智言“通”与“几”,皆本于《易传》,《系辞上》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方以智合“通”与“几”而用,尽管内涵稍有变化,但并不影响他以“通几”来代表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形上之道。另一方面,由于“质测”属于逐物之学,方以智视之为形而下者,也是切合原儒义理的。 道气(器)关系一直是儒家关注的重要话题,对两者内涵及其关系的处理,直接关系到内圣与外王的展开。在对原儒思想的历史叙述中,“道”始终是关注的重心,至于“气”或“器”究竟指向什么,儒者并不措意。虽然理学家不缺外王理想,但却是“政治本位”的,即他们的“经世观念所代表的入世精神以政治为其主要表现方式”(41),较少关注济民救世的实践才艺。方以智适时变通,将“器”的内容落实为具体的“艺”和“质测”之学,使“即器是道”的原儒义理能够主动地、必然地容纳新兴实学和近代西方文化的积极因子。这样,既可以借西方“质测”之学,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又不至于牺牲儒家道德学说。这种创造性地诠释,不仅能够将原儒思想与当下问题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联,维护了古典思想的历史有效性,而且使古典思想得以“增值”。 再者,由于“质测”与“通几”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关联,所以,在西学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新元素的同时,中国文化亦可补救当前西方文化面临道德沦陷之危机。西人“拙于言通几”,宗教神学是他们寻求终极意义唯一精神依靠。当这种精神依靠在工具理性日益盛行中逐渐隐退,科学研究出于纯粹实用之目的,谁还会相信科学技术能给人们有关世界的意义呢?如果不能赋予“质测”之学以终极意义,当人们把科学技术仅仅建立在物欲观念上,而不同时又建立在对普遍价值的宗教献身的理念之上,人类将置身于一个破碎的物质世界。中国儒家的内圣之学正好可以弥补西方内在道德修养之不足,正如罗素所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42) 方以智基于原儒道器关系所提出的“道寓于艺”的意义如下: 第一,打破了“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的观念,使经验知识在儒家道德理想中获得了积极性的存在,并享有“崇高性”(道)的地位。孔子论仁,要么关联着实际生活中具体个人的社会角色与功能,要么是针对具体事情的社会效果,如对于“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一事,孔子赞许曰:“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然而,自北宋张载提出“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之说,道德修养与生活可欲之事业开始发生分离。按照“道寓于艺”之原理,实学不再是王阳明所说的“只是装缀”,各种谋生的职业技艺蕴涵着超越单纯技术层面的道德意义。在心理效果上,“道寓于艺”将经世事业从传统伦理屏障中解放出来,不止使属于见闻之知的技艺合理化,而且可以消除追求财富无关德性的心理顾虑。诸如吴与弼整日“正襟端坐”,不务经济日用,以致“往邻仓借谷,因思旧债未还,新债又重”(43),最后不得不以“须素位而行,不必计较”的心态推塞债务的行为,只能是背离圣境越来越远。 第二,对当前社会职业伦理建设的启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投入到世界现代化的激流之中,西方的科学技术日益深入人心,人们认为通过理智的计算可以掌控一切,世界不再有什么神秘的力量。然而,在我们狂热地崇拜西方科技文明的同时,却遗落了西方文化的另一传统,即对上帝的信仰,然而正是科学理性与信仰的统一,才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独特个性。他们把勤奋创业理解为上帝的召唤,把学术工作等职业理解为基督教的天职。缺少西方宗教关怀的人文背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以及更开明的政治生活。这种片面强调工具理性的直接后果,必然淡化人们对终极意义的追求,敬业精神也就无从谈起。如今,人们离开“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的传统语境越来越远,有关生命与世界的意义便无从谈起。当原初的道德信念被遗忘时,一方面,对于诸如圣人、君子的称颂虽然仍弥漫于社会之中,却没有为道德自律原则提供任何类似于传统的解释与合理性证明。另一方面,传统的包括来自不同新领域的各种道德规范变成了独断的禁令。我们冷静地反思先贤关于天道与事业之间关系的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德育启示。在现实生活中,“道外无艺”是一种职业态度,技艺本身不是目的,通过献身一种职业劳动从而获得通向圣人之路,才是终极目的。“道寓于艺”之“艺”不再是无关道德的逐物之学,其中蕴涵与绝对善相统一的精神信念。 第三,会通中西文化的启示意义。如何嫁接泰西的“质测”之学,而不摧毁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如何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提高民族自觉?如何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加速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良性的文化支持?这些问题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切、最用心思索的难题。科学欲发达,文化为其根;天下之物,未有根萎而枝叶茂盛者。主张西化者,多称西方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然于其根本精神为何,却未加留意。主张以中学为本者,并不深究先圣义理,视六经如古代之器物。如此会通中西,岂不两失。“质测即藏通几”的提出,是以先圣义理为根基的。尽管方以智认识到“太西质测颇精”,但是,他不是用“添加法”来扩大中国儒家文化的外王理想,而是通过对儒家固有的道器关系的再诠释,将“质测”之学合理地植入儒家道德形上学体系之内,使之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与历史形成过程的存在。我们发掘“道寓于艺”的哲学意蕴,就是要从传统儒学内部找到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自我创造的精神动力与伦理资源,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提升和创造转化(44)。 ①《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2页。 ②⑤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7,224页。 ③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页。 ④⑥《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3,25页。 ⑦方以智:《通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页。 ⑧⑨方以智著,庞朴注:《东西均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6,175页。 ⑩牟宗三认为宋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二期形态”,其学术使命在于彰显道德主体性,“故宋学之彰显此道乃为纯反省的:由主静,主敬,向里收敛,反显此普遍理性之绝对主体性”。并认为宋学涤除“属于气质”者,“乃为必然应有者,且亦是极大之心力”。见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公司,2010年版,第12页。 (11)(12)(14)(15)(16)方以智著,庞朴注:《东西均注释》,第182,147,110,47,164页。 (13)刘述先:《儒家哲学研究:问题、方法及未来开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 (17)方以智著,庞朴注:《一贯问答注释》上,载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儒林》第1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 (18)吴根友:《试论〈东西均〉一书的“三教归儒”思想》,载《哲学分析》2011年第1期。 (19)方以智:《通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7册,第50页。 (20)方以智:《通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7册,第30页。 (21)方以智著,庞朴注:《东西均注释》,第178-179,183页。 (22)《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 (23)方以智著,张永义、邢益海校:《药地炮庄》,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页。 (24)《颜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4页。 (25)(28)方以智著,庞朴注:《东西均注释》,第183,179页。 (26)(27)《张载集》,第13,9页。 (29)(31)《二程集》,第59,139页。 (30)方以智著,张永义、邢益海校:《药地炮庄》,第63页。 (32)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23页。 (33)(34)《王阳明全集》,第122,791页。 (35)《王阳明全集》,第28页。 (36)方以智:《通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7册,第30页。 (37)(38)(39)方以智:《物理小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42页。 (40)方以智著,庞朴注:《一贯问答注释》上,载《儒林》第1辑,第263页。 (41)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 (42)[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43)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页。 (44)高旭东:《论儒家伦理的宗教功能及其文化作用》,载《理论学刊》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