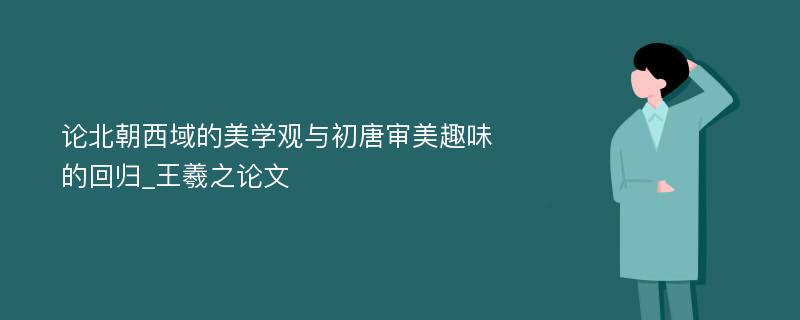
论北朝西部审美观与初唐审美兴趣的复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唐论文,北朝论文,审美观论文,兴趣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5)01-0076-09
在中国美学史上,论及江南六朝美学对唐代尤其是初唐美学之影响者,可谓多矣。然而,对于真正作为初唐美学思想渊源、影响初唐美学观念发展变化的北朝西部审美观念及其与初唐审美兴趣重心复归的内在联系,却鲜有文章论及。本文试对这一论题加以探讨,以就正于海内方家。
一
与浑朴雄劲、带有戈壁风沙气息的北朝乐府民歌在文学上的开拓相对应的,是北朝石窟雕塑在艺术上的创造。它既是北朝西部审美观的起源和出发点,又是体现北朝时代西部理想人物雄豪勇健的气骨风格的美学风标。
先以最为著名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那些大型石窟雕刻作品为例:“云冈石窟制作规模的巨大,首先见于在石壁上雕出那些高达14~18米的硕大的佛像。……这些佛像体积庞大,而且能够给人以生命力异常充沛的感觉,所以是雄伟而健康的形象。宾阳洞洞口作尖拱形。洞口两侧石壁上雕出怒目蹙眉象征其孔武有力的力士,右手五指张开置于胸前,极有神气。”(注:王逊:《中国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146、150页。)又如驰名中外的敦煌莫高窟雕塑:“北魏塑像的特征是佛菩萨的体格都较高大。面相则额部宽广,鼻梁高隆通于额际,眉眼细长,颐部突出,唇很厚,发髻作波状或螺旋形。……北魏的造像躯体挺直,衣褶劲利如锥刀,面相清癯瘦削,给人的印象是睿智、威严、坚定。它们虽然嘴角带着微笑,仍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种森严的力量。”(注:潘絜兹:《敦煌莫高窟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57页。)在佛道与帝力相成相长、互为巩固的北朝,这些充满威严、豪迈之气的石窟大型雕刻作品,乃是时代审美意识的必然反映。从这些虽出于民间无名工匠之手,却体现了统治阶级美学观念的雕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时代、一个集团的美学风姿。所谓“陛下即是当今如来”(注:《魏书·释老志》:“治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一语破的,道出了个中奥秘:北魏雕塑之美学模式,与其说是严格遵守印度原来的造像仪型,毋宁说是更多地带有西部游牧部落勇武剽悍的民族风习。如云冈第20窟大佛,即昙曜最早营造的大佛像之一:“整个形象洋溢着游牧民族特有的健康、豪爽、剽悍和坚毅等气息。那方圆结实的脸庞、饱满高挺的胸脯、丰厚壮实的双臂与肩膀所蕴蓄的男性的力量与魅力,是印度各种流派的佛像不能望其项背的。”(注:洪惠镇:《北魏云冈石刻大佛》,收入《中国美术名作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23页。)所有这些,无一不既展示着北朝西部审美观念与江南六朝审美观念的不同,同时也表现出北朝西部审美观念自身具备的独特美学魅力。
艺术作品无疑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唐人李延寿撰《北史》上记载的那些戎马一生的帝、王,就是北魏审美标准最早的原型与模特儿:“神元(帝)有雄杰之度。……桓帝英杰魁岸,马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牛角容一石。”“(穆)帝天资英峙,勇略过人。”“(平文)帝资质雄壮,甚有威略。”西方美学家格罗塞在其名著《艺术的起源》中指出:“原始部落通常十分引以自豪的,就是自己种族的身体的一切特点。”(注:转引自曹葆华译《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3页。)与北朝乐府民歌将勇武的健儿确立为美学风范,讴歌赞美所向披靡的剽悍勇将,将其引以为时代的骄傲和自豪的情形不谋而合,北朝石窟雕塑最早的审美客体,实即审美主体自身。随着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重合,萌生了北朝美学模式的雏形。“雄杰”“魁岸”“英峙”“雄壮”等阳刚之美,不仅在审美主体即北朝统治者自我的审美观照上造成了气可凌云的壮阔景象;更重要的是,在更大范围的审美主体面前,它作为一种供人瞻仰膜拜的象征性的偶像,如同一座雄伟的大山,起到了震慑敌视者和安抚拥戴者的双重作用。“既威严又亲切”,让芸芸众生在精神上有所寄托,给广大依附者心理上带来一种安全感,产生很想在上面靠一靠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云冈、龙门、敦煌等大型石窟雕塑中的北魏大佛,实即当时时代与社会美学意念中理想统治者的化身:“昭成皇帝……生而奇伟,……身长八尺,隆准龙颜,立发委地,卧则乳垂至席。烈帝临崩,顾命迎帝,曰:‘立此人则社稷乃安。’”(注:帝时年十九)《北史》上关于统治者的记载,就是有力的证明。
壮美的艺术形式,意味着勇武的美学内涵。这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北史》上更多的,是这类记载:“秦王(元)翰,少有高气,年十五,便请征伐,昭成(皇帝)壮之,使领骑二千。长统兵,号令严信,多所克捷。”“(常山王子之)长子可悉陵,年十七,从太武(帝)猎,逐一猛兽,陵遂空手搏之以献。帝曰:‘汝才力绝人,当为国立功立事……’即拜内行阿干。又从平凉州,沮渠茂虔令一骁将与陵相击。两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坠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剑,以刀子戾其颈,使身首异处。帝壮之,即日拜都幢将,封暨阳子……”空手搏兽,以刀戾敌,这一朴野粗鲁乃至带有血腥气味的行为方式,在最高统治者推波助澜的鼓励与提倡下,风靡北朝,成为时代与社会的美学风尚。尽管它是那样的稚拙、原始、不登大雅之堂,以致后代史学家多持否定态度,但它却蕴蓄着北方新兴民族的充沛的生命力,溢射出具有人类原始蒙昧阶段野性的粗犷的美。这也正是唐代美学模式的重要特征。联想到唐代野史笔记对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父子的记载:“高祖少神勇,隋末,尝以十二人破草贼号无端儿数万。又龙门战,尽一房箭,中八十人。太宗虬须,尝戏张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长带箭一扶,射洞门阖。”(注: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我们能说这不是一脉相传的美学风尚,而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
二
如果说唐人的审美观起源于北朝的话,那么建国后其审美兴趣的重心就开始逐渐由北向南推移。这是毋庸讳言的。唐之前的隋炀帝,就是一个关陇军事贵族仰慕江南文化的急激冒进型的先行者。唐初统治者虽然接受了他骄奢淫逸以至亡国的教训,却仍然抵御不了(也许根本就没想到要抵御)江南先进的文明和柔弱绮靡的风气的诱惑,全盘接受了南朝的文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江南六朝政治、军事上惨败之后,却以文化征服了唐初士人。关陇健儿在政治、军事上是征服者,在文化上却是被征服者。但即使是在这双向错综交织扭结的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仍然表现出一代占有者的美学情趣。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在唐初的流传,即开此风潮之滥觞。唐初书家,首推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但无论是劲险刻厉、自成面目的“欧体”,还是外柔内刚、圆融遒丽的“薛体”,抑或丰艳流畅、变化多姿的“褚体”“薛体”,无一不从二王的书法脱胎而来。唐初四大书家,莫不是二王书法流派的传人,或传人的传人:“(欧阳)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注:《旧唐书·儒学传上》。)“(虞世南)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注:《旧唐书·虞世南传》。)“(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太宗尝谓侍中魏征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征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注:《旧唐书·褚遂良传》。)在历史上,文明程度较低的部族(或集团、群体)向文明程度较高的部族(或集团、群体)。学习,接受一种较高的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即使这文明程度较低的一方处于征服者的地位,在文化上也仍然会被文明程度较高的被征服一方所征服。北朝至唐之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大融合,即属于此。从控制论的角度来讲,人必然趋向于一种较高级的本质,以较高的文明表现为美。这是人类日日上征、时时向前的心理上的主观动力。这种主观心理的客观基础,便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的必然要求。唐初四家的书法风格及其代表的当时书坛的审美趣味,就在潜意识中流露出了这种唯美是从的审美心理趋向。这一代征服者、占有者、胜利者从边关塞外走来,戈壁大漠的沙尘和烽火狼烟的气息尚未洗去,时代与社会就已经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美的境界。在这种“同夫拨云睹日,芙蓉出水”“阴阳四时,寒暑调畅”“清风出袖,明月入怀”(注:李嗣真:《书后品》。)的美的意境面前,他们倾倒了。“自书契之兴,篆隶滋起,百家千体,纷杂不同。至于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惟在右军王逸少一人而已。”(注:欧阳询:《用笔论》。)“逸少、子敬剖析前古,无所不工。”(注:虞世南:《书旨述》。)“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靡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注:李世民:《王羲之传论》。)这些仰之弥高、测之弥深、大力推崇、无以复加的赞美,酣畅淋漓地宣泄了昔日之金戈铁马上的健儿彼时彼地的审美感受,证明唐人审美兴趣的重心,已由质朴古拙的魏碑,转移到六朝妍美流便的新体上去。唐太宗派萧翼到释辩才处骗取《兰亭序》的故事,是这一审美崇尚的极端。这位唐朝第二代英主,对右军书法的珍品由购求、征收、掠夺发展到拐骗,临终还要下令将其随棺入墓,可见其爱好到了何种程度。在最高统治者有形与无形的倡导下,摹仿王书,自然而然地成为从宫廷到社会的美学风气。
不过,这并不是一股盲目崇拜南风的数典忘祖的美学思潮,而有着关陇军事集团自身内在的审美价值尺度。“太宗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朕少时为公子,频遭阵敌,义旗之始,乃平寇乱。执金鼓必有指挥,观其阵即知强弱。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而返击之,无不大溃。多用此制胜,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注:李世民:《论书》。)话虽不多,却精辟地道出了书法与兵法的相通之处。这位杰出的军事贵族领袖以其娴熟的战阵之法来衡量书法,江南六朝浮薄软弱、柔媚无力的书法风格自然与其格格不入:“(王)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萧)子云近世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耶?”(注:李世民:《王羲之传论》。)这些评论,都说明了唐初书家与六朝书家在审美趣味、审美感受、审美理想等美学观念形态上的不同。“无丈夫气”“无一毫之筋”“无半分之骨”的反面,就是要有“丈夫气”,要刚健有力。相形之下,王羲之的部分书法墨帖如《丧乱帖》、《频有哀祸帖》,风格雄强,直抒胸臆,奔放不羁,顿挫有力,时露锋芒,“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注: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关陇军事集团的审美需要。唐太宗李世民的《论书》,或许即受了王羲之《书论》的启发:“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强弱不等,则蹉跌不入。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注:王羲之:《书论》。)两相比较,其中的渊源脉络不是一目了然了么?关陇军事贵族从他们特定的角度继承了王羲之的宝贵遗产,以他们听得懂的语言理解了王羲之的经验之谈。可以这么说,唐初书坛学王风潮之所以如此兴盛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字势雄强多变化,英俊豪迈、饶有气势的二王书法,与勇武刚健的唐人的审美观不谋而合。
唐初书坛仿二王书法的风气,是一次唯美主义的书法美学浪潮。“夫用笔之体会,须钩粘才把,缓绁徐收,梯不虚发,斫必有由。徘徊俯仰,容与风流。刚则铁画,媚若银钩,……若枯松之卧高岭,类巨石之偃鸿沟,同鸾凤之鼓舞,等鸳鹭之沉浮。仿佛兮若神仙来往,宛转兮似兽伏龙游。其墨或洒或淡,或浸或燥,遂其形势,随其变巧,藏锋靡露,压尾难讨,忽正忽斜,半真半草。唯截纸棱,撇捩窈绍,务在经实,无令怯少。隐隐轸轸,譬河汉之出众星,昆冈之出珍宝,既错落而灿烂,复趢连而扫撩。方圆上下而相副,绎络盘桓而围绕,观寥廓兮似察,始登岸而逾好。”(注:欧阳询:《用笔论》。)“拂掠轻重,若浮云蔽于晴天;波撇勾截,若微风摇于碧海。气如奔马,亦如朵钩,轻重出于心,而妙用应乎手。”“至于顿挫盘礴,若猛兽之搏噬;进退钩距,若秋鹰之迅击。……亦如长空游丝,容曳而来往;又如虫网络壁,劲而复虚。”“既如舞袖挥拂而萦纡,又若垂藤樛盘而缭绕。蹙旋转锋,亦如腾猿过树,逸蚪得水,轻兵追虏,烈火燎原。或体雄而不可抑,或势逸而不可止,纵于狂逸,不违笔意也。”(注:虞世南:《笔髓论》。)唐初书家的这些变怪百出的譬喻,既是准确地再现了客观世界中某些事物的健美特征,却又并非任何一种具体事物的简单反映。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里既有表象的分解与综合,也有表象的联想和转化。“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注:孙过庭:《书谱》。)受这些观念影响制约的唐初书法,既艺术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具有美学含义的特征,也寄寓了唐初书法美创造者自身的审美好尚和审美情趣。
不过,这已经不是六朝人心目中与二王书法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美学意境的本来面目了。六朝人心目中二王书法的美,亦即二王书法美学意境的基调或主旋律,是一种悦人心神、含蓄有味的美。尽管王羲之书法也有风格雄强的一面,如《丧乱》《频有哀祸》诸帖,但真正能代表其主要风格的,还是《兰亭序》表现的那种平正安稳、匀称自然、轻快舒缓、很有节奏的美学韵味。而枯松高岭、巨石鸿沟、腾猿过树、奔马朵钩、兽伏龙游、猛兽搏噬、秋鹰迅击、轻兵追虏、烈火燎原等颇富阳刚之美的艺术形象,及其给欣赏者带来的那种振奋、开阔的审美感受,与其说是二王书法美学意韵的余波,毋宁说是更多地掺杂了唐人自己的理解和再创造。欧阳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的转折,即鲜明地体现了唐初书家那强烈的审美个性。他们仰慕江南文化并为之倾倒、折服,却并没有变成六朝人的再世,在南北文化之水乳交融中没有失去自我,其审美感受、审美情趣、审美理想都还保留着北朝以来那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旺盛生命力。这是唐代美学思想潮流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对唐人来说,被美征服只是被征服,而不是被奴役、被俘虏;对对方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对自我的否定。一言以蔽之,占有,而不是被占有,乃唐初统治集团的美学主旨。
初唐音乐舞蹈及诗歌的演变情形,与此相类似。关陇军事集团成员谢偃(本姓直勒氏),写过《听歌》《观舞》二赋,对唐初宫廷乐舞极尽赞美讴歌之能事;而此时谢偃津津有味地描述的音乐与舞蹈,与其生长其中、耳濡目染的西部乐舞,显然已不是同一指向。无论那止有余态、动无遗妍的举手投足的神态,还是短不可续、长不可去的抑扬顿挫的节奏,差池燕接、飒沓凫连的场面调度的安排,延促合度、舒纵有所的舒缓疾徐的韵律,以及繁会微引、殊姿异制的格调所传达出来的江南六朝时代风格的行为方式、文化教养、气质风度与趣味特点综合而成的文化意味,皆如此。此时审美主体兴趣的中心,已不再专注于歌舞的内容,而逐渐转移到歌舞者华丽的服饰、窈窕的体态;创作和表演歌舞与其说是表现主题的需要,毋宁说是为了给观赏者更多的审美享受。江南丝竹的袅袅余音与水乡女子的娇姿柔态,契合了占有者的美学情趣和审美期待;为艺术而艺术,为欣赏而欣赏的唯美主义思潮,滋蔓于唐初的宫廷内外。“好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仪等宫廷诗人的宫廷诗“上官体”,就在这歌舞升平的宫廷氛围内萌生。
西部乐舞、中原古乐、江南丝竹三大艺术传统板块,在这里又一次碰撞。后者以其渗透力极强的文化意味和以柔克刚的艺术魅力,形成巨大的文化冲击力,冲击前者而在唐初宫廷乐舞中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而处于中间地带的为历代儒教正统乐论者倡导的中原古乐,却明显地被审美主体遗忘。儒教重视音乐舞蹈与诗歌的教育意义,如孔子不喜欢郑声,认为“郑声淫”(注:《论语·卫灵公》。),是太过,太刺激,不够朴质。而“掩余韵于雕扇,散轻尘于画梁”(注:谢偃:《听歌赋》,《全唐文》卷157。)的江南丝竹的靡靡之音,正是以其郑卫淫风式的富有强烈刺激的妩媚魅力,征服了唐初的当代英雄。与此相比较,那雍容典雅、舒缓端庄的中原雅乐正风,自然显得平淡寡味,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唐太宗有一段名言,可以说明此时唐人的审美观点: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大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注:《贞观政要·礼乐》。)
这就是声代音乐美学史上最为流行的权威观点。倘若按照儒家传统的音乐美学观念,“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音乐的哀乐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兴替,故而是万万忽视不得的。这种审美观念要求人们在继承前代音乐美学遗产时,要以传统的审美价值尺度标准严格择取,“放郑声”(注:《论语·卫灵公》。),禁淫乐,循规蹈矩,老成持重,不得越雷池一步。这对加强儒家封建正统观念在音乐美学领域定于一尊的思想统治,固然有其主导作用;但它却严重地束缚人们的思想,戕贼审美主体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而这正是主观美感的源泉),从而限制了音乐舞蹈艺术的繁荣。唐太宗李世民从唐人自我的审美感受出发,提出“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强调审美主体在审美观照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音乐的新旧变更无关政治的兴亡,甚至《玉树后庭花》《伴侣曲》等“亡国之音”亦可拿来进行审美享受,不啻音乐美学思想的一次解放。盛唐以后音乐之以哀音为美,与其先驱唐太宗这一审美观念当不无关系。这一震惊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界的崭新观念的提出,代表了唐初时代审美主体的核心——唐统治集团那勇敢得几乎达到忘我程度的趋向华美的美学风调。
三
一代美学思潮的运行与后人顺理成章的推想往往并不一致。初唐美学思潮并未如后代某些学者推论及设想的那样,沿着江南六朝的美学道路前进多远。恰恰相反,南风僭居唐人审美崇尚的中心,只是唐代美学思潮这一思想长河运行过程中极其短暂的那么一小段,很快,北风就又取代南风,重新成为时代美学大潮的中坚。
即以在文学史上久负盛名的王勃《滕王阁序》为例,同样是描写台阁,但字里行间之气魄却何其宏伟!这与六朝文人笔下那些曲院回廊、竹径幽深美学风格的亭台楼阁,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而更多地含有《木兰诗》《敕勒歌》所给人的那种开阔、壮观的美学意味。又如初唐诗人苏味道等以京都上元夜的狂欢为题材的那些诗歌,同样是描写游乐,但热闹之中却何其奢华、豪荡、快活、惬意!这显然不是六朝门阀世族那种柔靡香软、令人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的醉生梦死的趋于没落的美,而是一种溢射出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特有的美学风标的壮美。“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注:《大唐新语》卷8。)京都上元彻夜狂欢市、井街头恣意游乐的盛大场面,从社会审美心理发展大趋势的广角,透露出审美兴趣复归的唐人大胆、放纵、肆无忌惮地表现自我审美价值时的自豪与狂喜,与随之而来的在审美判断中对自我的肯定,以及这一社会审美心理学现象所意味着的一系列美学观念的复归。
初唐审美兴趣重心的复归几乎无处不在。如初唐坊邑街头盛行的表现西域泼水乞寒习俗的西部乐舞《苏摩遮》:“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摩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督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欢,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书》‘曰谋,时寒若。’何必裸形体,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注:《新唐书·宋务光传》末吕元泰疏。)吕元泰此疏,是痛心疾首之言。但它却从反面透露了《苏摩遮》风行时的盛况。时代审美兴趣重心的复归,决非一二道学之士所能阻遏得住,这种裸体跳足、挥水投泥的“泼寒胡戏”流行于两京及各地,势不可挡;非但吕元泰“书闻,不报”(注:《新唐书·宋务光传》末吕元泰。),而且唐室诸王亦有此好,唐中宗还亲御洛城南门楼观之,并令诸司长官观看,(注:《旧唐书·中宗纪》。)一时间“乘肥衣轻,竞矜胡服,阗城溢陌,深点华风”(注:《唐大诏令集》卷109《禁断腊月乞寒敕》。),西部戎风重又风靡整个时代与社会。万众瞩目的时代美学风标九重之内,风气更为开放:“上(唐中宗)数与近臣学士宴集,令各效伎艺以为乐。工部尚书张锡舞《谈容娘》,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獐》,左金吾将军杜元诵《婆罗门咒》……”“上又尝宴侍臣,使各为《回波辞》……”胡三省注:“时内宴酒酣,侍臣率起为《回波舞》,故使为《回波辞》。”(注:《资治通鉴》卷209。)北朝风行的西部音乐舞蹈流行歌曲,重新回荡于大唐宫廷内外;唐代统治者的审美选择标准,必然要影响到时代美学风气的变化。
需要说明,这并非儒教传统审美理论指责的腐化与堕落。恰恰相反,它是信心十足的唐人在实现自我美学价值时,表现出的那种冲决罗网自由发展的勃勃生气。须知,正是这种没有任何枷锁可束缚的生气,孕育了即将来临的盛唐气象。如初唐以来流行的击鞠即马球运动:“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注:《封氏闻见记》卷六。)“上(唐中宗)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注:《资治通鉴》卷209。)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注:《封氏闻见记》卷6。)我们能说,这仅仅是一般的游乐,而不含有耀武扬威、震慑番邦之政治意义在内么?我们能说,这仅仅是一般的嬉戏,而没有显示出一种踔厉风发、激荡人心的美学风采么?盛唐美学思潮的源泉,正汨汨流经于此,盛唐美学意象的根苗,正在这块肥沃的土壤上滋生。细心的读者若认真体察,将不难感到初盛唐之间那密不可分的思想源流和血缘纽带的绾合。
恩格斯讲过:“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78页。)导师的本意,是指5世纪日尔曼等蛮族的大迁徙对古罗马帝国的冲击;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北朝至唐美学思潮发生发展的历程,而且要更为恰当和透辟。日尔曼等蛮族的源源侵入,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冲断了昔日无比强大的罗马帝国对欧洲的统治,宣告了盛极一时的罗马奴隶制在历史上的终结;北朝民族的浴血鏖战,结束了南北军事豪强更相取代割据称雄的混乱,促成了大一统的隋帝国的诞生。二者一个使统一的欧洲分割成一个个分裂的公国,从光辉的古罗马时代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一个使分裂的华夏统一成南北融合幅员辽阔的强大帝国,从哀鸿遍野鸡犬不宁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进入繁荣昌盛日升月恒的隋唐。一个割断了古罗马奴隶制城邦的文明进程,却并未马上吸收高度发达的古罗马文化;一个促进了南北华夷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水乳交融,在此基础上走向新的更高一个层次的进步与文明。但是,二者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带来了野蛮部族那还残存着原始氏族公社阶段气息的野性,给在垂死的古老文明中挣扎的时代注入了生气。欧洲且不论,仅就中国北朝至唐美学思潮发展的过程而言,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股原始野性气息的外溢。如武则天登基前开凿的闻名遐迩的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那尊高17.14米的卢舍那大佛,“佛像头部圆满秀丽,既有男子汉的庄严,又略带女性的慈和,下视的眼神透出威武与英睿,微翘的唇角显得尊贵与严峻。”“它的雄伟壮丽、典雅崇高与严肃睿智,常使人不禁联想起希腊巴底农神庙的主神雅典娜像,但它比雅典娜像更稳重,更完整,更有气魄,象一座不可摇撼的山岳。”“它确实形象地体现了初唐自强奋发、激昂向上的时代精神。”“大佛曲眉丰颊的面部特征与硕壮丰满的体魄,反映了唐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审美观点与美学思想,并逐渐形成有别于历代风格,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造像样式,给人以清新、健美、雄浑、典丽等等美的享受。”(注:洪惠镇:《龙门石刻大佛》,见《中国美术名作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这不正是远古蒙昧时代的母权制复归给唐人的美学观念和审美模式带来的新鲜活力么?“卢舍那大佛面容庄严典雅,表情温和亲切,是一富于同情而又睿智明朗的理想性格。他的右手掌心向前举在胸前,五指自然的微屈,也能表现出内心的宁静而又坚定,(不是冷酷的,也不是焦躁的),他向前凝视的目光中仿佛看见了人类的命运和归宿,人类历史的前进的道路。”(注:《中国美术史》第217~218页。)这不正是被高度美化了的大唐帝国高居九重的帝王的化身么?“在这一形象中表现了唐代艺术家自己面向着充满斗争与变化的广阔的生活景象时的伟大的开阔的胸怀,艺术家对于这一形象进行了自己的解释和贯注了自己的情感……”(注:《中国美术史》第218页。)而这,与那由于注入原始野性的鲜血而生命勃兴、蒸蒸日上的时代是分不开的。
不只卢舍那本尊大佛,神王、金刚、甚而至于小鬼等形象莫不映照着那个充满生气的时代。你看,“神王的硕壮有力而威武持重,金刚则全身筋肉突起,是非常暴躁强横的神情”,“奉先寺诸像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还有神王脚下的小鬼。他承担起神王的巨大的躯体的重量,他的头、胸、臂、腹等部筋肉以夸张的表现,因而出现小鬼无所畏惧的压不倒的力量。在这一形象的创造中,虽然表现为踏在足下的,然而作为勇敢的对抗的力量得到赞扬。”(注:《中国美术史》第218页。)这里突出加以表现的,是那种原始游牧部族赖以同艰苦环境拼搏因而获得生存权利的蛮勇的力。那些少许有名,更多是无名的雕塑家们,在塑造正确的人体结构和体质的同时,以果断准确的刀法夸张肌肉的紧张与劲健,给人一种强烈的咄咄逼人的力量感。我们只要将奉先寺诸像中神王、金刚、小鬼的形象与宋代以后各地寺院中那些“天王”“金刚”的形象比较一下即可看出,它不像后者那样外强中干,色厉内荏,以表面上的突嘴努眼、摆空架子掩盖内心的空虚和乏味;而是由形象内部激发出来的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的外化。正是在这雄强有力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才体现出生机勃勃、气吞河岳的气概来,也才有后来“刷天王须,笔迹如铁”(注:段成式《京洛寺塔记》评吴道玄画。)的造型风格。以北朝传统审美观念为指向的时代审美心理的复归,表现在诗歌史上就是所谓“初唐四杰”的出现。
初唐时期的唐人正在逐渐成熟。在形形色色的美的大千世界面前,他们不再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美;而有着自信和勇气,根据自己的喜怒爱恶择美而从,并开始着手建立以自我为内在核心的一整套审美观。这个可喜的变革,又进一步为盛唐美学思潮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而所有这些,都与作为唐人思想渊源的北朝西部审美观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标签:王羲之论文; 美学论文; 王羲之书法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审美观论文; 书法欣赏论文; 唐朝论文; 文化论文; 南北朝论文; 北史论文; 六朝论文; 书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