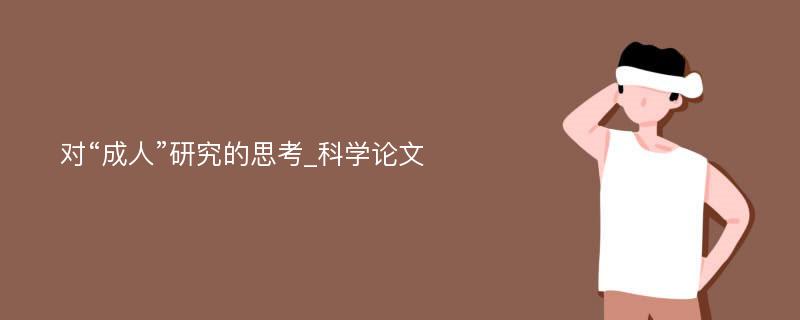
走向“成人”之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学论文,成人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就是使人成为“人”。教育学乃“成人”之学。教育和教育学的旨趣即在“成人”。
一、教育:为何?何为?
我们把A事物命名为“X”,就赋予纯粹的符号X与A对应的指称关系这一逻辑事件而言,其内在的根据往往更多地取决于词语的历史继承性,而不仅仅取决于事物A的本质的或偶然的特性。 这种指称的历史继承性,克里普克称之为“一根因果的(历史的)链条”(注:索尔·克里普克:《命名与必须性》,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第139页。),事物的名称沿着这根链条一环一环地传递下去。实际上,这种传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解释的过程,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对“X”的解释。这种不断传递着的解释必然地,有时甚至是有意地发生信息的损耗和变形,以致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后,X 所指称的不再是A,而是A+B或A-B或者干脆就是指B了。“教育”也是一个“X”。
教育:为何?何为?我们一遍一遍地询问和自问。在这样一个危机与希望并存的时代,我们必须重新对此作出我们的解释。教育:为何?何为?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教育在做什么?教育能做什么?教育应该做什么?教育如何做?
海德格尔说:“关于某物是什么的问题总是多义的。”我们问:教育是什么?这个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问“教育”这个词在我们观念体系中的意义是什么;二是问与“教育”这个能指所对应的那个作为所指的事实是什么。在第二层含义上我们也可以问:什么是教育?这种直指教育事实的古希腊式的追问,村井实又将它分为三级水平,即教育观的水平,常识的水平和科学关注的水平,其中常识水平的理解又是直接与“如何教育”或“教育如何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注:大河内一男等:《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曲程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教育如何做”又必然引出“教育能做什么、在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问题,而应该做什么又直接以“教育为什么”为前提。这一系列问题相互联系在一起,我们总括起来用一个多义的疑问式来表达——教育:为何?何为?
教育:为何?何为?教育思想史上无数个解释构成了“历史的、因果的链条”。这根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尽管都不尽相同,但贯穿所有环节的却是同样一个主题。不管这个主题在某个环节上的表达是直接的还是曲折的、是全面的还是片面的,其基本的思想却在每一个环节上都熠熠生辉。这个主题就是:使人成为“人”。我们借用我国儒家的语汇称之为“成人”。
教育:为何?何为“教育是什么?”作为一种古希腊式的诘问,这个问题最终寻求的是确定一种能指与所指确切的对应关系,它因而是直指教育事实的。但是,这种对事实的追问与“月亮是什么?”、“狗是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有着重要的区别:对后一类问题的回答绝不会对月亮和狗产生什么影响,而对“教育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所作出的解答却可以深刻地影响到人的教育活动。“教育是什么?”这是一个要求人自己对自身行为作出根本性解释的问题,它是一个“爱智”的难题。
既然“教育是什么?”这个问题所指向的事实是人的活动,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教育做什么?”这一问题的追问来探赜索隐。教育做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又有现实的、可能的和应该的三个向度。《列子》中那个“歧路亡羊”的寓言在我们的“心路”上应验了,如果我们分别从三个向度去探究——这往往是找到“羊”的必要办法,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最终得出统一的答案来回答“教育是什么”?我们毕竟不能以扬子式的郁郁寡欢来作为这条心路的终结。这是一条海德格尔的“林中路”,它的终点是一眼源泉。
教育做什么?这是问人做什么,因为教育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体现着主客观的统一,表达这种主客观统一的就是“目的”。“一提到目的,我们必不可立即想到或仅仅想到那单纯存在于意识之内的,以[主观]观念形式出现的一种规定。康德提出了内在的目的性之说,他曾经唤醒了人们对于一般的理念,特别是生命的理念的新认识。亚里士多德对于生命的界说也已包含有内在目的的观念,他因此远远超出了近代人所持的只是有限的外在的目的性那种目的论了。人们的需要和意欲可说是目的的最切近例子。”(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第389页。)人的活动作为生命理念的一种表达内在地包含着目的,这种目的本身就体现了主观见诸客观的辩证统一。人的活动在现实的、可能的和应该的三个向度上最终必然统一于“目的”,于是“教育为什么?”的问题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无论是在哪一向度上,教育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总是要为了什么而“做什么”的,弄清了教育为什么,也就同时明白了教育做什么。
教育为什么?总的说来,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一是为自然(客观世界),一是为人。人是一种主体的存在,主体的存在是“为我”的存在,所以教育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是为了人的,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只是问题答案的第一个层次,因为我们还必须对这“为了人”作进一步的追问:人是什么?或者按照赫舍尔(Abraham J.Heschel )的更恰当的方式来追问:人是谁(Who is man)?这是一个更大的“爱智”难题。
“人是谁?”和“人是什么?”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前者内在地把人和自然区分了开来。人是谁?在人类智慧的光谱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个端点:一个是理性,另一个是非理性。无数答案分布其间。我们教育理论过于重视这理性的一端,而对那非理性的一端却有程度不同的忽视,因此,这种教育理论往往片面强调人在理性方面的发展,忽视情感、意志、信仰、直觉等非理性方面。完整的人的存在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教育要同时从这两个方面来“为了人”。但是,这仍然不能保证教育所面对的是完整的人,因为人的存在无论是在理性方面还是非理性方面都有言说的存在与缄默的存在两个层面。既往的教育理论往往在关注人的言说的存在的同时遗忘了其缄默的存在,正是由于这种遗忘,它把教育限定在人的存在的言说的层面上,即限定在“教授”范畴内,而把不可教授的缄默的层面排斥在教育之外,因此,这种教育理论不仅片面强调“知”的精神,片面强调人在理性方面的发展,而且还片面地以某种外在的自觉性和目的性来限定教育,并片面强调教育所引起的人的外部的可观察的变化。正如赫舍尔所言,“把人的本质与人的外部表现等量齐观是错误的。人的存在的力量和奥秘既存在于人为自己创造的各种表达形式中,也存在于未说出和未宣布的事物中,存在于沉默不语和不可言喻之中,存在于无法表达的意识活动之中。”(注: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缄默的存在与言说的存在的统一才是完整的人的存在方式,所以,简单地加上情感、意志、直觉、信仰或“非智力因素”之类,并不一定就能造就全面的教育。只要还限于言语的层面,或者说限定在“教授”的范畴内,这种教育就还没有真正面对完整的人,因而它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教育”。这是一种更加深刻层次上的残缺。
包含缄默的、尤其是不可言说层面的人的存在,只能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人”,即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活动着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思维着的人。只有“现实的人”才同时包含人的存在的言说的和缄默的层面,其中缄默层面下的不可言说的层面更是只能以现实存在的方式呈现出来。“马克思不再仅仅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自由、理性,而是进一步理解为人的客观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注:杨金海:《人的存在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现实的、完整的存在方式表现为人的生命活动,他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这就是马克思对“人是谁?”的回答。在古希腊,“实践”最初就是指所有生命存在物的生命活动,而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就专指人的生命活动了。(注:张汝伦:《历史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正是用“实践”来回答了“人是谁”。
人的完整的存在方式表现为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它不能被归结为某种抽象人性,而是具体人的活动。“它既包括过程,也包括由其存在的事实组成的结构,以及发生在他的实存中的奇迹和事件。”(注: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教育要面对完整的人,全面地“为了人”,它就必须面对这个包含了理性、热情和事实、奇迹的、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过程,即表现为现实的人的具体生命活动的社会生活过程。一切教育都在这个现实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通过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得以实现,而教育本身就是现实人的活动,所以这是教育的自身同一。黑格尔说:“本质只是自身联系,不过不是直接的,而是反思的自身联系,亦即自身同一。”(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7页。)我们在教育的自身同一中把握了教育的本质,也就是对“教育是什么”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同时也在总体上对“教育为何?何为?”作出了回答。在这条探究的心路上,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起点,这是一个辩证法的循环。
二、教育学:为何?何为?
教育学:为何?何为?这个问题是“教育:为何?何为?”进一步的反思性的逻辑延伸。村井实认为:“只有在把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科学才能开始。”(注:大河内一男等:《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曲程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这后面还可以追加一句:一门学科只有在把自身也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它才开始走向成熟。教育学:为何?何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解决另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否可能?
“当人们看到一门科学经过长期努力之后得到长足发展而惊叹不已时,有人竟想到要提出这门科学究竟是不是可能的以及是怎样可能的这种问题。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人类理性非常爱好建设,不只一次地把一座塔建成了以后又拆掉,以便察看一下地基情况如何。”(注: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页。)在教育学的地基下面, 有两块奠基石:哲学和科学。(注:项贤明:《试论教育学的哲学一科学基础》,《上海教育科研》,1997年第2 期。)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否可能的问题, 最终归结为这两块基石间的关系问题。
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否可能?这里我们首先必须弄清“科学”一词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意思。在古希腊,“科学”和“哲学”可以说是同义的,都是指人类知识的总汇、指人类用以概括反映客观世界和人自身的概念体系。拉丁文中的scientia就是学问或知识的意思。只是到近代以后,随着实证科学的分化独立,“科学”一词才被特别赋予了“实证性”的意义。在培根(Francis Bacon)的母语英语中,science在严格意义上主要是指近代的实证科学。牛津版《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对science的释义是:"knowledge arranged in an orderly manner,esp.knowledge obtained by observation and testing of facts." (依有序方式编排的知识,尤指通过对事实的观察与试验而获得的知识。)(注:A.S.Hornby et al.,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Hong Kong,1970.)这就是我国在五四运动时期请进来的那位“赛先生”。然而,在德文中,Wissenschaft 仍然有泛指一般知识的意思。(注:萧焘主编:《科学认识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所以, 在“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否可能”这一问题中,“科学”一词可能有两种意思:一是知识或学问;二是实证科学。
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否可能?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科学”理解为实证科学,那么我们就很难对这一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教育学要成为一门实证科学,它必然会遭遇很多实证科学本身所无法克服的障碍,其中有些障碍甚至是无法克服的。这是因为教育学不仅要面对一些关于人的“自然事实”。与自然事实不同,人文事实是和人的主体活动直接同一的,因而它内在地包含了人的主体性,并且直接反映着人作为主体的基本特性:自主性、主观性和自为性。(注:高清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下册,第六章,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人文事实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教育学难以成为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首先,当教育学面对人文事实时,由于人作为主体的自主选择性这一“能动变量”的加入,我们就无法在经验事实与人的生长发展之间全面确立某种客观的、必然的因果联系,无法得出一个可以描述人的全部生长发展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模型。在教育活动中,往往是同样的条件却可能得出很多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果,我们根本无法用“如果A则必然B”来全面描述人的教育过程。其次,教育是人作为主体的自我创造,这种能动的人文事实是不可重复的,因此即使我们在一时、一地、一人的教育活动中发现了某种偶然的因果关联,我们也难以真正在“实证”的意义上对这种因果关联进行验证,因而这种因果关联也就难以获得实证意义上的普遍有效性,难以在“定律”的意义上推广到其它教育活动中去。它只能作为一种所谓“前科学”的经验概括而对人们的教育信念产生影响。(注: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 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72—77 页。)第三, 由于上述必然因果模型的无法建立和偶然因果关联的不可推广,教育学就不可能在实证的基础上对人的生长发展作出预测,而只能提供某种经验性的、或然的估计。我们无法从教育活动中获得进行实证性预测所必需的那种不变的因果关联。第四,人文事实中所包含的“价值”,更是宣称“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所无法包容的,而教育活动作为人文事实所内在包含的价值意义又是不可排除的,所以教育学也就无法回避“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它不得不包含一些具有主观性的立法性规则,这使得它不可能象实证科学那样通过建立自足的客观定律体系来完善自身的逻辑体系。这些问题都决定了教育学无法真正成为一门实证科学,并且不同“事实”之间的本质区别决定了这些问题无法通过实证方法的改进而得到解决。
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否可能?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科学”理解为一种“学问”,一种包括实证科学在内的“知识体系”,或者象瓦托夫斯基(Marx W.Wartofsky)所说的那样,“把科学定义为理性活动”(注: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549页。),那么, 这一问题的答案理所当然是肯定的。这是不证自明的。
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说:教育学是一门科学。那么,教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它是关于什么,为了什么的科学?人们运用这门科学做什么?这就是我们进一步追问——教育学:为何?何为?
教育学:为何?何为?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学”是指关于教育的科学,这是符合一般语义规则的一个合理的解释。如前文论述,教育就是使人成为“人”。由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演绎出这样的结论:教育学是关于使人成为“人”的科学。所以我们说:教育学乃“成人”之学。在这个简单的三段式推理过程中,大前提是按照一般语义规则进行直接的解释而得来的一个简单判断,这里不存在多少可以诘难的推进过程。影响结论真实性的主要因素来自小前提,也就是说,我们对教育学的理解主要取决于我们对教育的理解。
教育思想史上主要存在两种对教育的不同理解:一是把教育仅仅看作“教授”的过程,认为教育就是把某种知识、技能或别的什么东西传授给人;二是把教育看作包括教授在内的所有使人全面地生成为“人”的过程。由于这种教育理解上的分歧,我们对教育学也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这就是亨德森(E.N. Henderson )所说的“新教育学”(education)和“旧教育学”(pedagogy)的区别。(注: 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 页。)我们把“旧教育学”作称“教授学”以示区别。这种名称上的区别反映了本文倾向于第二种意义上理解教育学。最主要的理由,既把教育理解为“成人”,前文对此已有论述。另外有理由,即关涉到教育学为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
教育学:为何?何为?既然教育学是关于人的教育的科学,那么教育学当然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自然的,这是顺理成章的事。问题在于它到底该如何为了人,是全面关注人的生长发展,还是只关注其中因教授而引发的那部分?
如果教育学只关注教授行为在人身上引起的那部分生长发展,那么我们会面临这样一些难题:首先,很多影响人的生长发展的东西是不可教授的,它需要人去亲身经历、体验、感悟和意会,所以,教育学如果把自己限定在教授的范围内,它就不可能“全面地”为了人。其次,教育学要是只关注教授所引起的人的生长发展的话,那么人的其它部分生长发展应当由哪一门科学来进行研究?教育学不能“全面”关注人的生长发展,它所遗弃的那部分怎么办?人的“片面”发展又怎么可能避免?再次,即便我们另外建立一门科学来研究教育学所遗留的空白区,我们权且称之为“育教学”,我们也仍然会面对这样的两难问题:如果这门“育教学”是和教育学根本不同的科学,那么如何保证它们关于人的生长发展研究的一致性,从而保障我们在同时运用这两门科学认识和指导人的生长发展时不会存在任何的缝隙、抵牾和困难?如果这门“育教学”和教育学没有什么根本不同,那么它与教育学独立并存的学理依据何在?
教育学不仅要“为了人”,而且必须全面地“为了人”,这就是“教育学乃成人之学”这一命题所表达的真实意义。教育学走向“成人”之学,用本尼(Kenneth D.Benne)的话来说, “这里包含着一个从集中关注对年轻人进行的学校教育的‘教授学’(pedagogy)向一种关注对所有年龄的人进行的教育和再教育的‘人类学’的转变。 ”(注:Kenneth D.Benne,The Task of Post-Contemporary Bducation,P.120.Teachers College Press,Columbia University,1990.)这是理论基础的深刻变革过程。
教育学:为何?何为?要全面地为了人的生长发展,教育学必须保持科学所必备的那种探索的意志。探索,这就是教育学所应做的。人的生长发展纷繁复杂,瞬息万变,这是最需要探索的一片领域。探索也是科学之区别于艺术的本质的特性。科学探索,而艺术制作。教育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就不能停留于内容的复述和形式的翻新,而要磨厉探索的意志。
教育学探索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说明”(explanation ),一种是“解释”(interpretation)。前者对应于“自然事实”,而后者则对应于“人文事实”。这两类事实都存在于“成人”的过程中。
三、走向“成人”
教育和教育学的旨趣即在生成“完整的人”,这是“成人说”的第一层意思。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完整的人”?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一个“人的分裂”的时代,“教育发挥作用的方式及其分配给青少年的途径,对年轻人的训练,对无人可以逃避的大众信息——这一切都有助于人格的分裂。”(注: BdgarFaure,et al.,Learning to be,P.155,Unesco,Paris,1972.)所以,我们必须把“完整的人”作为变革现代教育的目标之一。其二,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只有教育才能使人成为“人”,教育必须全面地承担“成人”的责任,因为我们不可能指望有别的什么东西来承担其余的责任。人类的弥赛亚(Messiah,救世主)只能是人自己,“人必须自我拯救,使自己新生。”(注: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孙恺祥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我们说教育和教育学的旨趣即在生成“完整的人”,这里的“完整的人”主要包括这样三层意思:首先,它意味着教育要给人以在各个方面都获得发展自由。这并不是说教育要保障每个人都成为样样出色的全知全能者,教育不应成为普罗克拉斯提斯的铁床(注:普罗克拉斯提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劫人之后,把人放在一张铁床上,高人将被砍去超过床长度的部分,矮人将被强行拉长,使其与床相齐。)。“全面发展”是指人在各方面都有获得发展的自由,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自主的而不是被强迫的获得发展,从而在总体上能得到一种平衡的发展。其次,它意味着教育应关注人的整体,教育的结果应当是一个整体的而不是分裂的人,他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应当是相互协调一致,统一一体的。在现代的教育中,“为了科学研究及其高度专门化的某种假想的需要,很多年轻人充分而全面的生成(formation)被弄得残缺不全。”(注:Bdgar Faure,et al.,Learning to be,P.155,Unesco,Paris,1972.)这是我们必须加以克服的。再次,它意味着教育应当关注“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因为只有“现实的人”才是人的完整的存在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说:“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卷,第3卷,第245、295、296、330页。)这种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是人的理性存在与非理性存在、言说的存在与缄默的存在的统一,是包含了人的肉体与灵魂、情感与理智、道德和欲望、思维和感千等各个方面的,因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完整的人。“把个体肉体的、理智的、情感的和道德的等各方面整合起来,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对教育基本目的的一种宽泛的定义。”(注:BdgarFaure,et al.,Learning to be,P.155,Unesco,Paris,1972.)
教育和教育学的旨趣即在“人的解放”,这是“成人说”的第二层意义。“完整的人”的生成道路,同时也就是一条走向“人的解放”的道路。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卷,第3卷,第245、295、296、330页。)所以,完整的人的生成过程与人的解放的历史运动过程是同一的,每一具体的“现实的人”的生成过程都是这个解放过程的一部分。教育,作为人的解放,这种对教育的理解主要有这样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人必须取代知识、技能等面真正成为教育的目的,而不是继续作为一种手段而遭受知识、技能的奴役。教育过程不应终止于某种知识、技能、价值观念等的获得,它要进一步在向完整的人的生成复归的过程中把这所有的方面平衡协调地整合起来。第二个层面,教育过程必须和历史的运动现实地统一起来。它不应脱离人的现实社会生活,而应作为人的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一个向度的人的生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作为人的解放,教育必须是向着现实社会生活全方位开放的,任何的限制和禁闭都同时是对人的奴役。“在这方面,所有过去那些教师和教育家们创造性的直觉都和现实相吻合,他们单独地或共同地从这一理念中获得鼓舞:教育能够而且必须是一种解放。 ”(注:Bdgar Faure,et al.,Learning to be,P.155,Unesco,Paris,1972.)
教育和教育学的旨趣即在人作为主体的生成,这是“成人说”的第三层意义。教育要使人成为“完整的人”,它就要使人在各个方面都获得自主的发展,它本身就要作为一种人的解放在人的历史生成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些观点已经内在地包含了“成人说”对人的教育主体地位肯定。概括地说,“成人说”坚定地肯定人的教育主体地位,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动机;第一方面,在历史的层面上,由于以往的教育理论从笛卡尔“我思”的主体观出发,把人的教育活动解释为主体改造客体的活动,这就在现实的教育过程中造成了人的“凝固化和异化”,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才相互都作为客体被嵌入对方的主体性之中,人在教育活动中原本应有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积极性遭到压抑和扭曲,教育被降格为类似于动物训练的东西,它给人带来的不是自我创造的审美愉悦,而是痛苦、挫折和做人尊严的贬损。“成人说”认为,教育不应如此,相反它应当成为人积极地扬弃异化的中坚之一,所以,“成人说”要作为对“改造说”的反抗来取而代之。第二方面,在逻辑的层面上,以往那种把教育解释为主体改造客体的活动的教育理论本身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譬如:它无法把教育过程中作为教育客体的人和作为教育客体的物区分开来;它强调教育要发展人的主体性却又同时把人视中作客体。“成人说”的提出,正是要在逻辑上克服这些矛盾,探索教育理论新的发展道路。教育和教育学的旨趣即在人作为主体的生成,这个命题主要包含了三层意思:其一,教育是人作为主体开发、占有和消化人的发展资源从而能动地生成“完整的人”的过程。其二,教育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际交往关系。其三,这种主体际交往关系构成了人的社会关系,所以教育活动是在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过程中进行的,是与社会生活过程直接同一的。
教育和教育学的旨趣即在于人在自然之中与自然协调地生成,这是“成人说”的第四层意义。人作为主体的生成过程不仅排斥对人的压制和奴役,而且也不以对自然的肆虐和否定为前提、背景或结果。人作为主体的生成过程是同自然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相同一的。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以往的教育理论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它错误地把“真理”约简为“正确”,因而热衷于对正确知识的掌握,热衷于这些知识以对人的训练为中介,在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过程中的效用,却反而把人本身,把人的幸福忘却了。“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的看护者。”(注:海德格尔:《论人类中心论的信》,第89页。)人对自然的责任和人对他自身的责任是一致的。人是在自然中生成的,人是和自然一起生长着的,这两者原本就是统一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自然即由之而生,自然即是循之生长,凡生成的东西都具有自然”。(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 7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人的生长与自然的生长所不同的即在于人的生长的文化性,而自然与文化的区别也只是:“自然产物是自然而然地由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文化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撇开文化现象所固有的价值,每个文化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与自然有联系的,而且甚至必然被看作是自然。”人与自然的统一表现为文化与自然的统一,表现为人的现实社会生活。马克思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所以,人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生成同时也就是在自然中的生成。
人,诗意地生长在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