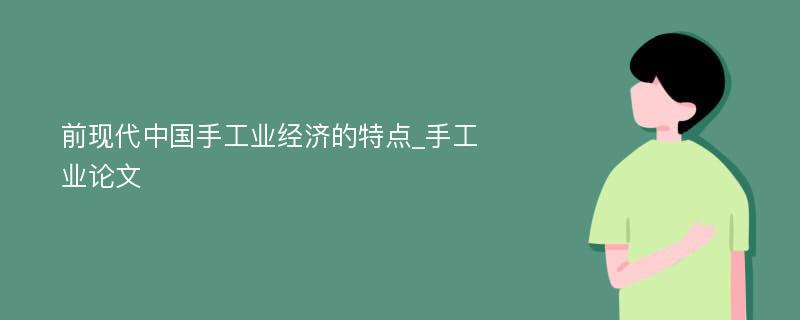
中国前近代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工业论文,中国论文,近代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6-0079-07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是传统社会的三大经济部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基本依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大经济部门的出现,反映了人类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一定水平。就三大经济部门本身来说,手工业是仅次于农业的一个生产部门,是人类早期生产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同时,手工业还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商品生产部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手工业经济具有不同的特点,这既包括对其自身(这些特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手工业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明显特点的总结,同时也有与近代企业之间的比较。下面只是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就中国前近代手工业经济的若干基本特点进行简要总结。
一、家庭副业手工业一直比较活跃
家庭副业手工业是手工业的基本类型之一,在传统社会自始至终都比较活跃。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家庭副业手工业包括农民家庭副业手工业和地主家庭副业手工业两种情况,二者所经营的规模差异比较大,同时生产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从整体上看,家庭副业手工业在传统社会主要以纺织品生产为主,是有深刻原因的,其中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与政府的赋税内容主要包括纺织品有关,二是纺织品是居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纺织品与粮食同样重要,须臾不可或离。正因为如此,在古代往往是“衣食”连称。
在讨论我国历史上私有手工业是否发展的情况时,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政府对于民间工商业者的态度。众所周知,在私营工商业政策方面,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一些国家为富国强兵,也多对其采取鼓励宽容政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通商惠工”政策[1](《闵公二年》)。此外对私营工商业仍采取“弛关市之征”的办法,鼓励其他国的工商者前来本国从事生产或商业活动。晋国还实行“国无滞积”,“公无禁利”,开放山泽之利,让民私营,这无疑促进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春秋末期卿大夫与公室的夺权斗争中,一些公室或卿大夫也为了争取工商阶层的支持,推行一些积极发展工商的政策,这一做法成为整个古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国策而被实施。
考察我国历史上的手工业经济就会发现,家庭纺织品作为商品最早进入到流通领域,一开始它是通过以物易物的形式出现的。《诗经·国风》中就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的说法。这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丝织品就已经作为民间商品而进入流通领域,同时也说明当时纺织业的分工比较明显,布与丝是作为不同的商品而进入到流通领域的,其中有的人既是商品如丝织品的销售者,同时又是布匹的消费者。这与《盐铁论·错币》中说的“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是一个意思。这里的“布”和“丝”都是纺织品及其原料,证明在比较原始状态下的市场交换中,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纺织品及其原料,是市场中的最基本的商品,这是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又没有充分发展的体现。据《诗经·豳风·七月》言,“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粗麻织成的短衣,是劳动人民御寒过冬的必备物品,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这样的纺织品是由自己家庭成员生产的,家庭纺织手工业作为副业,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因此,“男耕女织”、“晴耕雨织”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个自然分工,“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2](《鲁语下》),就是先秦及以后家庭成员自然分工的传统。这种情况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在近代化以前的传统社会,家庭副业手工业中,家庭纺织自始至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正因为如此,著名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将纺织品(纤维)与食品、燃料和建筑材料一同列为人类四种生活必需品。而中国传统说法中的“衣食住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七件事,均直接或间接与手工业分不开。正因为如此,《汉书》卷24《食货志上》记载贾谊向汉文帝上书中强调了“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可见家庭副业手工业与农业生产一样,是个体小生产农业经营者所必须同时兼顾的,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生产需要。
在我国纺织手工业经济中,丝麻的历史非常悠久,因是居民生活的必需品而受到喜好和重视,但是其生产数量越来越因人口的不断增加而显得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新的纺织品原料就成为日益迫切的事。植棉技术在中国广大地区的普及正好适应了这一要求。据王祯《农书》卷21记载,棉布较传统的丝麻纺织品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优点:降低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收获相对稳定,纺织加工方面比较简单。另外,棉布的御寒功能并不比丝麻逊色。这样就为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明代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曾经“令益种棉花,率蠲其税”[3](卷232),旨在鼓励棉花生产,提高纺织品数量。这是通过政府手段来鼓励民间纺织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当时的棉花作为纺织品的重要原料,已经成为政府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
以纺织为主的家庭副业手工业,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也显得比较活跃,它既是农民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同时也是农民进入市场的重要商品,另外还是劳动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明代经济比较发达的松江地区,作为商品而生产的棉布比较多,但纺织仍然主要是作为一种副业。研究表明,清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经营普遍,以别业而论,莫过于纺织业,因此纺织业仍然是包括清代在内的我国封建社会内最典型而又有广泛基础的农村家庭手工业[4]。不仅鸦片战争以前,即使在鸦片战争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棉纺织业还基本保留了农业家庭手工业生产方式[5]。据专家研究表明,即使进入近代社会,甚至在当代经济发达地区,家庭副业手工业也仍然是农民的必要经济补充(注:2004年5月14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等举办的第三次“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就这一现象进行了热烈讨论。另外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著《中国村庄经济——无锡、保定22村调查报告(1987—1998)》,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实际上,家庭副业往往不局限于纺织品,一些简单的手工业生产,也是农民在主业粮食生产之余所进行的,以作为主业的必要补充。民间手工业品中,有一部分是作为商品进入到流通领域的,这一部分积少成多,成为当时市场中商品的主体部分。政府对于民间手工业品,尤其是进入市场或作为上缴官府的产品,则有一定的规定,有些时期这一方面还显得具有强制性。如唐玄宗开元八年(720)敕令中就有这样的规定:“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准,故遣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6](《食货志上》)这种情况在整个封建社会比较普遍,系国家职能的一种体现,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从整体上看,政府的这些做法是有利于民间手工业经济或民间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尤其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合法权益得到了某些保护。
二、官府手工业自始至终比较发达
官府手工业大体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直接为皇帝、贵族、政府和军队的特殊需要而设立,涉及到纺织、瓷器、金银器、建筑、兵器、铸币等;另一部分则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物资,因其社会需求量大,利润高且有些涉及到国家安全,往往由政府直接经营,如盐、铁、酒、茶叶等,主要实行政府专卖制。正因为官府手工业首先是为统治阶级及其军队服务的,尽管其技术装备良好,原料充足,人手得到充分保证,技术全面,由于其管理属于各级衙门,其产品主要用于消费而不是为市场而生产,故效率低下,一般属于高投入低产出。从整体上看,我国历史上的官府手工业一般机构重叠,政出多门,贪污之风盛行,盘剥工匠屡见不鲜,人力、物力和财力浪费现象严重。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是,由于官府生产不计成本,人手充足,工匠技术全面,一些重大发明往往是由官府发明而逐渐向民间传播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保证官府手工业有比较充足的人手和原料,这是官府手工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北魏天兴元年(398)正月,就曾经“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7](《太祖道武帝纪》);隋代建立之初,“征天下工匠,纤微之巧,无不毕集”[8](《苏孝慈传》)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唐代中后期在雇佣官府工匠比较普遍的情况下,仍然规定“巧手供内”者不在“纳资”的范围之内,以保证官府手工业内的技术人手。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诸如不允许“隐巧补拙,避重就轻”等措施,以保证官府手工业作坊的工匠是“材力强壮、技能工巧”[9](卷7注文)者。这是前近代社会的一个通例。
对于盐、铁等商品实行专卖或征榷制,是汉代以来的一项基本国策。《汉书》卷24《食货志上》记载:秦时“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道出了政府控制盐铁等的经济利益之所在,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是由规模效益所决定的。随之而来的是其内容在不断扩大,酒和茶叶也往往成为专卖的内容(注:其中茶叶作为国家的正式税收,按《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记载始于饮茶盛行的唐代德宗时。酒的专卖和控制,各个时期情况不一,不可一概而论。)。政府的专卖商品,首先就涉及到对于这类商品的加工,这是当时官府手工业经营的基本内容,也是官府手工业发达的基本原因之一。这种专卖制在后来多有变化,其总的趋势是专卖的内容在不断扩大。就整个封建社会来说,随着直接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和商品经济的相对活跃,官府手工业逐渐显得冷落,民间手工业相应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官府手工业与民间手工业的消长往往反映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即使如此,官府手工业自始至终还是比较发达的,这是我国手工业经济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
我国历史上官府手工业发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下面的原因无论如何不可忽视:民间个体工匠保证了官府手工业生产人手的基本来源,民间手工业是官府手工业取之不尽的技术源泉,官府手工业机构能够通过国家配置资源的能力提供所需的手工业原料,官府手工业具有不断吸取外来技术的便利条件,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在客观上为官府手工业的一些技术不断提高提供了可能。
三、集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前店后坊模式比较普遍
我国历史上私营手工业者往往是集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前店后坊的经营方式,因此历史上工商往往不分,我们今天在历史文献中将二者截然分开是相当困难的。手工业集生产与销售于一体,与当时市场发育水平有直接的关系,应该说是市场发育达到一定水平而又不够发达的产物,实际上这也不是绝对的,即使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产业资本家也还比较普遍地采取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
《景德镇陶录》卷5《历代窑考》引《(景德镇)邑志》记载:早在“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按这里的昌南镇,即后世著名的瓷都景德镇。陶氏生产出质量精良的陶瓷,并亲自将其带到当时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关中地区,以“假玉器”之名贡献于朝廷,这正是手工业生产者追求产品知名度的惯用做法。陶瓷生产过程相当复杂,一般需要相当数量的工匠协作才能够生产,非一家一户所能独立完成。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私营手工业作坊。陶氏生产的陶瓷精品,除了在当地销售外,就连去京师提高知名度也由主人自己亲自完成,说明销售及提高产品知名度对其非常重要。这实际上是将生产和销售合而为一,陶氏兼有手工业作坊主与商人的共同特点。在手工业商品生产和销售中,由于竞争激烈,出现了促销活动,其中有个体工匠销售瓷器,顾客购买达到一定数量时便赠送其他物品。其中如《唐国史补》卷中记载,唐代巩县私营瓷器作坊的促销活动是:多制“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即使今天,这样的促销活动仍然被厂家或商家普遍应用。
与此同时,手工业生产者中还出现了为用户定做手工业商品的经营方式,像杨收建造白檀香亭子,宣州观察使李璋事先令工匠“度其广袤,织成地毯”,等杨收会亲宾观亭之日将货送到,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10](卷237“李璋”条引《杜阳编》)。这里虽然主要说的是官员贿赂的史实,却透露出当时定做手工业品的情况。手工业者同时兼商人者,在前近代是比较普遍的,所谓“前店后坊”就指此。实际上,这种情况还包括手工业生产者同时兼做长途贩运的生意。如《太平广记》卷355“广陵贾人”条引《稽神录》:“广陵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凡什器百余事,制作精良,其费已二十万,载之建康,卖以求利……复归广陵,至家,已有人送钱三十万……”
集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工商形式,在前近代不同时期均存在,而且是民间私营手工业和作坊手工业的基本形式,说明当时生产与流通的合而为一,这是当时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不够充分的体现。
四、合伙制具有近代企业萌芽的某些特征
我国历史上的手工业行会,其作用和性质与欧洲中世纪相比差异比较大,中国的行会一开始就表现出与国家政权的密切关系,甚至有国家政权控制手工业生产者的最基层组织的某些职能[11]。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唐代以后手工业行会的情况,大体上与唐代差不多,这是由我国强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所决定的。中国传统手工业中的合伙制出现得比较早,且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发展比较快,成为我国手工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
合伙制至迟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苗头。《太平广记》卷134“王珍”条引《广古今五行记》:“唐定州安嘉县人王珍,能金银作。曾与寺家造功德,得绢五百匹。同作人私费十匹,王珍不知。”王珍作为作坊主一次性得到500匹绢的报酬,可见其金银加工作坊的规模一定不小;再从其雇佣的工匠预先擅自支出10匹绢而王珍居然没有觉察的史实中可以看出,这类工匠与主人之间似乎没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系一种比较简单的雇佣关系。据此可以作出如下推测,在作坊主王珍手下从事金银器加工的工匠人手不少,这里的“同作人”可能是作坊内的技术或部门负责人,也可能系资金方面的合伙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合伙制在后来有了进一步发展,据《天工开物》记载,明代在陶瓷中有“合并众力众资”从事生产的情况,便是这一领域的合伙制。明代在四川井盐开采中也实行合伙制,以解决人力、财力方面的问题[12](P206-230)。清代的合伙制在民间手工业中更加普遍,至少在十六七个行业内出现了合伙制,这在清代以前是未曾有过的。这一时期的民间手工业中的合伙制主要有劳动合伙制、资本与劳动兼而有之的合伙制、资本合伙制等三种形式。其中第三种形式即资本合伙制又分为两种不同情况:一是合伙人只投入资本,本人不参加劳动,但是投资者一般亲自参与经营管理,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二是投资者本人既不参加劳动,也不亲自参与经营管理,而只是作为资本的股东参与分配,企业有专门的管理人员,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13]。总之,合伙制虽然与近代企业不是一回事,但是合伙制的发展对于产生近代企业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如果没有外来影响,这可能就是我国境内产生近代企业制的一个环节。
五、民间手工业生产者的土地投资偏好
“以末致财,用本守之”[14](《货殖列传》),是对传统财富观及其投资趋向的总结。现在的一些论著在论及这里的“末”时,认为只是特指商业,这是不完全的,因为按当时人的意思,则应包括手工业和商人两种职业。《史记》卷68《商君列传》注文是如此解释的:“末谓工商也。”可谓一语中的。正因为如此,在古代往往是工商连称。从历史实践来看,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实际上只是讲对了一部分,因为在当时,致富的途径除了从事工商外,从官也是致富的途径,甚至比从事工商业来说更加快捷方便,机会成本更低,回报率却更高,故有“奇货可居”[14](《吕不韦列传》)之说。因此,确切地说当时是“以末或官致富,用本守之”。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认为土地财富的投资是风险最低而相对保险系数最高的,工商业者和官吏向土地投资便成为一种偏好。
从《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可知,秦汉及其以前从事工商业者,一般都从事土地投资,而不是完全从事工商业的扩大再生产,其中有的工商业者是在从事手工业的同时还进行土地的经营。这种情况在秦汉以后进一步明显。刘宋孝武帝时沈庆之是一个集高级官僚、地主和工商业主于一身者:“居清明门外,有宅四所,室宇甚丽。又有园舍在娄湖。庆之一夜携子孙徙居之,以宅还官。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闬焉。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身享大国,家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再献钱千万,谷万斛……妓妾数十人,并美容工艺。”[15](《沈庆之传》)这种现象在唐代以后更加明显。
相当普遍的是,工商业者中有不遗余力地培养子弟在科举考试中求得功名,以保住已经获得的财富以便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这种情况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中后期。
在我国古代的一个明显的史实是,作为手工业生产者,从来就没有完全与土地脱离,我们从历代授田中手工业者也有一定的份额中可以看清楚。《汉书》卷24《食货志上》:“士、工、商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北魏、隋、唐实行均田制时,按规定工商业者同样会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这种情况在后来也没有多大的改变,严格意义上的完全脱离土地的手工业生产者在实际生活中是非常少的。
当然,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这就是政府往往将“男耕女织”或“晴耕雨织”型的家庭副业手工业,归于“本”之中而大加鼓励,并不像手工业生产者那样受到诸多限制。
六、工匠的身份变化比较大
“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16](《食货志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即四民分业,道出了士、农、工、商的专业生产性质,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排序。从我国历史看,秦汉时期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最低,并且确立了其社会地位的基调。但是,随着封建经济领域内商品经济的相对活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直接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弱,工匠的身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另外,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与其经济地位往往并不完全一致,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在讨论工匠身份变化时尤其需要注意。
秦代实行严厉打击工商业者的基本国策,是人人皆知的史实,这种国策被汉初决策者所继承。《史记》卷30《平准书》如此记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也就是说,当时对工商业者的衣饰及交通工具方面多有限制,而且对工商业者本人及其后裔进入仕途多有限制,这种情况在隋唐以后的一千余年的科举时代,依然存在。
从整个古代社会的法律规定看,手工业生产者的地位较一般的编户齐民要低,尤其在封建社会的前期更是如此,即使在封建社会后期,手工业生产者的地位上升乃至与农业生产者几乎没有多大差异时,工商业者地位低下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一种观念的改变要较一种制度的改变困难得多。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首先是当时的法律规定工商业者地位低下,与其在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形成比较大的反差。二是工商业者凭借自己的经济优势,往往对政府官员施加影响,从而跻身官吏行列。“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14](《货殖列传》),是对社会现实的总结。在长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手工业生产者与商人一样,较农业生产者明显占有优势。正因为如此,工商业者的法律身份规定与社会现实中的地位相差比较大,正如晁错上书汉文帝时所言:“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16](《食货志上》)这种情况不仅仅只是汉代的特例,几乎是汉以后社会的一个通例,一直持续到匠籍制度的废除。如在北魏时洛阳“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17](卷4《城西》)。正因为如此,尽管在我国古代社会绝大部分时期,工商业者作为“末”业者,其政治地位没有农业生产者高,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手工业生产。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在工商业者的身份与实际地位之间的反差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工匠的身份相对于农民来说要低一些,除了在政治上的待遇低外,受政府的盘剥似乎也较农民为重,其中主要负担是在官府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在后来尽管“和雇”比较普遍,实际上并不是合理的劳作报酬,官府中的待遇往往低于市场价,再加上交通往来的费用,就更可想而知了,尤其对于能工巧匠来说,在官府中获得的报酬与其所付出不成比例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工匠隐瞒匠籍的事一直存在着,即使在明代亦然。明洪武十七年(1384)正月,工部尚书麦至德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天下工匠,多有隐为民籍而避役作者。”[3](卷159“洪武十七年正月甲寅”条)作为工部尚书所言,应该比较权威,可见工匠隐瞒匠籍而为一般民籍的现象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作为手工业直接生产者的工匠来说,不论是官府工匠还是民间工匠,政府对他们的人身控制经历了一个由严格到相对松弛的过程,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明代洪武十一年(1378)五月,曾经诏令工部:“凡在京工匠赴工者,月给薪米盐蔬。休工者停给,听其营生勿拘。时在京工匠凡五千余人,皆便之。”[3](卷118“洪武十一年五月壬午”条)根据当时的规定,在京师从事生产的工匠有一定的报酬,其中工匠的报酬在后来还规定由“薪米盐蔬”到“凡役于内府者皆给钞”[3](卷214“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戊寅”条),成为纯粹的货币报酬;而没有在官府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则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在这以前尽管也有类似的做法,而如这一次由朝廷的诏令规定受惠的工匠在京师就多达五千余人,在以前是未曾有过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地方工匠的“轮班勘合”,就是“令先分各色匠所业,而验在京诸司役作之繁简,更定其班次”。一般情况下是“三年或二年一轮”。这样就使“赴工者各就其役而无费日,罢工者得安家居而无费业”。当时勘合的工匠人数多达232089人。这次工匠勘合对于工匠是一次比较明显的控制松动,故“人咸便之”。相对而言,这样的编制比较合理,便于操作。因为在这之前的情况是,“诸色工匠岁率轮班至京受役,至有无工可役者,亦不敢失期不至”[3](卷230“洪武二十六年十月”条)。
清代顺治年间(1644—1661)匠籍制度的终结,使工匠自由支配生产的时间增加,进一步表明工匠身份的相对提高,对我国手工业经济的影响重大而深远。
七、工匠技术的传授主要通过父子相承或兄弟相承
不论对于官府手工业还是民间手工业者来说,技术的获得和传承是非常复杂而重要的。在信息相对闭塞的传统社会,一项比较复杂的工艺往往需要若干年乃至若干代摸索和积累才能获得,成本是非常高的。尽管“不耻相师”(注:《全唐文》卷558韩愈《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是我国历史上工匠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国历史上工匠的生产具有非常严格的师承继承制度,民间工匠技术只传于家族内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防止技术外传是普遍遵循的一个原则。
在唐代有“代传染业”的染工[10](卷36“李清”条);有能制作“莹竹如玉”而世间“莫传其法”的笔匠[18](卷乙);唐宋时期有家传长达300年绝技,能织“举之若无”的高级轻纱的专业户(注:《老学庵笔记》卷6:“毫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一州惟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余年矣。’”);唐宋时期著名的宣州制笔专业户诸葛氏,在数百年中保持着在家族内生产名牌笔的记录。如此记载,不一而足。上引几则史料显示出,个体工匠为了使若干年乃至若干代积累起来的一技之长,成为自己在社会中竞争立足的本钱,是不会轻易地对外泄漏家技的,这样就往往使个体工匠尤其身怀精湛技艺的工匠家庭的婚姻,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选择配偶的余地比较小,严重影响了这类工匠家庭人口的再生产,长期以往则必然会使这样的手工业家庭出现萎缩。这样,就出现了“相与世世为婚姻”者[19](卷6),甚至“终老不嫁”的现象也不足为奇。一方面这样做保证了技术在家族内部的传承,另外一方面也不利于技术的传播,我国历史上一些手工业技术的失传,当与此有一定的关系。这一般由两种情况所致,其一是工匠还没有来得及传授技术便因身体等变故而使技术中断;其二是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高超的技术对于未成年的女子是保密的,主要害怕一旦女子外嫁后技术会外传,从而对本家庭造成一定的竞争,有的工匠家因没有符合传授家传技术的男性人选而导致技术失传。
师承制度也适应于官府,并且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其技术传授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大体上反映了秦汉以来官府手工业工匠技术培训的情形[14](《货殖列传》)。通过培训保持官府内手工业者技艺骨干队伍相对稳定和技艺在官府内的公开和协调。由于官府手工业的生产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为了保证官府生产品的质量,官府手工业的生产是师徒共同署名,实行责任连带制。
早在西周时期,在官府手工业中服役的工匠,不但都具有专门技能,而且都是世代相传的,各种工匠都掌握着特殊的熟练经验与技巧。一个有专门技艺的工匠的培养是不容易的,较高工艺水平产品制造者的培养尤其不易。所以,周人在灭商后,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氏族受到有效的保护。即便是对违反酒禁的手工业者,也表示了特别的宽大。这在《尚书·酒诰》中比较清楚地表现出来。实际上这不仅仅只是西周的情况,像北魏和元朝建立时均有此类的记载。为了保持手工业队伍的安定,西周还规定手工业者不能迁业,世代相传。如《周礼·考工记》所言:“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父子世以相教)。”《荀子·儒效》亦谓:“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这一制度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乃至后世都为手工业者所恪守,《国语》卷6《齐语》中有如此记载:
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
“工之子恒为工”实质上就是“父兄之教”和“子弟之学”,这对于保持手工业劳动者的数量,保持手工业队伍的相对稳定,对手工业者相互切磋提高技艺,都有积极的作用,尽管这种制度本身有束缚手工业者人身自由,加重对其剥削的一面。秦汉以后对于官府工匠的培训制度更加成熟和完善,其中如唐代官府工匠根据工种的难易程度师徒传授技艺的时间是九个月至四年不等,至于一些简易工种则是“有三月者,有五十日者,有四十日者”。为了保证这种师徒培训制度的成效,政府严格规定:“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20](《百官志三》)[9](卷22《少府监》)在培训期间,培训者即技艺高超者须向被培训者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被培训者所生产的产品同时要注明培训者的名字,实行责任连带制。这种情况在古代社会自始至终都存在,这就保证了官府手工业作坊内生产质量与产品质量的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