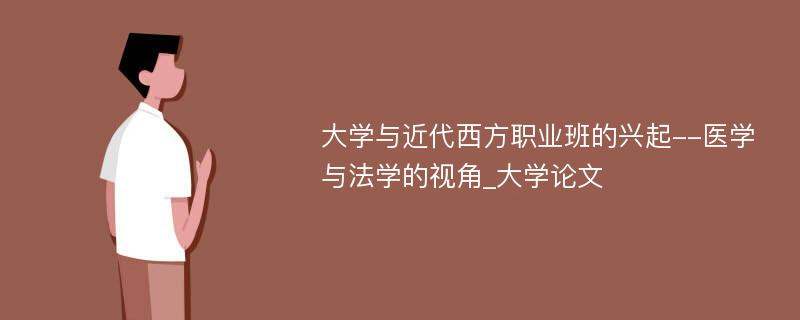
大学与近代西方职业阶层的兴起——以医学和法律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阶层论文,视角论文,医学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4203(2011)06-0092-06
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医生和律师是被人们普遍认为具有高深的知识技能体系、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专业学习和培训、有规范的专业组织、强调专业标准和职业伦理的两种职业,具有较高的经济收入、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作为历史悠久的职业,医生与律师今天的职业形象与社会地位是什么时候确立的?其职业形象与社会地位又是怎样获得的?过去的研究更多强调的是职业自身的发展[1],而忽视了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实际上,近代西方医学和法律两种职业阶层的形成与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中世纪大学不但是近代大学的直接渊源,而且也为欧洲的法律与医学知识的传承和创造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组织和制度上的载体,从而为西方社会培养了大批医学和法律人才,为近代西方职业阶层的兴起和专业形象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在近代西方文明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一、中世纪知识的复兴和大学的兴起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虽然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日耳曼蛮族的入侵让欧洲古典时代繁荣的知识活动暂时停滞,但这一状况并未持续贯穿整个中世纪。欧洲社会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黑暗之后,随着十字军东征打破了社会的封闭,加强了与东方阿拉伯世界的联系,阿拉伯人的科学和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文献被带到欧洲,这些科学和文献在翻译家的努力下重新进入欧洲人的文化视野,唤醒了西方世界的求知热情。[2]随着中世纪西欧社会经济的逐步复苏,具有经济职能的自治城市在欧洲西部和南部出现,基于商业活动与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需要,新兴城市对各种职业和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多,不但需要更多能书会写的文职人员,也需要能够解决法律纠纷的律师、医治病患的医生和传教布道的牧师。于是从11世纪开始,西欧社会在医学、法律、神学等知识领域开始出现复兴的迹象。[3]中世纪科学史家格兰特(Edward Grant)把1000年到1200年的“翻译时代”称为中世纪“黎明的曙光”。他这样形容11世纪末期十字军东征后,欧洲开始向阿拉伯人学习的情形:“随着基督教徒1085年攻陷托莱多和1091年占领西西里,一个充满活力的基督教欧洲开始成为阿拉伯学术的伟大中心。阿拉伯文书籍随手可得,智力饥渴的欧洲人热切地把它们译成西欧学术的通用语言——拉丁文,翻译者来自欧洲的各个地方,他们……把阿拉伯文的专业性科学和哲学论著译成对这些内容几乎一无所知的语言。”[4]
翻译运动为西方人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知识世界,正是对于知识的强烈兴趣,使得中世纪欧洲出现了一些知识交流与传播的中心和一批伟大的学者,他们的名声和活动吸引了更多求知人士的到来。于是,12世纪和13世纪之交,围绕着知识的学习和教学活动,在西欧的博洛尼亚、巴黎、蒙彼利埃等城市,教师和学生模仿城市里普遍存在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的形式自发组织起来形成学者的自治团体(universitas)①。这样的团体有着对外保护和对内规范的双重功能,一方面保护成员的人身安全、保障团体的利益不受外界力量的侵犯,另一方面能够选举团体的领导者、控制团体的招生、制定团体的法规和章程、迫使团体的成员遵守集体纪律和互助规则,也可以自由组织教学,规定课程、学习的时限、考试和评价学生成就的形式以及学位的授予,它们还是得到外界权威(宗教的或者世俗的)认可的、拥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人实体(corporation)。
教师和学生最初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教学和学习的习惯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的传统和习俗。随着学术群体的壮大和发展,群体中各种具体和特殊的习俗逐渐增多,发展成为大多数人自觉遵循的惯例,在日常生活不断得以运用的过程中,它们开始向一般性和抽象性的规则转变,最后人们以成文法律的形式(即大学章程②),将这些规则记录下来并且正式颁布。这些成文的法律规则在得到了宗教或者世俗权威认可之后,组织便拥有了合法的地位,同时这些法规也具备了继承、模仿和借鉴的基础。因此,中世纪知识的保存、传播、创造和应用活动经历了从习惯到习俗、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法律规则的过渡与转化的动态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延续至今的大学组织和制度就产生了。
二、大学组织与制度对知识持续发展的影响
在欧洲南部,知识的复兴最早是从医学和法律两个领域开始的。最早兴起的一批大学中,欧洲南部大学数量是最多的,这些大学中主要的学科是医学和法律。在中世纪师生组建社团的努力下,大学的组织机构得以逐渐完善,一系列学术制度建立起来,不但为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固定的场所,也为求知者的人身安全提供了保护,甚至让他们获得了其他社会团体成员所无法企及的自由与特权。[5]在大学这样的组织之中,教师与学生们逐渐将医学与法律知识概念化、系统化,使其融合为规范的知识体系,作为一门学科来教授和学习,教学有固定的方法,学习有一系列从低到高的标准、程序和评价体系,授予学位作为掌握知识和从事教学的凭证,逐渐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学术制度。这样的学术制度赋予了知识和学问超越地域和国界的性格,使得知识的交流与传播不仅有了统一的语言——拉丁语,也有了统一的方法,即经院主义的方法。可以说,大学组织的发展与知识的持续进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博洛尼亚、巴黎、蒙彼利埃、牛津等地大学与知识的发展验证了这一事实,而萨莱诺恰好是相反的例子。
在中世纪医学知识复兴的过程中,萨莱诺这个城市曾经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地处意大利西海岸的萨莱诺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医学实践活动,9世纪至10世纪萨莱诺成为“希腊、拉丁、阿拉伯和犹太文化的交汇处”[6],为中世纪医学知识最早在这里复兴奠定了基础。11世纪医学文献和医学者的名字开始在萨莱诺出现,11世纪末12世纪初期,大量阿拉伯文的医学和科学作品,以及阿拉伯文的希腊医学作品被翻译成拉丁文引入萨莱诺。12世纪萨莱诺的医学教学活动虽然十分兴盛,但是医学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个体教师的行为,没有真实的历史证据③表明教师与学生们中间形成了任何类似行会的法人组织。12世纪不但见证了医学知识在萨莱诺的复兴,也见证了法学知识在博洛尼亚的发展、神学知识在巴黎的发展以及医学知识在蒙彼利埃的发展。但是与萨莱诺不同的是,在博洛尼亚、巴黎和蒙彼利埃,在知识复兴和发展的同时,大学组织也在孕育,教师和学生们在这些地方组建起了独立的、有自己的章程、特权和单独颁发学位和许可证权力的法人团体,到13世纪早期,这些地方的大学得到了世俗或者教会权威的认可,获得了正式与永久的形式。12世纪萨莱诺大学组织制度的缺乏,恰好与其他地方大学组织制度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到13世纪,当博洛尼亚、巴黎和蒙彼利埃等地的大学组织蓬勃发展之时,萨莱诺的医学开始呈现衰落的迹象。到14世纪初期,萨莱诺的衰落已成定局。政治困境和战争④都有可能是造成萨莱诺医学知识与活动衰落的原因,但并不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著名大学史学家科班(Cobban)认为:“如果要使智力活动的契机不消散,那么在取得学术成就之后,必须作出制度上的反映。缺乏固定的组织,在开始时也许为自由探索提供了机会,但经久不息和有组织的发展只有通过制度上的架构才能得到。”[7]而“萨莱诺最致命的弱点在于,它没有能发展起一套具有保护性的、有内聚力的组织来维持其知识上的进步”[8]。所以,当博洛尼亚、巴黎和蒙彼利埃大学兴起之后,医学知识的持续发展逐渐转移到这些新兴的大学之中,萨莱诺的医学在欧洲的重要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萨莱诺的医学虽然有着辉煌的开始,但在其发展的顶峰时期,没有能够围绕医学以及相关的知识成就形成有聚合力的组织,确保获得进步的发展,达到完全的大学水平。等到博洛尼亚、巴黎和蒙彼利埃等大学的医学教育兴起之时,萨莱诺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三、中世纪大学知识的学科化和专门化
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初期,知识的传授方式是父亲传给儿子、师傅传给徒弟的师徒制方式,正是大学在中世纪的产生,改变了知识从个体到个体的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大学将中世纪各种知识整合到一起,变成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将中世纪零散的教育活动归并到一种机构之中,并且发展出一套共同的教学标准和评价体系,使得知识的传承和人才的培养开始具备相对稳定的组织和制度载体,将知识的发展提高到科学的水平,作为一门有组织的学科得到承认。一个普通人只要有意愿,都有机会到大学中去习得这门学科的知识体系,并且通过获得学位来衡量与评价他在大学中学习的成果,成为进入相关职业团体的凭证。
医学和法律两个知识领域是中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例子。众所周知,医生和律师是今天西方社会普遍受到尊敬的两种职业,专业化程度非常高,从业者有着良好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虽然这两种职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中世纪大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两种职业只能被称为手艺或者技艺(craft)而不是一门专业或者职业(profession)。[9]大学出现之前,医学和法律知识只是“自由艺术”(liberal arts)的一部分,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是一种预备知识。[10]中世纪大学的学习和教学活动,使得医学和法律成为独立的学科而被人们普遍接受。
美国当代著名法律史学家伯尔曼教授在其著作中写道:“十二世纪以前西方流行的法律依然是血亲复仇法,决斗裁判法,水、火裁判法以及宣誓断讼法。无论是王室还是教会,都没有专业法官、职业律师和法律书籍。习惯统治一切:部族习惯、地方习惯和封建习惯。在国王的宫廷和在修道院,尚有几许‘文明’存在,但是若无制度化的法律,要把文明由各个中心传播于四方则极为困难。”[11]而12世纪之后,这种制度化的法律开始逐渐形成,这是与中世纪晚期大学在西欧社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在谈到大学与法律制度的关系的时候,伯尔曼教授明确指出:“近代西方法律制度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出现与欧洲最早一批大学的出现密切相关。在那里,西欧第一次将法律作为一种独特的和系统化的知识体亦即一门科学来教授,其中零散的司法判决、规则以及制定法都被予以客观的研究,并且依据一般原理和真理而加以解释,整个法律制度均是以这些原理和真理为基础的。”[12]
中世纪大学将教师与学生聚集在一起,将医学、法律与神学并置为独立和专门的学习领域,并且用“经院主义”的方法来教授和研究这些知识。在中世纪大学中,医学和法律不仅有实际的社会用途,而且它们也建立在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例如,在大学中,医学不仅仅是治疗,还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和盖伦学说基础之上的理论学科。[13]所以,医学不再完全是实践的和技术的知识,而是具有高深理论基础的知识。
在中世纪大学里,法律和医学不仅成为了专门的学习领域,而且也成为了能够授予学位的高级学科,只有在完成低级的文科课程的学习之后才能开始学习。为了获得医学和法律知识,一个学生必须经历很长一段时间艰苦的课程学习和训练,这种学习和训练是普通人和大学之外的人无法获得的。结果,受过大学训练的医学者和法学者被认为具有高深的理论知识和特殊的能力而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大学出现之前,医学和法律从业的职业门槛并不高。例如修道院的僧侣只要学过一点自由艺术方面的知识就可以医治疾患,世俗的人士只要有“技术”而不需要有“学识”便可给人治病,比如当时社会上充斥着大量的理发师(barbers)、手术师(Surgeons)、药剂师(apothecaries),他们都在从事医生的职业。大学出现后,随着法律和医学教学与学习的专门化,医学和法律从业者内部出现分化。受过大学教育的从业者并不希望与社会上的工匠们有同等的身份。为了取得跟律师和神学家一样平等的地位,有平等的理论体系,受过大学教育的医生试图建立一种医学哲学,治疗病人的技艺逐渐被看做是不值得医生去做的低微的事情,他们要在大学当中研究更加高深的普遍的理论,让大学成为医学知识的守护者。中世纪“医生”称呼的变化显著地反映出了这一分化过程:在中世纪早期,普通的医学从业者,常常被称为medicus,随着大学的出现,physicus这一术语逐渐替代medicus,用来指受过大学医学教育的人。[14]受过大学教育的医学者逐渐与社会上其他医学从业者如手术师、理发师、药剂师等区别开来。为了确保非大学的从业者承认其能力,大学毕业生甚至使用大学自身的权力来加强其身份和独特的地位。
这种分化因为大学组织与制度的发展以及知识的专门化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一方面,大学拥有大量的教师、图书馆和其他资源,允许开展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中世纪大学的教学语言是拉丁语,医学和法律的教科书与文献都是用拉丁文撰写的。不懂拉丁语的从业者越来越受到自身知识的局限,无法与其受过大学教育的对手竞争,只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能获得全面而深入的专业知识。因此大学教育不仅传授予高级的知识,而且大学训练也淘汰掉了大多数竞争者。另一方面,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通过设立较高的专业标准和强调职业伦理,提高了职业的门槛,限制了大学之外从业者的数量和类型,使得大学之外的实践活动在水平上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四、大学与近代职业阶层的兴起
在基督教会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社会,从理论上来说,神学是中世纪大学中最具特权地位的学科,神学家对其他领域具有监督作用,这样能保证基督教教义的正统地位。过去我们也认为中世纪的大学教育过多局限在神学领域,实际上这是极大的误解,医学和法律才是中世纪大学中更为普及的科目,尤其是法律学科是最为普及的。“为适应这种知识界的新情况或学以致用的需求,大学在整个欧洲遍地开花,人们在大学里从事理论学习。但所有的大学中,法的教育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但我们必须说,大学在法的发展中,在社会发展中(通过法的发展而发展),占有一种越来越突出的地位(简直是不可或缺)。在很大程度上,近代欧洲乃是法学院所刻意制作的一种社会想象的产物。”[15]虽然大学的学科都渗透着神学的色彩,接受神学思想的指引,但从数量上来说,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大学中教授神学。例如1385-1473年,佛罗伦萨大学的教师数量中,只有13人教授神学,但有47人教授教会法,75人教授民法,57人教授医学,129人教授人文学科。[16]即使是在神学最为强大和活跃的巴黎大学,也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接受真正的神学教育并且顺利毕业,而且标准是极其严格的。“在巴黎大学,完成神学课程和获得博士学位需要15年的时间,这种教育不可能在所有的僧侣中普及。”[17]但是法律学科则不同,雅克·韦尔热(Jacques Verger)认为:“那个时代学习文化中的主要学科,无论从数量还是社会等级上来看,都是法律。中世纪的最后几百年都是法学者的黄金时代。在一些国家里,实际上这一时代延伸到了18世纪末期。”[18]拉什达尔也说:“经院哲学和神学代表了这一时期最高的知识成就,但并不代表中世纪最广泛传播和最具实际影响的学习,法律才是中世纪大学中最为普及的科目。”[19]即使是在经院神学占主导地位的巴黎大学,虽然民法的学习曾一度遭到教皇的禁止,但教会法学习的热情依然十分高涨,因为教会法和民法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民法是教会法的直接来源之一,所以民法的学习仍然是教会法学者必不可少的知识基础。实际上,大学中教会法教师和学生与民法学家的关系要比与神学家的关系更亲密一些,后来抽象的神学甚至被放弃了,教会法远离了神学,成为与民法并驾齐驱的学科。因此,教会法学者中,越来越少的人成为神学家,而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律师。[20]
大学的法律教育不仅适应中世纪自治城市商业活动的需要,而且在中世纪教权与王权激烈斗争的政治舞台上,也满足了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双重需要。世俗方面,众多大学毕业的法律毕业生担任了中世纪城市、王室和封建领主的顾问、书记员、律师和法官,他们的劳动减少了教会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加速了社会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在宗教方面,许多主要的中世纪教皇在大学兴起之后都是教会法学家而不是神学家,法律的训练促进了基督教社会的立法和复杂等级组织的管理。教皇法庭也需要很多受过训练的骨干助理。受过大学教育的博学的法学家带来了罗马法以及他们的法律教学的经院技巧,影响了教会法的程序和实体。而且,主教法庭也需要学习宗教法的学生担任辅助职位以及各种各样的司法职位。宗教法庭的司法权到中世纪后期得以延伸,包括家庭和遗产法条款以及许多与契约和法团相关的问题。教会在事实上成为最重要的吸收大量博学的法学家的实体,因此成为了新兴法律职业的主要根据地。
一些数据可以直观地说明问题:中世纪晚期受过大学教育的主教日益增多。在15世纪和16世纪,大约90%以上的主教接受过大学教育,他们通常是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自1485年亨利七世即位,到1529年宗教改革会议召开,先后有46人任主教职位。其中6位主教是意大利人,余下的40位英格兰籍主教,有以下共同特点:(1)早年都是修道士。(2)都接受过大学教育,而且大多学习过法律。(3)已知36位获得过学位的主教中,在获得文科硕士学位以后,都继续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其中1人获得过医学博士学位,10人专修过神学,24人专修过法律,还有1人获得神学与宗教法双重博士学位。在24位专修法律的法学家中,研习罗马法的人数超过研习宗教法的人数,也有人两种法律都研习过。[21]
大学的出现不仅要求所有的法律内容,从程序到决策都要求有学术精神(mens legis),建立在证明的理性和原则的普遍性之上[22],而且大学也为西欧社会培养了大批受过系统法律教育的人才,这些人作为公证人、法官、律师、顾问、行政官、立法人进入中世纪社会各级宗教和世俗管理部门之中。从下层的公证人到上层的法学家,他们在社会上都享有可靠的地位,使得西欧社会的宗教、政治和法律机构得到不断的修整与完善,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法律人士也能够对专制统治进行有效的制衡和协调,起到规范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正如美国历史学教授威廉·鲍斯玛(William J.Bouwsma)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律师在塑造整个欧洲现代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3]
可以说,大学在近代医学和法律知识专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通过大学教育,医生和律师们不仅获得了收入,也获得了权力和声望,并且确立了一直延续到现代的职业形象。从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大学的诞生提高了医学和法律两种职业阶层在西方社会的地位,从而进一步造就了文明的社会。
注释:
①从词源上来看,英语中的“大学(university)”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universitas,意思是人的集合体。在中世纪早期,这个词并没有特别和专门指称的对象,最初可以用来泛指中世纪任何具有共同利益和享有独立合法地位的团体。逐渐地(也许是偶然地)这个词专门用在了教师和学生团体上。
②大学章程(statutes)是大学制定的有关校长及其他官员职权、教学大纲、课程、教师薪水、学生纪律、服装和住宿等方面的规定。
③12世纪萨莱诺大学组织发展的证据后来被证明是15世纪伪造的。详细参见Paul Oscar Kristeller.The School of Salerno:Its Development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Learning.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XVII(1945).164.
④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在1194年征服并洗劫了这个城市,将城市的许多居民掳为奴隶。参见Vern L Bullough.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as a Profession[M].New York:Hafner,196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