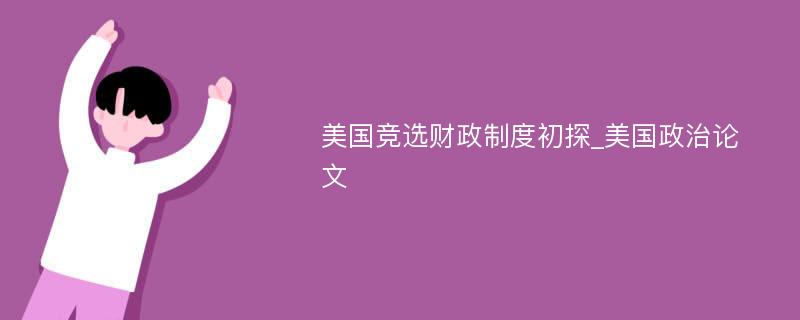
美国竞选财政制度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竞选论文,财政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竞选财政制度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几十年来,随着竞选捐赠的发展及重要捐赠工具政治行动委员会作用的日益显著,这一制度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并日益成为美国选举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人认为,美国的竞选捐赠制度导致了“富人政治”的出现;有的人则认为,限制竞选捐赠是对美国公民自由权利的限制。美国竞选财政制度何去何从,意见纷纭。事实表明,美国的政治制度并非完美无缺。笔者在此拟就美国竞选财政制度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美国的竞选捐赠和政治行动委员会
从20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竞选主要操纵在政党手中,政党控制着竞选人的提名、初选和大选等各个环节,因此也控制着竞选财政。当政党在竞选中需要大笔钱款的时候,便转向那些倾向于本党的富有者。这种竞选财政模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科学技术和媒体传播手段的发展,竞选费用支出也随之大幅度上升,竞选制度日益走向商业化。据赫伯特·亚历山大估计,1964年美国的全部竞选支出为2亿美元,到1972年上升为4.25亿美元。[1](p.11)
此期间,政党在竞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发生变化,选民由以往聚集于政党周围逐渐转向了竞选人。竞选人逐渐摆脱政党的控制,发起“自己的”竞选,以往以政党为中心的选举制度转变为以竞选人为核心的选举制度。竞选人雇用专家、媒体、乃至一些专门机构来为自己服务,并为此支付大笔款项,导致了竞选支出的上升和越来越多的竞选捐赠行为。
鉴于竞选捐赠带来的问题,美国早期的法律便限制公司集团的捐赠活动,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公司集团一直被禁止进行竞选捐赠。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了《战争劳工争议法》,禁止劳工在战时举行罢工,同时禁止劳工在战时进行竞选捐赠,将以往对公司竞选捐赠的限制扩展到工会组织。在此情况下,为了适应竞选捐赠的需要,美国产生了一种与利益集团联系密切,又与利益集团不尽相同的组织形式——政治行动委员会。公司、工会以及其他利益集团可以通过隶属于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去进行竞选捐赠活动。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塔夫脱—哈特利法》,进一步确定有关禁止工会捐赠的规定,除此之外,还禁止公司和工会组织直接为候选人提名会议和初选提供财政捐赠。然而这些法律未能奏效。《塔夫脱—哈特利法》通过后曾有六次关于捐赠活动的诉讼案被提交联邦最高法院,但联邦最高法院始终拒绝判定捐赠禁令具有合宪性。联邦最高法院的暧昧态度起到了使公司、工会政治行动委员会行为合法化的作用,于是,一系列其他组织如贸易协会、职业协会等等也陆续建立起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到1964年选举时,在国会登记的工会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达31个,非劳工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26个,其中包括“政治教育委员会”、“企业和工业政治行动委员会”和“美国医疗政治行动委员会”等组织。[2](p.118)
20世纪70年代初,依据1971年美国国会《联邦竞选法》关于建立“用于政治目的的分别隔离的资金”的规定和1972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对“管道安装工第562号工会诉美利坚合众国”一案所作的判决[2](p.120),政治行动委员会获得了合法地位,其捐赠行为具有了合宪性。此后,政治行动委员会迅速发展。1974年,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有89个,1976年增加为433个[3](p.6),1980年又猛增为1204个[4](pp.10~13)。从1974年到1997年,工会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量增加了65%,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量更骤增1700%[5](p.196)。1976年以后,合作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非股份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联系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也迅速发展起来。非联系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1977年为110个[5](p.151),1978年为165个,1980年更增加到574个[3](p.6)。20世纪80年代是政治行动委员会数量迅速增长的时期,1988年和1989年分别为4268个和4234个。90年代数量有所下降,1996年为4079个,1997年降为3875个,据1999年12月的统计为3835个。其中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量最多,占政治行动委员会总数的40.8%,捐赠款项的数额也最大。[6](p.2)
二、美国利益集团竞选捐赠的倾向与手段
美国利益集团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竞选捐赠主要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国会竞选捐赠,二是总统竞选捐赠。
关于国会竞选捐赠 利益集团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赠主要倾向于现任议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集团包括公司和贸易协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赠倾向,维护商界和企业界的经济利益是这些委员会捐赠的主要因素。从1954年到1994年,民主党不间断地控制众议院达40年之久,多数时候也控制着参议院,因此,在1994年共和党控制国会前,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竞选捐赠主要倾向于民主党现任议员,目的在于寻求“进入”国会,影响决策过程。1992年,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向众议院现任议员的钱款占其总资金的52.6%;投向参议院现任议员的钱款占其总资金的19.4%。此期间,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向众议院外竞选者的钱款仅占其总资金的6.6%,投向参议院外竞选者的钱款占5.1%[2](pp.128~129)。1992年,民主党候选人作为整体得到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总额64%的捐款,1994年,共和党得到政治行动委员会54%的捐款[5](Chapter 9,p.203)。政治行动委员会还表现出对重要议员如对国会政党领袖、国会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主席以及资深议员进行捐赠的倾向。1996年,美国国会的预算委员会主席卡西克、商业委员会主席布利利、资源委员会主席扬、交通委员会主席舒斯特、拨款委员会成员罗伯特·利文斯顿和司法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等都曾接受巨额捐款[7](Part 2,4,p.54)。如今,政治行动委员会已成为国会选举中的重要竞选资金来源,在一些竞争激烈、支持率极为接近的竞选中,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常常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总统竞选捐赠 根据美国有关总统竞选捐赠的法律,政治行动委员会不得在大选中直接给总统竞选人提供捐赠,但法律并不限制利益集团给总统竞选人提供捐赠以外的支持活动。因此,利益集团便将钱款提供给政党,间接帮助竞选人,并在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竞争中,帮助筹集资金,将自己联系人的名单提供给政党,协调组织成员的捐赠等等。此外,利益集团还将大量钱款用于电视、广播、报纸和广告等,以帮助总统竞选人。1996年,利益集团的此类支出额为320万美元,当年竞选受益最大的是竞选人乔治·布什[7](p.45)。竞选中,利益集团还采用一些间接的方式去支持竞选人,如通过宣传对某问题的立场或发行内部通讯去影响其组织成员的投票选择,动员本组织成员投票,寻求竞选服务自愿者等等。利益集团还在竞选中资助两党全国代表大会,1996年,代表有关方面利益的公司、工会和贸易协会的各种委员会以及个人,分别向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捐赠了1360万美元和1240万美元[8](pp.98~104)。如今,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尤其在初选中,钱款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总统竞选人要想获胜,必须在竞选开始前筹集大笔资金,建立强有力的竞选组织,购买媒体,以争取得到本党的竞选提名,为通往白宫铺平道路。
关于竞选捐赠手段 利益集团政治行动委员会除了一般捐赠钱款外,为避开法律的限制,还采取其他一些手段去帮助竞选人,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独立支出”。所谓独立支出是指不与竞选人或竞选官员发生直接联系的竞选开支。根据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政党有权支配这样的开支。1980年,“全国保守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刊登独立广告的形式反对自由派民主党人,开创了“独立支出”的先例。此后,竞选中的“独立支出”便成为一股潮流,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1993至1994年竞选周期中,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独立支出”总额为470万美元,占竞选支出的2.5%。[9](p.181)
(2)“捆绑”手段。所谓“捆绑”是指政治行动委员会将许多给某竞选人的捐赠款项集中起来进行捐赠。一些利益集团动员捐赠者为某竞选人提供捐赠支票,由集团负责将这些支票集中交给竞选人。这些支票毋需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账目,因此不在法律限制之列。政治行动委员会将集中起来的大笔款项送交竞选人,能够大大地博得竞选人的欢心。1994年美国非联系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埃米莉名册”组织用这一办法支持民主党妇女竞选人,捐赠的钱款达820万美元。[10](p.149)
(3)“实物”捐赠。所谓“实物”捐赠是指向竞选人捐赠钱款以外的“礼物”。一些利益集团将大笔经费支付于竞选服务,如提供复杂的计算机技术,在划分选区、争取选民的策略方面为竞选人提供帮助等等。此类工作复杂艰巨,费用高昂,竞选人自己往往难以承担,因此,此类捐赠对竞选人具有重要意义,对竞选结果也具有较大影响。
(4)使用“软钞”。在当代美国竞选财政中,变化最大的是越来越多地使用“软钞”。所谓“软钞”是指名义上非用于竞选,但实际上仍用于支持竞选的钱款。由于它在名义上非用于竞选,因而不受法律的限制。美国竞选中首先使用“软钞”的是共和党人。1980年里根竞选时利用了德克萨斯、俄亥俄等重要州的“软钞”,数额为160万美元[11](p.143)。到80年代末,为两党竞选人支出的“软钞”上升到1500万美元[12](p.1198)。“软钞”在竞选中可用于政党的行政支出,也可变换方式将钱款转给竞选人,或建立基金以购买计算机、录音机等供竞选使用。1991至1992年,两大政党支付的“软钞”占政党竞选总支出的16%,1995至1996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0%,同期两党筹集的“软钞”数额增加了近4倍。1996年,民主党人大大增加了“软钞”支出,总额达12180万美元,共和党的“软钞”支出总额则为14970万美元[11](p.142)。“软钞”的出现是美国竞选政治中追随金钱的结果,它多源于美国人称之为“肥猫”的富有者。这一现象对美国现行的代议制提出了挑战,也越来越多地引起美国政界、学术界、新闻媒体人士和美国公众的关注。
三、美国的竞选财政制度改革
在美国竞选财政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限制竞选捐赠的立法也在不断进行之中。早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就曾试图控制竞选捐赠,1867年颁布了《海军拨款法》,禁止政府官员和雇员从海军工场工人那里寻求财政资助。1883年,国会又制定了《公务员改革法》,将《海军拨款法》的规定延伸到所有政府公务员。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法律应当禁止公司对任何政治委员会或为任何政治目的所进行的捐赠”[13](p.1)。罗斯福还主张通过政党为联邦竞选人建立公共财政,但他的提案没有明确禁止公司的竞选捐赠。[14]
美国早期较为重要的竞选财政改革立法始于进步运动时期。从189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主义者反对通过巨额捐款影响政治。1907年,美国国会在州立法的基础上首次进行了改革。针对公司财富政治影响日增的状况,《蒂尔曼法》首次禁止银行或公司直接对联邦竞选人捐款。这一法律由于缺乏实施措施而未能真正发挥作用,但其规定内容的效力延续至今。1910年和1911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国会议员竞选财政公开,并对国会竞选人的竞选财政支出加以限制,反映了进步主义者“通过公开实施控制”的愿望。[9](p.5)
与以上各项法律相比,含义较鲜明的立法是1925年美国国会的《联邦腐化改革法》,这一法律在竞选人报告竞选财政状况与限制竞选基金筹集和支出方面做出了规定。根据这一法律,竞选人的竞选支出须根据以往选区的投票数量限制在25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13](p.1)。这部法律同样由于缺乏实施措施而未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是它的基本原则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国会立法中,成为美国70年代《联邦竞选法》的前身。
1940年,美国国会又制定了《哈特法修正案》,将美国公民个人每年捐赠给联邦竞选人或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钱款限制在5000美元,但并不限制个人向多个委员会捐赠,同时禁止为联邦工作的人员和隶属于联邦的企业为联邦竞选人提供捐赠。基于30年代工会向联邦竞选人捐赠款项日增的状况,1943年,美国国会的《史密斯—康纳利法》又将禁止公司、银行向联邦竞选人直接捐赠的规定延伸到工会。1947年,美国国会的《塔夫脱—哈特利法》进一步重申永久禁止工会、公司和州际银行向联邦竞选人捐赠。
1967年,前美国国会议员W·帕特·詹宁斯作为国会众议院秘书首次履行其职责,根据1925年《联邦腐化改革法》收集竞选财政报告,并报告违犯法律的行为,但司法部门对其报告置若罔闻。
由此可见,尽管20世纪以来美国国会关于竞选财政改革的立法不断,但都没有明显效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法律本身不健全、不严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缺少专门机构来监督和实施法律,以实行竞选财政公开制度。美国政府的司法部门也没有为此建立专门的预算,因此对违犯竞选财政法的行为不具备调查和惩罚机制,从而使这些法律在实际政治中成为一纸空文。
针对美国竞选捐赠中的问题,1971年,在以往立法的基础上,国会制定了《联邦竞选法》。这一法律重申了1925年《联邦腐化改革法》的原则,对联邦竞选财政制度做了全面综合的规定。要求全面、及时地公开竞选财政状况,限制竞选中媒体广告费用的数额,限制竞选人及其家庭的捐赠数额。同时允许工会和公司向其组织成员、雇员和股份持有者征求捐赠,允许工会和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使用其母机构的财政钱款,为总统竞选建立公共财政基金。1971年的《联邦竞选法》是美国竞选财政改革史上的一部重要法律,它成为1974年《联邦竞选法修正案》的前身。
1972年,尼克松连任竞选中水门丑闻的出现,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竞选财政中违法行为的关注,并对竞选中钱款的来源、财政报告制度状况以及钱款捐赠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疑问,反映出人们对竞选财政中种种不轨行为的不满,由此导致了1974年《联邦竞选法修正案》的出台。该修正案的内容包括对国会议员和总统竞选财政的种种规定,从某种意义上,可视之为一部全新的综合性的法律。这次改革和此后美国国会制定的一系列修正案,其目的主要是:
(1)使政治竞选具有更大的平等性。据统计,1972年,美国51个百万富翁在竞选中共捐赠了600万美元,其中W·克莱门特捐赠的数额最大,向理查德·尼克松捐赠了200万美元,有21个公司非法捐赠了10万美金。这种状况使人们对美国政治的平等性提出了质疑。人们提出,是否富有的人能够通过金钱去接近决策者,使决策者以立法投票作为得到巨额捐赠的交换。改革者认为,巨额捐赠创造了一种“交易”政治,损害了平等原则。正如一位改革者所说:“所有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进入政府决策过程的权利,但钱使一些公民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平等权利”[15](p.55)。《联邦竞选法修正案》的制定者试图通过改革措施去“消除腐化和腐化的出现”[15](p.55),建立一种以小数额捐赠者广泛参与和为广泛的公共利益而自愿捐赠为基础的代议制。改革者认为,大数额捐赠具有复票作用,妨害了美国选举制度中的“一人一票”原则。1974年《联邦竞选法修正案》对个人捐赠数额的限制便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
(2)保证选举制度的正直与诚实。改革者试图通过竞选资金筹集和支出的完全公开化来实现这一目标。根据法律,每名竞选人必须向竞选委员会登记注册,竞选委员会负责报告其竞选支出,通过新闻媒介使公众了解竞选人的财政状况,使竞选人的竞选财政行为处于委员会和公众的监督之下。
(3)增进竞选人、公民个人和政党的政治参与。美国各州都规定了总统竞选人支出的最高额,目的在于鼓励那些不十分有名的人参与竞选,也使选民在总统竞选的初选阶段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改革的具体目标则是对政治行动委员会、个人和政党的竞选捐赠加以限制。总结以往立法的经验教训,70年代的竞选财政制度改革着重解决竞选财政法的实施问题,建立专门的行政机构联邦选举委员会负责实施法律、监督竞选资金的筹集、接受和公开竞选财政报告,强化竞选财政公开和报告制度。
1974年《联邦竞选法修正案》的通过,使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起一种综合的控制竞选财政的制度,目的在于解决富人控制竞选财政的问题。然而,这部法律出台不久便遇到了麻烦。197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受理“巴克利诉瓦利欧”一案的判决中对《联邦竞选法修正案》中部分内容的合宪性提出了质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竞选钱款的捐赠和支出均视为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加以保护的公民权利(即自由言论权)的一种形式。联邦最高法院维持了修正案中公开竞选财政、限制个人捐款数额的规定以及有关建立总统竞选公共财政的规定,认为这些规定具有防止腐败的作用,且不影响人们通过钱款捐赠去自由表达意见。但推翻了对竞选人支出的限制(除非竞选人接受了公共财政资助),推翻了对竞选人及其家庭为自己竞选进行捐赠的限制。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认为,限制竞选人在竞选中使用自己或家庭钱款的规定,严重限制了宪法予以保护的政治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权利,提出:“竞选人与任何其他人一样,享有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中的权利去讨论公共问题,有力地不懈地去争取赢得选举”[16](pp.209~210)。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还取消了修正案中对“独立支出”数额的限制,认为,规定个人独立于竞选人的支出的最高数额是限制了人们自由表达意见的宪法权利,个人和集团帮助竞选人的支出,只要不直接向竞选人捐赠,就可以不受限制。集团可以发起对某问题表示支持的竞选活动,可以针对某问题批评某竞选人的观点,但要避免直接提出支持或反对某竞选人。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判决,事实上为建立“非联邦支出”即“软”基金奠定了基础。此类资金的筹集处于联邦法律限制范围之外,但事实上同样对竞选结果产生影响。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削弱了国会竞选财政改革的力度,为国会竞选财政改革设置了障碍,它涉及竞选财政改革措施的合宪性问题,意味着竞选财政制度改革与美国公民权利保护间的根本性冲突。
1976年和1979年,美国国会又相继修改《联邦竞选法》,试图对竞选财政制度加以调整。然而,尽管国会对竞选捐赠做出种种限制,利益集团和政治行动委员会仍然利用法律规定中的漏洞,采取迂回的办法扩大它对竞选人的捐赠。利益集团越来越多地适应于现实环境,使自己处于一种合法化的环境之中。美国的竞选财政实践表明,改革者和法律制定者的设想与法律的具体实施之间存在着距离,虽然建立了竞选财政报告和公开制度,但有关竞选人竞选财政的信息实际上十分分散,有时直到选举结束后才公布,因此,一般公众难以从中得出评价性结论。政党活动的组织者却仍在抱怨说,他们缺少足够的财政资源去有效地参与和组织联邦和州的竞选。
从1979年到1990年中期,美国的联邦竞选财政控制一直处于疲软状态,作为联邦竞选财政的管制机构联邦选举委员会未能发挥重要作用。面对竞选支出增大和有关捐赠的法律限制,竞选人、政党和利益集团相继寻求新的途径去为选举争取财政支持。随着两党在选举中的竞争日趋激烈,寻求竞选财政资助的趋势也进一步加强。尽管改革者仍不断试图通过改革,将竞选财政制度建立在小数额捐款的基础之上,但改革的效果并不乐观。
四、美国竞选财政制度的影响与改革的障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竞选财政制度和种种竞选捐赠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批评,美国人用“哪里有权力,钱就流向哪里”来形容竞选钱款与政治的关系以及钱款对竞选结果和公共政策产生的影响。改善和增进与竞选人的关系,接近当选议员,为院外活动分子立法游说创造条件,从而得以参与国会立法过程,最终影响国会决策是利益集团和富有者参与竞选捐赠的主要目的。正如一位政治行动委员会主任所说,“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如果一名国会议员的投票纪录始终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便不会再将钱投到老鼠洞里去”[10](p.151)。对竞选基金的需求也影响着竞选人的行为,他们通过支持利益集团的政策要求去获得竞选资助,以求赢得竞选或连任竞选。钱款对议员的投票选择产生着影响,对议员在立法过程中的选择起着某种引导和强化的作用,利益集团的竞选捐赠行为在许多时候左右着决策者的选择。正如记者布鲁克斯·杰克逊所说,问题“在于腐化,甚至比这更糟”,钱能“扭曲普通立法者的行为。以金钱为基础的选举和游说制度使那些提供丰厚资金的人受益……”[2](p.115)
如今在美国,人们对竞选财政制度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发展感到疑惑。政治行动委员会对国会竞选人的捐赠从1975年至1976选举年度的不到2300万美元,发展到1995至1996选举年度的43000万美元[5](p.3)。美国国会内外的改革者一直试图通过限制国会竞选支出,限制个人给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赠数额,限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赠总额,以便将竞选捐赠的政治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但由于议员自身利益需求和国会两院对控制竞选支出和集团捐赠的意见不一致,改革难以进行。
目前美国人对现行的竞选财政制度持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人们对以金钱作为竞选资源深表怀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钱可以买到席位,使竞选人赢得选举,也使利益集团买到了赢得选举的官员和议员。另一方面,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国人在选举年度中又在自愿地进行捐赠。人们一方面不相信眼前的竞选财政制度,另一方面又在支持和养育着这种制度。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决定了美国人难以在竞选财政改革问题上达成一致,因而也无法使改革真正取得成效。
归根结底,美国竞选捐赠改革的障碍在于竞选人对竞选钱款的需求和利益集团对进入国会决策过程的需求,这两种需求使强制限制利益集团捐赠的法案难以通过。然而只要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赠不受到实质性的限制,捐赠钱款就将继续在竞选和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
美国现行竞选财政制度改革的障碍还在于它涉及有关公民宪法权利的问题。一些人认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赠有助于院外活动分子与议员之间的联系,捐赠行为与院外活动分子的自由言论权利和公民向政府申诉苦情的权利相关联。禁止捐赠意味着禁止院外活动分子乃至普通公民与议员的联系,意味着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国会议员们也承认,对政治行动委员会及其捐赠行为的改革很可能引起关于合宪性的争讼,最终可能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美国政治的两难问题在竞选财政制度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竞选捐赠问题上明显地反映出来,这是美国政治体制所使然。
由于现行竞选财政制度的明显问题,美国国会关于竞选捐赠制度改革的努力还将继续。与此同时,有关竞选财政制度改革的争论也仍将继续下去。
标签:美国政治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美国最高法院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美国选举论文; 政治论文; 企业工会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美国国会论文; 法律论文; 总统竞选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