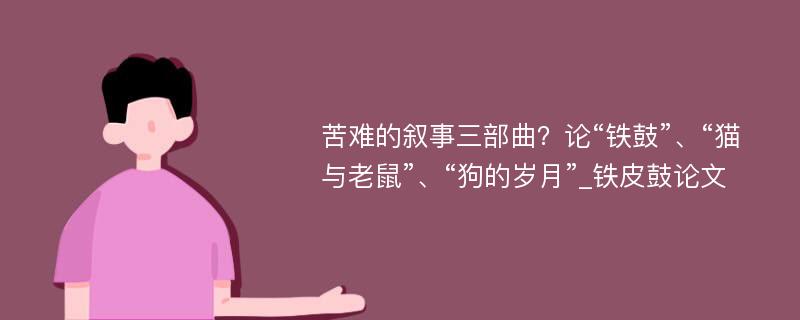
苦难的叙事三部曲?——论《铁皮鼓》、《猫与鼠》、《狗的岁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铁皮论文,苦难论文,岁月论文,三部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劲 北京外国语大学
君特·格拉斯在1964年就抱怨,人们往往忽略了《铁皮鼓》,《猫与鼠》与《狗的岁月》之间的联系①。这个所谓的联系是怎样的?真有一种联系吗?若有的话,是否主要指这三部作品的批判性呢?现在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一方面因为《狗的岁月》出版至今已近八年,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还可以把这三部作品与《局部麻醉》作进一步的比较。
单从作品的产生来看,情况一清二楚:这三本书在构思上是融为一体的。中篇小说《猫与鼠》可谓创作《狗的岁月》的副产品,这已广为人知。格拉斯自己也描述过,他在1960年左右如何动笔写一部新长篇,而后未果:“写了三百五十页,然后就写不下去了,叙事方式显得勉强和做作。短篇小说《猫与鼠》原本是这个新长篇的一部分,后来单独出来了。”②较少为人所知的是,《猫与鼠》及《狗的岁月》中的主要成分在1959年,也就是《铁皮鼓》出版的那年,就已经全部构思出来了。例如,按K.L.汤克的看法,约阿西姆·马尔克原本是《铁皮鼓》里的人物,由于所占篇幅不断增大,以至于孤立出来,只得留待日后再用③。还很明显的是,《狗的岁月》中的瓦尔特·马特恩与另两部作品中的人物,不无相似之处。首先,马特恩在《铁皮鼓》里是作为克里尔舍和那个秃头演员出现;其次,1960年,瑞士月刊《你》刊登的一篇有关格拉斯的文章中有张照片,下面注明:“君特·格拉斯在他创作《铁皮鼓》的巴黎寓所里,1959年。墙上是作家为该长篇的各章所拟的提纲。”④照片上的这两张提纲中,只有少许细节能有把握地辨认出来;不过,其中一张上面的标题异常清晰:“克利舍尔。”《铁皮鼓》里没有克利舍尔这章,这个记号莫非是指某人物和某素材,它们原本是给这第一部长篇准备的,后来却找不到用武之地?或许这已涉及到了对后来创作的长篇的第一步构思?另一个记号也很有意思:第一个提纲上标的都只是数字(页数?)第二个则密密麻麻写满了提纲,可惜大多无法辨认;这个提纲中间的大块地方写了两遍“骨头山”这个词(一个下面还划了线)。这又让人迷惑了,这究竟是一个没派上用场的《铁皮鼓》的素材,还是一个全新的构思呢?不管怎样,这是个确凿的证据,它说明《狗的岁月》中极重要的骨头山这个比喻在1959年就已酝酿出来了。
此外,难以数计的外在因素使这三部作品显得像三部曲,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统一的时间、地点:《铁皮鼓》的三篇与《狗的岁月》的三篇在时空上几乎完全一致,第一、二篇:战前和战争时期(但泽——还有格拉斯偏僻的家乡但泽一朗弗尔——但泽地区);第三篇:战后(西德)。篇幅小得多的中篇,基本上没写战前和战后时期,它在时空上与那两部长篇的第二篇一致。(与《局部麻醉》相比较就显而易见,早期作品在时空上是多么一致。在《局部麻醉》中,但泽和1945年以前的时期其实只是极少的零头,是失却的、在斯塔乌斯的回忆中变了形的过去;这部长篇的故事都发生在当前(即1967-1969年)和战后——甚至战后斯塔乌斯的“回忆”也根本不可信,(纯粹是随意的杜撰)。就各人物而言,也总使人觉得,所有人物都是一个世界里的:奥斯卡·马策拉特、扬·布朗斯基、除尘队、贝布娜、图拉·彼克利夫克、海利·皮伦茨、瓦尔特·马特恩以及很多其他角色都不只出现于一部作品;《狗的岁月》中,一次密谈讲到了奥斯卡和艾迪·阿姆热尔,《猫与鼠》的精采开头里所写的皮伦茨对马尔克的首次跟踪,在后来创作的长篇里的重要位置上又提到了;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的故事是《狗的岁月》中的重要一环,而在《猫与鼠》中只作过简要勾勒,显然,这个故事是为后来创作的《狗的岁月》保留下来了。格拉斯自觉地把业已消逝的但泽这个世界奇迹般地、生动地再现出来,这确实是值得注目的成就。因此,对格拉斯的作品有所了解的读者——无论是联邦德国人,英国人还是日本人——在阅读《狗的岁月》的头两篇时,都会有熟悉之感。
诸如此类的共同点可能是有趣而且重要的,但所有探询这三部书的内部联系的关键问题仍存而未答——例如:这三部作品有共同的主题范围,共同的风格,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视角及态度吗?换句话说:格拉斯在创作《狗的岁月》时与以前创作《铁皮鼓》时思考的是同样的问题吗?或从相反的角度来提问:《局部麻醉》与那三部作品大异其趣,由此反观那三本书,它们是不是显得像一个相对完整的综合体?“相对”这个词(它在《局部麻醉》中是个关键词)是绝不能舍去的;作为作家的格拉斯在写《铁皮鼓》和写《狗的岁月》之间迈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历程,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这点,这两部作品在某些地方判然有别;同样明显的是,早期作品中的很多主题和题材,包括最重要的,都在《局部麻醉》中改头换面地出现了;如果只着眼于一些局部,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即《狗的岁月》与《局部麻醉》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它与《铁皮鼓》的(例如就主人公而言:在阿姆热尔/马特恩这两极与牙医/斯塔乌斯这两极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对应关系;《铁皮鼓》中则没有类似的对应物)。可以作此结论:这三部作品构成的绝非一个简单划一的整体,或一部作品分成的三个连续部分(或许这是一个遗憾⑤;因此只能把它们作为相对的共同体来研究。我认为以此为前提,稍带保留地视这三部作品为三部曲,或者采用格拉斯自己的定义:共同综合体⑥。
首先,我们仅谈谈这四部看起来不像三部曲的散文体作品(包括《局部麻醉》)中的几个局部问题。无疑,格拉斯始终没有根本变化叙事结构。艾贝尔哈特·斯塔乌斯所充当的叙事动力这个角色实际上与之前的奥斯卡·马策拉特并无二致:在现实面前完全束手无策,阳萎,自称想当隐居者,因而程度不同地过着避世的生活,在“回忆中的过去”里寻求慰籍。(从这一点来看,斯塔乌斯那伺机而发作的写字台与奥斯卡的白漆金属病床是很类似的道具)。皮伦茨(《猫与鼠》)和马特恩(《狗的岁月》)里的第三篇出场时的情形也没有本质区别:两者都是被驱逐,找不到一点儿方向的怪人,他们出于不同原因,只得讲述自己那可怜的、有着暴行的过去。这样的叙事方式自然会取得多种效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讲述具有了高度的敏锐性,即不可信性。流传下来的模仿说——即直接再现可摹写的现实——被格拉斯完全打破了。他相当成功地运用了“多重反射手法”。尽管他还用“可摹写的现实这个概念,却并不把一本书中各虚构的现实像受青眯的商品一样罗列于厨窗,而是通过多重“反射”让人隐约意识到而不是直接目睹。值得注意的是,《铁皮鼓》的开头几行就已点明了这种根本性的视角,格拉斯让奥斯卡首先讲述“我一生中的事件”,然后讲的却是“我的故事”,最后甚至明确地说是“谎言”(“每当我给他讲了点编造的故事时”)。
对于忽视了此类暗示的读者,这部长篇必然丧失了其独特的氛围。首先,奥斯卡所讲的他自己的事基本上是可疑的。举两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批评家差不多都一致地轻信并承认了奥斯卡对地下室楼梯事件及多罗塔·昆格特——事件的解释;若要透彻理解这本书,则须认识到,正如奥斯卡在别处自认是在撒谎,他在这儿很可能或恰恰如此——甚至可以想象,这个大嘴侏儒并非有意从楼梯上摔下来,他在多罗塔·昆格特的死中并非无辜⑦——简言之,他的所有自我描述(出众的、自由自在的神童)不过是个发育不全、背信弃义、阳萎、甚至有智力障碍的失败者所精心编造的谎言。把奥斯卡的自述当真,就会有那种完全错误的很普遍的解释,霍卡特胡森的看法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奥斯卡)是无限自由原则的化身,这自由超越了他生下来就落入的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摆脱生理的重重束缚的幻想自由以及精神自由,以反抗社会现实的粗暴行径(等等)”⑧。
说得更确切些,奥斯卡与其说是现实的驾驭者,不如说是牺牲品。
叙事者马特恩的特点是,很想撒谎,却又迟钝愚笨得连撒谎的本事都没有(参阅《马特恩的经历》的首页,“所有淡而无味的谎言”,以及接下来马特恩在阿姆热尔/布朗克塞尔面前撒的谎)。当马特恩企图炫耀他的“马特恩的经历”时,读者已把他看穿了,因此他那四处张扬的伪英雄主义的莽撞之举所取得的效果恰与愿违:他的所作所为只是越来越无情地暴露了他的真面目。《局部麻醉》中也有类似的暴露过程(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正如《狗的岁月》里所生动刻画的那样,斯塔乌斯和马特恩本质上是同一类型的:他们都是“捣乱者”,两人——一个能言善辩,一个使用暴力——都直截了当地否认了残酷至极,却又无法抹煞的现实)。《局部麻醉》的首句就充分体现了“间接反射”的原则:读到“我讲述给我的牙医”这些话,了解格拉斯作品的读者就会立即明白“讲述”这个概念的双重内涵;因为读者知道,讲述的内容既可以是“我一生中的事件”,也完全可以是谎言。从小说起首这些话起,格拉斯就让读者看穿斯塔乌斯;通过如此敏锐、间接的叙事手法,读者就会越来越趋近于虚构的现实。斯塔乌斯被一步步地暴露无遗,很明显,牙医(与布朗克塞尔类似)对待他像处理“洋葱”一样,“一层层剥皮,洋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透明。”起初,人们还愿意倾听他那伤感的订婚故事,后来却越来越明白,这个故事不过是一个受过打击的无能者所杜撰的蹩脚的经历,权作真实经历的代替品,这个无能者和那个疗养及护理院的居住者奥斯卡有着同样绝望的孤独和畸形的内心。
中篇小说《猫与鼠》的情形十分独特而且复杂,从中能看出很多问题,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这部作品极其简洁——体裁所限,书中根本没有什么长篇大论,一切都只是点到即止;另一方面,它的叙事方式甚至比长篇中的还要间接得多。这又有两个原因:海利·皮伦茨所讲述的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这个人充满痛苦的认识及由此而生的动力都是皮伦茨不可能理解的(“他从未对我谈过自己的内心世界。我总是捉摸不透,他在想什么”。);第二,讲述跟踪阿希姆·马尔克这个故事的人,不但根本无法理解他,而且同后来塑造的瓦尔特·马特恩一样,属于受过打击、寻求平衡的追踪者类型(斯塔乌斯当然也属此类,只不过他的追踪欲在伤感而又可笑的幻想中得到了满足,正如小说倒数第二段——最长的一段——所描述的)。
叙事结构上,皮伦茨的讲述具有双重隐蔽性:揣测不到真相,他只能浑然不觉地让真相透射进来,即使他所知道的,他也复述得走了样,以便尽量掩盖自己所扮演的该隐的角色。这双重效果在十分精采的第一段里就基本有了:皮伦茨只是含糊而且不情愿地承认,是他把猫按在了马尔克的脖子上;格拉斯让他只是顺便而且毫无预感地暗示故事的真正开始,即马尔克谜一般的要学会游泳的意志(以及其它的平时回避了的):“……马尔克已经能够游泳了,有一次,……”如果看不透这个结构,读者必然会读偏这个小说的真正主旨,正如心理学家艾米尔·奥廷格尔那样,他称马尔克为有强迫性神经症,生理障碍、精神分裂的疑病患者,认为官员克洛热是可尊敬的社会秩序的明察秋毫的代表(“有节制,不乏礼貌”)。⑨实际上恰恰相反。不是官员克洛热,而正是马尔克明察秋毫,他一直是个很一般、有点虚弱、难得被同学们注意到的男孩,当他猛然认识到,自己已置身于充满威胁、荒缪至极的社会秩序,可怜的他深感震惊并转变了。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人们即可以靠阻止破坏行径(马尔克已故的父亲),也可以因为尽量造成破坏(铁十字勋章佩带者)而受嘉奖。这个终无所获的“反荒诞英雄(引用格拉斯对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人物所下的评语)身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偏偏当他为了逃离群猫而放弃由不为人知姓名的普通人所形成的保护时,却进入了群猫的视野。这种上进型逃离(此外,格拉斯的主人公几乎都逃离)未成功:没有一个孤零零的反抗者能对抗迷宫般的社会,这个社会热衷于破坏,却又太《彬彬有礼》,以至于无法容忍一个蔑视礼俗的铁十字勋章佩带者。(比较《铁皮鼓》和《狗的岁月》:梅因和马特恩都分别被冲锋队和保安军开除了——一个因为虐待猫,另一个是因为偷了钱)马尔克必然走向毁灭(从双重意义上讲):对他的具有典型性的命运作一逻辑性阐释,即他犹大般地出卖了永恒的玛特·多诺罗莎之子(此外,这个儿子住在复活节监牢里,可能死于星期五,这都不是偶然的)。还应弄明白的是,《猫与鼠》并不仅仅是个执拗的孤僻的人(这样说,不是作为心理学病例的描述)的故事;它实质上是一曲动人而又饱含诗意的耶利米哀歌,揭示了整个“群猫般”的社会制度的极端荒诞。用格拉斯自己的话来说:“马尔克的经历揭露了宗教、学校、英雄主义——整个社会,一切都跟他过不去。”⑩
叙事手法上,几乎没有例子可为三部曲的设想作论据。如果从这些作品内部蕴含的基本态度及外部形式上的表现手法来研究,情况就复杂多了——这也很自然,因为这种研究触及的是不同作品的最根本,而且极其细微的结构。
注释:
①海因里希·福姆维克:《成名者——海因里希·福姆维克拜访君特·格拉斯》,见1964年的年刊《马克鲁姆》。
②格诺·哈尔特劳普:《我们这些余存的……》;转摘自《从书到书——君特·格拉斯评论集》,格尔特·诺西兹主编(路赫特汉特,1968年版)。
③库尔特·诺塔·唐克:《君特·格拉斯》(科诺基乌姆,1965年版),54页。该文发表后,格拉斯认为文中观点是错误的;原话摘自格拉斯写给作者的信:“这里唐克的一个错误”。
④《你》总232期(1960年,六月),17页(胡果·诺策尔所写的文章《君特·格拉斯》)。
⑤例如,瓦尔特·杰斯错误地称《狗的岁月》为《铁皮鼓》的重复和扩展了的《猫与狗》的重演(见《君特·格拉斯的魔窟》,载于《时代》,63年9月6日,第17版)。
⑥摘自作者的一封信。
⑦这个论点及本文提到的很多观点,都在约翰·雷狄克的《君特·格拉斯的古怪的叙事世界:谈谈〈铁皮鼓〉〈猫与鼠〉及〈狗的岁月〉》中有充分阐述。(牛津,哲学,1970年)。
⑧H·E·霍尔特胡森:《先锋主义及现代艺术的未来》(慕尼黑,皮普[1964年]),56页。
⑨艾米尔·奥廷尔:《以君特·格拉斯的中篇〈猫与鼠〉为例来多层面地谈谈青年的犯罪问题》;转摘自《从书到书一君特·格拉斯评论集》,38-48页。
⑩摘自与作者的一次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