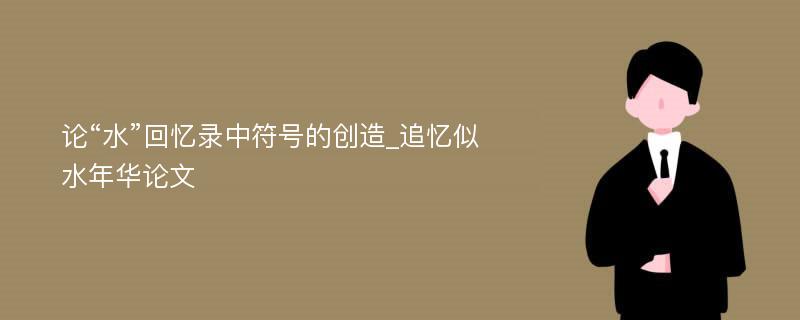
论《追忆似水年华》中符号的创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似水论文,符号论文,年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追忆似水年华》(以下简称《追忆》)出版初期,法国评论界并没有真正理解这部作品的意义。只是后来人们才渐渐发现,作者试图以特殊的方式寻找失去的时光,再次体验过去的生活,并且带领读者和自己一起去体验。一方面,作品描述了一个文人学习的过程[①]:主人公在社交世界、爱情世界、印象世界和艺术世界中不断学习,逐步认识周围的世界,了解生活的真谛;另一方面,作品也叙述了一位作家的创作历程[②]:从创作冲动到失望,再从失望到升华,其结局展现了作者进行创作的工具——符号机器。作者从艺术创作中得到某种享受,从对生活进行新的、从容不迫的、艺术性的第二次体验中获得享受。同时,这种创作旨在使过去的时光变得更容易理解,并从美学上加以透彻的思考。这些也许就是《追忆》的特性和获得成功的秘诀。
普鲁斯特的小说创作主要依靠两个形式,即“我”和时间。“我”统一了叙述视野,使人物服从于中央视角。同时,“我”没有打上明确的个性印记,具有足够的普遍性,成为一切人的我。作者有意让叙述者匿名,目的是让每个读者在书中读到自己。关于这一点,法国评论家塔迪埃在《普鲁斯特与小说》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述。时间则控制着小说的进展、故事的叙述和人物的生活。不过,从《追忆》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创作初期并未发现时间的作用,只是到了小说结尾时,在盖尔芒特家的聚会上,作者好像第一次感到:“而我自童年时代以来,一直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以致从所有那些人身上发生的变化上,我第一次发现时光的流逝,从对他们而言的时光流逝联想到我的似水年华,我不禁大惊失色。”[③]惊恐之余,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回忆,将过去的时光追寻回来,并用文字,用符号把它固定于文学作品中,使它永恒。换言之,《追忆》以符号的形式重新创造和安排时间,使过去、现在、未来融为一体,组成一个独特的时光体系,造就了《追忆》的巨大魅力。
一
任何小说都必须有一个时序。作家追踪人物的一生,重现人物的社会活动,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时光对钟表来说也许是相等的,对人则不然。在现在之中出现过去甚至将来,就使时间出现不相等的现象。如《追忆》中提及的德雷福斯事件、尼古拉二世访问法国、欧伦堡事件、俄国芭蕾舞团等,可以用历史年表作参照,是真实的时间;相反,书中人物的年龄、年龄差距、人物活动的时间大都与历史年表不相吻合,是一种想象的时间。阿尔贝蒂娜在1897年是17岁的少女,到1908年她仍然是那位妙龄少女,似乎在时间空洞里生活了十多年。时间上的这种自由性是要突出时间标志——时光符号的重要性,书中的时间多数不是某年某月某日,而是某地的某样东西,某人去某地的那天,或某人做某事的时候,如阿尔贝蒂娜的自行车、巴尔贝克的汽车、两年以后的巴尔贝克小住、莱奥尼婶婶的衰弱、凡德伊与女儿相依为命等。这种用人物、事件、物品等来表示时间的方式是创造时光符号的主要手段之一。另外,书中也使用了诸如钟点、天、季节、年等时间单位,但它们是时间的形式单位,都经过叙述者加工处理,随意将它们加快或放慢,以满足叙述的需要。这样,时序的安排就不必遵循真实时间的先后顺序,也不必顾忌叙述时间与实际时间在逻辑上是否合理,而可以按自主记忆或非自主记忆进行随意安排。既然书中的时间是用人物、物品、事件和形式时间来表达的,那么时间也就成为叙述的形式符号,提取不同的时间,对它进行加工和安排,就创造出时光符号,然后对时光符号进行系统化,构成整个作品。
从提取时间并使它成为符号的方法来看,《追忆》中有反理性法、组合法、运转法等。所谓反理性,是指作者在叙述时,不追求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不拘泥于整体与部分在表面上的和谐。传统的观念认为,要使部分具有价值,它就必须反映整体,哪怕是一个微小的部分,它也应该是整体的缩影;应该借用类比和近义等手段使作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一个充满内容和思想意义的网络,这样即使将它打碎,也能从中找出某种理性,正所谓见一斑而知全貌。然而,当时光成为作品的客体(抑或主体)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对过去时光的记忆是一堆难以粘合的碎片,是拼画中的不规则纸块,找不到它内在的统一性。如果说有什么统一的东西,那就是符号语言在不断复述自己,艺术作品的形式结构解译着它所使用的零碎材料,这些材料来自于作者不自主的模糊回忆。普鲁斯特在追寻模糊记忆的先驱时,列举了波德莱尔,然而,他却批评波德莱尔在使用这一方法时过分“自主”;相反,他似乎很赞赏夏多布里昂的感觉:“从一小方块蚕豆花盛开的田里,散发出天芥菜甜丝丝的香味;给我们送来芳馨的不是故国的微风,而是纽芬兰的狂野的风,与谪居作物没有关系。”[④]言下之意,一部以时光为主题的作品,就不应该墨守陈规,落入俗套,不必在客观性和整体性上浪费笔墨。一部有特色的作品,必须在形式上有所突破。利用模糊记忆,开发记忆深处的沉积,寻找记忆之间的结合点,是创造时光符号的最佳途径。
《追忆》中描述的观察者、朋友、哲学家、闲聊者、同性恋者、文人等人物符号,从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联系,但从深层看,却有某种辩证的理性:即在智慧的主宰下,叙述者将观察事物、发现规律、组成词语、分析观点等活动连接起来,使部分与整体、整体与部分之间建立起形式关系。作者建立了一系列的形式对立:如观察与感受、哲学与思想、思考与解译、友谊与爱情、谈话与无声表述、名词与名称、显性符号与隐性符号等:“我素来奉行一条原则,跟那些非要等到认定书写文字只是一套符号之后才想到用表音文字的人们背道而驰;多年来,我完全是在别人不受拘束地直接对我讲的那些话里,来寻觅他们真实的生活、思想的线索,结果到了这种地步,只有那些并非对事实作了理性的、分析的表述的证据,我才认为它们是有意义的。”[⑤]作者拒绝传统的大主题,如热情、科学、对话、理性、雄辩等,而通过人物的对话去观察事物、发现规律、组织文字、分析思想,编织书中各部分与整体间的关系,使整体与各部分和谐,这就是叙述理性。请看《追忆》中三个次要人物的共同点:圣卢是广交朋友的知识分子,他关于战争艺术的高论就是要用花言巧语欺骗对手;诺布瓦深谙社交界的客套和外交辞令,是玩弄政治手腕的行家里手;戈塔尔是外科医生,他用冷酷的科学语言故弄玄虚,掩饰自己胆怯懦弱的本性。这三个外表不同、甚至对立的人的共同点,就是竞相使用各自的语言符号。可见,作者通过展现符号语言的形态,揭示符号语言与人物的内在联系,探索使用符号语言的方式,以便达到作品在叙述形式上的统一性,最终实现作品风格上的一致。
组合法是创造符号的另一种常用方法。普鲁斯特在构建符号时一般采用两种组合模式:包容式和并列式,德勒兹把这两个模式比喻为纸盒与花瓶[⑥]。第一个模式采用镶嵌、包含、蕴涵等手段,建立外壳与内容的关系,如事件、人物、名字等。第二个模式采用累加、并列、衍生等手段,建立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如话语、时间、地点等。包容模式像一个能够打开的纸盒,从里面可以取出一个形状和性质都不同的东西。作者童年记忆中的屋脊线、石块的形状等,恰似一个巨大的顶盖,包容着下面的芸芸众生;夏吕斯是一个色彩斑驳、满腹狐疑、捉摸不透的人物,犹如来自远方的一件令人怀疑的包裹;名字则像个半开的盒子,里面装着它所代表的人物的品质。“那时候,盖尔芒特的名字也像一个注入了氧气或另一种气体的小球:当我终于把它戳破,放出里面的气体时,我呼吸到了那一年,那一天贡布雷的空气,空气中混杂有山楂花的香味。”或“像挤颜料管似的,从中挤出流去时光的神秘而新鲜的、被人遗忘了的细腻感情。”[⑦]在这个包容模式中,叙述者的活动就是解释,即摊开或展开与外壳相去甚远的内容。有的内容表达非现时的真理,即逝去的时光的真理,有的内容则表达现时的真理,即重现的时光的真理。名字、人物和事物中充满着内容,几乎撑破外壳,正是这些互不相同的、被打成碎片的真理构成了过去的时光。但当过去的时光在艺术中重现时,当现在的时光与从前的时光艺术地结合时,现在和过去就成为完整的和永恒的时光,封存于某个人物或某件物品之中。
并列模式像封闭的花瓶,互不对称和互不相通的部分相互共存。它们或组合成分离的两半,或并列于两“边”或两条方向相反的道路上,或像六合彩那样飞旋,把固定的彩球混合为一体。如贡布雷的两个“那边”,即酒乡梅塞格利丝那边(也叫斯万家那边)和盖尔芒特家那边相互并列,但方向相反[⑧],是两个不相通的“边”;同样,人物的面孔也有不对称的两边,就像“车两边的两个轮子,永远是不相通的”,再如在阿尔贝蒂娜的面孔中,既有信任他人的一面,又有怀疑和嫉妒他人的一面,恰似两个封闭的花瓶。在每个花瓶中,都有一个自我在生活着,在感受着,在希望着,在回忆着,在醒着或睡着。封闭花瓶意味着数量上的累加,如爱情是无数连续爱情的组合,嫉妒也是各种不同的瞬间嫉妒的总和,但是这种连续不断的形式会使人产生一种统一性的幻觉。另外,在这些封闭的各部分之间,存在一个过渡体系,即一些横跨线:如嫉妒是爱情的横跨线,旅行是地点的横跨线,睡眠是各个时间段的横跨线。封闭的花瓶时而互不相干,时而分布于两个相反的方向上,时而组成循环结构。在并列模式中,叙述者的活动不再是解释或展开内容,而是为某个时光中的自我挑选一个花瓶,从人群中挑选一位姑娘,从她脸上截取一个侧面,从她的话语中提取某些用词,从她的喜怒哀乐中撷取一丝情感,然后再挑选一个合适的“我”。不过,包容模式和并列模式有时会在同一个人物符号中体现出来,如阿尔贝蒂娜就具有这种双重性:一方面,她身上包容了海滩和海浪,与“海上的一系列印象”相关,有待我们去解析;另一方面,她身上又累加了许多人物,许多姑娘,或者说,阿尔贝蒂娜是一架观察工具,通过她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姑娘。因此,这里有两种符号,即需要解释的盒子式符号和只需选择的花瓶式符号;符号之间有一种距离,一种时间上的距离,使符号或相互包容,或相互并列;流逝的时光使事物之间产生距离,重现的时光则使相距遥远的事物连接起来。重现的时光具有超凡的结合能力,它能将日常琐事、空间、甚至时间段统一起来,这就是连接所有空间、包括时间空间的横跨线。
运转法是作者创造时光符号的另一种方法。《追忆》可以被看作一台机器,即作者边制造边使用的符号机器。马科姆·罗瑞在谈到现代艺术作品时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部交响乐,或是一部歌剧,一部西部歌剧;它也像爵士乐、像诗歌;它是一首歌曲、一出悲剧或喜剧、一出滑稽剧等……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部机器。”[⑨]普鲁斯特本人也告诫读者:不要阅读他的作品,而是把他的作品作为一个工具去阅读自己。现代作品是一部生产机器,一部生产真理的机器,它的功能在于它的运转性。它像机器那样,从人们的印象和生活中吸取原料,把它们加工成艺术印象。在《追忆》中,有三部机器生产三类不同的符号:第一部机器采用模糊回忆的素材,加工出表现重现时光的自然符号和艺术符号;第二部机器集合人物的欢乐和痛苦,制造出表现失去时光的社交符号和爱情符号;第三部机器则收集衰老、疾病、死亡等征兆,生产出表现异化和死亡的时光符号。三部机器呈立体式运转:模糊回忆为作品的第一维,通过向爱情与痛苦的转折,进入作品的第二维,又通过向异化和死亡的转折,进入作品的第三维。作品在运转中不断复制和创造自身,使全书成为一部三维的作品。
其实,社交界的欢乐和爱情的痛苦位于作品的第一层次。在这一层次上,普鲁斯特集合了社交符号和爱情符号,并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即解译这些符号的能力和智慧是在对它们进行了解和学习之后才获得的。因此,最初生产出的符号是零碎的物品、互不相通的花瓶、相互隔绝的场景;作者并没有把它们融为一体,而是按某种需要调节着它们之间的距离、空间和间隔。梦幻中见到的人物没有整体的特征,被当作零碎物品处理。这些零碎物品后来通过复现和共鸣手法得以相互联贯,在作品的运转中超越距离的分割,组合成不同的世界。而在第二层次上,作品通过非自主记忆使两段时间相互呼应,即现在的一段时间呼应过去的一段时间,引发共鸣效果。为获取这种效果,作者有时会不顾回忆的真实性,一任想象的翅膀翱翔于模糊记忆之中:“某些隐隐约约的印象曾以另一种方式撩拨着我的思维。它们似隐约的回忆,但并不隐藏往昔的某个感觉,而是一条新的真理,一个我力求揭露的可贵形象。”[⑩]这样,作者就可以根据写作的需要制造出一些时间段,通过词语的结盟使相距遥远的时间段互相呼应,实现文字机器的共鸣效果。在《重现的时光》中,共鸣层出不穷,仿佛文学机器处于最高速运转状态。第三层次则通过回忆往事突出异化和死亡的意识。在盖尔芒特家的客厅里,扭曲的面孔、破碎的动作、支离的肌肉、色彩的变化、往日的琐事等预示着死亡的到来,预示着过去的时光正在飞逝。当叙述者弯腰解开靴扣时,现在的时间段呼应出过去的时间段,出现了当年祖母弯腰的情景,出现了一个个过去时光中的“我”。对过去时光的回忆,两个时间段的呼应,使叙述者感受到时间的非逆向运动:时间从过去到现在,把一个个时间段推向远方,把一段段往事推向遗忘,把一个个人物推向死亡,像一部机器那样不停地生产着正在消逝的时间段。
这时,作品叙述的已经不是书斋文人自身的经历,而是作品本身进行的艺术实验以及文学实验的结果。所以,普鲁斯特称自己的作品是望远镜,它对别人产生效果,同时也对自身产生效果,并充满了自己孕育出的真理。普鲁斯特认为,文学机器——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生产、再现和复制时光段。乔伊斯的作品就反映出这种特点。乔伊斯善于从事物中寻找内在的秘密,在包含能指的内容中构建新的能指,在主观经历中注入新的理想意义。一部作品应该自成体系、不断创造自身的特殊意义,产生新的共鸣效果,勾勒出自然事物的珍贵形象,并在艺术中再现这些形象。正如艾柯在《开放的作品》中所说:“能指和所指像电线短路般融为一体,但就本体论而言没有什么根据,也出乎寻常。符号化的语言并不参照作品之外的客观世界,只有在作品内部才能被人理解,并受作品结构的制约。作品作为整体,将构筑它所遵循的新的语言公约,同时成为解译自身符号的钥匙。”(11)况且,作品的新意就在于它造就了一套新的语言公约。由此可见,整部《追忆》采用了三部生产作品的机器:生产零碎物品的机器、生产共鸣效果的机器和非逆向运动的机器。每台机器都生产出真理,生产出时光符号:零碎物品显示消逝的时光,共鸣显示重现的时光,非逆向运动用运转法显示时光的消逝,赋予时光符号一种统一的形式。
二
三部符号机器制造了大量的时光符号,构成了《追忆》这部作品。但这些符号是散碎的、五彩缤纷的。正如乔治·布莱所说:“普鲁斯特的世界是一个碎块世界,每一个碎块又包含着另一个由碎块组成的世界……时间上的断续性又受制于另一个更为极端的断续性,即空间上的断续性。”(12)那么,是什么东西将这些符号编织在一起的呢?用巴特的话来说,是什么新型水泥将间断的和分散的意义单位结合成统一的巨大的意群单位的呢?读者可以发现,《追忆》在展现学习历程的同时,还展现着创作的历程。学习经历了暂时的欢愉和长久的失望两个阶段,最后发现了真理,即创作;同样,创作也经历了创作冲动期和失望徘徊期,最后找到了重现过去时光的符号,发挥了作者的天赋,作品即告完成。作者根据创作的需要,重新安排时间标志,协调叙述话语,显示创作过程,使各种时光符号编织成网,服务于创作这个神圣使命。
在时间的处理上,作者采用了对比、插入和循环等方法。对比就是通过改变时间的速度、内容来表示时间的流逝。小说中的时间具有不同的速度,有时对几个星期的幸福一带而过,有时则在一瞬间的痛苦上滞留很久。为了使读者感到时间的流逝,就要改变时间的速度,使时序和时间结构具有艺术性。普鲁斯特将时间分解为不同的单位,有时让它减速,有时让它停止。在事件发生的高潮时日,如蒙儒万的那一天,阿尔贝蒂娜出逃的那一天,马丹维尔钟楼的那一天,都是时间的最强音。在某一天里,时光的辉煌中夹杂着一连串回忆、痛苦、激情,使叙述者成为长夜难眠的诗人。时间有时也有急板,如叙述者在巴尔贝克饭店第一次想亲吻阿尔贝蒂娜时,动人的场景却以突然的决裂告终:“这个从未品尝过的粉红色果子,闻起来是什么味,吃起来是什么味,我马上就会知晓!就在这时,我听到急促、延续而又刺耳的声响。阿尔贝蒂娜已经使足全身力气拉了铃。”(13)这里,作者用快慢对比表示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同时,作者还用时间标志即时间内容的对比来表现时间的流逝,他可以拨快时针,使读者在几分钟里越过数十年:如读者可以看到,叙述者昔日的情人在数页纸后已经成为八旬老妪,父亲说他已经长大的话使他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地位的变化,揭示了岁月的流逝。
时间跳跃也是表示变化的一种方法。从叙述角度说,跳跃就是作者将各时间段插入作品,或是把时间空白插入作品。一方面,各种时间的插入好似在一块土层中混杂着不同时期的沉积物,叙述伊始便预示着结尾,而结局又紧接着开场:如叙述是在《重现的时光》中回归当松维尔以后开始的,然后是叙述者在贡布雷的童年,后面又加上短暂的回归《重现的时光》;再如斯万的爱情发生在叙述者出生之前,接着是叙述者在巴黎的少年时期,后面是重返布洛涅森林。另一方面,插入空白也是安排时间的很典型的形式。如两次巴尔贝克生活之间隔着好几年的巴黎生活,斯万对奥黛特的爱情和叙述者对吉尔贝特的爱情相距15年,从结束与吉尔贝特的爱情到巴尔贝克之行,用“两年以后”便跳了过去。时间空白为重现时光作了启示准备,使之更为真实,叙述者和其他人物在我们看不见的时期内衰老了。这种方法能让作者按小说的需要巧妙自如地重组时间结构。还有一种方法是重复法,也可称之为循环法,它与时间的线性发展相对立,用以显示时间的环形结构。从叙述者在贡布雷的童年起,同样的钟点带来同样的事件,同样的人物,他的生活大多数是相似的事件和相仿的会见。在阿尔贝蒂娜死后,每天都是纪念日,“人物彼此相似,相互重复,结果是叙述时间以重复作为节奏,而重复似乎消除了时间的进展,永远回到起点。”(14)这种循环反复、螺旋上升保证了叙述向着未来进展,其间有空白,有跳跃,有加速,有减速,但总是忠实于中心人物的视野及作者的创造。读者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想象的时间,一个独特的、经过浓缩或膨胀的时间,但表面上又是历史的时间。
那么,这种时间又是怎样通过叙述而合为一体的呢?这就涉及到叙述话语的协调问题。叙述者的话语和作者的话语是相对应的,但并不相等。叙述者在书中占重要地位,但他并不能主宰作品的言语;主宰言语并进行写作的是作者。作者要面对语言的类型,将模糊回忆转换成叙述话语,改写成具有诗意的话语成分,构筑成小说客体。在时光符号中,时间上的安排构成了叙述的内在结构,而许多事件和人物的名字则构成了叙述的形式结构。特别是专有名字——人物符号为《追忆》的写作提供了充足的素材。专有名字具有三个功能:一是它的对应能力,即一个名字对应于一个参照物;二是它的本质化能力,即名字能够命名它所包含的本质;三是它的释义能力,它像被打开的盒子那样,能够展示出它所包含的所有内容。如盖尔芒特这个名字专指作者童年生活过的一个地方,而不指任何其他地方;但这个地方在作者脑海中仅仅是一个模糊的回忆,在作品中必须由盖尔芒特这个语言符号来体现它;这一符号的内涵,抑或对这一符号的解译,便成为写作的源泉。专有名字主要有人物和事件两类,从各自的角度构建叙述时间,粘合时光符号。
在《追忆》中,人物被用来标志时间。首先,人物的年龄被用来表明时间在人物身上的进展。这里,作者使用的是非固定的年龄,如青年、成年、老年等年龄范畴。较之固定的年龄标志而言,非固定的年龄常常使人们想起时间的流逝,“人是一种没有固定年龄的生物,它具有在几秒钟内突然年轻好多岁的功能,他被围在他所经历过的时间所筑成的四壁之内,……一会儿把他托到这个时代,一会儿又把他托到另一个时代。”(15)这种情况首先表现在叙述者身上,其他人物在陆续出场后也显示出这种变化。因此,人物外表,如身体、面孔等的变化也表示着时光的流逝。面貌大变的阿尔让库尔仿佛是时间的启示,使叙述者看到了时间的一部分;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的面貌显示她的高龄,既与往日相同,又与往日不同。再则,人物的语言也能反映人物的变化,体现逐渐衰老的过程。布洛克放弃了新荷马派的风尚,圣卢每隔五六年就改变他喜欢用的常用语,弗朗索瓦丝一改漂亮的外省腔调,变得南腔北调。最后,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揭示着岁月的变迁。期万和奥黛特结婚后,吹嘘他的社交关系,但已今非昔比;布洛克变成贵族,奥黛特地位下降,显示了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的规律。这些变化就是要努力标志出时间间隙的变化。作者从分割钟点出发,在更为广泛的时间中展开某一时刻的人物,不但使人物打上时间的烙印,还反过来让人物体现某一段时间,体现与时间的某种关系,成为时间的象征:弗朗索瓦丝是叙述者的童年和贡布雷,圣卢是法国小农的化身,阿尔贝蒂娜的外表时刻变化着,是提供时间镜子的女魔术师,圣卢小姐身上则汇集了所有人物的命运并且体现了时间:“无色无嗅、不可攫住的时间,可以说是为了使我能够看到它、触摸它,物质化在她的身上,把她塑造成美的杰作,与此同时在我身上,唉!却只是完成它的例行公事。”(16)由此可见,被时间创造出的人物,他的存在本身就标志着时间,作品重新安排叙述时间,刻画变化着的人物,塑造出一尊尊时间的雕像。
时间作为形式,不仅包括人物,还包括事件。每个作家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构思事件和处理事件。普鲁斯特构思事件,其目的还是为了描述时光。《追忆》中的情节是次要的,它把分散的、不为人所理解的因素结合起来,把叙述者和其他人物的不同经历聚集起来,以构成时间流逝的历程,描述叙述者发现生命意义、学习生活经验、进而描述人生的历程。如《重现的时光》中盖尔芒特家的聚会,表明了时间的命定作用,即与事件相连的时间产生了自我相遇的感受:西尔旺德认出自己的经历,斯万认出自己的经历,还有叙述者的经历都显示过这一场面。“此刻我就是这个饮酒人。我到镜子里去寻找这个饮酒人。突然,我看到他了,是一个相貌奇丑的陌生人。他也在瞪眼瞅我。”(17)这些场面表明,人物可以在时间中相遇,使人物既能发现他人的秘密,又能看到自己的变化,进而找到人物的时间标志。相遇还促成了超时间性与天赋的结合,“相遇的偶然性、对立面的压力,这是普鲁斯特的两个基本主题。准确地说,遇见的对象是符号,而符号对我们施加这种暴力。相遇的偶然性使臆想成为必不可少的。”(18)因此,相遇构成了作品中最理想的事件。我们不应根据事件的内容来确定其重要性,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与人物、天赋的关系,在于它是否通向深层,即它的意义有无空间和时间范畴。小说的真正主题不是人物的生活,而是通过生活发现一个形式体系,进而构建叙述话语。叙述者不是为了再现生活而描述,而是为了写作去观察和抓取事件;叙述者并不描述事件,而是交待人物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如盖尔芒特先生对犹太人和德雷福斯事件发表的一番议论就是典型例子。(19)重述德雷福斯事件,目的是为了展现人物对事件的观点,而不是记载历史事件,小说的真正主题是通过对事件和人物在时间中的观照,提高它们的价值,使之上升为对人的启示和对艺术的启示。
普鲁斯特在安排叙述的内在结构和形式结构之时,还对作品的创作过程作了描述。《追忆》中的故事像是一部启蒙戏剧,展现了作者从创作愿望到尝试失败,最后得以升华的全过程。这部三幕启蒙剧的框架大致如下:第一幕宣告了作者的创作愿望。少年叙述者在家庭交往中认识了许多文人和艺术家,对文学、音乐、绘画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作家贝克特的到来给他带来强烈的欢乐。当他从这位大作家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思想时,突然感到他与名人之间的距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遥远,况且,贝克特还确信他具有欣赏智力乐趣的天分,因而他受到极大的鼓舞;还有马丹维尔的钟楼,那形象显示了一种暗藏的美,不断地“爆炸,冲击着我”。于是,他决定要像贝克特那样当作家,并对将来可能做的一切充满希望。第二幕描述了作者在创作上的无能。主要以三次困境为标志:诺布瓦口若悬河,但全是谎言,使叙述者对文学产生了一种失望感;后来他看到了龚古尔日报中的一些文章,那些太表面化的内容令他望而却步,因而确信自己没有能力将感受付诸纸端;尤其严重的是,他还发现自己除了缺乏才能外,还缺乏作家应有的敏锐:在回巴黎的火车上,他发现自己对乡间的风景熟视无睹,得出他永远不会创作的结论。于是,他灰心丧气地放弃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准备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地打发余生。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当他摆脱了失望的纠缠、从心理压力下解脱出来之后,当他的学习获得累累硕果时,他的才华开始显露出来。某一天上午,当他再次去盖尔芒特伯爵夫人家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已经具备创作的能力,这就是第三幕。
第三幕占据了整个《重现的时光》,展示了作者创作天赋的实现。该幕可分为三个片断:第一片断由三次记忆恢复(圣马可、火车上看到的树、巴尔贝克)组成。在盖尔芒特公馆,有三桩小事激发了叙述者的创作激情:即院子里高低不平的鹅卵石、小汤勺的声音和一条侍者递过来的浆过的毛巾;他当时感到,这些记忆的恢复真是莫大的幸福,如果要将它们留住,或是能随意回忆起它们,那就必须弄懂它们。第二片断组成了普鲁斯特文学理论的主体,叙述者系统地探索所接收的符号,努力去理解世界和书本,把书本当作世界去探索,又把世界当作书本去读。最后一个片断是彻悟。他清醒地认识到:别人的时光在流逝,自己的时光也在流逝,时光既给了他创作的天分、创作的条件,同时也会剥夺他的创作。时光的消逝将导致生命的结束,而一旦生命结束,创作即告终止,使命也就不能完成。为了完成对时光的追寻,为了成就一部给作者带来幸福的作品,他必须开始这项艰巨的工作;他必须立即终止社交生活,与世隔绝,伏案疾书,开始他的作家生涯。
事实上,《追忆》的叙述者是一只栖息在自织的网上的蜘蛛。它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巴,而只有触角,仅对信号有反应。一旦四周有丝毫振波传来,它就会扑向目标,将目标织到自己的网上。(20)作品就是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它承载着叙述者这只蜘蛛,同时也是蜘蛛的杰作。每当蜘蛛截获一个信号,就相应地布上粘丝,使网不断增大。而且“在这些鸿篇巨制里,有些部分还只来得及拟出提纲,由于建筑师计划之宏大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完工。”(21)相反,作者则是一个超级大师。他构思了《追忆》这个前后呼应、相互映衬、不断重复的庞大形式体系,从混杂的素材中取得一种特有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把所有人物、事件等都创造成符号,即重现时光的符号,然后依照自己重新体验生活的方法及艺术审美观,将它们有秩序地、互相依赖地排列起来和融合起来。这些时光符号闪烁着同样的智慧之光,具有某种透明的一致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个字眼游离在作品之外。普鲁斯特不仅奉献给读者一部追忆生活历程的巨著,而且还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自我的工具,这便是大师手艺的高明所在。
注释:
① ⑥ (18) (20) 德勒兹《普鲁斯特与符号》,法文版,法国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11、142、25、218页。
② 巴特《普鲁斯特和名字》,见《新评论集》,索伊出版社,1972年,第121页。
③ ⑩ (16) (21) 普鲁斯特《重现的时光》,中译本下卷,徐和瑾、周国强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第535、508、594、595页。
④ 夏多布里昂《墓外回忆录》,见普鲁斯特的引文,《重现的时光》,中译本下卷,徐和瑾、周国强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第531页。
⑤ 普鲁斯特《女囚》,中译本下卷,周克希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第50页。
⑦ (17) 普鲁斯特《盖尔芒特家那边》,中译本中卷,潘丽珍、许渊冲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第4、97页。
⑧ 普鲁斯特《在斯万家那边》,中译本上卷,李恒基译,译林出版社三卷版,1994年,第80页。
⑨ 马科姆·罗瑞《词语的选择》,德诺埃勒出版社,第86页。
(11) 艾柯《开放的作品》,巴黎索伊出版社,1971年,第231页。
(12) 乔治·布莱《普鲁斯特的空间》,法文版,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3年,第54页。
(13) 普鲁斯特《在少女们身旁》,中译本上卷,袁树仁译,译林出版社三卷版,1994年,第543页。
(14) 塔迪埃《普鲁斯特和小说》,中译本,桂裕芳、王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309页。
(15) 普鲁斯特《女逃亡者》,中译本下卷,刘方、陆秉慧译,译林出版社三卷版,1994年,第352—353页。
(19) 普鲁斯特《索多姆和戈摩尔》,中译本中卷,许钧、杨松河译,译林出版社三卷版,1994年,第393—3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