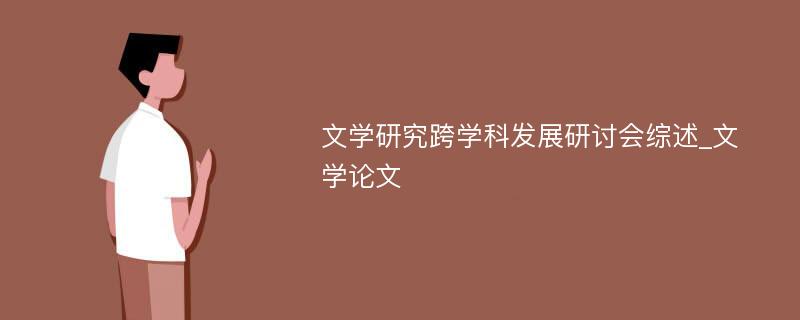
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发展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讨会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3月27日“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发展研讨会暨《文学评论》编委会”在南京金陵饭店召开。这次会议由《文学评论》编辑部与南京大学中文系共同主办。
新时期以来,尤其90年代末以来,在文学研究坚持自身研究的前提下,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研究以及广泛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成了时代的发展潮流,面对这个潮流和态势,由这些文学研究中各自所在研究领域的专家和权威来共同探讨这其中的得与失,不仅是及时的,而且也是意义重大的。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就以下四个方面即何谓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发展、如何跨学科、跨学科的限度及方法以及跨学科的好处进行了热烈有效的讨论。
一、何谓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发展及跨学科的几种分布方式
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章培恒先生认为,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发展主要指两种情况,一是指文学内部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二是指文学研究与文学研究以外的联系。对于前者如搞古代文学的学者了解搞现代文学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看法,以及搞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学一些中外的文学理论。对于后者指把文学研究纳入到整个文化中去考察。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莫砺锋先生认为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发展有两种含义,这两种含义的不同是由“学科”这一词自身在哪个意义上讲引起的。如果说这里的“学科”是指二级学科,那么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主要指文学内部之间的关系;如果指的是一级学科,那么这里的跨学科主要指文学与文学之外如文学与历史学、哲学、艺术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人文的关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中文系教授蒋述卓先生认为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是一种学术事业,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利用相关学科知识来为自己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方法,从而拓宽自己学术研究视野,深化文学研究。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首先指出,他所理解的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是指文学与语言学、艺术学甚至数学等学科的交叉,这种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有几种分布方式:一是阅读兴趣所致造成跨学科的,搞文学研究的学者愿意多读点其他学科领域的书,这种方式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很多搞文学研究的学者往往精通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二是跨学科专指文学研究者论述范围而说的,作为论述范围的跨学科如今日渐时尚。三是作为研究视野和理论预设的跨学科,这一点在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中最切实可行,也最具实效性。上海社科院的《社会科学报》主编许明先生也强调了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主要指研究者研究视域和方法的多学科,而不是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多学科。
二、如何跨学科及跨学科的具体案例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赵园研究员认为,跨学科研究主要是在相关学科的交叉处突破,她认为在跨学科研究时要考虑两点:一是应先考虑本学科发展到什么水平、本学科状况如何,目前就现代文学研究状况来说,首要的是要反对这门学科的平庸化和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平面化,提高该学科的专业水平,现在似乎还不具备鼓励该学科去跨学科,她期待多学科中的各个学科发展,也期待象《文学评论》这样的杂志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贡献;二是那些提倡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者首先要改变自身的专业知识状况才能有资格和条件进入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陆贵山先生认为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是必要的,尤其在文学自身研究陷入窘境时,但他也认为在跨学科研究时要意识到自己的专长,要在自己所擅长的专业领域内研究,不要轻易转移阵地,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专长和优势,同时研究问题要具体,要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自身特性出发。章培恒先生认为文学内部的跨学科研究可以表现为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贯穿,即搞古代文学的学者应了解搞现代文学的学者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看法,搞现代文学的学者也应重视古代文学以及搞中国古代文学学者的看法,以便双方在某一问题上融会和沟通。比如说,搞现代文学的学者往往认同鲁迅先生和朱自清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看法而没有征求搞古代文学学者的看法,鲁迅先生对唐宋八大家尤其韩愈持批判态度,朱自清先生则有《荷塘月色》中赞美了六朝梁元帝的美文《采莲赋》,但搞古代文学的学者则沿袭明清以来的传统,对唐宋八大家持厚爱态度,而对六朝美文则沿袭白居易观点持否定态度。这样,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就存有分歧,这种分歧就需要在跨学科的研究中来解决。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则以自己的治学实践谈到了如何跨学科。杨义先生先前治中国现代文学史,写有三卷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后来转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中国叙事学》等成果问世。他认为把古典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打通之后,文学研究中各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交叉效应就出来了,并且这种交叉产生了新的思维,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创新的空间。最近他在研究文学史与图画的关系。他认为过去研究文学史只注重文字材料而忽略图像材料,现在他把文字材料和图像材料结合起来重新研究中国文学史,目的是打通文学史与美术史、版画史、文明史之间的壁垒,让各个学科融会贯通,相互增益。蒋述卓先生认为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已成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态势。我们对这种态势要持宽容态度,但在跨学科操作时要胆大心细,要有自己本专业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同时对所跨的其他学科也应有所了解,以免漏洞百出。
三、跨学科的限度及方法论问题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元迈先生不反对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发展,但他认为这里有个限度的问题,这个限度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跨学科研究的动力出自我们研究对象的需要,而不是赶时髦;二是跨学科研究最终是要返回到文本中来,要强调文学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他基本上对跨学科研究持保守和谨慎的态度。陈平原先生认为跨学科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所有文学研究者的学科延伸就是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陈平原甚至认为,若是文学内部自身研究方向的调整如从中国现代文学延伸到中国古代文学,这不叫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而是文学研究的多专业,因为这两者都是属于文学内部自身的;同样,从文学研究转到其他领域研究,这不是跨学科而是跳学科。陈平原还认为,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发展成了一个潮流,但往往是名声好听,落实很难。究其大略,跟研究者自身对跨学科的限度以及跨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弊端认识不足有关系。以北大的文科实验班为例:北大文科实验班的学生进校后不分专业,所谓要文史哲打通,等两年后再分专业,但实际效果是很多学生知识面确实很宽,但“汗漫无所不往”,对某个专业知识的了解仅仅是一种概论性的了解,叫他们写杂文、文化随笔可以,但做专业不行,原因就在于他们一开始就跨学科发展,而没立足于某一点或某一个专业作深入的了解和延伸。由于他们从中学的教科书中汲取的知识很有限,一下子叫他们跨学科甚至打通中西文明界限不符合实际。这种情况在提倡跨学科研究的部分学者中也存在。陈平原还认为,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学者还应向所跨专业的学者请教,必要的话自己还该亲自动手做所跨专业领域的论文,体会该专业的运思模式和学术规范,并得到该专业领域专家的认同。杨义先生认为他从中国现代文学跨到中国古代文学这一领域后,他发现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就不太一样。他在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时就请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曹道衡先生把关。赵园先生则不认同陈平原先生提出的在跨学科时要向所跨专业领域内的专家学习并得到他们认同的观点。赵园先生曾用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明清士大夫这一特殊阶层,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她认为她在研究这一课题时是向史学学习的,但她所得出来的结论却并不一定要征求史学界的意见,她认为如果该研究对于相关学科提供了启示,开启了新的思路,那么该研究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就不要管它是属于哪个学科领域的,我们也没有必要用别的学科尺度来丈量它。
对于跨学科的方法论问题,陈平原先生认为文学研究者在跨学科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一方面要适应专业化的大潮,另一方面则要持重平衡于学科之间;2、以课题为中心,自然延伸知识;3、自我设置限制和边界,不要为跨而跨。陈平原还强调,跨学科中的“跨”主要指自身的知识和理论视野跨越了本学科知识和理论,而不是自身论述范围的跨,跨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要强调我的问题意识,推导出原来学科得不出来的结论。
莫砺锋先生认为,现时代的学者面临着双重困难,一是学科分工已成大趋势,自身所研究的专业的文献数量在剧增;二是每门学科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的跨学科研究要最终落实到具体领域和具体问题中来,我们并不需要无原则的跨学科知识,我们需要的是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和解决某一学术问题的某一种方法,而不是十八般武器和方法都使用。
四、跨学科的好处
章培恒先生认为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有它的好处,尤其把文学研究放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中即与文学研究之外的联系中考察,会有助于看清文学自身的特点,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这样也会有助于推进其他学科发展。他认为美国的大学把中国文学研究放在东亚系作为东亚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日本和新加坡大学对文学系的改革,这些做法实际上就是试图把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把文学研究纳入到整个文化研究范围内。杨义先生认为西方文明史离不开古希腊的雕塑和文艺复兴的绘画,同样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也离不开图片,他自己就把图像作为新文学史的资料来运用。由于引进了图像研究,先前文学史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得以澄清,某些不充分有力的观点和结论也得以加强。如上世纪20年代中期出版的由郑振铎先生编的《小说月报》的第一幅图是“孔子寻道像”,这一图像的出现就引人寻味,要知道10年前《新青年》杂志是反中国传统文化反孔子反得最厉害的,这小小的一张图已暗含了当时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已有所调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先生认为,文学研究中的多学科发展,实质上是一个学术视野转换的问题,它会扩充我们文学研究的空间,由于从多个侧面关注文学本身,有利于我们深入探讨文学自身,看清文学自身的方方面面。如他所提倡的文化诗学研究,就是避免单一的政治、社会和文学批评,而是把文化视野和文学自身的诗情画意、文学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研究。蒋述卓先生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把文学放到文化大视野中去关照,避免了学术研究中盲人摸象的后果,提高了对文学的整体关照意识,扩展了自身的学术视野。他自己本人就从宗教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文学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蓝棣之先生则介绍了清华大学跨学科的情况,认为跨学科成了学术研究的一种必然趋势,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有助于我们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在跨学科过程中文学相对于其他学科它的意义何在。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科学报》的主编许明先生提出了一个我们文学研究者值得反思的问题,即我们文学研究为什么守不住,要跨行、跨专业,而在其他研究领域谈跨学科、跨专业总是小心翼翼。这里面既有文学研究专业性不强、学科自身边界模糊有关系,也牵涉到我们治学过程中学术规范问题。童庆炳先生介绍了他的博士生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如何遵守学术规范问题。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健先生还专门谈到了与学术规范有关的学术腐败问题。
总的来说,这次会议的召开对我们重新认识20世纪80年代美学领域中的科学主义倾向,近期讨论的文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建立大文学史观念(现当代文学的合流以及现当代文学如何与近代文学、古代文学沟通)和评估刚刚兴起的文化研究、文化诗学研究等都大有好处。
这次会议本身也是文学内部自身的一次跨学科讨论的尝试,搞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的各个专业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坐在一起商讨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发展大略。这次会议的成功以及讨论本身的卓有成效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学研究跨学科发展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因为各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之所以相互之间对话成功是因为他们自身知识结构中就有跨学科的视野和理论水平,有了这样的一个知识和理论平台,他们讨论问题时就能相互激荡、启示并进一步深入。稍微有些遗憾的是,有些与会者已意识到了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发展在19世纪以来就开始存在,如文学中的神话学和人类学研究,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在中国古代也已有之,但与会者没有重点凸显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其与以往的不同,与会者对各学科以及文学这门学科是如何设置的以及这种设置的得与失也深入反思不够。但不管怎样,这次会议是成功的,也是卓有成效的,它必将推动和促进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