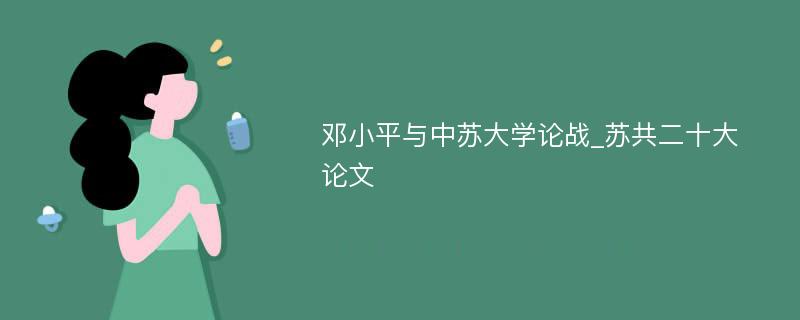
邓小平与中苏大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苏论文,大论战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D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8)01-0032-12
一、“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
邓小平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担任此职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这期间,正是中苏关系复杂多变的一个时期,其中最大的事件便是中苏两党之间发生的大论战。由于处在总书记的位子上,邓小平不仅亲历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与论战,而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①
(一)以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参加苏共二十大,直接听取苏方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通报,并亲自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汇报情况
1956年2月,邓小平以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出席苏共二十大。其间,邓小平的如下几点表现得特别突出:一、对朱德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六周年电视讲话稿提出修改意见:不要光讲苏联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还要讲条约签订六年来两国的互相合作与支持;讲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时要注意分寸。二、在中共代表团内部讨论时,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提法发表了不同看法②。三、直接听取苏方向中方通报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秘密报告的情况后,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③。但在中方代表团私下议论时则明确表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人物④。四、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下午,朱德应邀出席一个工厂举行的庆祝二十大闭幕的群众大会,邓小平在对讲稿提意见时说:讲话不要对苏共二十大评价过高⑤。五、苏共二十大后,朱德率团继续在苏联进行友好访问,邓小平回国直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汇报情况⑥。
此后,经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即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既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随后,毛泽东在一系列内部讲话中明确表达了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的不同看法。围绕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中苏两党很快便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之中。在这场争论中,邓小平不仅见证了中苏分歧直至论战的全过程,而且是争论中中方的主角之一。
(二)以总书记的身份积极参加或主持了对苏争论和论战的一系列相关文件的起草工作
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有针对性地写一篇文章,以表明中方的态度。该文后来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题发表,邓小平直接组织并亲自参与了文章的讨论修改。在讨论中,邓小平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主要是从斯大林个人性格方面讲的,但个人性格并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在这么长的时期内犯了一系列错误。不能把斯大林的错误都归结为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还反复强调,文章应突出中共历来提倡的与个人崇拜相对立的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⑦。这些观点在文中都有明确的表述。
196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撰文对赫鲁晓夫进行有组织的反击。纪念列宁的重头文章主要有三篇,即由胡乔木牵头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由陈伯达牵头撰写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和由陆定一牵头准备的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述工作都是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进行的。邓小平曾多次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编辑列宁文章的小册子以及上述三篇文章的分工、撰写思路、中心思想、初稿和定稿等问题。后来这三篇文章又合编成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印成中、英、俄、德、日、法文公开发行,引起很大反响。
在同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中苏斗争空前激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与赫鲁晓夫直接交锋,而在幕后指导代表团进行斗争的是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最后作决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⑧。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以及会议前后,邓小平直接领导了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答复信》经过反复酝酿和修改,并在书记处会议上多次讨论。在北戴河会议上,邓小平讲话指出:对赫鲁晓夫,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照他的办,跟着他搞修正主义;一个办法是顶住,坚持原则,即使只剩下我们一家,也坚持到底⑨。《答复信》定稿后,由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并把《答复信》交给了他。
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方先后发表七篇论战文章,邓小平主持或参加了这些文章的修改。如12月1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认为“写得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⑩。12月29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给毛泽东审定,并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毛泽东在批语中认为“写得好,题目也是适当的”(11)。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详细提出了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问题。4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起草复信的问题,邓小平是这项工作的直接主持人。这封复信的起草相当艰难,书记处进行了反复讨论,最后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据邓小平本人讲,“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用了“将近七十天。这个文件,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12)。这封信便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又名《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著名的《二十五条》。
1962年底,中共中央组成了一个非正式写作班子,于1963年2月正式定名为“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批判苏共的一系列重要评论文章都是出自该写作班子之手。这个小组的组长虽然是康生,但实际工作是由邓小平主持的。小组写成的文稿一般都是先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再送常委审定。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即通常所说的“九评”。这些文章一般都是由毛泽东点题,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主持下由中央反修文件小组反复酝酿、修改写成的。文章初稿先送邓小平审阅,并在邓小平主持下由小组全体会议讨论。讨论的时候一般是逐段地边读、边议、边修改。这样反复讨论修改后的稿子,才送毛泽东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审议。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在主持“九评”写作工作中的关键作用。
(三)与苏共进行直接、公开的争论和谈判
1957年11月,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随毛泽东访苏。代表团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就《各国共产党共同宣言》问题与苏方进行谈判。由于中方对苏方提供的《共同宣言》第二稿仍不满意,中共代表团遂在邓小平主持下日夜奋战,边起草边讨论,不到两天便拿出了一个初稿。该稿经毛泽东审定后交给苏共中央。此后,邓小平率中方代表,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方代表用长达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宣言草案进行逐页讨论,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争论激烈。例如,中共同意把苏共二十大写进莫斯科宣言,同时在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得到了苏共一定程度的让步。但中共的妥协只是形式上、文字上的,邓小平后来在总结情况时说:在宣言中写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是讲大会的决议。《宣言》中说,“不但对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这是肯定的;“而且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这个评价比较高,但也可以作各种解释,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短句,即“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把它扣死了,把它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发展”这个短句上。当然,苏共二十大最好能够完全去掉,但在目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我们作了这么一个让步,又作了这么一个限制,就取得了苏共支持我们对苏共二十大其他问题上的观点的修改。这还是值得的(13)。
1960年9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在前后举行的五次会谈中,双方互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10月,26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邓小平再次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起草委员会会议。经过三个星期的当面交锋,最后达成的协议终于删去了中方坚持要求删除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内容。11月,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正副团长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会议达成妥协。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向全会作关于1960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情况的报告(14)。1963年7月,邓小平再次率团赴苏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方代表团谈判。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团的发言,除在国内准备的一个综合性提纲外,基本上都是临时准备的。其工作方式是:代表团成员在邓小平主持下商定每次的发言要点,随后由顾问们集体讨论撰写,然后送邓小平和代表团审阅定稿。会谈仍是不欢而散。此后,中苏两党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交锋逐渐为连篇累牍、铺天盖地的笔墨官司所代替。
对于邓小平在与苏方谈判和争论中的表现,中苏双方有着大体一致的看法。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谈到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作用:“我们党有九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方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你这根棍子是出名了”;“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15)。赫鲁晓夫也承认邓小平“很厉害”,“是一个重量级拳师”(16)。
总体上看,邓小平在中苏大论战中是中方的主角之一,如果说毛泽东是这场论战的中方主帅的话,邓小平就是中方的主将兼总指挥。邓小平在论战中的表现深得毛泽东赏识,也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得以东山再起的资本。因为在毛泽东看来,邓小平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促使毛泽东作出这一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17)。
二、“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
中苏论战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当年直接指挥中苏论战的主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作为“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对自己当年亲身经历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苏论战进行了深刻反思。
(一)“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反对得对了”,但就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本身而言,“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我们有些东西今天回过头看也站不住脚”
在反思中,邓小平把当年的那场争论明确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政治领域干涉与反干涉的恩恩怨怨,其二是意识形态领域理论争论的是是非非。当年的论战,实际上是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搅和在了一起。
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国家间关系到正常国家间关系的痛苦蜕变过程。就中苏关系而言,正是在这一磨合过程中,苏联急剧膨胀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发生了强烈碰撞。斯大林时期,损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也一直心存芥蒂,用毛泽东的话说:“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对他就不怎么样”,“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18);“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这些事情想起来就有气”(19);“讲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火”(20)。但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斯大林,在处理对华关系和中苏两党关系时相对比较谨慎。从中国国家利益考量,毛泽东对斯大林一些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也委曲求全,隐忍未发。
当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以赫鲁晓夫赤裸裸的、咄咄逼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淤积在中国领导人内心深处的愤怒便勃然爆发了。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在事先不照会兄弟党的情况下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不管这种批判的后果是消极还是积极,都说明苏共骨子里还是以“老子党”自居,压根儿就没把兄弟党放在眼里,更何况在随后接连出现的诸如联合舰队问题、台海危机问题、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问题,以及公开批评指责中国国内政策和外交路线等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赫鲁晓夫的信口开河一再触怒毛泽东。这样,随着两党理论分歧的加深,意识形态争论便越来越多地掺入了干涉与反干涉、控制与反控制的因素。对中共而言,愤然而起与苏共论战,所争的并不单单是理论上的大是大非,而是决不允许赫鲁晓夫染指中国的内政和主权,决不允许苏联以势压人、强加于人,决不允许苏共垄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专利权。从这个层面上说,中苏两党冲突愈演愈烈的实质,就在于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却“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中苏之间的问题说穿了就是赫鲁晓夫时期就想控制我们,把我们套在它的战车上,我们抵制并拒绝了”(21)。
今天,我们只有把中苏论战放在当时特殊的国际关系与中苏关系背景下,才能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所特有的政治敏感和激烈反应。后来,邓小平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22)。
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本身,邓小平后来的态度始终比较明确:“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我们有些东西今天回过头来看也站不住脚”;“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很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23)。邓小平表达了至少这样几层意思:
其一,以“九评”为核心的理论观点从总体上应该否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24),“包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也是‘左’的”(25)。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九评”是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上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制定“反修防修”战略的,是立足于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大战迟早会爆发这一基本判断来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中苏论战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诱因,贯穿于“九评”的“反修防修”大思路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九评”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以及我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因此,“九评”的总体思路是不应当肯定的。
其二,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26);“在我们同东欧各国各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有相当的责任。我们在相当一个时候,对东欧各国各党所处的特殊环境理解得不够”(27)。邓小平后来说过:“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28)我们“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政策,同样也要尊重别的国家、别的党的实际”。(29)
其三,中苏两党在大论战中“都讲了许多空话”。尽管双方都信誓旦旦地认为自己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引经据典地搬出“老祖宗”以论证对方的错误,但事实上,“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同样,我们过去的认识也“不是完全清醒的”(30),也就是说,在当年的论战中,双方都是在隔空喊话,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上并不对症,当然只能放空炮,讲空话。
其四,在论战中,苏共的根本错误在于以自己为中心发号施令,中共的根本错误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去评判国际共运的是非。至于论战中双方的具体观点,则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例如,虽然毛泽东把苏联和南斯拉夫当时为搞活经济所采取的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统统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但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警惕“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这一论断背后蕴涵的东西要比那些以歪曲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深刻得多,也复杂得多。尽管毛泽东最终也没能跳出斯大林模式的窠臼,但他提出“以苏为鉴”,试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仍可看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步。今天反思“九评”,不能在倒掉污水的同时也把婴儿一起倒掉。这或许正是邓小平针对当年那场论战,说“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很正确的”(31)这句话的深意。
(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32)
这里所谓的“苦头”,就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遭遇的种种曲折,其中就包括中苏论战。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针对许多相关问题提出的论点,就其本身来看,并不是直接针对中苏大论战所作的评论,但显然吸取了论战的经验和教训。当然,对于这场论战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一方,而是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高度对中苏双方言与行的深刻反思。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评价毛泽东,不仅涉及毛泽东个人,也“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表示,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33)。邓小平在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所面临的,与当初赫鲁晓夫如何对待斯大林问题如出一辙,斯大林问题也是中苏论战中双方争执的一个主要问题。不难看出,邓小平吸取了赫鲁晓夫处理斯大林问题的教训,并就中苏论战中双方的观点进行了认真反思。
公开论战的方式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更容易激化矛盾。中苏双方当年都曾为弥补裂痕进行了多种尝试和努力,但在剑拔弩张的论战气氛下,任何一方试图改变对方的努力都只能反过来加剧彼此间的隔阂、猜忌与敌意。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在谈到同外国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问题时指出:“政治问题上要维持和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对他们的理论、思想观点,我们不替他们宣传。他们自己宣传什么,主张什么,我们不作评论,不同他们争论,更不要像过去那样公开地批评他们。是对是错,由他们自己去判断。”(34)邓小平后来曾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应该说,这一“发明”不只是针对国内不同意见分歧的,也是针对国际上兄弟党对我们改革开放政策的不同看法的。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当一些党对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时,我们没有再同它们进行论战。这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政治智慧,一种政治艺术。实践表明,改革开放实际绩效的说服力,远比隔空喊话的口水战要强大得多。“不搞争论”是对大论战方式的直接否定。
“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不当头”也是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教训。从两大阵营对抗的基点出发,毛泽东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必须要有一个“首”,而这个“首”只能是苏联。毛泽东多次使用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等概念。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使用了“以苏为首”的提法,并对反对使用这一提法的波兰等国进行了说服工作。后来,“以苏为首”问题成了中苏双方争执的问题之一。毛泽东认为“为首”不过是“召集会议的人”,而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共不能既奉苏联为首而又处处与苏共唱对台戏。实践表明,中方对苏方在“为首”过程中表现出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极为不满,而苏共领导人的心情也并不愉快,感觉中共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另一方面“向苏联脸上吐痰”。毛泽东提出让苏联当头,主要是中国经验少,实力小,“没有这个资格”,“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35)。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认识显然更深了一层。在邓小平看来,“不当头”并不仅仅是一种韬晦之术。“力量不够”固然是“当不起头”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这一认识不仅来自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也是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中苏论战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
与此相关的是邓小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论的否定。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曾把共产国际视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其后又把苏联看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虽然后来苏方一再提出改变这一提法,但中共中央直到1960年底莫斯科会议期间才最终同意。其间,中共积极维护了苏联的“中心”地位,例如,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积极工作和中国党的坚持,以苏共为中心才得以写进1957年《莫斯科宣言》;苏共二十一大召开前,针对苏共拟在报告中取消以苏为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为中心的提法,中共代表团明确表示不赞成,并最终得到了苏方的让步(36)。中苏论战全面升级之后,中共不再坚持以苏联为中心,但在继之而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则公开宣布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邓小平在反思社会主义国家党际关系的曲折发展时指出:“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任何大党和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37)。
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是希望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遗憾的是,在中苏论战的背景下,这一探索后来逐步走向了反面,走上了一条比斯大林模式更“左”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后来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38)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既是毛泽东未能完成的探索的继续,也是对“九评”理论基础的根本颠覆。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观,是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形成的,其总的指导思想是“左”,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被当作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加以批判的东西,有的直接来自“九评”的一些结论,有的是从这些结论中推演出来的。如果肯定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那种社会主义理念,就必然要否定而且也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必然要否定而且也不可能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反过来也可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从根本上对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理念的否定。
首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彻底抛弃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认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39);“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一褒一贬之间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模式。“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因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也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40),所以必须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其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就必须对总的国际局势作出新的判断。“讲战争的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新的判断就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41)。这个判断修正了“九评”所坚持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传统战争与和平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一判断之上的。
再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路,还必须对总的国内局势作出新的判断。“九评”的一个基本支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结果,“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42)。改革开放以后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了“九评”所依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否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它既“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搞清楚”(43)。
最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彻底否定“九评”的自我封闭主张,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一种封闭形态的社会主义,其封闭性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社会主义因素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它必须在“空地上”创造新的经济形式。这种理论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一切资本主义的因素,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思想观念的,都要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以便建立起“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对外,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与整个世界市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其“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以及“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出现(44)。从两个平行、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出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便不再有和平共处的可能。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中断了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甚至在西方科技革命蓬勃开展之后,自身生产力已十分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拒绝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拒绝实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政策。封闭形态的社会主义,无论其理论还是实践,集中到一点,就是认定搞社会主义必须绝对排斥资本主义,必须同资本主义体系绝对对立。这一认识严重制约了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苏论战时期,我们甚至把赫鲁晓夫访美期间接见企业代表时所说的“要在工业、农业方面学习美国,学习美国的利润原则,要采取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法”也斥之为“假共产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首先,从思想层面来看,我们基本上能够用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当代资本主义这个“天敌”,对改革开放背景下出现的新事物不再动辄上纲上线,斥之为“资本主义复辟”;对“资本主义的”东西卷土重来能够冷静对待,不再简单地把资本主义与“腐朽”、“罪恶”等划等号;开始更多地从共性方面看待对方,强调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属于人类文明成果的东西,强调全球化背景下两种主义和两种制度之间的共存、交流与合作。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5)其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重新解读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将会长期共存,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还要发展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和平共处、合作交流、和平竞争已逐渐成为两种制度相互关系的基本态势。正是在总结过去处理同资本主义世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而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46)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②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④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
⑤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第88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6页。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第6—7、8、18—19、21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68、1086页。
⑨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40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92、1264—1266、1277页。
(11)同上。
(12)同上。
(13)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60、97—98、153—154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93、1117页。
(15)吴冷西:《十年论战》,第440、624、717、738页。
(16)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18)《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19)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3页。
(2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页。
(21)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3、294—295页。
(2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246、272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25)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27)《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2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83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63页。
(3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72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5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301、299、301—302、344、353、347页。
(3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79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25—626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71、203—204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37、191页。
(38)同上,第261页。
(3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7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203、373、178页。
(41)《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3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
(4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57页。
(44)《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
(4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
标签:苏共二十大论文; 斯大林论文;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论文; 中苏论战论文; 邓小平论文;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赫鲁晓夫改革论文; 邓小平主席论文; 中苏关系论文; 中苏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毛泽东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莫斯科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