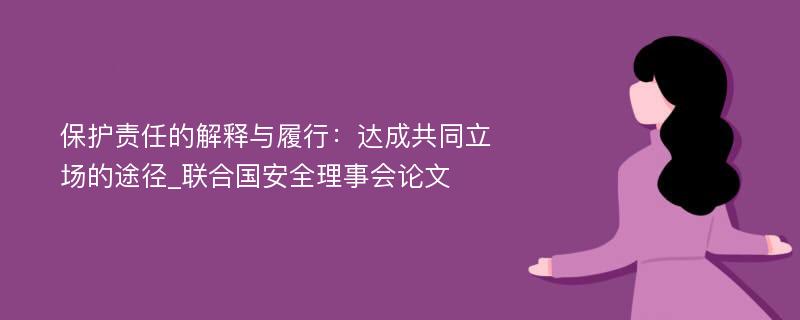
诠释与落实“保护的责任”:通往共同点的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点论文,途径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保护的责任”一词源于2001年“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ICISS)的报告。之后,该提法持续不断地引起关注,并被多角度地视为一种观念、一种规范、一项原则、一个政策框架,以及一种信条等。“保护的责任”旨在应对非国家武装力量滥杀民众这一反复出现的现实世界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鉴于与之相关的主权、干涉和国际社会义务等概念不断演变,“保护的责任”也派生出诸多规范、法律和政治问题。 13年以来,尽管学术界、非政府组织、相关政府、区域性组织,尤其是联合国投入巨大的资源以明确、塑造和实施“保护的责任”,但其依然争议不断,实施起来亦困难重重。利比亚和叙利亚出现危机后,大国之间的僵持引发了关于“保护的责任”的意义和应用问题。无论对批评者还是拥护者,僵持可能导致对“保护的责任”支持的弱化。在繁忙的全球日程中,由于一些地区更具备成熟的解决条件或已采用缓和措施,“保护的责任”可能会被搁置。在世界秩序中心多元化、全球力量不断转移变化的今天,“保护的责任”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本身,还是作为诸多即将延续和发展的规则及规范的“领头羊”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 笔者在此简要介绍“保护的责任”的源流,概括其目前所陷入的僵局,并对如何促成建设性的对话提出建议。虽然所涉及的方面和问题远超中美两国,但倘若中美两国置身事外,将难以想象任何富有创造性和现实意义的解决方案能够得以达成。 一、起源和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人类安全的思想开始扎根,“保护的责任”即起源于此。到底为了谁的安全?威胁究竟来自何方?以何种方式?这是永久的辩题,个人成为这场辩论的焦点所在。它致力于解决武装冲突或其他形式的有组织暴力中个人和群体的保护问题,并在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2001年10月的报告中提出创造性的设想。①该报告产生的背景是:在索马里、塞拉利昂、卢旺达、波斯尼亚和东帝汶等一系列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不干涉)引起了种种争议,科菲·安南请求国际社会制定一致认可的应用原则,以确定在必要情况下如何采取强制行动以保护处于困境的人民。该报告特意在联合国的框架之外开启该议题。 “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在报告中明确避免使用“人道主义干涉”和“干预的权利”等术语,而是从保护责任的角度界定与主权和干涉相关的问题,从而聚焦在人民需要支援上。它确认了一系列与《联合国宪章》下的国家主权、《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现行国际法规定的法律义务,以及国家、区域组织和安理会的发展实践等相关的原则。它扩充了保护责任的范畴,当面临某个国家无法或者不愿承担责任的时候,保护的责任将包括防止的责任、反应的责任、重建的责任。此外,它对正当行动的前提、预防原则、权利权威和行动原则等概念做了精确的定义,以允许在某些极端事态下不经许可而介入。 国际社会对“保护的责任”反应热烈,众说纷纭,其主要舞台在非洲和联合国。科菲·安南的“威胁、挑战和变化高级讨论小组”(High Level Panel on Threats,Challenges,and Change)宣布“集体的国际保护的责任”,并将“保护的责任”定性为“未来规范的雏形”。他在2005年的报告《更大自由》(In Larger Freedom)中提出“保护的责任”作为集体行动的一部分,以促进共同发展和治理,而不仅是全球和平与安全策略。 这种将该规范制度化的努力在2005年联合国世界峰会上达到顶点。峰会成果文件(A/Res/60/1,2005年,此后为World Summit Outcome Document,WSOD)尤其是第138、139段,宣称主权国家负有保护其人民的首要责任。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责任则限于协助有关国家落实保护人民的责任。如果一个国家“显然未能”尽到保护人民的责任,国际社会有义务“携手有关地域性组织,在一事一议的基础上”采取和平手段保护遭受明显灾难的人们;如果和平手段有所不逮,将进一步考虑采取军事行动。后者必须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同意,且仅局限于以下四种犯罪行为:种族大屠杀、战争罪行、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的极端罪行。联合国秘书长的三个报告对此予以细化,2012年的巴西关于“保护时的责任”(responsibility while protecting)的倡议也进一步补充了该思路。② 《联合国宪章》中有关国家主权、平等和非干预等原则和规范,是与《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人权宣言》《联合国发展报告》,以及国际人道法律和刑法所保障的人权与保护遭受胁迫的公民的原则相互抵触的,“保护的责任”的倡导者试图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其关于使用武力的条款已经在包括科特迪瓦和利比亚争端等事例上成功地付诸实践,但在肯尼亚、达尔富尔、苏丹和叙利亚等有关问题上却引起了明显分歧,甚至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也不能幸免。 二、目前的僵局 造成联合国安理会在叙利亚应用“保护的责任”的僵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对“保护的责任”的内涵与外延的不同理解,关于其在利比亚应用所导致的分歧未能得到解决,以及国家利益的冲突。 中国对“保护的责任”的态度历经三个阶段的变化,其想法对于理解当前的局势非常重要。虽然中国官员尖锐批评“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报告所提出的思路,但它与数个国家(包括加拿大)的学术机构合作主办研讨会,探讨其中的主要因素和含义,并最终批准了2005年峰会成果文件勾画的更为严格限定的版本,即强调联合国安理会作为唯一合法的授权机构,强调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严格限制可能引发军事干涉的行为。之后,他们积极参与其机制建设与实施的讨论,成为——如布莱恩·乔布(Brian Job)与阿纳斯塔西亚·舍斯捷里妮娜(Anastasia Shesteinina)所言——“规范的塑造者”而不是“规范的接受者”,期望“塑造和引导保护的责任以符合其立场和利益”。③ 目前,中国的立场是既不全盘接受也不一概否定“保护的责任”。一方面,中国希望遵循威斯特伐里亚体系中关于主权至上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情况许可时保持介入的灵活性,这一矛盾态度体现在其对“保护的责任”的立场上,既小心内敛,又灵活多变,且注重实效。中国官员既不将其视为带有义务的规范(norm),也不将之视为在国际法上具有约束效力的原则(principle)。反之,他们将之视为一种在个别情况下可以借用的概念(concept)。与被公认的原则(如主权)所不同的是,“保护的责任”在应用前必须经由反复辩论并达成共识。虽然中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其海外公民,但对于何种情况才能够介入海外争端,始终谨慎对待,其着眼点专注于《联合国宪章》第7章有关和平与安全的规定。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和敦促外国政府自行解决国内危机,主张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外国势力才能介入(譬如在苏丹问题上)。中国在联合国批准的维和行动,以及支持地域性组织(包括在失败国家问题上和非洲联盟的合作)方面逐渐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④ 2011年,在辩论是否在利比亚应用“保护的责任”时,一开始,中国同俄罗斯一道对授权军事入侵的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弃权。后来,中国猛烈批评军事行动的扩大化及推翻卡扎菲政府。⑤与此同时,中国官员组织在利比亚的中国公民撤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PLAN)给予积极配合。关于叙利亚,2月4日,俄罗斯与中国对授权军事力量行动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投了否决票。中国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并积极斡旋派遣特使到大马士革及邻国首都,寻求和平解决方案。3月4日,中国支持阿拉伯联盟的努力,寻求以政治手段解决危机。 在学术界和第二轨道的讨论中,中国学术界对“保护的责任”所肩负的人道主义目的表示支持,但批评其沦为西方国家和其他政府的工具,认为其目的不在于公民保护,而是成了推翻政权、制造长期不稳定因素,以及怀着民主的本意为当地提供一些根本不适用的解决办法的借口。 作为“保护的责任”的倡导者美国,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继续采取不同的立场。2012年,美国政府在总统第10号安全令的基础上成立“暴行预防委员会”(Atrocity Prevention Board),旨在防止群众暴行和种族屠杀,这被视为是“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和核心道义责任”。2013年7月,由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和理查德·威廉森(Richard Williamson)领导的特别工作组所提交的报告又扩展了这一概念。该报告针对美国和国际受众,提出了四个主要论点。⑥ 第一,该报告将“保护的责任”视为规范和信条。报告称,“世界上每个国家都确认其有责任保护公民免遭种族屠杀、战争罪行、反人类罪行和种族清洗,至少在理论上,它们负有采取相应行动的责任”(第7页)。这包括当某个国家很明显已经无法保护其公民或者将其公民作为迫害对象之时,根据《联合国宪章》,其他每个国家都负有保护的义务,国际社会负有支持并准备采取“补救行动”的承诺。 第二,报告认识到“(‘保护的责任’)成功与否取决于今后一段时间内许多国家的态度与行动,但美国是否愿意当领头羊将举足轻重”。在这个基础上,报告注意到尽管“保护的责任”反映美国“最佳的利益和传统”,却经常遭到美国民众的误解,在国会中亦未得到足够的关切,也未能有意识地融入公众心中。美国官员和社会人士不应回避“保护的责任”,并应明确认识到其重要涵义:该概念旨在加强而不是弱化国家主权。它重点强调国家负有保护本国人民的义务,其次则着眼于帮助各国政府提高其履行承诺的能力。只有当一个政府不能或拒绝实施其主权责任之时,它才会遭遇外来干涉的风险。即使如此,“保护的责任”的落实将依照《联合国宪章》,这就意味着其核心决策机构是联合国安理会,尽管其并非完美无缺。虽然“保护的责任”植根于国际法的长期传统,但它没有将任何新的法律义务强加给各国政府。军事干涉并非义务。“保护的责任”压倒一切的目标是鼓励,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帮助国家保护其人民。当未能实现保护时,一般首先依靠外交、经济和其他措施。通过军事行动执行“保护的责任”将少之又少。(第10页) 第三,报告列出了一整套预防和监督冲突的手段,包括来自无人机、卫星图像、群源基层(crowd-sourced grassroots)报告及相邻国家等提供的预警机制;加大危机预防和维护稳定,以及增加对促进民主项目的资助(包括来自资助机构的援助);增加对国际刑事法庭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支持;支持区域性组织的应急反应力量;以及提高国会的参与意识。 第四,在分析“保护的责任”运用的实践方面,该报告赞扬了几个成功的事例,包括肯尼亚、科特迪瓦和利比亚。报告赞扬在利比亚拯救生命的行动是一次成功的经历,其所伴随的政权更迭是必要的,也可能是无意的,对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权限虽有延伸,但没有越界。报告提到将在叙利亚落实“保护的责任”,并且在将来一段时间内将推广到苏丹、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斯里兰卡。 隶属于中国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最近撰文,主张以“负责任的保护”(responsible protection)替代和补充奥尔布赖特和威廉森报告中所提出的“保护的责任”,因为后者的定义似乎过于宽泛。阮宗泽在开篇提出中国必须在保护责任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领导作用。中国已坐上了国际舞台的主桌,需要适应在聚光灯下的新环境,国际社会同样需要适应中国这一新角色。尽管这意味着在应对和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时,将面临更加艰难复杂的取舍、抉择,但中国必须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思想。“负责任的保护”反映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建设性地塑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努力。⑦ 他赞同2005年峰会成果文件所强调的“保护的责任”的四个基本元素,但尖锐地批评美国和西方企图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应用“保护的责任”。他所主张的“负责任的保护”有六个要素:第一,保护的对象必须是无辜平民,而不是特定的政党或武装力量;第二,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才能充当合法的保护者;第三,保护的方式应强调外交和政治对话,因为军事力量会造成大量民众伤亡、破坏基础设施、危害经济、“加剧人道主义灾难,让被‘保护’对象长时间处于艰难的灾后重建中”;第四,保护的目的必须严格遵守人道主义。“绝不能因为保护而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更不能成为推翻一国政权的借口”;第五,提供保护的国家有帮助它们所干预的国家重建的义务;第六,联合国应行使监督、评估的责任,并对行动实施事后问责制。⑧ 不仅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主张限制“保护的责任”的目的和使用范围,亚太地区保护责任中心(Asia Pacific Centre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两位主任最近也联合撰文指出:倘若在叙利亚落实“保护的责任”,其将面临三个相互冲突的立场:第一,未经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的行动将与“保护的责任”相抵触;第二,军事行动将违背“保护的责任”,但具有国际合法性,尤其是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团结一致共策和平(uniting for peace)的决议;第三,出于对安全的关注,西方强国将强行干预,且美其名曰“基于人道主义需要的建设性非遵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对“保护的责任”约束性诠释有利于维护该规范的长期效力,部分原因在于像在叙利亚这样如此复杂的冲突中落实“后果平衡”的主要原则是非常困难的。军事行动的直接代价惊人高昂,实际上可能导致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⑨ 三、构筑共同点 中国和美国都不是“保护的责任”的最坚定支持者,也都没有签署加入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两国都认识到“保护的责任”并未强加任何新的法律义务,相反,“保护的责任”保留了在某些地方、以某种方式运用的权利,这违背了两者的最佳利益。两国都承认《联合国宪章》的根本性,以及安理会作为授权行动的正当机构。两国在保护海外冲突地区本国国民的利益方面有着共同和广泛的利益。尽管分歧的壕沟仍在,但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人、美国人和国际社会正在逐渐靠近,而不是越走越远。阮宗泽在《负责任的保护》中所提到的六点大多与“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最初报告所提的看法是相呼应的。 如果“保护的责任”要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全球概念、规范或原则——更不用说它是否能够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付诸实施——它就需要更广泛的支持者,不能仅限于西方国家及与之抱着相似看法的国家和个人。获得中国、俄罗斯及众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和巴西的同意和支持,不仅是难能可贵的,更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的作用是关键的。或许目前正是与中国官员和学术界人士展开建设性对话的时候了——有必要以2005年峰会成果文件为基础,就“保护的责任”的合法性、范畴、含义展开深入探讨,探索如何达成与巩固共识。 对话至少需要聚焦在四个领域。第一,关于授权。联合国安理会是最佳的机构,还是唯一的机构?出现僵局之时,其他多边机构授权“保护的责任”合法吗?第二,行动的对象——“无辜平民”——该如何界定?对起义者的大批屠杀是2005年峰会成果文件涉及的四种罪行之一吗?第三,当一国政府对本国公民犯下大规模灭绝罪行时该怎么办?政党和政权是否能成为外来军事介入的合法目标?推翻政权能否成为正当的目标,如果是的话,前提是什么?第四,在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内部冲突中,如何能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危机可能深化的警告信号是什么?如何评估外来干涉是否可能成功,而不触发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暴力?奥尔布赖特和威廉森在报告中所提及的新空间技术能部分地提供解决方案吗? 诸如此类的讨论需要在政府、双边、联合国及区域性组织的层面上进行。此外,有必要开辟第二轨道进程以深入探讨预防性外交,在危机局势下采取何种措施保护在海外的公民,以及必须遵守何种外交礼仪等多个领域。同时,一些非政府机构如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所从事的深入研究也值得借鉴。 (本文系提交给2013年“北京论坛”分论坛的论文。笔者在此感谢布赖恩·乔布(Brian Job)和阿纳斯塔西娅·舍斯捷里妮娜(Anastasia Shesterinina)对拙文的评论,以及惠赐两篇他们即将问世的大作。本文亦参考了笔者为《人类安全手册》一书所撰写的章节,参见"Human Security and East Asia," in Mary C.Martin and Taylor Owen,eds.,The Human Security Handbook,London:Routledge,2014。)标签: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