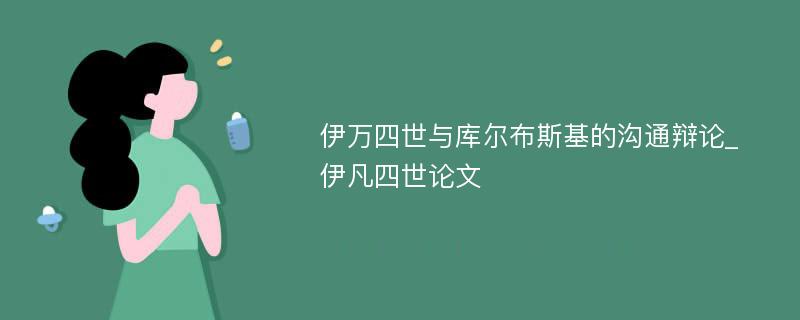
伊凡四世与库尔勃斯基的通信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基论文,库尔论文,伊凡论文,通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6世纪中期的俄国爆发了一场著名的君臣之争,争论的一方为俄国的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Ивαн Ⅳ Вαсилъевич Грозный,1530 —1584),另一方为逃离俄国的库尔勃斯基(Андрей Михαйлович Курбский,1528—1583),他俩的论战是通过书信进行的。这场延续了近20年之久的通信论战,也构成了俄国文学史上一个精彩而又重要的事件。
一
1564年4月,担任俄国尤里耶夫(今爱沙尼亚境内的塔尔图)军政长官的库尔勃斯基突然逃往波兰控制下的立陶宛,此后不久,他给伊凡写了一封信,在为自己的出逃做出解释和辩解的同时,也对伊凡的行为和政策发出了谴责。伊凡接信后“龙颜大怒”,立即对旧臣库尔勃斯基的“挑衅”做出反应,痛骂了对方的胆大妄为和背信弃义。接下来,库尔勃斯基又给伊凡写了两封信,伊凡也有一封回信。这五封书信,就是人们如今能够了解到的伊、库之争的全部内容。
伊凡雷帝和库尔勃斯基两人书信的原件都没有保留下来,现存均为抄本。最早一份抄本出现在基辅修道院的文献中,其年代可确定为17世纪20—30年代,也就是说,与书信的写作年代相距约60年。在此之后,各种抄本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众多的版本和异文,据俄国史学家考证,仅库尔勃斯基第一封书信第一种版本的已知抄本就多达24种。[1](257) 散见在俄国古代文献中的各种版本的伊、库书信,恐怕不下百种。以现代正式出版物形式出版伊、库书信的最早尝试,出现在1833年,在乌斯特里亚洛夫主编的《库尔勃斯基公之传说》中,收有库尔勃斯基致伊凡雷帝的两封信。昆采维奇于1914年编辑、作为“俄国历史丛书”第31卷出版的《库尔勃斯基公文集》,不仅收入了库尔勃斯基的书信,还收入了伊凡雷帝的两封书信。1951年,利哈乔夫和卢里耶在编辑《伊凡雷帝书信集》一书时,也收入了库尔勃斯基致伊凡的第一封信。伊、库通信的最全面、最权威的版本,还是由卢里耶和雷科夫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伊凡雷帝和安德列·库尔勃斯基的通信》(Перепискα Ивαнα Грозного с Андреем Курбским)一书,此书不仅收有多种版本的伊、库书信,而且还附有书信的译文,以及版本考证和内容评介方面的文章。
伊、库通信很早就引起了欧美学者的关注,也陆续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如德译本(莱比锡,1921年)、英译本(剑桥,1955年)、捷克语译本(布拉格,1957年)、法译本(巴黎,1959年)和意大利语译本(米兰,1972年)等。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凯南曾于1971年写出一部专著,全面否定伊、库通信的历史真实性,认为书信是一份古代“伪经”,是由另一位王公伪造而成的。[2](125) 当时的苏联史学界将此举视为西方学者对俄国历史的有意“歪曲”,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挑衅”,于是便组织力量反驳,从而引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史学大论战。这场论战,在客观上引起了人们对伊、库通信问题的兴趣,大大地促进了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今天回过头去看一看当时的争论,发现凯南提出的那些理由,面对俄罗斯著名史学家斯克雷尼科夫等人的逐一反驳,还是显得有些站不住脚的。其实,若抛开他们那场争论中往往成为焦点的史实和文本上的那些细节,仅从几个大的角度去看问题,还是可以判定伊、库通信的历史真实性:首先,同一时期出现的大量内容相近、版本却各异的抄本,本身就可以构成一种相互印证,说明它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因为各自独立的诸多“伪造”不可能在内容上如此吻合,而这些抄本的年代都经过了考古学上的严格鉴定;其次,在16世纪的俄国,通信已很盛行,伊凡雷帝和库尔勃斯基也的确都写过大量书信,在一些可信的历史文献中还保存有两人的其他许多书信,那些书信与伊、库的论争书信在风格上是吻合的;最后,诸多古代史籍对伊、库之争有过记载,而那些记载的年代与最早的抄本出现的年代几乎同时。
伊、库之争作为一段历史典故,一直为俄国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所津津乐道。俄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卡拉姆津在他那部著名的12卷本的《俄国国家史》中就记载过这场通信:“库尔勃斯基的首要之事就是要与伊凡交谈:要敞开他那充满苦楚和不满的心灵。怀着强烈的情感,他给沙皇写了一封信。……因为愤怒和良心上的不安而激动不已的沙皇,立即给库尔勃斯基回了信。”[2](214) 之后的俄国各类史书,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无论是文化史还是文学史,写及16世纪的伊凡四世当政时期,都不可能不谈到这场著名的君臣之争。
总的看来,两人在五封信里所涉及到的大致是这样三个问题:一,关于皇权及君臣关系。在库尔勃斯基看来,皇帝虽然高高在上,但也必须首先做一个灵魂纯洁的基督徒,要有面对上帝的虔诚和畏惧,要有面对臣民的仁慈和公正,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一位明君,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不幸和灾难;而伊凡雷帝却认为,沙皇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沙皇的地位和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沙皇的统治,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强盛。二,关于专制及国家体制。作为削藩制的直接受害者,库尔勃斯基自然对高度的专制制度深恶痛绝,认为伊凡雷帝统治早期的“重臣拉达”制度,亦即等级代表君主制,才是理想的治国体制;而作为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沙皇、俄国绝对专制制度的创始者,伊凡雷帝容不得任何权力旁落,他认为皇权不应该受到任何法律和规章的限制,沙皇就是最高的、惟一的审判者,包括大贵族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沙皇的“奴隶”,他从神赋皇权论推导出来的无限权力论,是他建立无限君主制政体的思想基础。三,关于上帝及末日审判。在争论中,两人都竭力标榜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都认为自己是站在上帝一边的,或者说,上帝是站在自己一边的,为此,两人在信中都大段大段地引用《圣经》,都以末日审判来威胁、诅咒对方,但是他们在争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态度,有几点却是值得注意的:首先,两人都忠实于东正教的传统和教义,这使得他们的争论焦点往往就聚集到了以何种方式保持俄国君主在正教中的“圣明”这一问题上来了。其次,两人在宗教意义的行为评判上,均是严于律人,宽于待己的,相比较而言,伊凡雷帝的宗教观要更功利一些,也许是因为他自视为“上帝之子”而颇有些张狂。最后,这两个在灵魂上都不完全干净的人,在通信中也流露出了他们对末日审判的恐惧,他们对对方的疯狂诅咒,有时实际上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良心负担;他们将自己暂时的胜利视为神的意志,因而得意洋洋地致信对方,这反过来也说明了,他们对神是否保佑自己、是否宽恕自己,其实是非常在意的。
二
伊凡的第一封回信洋洋数万言,要20倍于库尔勃斯基的来信,有俄罗斯学者感叹,“这几乎就是整整一本书”[2](224)。考虑到当时的书写条件和水平,考虑到伊凡雷帝的日理万机(据史书记载,他在写回信的那数周时间里还曾出宫巡视),人们几乎可以断定,回信不是伊凡一个人写成的,而是由他和他的“秘书班子”合作的。如今,要明确地区分出信中的哪些话是文书写的,哪些话是沙皇说的,已经不大可能。他的两封信也的确是一个各种文字风格构成的大杂烩:这里有一个君主的骄横和霸道,也有一个基督徒面对上帝的虔诚和卑谦;这里有羞辱人、压服人的盛气,也有摆事实、讲道理的愿望;这里有庄重的外交文体,也有粗鲁的骂人字眼;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和不无伤感的往事回忆,郑重其事的引经据典和装模作样的自我表白,教会斯拉夫文和村语俗字,真诚和虚伪,理智和疯狂、克制和暴躁……所有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使得他的书信看上去就像某种介乎于私人书信和法律文书、文学作品和事务文件、个人表白和政治宣言之间的东西。然而,伊凡雷帝鲜明的个性风格并没有因此而被淹没,这是因为,一方面,这种庞杂的构成本身就显示出了伊凡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另一方面,在书信的字里行间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只可能出自伊凡之手(或之口)的东西。
首先,这些书信向我们证明,伊凡并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昏君,而是一个很有修养的帝王。在俄国历史上,伊凡四世由于其残暴而永远成为一个恐怖的形象,而其精通文墨的一面却相应地为人所忽视了。其实,自幼生长在宫廷中、三岁就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的伊凡,接受到了他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俄罗斯著名学者利哈乔夫断言:“雷帝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教养的人之一。”[3](186) 伊凡书信的立意、框架以及主要思想,恐怕还是出自伊凡本人,伴在伊凡这样一位暴君身边的文人墨客,恐怕不敢在书信的写作上过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敢擅自添加,或越俎代庖。而信中那些既富有逻辑又蛮横无理的话语,也只有伊凡这样一位目空一切的独裁者才能说得出来。
其次,这些书信表明,伊凡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当然,他首先是一位君王,他之写作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伊凡留下的文字大部分为书信,而他书信中的大部分又都是写给自己的敌人的,也就是说,写作对于伊凡来说首先是一种打击敌人的方式,而正是在诸如“声讨信”这样的文字形式中,伊凡雷帝那种坚定自信、飞扬跋扈的天性获得了最佳的体现。个性和文体的相互吻合,不仅使伊凡的书信具有了强烈的政论色彩,而且还使伊凡的文学天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就对自我立场和观点的坚决捍卫而言,就捍卫方式上的不择手段而言,伊凡雷帝都是一个出色的政论作家。然而,伊凡雷帝的文学才能还不局限于此,至少在这样几个方面,他表现得很是出众:1)语言运用能力。伊凡书信最大的语言特征,就是其口语色彩,他的文字像是在说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像是在“训话”,这表明他的书信可能是由他口授的。这里不仅有大量的口语句型结构,还充满了众多的呼语、问句(包括疑问、质问、设问和反问等等)和感叹句;所用的词汇也十分丰富,从崇高的教会斯拉夫用词,到日常生活中的字眼,直至连那些连篇的骂人话也是富有变化的。2)比喻能力。伊凡的信中会不时冒出一句出彩的比喻来,比如:“你的话冠冕堂皇,像蜜糖,却比艾蒿还要苦。”“你像公狗一样狂叫,像蝰蛇一样吐毒。”“受妻子管制的丈夫是痛苦的,受众人管制的城市也是痛苦的。”这样的话语方式可能来源于民间文学,伊凡的书信和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一样,都带有某种明显的转型色彩,当时的俄国文学正处在一个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官方、从宗教到世俗的转换时期。3)讽刺能力。应该说,如潮水一般倾泻而下的挖苦和嘲笑,是伊凡信中比重最大的内容。而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刻薄的嘲讽:库尔勃斯基在来信中曾发誓,要把自己的那封信带到棺材里去,在末日审判时展示出来,而在此之前,他不会再让伊凡看到自己的脸了。伊凡则针锋相对,对库尔勃斯基信中这最为激昂的“誓言”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你祈求评判一切的上帝;的确,上帝会公正地评判一切事情,无论善恶,不过每个人都该想一想:他做了什么事情,该得到怎样的评判?你把自己的脸看得很重。可是谁又愿意看到你那张黑鬼似的脸呢?又有谁看到过,一个诚实的人竟长着你那种蓝眼睛呢?你这张脸就已经暴露出了你狡诈的天性!”4)抒情能力。像每一位高明的君主一样,伊凡也善于“演戏”,在他的表演中有虚伪的成分,有变换角色的本领,也包括某种旨在打动人心的情感抒发。在第一封回信的中间,他出人意料地一转笔锋,竟然伤感地怨诉起自己“不幸的遭遇”来,这段长达数千字的“抒情插笔”,是伊凡书信中最精彩的段落,它夹叙夹议,温情与激愤交织,回忆与现实叠加,构成一篇文学性很强的抒情散文。
伊凡雷帝若没有他的这几封书信传世,后人也许永远不会了解到他的文学天赋;就连背负着沉重的政治抱负和统治野心的伊凡雷帝自己,也未必清楚或在意他的文字风格。然而,正是在他的书信中,人们却更全面、更丰富地认识了他,更具体、更直观地了解到了他的文风,乃至他的个性。利哈乔夫在总结伊凡雷帝作品的风格时这样写道:“大胆的革新者,令人吃惊的语言大师,时而愤怒,时而抒情……‘刻薄’风格的大师,全罗斯的独裁者,热衷于玩弄恭顺的游戏,展示自己的屈辱或受害,为了一个目的,即说服并嘲笑自己的对手,他可以置许多文学传统于不顾,——其作品中的雷帝就是这个样子的。”[3](201—202)
与伊凡雷帝相比,库尔勃斯基更像是一位“职业”作家,除了写给伊凡雷帝的这三封信外,他还有大量的其他书信传世,而那部《莫斯科大公传》的存在,更使他步入了16世纪俄国大作家的行列。库尔勃斯基同样是那个时代最有修养的人士,他不仅精通文墨,熟读经典,而且还懂得多门外语,翻译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著作。库尔勃斯基致伊凡的书信写得很是标准,句式规范,用词精确,整体结构也显得简洁、得体。从库尔勃斯基的后两封信中不难看出,面对伊凡雷帝,库尔勃斯基在文字上是颇为自信的,甚至有些看不起自己的对手,他曾称伊凡的信是“惊天动地、吵吵嚷嚷的”,充满疯狂的呓语和粗鲁的叫骂,“像是醉婆娘的闲话”,不值得一读。如果说,伊凡在这场论争中一直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那么,库尔勃斯基则始终带有某种文学修养上的优越感。我们很难通过这里的几封信来给伊凡雷帝和库尔勃斯基和文化水平分一个高低,然而,正像文学史家们所说的那样,“实际上伊凡四世思维敏捷,不受拘束,给人留下的印象比库尔布斯基(即库尔勃斯基。——引者按)的信更为鲜明生动”[4](17)。就书信中所体现出的个性色彩而言,库尔勃斯基的确逊色于伊凡雷帝,这也许是因为,作为一位臣子的库尔勃斯基,原本就没有沙皇伊凡那样十分张扬的个性;也许是因为,作为一位十分多产的作家,库尔勃斯基有意无意之间更多地受到了当时文字规范的制约。不过,库尔勃斯基所处的社会和生活环境对其个性及其文字风格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细细地阅读库尔勃斯基的书信,我们往往能在庄重和严谨的语言外表下感觉到几丝犹豫和无奈,与伊凡雷帝自始至终的肆无忌惮形成对比的,是他不时表露出的闪烁其词。也就是说,书信中的库尔勃斯基不时表现得很矛盾,而这种矛盾心态就构成了其书信最大的情绪特征。比如:1)从书信的写作动机上来看,库尔勃斯基将伊凡四世视为残忍的暴君,忘恩负义的小人,逃离了伊凡魔掌的他,自然对伊凡充满仇恨和厌恶,然而,他却又不得不拿起笔来给自己的迫害者写信,在暴君的面前寻求公正,以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清白。2)从库尔勃斯基的自我辩护上来看,一个逃离了祖国的人,却在反复证实自己对祖国的爱;一个实际上已经完全否定了其过去的人,却在津津乐道于自己从前的功勋。起先,他将自己流亡的罪过归咎于伊凡,认为伊凡是他背井离乡的罪魁祸首,也就是说,他也承认“叛变”是一种罪过(第一封信);但后来,他却又因为伊凡的失败而幸灾乐祸,因为自己率领异国的军队攻下俄国的城池而沾沾自喜(第三封信)。3)从库尔勃斯基对上帝的态度来看,一方面,他认为伊凡良心不洁,对上帝不够虔诚,他还多次用末日审判来威胁伊凡,可另一方面,他却认为伊凡是“异教徒”,而他“现在听命于真正的基督徒君主”,即波兰—立陶宛的国王。也就是说,他一面标榜自己是虔诚的正教信徒,一面又在俄国东正教和波兰天主教的对峙中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后者。4)在对文字的态度上,库尔勃斯基也体现出了相似的矛盾。作为一位俄国王公,他使用标准的俄语给俄国的君主写信,并因为自己的文字(俄语)能力而自豪,可是,他似乎更推崇他寄居之国的文字和文化,认为“这里的人不会像你那样写信”,于是渐渐地,在他的第三封信中,与“你们那里”、“你的国家”等用词形成呼应的,就是越来越多的波兰用词(полонизм)。
库尔勃斯基书信中的矛盾色彩,直接来源于他的处境,背离了自己国家的他,迫切需要一个洗刷自我的机会,他要通过给沙皇的信来向俄国公众表示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处在新主子的庇护之下,他又必须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为自己定位,找到一个合适的社会新角色。库尔勃斯基的彷徨和迷惘,也是特定历史阶段中特定历史人物的特定感受,伊凡四世来势凶猛的削藩行动,如同任何一次社会改革,在当时就曾激起了不同社会阶层截然不同的反响,而在某一个具体的人的身上,也会引发出复杂的心态来,国家的强盛与实现这一强盛所需付出的代价,专制制度的必要性与其不合理性,暴发阶层的既得利益与被废黜贵族的历史功绩,恐怖与仁慈,忠诚与背叛,战争与和平……这一切形成一个又一个二律背反,摆在库尔勃斯基和他的同时代人的面前。库尔勃斯基的尴尬处境,更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与专制君主进行思想对峙时所常常遭遇的,如何将爱和恨分别投向国家和统治着国家的君主,如何不使个人情感与民族情绪构成冲突,如何……这是曾经苦恼过一代又一代俄罗斯思想者们的难题。
利哈乔夫在论及库尔勃斯基的创作风格时说道:“作为一个人,他不止一次地改变过自己的行为,与此同时,他也在不断改变其作品的风格。库尔勃斯基没有一种严格的创作上的完整性。”[3](203) 我们觉得,库尔勃斯基创作上的多变,其原因就在于其深刻的现实难题和思想矛盾,而反过来,这些难题和矛盾却强化了其作品的思想内涵,丰富了其作品的表现风格,就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而言,库尔勃斯基还是体现出了其独特的“完整性”。
三
“雷帝和库尔勃斯基的通信,属于俄罗斯古代文学中最著名的文献。”[5](214) 这场通信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了俄国文学和文化之后的发展。伊、库通信的文学史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作品风格和作家个性的彰显。在伊凡四世和库尔勃斯基展开通信争论的时候,俄国文学已经有了好几个世纪的发展历史,斯拉夫原始部落中的口头创作没有、也不可能流传下来,从11世纪开始出现的“史事歌”(又译“壮士歌”)就成了俄国文学的源头。16世纪之前的俄国文学大致由这样几个板块构成:10世纪开始出现的“编年史”,12世纪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的“战争故事”,以及大量的宗教文献。回顾这些文学,我们发现,除了不朽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外,其他的作品文学性都不是很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似乎都缺少风格,都很难看到作者自己的身影,这也许是因为,中世纪严厉的世风是压抑个性的,异族的长期统治也造成了自觉的民族意识的缺失。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俄国古代文献大都出自僧侣阶层之手,他们克制、禁欲的生活方式无疑也会影响到早期的俄国文学。不管怎样,到伊凡当政时,俄国君主的个性已得到了充分的张扬。而那一时期俄国作家的个性却尚未获得足够的发展,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伊、库的书信,尤其是伊凡雷帝的书信,如前所述,却体现出了鲜明的个性风格,作者在作品(书信)中走向前台,大胆地表现自我,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好恶,写作者成了文本的主人和主角,构成了俄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特例。“在整个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甚至连一个与此大致相似的例子我们都难以找到。俄罗斯古代文学不懂得谋求风格。”[3](201) 我们也许可以说,正是从伊、库的书信开始,作者的个性以及随之而有的独特的作品风格,就开始出现在俄国文学中了。
其次,是激情文学基因的确立。伊、库书信的最大特色,就是其中饱含的激情,无论是库尔勃斯基的自我辩白,还是伊凡四世的愤怒驳斥,都洋溢着昂扬的情绪和战斗的精神,这与此前那些冷静、平和的历史和宗教文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伊凡和库尔勃斯基同时,还活跃着其他一些俄国作家,如西尔维斯特和马卡里,还有为伊凡的国家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的作家伊凡·佩列斯韦托夫(他也曾上书伊凡四世,但要求皇帝进一步强化专制制度,与库尔勃斯基相反,他是从立陶宛逃到俄国来的),但与伊、库相比,他们在文字的力度和论战性方面还是有差距的。政论是那一年代主要的文学体裁之一,“政治局势的紧张使政论文在16世纪文学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而“16世纪最富有时代特色的政论文是伊凡四世和库尔布斯基(即库尔勃斯基——引者按)公的通信”。[4](17) 伊、库的书信开创了俄国文学中强大的政论传统的先河,之后,无论是在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还是在普希金与恰达耶夫关于俄罗斯民族性问题的争论中,无论是在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中,还是在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对现实的审视中,直到苏维埃文学的“生活教科书”理论,直到索尔仁尼琴的“新斯拉夫”学说,激越的斗士激情,崇高的公民责任感,以及对现实问题的热切关注,一直是俄国文学的主要旋律之一。作为激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伊、库书信中那种由痛苦的回忆,悲愤的控诉和虔诚的表白组合成的“感伤”模式,也影响到了从阿瓦库姆开始的许许多多的俄国作家,从而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注重内心情感体验的“忏悔文学”传统。
最后,是流亡文学传统的形成。一部《俄罗斯侨民文学史》的作者曾写道:“俄罗斯的流亡文学历史悠久,早在十月革命前很久就开始了,第一位俄罗斯流亡作家大约要算是安德烈·库尔勃斯基公,他逃离‘沙皇的压迫’,并给伊凡雷帝写了几封抨击性的政论书信,这些书信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恩怨。”[6](3) 作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持不同政见”的流亡作家,库尔勃斯基的意义非同小可。20世纪俄侨文学的强大存在,使得众多的文学史家们有理由指出,在20世纪的俄罗斯同时并存着两种文学,自始至终都有两部文学史在平行地发展着。这的确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罕见、很独特的景观,而这“另一种文学”的传统,我们就可以一直追溯到库尔勃斯基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