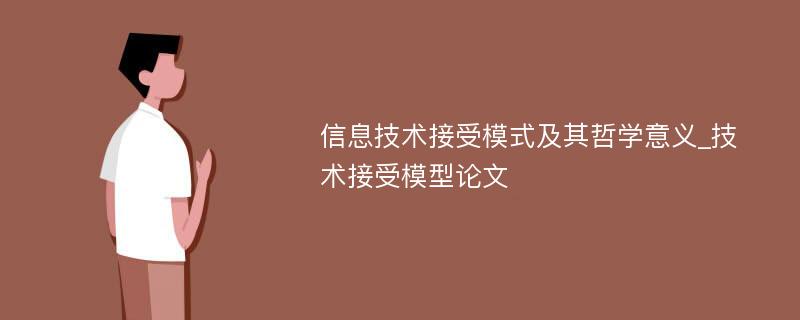
信息技术接受模型及其技术哲学涵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技术论文,涵义论文,模型论文,哲学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0)05—0037—05
信息技术一经出现,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围绕着信息技术产生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以及信息经济学等学科上的新理论和新模型,备受企业界及学界瞩目的是用于信息技术上的巨额投资却收效平平的原因。事实上,为支持生产力发展而设计出的信息技术,只有被接受、使用以及持续使用,它们的价值才能显现出来,目前这一观点在学界已形成共识,影响信息技术接受和使用决策的研究成为现代信息系统文献中最多产的、最成熟的研究领域之一。其中,信息技术接受模型是最有影响的理论,它的影响不仅在于模型本身,还在于它深刻的技术哲学意蕴。
1 信息技术接受模型
信息技术接受模型中的技术接受可以界定为使用主体对市场中的技术进行符合预定功能或不符合预定功能的操作、利用和发挥的活动,它是信息技术与社会系统中的使用主体相互建构的过程。信息技术接受的研究主要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研究个人接受信息技术的心理历程,其出发点在于外部变量(如用户的个人特征、系统特点、任务特点等)只有通过个人的内在信念才能对其使用意向和使用行为发生作用,其主要研究包括个人信念与使用意向的关系以及信念的构成因素。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以戴维斯(Davis,1989)、文凯蒂什(Venkatesh,2000,2003,2008)等人为代表提出的信息技术接受模型最有影响,如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技术接受扩展模型(The Extens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2)、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模型(the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UTAUT)和Venkatesh和Bala(2008)[1]的TAM3(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3)模型。这些理论模型以个人的使用意向或使用行为作为研究的因变量,以个人对于使用信息技术的信念作为自变量,阐明了人们对信息技术的接受是如何由内在信念(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态度等因素决定的。
技术接受模型(TAM),由戴维斯等人(1989)[2]最先提出,他们将社会心理学中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简称TRA)运用到管理信息系统中,以内在信念(感知有用性① 和感知易用性②)、主观态度和行为意向以及外部变量等因素,解释和预测人们对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TAM的研究对象是人们的行为意向,通过行为意向推测人的使用行为。
技术接受扩展模型(TAM2)是文凯蒂什和戴维斯(2000)[3]以TAM为基础提出的,它以社会影响过程(social influence processes)和认知工具性过程(cognitive instrumental processes)两个复合变量解释了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意向(intention to use)。社会影响过程包括社会规范③(subjective norm)、形象(image)以及两个干扰变量——自愿(voluntariness)、使用经验(experience);认知工具性过程指“人们形成感知有用性的判断,部分来自于认知的比较,即该系统是否有能力达到他们的工作要求”(文凯蒂什和戴维斯,2000),包括工作相关性(job relevance)、产出质量(output quality)、结果示范(result demonstrability)与感知易用性四个因素。TAM2以个人的行为意向作为研究对象,它与TAM相比,细化了影响信念的构成因素。
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模型(UTAUT)是文凯蒂什等人(2003)[4]在理性行为理论(TRA)、技术接受模型(TAM)、动机模型(Motivational Model,简称MM)、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ing Behavior,简称TPB)、组合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的模型(Combilned TAM and TPB,简称C—TAM—TPB)、计算机可用性模型(Model of PC Utilization,简称MPCU)、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简称IDT)以及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简称SCT)等八个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将主要因素进行整合而形成的综合模型(UTAUT)。UTAUT模型提出有四个直接因素对用户接受和使用行为起决定作用,即绩效预期(performance expectancy)、努力预期(effort expectancy)、社群影响(social influence)和便利条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有四个调节变量起间接作用,即性别(gender)、年龄(age)、经验(experience)和自愿使用(voluntariness of use)。该模型也是以个人使用意向作为研究对象,影响信念的主要因素是在上述八个模型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
技术接受模型3(TAM3)是文凯蒂什和巴拉(Bala)(2008)[5]从组织层面研究工作场所员工为何及如何接受和使用信息技术的综合模型,是对TAM2和感知易用性(Venkatesh,2000)[6]决定因素模型的整合与改进。该模型认为社会规范、形象、工作相关性、产出质量、结果示范和感知易用性决定着感知有用性;计算机自我效能感(computer self—efficacy)、计算机焦虑感(computer anxiety)、计算机娱乐性(computer playfulness)、外部控制感(或便利条件)(perceptions of external control or facilitating conditions)、感知愉悦性(perceived enjoyment)和客观可能性(objective usability)决定着感知易用性。TAM3模型的研究对象是个人的使用意向,影响信念的因素是对前述的总结,与其他模型相比,它更完备、更具有操作性。
综上所述,TAM提出了一个简约模型,它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TAM2通过扩展TAM,探讨了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决定因素的来源,它为UTAUT和TAM3模型提供了重要支撑;UTAUT是在综合包括TAM和TAM2模型在内的八个模型基础上提出的整合与改进模型,它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扩展空间;TAM3是对TAM2的进一步扩充和延伸,又融入了其他模型的因素,提出了信息技术接受和使用决定因素的综合模型,与上述其他模型相比,其主要优势在于它既具有全面性,又具有潜在的可操作性。从最初戴维斯等人的TAM到文凯蒂什和巴拉的TAM3,它们始终围绕着一根主线——使用意向决定使用行为——而展开。纵观这些模型,一般是推出一组相互关联的因果假设,通过数据收集与分析,验证建立的模型假设与数据分析是否吻合。可以看出,个人对信息技术的接受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过程,概括起来就是它由行为、行为意向和态度组成。个人对信息技术的接受和使用过程是一个认知发展过程,个人的信念决定着使用意向和使用行为,反之,个人的使用经验又会修正其行为信念,并决定未来的使用意向。与此同时,使用意向也取决于外部强加给个人的社会压力,如单位制度的硬性规定必须使用某种特定的技术,从这一角度看,信息技术的接受和使用也是一个社会影响过程。
2 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的技术哲学涵义
质疑和辩护是哲学的灵魂,质疑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过质疑来拷问现实,是对合理性的一种辩护。探讨TAM系列模型技术哲学意涵的目的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从技术哲学的观点来看,TAM系列模型符合“经验转向”的技术哲学内涵,无论从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研究的演进来分析,还是从模型本身的含义来看待,其技术哲学意蕴都是十分丰富的。
1)信息技术接受模型演进的技术哲学意涵
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研究的基础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本身就具有技术哲学的意涵:一方面,它具有技术哲学的属性——“解释的弹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④,它拥有多种潜能,在现实中有多种发展方向,可用来实现不同的目的、服务于不同的人群[7]。如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对于政府、企业等单位组织而言,可以作为行政管理工具监督公众和员工;对于公众而言,也可以作为一种学习、交流、娱乐的工具。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也具有中介属性。传统意义上,技术是人与物质对象之间的中介,尤其是人和自然的中介。但信息技术使得技术作为中介的特性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此时信息技术即使还是中介,也更多地成为人和人之间的中介,或者说是不同信息世界之间的中介,而不是人和自然的中介。信息技术接受模型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中介,引伸开来就是它是单位组织与用户之间的中介,它通过研究用户接受信息技术的行为,反馈给企业组织,企业组织通过改进技术,迎合用户的口味,提升和推广自己的技术。
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的演进过程符合技术哲学中的“约束机制”。所谓约束机制是对“解释弹性”的限制,不同的解释必须在一定时间段内达成共识,一旦达成共识,就意味着问题得到了解决,技术进入了稳定状态[8],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结束,人们在技术成形之后,也可以通过再设计、再开发继续技术的完善过程。戴维斯1989年提出TAM模型,经过10多年的发展和应用,该模型在所有的预测和分析信息技术接受行为的理论中,影响最大、使用最普遍。2000年1月,科学信息和社会科学引证指数机构列出424个刊物引证了戴维斯等人的TAM模型。经过10多年(1989—2000年)的发展,TAM已成为强有力的预测用户接受的简约模型[9]。此后,文凯蒂什和戴维斯(2000)在其基础上提出了TAM2模型,时隔3年,文凯蒂什(2003)在整合TAM、TAM2、MM、TPB等模型基础上提出了UTAUT模型,UTAUT成为继TAM之后又一有较大影响的模型,它是现阶段技术接受理论通用的研究模型。TAM3模型是2008年文凯蒂什和巴拉融合了TAM2和感知易用性(文凯蒂什,2000)决定因素基础上提出的,它的完备性和可操作性要好于此前提出的模型。无论上述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的哪一种,都是一个阶段性的结论,通过再设计、开发,不断出现新的模型,随着新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会出现更新的替代模型。
2)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的技术哲学意涵
(1)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的方法问题
该模型可以作为宏观层面(如国家)和中观层面(如企业组织)控制公众和员工的一种方式。技术作为人的工具和手段,是对技术最为公认的理解。该模型探讨人们接受信息技术的方法主要采用了技术哲学中的还原方法,即根据简单性原则把整体、系统拆分为部分、要素加以认识,再把对部分、要素的认识作为人们对信息技术接受的认识,最终使模型达到数量化、精确化和标准化。数量化有利于运用计算机进行实际运算,精确化有利于进行价值评估,标准化则有利于将模型应用于不同的领域。还原方法是技术哲学诞生之时的主导方法,其本质是机械化、简单化、定量化(有量无质)、标准化和统一化、线性化、齐一化。技术接受模型所采用的方法正是技术哲学还原方法的再现。但同时,它还蕴含着技术整体论的涵义,技术整体论(technologicalholism)认为,普通人是技术过程的内在参与者。技术接受模型在验证过程中,它的调查对象是以学生、雇员、商人等为受访者,这些受访者正是技术接受模型建构过程中的参与者。
(2)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的本质问题
信息技术接受模型作为预测人们接受技术的工具,所体现的是一种认知技术或认知思想。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认为的“每一种技术都是思想的物质体现,因此一切技术都是人的理念的外化。在外化中并通过外化,我们可以读到技术所体现的思想”[10]。这里他把技术分为二等:第一等是改造外部物质世界的一般技术,第二等是改造内在心灵世界的认知技术。信息技术接受模型所体现的就是这种认知技术,它通过感知测量来推测人们对技术的接受行为。TAM一经出现(1989年),在不到20年(到2007年)的时间内,它的引证率就多达5000多条⑤[11]。它说明这种认知技术比一般技术进步的速度快,通过现代搜索技术和信息加工,以复制和延伸自然能力的方式,使人能够达到过去自然能力不能运作的领域[12]。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的本质揭示了信息技术“实际上就是一个文本,其间包含着多种复杂的异质社会因素,它只有通过使用者的‘阅读’行为才能获得其稳定的意义,从而实现自己的某种功能”[13]。技术的本质在于其功能发挥作用的广阔语境,同样,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的本质则在于应用领域的广泛性。
(3)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的集体意向性问题
所谓集体意向就是个体意向与集体行为有机统一、相互融合的模式。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体行为在根本上是由个体行动者实现的,他的个体意向是其行为的原因,该行为既是他自己的个体行为,也是其所在集体行为的有机部分。二是个体心灵是集体意向性的根源,其行为是相应心理意向的表现,个体的这些行为和意向表达了集体意向性。因此,可把集体意向性看做是个体意向与个体集体行为的内在表征[14]。在TAM模型中,“感知有用性决定人们的使用行为”,实际上是以“意向→行为”的模式为前提背景的,以实存的心灵为前提,把心理意向作为对行动解释的充分条件;“社会规范、团体压力等外部变量是影响感知有用性的因素”又暗含着“行为→意向”的模式,外在的规范和约束力量——换句话说就是集体行为——促使个体形成相关意向状态。诸多社会行为中,其中的个体并非都具有清晰的相关行动意向,反倒是外在的行为环境使个体产生相应意识状态。塞尔认为,不存在没有意向的行动,甚至不存在没有意向的无意向行动,因为每一项行动都有一种行动中意向作为其构成成分[15]。行动与意向不可分割,意向是行动的内在组成部分,行动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特定行动意向的表现和满足。
(4)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的建构性问题
从技术哲学的观点来看,技术接受模型的建构过程与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提出的“技术编码”理论,极为相似,它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建构主义的技术哲学思想。芬伯格认为“技术编码结合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类型的因素,它本质上是规则”[16]。技术编码表明,技术设计并非由技术的内在“效率”标准唯一地决定,而是由具体语境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种标准共同决定的。同样,在TAM模型建构阶段,它是许多参与者共同协调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社会行动者如研究者本人、研究者的助手、参与调查的单位组织领导、被调查的对象(如学生、雇员、商人等)、政府官员等等都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着参与。他们通过确定研究方案,通过实施调查措施,通过提供或控制信息感知,而对模型建构施加着影响。既然技术接受模型建构是一个多种社会因素随机参与的过程,是参与者之间互动与协商的过程,那么这一模型的发展必然表现为一种偶然的、非确定的过程。从模型验证差别较大的解释力度来看(34%到70%)⑥,这一由研究者设计出来的接受模型并没有按照最初的设想去运行。这说明在意向解释中,解释项与被解释项之间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二者之间是以“合理性”关系的预设为前提的。
(5)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的转换性问题
信息技术接受模型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既可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富裕环境,又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环境。通过充分利用TAM独特的思想资源进行话语转换,从我们自己的理论视野来考察这一问题,提出与中国的信息技术接受理论发展相关的问题,并寻求与欧美传统的结合点,我们有可能作出一些既有自身特色和现实意义,亦为国外同行感兴趣的工作。对于一项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使用者是否使用和如何使用取决于他们的生活世界。以计算机、网络等为主导的信息技术起源于西方,它反映的是发明者对西方世界“实然状态的理解和应然状态的期盼”,如最初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以英语为设计语言,这对于非英语国家的使用者而言,既需要克服语言关,又必须掌握计算机知识,才能正常使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明者“至多能提供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框架’,而社会却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道义的等等‘质料’填入这个框架”[17]。也就是说信息技术的发明者提供了一个结构或框架,提供了一种具有某些潜在功能的信息技术,至于如何“填充”这一框架、利用这一框架所承寄的功能则是来自不同环境之中具体使用者的事情。技术之所是——既包括技术发明创造时之所是,也包括技术使用和转移时之所是——取决于生活世界之所是,取决于生活世界具体情景之所是。[18]
3 结语
从组织行为学视角看,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研究的是使用者如何接受信息技术,为组织提供决策依据;从技术哲学视角看,该模型则打开了技术使用的黑箱,为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提供了实际案例。之所以考虑TAM的技术哲学内涵,是受到当代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启示。克罗斯(Kroes,2000)认为,导致技术哲学研究“经验转向”的理论根据是技术人造物具有二元本性[19]。这个研究纲领指出,技术人造物具有二元本性,即一方面它是人所设计的物理结构,另一方面这个物理结构是为了实现承载着某种意向的功能。前者说明技术人造物作为自然对象,适合关于世界中物理的或物质的观念,后者则说明它们作为具有一定功能的对象,更属于意向性的观念[20]。
信息技术接受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行为意向决定使用行为”这一假设关系上的,它并没有论证行为意向如何决定使用行为,它隐含着这样两层涵义:其一,原因与结果之间不必存在严格的定律;其二,通过外部变量的干预,行为意向的值发生改变,使用行为也发生相应的改变。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即使原因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定律,这种因果关系仍然能够成立。尽管诸多学者对TAM模型的实证测试结果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行为意向与使用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70%,最低为34%,他们仍然断定二者存在着合法关系,这样的断言多有牵强之嫌。Davis等人的研究实质上是以当代意向性研究问题域中“意向性的因果性问题”这一尚未有定论的结论为理论基础的。意向性的因果性问题是当代心灵哲学中与心身、心物关系问题以及行动哲学中的行动解释问题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崭新的、前沿的课题[21],或许Davis等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注释:
① 感知有用性是用户主观上认为某一特定系统所提升的工作绩效程度。
② 感知易用性是用户主观上认为使用某一特定系统所付出努力的程度。
③ 社会规范(也叫主观规范或社会影响)指个人对于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网络成员(如同辈群体、同事、家庭成员等)的压力。
④ “解释的弹性”,是芬伯格借用的建构主义者的概念,它原本用来讨论观察数据的模糊性,但后来被平奇(Trevor Pinch)和比克(Wiebe Bijker)用来解释技术装置功能的模糊性。这后一种用法可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种技术装置只有一个名字,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和设计,如自行车。芬伯格说的正是“解释的弹性”的这样一种用法,认为它可以挑战建立在“技术必然性”基础上的专家治国论,为寻求技术的多种选择提供理论支持。(参见,孙浔,走向技术民主和文化多元——安德鲁·芬伯格技术哲学研究[D],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P22-23)
⑤ 2007年12月,社会科学引证指数列出了1700多条引证,有学者在Google上搜索出了5000多条引证TAM的两篇文章(Davis,1989; Davis et al.,1989)。
⑥ TAM对意向变量的解释力度分别为45%-57%;TAM2对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意向的解释力度分别为40-60%和34-52%;UTAUT模型的解释力度为70%;TAM3对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解释力分别为52-67%和43-52%。
收稿日期:2009—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