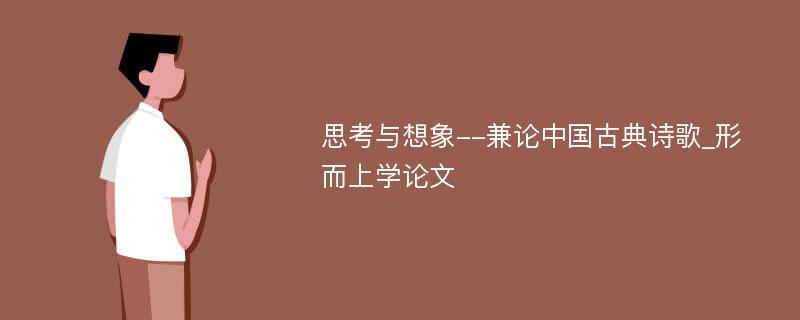
思维与想象——兼谈中国古典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典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哲学界在讲到把握世界的方式时,似乎只谈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而最终推崇的只是理性认识,只是思维;至于想象,则根本不谈,即使谈到了,也是把它当作一种低级的认识能力而加以贬斥。
这种哲学观点主要源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旧形而上学。柏拉图关于“想象”、“信念”、“理智”和“理性”(“知识”)的四分法实可归结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二分法。柏拉图把前两者概括称之为“意见”,后两者概括称之为“心智”;实际上,“意见”就是指感性认识,“心智”就是指理性认识。柏拉图认为前者所讨论的是生成变化,后者所讨论的是存在,〔1〕后者高于前者,思维高于想象。
我们知道,柏拉图所谓的“想象”,以感性事物的影像为对象,想象是对此种影像的认识能力;他可谓“理性”以概念、理念为对象,是对概念、理念的认识能力。他认为感性事物是想象中的影像的原本,而感性事物又是理性中的概念、理念的影像,感性事物以理念、概念为原本。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的最高任务就是认识理念,亦即从感性中直接出场(在场)的东西(作为理念之影像的感性事物以及感性事物的影像)追溯到它们的原本即永恒在场的东西(“理念”)〔2〕;诗人、画家与影像打交道,因而应被逐出哲学领域之外。
自柏拉图以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对思维与想象及其关系的理解,基本上都建筑在这样一种“影像——原本”(“IMAGE-ORIGINAL”)的公式之上。我在其他许多文章中都已阐述过,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崇尚在场和水恒在场的领域,而这样的领域乃是与“影像——原本”的公式分不开的。也正因为如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一般都贬低想象:直接感性中或者说知觉、直观中的事物也好,概念、理念也好,都是在场的东西;想象却总是要飞离在场,这在一心以追求永恒在场者为根本任务的传统形而上学看来,显然是难以容忍的。传统形而上学不屑于与不在场的、空幻的“无”打交道,因而压制想象、怀疑想象(形而上学并不简单排斥想象)就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本性。
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几乎是第一个打破柏拉图关于想象的旧观点的哲学家。他说:“想象是在直观中表象出一个本身并不出场的对象的能力。”〔3〕他的这一定义虽然仍有柏拉图从影像追溯到其原本的思想痕迹,但在康德这里,旧形而上学得到了一次再定位,康德不是把想象放在一个趋向“纯粹在场”的领域,像柏拉图所主张的那样,而是放在一个既有在场又有不在场的领域。康德认为想象乃是主体的综合能力,即为主体构成对象所需要的综合能力,想象是概念与直观之间的中介,是使知性纯概念同直观对象相结合,从而使经验、知识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桥梁。只是通过想象,概念才不再如柏拉图的理念那样成为“纯粹在场”的“离开了空气的鸽子”,康德的想象为概念提供了一个“图式”。所以在康德这里,想象的作用不再是为了经由它而回到原本——回到”纯粹在场”,而是要把在场与不在场综合为具有统一性的整体而成为现实的知识对象
但第一,康德的想象虽然是为了把“纯粹在场”(“永恒在场”、“常在”)与感性直观综合在一起,他最终还是把思维、概念看得高于想象;第二,康德认为在实践理性的领域里,是不掺杂想象中的感性杂质的,康德显然没有脱离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那种崇尚思维、概念而轻视想象的窠臼。
2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几千年来受压制的想象得到解放,当然这种解放不是一蹴而就的。
胡塞尔严格要求回到事物本身,因此,在胡塞尔的现象学那里,初看起来,似乎没有想象的余地。但胡塞尔的现象学从来不是简单地回到事物本身,他认为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敞开一个使事物如其本然的那样显示出来的领域。胡塞尔甚至明确断言:“幻想’构成现象学的最关键的因素……,幻想是‘永恒真理’的知识得以维持的源泉。”〔4〕胡塞尔认为一般的想象乃是指“影像—意识”,它以知觉为基础,而“幻想”则是一种特殊的想象形式,“幻想”是没有物理的东西作基础的,“幻想”甚至可以说没有被表象、被代表的东西,因而具有非真实性的性格,例如幻想石头经过窗户而不打破窗户,就是如此。声称严格要求回到事物本身的胡塞尔却更重视“幻想”,而不仅仅是重视一般的想象。何故?
胡塞尔所强调的所谓回到事物本身的“严格性”,实际就是要求真理必须得到确证。他所讲的“本质直观”就是要求直观到本质,或者说,让本质在直观中出现。“本质直观”(又称“本质洞见”)与“经验直观”(又称“个别直观”)有相同之处,即二者都有直观的性格,在“本质直观”中,本质就像“经验直观”中的个别事物一样是被给予的、现成的;但“本质直观”又有不同于“经验直观”之处,“本质直观”起于“经验直观”,是“经验直观”的变形,具体地说,“本质直观”是在有了“经验直观”的基础上,以“经验直观”中可见的个别事物为范例而形成的。但“本质直观”中所需要的这种范例只要原则上是能出现的和可见的就可以了,而不必只由知觉提供,——不必实际存在,也就是说,此种范例也可以由“幻想”来提供〔5〕,即此种范例可以是实际经验中从未出现过的。因此,在胡塞尔看来,“幻想”可以让无穷多的个别事物作为本质的范例而被直观到,让本质、真理在无穷多的范例中得到确证。这也就是说,“幻想”可以达到现实中被给予的、现成的东西所达不到的可能性〔6〕。据此,胡塞尔认为,诗歌、艺术,甚至几何学,都是通过“幻想”而洞察到本质,或者说,都是通过“幻想”而达到一种“本质直观”。
3
我们平常说,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乃是从认识个别到认识普遍,从认识千差万别、变动不居的现象到认识同一、永恒、常住不变的本质,这普遍、本质、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剥离了具体的感性杂质的,因而是抽象的(黑格尔所谓的“具体抽象”,归根结抵仍然是不同于感性具体的抽象)。究竟是怎样从具体走到抽象、从感性直观走到思维概念的?尽管我们平常都说,这个过程是靠我们的认识一步一步地撇开具体性、特殊性而达到愈来愈大的普遍性,但最终总有一个高于具体性、特殊性的抽象普通性。我们把这个过程叫作“飞跃”——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感性直观到思维概念的“飞跃”。但“飞跃”一词远未能说明和解决感性直观与思维概念这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和结合问题。康德早已通过他的“图式”说(SCJEMATISM)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是一种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一种使本质概念成为可见的东西的一种方式。康德认为,“图式”是本质概念与感性直观中的个体相联结的桥梁。例如三角形的概念是抽象的,但我们对某一个个别的具体三角形却可以抽去其特殊性如边的长短、角的大小等不相干的规定性而构成一个三角形概念的“图式”〔7〕,此“图式”既非个别三角形的感性具体形象,又非抽象的概念,但又具有这两方面的特质,它乃是通过一个感性具体的三角形为抽象的三角形概念提供了一个具有一定感性成分的“略图”(我们甚至可以在不严格的意义上把这个范例称为概念的“影像”),而此“略图”即“图式”,“其本身总是想象的产物”。〔8〕康德的“图式”说要求我们,从感性直观到思维概念的“飞跃”,必须通过想象,必须以想像的产物“图式”作为两者的结合点。康德至少启发了我们,我们平常讲认识论不讲想象,未免太粗糙了、太简单了。
但康德的“图式”说是否就解决了从感性直观到思维概念的飞跃问题呢?他的“图式”终究不能使本质概念本身成为可以被直观到的东西。
前面谈到的胡塞尔的“本质直观”说,是对康德“图式”说的继承和发展:他企图通过范例意识,即通过感性具体直观中的个别事物作为范例以直观到本质;他强调通过想象,特别是通过“幻想”,以达到平常实际知觉中所达不到的可能性,为人类的视域展开无限广阔的天地,从而为诗歌、艺术、甚至几何学的可能性提供理论根据。这些,都是胡塞尔的哲学贡献。但是胡塞尔越是力图通过个别的感性范例使本质概念成为可以被直观的东西,本质概念本身是否可以被直观的问题就越是明显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康德的“图式”说也好,胡塞尔的“本质直观”说也好,本意都是不满意于纯思维概念的抽象性,不满意于其脱离感性具体的特性,都是出于对柏拉图的“理念”的“鸽子”企图脱离空气而飞翔的旧观念的批判和拯救。但只要我们不超越那种以本质概念为万物之本根的哲学方向,我们无论采取康德的方案还是采取胡塞尔的方案,都摆脱不了本质概念本身不能被直观的问题,这种哲学方向注完了它的抽抽性
4
对于当前事物寻根问底的方式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由感性中的东西进到理解中的东西追问,这种方式以理解中的东西如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为根为底,这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追问方式。西方现当代的人文主义思潮如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的哲学已不同程度地不满足于此种方式所固有的抽象性。他们也主张超越当前事物,追问其根底,但不是到抽象的本质概念中去找根底,而是从当前在场的现实物出发超越到其背后、作为其背景的未出场的东西,这未出场的东西不是抽象的本质概念,而仍然是现实物。这背后的现实物乃是当前出场的现实物的根底。如果前者叫作“纵向超越”,则后一种追根问底的方式就可以叫作“横向超越”。由于任何当前出场者所植根于其中的未出场的事物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此种方式,我又把它称之为“无底论”,它的底是无底之底,相对而言,则前一种方式可以叫作“有底论”〔9〕。有底论所崇尚的把握事物的方式是思维,思维的产物是本质概念,是同一性、普遍性。无底论则超越此种方式,它要求把在场的现实事物与不在场的、然而也是现实的事物综合、结合、融合为一个相通相融的整体,因此,它所崇尚的把握事物的方式是想象,而不是停滞于思维。这里所说的想象是指把当前在场的现实事物与不在场的现实事物综合为一个“共时性”的整体的能力。只有哲学的这种横向转向,才能打破、超越传统形而上学所固有的抽象性,从而超越本质概念本身不能被直观的问题。总之,人们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普遍性的本质概念的追求,而是聚焦于现实事物间的结合与融通。
5
这种转向在胡塞尔那里已有了比较明确的发端,海德格尔等人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方哲学在作了这种转向以后,思维、概念(还有感性直观)因其固执于在场的东西,不再像在旧形而上学那里那样,被奉为至上的东西,而是被视为在把握事物的途程中需要被超越的次要环节;想象则因其飞离在场,不但不像在旧形而上学那里那样难于被容忍,反而成为受尊崇的最高环节。过去人们注重一步一步地摆脱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的具体联系,以达到“纯粹的在场”(PURE PRESENEE)或“恒常的在场”(CPMSTANTPRESENCE),如数量的概念、各种事实的概括概念,它们都是思维的目标和对象;现在则注重于超越在场者,超越直接感觉的距离,而高扬不在场者,显现不在场者,力图把事物背后的、隐蔽的方面综合到自己的视域之内。过去人们注重把同类的东西概括在一起,撇开同类事物所包含的各种可能的具像,找出其中的同一性,划定同类事物的界限;现在则注重不同一性,即不但注重同类事物所包含的无穷多不同的可能的具像,而且注重超出已概括的普遍性的界限之外,达到尚未概括到的可能性,甚至达到实际世界中认为不可能的可能性。
6
“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人们多次对各种具像进行感觉观察后运用思维所概括出的普遍性或同一性,它成了“恒常的在场者”,人们据此而推定下次观察中乌鸦黑的现象必将出场,这是思维的逻辑所告诉我们的。但是思维的逻辑果真能保证下次观察中出现的乌鸦必然是黑的吗?不能。由此可见,推断下次观察到的乌鸦必黑,实无逻辑必然的理由,思维的概括功能的可靠性并非绝对的,而且这种可靠性与事物无限性相比甚至可以说趋近于零。所以严格说来,科学家们凭直观和思维得到的规律,也不过是关于已经观察到的事物的规律。思维总是企图界定某种事物,划定某种事物的界限,但这种界限是不能绝对划定的。我们应该承认思维的局限性,但也正是在思维逻辑走到尽头之际,想象却为我们展开一个全新的视域。想象教人超出概括性和同一性的界限,而让我们飞翔到尚未概括到的可能性。前面说的下一次观察的乌鸦可能不是黑的,乃是我们运用想象的结果,它是一种想象的可能性——种尚未实际存在过的可能性。但尚未实际存在过的可能性并非不可能,想象的优点也正在于承认过去以为实际上不可能的东西也是可能的。想象扩大和拓展了思维所把握的可能性的范围,达到思维所达不到的可能。思维的极限正是想象的起点。
想象并不违反逻辑,例如说下次观察到的乌鸦可能不是黑的,这并不违反逻辑,但它并非逻辑思维之事,可以说,想象是超逻辑的——超理性、超思维的。逻辑思维以及科学规律可以为想象提供一个起点和基础,让人们由此而想象未来〔10〕,超越在场的东西,包括超越“恒常在场的东西”。科学发现和发明主要靠思维(包括感性直观),但也需要想象。科学家如果死抓住一些实际世界已经存在过的可能性不放,则眼光狭隘,囿于实际存在过的范围,而不可能在科学研究中有大的创造性的突破。科学的进展过程中时常有过去以为是颠扑不破的普遍性原理被超越,不能不说与科学家的想象力,包括幻想,有很大的关系。
7
思维以把握事物间的相同性(同一性、普遍性)为己任;想象以把握不同事物间即在场的显现的事物与不在场的隐蔽的事物间的相通性为目标〔11〕。对后者的追求并不排斥对前者的追求〔12〕,只是后者超越了前者。我们说想象是超理性、超思维、超逻辑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在场的东西与不在场的东西的结合与融通,其中的在场者与不再场者都不只是指此一简单的物与彼一简单的物,而更多地是指蕴涵理在内的事物。凡事物都包含有理,凡个别都包含有普遍,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所谓想象的综合力,应是指把在场的、事与理相结合的事物同不在场的、事与理相结合的事物综合在一起的能力,这也就是想象综合力之所以既不排斥思维而又超越思维的一个重要含义。
8
前面说的哲学转向是就西方哲学发展的大概趋势而言的。中国传统哲学一般说来不太重视“纵向超越”所追求的本质概念的同一性、普遍性,而重“横向超越”所追求的现实事物间的融通。中国哲学所讲的天人合一或天人相通,就天之自然意义而言,乃是指人与自然间的相通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哲学已达到了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横向超越”的水平,我更无意说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横向超越”不过是步中国传统哲学之后尘。相反,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横向超越”,是经过“纵向超越”之后的哲学转向;而中国传统哲学,从占主导地位的整体角度来看,则缺乏“纵向超越”的阶段。
中国古典诗在讲究从在场的现实事物想象到不在场的现实事物的关系方面,是最具特色的。
刘勰《隐秀篇》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他所讲的隐和秀,其实就是讲的隐蔽与显现的关系。文学艺术必具诗意,诗意的妙处就在于从“目前”的(在场的)东西中想象到“词外”的(不在场的)东西,令人感到“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这也就是中国古典诗重含蓄的意思。但这词外之情、言外而之意又不是上述“纵向超越”所要求超越到的那种抽象的本质概念,而仍然是现实的东西,只不过这现实的东西隐蔽在词外、言外而未出场而已。抽象的本质概念是思维的产物,词外之情、言外之意则是想象的产物,这也就是以诗的国度著称的中国传统 之所以重想象的原因。且引柳宗元的两首诗作一对比: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
这首诗所描写的画面真是状溢目前,历历可见,可谓“秀”矣。但如果仅仅看到这首诗的画面,显然还不能说领会到了它的诗意。实际上这首诗的妙处就在于它显现了可见的画面背后的那种遗世而独立的孤高的人格和境界:你不仅仅可以想象到作者柳宗元本人谪居异地、不畏雨 横风狂而泰然自若的情景,你还可以想象到其他一些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的高风亮节,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诗人的言外之意,词外之情,虽未出场,却很现实,虽未能见,却经由画面而显现。这里的“显现”不是感觉直观意义下的显现,而是想象意义下的显现。当然,这首诗的“孤舟”、“独钓”之类的言词已显露了孤高之意,但这只是表面的,其深层的内涵仍然可以说隐蔽在词外、言外,而有待人们的想象。
柳宗元的另一首诗云: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毲 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渔翁》)
此诗的前四句本已通过一幅历历如在目前的画面令人想象到了渔翁那种悠闲自在的境界,但作者偏要在最后用“无心”这样的概念来作一概括,就反而了无余味,因为前四句让人想象到的那种人与自然合一的高超境界,可以引起许许多多的生动的画面,决非渔翁的“无心”所可以简单概括的。这首诗之所以遭到后人批评,实因其缺乏“隐秀”之意,当然,从这方面来说,白居易的许多诗作之概念化的毛病就更多了。
9
中国古代绘画讲究神似与形似,其实也可以用“隐秀”的道理来说明。一幅真正有诗意的画总是主客的融合体,它表达了画家与其所画之物的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所谓形似与神似的统一,就是指这种主客的融合。那种刻板地一味摹拟事物的单纯形似之作,是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的。真正的艺术品既似物,又能于所画之物中令观赏者想象到隐蔽在此物背后的神,这就是“神似”。五代时期的画家荆浩说:“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仅有形似,不算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必“气质俱盛”,即形似与神似的统一。所谓“不似之似”就是艺术的真实。有一种看法认为“神似”是指画家本人的精神与所画之物的精神相似。这种讲法表面上意在说明两者的统一,实际上是把它们分裂了。主客融合、天人合一的境界并不是两种不同精神的融合或合一,而是一种精神(实即境界)。离开了人,物(形)本身说不上有“神”;离开了物(形),神本身亦无着落。所谓?“神似”,乃是要求我们通过艺术品进入一种(唯一的)精神境界中,于其形中见到神,于其显现的、在场的东西中想象到隐蔽的、不在场的东西。
10
诗人之富于想象,让鉴赏者从显现的东西中想象到隐蔽的东西,还表现在诗人能超出实际存在过的存在,扩大可能性的范围,从而更深广地洞察到事物的真实性。我们通常把这叫作夸张。李白《秋浦歌》之十五:“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里的极度,夸张,真实就是想象的一种极端形式“幻想”,一种对实际存在中从未出现过的东西的想象。白发竟有三千丈之长,此乃实际世界中从未有过的,诗人却凭幻想,超出了实际存在的可能性之 外,但这一超出不但不是虚妄,反而让隐蔽在白发三千丈背后的愁绪之长显现得更真实。一个毫无想象力的人也许会凭感觉直观和思维作出白发一尺长或两尺二寸长这类的符合实际的科学的概括,但这又有什么诗意呢?〔13〕如果说科学家通过幻想,可能做出突破性的发现和创造性的发明,那么诗人则是通过幻想以达到艺术的真实性;如果说科学需要幻想是为了预测未来(未来的未出场的东西),因而期待证实,——期待未出场的东西的回答,那么诗意的幻想则不期待证实,一一不期待未出场的东西的回答,它对此漠不关心,而只是把未出场者与出场者综合为一个整体,从中显示出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
11
西方传统美学的典型说基本上是以前面说的“纵向超越”即以追求普遍概念为目标的理论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学家描述已发生的事情,诗人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诗比历史更哲学、更严肃,因为诗所说的大多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东西(《诗学》第9章)。亚氏所说的普遍性就是典型,诗意就是从个别的东西中见出普遍性。亚氏还把典型与理想联系起来,认为艺术品应当按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摹仿,例如画美人就该画出集中美人之优点的最理想的美人。这种典型观,实以本质概念(例如理想的美人的概念)为依归,来源于柏拉图的“理念”。“理念”本来就有普遍性、理想性的意思,艺术品应以“理念”为原型或模型。西方近代流行的“典型”一词与“理念”有密切的关系。康德虽然承认审美意象所包含的意蕴远非明确的普遍性概念所能充分表达,有越过“纵向”结构的传统的思想因素,但他没有充分发挥这一思想,而且他的美学思想中的“规范意象”显然未脱旧的追求普遍性概念的窠臼。近代美学的典型观已经把重点转到特殊性,重视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但即使是强调从特殊出发的歌德,也主张在特殊中显出普遍,所谓“完满的显现”就是显现出本质概念,仍然是走的“纵向超越”的传统道路。黑格尔所谓“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明显地是要求艺术品以追求理念为最高目标,尽管他也要求典型人物须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前面谈到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所要求的词外之情、言外之意,一般不是西方传统美学所要求达到的普遍性概念,而是和文内、言内所言及的物象一样是现实的。例如柳宗元《江雪》的言外之意是孤高的人格和境界,它引起读者想象到的各种具体的情景都不是抽象的普遍性概念,而是非常现实的,只不过这些现实的事物没有在诗中出场而已。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诗中的一个“在”字用得很妙,它点出了白头宫女的在(场),却显现了(在想象中的显现)昔日宫中繁华景象的不在(场),从而更烘托出当前的凄凉,然而后者只是言外之意、词外之情,既是隐蔽的,却又是现实的,而非抽象的普遍性概念。我国文艺理论界近半个世纪以来往往用西方旧的传统典型说来解释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所讲究的言外之意,认为此“意”即是普遍性,能在个别中寓以普遍,就算是言有尽而意味无穷,就算是给读者留下了最广阔的想象余地。其实,思维中普遍性概念重在界定在场的某类事物,而想象则重在冲破界限、超越在场,不仅冲破某一个别事物的界限以想象到同类事物中其他的个别事物,而且冲破同类的界限以想象到不同类的事物。所以前者与后者相比,其给人留下的可供玩味的余地显然是很有限度的。用西方传统认识论来解释中国诗的言外之意,把中国古典诗的艺术鉴赏当成一种理性思维的认识过程,则有如隔靴搔痒,很难把握中国古典诗的妙谛。莫里哀的《伪君子》倒是写出了典型人物或者说同类人物的最具普遍性的特点,而不是某一个别人的精确画像,它与中国古典诗歌理论所要求的重含蓄、重言外之意相比,乃是两种不同的哲学理论基础的产物,不可混同。即使是强调个性、强调让鉴赏者从个性中看到同类事物中其他很多很多具 体的个体事物的理论观点,与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之强调言外之意相比,也是大不相同的,前者 是在此一个体事物中看到同类的其他个体事物,仍然是在同类型即普遍性的概念范围之内打 圈子,就其为同类型而言,此一个体事物与其他个体事物同属在场的东西,这是西方传统哲学 以追求“永恒在场”的概念、理念为目标的思想表现。像中国古典诗由白头宫女之在(场)想象到 昔日繁华景象之不在(场),显然不是西方旧的典型说所可以容纳的。
注释:
〔1〕柏拉图:《理想国》509-511,533-534。
〔2〕柏拉困所谓的“理智”是数字、几何学之事,它们所讲的概念仍夹杂有感性形象,故“理智”居于“意见” 与“理性”之间.这个问题与本文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
〔3〕〔7〕〔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151、714、179。
〔4〕〔6〕胡塞尔:Ideen zu einer reinen Phanomenologic und ph anomenologicshenPhilosophie,erstes Buch,Husserliana 3,ed.Walter Biemel (The Hague:MartinusNijhoff,1950)§70,§70。
〔5〕同上,§3,§4;并参阅John Saltis,double truth,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 Press,1995年,第128-130页。
〔9〕参阅拙文:《哲学的转向及其影响》,载《方法》杂志1996年第7期。
〔10〕想象当然总是具有或然性。我这里所讲的实际上是体谟的归纳问题。我从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思维与想象的角度来论述他的问题,用“想象”代替了他的“习惯”,但这并不是名词上的不同。动物和人一样 有习惯,但动物没有想象。
〔11〕关于相同性与相通性,请参阅拙文《相同与相通》,载《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12〕我既不同意实在论把普遍性、同一性之类的概念(共相)看成是独立存在的实体的旧形而上学观点,也不同意把共相看成仅仅是名称而无指称对象的唯名论观点。我以为这种概念是一种理想性的设定,它既非实体,也非任意的虚构,科学家可以让他们在某种科学理论体系中起作用,从而使此种理论体系具有说服力和预测未来,所以,对普遍性、同一性的追求,是科学的需要。
〔13〕在我国文学史上,居然也可以找到这样缺乏想象力的文学评论家的实例:杜牧《江南春》中“千里莺啼绿映红”本是一首极富想象的佳句,而杨慎《升庵诗话》却责备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录……皆在其中矣。”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柏拉图论文; 康德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胡塞尔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