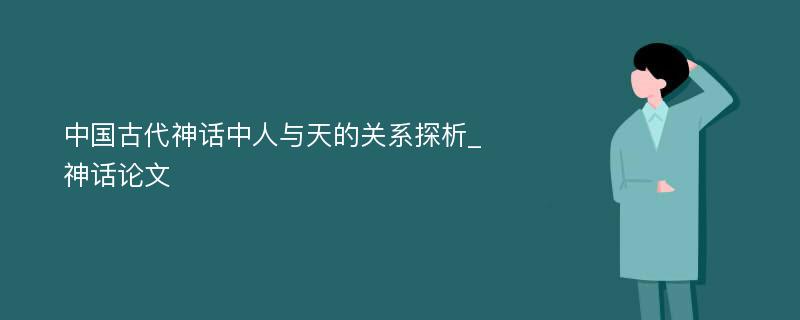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天人关系”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神话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社会,神话常常被人与荒诞、夸张等相提并论。因为这些被远古时代的先民们所“创造”出来的传说和故事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和离奇的内容。然而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说:“我们从历史上发现,任何一种伟大的文化无一不被神话原理支配,渗透着。”(注: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5页。 )对这些“神秘而荒诞”的故事和传说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寻找到我们文化传统的根之所在,并且帮助我们把握到我们的“人与自然”、“人与环境”观念的变化与发展历史。神话的研究现在已经涉及到许多领域,例如分析考察神话故事背后的历史事件真相,考察探寻神话人物的演化过程以及神话人物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作用,研究神话思维的方式和通过神话故事所叙述的内容探究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即神话中的哲学等等。本文则试图根据中国神话中的创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以及自然神话的故事内容来探讨中国“神话中的哲学”的一个方面即“天人关系”。
“神话”这个概念原本是舶来品,而非中国特产,因此我们不能按中文字面望文生义。英语(Myth)、德语(Mythos)、法语(Mzthe )的“神话”一词的第一层含义都有传说和故事的意思,它们都来源于希腊语(mythos),指传说、故事、历史、寓言。汉语文化界在翻译时选择了“神话”这个词与之对应,但它并不表明,神话的先决条件是“神”,似乎必须有“神”,然后才有“话”。对此误区,袁珂认为“只是因为它和宗教的关系密切,宗教奉祀的神多有神话为之传述形迹,所以才引起人们对神话必须有神的错觉。在原始社会前期,当宗教尚处萌芽状态,即仅有宗教意识而无宗教仪式,无所谓对神的崇拜,因而早期神话中并没有出现后世概念中所谓的神。”(注: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5页。)
神话之所以产生和传播其解释功能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原始人对自然现象,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以及对人类起源和历史的探究是通过神话“公布”于众并流传后世。我们通过对神话的分类可见其“思考”和“解释”的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神话都可以被分为创世神话(其中包括关于宇宙起源即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文化起源以及氏族和民族起源等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自然神话(包括日、月、星辰、四季和五方神话)等等。这些话题不正是今天人们关于世界的本原、人类的历史、宇宙的形成等哲学、历史和科学所关心讨论的问题吗?由此可见神话与今天人类的文化传统以及科学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类要想在地球上生存,首先必须了解和认识自己的生存环境。因此也就有了关于自然(天)、人类以及自然与人类(天人)关系的讨论。中国神话中就有许多解释什么是自然、人类是从何而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故事。例如神话用“烛龙的故事”解释了昼夜和四季的产生原因是:“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臂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东山下。”(注:《山海经·海外北经》。)雷鸣这一自然现象被理解为是雷神鼓腹发出来的声音。在神话中可以发现这样的说法:“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注:《山海经·海内北经》。)
干旱的故事在中国的神话中也经常出现,但说法不一,或许是因为形成这类神话的地区各有不同。然而它所带来的灾难和恐惧在原始人心中留下了太深的印记。一种说法是应龙(有翼的龙)杀死了蚩尤和夸父,不能再上天宫,天上没有应龙储水降下来,因而大旱。另一解释是应龙与蚩尤大战时,蚩尤使狂风暴雨助战,应龙无法施展他的技能,于是黄帝便派名叫魃的青衣女子与蚩尤作战,魃一到,雨便止,蚩尤兵败被杀,魃也因此不能重上天宫,她所呆的地方就不再下雨。此外,天旱也是“十日并出”的缘故,这是著名的“后羿射日”故事中的解释。
对于太阳的关注在中国神话中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因为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人类的生存与太阳的变化息息相关。神话中的太阳神帝俊被尊为天上的首领,多妻又多子,还拥有属地。因而太阳神的家完全是一个人“观念”中的美满家庭。或许有关太阳的神话产生于沿海一带,太阳神的妻子们都以洗澡的形象出现,例如:“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注:《山海经·大荒南经》。)另一妻子则生了十二个月亮,对她的描述是:“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此始浴之。”(注:《山海经·大荒西经》。)太阳神还有属于他的竹林和祠坛,将竹林的竹子截下一节,分剖开来,就成为两只天然的船。而帝俊的祠坛有美丽的五彩鸟帮他管理:“卫丘方员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注:《山海经·大荒南经》。)“帝下两坛,采鸟是司。”(注:《山海经·海内北经》。)由此可见原始人是以人类社会为原型来复制自然,解释自然,使自然界包括动物、植物、无机物和有机物都被人格化,并具有类似于人类的组织形式和社会特征,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古代先民们的这种“以己度人”(应是以己度物)的思维方式就认为原始人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在中国神话中人类同样也被视为是自然的一部分。“女娲造人”在解释人类起源时,就认为土是人类形成的基本原材料,造人时,工作忙碌极了,以至远不能满足需要,只好用绳子粘上泥浆挥洒成人:“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注:《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自《风俗通》。)这大概是因为原始人发现植物与土地的联系而受到的启发。这也可以说明,人类把自己与植物同等看待,而没有将人类摆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
不仅如此,一些神话传说还主张某些氏族部落的始祖起源于动物,例如殷商始祖契的出生便与玄鸟有关系。神话中有“玄鸟生商”的故事:“殷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注:《史记·殷本记》。)神话的这种对人类起源的观念是将人类归于物理世界,或者说是把人类起源“拟自然化”。这种观点还可以在原始部落的断发纹身风俗中找到印证。闻一多称之为“人的拟兽化”。他在“伏羲考”一文中认为:“在我国古代,有几个著名的修剪头发(断发),刺画身体(纹身)的民族,其装饰的目的则在摹拟龙的形状”。(注:闻一多:《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页。)“他们断发纹身以像龙,是因为龙是他们的图腾。换言之,因为相信自己为‘龙种’,赋有‘龙性’,他们才断发纹身以像‘龙形’。”(注:闻一多:《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页。)可见,远古的人们并不把自己看得比动物高等。“人类是万物之灵”只是一个现代人的观点。所以,卡西尔认为,“对神话和宗教的感情来说,自然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生命的社会。人在这个社会并没有赋予突出的地位。他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但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比任何其它成员更高。生命在其最低级的形式和最高级的形式中都具有同样的宗教尊严。人与动物,动物与植物全部处在同一层次上。”(注: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同样,神话对人与自然的这种解释虽然在现代人看来奇怪甚至荒唐,但它并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原始人的无知和幻想。古代的先民们虽然处于原始的思维状态和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但对周围环境仍有相当的观察、区分和认识的能力,否则这些未开化的人们无法在环境艰苦的世界生存。神话对人与自然的解释是建立在一种观念的基础上的,即“天人同构”或“物我同一”的观念上。这种解释天人关系的方法我们在中国历代哲学家的理论中都能寻找到一些痕迹,春秋战国时期的庄子就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西汉的董仲舒也认为天和人在结构上有共同之处,只是在他看来天比人的地位要高得多,人是天的缩影,人的精神、形体、情感等都与天相符,叫做“天副人数”,董仲舒因此也认为天和人是相互沟通的,他称之为“天人感应”;也就是说,天可以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来指导万物和干预人类社会,人的行为也能够感动天。
神话之所以会形成“天人同构”、“物我同一”的观念,乃是因为“神话是情感的产物,它的情感背景使它的所有产品都染上了它自己所特有的色彩。原始人绝不缺乏把握事物的经验区别能力,但是在他关于自然与生命的概念中,所有这些区别都被一种更强烈的情感湮没了:他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族关系似乎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注: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05页。)从这种情感和观念出发, 神话中的许多奇怪的形象和故事便可以得到解释。例如,人首蛇身或人首龙身的形象并不是原始人的荒唐幻想,而是以这种“亲族关系的预设”和“天人同构”、“物我同一”观念为前提的氏族图腾在社会的发展中演变的结果。闻一多先生称之为由“人的拟兽化”到“兽的拟人化”的演变,是图腾开始蜕变为始祖的一种形态,但这种拟兽化的企图只能使人做到人首蛇身或人首龙身“半人半兽”的地步,虽然纹身可以使人身看上去像龙身,但人的脸孔最终却无法改变得像龙的脸孔,于是也就成了人首蛇身(龙身)。按以己度人的思维方式来想象自己祖先的模式,祖先也必定是半人半兽,所以女娲便成了人首蛇身,当然还有伏羲,烛龙和共工等。此外,神话故事中还有人面鸟身(祝融)、人面马身(句芒)等等,这也应该是鸟的图腾和马的图腾的蜕变形态。
同样基于“亲族关系的预设”和“天人同构”、“物我同一”的观念,还有大量的神话表达了天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应是同一和谐关系的愿望,因为这些神话认为,最初的时候人和神可以通过天地之间的“天梯”(一种与天地相连的树或山)相互来往、相互沟通。所谓:“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注:《淮南子·地形篇》。)而“建木”这棵神奇的通天大树是由黄帝所植,伏羲和太昊可以由此上下于天地之间。除此之外,昆仑山也被看作是一座神圣的“天梯”,登上山的第三层,即山颠,便可以到达天帝居住的地方。“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注:《淮南子·地形篇》。)神话在故事中所描述的是原始先民所向往那种人与自然融洽和谐的生活环境,这种愿望和憧憬,我们在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逍遥游”中也能深深地感受到。
然而人与天的冲突和对立同样是神话世界不可回避的内容。古代神话常常涉及到这种对立和冲突。许多神话认为,对立与冲突是由于世界的原有的秩序遭到破坏,其中既有自然界(天神)自身的原因,也有人类的作用。神话在叙述中特别强调自然界尤其是天界的秩序,并说在东北角和大荒的西北角与最西端有神人专门负责日月星辰运行,不使它们的前后秩序发生混乱,但一旦秩序被打乱,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便由和谐一致变为对立斗争,自然界的秩序的混乱表现为自然灾害,它给人类造成了生存的危机,其中干旱的恐惧在原始人的记忆中尤为深刻。在一些神话中多次提到干旱的原因是太阳不按顺序轮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注:《淮南子·本经篇》。)另外应龙与蚩尤打仗,离开天宫不能再行使蓄水的职能,旱神女魃因助应龙战蚩尤,离开天宫不能返回,致使女魃所居之处大旱。这些都是天界次序混乱的表现。
但中国神话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在:它不仅仅将自然灾害归罪于天,而且也更多地指出人为的原因。人类的破坏活动同样会造成自然秩序的混乱,从而给天人关系带来的不和谐与不平衡,著名的故事是共工怒触不周山。《淮南子·天文篇》描述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此外,“绝地通天”的故事指出了人为的活动,主要是人类的战争会造成自然秩序的混乱。为了避免这种混乱,颛顼当国君时,断绝了天地相通的路径,使天地、神不相往来。《国语·楚语下》记载:“古者民神不杂。及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天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通天’。”由此可见中国神话与西方神话的一个重要区别,后者大都将天灾人祸说成是上帝或天神的喜怒哀乐与恶好的结果。
既然自然灾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类当然要奋起与自然进行抗争,因而,神话中也有许多人类与自然斗争的记载。这些故事和传说充满了原始人复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它用充满感情的语言歌颂故事中主人公不屈不挠与自然抗争到底的精神,表达了先民们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愿望。夸父追日(和太阳竞走),一直追到死,至死都不认输,还让手中的手杖化为一片桃林与太阳抗争:“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注:《山海经·海外北经》。)精卫填海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虽是一只小小的精卫鸟,却要衔小树枝小石头来填平大海,以抗议大海将她淹死。若说这些故事的主人是为个人而奋争,那鲧则是为了广大百姓的生存与洪水抗争,他偷了天帝的“息壤”这种能够生长不息的土壤以堵挡汹涌的洪水,被天帝派来的祝融杀死在羽山。但鲧这种抗击洪水的精神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大禹来延续,这反映了远古先民对天的认识的变化,即他们开始感到不能只听凭自然力量和超自然力量的摆布,应当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哪怕是凭借精神和意志的力量。
然而神话还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或者说是神话的一种隐喻,即:在大量的人类与自然灾害抗争的故事和传说中,在神话中受到歌颂的英雄大都是悲剧性人物。夸父追日,结果渴死途中。后羿射日,虽射下九个太阳,为民除了害,但他却是众叛亲离,妻子嫦娥偷走了羿的长生不老之药独自上了月宫,羿本人不曾死在激烈的大战中,而是死于自己的学生逢蒙之手,因为“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唯羿愈己,于是杀羿。”(注:《孟子·离娄下篇》。)鲧为堵住汹涌的洪水,被天帝杀死于羽郊。精卫鸟虽锲而不舍地填海,可填平东海的目的可谓遥遥无期。只有大禹是个成功的英雄。但并不因其有与自然一样强大的力量,而是因他认识了自然的某些运动规律,顺势利导的结果:“禹尽力沟恤,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注:《拾遗记》·卷一。)因此,神话在讴歌那些以死来与自然力量抗争的悲壮气氛和抗争精神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个事实,即自然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只能顺应自然的发展,“无以人灭天”(注:庄子:《大宗师》。)。要征服自然,其结果同样是悲剧。
同时,在神话中依然可以发现原始人的这样一种信念:人与自然可以通过特殊的形式而达到相互感应。更确切地说,“自然界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行为。自然的生命依赖于人类与超人力量的恰当分布与合作。严格而复杂的仪式调节着这种合作。”(注: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例如, 各种巫术的仪式、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与天、神对话和合作以祈福消灾的一种行为,神话传说记录了名为女丑的女巫的求雨过程:“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下。”(注:《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注:《山海经·大荒西经》。)在神话中,旱神女魃是位穿青衣的女子,原始人相信将女巫打扮成女魃的形象,在太阳下曝晒,天帝会有所反应,降雨除旱。另一种说法是制做一个假的应龙,在久旱之后可以求得大雨:“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注:《山海经·海内北经》。《山海经·大荒东经》。)虽然人与天的这种对话并不总是成功,例如女丑穿青衣扮成旱魃祈雨,却被十个太阳暴晒致死,于是便有了后羿射日的故事;但是,求雨的巫术也常常是有效的:“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翦其发,历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注:《吕氏春秋·顺民篇》。)汤王祈雨的成功表明天人原则上是能够沟通与合作的。
正是因为神话在记述天人的对立和冲突时仍然基于“天人同构”、“物我同一”的观念和“生命形式都具有亲族关系的普遍预设”,故而巫术的理论才能得以成立和维持。反之巫术活动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原始人过分地相信自己的能动性,夸大自己的力量——意志与精神。
总之,中国神话在解释自然与人类,天与人以及两者的关系时,始终把自然、天看作是一个具有生命形式的活的总体。而不是像近现代西方哲学那样把自然看作无生命的物质对象。从人的本性上说,他与自然是同一的,同构的,或者说是亲族关系,所以天人可以通过巫术的复杂仪式和祈祷互相沟通并合作,使自然与人类、天与人达到和谐一致。这些观点看起来幼稚可笑,甚至荒唐,但却有其合理性。在经历了人类把自然作为一个实验室研究的无生命的物质对象,用科学技术和各种手段无节制的对自然进行肆意掠夺与征服以及遭到自然生态平衡失调给予人类的无情报复这样一个轮回之后,人们也发现自然就整体而言是一个庞大的生物链,一个生态系统,所以从这个视角看,自然确实是一个具有生命形式的活的总体。人们应当重新审思对“天”或“自然”观念,而不能只是在实验室去观察或解剖“天”或“自然”。
但另一方面,神话在情感上的那种征服自然的欲望也的确推动了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如卡西尔所言,“在人类文化的任一领域中,‘卑躬屈膝的态度’都不可能被设想为真正的和绝对性的推动力。从一种完全被动的态度中不可能发展出任何创造性的活力来。”(注: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恰巧是这种欲望和冲动,才使得人们去努力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综上所述,在古代神话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基本情绪和哲学内涵,并不会因为年代的久远而丧失其研究价值。相反,在中国神话中曾经表现出来的那种“天人和谐”的素朴理想与征服自然的情感欲望之间的矛盾,事实上仍然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
标签:神话论文; 中国古代神话论文; 国家的神话论文; 读书论文; 山海经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原始人论文; 动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