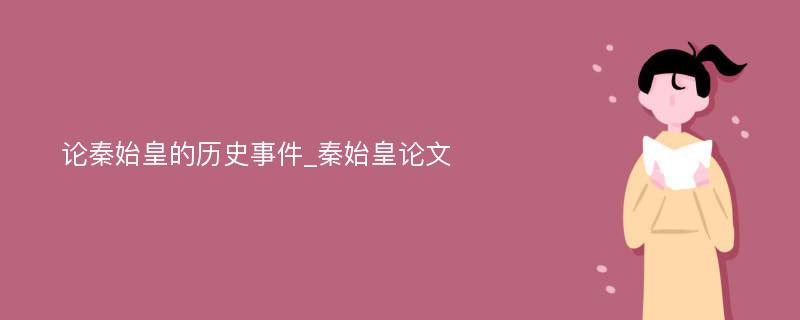
秦始皇史事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始皇论文,史事辨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秦始皇的血统问题
秦始皇的血统问题,向有不同说法。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载,秦始皇为吕不韦的私生子。原文是如下: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一名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这篇记载不为明代汤聘尹、王世贞等人所信,郭沫若则先是“深信不疑”,后又觉得“实在是可疑的”(注: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他们一致的看法是,记载中所说的“大期”,“《集解》徐广曰:“期,十二月也”。梁氏曰:《左氏僖十七年》,孕过期。夫不及期可疑也,过期尚何疑?”(注:梁玉绳:《史记志疑》。)又“异人请妇,至大期而诞子,未必请之时遽有娠也。”(注:汤聘尹:《史稗》。)据此,有人还指责司马迁既说“姬自匿有身”,又说“至大期时生子政”有矛盾,以此否定《史记》对此事记载的真实性。梁玉绳甚至干脆说司马迁紧接“姬自匿有身”而又写“大期始生”乃是“别嫌明疑”,以表示司氏也不信秦始皇为私生子之说。其实,这是误解了司马迁这句话的意思。他们显然是把姬的孕期从子楚与姬同居的时间算起了。同居十二个月后才生政,秦始皇非私生子岂非不辩自明?但实际上,文意昭然。吕献姬时,既然“姬自匿有身”,那么“至大期”自然是指从“有身”之时起至生政时的时间。这样,尽管姬的孕期为十二个月,秦始皇仍为吕不韦的私生子,是毋须争辩的。
还有学者问:司马迁所记的事若真实的话,何以《战国策》不载?这样的责问实难成立。第一,各人写史,取材不同,你取我弃,完全是正常现象,岂能因《战国策》未写秦始皇为私生子而《史记》的记载就不可信?实际上,《史记》中还写了“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而《战国策》同样也无。我们就能断定子楚是没有妻子的吗?这太说不通了。第二,私生子即非婚生子女,至少说明其母行为不轨,因而是不宜张扬的。所以“姬自匿有身”,只能有姬和吕不韦两人知道,连子楚也是会被蒙在鼓里的。及至政接了王位,吕自然就不敢说出去,一旦泄露了,在国人面前将何以自处?对秦王也不好交待。若秦王不承认吕这位生身之父,其命运是不难想象的。由于这个原因,《战国策》非不载也,是作者对此事不知道。
那么司马迁又何以会知道的呢?如果按照郭沫若猜测秦始皇为吕不韦私生子事是汉时吕后族人造的篡权舆论,意为秦早为吕氏天下,被刘氏夺去,现从刘氏手中夺回是应该的。那么这问题也就不必回答人人都能自明。但这样重大的篡权根据,在《史记·吕太后本纪》及吕氏诸人的“传”中,司马迁竟一字不提。这是不好理解的。所以此说未必确实。这里我倒也有一种猜想:《战国策》写到公元前221 年秦灭六国时止,秦始皇为吕的私生子,很可能是到了秦汉时才出于儒生之口。这些儒生身受秦始皇暴虐之害,不仅使他们记恨秦始皇,报复之念也是一直存在的。他们私下里或公开散布秦始皇为吕的私生子的流言以泄忿,也就实在算不得什么。而司马迁写史时,自然会探求和寻找流言的根据。以决定取舍。而从他在《史记》中对吕不韦的为人的描述来判断,真是“无丝有线”,不能不使他认为这是实有其事的:
第一,子楚在赵原为秦的质子,确是“落难王孙”,吕不韦从结识他那天起,就以商人的眼光视他为“奇货”,想从他身上获“泽可以遗世”之利,为此以姬为资本,设计献给了子楚。一旦子楚归秦继承了王位,自己的目的也就能达到。此目的,他在献姬前有计划地为达到让姬“有身”,以便日后加深和密切吕氏与子楚以至秦王室的关系,这怕不是说不通的。
第二,《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还讲到,吕既向子楚献姬,又在这之后与姬私通,为满足姬的淫欲,同时也怕事发而获祸,又以极下作的手段荐缪毐代己。这样一个品德极有问题的人,有什么无耻的事干不出来?因此,先使姬“有身”,然后让姬“自匿有身”献与子楚,这也同样不是吕所不可能做出来的事。
除了以上所说,我在这里举一个旁证。前面已说过,据《史记》所载可知,子楚在赵是原有夫人的,但未见夫人有子。子楚回秦继王位后,是为庄襄王,后宫自然不止夫人一人,但史书上也未见有谁生子的记载。姬在与子楚同居期间,除了生政外,又别无所出。由此可知,秦始皇是个无兄弟姊妹的独子。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子楚生理上是否有缺陷?如果这怀疑可以成立的话,则秦始皇就不可能是子楚有的,他为吕的私生子因此而得到证实。也因此司马迁才把这事写进了《史记》,后班固撰《汉书》又直称秦始皇为“吕政”,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持同样看法。可见,历史上几位史学大师对这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我想他们如此落笔不会是人云亦云而无一点依据的吧?因此,秦始皇的私生子身份怕不能轻易否定。
对秦始皇“禅贤”的蠡测
《说苑·至公》有如下一段论述: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始皇闇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皇位自然也是一种私产。赢政削平六国,当上了秦始皇,居然提出帝位禅让,这仿佛神话一般。因而有的学者说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或者说这纯系“小说家言”。这看法是一种可能。不过我们从深一层去考虑的话,亦许就这一问题来说,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答案。
一种是,秦始皇大搞专制独裁,以及子孙承传的“二世三世至于万世”的“家天下”制,引起人们的不满,因而就有人对此造出一个颇具神话色采的“小说”性的故事来,然后借鲍白令之之口,揭露秦始皇自己说出鲍白令之“令众丑我”的话,以达到丑化、讽刺、鞭挞秦始皇残暴统治的目的。
再一种是,秦始皇一坐上皇帝宝座,国内就并不太平,不说六国后裔皆在,且他本人身受兰池之患,博狼之惊,难免会引起不安而想起皇位是否稳固、皇帝能当多久的问题。为测试大臣之心,他故意向博士说出了“禅贤”的话,用意和后来二世时赵高为篡位而“指鹿为马”一样。看来,鲍聪明绝顶,一眼就洞察出始皇的用心,故意把他比为桀、纣,以让他收回放出的“禅贤”之钩,以表示自己是完全忠于他的。而秦始皇呢,因此摸到了一些情况,也就顺水推舟,“遂罢谋,无禅意也。”
除以上两种可能的答案外,还有第三种答案,即:秦始皇提出皇位禅让似乎非无根无由,是有脉络可寻的。下面我分六点来说。
第一,人所共知,秦始皇做事反复无常,思想上矛盾之处很多,如他希冀长生不老,派方士求不死之药;却又同时大造坟墓,知道自己总归要死的。他迷信思想极重,却又指责“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注:《琅玡刻石》。)。嫪毐叛乱,平定后,“仲父”兼丞相吕不韦受牵连,秦始皇在不欲追究他的责任时,说吕“奉先王功大”,为他开脱;后来要把吕赶出河南,贬蜀,又说吕“何功于秦”。……这样出尔反尔,无一贯主张的事举不胜举,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在实行“家天下”制的同时,又提出与“家天下”相背道而驰的帝位“禅让”是有这可能的。
第二,先秦时称“土木金火水”为“五德”。每一德代表一个朝代,这“五德”是相生相克,周而复始的,如木代土,即为夏;金代木,而为商;……秦灭周,自以为是水代火。因为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自认为自己属水。这样有次序地相代,就是互相递禅。据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这“大约就是禅让说的扩大”。因而秦始皇提出禅让来,这与他信仰的“五德终始”说的思想是一致的。
第三,据《战国策·秦策一》载:秦始皇的先祖,即那个用商鞅变法的孝公,他在临终前,就曾打算把王位禅让给商鞅,商鞅辞谢不受。及至秦始皇,他同样打算搞“禅贤”,会不会是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他先祖孝公的遗风呢?怕不能完全否定。
第四,古代的“五帝”虽为传说,但确是人民理想化了的贤君,他们均通过“禅贤”君临天下,统治万民。秦始皇自称皇帝,并自以为“德高三王”,“功过五帝”,因而以“五帝禅贤”为由,想把帝位禅让给人,沽名钓誉,以称贤于世,这也是顺利成章的。
第五,秦始皇“仲父”吕不韦是公开宣扬“官天下”的,他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又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注:《吕氏春秋·贵公》。)。而秦始皇自小就是吕不韦的受教者,我想吕的这个“公天下”的思想不可能不给秦始皇一点影响,因而秦始皇为表明自己“大公无私”,“天下为公”,产生了“官天下”的禅让之念,似也是说得通的。
第六,秦始皇是从“百家争鸣”的时代生活过来的,各家各派的思想他都沾染过。他又受教于吕不韦,而吕是个“杂家”,而禅让说也是为各家默认的,像儒家的“选贤与能”,墨家的“尚贤”,就是导致禅让的一种学说,秦始皇提出“禅贤”,怕就是这种学说的具体实践。也许有人会说秦始皇以法治秦,法家是没有禅让一说的。这是不察之论。试问,上面说过的秦孝公,不就是用商鞅变法的吗?而恰恰是他提出把王位禅让给商鞅。即就法家这个学派来说,也没有公开反对禅让。韩非是集法家之大成者,他在《韩非子·显学》中说过“上法而不上贤”的话,只要善于法、术,就是君王非圣贤,也照样可治理国家。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
民食果蜯蓏蚌,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以上两段文字中说的“民悦之,使王天下”,显然也只有在“选贤与能”、“尚贤”的前提下才做得到。这样,实际上韩非也有过“禅让”的思想。至少承认上古有过这种事。人所共知,韩非是秦始皇所推崇的人物,上引两段文字出自他的《五蠹》,而《五蠹》正是秦始皇十分欣赏的,那么秦始皇所说“禅贤”与法家的理论也有共同之处。
由上述可知,秦始皇要搞王位禅让,不一定是无稽之谈。只因为除《说苑》外,其它典籍未载此事,且最终秦始皇还是实行了“二世三世至千万世”的“家天下”制,因而人们对他的“禅贤”说就产生了怀疑。而如何解开这个疑团,则得靠充足的材料来说明,我不过是根据一些记载作一猜测罢了。
秦始皇“坑儒”之疑
秦始皇于始皇于三十五年“坑儒”。这事我是一直相信的,近读史又发生了怀疑。“坑儒”事件全过程《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上乐以淫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后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终去不报,徐芾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前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此事颜师古、孔颖达也均谈及。颜注《汉书·儒林传》引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说:
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孔在《尚书正义》中引卫宏《古文奇字序》说:
秦改古文为篆隶,国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方相论难,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终命也。
在肯定“坑儒”实有其事的前提下,卫宏所说被坑对象,前者为“焚书”后“天下不从所改更法”的人;后者为“改古文为隶篆”而“多诽谤”“不从”的人。这两说不仅与《史记》所载的化资巨万,为求仙药不得又“诽谤”秦始皇后逃跑的方士有异,且坑的起因也不同;至于两说更不一样。有学者因此猜想,卫说的“坑儒”会不会非《史记》所载的那一次?说不定始皇有过多次的“坑儒”。我认为就上述所记而言,不大可能。试想,秦始皇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同一种欺骗手段骗儒生去看冬天温谷“瓜实”,而儒生也不顾前车之鉴,也一次又一次地自愿走向死地,他们能天真到如此地步吗?再说,卫宏是东汉初年人,离秦已很远,对材料来源却未作出任何交待,加上两说是一事还是两事?此种含混不清的记述,显然有想象的成分。可靠程度是很差的。
那么《史记》所论又如何呢?诚如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所说,司马迁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写作态度严谨,但由于“其间残缺盖多”,他只能“旁搜异闻以成其说”,特别是秦始皇一代之事,一大部分通过调查从传闻中得来,而传闻的东西虽然不能一概不信,但若无旁证或充足的理由,一传二,二传三,传到后来往往失真,甚至远非本来面貌,而听者还当真实的看待。司马迁就“坑儒”事件是否也有误听误信的呢?我以为这是值得作探究的:
第一,“坑儒”所坑的主要对象是“方士”,因为他们是事情的引发人。尤其是像被秦始皇点名的侯生、卢生、韩众、徐芾更性命难逃。这在情理之中。可是,事实告诉我们:他们中却没有一个被坑。除韩众不知所终外,若说侯生、卢生逃跑了,那么徐芾是一直在秦始皇身边的,他“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而始皇不仅未把他坑掉,反而在“坑儒”事件发生的第二年,即始皇三十七年,徐芾仍敢于为求仙药而向始皇诈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听后也与“坑儒”前一样,照信不疑,“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侯大鱼出射之。”结果,“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后来在之罘总算“射杀一鱼”,而徐芾也还是未求得仙药。(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再次受骗,却默认了,无一点“坑儒”那样的报复之举。这是疑点之一。
第二,秦始皇在“坑儒”前抓捕过一些人交御史“案问”,经互相揭发,最后有四百六十人(卫说700人)被坑。 这些人既为“诸生”,且如卫文中所说,还有“博士”,有的甚至被拜为“郎”,这当是社会或官场中的头面人物,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不说全部,也一定会有不少人的名字是为人所知的。可是却一个人的姓名也没有留下,连司马迁也说不出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这就不大好使人理解。而更难理解的,方士倒没有一个被坑,这除了侯生、卢生、韩终、徐芾外,还可见下表:石生: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因使韩众、侯公(生)、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注:《史记·秦始皇本纪》。)。黄公:东海人。名不知。少时为幻。秦末有白霓见于东海,“诏遣黄公以赤刀往压之,术既不行,遂为霓所杀。” (注:《太平御览》卷891引《西京杂记》。)茅濛:字初成,太原人,始皇三十一年九月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龙,白日升天。有歌谣一首留下,劝始皇求长生术,始皇欣然(注:《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太原真人茅盈内纪》(盈为蒙孙,亦方士)。)。此外尚有宋无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或云羡门、高誓、子高,最后等,均“方仙道”(注:《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封禅书》。)。一次始皇还曾使卢生求高誓。又,《艺文类聚》引《列仙传》有安期生者,琅邪阜乡人,人言千岁公,始皇曾与语三日三夜。自称后千岁始皇“求我于蓬莱山下”。此人直到秦末还活着。(注:《史记·田儋列传》。)
以上这些人,除个别的在“坑儒”前已“升天外,大多数人安然无恙,似“坑儒”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这是疑点之二。
第三,据《说苑·反质》载:“坑儒”事件过后,逃走的侯生被秦始皇捉住,始皇“升阿东之台,临四通之街”,打算在拷问他一番后车裂之。不料侯生不但泰然,反把秦始皇骂了个狗血喷头,骂他“奢侈失本,……黔首匮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还骂他“淫万丹朱而千昆吾桀纣”,“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最后说秦之亡徵久见,想改也来不及了。这番话简直是给秦始皇送终发丧,与在他逃跑前所说的“妖言”相比,真是过之而无不及,始皇听后无疑会罪上加罪。出人意料的是,始皇不但未恼怒,反而感动得“喟然而叹”,最后竟大发仁慈,把侯生放走了。这件事,经郭沫若分析,认为“也怕是事实”。那么,对暴虐成性的秦始皇来说,这样处置与他敌对到底的“逃犯”究是为何?这是疑点之三。
以上疑点若不弄个明白,我想“坑儒”云云,是很难肯定下来的。
这里我想提一下汉初的贾谊。他是文帝时人,出生在公元前201 年,上离“坑儒”仅十三年,秦亡五年。对秦的历史非常熟悉。他写的《过秦论》严厉地批评了秦始皇的过失,分析了秦立国十五年即亡的原因。实际上是当代人记当代事。可信程度胜于《史记》。秦史研究者均知,自汉以后,凡讲“焚书”,无不是连“坑儒”一起说的,所谓“焚书坑儒”。而贾谊在文中只讲了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而对于比“焚书”更残暴的“坑儒”却未涉一言,故意讳言,当然不可能。那么这又作何解释呢?
还要一提的是,秦末陈胜、吴广领导农民起义,“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注:《史记·儒林列传》。)可见他们是抱着对秦始皇“焚书”的报复之心参加起义队伍的;而对“坑儒”也无一句指责的话,更未像“焚书”一样,成为他们参加起义队伍的动因。这又是为什么?
那么如此说来,秦始皇又为什么在“坑儒”时因扶苏谏言不合他的意而使扶苏去长城监蒙恬军呢?关于这事,我以为颇有斟酌之处,我在下一节中将作较详细的分析和回答。
现在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是古代君主中比较守法的,他不“做事乱来”。以法家为治,刑罚依科,不像武帝那样滥刑。以此证明“坑儒”是依法办事。其实,若如此,则按照秦律“诽谤者族”,方士“妖言”惑众,犯了“诽谤”罪,“依律灭族”就够严厉的了,为什么要用无法可依的“坑”的手段呢?这种不合秦法的暴行,如果秦始皇确是不“做事乱来”,不“滥刑”,那么不恰好反证“坑儒”是子虚乌有的吗?
秦始皇何时使扶苏监蒙恬军?
秦始皇是在什么时候使长子扶苏任戍边长城的秦将蒙恬的监军的?有学者说:“焚书坑儒”……秦始皇实行李斯的主张,皇位的当然继承人扶苏,替孔孟派儒生说话,秦始皇发怒,使扶苏到上郡(治膚施西延安县)监蒙恬军。
由此可知,扶苏北监蒙恬军是在坑儒事件发生之后,即最早不会早于始皇三十五年。这说法系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关于秦始皇于始皇三十五年“坑儒”时扶苏谏秦始皇的如下一段记载:
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那么这段记载可靠吗?是值得一辨的:
一,“坑儒”纯因方士批评秦始皇“刚戾自用”,“以淫杀为威”等而被秦始皇加上“诽谤”罪而导致的。当时除主犯方士外,不管哪家哪派,经互相揭发,凡犯有这种罪的人,都在被坑之列,而并非是专坑孔孟派儒生。这情况,扶苏不会不知道。因此他怎么会不合实情地说被坑“诸生皆诵法孔子”呢?
二,秦始皇本来对孔孟派儒生并无好感,所以此前“焚书”,而扶苏偏以“诸生皆诵法孔子”为由来为被坑人开脱,这样的理由,岂不是火上加油?对扶苏自己也是不利的。显然,扶苏不可能幼稚到这个地步。
我以为,扶苏向秦始皇进谏之事容或有之,但由于我在上面说过的,坑儒事很可疑,因而未必是因坑儒而“替孔孟派儒生说话”并由此触怒秦始皇,使他到上郡监蒙恬军的。须知,监军代表皇帝监督军队,与军中最高统帅并起并坐,可与统帅分庭抗礼,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军职。人选非常严格,特别是蒙恬当时“统兵三十万,其势足以倍畔”(注:《史记·蒙恬传》。)。秦始皇自然得选自己绝对信任的人,而不可思议的是,他却把这一职务交给了一个因谏“坑儒”而触怒自己,实际上被自己所贬的扶苏去担任。这在情理上似难说得通。
其实,扶苏任蒙恬监军的时间在《史记》中还有另一说。这记载在《李斯传》中。传中二世、赵高、李斯密谋后矫诏赐扶苏死时写道:“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那么这记载可信吗?我认为是可信的。第一,矫诏是在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死后发出的,如果扶苏是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坑儒”后才监蒙恬军,那么他监军的时间至这一年只不过二年,何来“十有余年”?马非百《秦集史》有条自注说:“《蒙恬传》“恬暴师于外十余年,而以扶苏为监(注: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第二版《史记》蒙恬列传只载蒙恬“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无“以苏为监”句。马非百此引不知据何本。录之备考。)。又《李斯传》胡亥为书赐扶苏,亦云:扶苏与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云云。则扶苏之监上郡,决非三十五年事。”注文尽管只提出了问题,而未进一步求个水落石出,但所说还是值得注意。第二,二世矫诏的内容是赐扶苏死,事关重大,赐死理由必得正确,不能露出破绽被扶苏抓住把柄生疑,否则必会败事。这点二世、赵高、李斯不会不事先考虑到,因此没说他监蒙恬军“三年”,而是“十有余年”,那肯定符合事实。第三,据《史记》载,蒙恬是在始皇二十六年秦始皇灭六国后被派去戍边长城的,上面已说过,当时蒙恬统帅的三十万军队力量强大到足可畔秦。我想秦始皇决无可能对这支军事力量毫无戒备,让监军一职在始皇三十五年前出现空缺。那么早于扶苏的监军是谁呢?史书上未提到。这好像是个谜。其实这个谜不难破解。人所共知,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秦始皇到始皇三十七年死,未另立太子。在临终前,还以书赐扶苏嘱“与丧会咸阳而葬”,把后事托付与他。这说明秦始皇对扶苏是既“宠”且“尊”并信任他的。这就使扶苏具备了任监军一职的资格和条件,因此我们把上引矫诏说的“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的话往上推,那么十分清楚,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屯边”,秦始皇即已派扶苏监蒙恬军了。因为从这时起到始皇三十七年发出矫诏时止,计十一年,正合“十有余年”之数。是一点也不错的。扶苏任蒙恬的监军与坑儒不发生一点关系,也就是说不是因“坑儒”而向秦始皇进谏,使秦始皇发怒而贬去的。
标签:秦始皇论文; 扶苏论文; 史记·秦始皇本纪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战国策论文; 蒙恬论文; 司马迁论文; 吕不韦论文; 史记论文; 五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