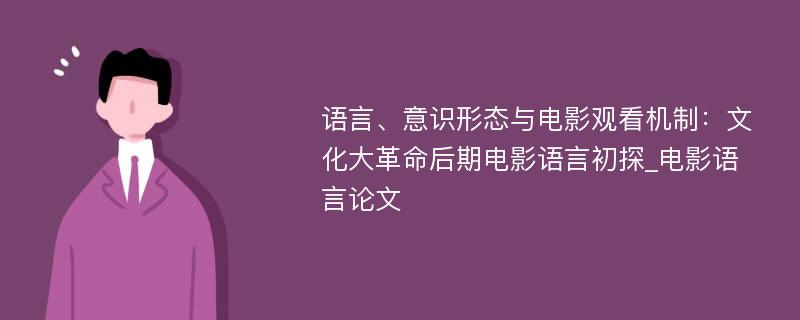
语言、意识形态与观影机制——文革后期电影语言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文革论文,后期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电影事业的空前破坏,无疑构成了中国电影史的重大断裂;但是,文革电影的独特形态却既有其历史的来源,又有其历史的延伸,而其来源和延伸都绝非单一。因此,文革的电影语言在统一僵化的总体格局之下,其内部/细部肌理仍十分复杂;而另一方面,其在观众中产生的效应也是复杂的、多向度的。可以说,文革电影的语言体系是电影语言变革的背景,因为在电影语言革新中,无论作为创作者还是观众,都必然以文革电影作“创新”的参照;同时,文革电影、尤其是文革后期故事片也是电影语言变革的潜伏地带,这不仅因为六、七十年代世界电影的技术/语言形式已经曲折地渗透进了中国电影人的制作工艺、艺术视野和创作意向;并且,文革电影语言也使观众有了发现真实的渴求,对电影语言的高度敏感性。
一、“三突出”和电影语言指令
1.“三突出”:文革电影的核心句
如我们所知,文革电影话语体系的核心句是“三突出”的电影叙事/镜语模式: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律令之下,产生了“敌远我近、敌俯我仰、敌暗我明、敌冷我暖”的一系列电影修辞法。这一体系最典型的代表即是革命京剧样板戏影片,而《智取威虎山》则是其第一个标准范本。(注:北京电影制片厂《智取威虎山》摄制组,《还原舞台,高于舞台》,《人民电影》1977年第7期第650页。)
但正如有些论者指出的,“三突出”体系并非凭空而来,它延袭了二元对立的戏剧式电影叙事/镜语体系的基本结构,(注:倪震,沈嵩生《光与非光》,引自倪震《探索的银幕》,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 )激化/僵化发展了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政治修辞法,(注:戴锦华《时代之子——水华电影艺术散论》,引处同20 , 第107—110页。)因此“三突出”体系无论在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那里,都已经历了长期的合法化、自然化过程。在笔者的访谈中,有两位差异极大的电影导演都坦陈自己在文革中对这一体系的信服态度,他们是第四代纪实美学的扛鼎者之一郑洞天(注:郑洞天/徐峰《郑洞天访谈录》(待发表)。)和新时期以来对商业片创作极其敏感的上影导演沈耀庭。(注:沈耀庭/徐峰《沈耀庭访谈纪要》(待发表)。)
2.电影语言指令及其参照系
在对样板戏/“三突出”及其观影效应进行简要论述之后,我们来进一步地讨论文革电影语言的另一个强制性力量,那就是江青关于电影创作的系列指示。
伴随“三突出”,从样板戏影片到文革后期故事片创作中,江青有一系列对电影技术/语言的指示,这些指示有时被认为是“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的,意在揭示江青的种种要求,无疑是一种对虚假的“三突出”体系的文过饰非的策略;其后人们意识到,“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作为西方文艺史上的重要现象和重要批评术语,在脱离其语境、在中国当代历史中被本土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其意义已有多般变化,并主要是作为一种极具危险性的贬意词而存在。于是一些电影批评人以“矫饰美学”一词取代了上述二词,意在区分文革电影主题先行、技术服务的创作原则与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差别,这是十分有必要的,本论文也将采用这一特定的概念。但也必须指出,在明晰它们意义区别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意识到,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作为“西方末落腐朽”的能指在意识形态运作中的功能。这一功能使任何形式探索与创新都处于体制/创作者自身的监控之下,使创作活动本身带着深刻的焦虑;而一功能恰恰无所不在地贯穿于我们研究的历史阶段之中。
下面,我们来看江青关于电影创作的主要指令:
(1)提倡运动长镜头, 曾强令崔嵬导演在拍摄影片《山花》时将镜头数限定在260个(或230个)之内(重点参考片例为墨西哥影片《在那些年代里》);(注:谢飞/徐峰《谢飞访谈录》(待发表)。)
(2)要侧逆光(及逆光),不要大平光; (注:韩尚义《也谈江青的“出绿”与“逆光”》,《人民电影》1977年第7期第17页。)
(3)暗部曝光(专用于黑白片, 重点参考片为墨西哥影片《网》);(注:《长春文史资料》(第二辑), 长春市史志办公室编, 第131—132页。)
(4)出绿; (注:韩尚义《也谈江青的“出绿”与“逆光”》,《人民电影》1977年第7期第17页。)
(5)两极镜头; (注:北京电影制片厂《智取威虎山》摄制组,《还原舞台,高于舞台》,参见《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册第654页。)
(6)视觉语言至上,曾要求一部将其对白限制在10句以内, 全片以视觉语言叙述故事;(注:任殷《看什么,干什么》,《人民电影》1977年第1期,第23页。);
(7)同期录音(对舞剧艺术片《白毛女》的要求)。 (注:桑弧/徐峰《桑弧访谈录》(待发表);沈西林/徐峰《沈西林访谈录》(待发表)。)
在对这一系列指令作了初步的罗列之后,可以看到,这些指令与电影工作者的某些创新要求不无重合之处。在对朱今明文章的讨论中,中国电影在镜头运用(“三镜头法”和“近、中、全三部曲循环”)、照明形态(平光照明形态为主导)等陈规,而这种陈规也多少在观众的接受中形成某种习惯。另外,有着“影戏”传统,对白至上的中国电影,对视觉语言的探索的确有待进一步深入。而在录音方面,现代中国电影基本上是同期录音,因工艺的便利、资金的节省,乃至于政治的功用(后期录音就可以随时变化对白),由杂用同期和后期录音工艺越来越趋向于后期录音,乃至最终彻底后期化。及至今日,同期观念不仅在创作者中阻力重重,在观众那里同样难有同鸣,甚至许多观众在已被后期录音习惯化之后,不能容忍同期录音所带来的声音的质感和空间感。因此,江青的指令并非全无可取之处。
而江青指令的参照系,应来自两个不同渊源的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的传统戏剧,一方面是六、七十年代的世界电影。例如,以“长镜头”要求为例,一方面,它是在样板戏电影拍摄中,为“原于舞台、高于舞台”,较好地保持戏剧表演的连贯与完整;导演谢铁骊在拍摄《智取威虎山》时,常被骂镜头“太碎”,(注:谢铁骊/狄翟《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电影艺术》1994年第1期,第11页。)于是其大量的工作, 就集中在推位摇移,深入舞台的长镜头调度上。另一方面,其参照系来源于西方六、七十年代电影,新浪潮之后,西方优秀影片中的场面调度几乎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不仅保持了动作/时空的真实与完整,并使影片的叙事线索与人物关系、情绪与意义更为复杂丰富;例如,江青所推荐的参考片《在那些年代里》,绝不是一部优秀影片,但仍是一部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场面调度,只有二百多个镜头的长镜头风格影片。
笔者以为,后一参照系(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电影),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事实上,在文革的专制主义体系中,在全民文化饥渴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却能看到同时期的西方各国电影。下面,是上海电影译制厂1972年至1976年译制的影片中被列入公开生产目录的部分:(注:《上海电影译制厂生产目录》(1971—1980)。)
1972. 巴黎圣母院 法国/意大利
简·爱 英国
冷酷的心墨西哥
1973. 白玫瑰 墨西哥
绿色的群山 阿尔巴尼亚
烈火行动计划阿尔巴尼亚
1974. 在那些年代里墨西哥
沉默的朋友 罗马尼亚
警察局长的自白 意大利
1975. 战斗的道路 阿尔巴尼亚
1976. 基督山伯爵 法国
生死恋 日本
阿里巴巴法国
沉默的人法国
蛇 法国
除此之外,未载入其中的还有《Z》、《马太伊案件》、 《鸽子号》等。可以说,这些内参片并未包含六、七十年代西方电影的精华部分,但仍关涉到了六、七十年代西方电影的多方成绩:高度纯熟的视觉语言、炉火纯青的长镜头调度、完备的同期录音工艺、复杂多样的叙事形态……
这些影片不仅构成了江青电影指示的参照系,也对电影工作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据“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提出者张暧忻回忆,在《春苗》剧组看到《马太伊案件》时,对其电影语言意识产生了极大的震撼,“看《马太伊案件》,第一次感受到我们从未见过的电影语言风格,它的镜头组接呀,叙事方法呀,确实和以前看的不一样了。”(注:张暖忻/吴冠平《感受生活》,《电影艺术》1995年第4期,第61—62页。 )并且,这显然不是第四代才有的感受,正如张暖忻回忆的:
谢晋老说:“唉呀,你们没看最近的几部片子,现在国际影坛电影分镜头的手法变化大多了,可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学苏联的那一套。他说,现在分镜头的观念完全和过去不一样了,起幅也没有起幅,落幅也没有落幅,镜头都在运动;镜头怎么从街上穿过去进到对面的咖啡店里,他讲的我印象特别深。(注:张暖忻/吴冠平《感受生活》,《电影艺术》1995年第4期,第61页。)
这一段追忆,十分清晰地表明了两代中国电影人在文革内参片中产生的电影语言变革的潜在冲动。
经过了前文的分析之后,我们可以说江青的一系列指令,是以一种专制主义的方式,试图使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同步;然而,在这些指令之前,中国电影人在相关范畴中都有过卓有成效的尝试,而正是在以其为主导者之一的文化法西斯主义之下,不仅打断了电影艺术探索的良性积累与渐变的过程,并且使中国电影陷入了历史的最低谷。但是,所有这些电影语言革新的努力,都同时作为已成就的电影文本、创作观念、技术手段、人员构成,会保留下来,而不会随历史的大断裂而消失;而所有这些探索在观众中的反应也绝非单一,即使在《农奴》这样大胆的尝试中,我们也可看到不同观众群的不同反应。在文革后期,权力斗争日益深化的时候,对经典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电影事业的争夺就会愈加深入;同时,文革电影还是江青对她本人在西方同期影片中建立起来的电影语言感进行指令性实践的试验场。所有这些都不能不促使对文革前电影创新资源进行争夺与利用。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下面的问题。
文革中电影技术领域有什么发展,为艺术提供了哪些可能性,有无实现这些可能性的可能?
江青怎样利用十七年已有的电影创新成果,组织进其电影指令/试验?在与“三突出”体系的强制下,得出怎样的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组问题。
二、技术的发展与电影语言变革的可能性
文革电影的“矫饰美学”本质,决定了它对技术部门的相对偏斜和技术条件的相对优化;众所周知,在江青看来,文联十个协会中,只有“摄影家协会”是好的,虽然也“放了毒”。(注:《六十年文艺大事纪》(1919—1979),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1979年10月版。)因此,相对于文革对电影艺术的致命挫伤,电影技术部门虽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却并未停滞不前;相反,作为意识形态控制焦点的电影业,其技术部门以一种畸形的优越地位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发展。这种发展固然在一种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承担主题先行、技术保障的功能,但同时它又为电影艺术的发展,乃至于电影语言的变革带来了潜在的工艺上的可能性。
可以认为,以下两方面的技术进展对电影语言的变革提供了最为直接的保障。
1.柯达电影胶片的引进与胶片工业的发展。
在文革前,中国电影界所采用的胶片,以保定片和东德爱克发胶片为主,柯达·伊斯曼电影胶片只占微乎其微的比例。而保定片的生产,完全依据着苏联的工艺技术;尤其采用苏联工艺的水溶性彩色电影正片,在色彩还原等主要性能指标上,远落后于柯达油溶性彩色正片。这样,以国产彩色胶片与东德爱克发胶片拍摄的影片,其色彩还原不准确,调子过硬并偏红。而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大量进口柯达胶片既不可能;而其作为美帝国主义的工业产品,也缺少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文革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柯达胶片开始大量被进口,用于保障样板戏电影的拍摄。大量进口作为经济事实同时也在意识形态使采用柯达胶片合法化。进而,六十年代末组织的大规模油溶性彩色胶片攻关会战,就完全以柯达彩色电影胶片为其工艺指标了;至七十年代,油溶彩色电影正片、负片、中间片和反转片先后研制成功,从而使中国的彩色电影胶片工艺,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注:谢宜凤《我国电影胶片工业回顾》,引自《电影技术百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4页。)
2.小光源与新光源
文革时期电影照明技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光源“小型化”和“新型化”的攻关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减轻照明工人的劳动量,而更对于中国电影的实景拍摄起到了致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没有与日光光谱相匹配的光源,日光型的碳精灯笨重而难以运输,中国电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拍摄实景;七十年代中期,上影照明技术人员与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对电影外景光源进行研究,研制成功了直流供电、色温5000—6000K,显色指数Ra>75的新型光源。 这一成果及其在《第二个春天》、《海霞》等影片中的运用,为中国照明技术服务于实景拍摄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注:晏仲芳《电影照明综述》,同上第218 —219页。)
所有的技术改进,对电影语言的转化都提供了更大的可能,而在一种专制主义电影机构下,技术进步提供的革命性又极难有发挥的余地。
三、自圆/分裂的文革故事片文本(text)
江青对其电影指令/试验的实施,是以十七年电影创新中的电影文本、创作观念、语言手段、人员构成为其基本条件的。这就决定了对一批文革前艺术骨干的起用,如谢铁骊、崔嵬、成荫、谢晋、桑弧、李俊、李文化、聂晶、钱江、高洪涛、沈西林、卢俊福……而对每一个重要的创作人员的选择,都是依据其文革前电影创作的成果、观念、手段。
例如,对崔嵬、聂晶、高洪涛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长镜头的选择。基于崔嵬与聂晶在《小兵张嘎》中卓越的长镜头实践,对其影片的镜头运用有特殊的要求。从《红雨》到《山花》,确实有愈加自觉的长镜头运用;同时,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三突出”作为文革电影语言的“核心句”,决定着电影语言的一切生成转换,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和弥散性。
例如,在《红雨》(导演,崔嵬;摄影,聂晶;1975年)中,第一个段落的镜头构成中,就结构/节奏性地运用了许多摇移长镜头,通过横向和纵向调度将劳动场景的整体感和沸腾的气氛充分表现了出来;影片的长镜头调度也包含了灵活的视点转换,如在第二个段落的开端,在一个红雨驱车(向画左)的远景跟移镜头之后,切入一个水平的移动镜头,根据前一镜头的运动方向、主人公的空间位置以及镜头的运动频率,这是一个主人公的视点镜头,随即镜头稍仰并右摇成红雨赶马车的中近景;在这一镜头中,运动与视点转换使镜头内部有充足的视觉调节和较丰富的内容;但同时,这也是将镜头主体转回主人公(英雄人物)的一种方式,并以其仰拍中近景结束,准确地对应了“三突出”的要求。再如,在第五个段落中,队长与中医(反面人物)对话,队长站于坡上, 中医站于坡下:镜头先由队长的特写左摇,后景中坡下的中医(俯角度)入画,他向队长作了政治表态之后,队长出画,镜头再左摇并前推,最后落幅于通过前景树枝俯拍的中医近景。导演与摄影于此将一个很难构图的镜头调度得颇为成功;同时,正是依赖这一调度,创作者成功地将权力关系与角色派定呈现在这一长镜头的结构之中。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不考虑政令式的要求对创作人员能动性的扼制(而这一点事实上极为重要),在这一所有电影话语必须是“三突出”核心外延的体系之中,长镜头调度体系也根本不能得以完善发展。因为即使不以真实美学/镜头的多义性为指标,长镜头毕竟会在其调度中包含一定的开放性。动作/时空的相对完整以及人物关系/叙事信息的相对复杂,这一切都会对英雄人物的“突出”地位引起潜在的动摇;而英雄人物永远需要“突出”,他/她的出场也永远要作为视觉重音来处理,这就使长镜头体系与“三突出”体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裂隙。正是这种结构性裂隙使文革后期故事片中最极端的长镜头语言的尝试以失败为告终。
这部影片即是1976年文化部重点推出的影片《山花》。这是一部以1964年“农业学大寨”为背景,表现“两条路线斗争”,并以1975年政治局势为实际指涉的影片,从开拍伊始就定下了长镜头的指标,江青指令将影片镜头数控制在260个之内,从很大程度上说, 崔嵬正是为保障这一指标的完成而被指派为导演的(与桑夫合作),摄影师则是北影四大摄影师之一的高洪涛(与于振羽合作)。影片自片头段落就以航拍推移长镜头标明其风格。在高山花(谢芳饰)出场的段落中,前半段为白石滩大队的青年为是否出外作工争执,一组人骑车上路,另一组人骑车追赶。在一个青松下高山花(着绿衣,“出绿”;戴白头巾,“劳动人民”的能指)立于高坡上下望的全景之后,是一个运动长镜头:在前者绕过山路时,后一队人抬车上坡,摄影机跟移并随其下坡摇降而下,拦住前者的去路。而就在这一极其流畅的运动长镜头之后,猛然切为高山花的近景;之后,影片在群众与高山花之间再对切一次,群众仍为全景,高山花则切至特写。在这里,“三突出”体系与长镜头体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清晰地显露了出来。显然,在一切与“三突出”体系矛盾的情况下,长镜头体系均需让路,这就使影片无法在指令的镜头数之内完成(因此又招致江青的怒骂);(注:《看什么,干什么》,《人民电影》1977年第1期第23页。)同样, 由于影片中长镜头不可能出现较复杂的人物关系/叙事信息,其镜头设置通常单调呆板,故在其短时期的放映期间,成为观众反响极差的一部影片,而其原因部分在于它的“拖沓、平淡”。 (注:谢飞《电影的镜头和镜头的组接》, 《人民电影》第2/3期第40页。)
然而在指出这种的结构性裂隙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些充满龟裂的文本,也是在特定话语体系中自圆的文本。上述的影片都产生在一个交互指涉的互本文场之中。通过《春苗》、《欢腾的小凉河》、《闪闪的红星》,甚至在其时受到迫害的《创业》与《海霞》,都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同一套电影语言体系的反复再现。例如,在对“长镜头”和“两极镜头”的使用上,有如《山花》中那样,在一个连续的多人调度中猛然切入主人公镜头,并一再对切直至其特写,成为文革电影中常见的镜语;在这种经典的文革电影镜语中,以表现强烈视觉冲击感的两极镜头,在此是作为呈现“普通群众”(远)和“英雄人物”(特)的对比关系和权力关系的手段,在“三突出”体系里与“长镜头”互为补白。
光的语汇是另一个呈现文革电影(尤其是后期故事片)结构性自圆/分裂的症候点。江青的著名批示“不要大平光(大平光,亮堂堂),要侧逆光”。我们在上面讨论过平光照明在中国电影/观众欣赏惯习中的主导位置,也讨论了突破这一用光观念的困难。相对于大平光照明立体感,层次感弱的平面化特征,侧逆光照明(140照明, 也称伦勃朗照明)固然能突出拍摄对象的轮廓、立体形态、色阶层次,但它毕竟只是一种单一的照明方式,用它来限定千姿百态的光的世界,本身已相当荒谬。而一种“三突出”的电影语言体系,及至在其间培养出来的观赏积习,更使这一侧逆光照前也不能真正达到其应有的照明形态:因为在侧逆光照明中,被摄入物均属明暗光线照明形态,即会产生明显的明暗面及明暗交界线;另一种被提倡的逆光照明则将使对象呈剪影,或半剪影形态。但是,无论是“三突出”体系,还是习惯于平光照明形态并内在于“三突出”语言体系的普通观众,都很难想象甚至无法接受主人公(英雄人物)被处理成“阴阳脸”(侧逆光明暗光线形态)或“黑脸”(剪影),于是必然性地,要用灯或反光板对主人公的面部进行补光。于是,经常出现诸如人物背对夕阳,脸上却光斑闪闪的画面,从而形成最为典型的“非光光效”(倪震、沈嵩生)。(注:倪震,沈嵩生《光与非光》,引自倪震《探索的银幕》,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 174页。)
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后期电影创作中,一种电影语言创新的确潜伏着。但同时又被紧紧桎梏,这种桎梏造就了自圆/分裂的文本。而在这些文本面前乃至文革样板戏电影面前,观众的接受效应又是怎样的呢?
四、文革电影的接受效应
下面则是笔者在观众调查中的五个相关问题及其答卷结果统计:
*当时对样板戏电影的感受(%):
喜爱 一般化 滑稽可笑 厌恶 恐惧 不记得
42 492 4 0 5
表2—1
*现在对样板戏电影的感受(%):
喜爱 无所谓 滑稽可笑 厌恶 恐惧 怀念
20 416 4 035
表2—2
*当时怎样看“三突出”原则(%):
赞同 反感 不完全同意,但有一定道理 恐惧
3610 48
0
表2—3
*现在怎样看“三突出”原则(%):
仍然赞同反感不完全同意,
心有余悸
但有一定道理
1319 595
表2—4
*您当时能熟练地通过人物的远近、仰俯、明暗、 色彩判断正反面人物吗?
能 不能 有时能,有时不能 没注意这方面
851 10 2
2—5
统计结果引导出一系列关于样板戏与“三突出”在接受中的复杂效应。我们将其简要地归纳为:“三突出”的自然化效应与“三突出”的公式化效应;其中“三突出”的公式化引起了观众对电影语言、真实感、欲望与快感的敏感性。下面我们再一一加以讨论。
首先,在文革中相当观众对“三突出”原则持认可赞同的态度,并且正如三位观众中在表中以相类的语句注明的,“当时认为理所当然”。因此“三突出”体系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是被极大地自然化的一种语言形态。耐人寻味的是,很多观众今天对这一创作原则仍表示“虽不完全同意,但有一定道理”;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三突出”叙事/镜语体系与二元对立的常规戏剧式电影形态之间的传承关系。“三突出”的镜语系统体现,则几乎是人尽皆知的语言规则(在调查中,有两位观众特别注明“太明显”)。
另一方面是观众对“三突出”/样板戏电影公式化的感受。大量观众在对样板戏的调察中指出,即使当时也有反感其“公式化”的心理感受,在其中也包括不少对样板戏电影十分钟爱的观众。显然,这一体系因其过度公式化无法被真正自然化,因为任何能被成功自然化的语言秩序均需在最低限度内“乱真”。电影本是最具这种能力的媒体,因为其与生俱来的摄录特性,电影是一种“能指约等于所指”的语言;(注:詹姆斯·莫纳克《怎样读解一部影片》,引自《世界电影》1986 年第4期第157页。)而经典电影的特征更在于, 通过空间与时间的幻觉构造一个封闭的“真实的世界”;由此,它可以成功地将陈述者与意识形态的话语(法文术语,disc-ours)掩盖起来, 造就一个似乎是在自我呈现的故事(法文术语,histoire,也译“历史”)。(注:麦茨《历史和话语——两种窥视癖论》,引自李幼蒸编《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25—232页。)而“三突出”体系则是一种“裸露话语”的语言,一切意识形态的话语和角色派定均要以一种最为直接而固定化的视听形式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其一,大量观众本不十分敏感自觉的电影语言意识被变得十分敏锐,因为每一道光影、每一块色彩都有其确定的意识形态语义。其二,随之而来的是,观众对电影语言变化的敏感性的渴求;其三,这也必然引起了观众对“真实性”的敏感,因为它是如此固化,而与生活情境毫不相干。最后,一个十分微妙而重要的效应,是“三突出”体系对于欲望和快感的禁忌与激化;事实上,在把所有“好的镜头、好的光线、好的色彩给英雄人物”的情况下,样板戏电影主人公的银幕表象并不缺乏视觉快感,但同时却因其是“三突出”中神圣的英雄人物(无论男女),使其不能真正成为“欲望的表象”;(注: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引自张红军编《电影与新方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于是, 样板戏影片,接受者就处于一个禁止又激化欲望的中间点上,其结果是大大强化了观众对欲望与快感的敏感性。
这一切效应都参予构成了观众的期待视野,成为新时期电影语言裂变的接受背景与潜在呼唤。
标签:电影语言论文; 电影论文; 电影艺术论文; 长镜头论文; 山花论文; 江青论文; 样板戏论文; 英雄人物论文; 胶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