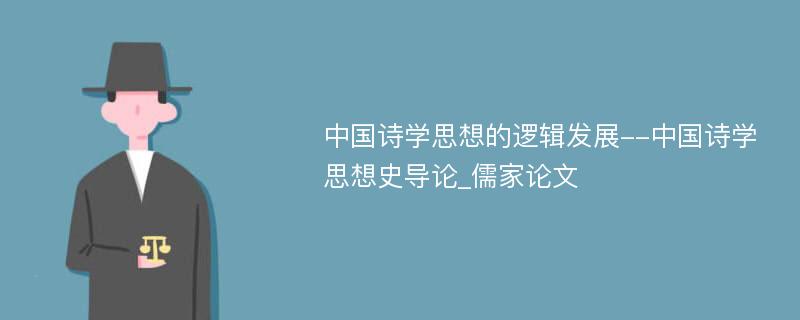
中国诗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中国诗学思想史》导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中国论文,导言论文,思想史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小引
所谓“中国诗学思想”,指中华民族所固有的、传统的诗学思想,它大致发轫于春秋战国之际,可以孔子为代表;迄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消亡(1911),可以王国维为代表。发表于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前夕的王国维《人间词话》(1908—1909),是尝试运用近代西方哲学、美学阐释中国传统诗学的真正开端,标志着中国诗学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折,从此随着西方美学和文艺学的不断输入,日益改变着传统诗学思想的固有风貌,已经不属于本书论述的范围。要之,从孔夫子的时代到王国维,其间大约二千五百余年,便是本书所涵括的上下时限。
本书所谓“诗学”,非指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包括一切文艺理论在内的广义的“诗学”,而是现代通常所说的狭义的“诗学”,即有关诗歌这一特定文体的理论。但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理论中,赋论中衰,词论、戏曲论、小说论晚起,能够贯穿这二千年始终的唯有文(散文)论与诗论,而传统文论基本上是议论文、应用文的理论,并非纯粹的文学理论,属于纯粹的文学理论而又能够贯穿始终的唯有诗论而已,由之最便于考察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一脉相传芊延不绝的演化变迁。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谓中国诗学思想史,也可以说是以诗学思想为主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本书所谓“诗学”,又带有一定的广义的性质。
即使单就狭义上言,“诗学”也是一个很广的范围。在“形上”层面,它包括对于诗的性质、功用等的认识与观念;在“形下”层面,又包括关于诗的具体作法、格律、声调、对偶等等。作为“诗学思想史”,本书侧重于前者。即使涉及到一些体格声调的具体问题,也力图从高处深处探寻这些问题提出、发展、演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潮的原因与底蕴。中国古代的诗与诗学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机遇,它们的鼻祖与源头是后来被奉为“经”、拥有崇高意义和神圣地位的《诗三百》,因而它们自然也成为“《诗》之苗裔”、“古《诗》之流”,往往被视为一种正宗、严肃、不可掉以轻慢之心的文学形式,宋代文坛的衮衮诸公和朝廷大臣可以以词的形式流连风月,抒泄风情,写起诗来却一本正经,述事议理。因而,诗学思想往往最关世道人心、政教风化,与一般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潮息息相通。侧重于在学术、文化思想流变的背景上考察诗学思想的流变,是本书的宗旨。循此方针,在具体展开上,既严格依照诗学思想发展的历史顺序,也力图体现出其固有的逻辑进程。
二、文化思想与诗学思想
诗学思想,从“诗学”的侧面说,根柢于诗歌创作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升华,由之体现出其独立发展;从“思想”的侧面说,它又无以脱离所处时代的文化思想和时代精神,它甚至就是一般社会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质言之,一定时代的文化思想总是要为该时代的诗学思想提供气候,造成氛围,着上底色,左右着诗学思想的风貌、色彩与发展方向。影响于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主要有儒、道、禅、骚,前三者皆属一般的社会文化思想。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主的楚辞创作的特异风貌及其所体现出的“楚骚原则”,本身便是一种诗学思想,又给予后世诗学思想以深远影响,表现出相对独立的诗学发展路线,并与前三者所熏陶影响下的诗学思想,特别是正统儒家的诗学思想,发生着龃龉与冲突。这是纯粹的诗学思想与经学的诗学思想的冲突。
一般文化、学术思想对诗学思想的影响,常常表现为不同的途径与方式:或直接的,或间接的,或仅仅为诗学思想的发展开辟着道路,开拓着空间。直接的影响带有强制的色彩,要求以诗的形式径直阐发宣扬某种思想原则和人生哲学。在儒家的经学期,这种影响表现为牵附政教风化的“讽喻诗”及相关的理论主张;在儒家的理学期,表现为明心见性的“性理诗”及相关的理论主张;在道家,表现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及相关的理论主张;在释家,表现为俚俗模棱的“偈语诗”及相关的理论主张。严格说来,上述种种诗体都算不上审美的诗作,甚至不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上述种种相关诗论也算不上审美的诗论。
间接的影响要经过诗人和诗论家这个中介,对相关文化学术思想加以融贯消化,真正化成诗人自己的人生态度与人格精神,用自己的心灵与情感创造为真正审美的诗篇,再由理论家上升为审美的诗论,如传统儒家的教化原则直接影响于诗学思想,最典型地体现在《毛诗序》及《传》《笺》中,以其美刺讽喻的原则解诗,便对《诗三百》中许多日常生活与爱情的诗篇,作出远离本意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歪曲,并引申出直接服务于政治的诗论。但是,其中所体现的仁民爱物的儒家民主主义精华,一旦化为诗人和诗论家的血肉感情和人文精神,在绵绵后世便创造出无数悯时伤物、鞭笞虐政的优秀诗篇,形成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诗学传统。《毛诗》系统原本用以比附解诗的“比兴”之法,经过世世代代诗人和诗论家的改造发挥,并与《周易》、道家“立象尽意”以及禅宗“拈花微笑”的明道悟理之法相融会,到明清时成为艺术创作形象思维和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美学范畴。道家的任“真”重“天”(自然),原是一种哲学思想与人生态度,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等艺术化为清幽冲淡的诗篇,到司空图又升华为相应的诗的风格意境理论。禅宗的“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原是对佛法的具象化的心领神会,后来则被发挥为对诗境、诗法的“参悟”、“妙悟”。诸如此类,皆可以说是文化学术对诗学的间接影响。至于文化学术思想为诗学思想开辟道路,可以以魏晋六朝和明代为例。魏晋六朝重“情”重“采”,主“缘情绮靡”,这是当时盛行的庄老道家思想“任自然”之说冲击了儒家礼法名教束缚人情和个性的结果,但重情重采实非庄老的初衷。恰巧相反,他们原是主张“人而无情”和“灭文采”的。明代诗学也极重情感因而极重艺术,这当与心学的流行对正宗理学的冲击有关,但重情也并非心学的本意。
当然,本书并不认为每一股诗学思潮、每一个诗学命题、概念以及术语的出现都与一般文化思想的影响有关,都应到某种学术思想或是某派学术著作中去寻觅,倘使如此,恐怕也很难保不牵强附会。诗有自己独特的表情达意方式,诗学是一门有自己特殊规律的学问,诗学思想的发展演化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它总要顽强地沿着自己的轨道随山路曲折而蜿转前行。如果一定要从某家某派的哲学、学术思想中寻找某一提法和概念的来路和出处,那么《诗三百》中诸如“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之类带有最初的诗论意义的作者创作自诉出自哪里?屈原作品中“发愤以抒情”、“长乡风而舒情”之类的来历又在何方?富有情感、富于文采是诗的一般特征,这种特征恐怕是和诗有生与俱的,和诗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特征在楚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嗣后的汉代经学鼎盛期受到了限制,当魏晋庄老道家思想的流行冲决了儒学的堤防时,诗学的这一固有特征便顽强地抬起头来,陆机从而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命题,遥承战国后期的楚骚传统。后来宋人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以理为诗,既乏情感,又匮词采意境,宋末严羽惩其流弊,重新强调诗的“吟咏情性”的特质,作为反对苏、黄、江西诗派的理论依据,并由之引申出“水月镜花”之论。明代前后七子论诗强调“格调”,主张拟议盛唐诗的高格逸调,公安派激而发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论,虽然也有个性解放思潮作为外因,但毕竟以诗自身特殊规律的内因为依据。凡此种种,皆表现出诗学相对独立发展的一线相承。再如六朝陆机、刘勰一前一后,皆提出“神思”、“神与物游”、“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文学构思论,这其实也根基于文学创作形象思维的经验积累与提升,恐怕无须到《庄子》“乘物游心”、“游于物之初”之说中寻觅理论渊源的(文字渊源又当别论)。一般文化思想主要是从根本精神上影响诗学思想,诗学理论在自身发展中常常借用古人著作中可资表达的词语形成自己的独特术语、概念,有时近于早期佛经翻译中的“格义”之法,恐怕很难说是什么影响。《文心雕龙》论文学构思贵于“虚静”,这本是任何思维活动都须保持的心态,不必归于《庄子》《荀子》同类词语的影响。有些诗学术语虽确实有取于一般文化学术思想,但与其在原典中的意义有很大的距离,如诗论中的“境”、“悟”、“参”虽受启迪于佛学,但也不过是启迪而已,是决不可牵强为解引喻失义的。另外,有些论者将古代教化的诗学思想归于儒家,将审美的诗学思想归于释、道的影响,虽诚然事出有因,但也不宜过分绝对。其实释、道又何尝不底于“教化”?只不过那有别于儒家的教化而已。任何学术思想自身都不是审美理论。中国古代那些最为流传最有价值的诗学理论与范畴是各种思想合力的结果,而其中起主导作用、加以熔铸融液的仍是诗歌创作自身经验的积累,总结、升华。
三、汉学与宋学
但本书仍不否认一般文化思想对诗学思想的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和时代精神常常濡染甚至决定着该时代诗学思想的风貌与走向,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各代的文化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该时代占主流地位的学术思想。先秦子学、汉代经学、六朝玄学、唐代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实学、晚清西学,对各自时代的诗学思想均有莫大影响。这里特别提出汉学与宋学,逗露出本书的两个主要观点:第一,所谓“汉学”,指汉代经学;所谓“宋学”,指宋代理学。这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两个阶段。从汉至唐,通称为经学期,宋、元、明通称为理学期;清代的情况比较复杂,有“新汉学”之称,但理学的影响也同时存在,并有汉、宋融合之势。特别提出与强调汉学与宋学,无疑意味着在笔者看来,一般文化学术对诗学思想的影响,乃是以儒学的影响为主;儒学的发展演变,是观察诗学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线索与参照系统。这也毫不足怪:与诗学一样,在近世之前,唯有儒学能够贯穿始终。汉代以后,它更成为统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先秦时期虽诸子并立,但儒学号为“显学”,其他“显学”如道家、法家的著作虽文采斐然有逾儒家,但却不言“文学”甚至嫉视“文学”,好谈诗论文者唯有儒家而已,并成为汉儒诗学思想的导引。汉代以后,魏晋六朝虽号为儒学中衰,但儒家思想在政治上仍是一面神圣的旗旛,不时地为统治者所祭起,文学理论批评中种种形式的“原道”、“征圣”、“宗经”之论也始终不绝如缕,并与种种文学“异端”相抗衡。再如隋唐虽称为佛学鼎盛,统治者三教并重,但首重的毕竟是可以经国图治的儒学。在诗坛上,要求矫革虚华绮艳诗风、恢复汉儒风雅比兴、讽喻美刺精神的呼声从初唐一直响彻到晚唐,形成一股十分强劲的“复古”思潮。庄老道家思想及其人生态度,虽对后世诗学有极深影响,但至少在汉代,除汉末外,其影响可以说是极其微小的,所以也无法贯穿始终。佛学后起,更不待言。尤其重要的是,道、释对诗学思想影响的强弱,是以儒学的盛衰为转移的,并且往往被吸收融贯在儒学之内,通过儒学的堂堂旗号而发生影响,如宋明理学即是。
在各代学术思想的嬗变中特别拈出汉学与宋学,所逗漏出本书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是:认为中国传统诗学思想可以宋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先秦至唐属前期,宋至清末属后期,与儒家的经学期与理学期大致相合。此种相合并非偶然,而有着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诗学思想发展演变中的主导作用。本书的分为上下两篇,即由此而来。
儒家思想由经学发展到理学是一件大事。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多次蜕变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次,犹如“二水中分白鹭洲”,将儒学分为风貌有异的前后两截。儒学与社会政治的联系最为紧密,由经学转为理学即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转向后期有关,与与此相联系的儒学所承当的历史使命的改变有关。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概言经学与理学的歧异:经学所以经世务,理学所以理性情;经学重在“经世”,理学重在“治心”;经学侧重“外王”,理学侧重“内圣”。当然这也并非笔者的创见,学者多有类似议论。
这种区分当然只是相对而言的,因为经学与理学毕竟皆属儒学,是儒学发展的一线两段。儒学总主用世,这是与宣扬遁世、出世的道、释之学的根本分歧。但所处历史时期不同,儒学用世的方向方法亦异。大致说来,经学用世的方向与手段是“礼”。“礼”是外在的社会政治伦理秩序与行为规范。汉承长期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和二世而亡的暴秦之后,重新整顿建立合“礼”的社会秩序和伦理关系便成为当世的急务,儒学恰巧最适于承担这一历史使命。汉代儒学主要承袭以“礼”为核心的荀学而来,且荀子之“礼”已不全同于孔、孟之“礼”,具有了“法”的性质,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汉代正需这样一种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纲纪与礼法,故视“礼”为“其政之本”,认为“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非礼无以制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礼”所要节制的这一切,包括了封建社会所有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
理学用世的方向与手段是“理”。“理”可以说是“礼”的内化,它将节制的对象与作用深入到人的心灵。这大约与中唐以后,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统治者的极其腐化荒淫、道德人心的极其败坏有关。从学术上说,由于“儒门淡泊,尽归于释,收拾不住”,为了与佛教争取“收拾”人心的主动权,它一方面吸取了佛教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治心”之论,一方面远绍先秦思孟学派诚意正心的“内圣”路线,逐渐形成为理学。理学的核心是“理”、“天理”,并认为天理就在人的心性之中,只要“反求诸己”、“反身而诚”,便可以体认天理,消除人欲,提升道德,由个人的“内圣”达到社会的“外王”。
汉学与宋学、经学与理学两种不同的致思方向,从深层上影响于前后两个时期的诗学思想。
四、情礼冲突与情理冲突
抒情是诗的本质特征,情是诗的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它必然与儒家的“礼”、“理”发生龃龉与冲突。本书将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发展分前后两期,为上下两篇,上篇题为“情礼冲突”,下篇题为“情理冲突”,与儒家经学、理学的两期发展正相表里,这并不是为了追求体系的整齐对称,强扭历史以就逻辑,而是大势如此。当然,无论“情礼冲突”还是“情理冲突”,都只是对前后两期诗学思想深层文化学术底蕴的大致概括,这是不言自明的。
先说“情礼冲突”。
“礼”是古老的人间秩序和行为规范,传为周公所制定,后来尤为儒者所重视,以之为人应有的存在方式。礼其实并不完全排斥情,它的制定考虑到人情所能接受的限度,所谓“缘情制礼”、“缘人情而为之”。这种基于人情的礼又反转来制约人情,所谓“以礼节人”、“情安礼”,使不流佚讹滥。礼既然是一种社会性的规范,它在制定之时就建立在人的共性的基础上,荀子称之为“千人万人之情”,这就必然漠视和束缚人的千差万异、生动活泼的个性。礼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其外在表现是遵行各种礼仪和礼节,这称为“文”;其内在素养便是要有合乎儒家之道的“仁”心,因而孔子说“人而不仁于礼何”,又认为“礼后”,即礼后于“仁”,以“仁”为质地,这称为“质”。二者结合起来便是“文质彬彬”,所谓“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董仲舒语)要之,不管从哪个角度说,礼都是对情的一种制约,因而情与礼的冲突早在先秦便已存在,主张“天”、“自然”即放任人的天然本性的庄老道家便主要集矢于儒家之礼,称之为“以人灭天”,加以尖刻的揶揄和激烈的攻讦。
按儒家的规定,礼也应是诗的存在方式。这也分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从内容方面说,诗应是“言志”的。“志”本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但儒家“诗言志”之“志”往往特指“道”,如孔子说“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荀子说“诗言是(道),其志也”。“道”也便是“礼”。到汉代《毛诗序》既承认诗的言情性质,又力图将情限制在礼的规范,提出一个经典性的表述:“发乎情,止乎礼义”。又规定诗应“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将“礼义”具体化为对上政的讽喻美刺。从形式方面说,儒家向来并不反对“文”、“文饰”,但要保持中庸的“文质彬彬”的限度。《毛诗序》所谓“主文而谲谏”,便是“文质彬彬”的原则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规定,即“文”应当服务于“谏”,含有“谏”的内蕴。总之,情、礼关系在内容上是情、志关系,在形式上是文、质关系。
在魏晋六朝“任情悖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时代氛围中,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无视“礼义”与讽谏美刺,情礼冲突变得剧烈起来。一方面是新变派在“缘情绮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缘情”发展为滥情甚至色情,“绮靡”发展为虚华淫艳,另方面是复古派力主恢复汉儒讽喻美刺、劝善惩恶的诗学思想,攻击魏晋以来特别是齐梁的诗歌创作“摈落六艺,吟咏情性”、“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裴子野语)。折中派如刘勰则在“原道”、“征圣”、“宗经”的神圣旗帜下,肯定魏晋以来文学新变的成就,实质上是意在调和情礼冲突。关于“发乎情止乎礼义”与“缘情绮靡”两条诗学路线的睽违与冲突,清人沈德潜、纪昀等多有所论,见本书正文。
唐代由于儒学的重振,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诗论家从初唐开始便不断抨击反拨齐梁诗风,一直持续到晚唐。他们以“人文化成”论为依据,主张恢复“六义比兴”的诗学传统,主张诗中有“兴寄”的内容和刚健的语言。中唐白居易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对情礼冲突有一定的调和意义。直到宋代理学兴起,情礼冲突才被情理冲突所代替。
宋代理学家所说的“理”有三个侧面的意义:一是“伦理”之“理”,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二是“物理”之“理”,他们认为万物各有一“理”,应当体认与揭示其“理”;三是“条理”之“理”,即事物的秩序与法则。这三个侧面,对宋代诗学思想皆有或轻或重、或显或隐的影响,也都与“情”存在着龃龉与冲突。
一般说来,“存理灭欲”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理学家的诗中。“欲”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情,但与情有所交叉。对这方面的抨击与反拨主要是晚明的一些具有异端思想的人物,如徐渭、李贽、汤显祖等,“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汤显祖语)便是其典型表述。“物理”层面之“理”对宋代诗人的影响比较深广,是宋人以理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深层原因。这方面的情理冲突发生得比较早,宋末严羽《沧浪诗话》主要便是针砭此种流弊的,用以针砭的思想武器便是“诗者吟咏情性”之论,并开启了明代前后七子一派对宋诗的攻讦。“条理”层面之“理”影响于宋人的好谈诗法,并一直影响到元、明、清的整个后期诗学。明代七子派主情而反对宋诗,但他们主张从体格声调上拟则唐人,其实也是从宋人的好谈诗法而来。公安派声音“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虽直接针对七子派的“格调”论而发,但深入追溯起来,却是对宋代以来拘守诗法的反拨。
清人主张“诗人之言与学人之言合”,主张“性情根柢于学问”,主张抒写关乎世运的“万古之性情”,对情理冲突带有综合、调和的倾向。
五、诗骚之辨与唐宋之争
诗、骚之辨与唐、宋之争是情礼冲突与情理冲突的具体化。诗、骚之辨主要贯穿于前期,唐、宋诗之争自然贯穿于后期。二者虽都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但其中的焦点皆关乎“比兴”、“兴”。
诗、骚之辨的实质就是情礼冲突。诗指《诗三百》,骚指以屈原为主的楚辞作品,二者皆是真正的审美诗篇,是不同时代的诗人抒情言志的真诚歌唱,虽风格有明显差异,却不存在什么矛盾冲突。但是第一,由于楚骚具有浓厚的南方文化色彩,与当时的中原文化有所不同,带有一定的异端色彩,其强烈的抒情性既不很合于儒家的“以礼节情”、“温柔敦厚”,其“惊采绝艳”的词采也不很合于“文质彬彬”的原则。第二,更重要的是,《诗三百》在汉代上升为“经”,楚骚则因“未经圣人手”,没有获得此项殊荣。汉儒用解释《诗经》所抽象出来的比兴讽喻、美刺时政的原则衡量楚骚,认为它们不合乎这些诗学原则,但也有人以此为标准对它们加以肯定。这是汉代的宗经辨骚。
魏晋南北朝是“楚骚原则”占上风的时代,“诗缘情而绮靡”其实正是楚骚传统的承续,因此对楚骚褒扬者居多。但当时南、北方的复古派敏锐地觉察到楚骚与魏晋文学自觉以来诗风新变的内在联系,将齐采绮艳诗风追溯到屈原、宋玉头上,裴子野是其代表。在此问题上,刘勰《文心雕龙》同样保持其“折中”的原则,对楚骚有褒有贬,有扬有抑。这是第二次宗经辨骚。
第三次宗经辨骚、宗经贬骚是唐代,承续了裴子野的论调,也将齐梁的虚华诗风归罪于屈、宋。由于唐人始终不满齐梁诗风,因此这次宗经辨骚历时长久,言词激烈,贬斥屈原作品远远超过汉代。唐代是汉代之后最重比兴(指经学的“比兴”,详后)的时代,他们攻击屈原作品的着眼点与攻击齐梁诗风一样,也认为其徒有华美的辞藻和逸荡的情感而缺乏比兴讽喻之旨。宗经辨骚是与前期诗学思想的发展演化相始终的。宋代以后,特别是苏轼盛赞屈原、朱熹作《楚辞集注》之后,宗经辨骚再未形成一种文学思潮。
唐、宋诗之争贯穿着整个传统诗学思想发展的后期。如果说诗、骚之辨主要着眼于诗的社会功用,则唐、宋诗之争主要着眼于诗的艺术形式。所谓唐诗,主要指盛唐诗,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由于理学盛行和时代精神、审美趣味的变化,对唐诗抱着疏离与不满的态度,这其实犹似人到中年以后,对少年的激情、风流、华采的隔膜与厌倦。宋人一是不满唐诗“浅薄”的抒情,他们一变而为议论说理;二是不满唐诗的描绘风景、争妍斗巧而“不知道”。所谓“后生好风花,老大即厌之”,他们一变而为枯索的“白战”;三是不满唐人似已走向“滑熟”的句法与铿锵的格调,他们一变而为拗涩瘦硬。这一切便形成宋人的“以文为诗”。
首先向宋诗发难的便是严羽,他几乎与他的当代人针锋相对,历数了宋诗的代表人物苏轼、黄庭坚、江西诗派的种种弊端,认为盛唐诗是第一高标,盛赞盛唐诗的“兴趣”、“兴致”、“意兴”和“镜花水月”般迷朦的意境,其《沧浪诗话》成为明代七子派的理论基石。
正象宋人处处与唐人立异一样,明人则处处与宋人立异。他们宣称“诗必盛唐”,极其鄙薄宋诗。这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以主情反对宋人的主理。由主情引申出主“兴”——这是六朝人所提出的“感兴”之“兴”,实即由即目所见的外物触发的创作激情,以之反对宋人的“先立意”、“辞前意”等。二是以主比兴反对宋人的“白战”。宋人不喜欢景物描写,而景物描写的诗中往往起到比兴的作用,因而宋诗的缺乏比兴几乎是古今的通识。中国古代的比兴观可分为两种,一是比附政教风化的经学比兴观,始于汉儒解诗;二是被今人称为形象思维的美学比兴观,六朝时虽有所透露,但基本成熟于明代,李梦阳认为比兴是“假物以神变”,可谓形象思维的同义语。明人反对宋诗的第三点是以拟则唐人的高格逸调矫正宋人的以文为诗。明代是一个极重艺术的时代,在矫革宋诗之弊中提出许多精微的诗论,清初王士祯“神韵”说其实便是七子派诗学的结穴。
清代诗学思想的主流是反明、远唐、近宋。清代的文化思想与时代精神其实与宋大不相同,但宋诗的几个特点引起他们的共鸣。一是清人惩于明人的空疏,推重实学,与宋人的重读书、以学为诗相契合。二是清人重史,主张以诗观史,以诗补史,与宋人的“诗史”说和宋诗的叙事详明相契合。三是清代一前一后遇上两个“天崩地解”的时世,喜欢淋漓奥博的诗风而不喜含蓄蕴藉,也与宋诗有所契合。因此清诗始终“祧唐祢宋”,并出现了“宋诗派”、“宋诗运动”、“同光体”。
六、中唐与杜甫
中唐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学术从前期转向后期的枢纽,理学便是由中唐韩愈、李翱发其端绪的,故历史学家吕思勉称中唐文化应属宋型文化。诗学思想也是如此,中唐诗可称为“宋型诗”(就主导思潮和代表人物而言)。与此相关,宋以后所说的唐诗实际上往往指初盛唐诗,尤指盛唐诗,本书则称为“典型唐诗”,以与中唐的“宋型诗”相区别。
中唐在诗学思想史上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时代。宋代以后对唐诗的评论,无论褒贬态度如何,其实总在中唐问题上打转儿,在中唐那里划界。宋代一前一后的“晚唐体”,所效法的都是中唐以后的诗人;苏、黄、江西诗派所推重的,也是杜甫、韩愈等(说见后)。严羽攻击宋代诗风,明确主张“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开元、天宝以下便属中唐。明人承袭严羽,也作如是观。高棅《唐诗品汇》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初、盛、中、晚,大致是由严羽的观点发展而来,以便严分盛、中之别而以盛唐为师。清人大致也严守盛、中这个界限(说见后)。
从宋到明,人们的严守盛、中之界,往往是凭着直觉,意会到盛、中诗风之变。在理论上指出这一点的,最早大约是元人袁桷,但语焉不详。比较详明地加以阐述的,是清初叶燮的《原诗》,指出中唐不仅是唐朝一代之“中”,而且是“千古百代之中”,这是极为深刻的。
与此相联系,是杜甫的问题。杜甫在诗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尤其敏感微妙,可以说是枢纽的枢纽。杜甫仿佛是历史老人的有意塑造与安排,使他不仅有超卓的成就,丰富多样可资从不同角度效法学习的伟大作品,而且使他恰巧生当盛、中唐之交这一历史转折的关捩点上。他的小部分作品写于开元、天宝年间,流露出一点盛唐气象,多数作品则写于安史之乱发生之后,那正是唐代由盛入衰的转折点,开始步入中唐。他的作品本身,也恰好体现着唐代由盛至中的诗风的演化,体现着中国古代诗学由前期向后期的演化。他的诗中已透露出一些理学思想的胚芽。他作诗好议论、说理、叙事、铺陈,风格转为苍老瘦劲,语言方面常用俗语,格律上常用拗体,总之,已开了“以文为诗”的先河。这些,正合于宋、清人的审美趣味和需要。他仿佛是中国诗学思想史上的“二传手”。“一传手”是《诗经》,汉儒解释引申出适应前期需要的诗学思想。杜甫则被称为“诗圣”,其诗被称为“小诗经”,对其解释发挥又正合于后期诗学的需要。他的诗又被称为“变体”、“别调”,其实就是“宋型诗”。因此宋人极其推崇他,以他的作品发挥出宋代诗学思想的主要特征。“祢宋”的清人也推崇他,以他与韩愈、苏轼为三个解释学支柱,显然也将他的作品视为“宋型诗”。凡是追求蕴籍、玲珑之美的则往往不喜杜诗,明代七子派的后学以及清初王夫之、王士祯对他尤有微词,甚至称之为“罪魁而功首”、“诗中秦始皇”,就是因为他扭转了传统诗风。给他在唐代诗学史上定位是颇费思量的事,许多诗话、诗论将他列入“盛唐诸公”之外,甚至列入“唐人”之外。本书则将他置入中唐部分述及。
以中唐为枢纽,中国诗学思想史的前后两期恰巧可以对应叠合起来:宋对汉,明对六朝,清对唐,晚清(1895—1911)对先秦。汉代是经学期的奠定者,诗学思想上重“礼”而轻“情”,魏晋六朝则重“情”而轻“礼”,是对汉代诗学的一个否定;唐代复古派要求恢复汉代诗学精神而又情礼兼重,可以说是一个合题,画下了中国诗学思想的第一个圆圈。宋代是理学期的奠定者,诗代思想上重“理”而轻“情”,明代则重“情”而轻“理”,是对宋代诗学的否定;清代“祧唐祢宋”,主“万古之性情”,情、理兼重,也可以说是合题,画下中国诗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圆圈。先秦与晚清都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为巨烈的时代。在诗学上,先秦可以说是向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淡入”,晚清则可以说是向近、现代诗学思想的“淡入”。这样,又画下了一个总的大圆圈。这便是本书所认为的中国诗学思想的逻辑发展。
本书各章试图以四字的标题概括各个时期诗学思想的主潮,并且这四字皆出于其当代人笔下,这是颇为费力而也许不讨好的。是耶非耶,只得一任读者诸君评判了。
标签:儒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诗学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思想史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理学论文; 毛诗序论文; 宋朝论文; 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