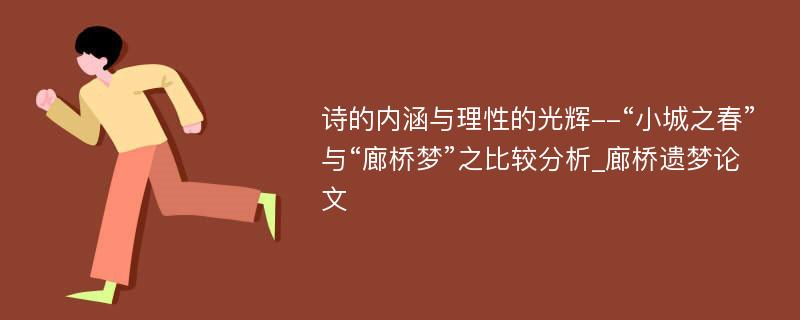
诗意的内蕴与理性的光彩——《小城之春》与《廊桥遗梦》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彩论文,内蕴论文,诗意论文,小城论文,之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城之春》(以下简称《小》)讲述的是1946年发生在中国江南小镇一个被战争摧毁的破落家庭中一段幽怨而哀伤的爱情悲剧。《廊桥遗梦》(以下简称《廊》)叙述的是1965年发生在美国依阿华州一段充满激情又满载惆怅的爱情故事,时间跨度从1965至1989年。两个爱情故事都是围绕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的情感选择而展开。《小》中的男女主人公最终无奈分手告别;《廊》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经历了令世人魂牵梦绕的四天激情浪漫的生活后也劳燕分飞,从此两地相思直至终年。
在中美电影史上,《小》与《廊》都以其独有的魅力占据显要位置,尽管两部影片讲述的是两个国度、不同年代的“悲情”故事,但都唤起了观众和影评人的共鸣与赞赏,甚至都在特定的时间形成轰动一时的热潮。相同的题材,不同的艺术旨趣形成了影片各自不同的风格。
《小》在放映后,因缺乏曲折的故事情节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感观刺激,票房惨淡,甚至被中国最具权威性的《中国电影理论史》一度称为是一部“具有消极意味”的电影。《廊》的放映曾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况,然而却最终与代表电影界最高荣誉的“奥斯卡”无缘,与《小》不同的是,它在票房上却是凯歌高奏!当所有的热潮退尽,当我们重新用审慎冷静的目光来审视这两部分属中美电影史上的杰作时,我们会发现其中有太多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值得去比较、分析、咀嚼和回味!
一、影片的叙事风格
(一)两部影片均以倒叙方式和独特的视角来讲述故事
《小》片中以老黄(管家)、戴秀(周玉纹小姑)、周玉纹送别章志忱开头,此时人物的感情抉择过程已经结束,事情的原委主要以女主人周玉纹的主观视角来交代,影片的叙事视角好像是周玉纹的双眸,但在叙述过程中,有些内容却跳出了她可察觉的范围。有她旁白的那些场面,有的是她在场,亲历的;有的却是过去时态,几乎是她后来得知的;有些则与她的旁白平行展开,更为甚者是她根本不知道的,却由她说出来,典型的是戴礼言吃安眠药一场,这似乎造成了叙事混乱,打乱了常规叙事的人称和视点界限。从理性的角度看,这种叙事模式是杂乱的,但若从审美情感上去感受却是独树一帜,既有别于西方的那些受“意识流”和“精神分析”影响的影片的叙事方式,又有别于传统电影的叙事方式。
《廊》片中采用同样的方式,即开始叙述儿子麦克与女儿卡珞琳发现母亲(弗朗西丝卡)的遗书(信件),浪漫情感随之以回忆的方式铺呈开来。在《廊》片中,导演多次运用闪回拍摄手法,来回穿梭于过去与现实之间,让昔日母亲与罗伯特感情世界清晰地浮现出来。影片时空建立在充分的假定性之上。为了思想,时空的变幻可以给创造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电影理论家潘洛夫斯基从分析电影的形式着眼,提出电影是“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1]。故而,影片在叙事中总是在男女主角感情渐渐澎湃时有意打断。如第一次弗朗西丝卡同罗伯特喝酒后即将进入第一个感情高潮插入了麦克与卡珞琳的对话,这种时间上的阻隔也实现了空间转换;第二次,罗伯特与弗朗西丝卡接吻时,影片镜头再次切换到1989年,且只是插入两句话;第三次是在第三天的晚上,当罗伯特与弗朗西丝卡有了爱的升华后,影片又一次加入麦克与卡珞琳的一长夜的对话。
如果说《廊》片追求的是对传统题材注入全新时代特色的话,那么《小》片可谓在展现情感冲突,关涉生命、人性、情感等心理表现时,更是导演在追求电影上“作中国画”的愿望的实现!虽然与《廊》同样采用倒叙手法拍摄,但费穆在谈及《小》片时说:“我为了传达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用‘长镜头’和‘慢动作’构造我的戏,做了一个大胆和狂妄的尝试。”[2]这或许也就是《小》片为何在80年代以降被尊为世界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它对既有现代特征又有民族风格的中国电影做了大胆超前的实验和成就卓著的求索,具有一种先行性的开启现代电影创作思维的历史意义,就连当今中国影坛炙手可热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也坦言难以超越费穆。
(二)对心理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揭示
《小》片中对心理世界作了灵巧的剖析与展现。由于在《小》片中,导演费穆“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化中‘诗’、‘骚’的抒情传统,并揉进了中国绘画的生动气韵。”[3]他没有追随主流趋势去表现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也没有慷慨激昂地颂扬轰轰烈烈的革命现实,而是以睿智的目光,“试验性”的镜头语言来揭示处于动荡年代里人的精神世界,去揭示女主人周玉纹在丈夫戴礼言和以前男友章志忱之间作选择时的痛苦的心理历程,从而使得影片“充满沉郁而悠远的诗情诗性。”[4]影片对当时时代生活保持不懈的诚挚而热情的投入与关注,对人类天禀生命力作了无限开发,尤其对知识者哀怨、苦闷、忧郁、情欲、爱念等心理曲尽其意。同时,也把欢乐、痛苦、勇敢和尊严授予人物性格与生命世界。因此,《小》片保持了人生中最微妙最渊深隽永的感受、体验和释放,将绻怀朋旧与感伤时事熔为一炉,于旧式感唱和伤怀中孕育新的感受、新的希望和新的震撼力量。
在《廊》片结尾部分更是如此。雨中,罗伯特·金凯的车停在十字路口,弗朗西丝卡坐在丈夫理查德·约翰逊车中,右手数次想打开车门随金凯离去,可是最终依然留在丈夫车中,任泪水模糊双眼!“我错了,罗伯特,我不说留下……可是我不能走……让我告诉你一遍为什么不能走……你再告诉我一遍,为什么我应该走。”这激烈的内心冲突确实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抉择的痛苦状态,令观众看罢心潮翻滚,久久不能平静。其中的人物选择仿佛就是自己在作选择一样,而且此类选择与内心冲突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处处存在着呢?选择过程中所折射的人性魅力在影片中被展露无疑。
二、优秀剧本及影片的象征意义
《小》与《廊》两片都是文学性极浓的影片,前者倾向于诗意化,而后者则倾向于小说化;前者充溢于心灵而惆怅无边,后者则源于激情又超越于激情从而理性弥漫。他们之所以成为电影精品与其剧本创造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后者。
沃尔特的8万字中篇小说《The Bridge Of Medison》(中译名为《廊桥遗梦》)在1992年出版后,连续3年高踞美国畅销书榜首,发行逾1 000万册,在中国初版即印15万册。导演伊斯特伍德说:“是故事中那种十分单纯的情节,故事中两个主人公孤独地生活在各自不同的世界中,他们相识、相知并相爱,没有十分复杂的情节,这可以使我们充分剖析他们的性格、体会他们的情感与进退两难的处境。”[1]费穆同样指出:“电影的第一线兵力是剧作家,剧本好了,纵使一切都差,仍不失为一部好影片。”[5]355话虽显得有些偏颇,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好的剧本对一部影片有多么的重要。李天济(《小》片的剧作者)的初本显然是不很成熟的,但其中蕴含的某些东西吸引了导演,就如同《The Bridge Of Medison》的单纯简洁吸引伊斯特伍德一样,“激发他的创作灵感,首先是剧本中所含的诗意;其次,剧本写出了对人——普通的知识分子个人一一的关怀,写出了人的心声;其三,是一个‘真’字。”[5]358由此可见,正是优秀的剧本为两部影片语言的完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娴熟婉转的“镜”语和流畅的造型风格中暗藏着哲理与机智,饱含诗意与韵味。
在两部影片中几乎都同时使用了象征性的“镜”语来阐释生活、预示未来,从而使得影片从平面走向深邃。
在《廊》片中,第一幅回忆的画面是理查德一家围坐在厨房吃饭,镜头依次划过每一个人,呈现出一个整圆的图形,这暗示出了家庭的完整。当然,在这中间也有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如父子俩的两次关门声,这或许就在预示着家庭中潜在的某种变化!但整个画面流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完整的,并且在结尾处类似的画面又出现一次,即弗朗西丝卡与罗伯特分手后,还是用同样的角度表现了同样的画面。影片重复出现这一画面,在于强调家庭的圆满和每一个人在家庭中的位置,这无疑是加在影片道德一方的砝码,也预知着风浪后的平静!另外,道尼太太(露茜)与人私通为全镇人诟病,把露茜酒后被辱和弗朗西丝卡上街买衣服联在一块表现,两组镜头交叉出现,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弗朗西丝卡的命运。影片最后让露茜嫁给道尼过上幸福生活,实际上暗示了弗朗西丝卡的行为带有反叛色彩与合理的因素。
在《小》片中,城墙反复出现。影片以城墙始,又以城墙终,周玉纹反复在城墙上走,她与章志忱的两次约会也在城墙。这里的城墙不是一种具体描写,而是一种抽象的表现方式。它实际上是那个我们在屏幕上看不见的“小城”的缩影,它是一种象征,又意含包围。
三、人物:丈夫·妻子·情人
两片主要人物关系几乎一样,然而每个人物都各具独自的性格特征。
《小》片中,丈夫与妻子关系用“病态”两字形容最为恰当不过了。表面上相敬如宾,内心却各自为政,走着自己的路,仿佛永远也没有交错的机会。身体孱弱的戴礼言在察觉妻子在遇到昔日好友时所迸发出来的青春,只是自叹自怜并曾试图以自杀来表明自己的存在,与其说是“爱的崇高”,不如说是“爱的苍白”。在他身上我们隐约地看出战后昔日地主阶层衰落的命运,想爱却又无力去爱的无奈。《廊》片中的理查德·约翰逊朴实、厚道,习惯于平静如钟摆的生活,在生活情调上他有着与戴礼言一样的“先天免疫力”,然而他并非像戴那样衰弱与空虚,他并不消磨时光,而是致力于经营庄园,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尤其可贵的是他对自己的生活有着自知之明,对于弗朗西丝卡的感情有着清醒的认识,如当他1983年去世时对妻子说:“我知道你有梦,可是我没办法让你实现了……”因此,在我们的视野中,戴礼言“悲得可怜可恶”,而理查德却是“悲得可亲可爱”。
两片中的妻子都同时面对两个男人:丈夫与情人。周玉纹对丈夫没有感情,尽管嫁给戴礼言,但这或许是个历史本身造成的悲剧,并非出于真心,面对孱弱无能的丈夫,自己情感也在这种“名不副实”的夫妻关系中日益耗尽,对他只剩下尽妻子的“礼”与“麻木感”,然而她并非情愿独守闺房、孤芳自赏,当遇到昔日情人时沉寂于内心多年的情感与欲望慢慢地被唤醒,无奈礼仪这条难以逾越的道德鸿沟横亘其间使得周玉纹只能“望情兴叹”。相对于周玉纹,弗朗西丝卡的感情显得更为汹涌、更为澎湃、更为刻骨铭心。四天的遭遇足足支撑着全部的感情生活,她在追求情感自由时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意大利女人天生就具有的浪漫气质给她更添几分妩媚,尤其是深藏在她内心的“美国梦”使得她即使在枯燥乏味的现实生活中仍能保持着活力与吸引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弗可以摒弃陈规旧俗的束缚。于是在疲惫的人生之旅和无穷的期盼中,观众看到了弗与罗“通过‘灵’与‘肉’的高度的、和谐的、优美的结合,终于找到了精神的家园与心灵的归属,终于使他们的人性得到升华。”[6]虽然从传统观念上说,她曾经背叛了自己的丈夫,但她仍不失是一个具有健全人格和优美情感的伟大女性。与弗和罗的情感比较,周玉纹同章志忱则呈现出“灵”与“肉”的剥离,不同的处理手法,究其根源自有着其背后隐藏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缘故,但在男女情感体验中,又都契合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廊》片让我们感受了现代版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悠远绵长的艺术氛围;《小》片中背景描摹让我们切实体会到了一千多年前杜甫《春望》所建构的沉郁悲怆风格,其中的情感叙述则又内含着《钗头凤》中“陆游唐婉式”的哀怨!显而易见,不同的国度在艺术旨趣的追求上往往是相通的,甚至是互为借鉴的。
作为情人,章志忱与罗伯特·金凯都富有活力、朝气,在影片中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较前者有更丰富的阅历和成熟气质,在追求情感上更为直白与坚定,敢于追求“伟大的激情”;章志忱虽然也充满理想,渴望激情人生,但“朋友之妻不可欺”的古训始终迫使他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发出“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的感慨。“他宁愿让美好的感情在想象中天长地久,让激荡的欲望在无为中自生自灭,也不愿背上离经叛道的罪名!”[3]
四、审美追求及深层文化阐释
《廊》片中人物虽然在梦幻般的四天中实现了“灵”与“肉”的结合,但最终与《小》片一样,“有情人终未成眷属”成为影片相似的结局,这或许是一种缺憾,但正是这种缺憾方使得影片保持着持久的魅力,它满足了我们爱情审美中的悲剧美感,让我们在欣赏影片时获得持久的审美愉悦。费穆曾谈到,《小》片力图割去“光明的尾巴”。故而在《小》片中,人物最终的命运走向,未来生活图景都不得而知。尽管《小》片在感情渲染上缺乏《廊》片浓墨重彩的笔力,但在艺术结构掌握上则显得更为开放,给予观众更宽广的创造空间!
《廊》片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影片情感抉择中所蕴含的“理”的精神,而《小》片则更多地在于对电影艺术与其诗境的自觉追求,因此,尽管同样的结局但其背后的民族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各自成因却大相径庭。《小》片展现了“情”与“礼”的冲突并且“止乎礼”,而《廊》片展现的是“情”与“理”的冲突最终“止于理”。
如前文所述,《小》片拍摄于1948年,费穆弃主流而另辟蹊径,将人物置于抗战刚结束的满目疮夷的江南小镇背景中,破天荒地让传统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让位于一个三角恋爱的情感冲突与选择,以此来表现情礼之间的困境,表现人物在情礼之间微妙的心理压抑与情感欲望的相互冲突与痛苦的煎熬,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真正地能够读懂影片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影片放映后外界反映平平,票房收入惨淡的原因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廊》片尽管未问鼎奥斯卡,但票房却大获丰收,各界对其更是褒奖有加。“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作家白桦语)。笔者试图探寻这一现象成因中其深层的社会文化背景。
其一,影片中弗朗西丝卡与罗伯特突破了横亘在周玉纹与章志忱中间的传统规范,实现了“灵”与“肉”的统一,在艺术上它满足了我们对爱情中人性升华的审美追求;在精神生活中,它又符合人们对异性渴望的原始本性,影片中纯美的爱情正是数以万计的观众所梦寐以求的,影片实际上以其虚幻的视觉符号满足了观众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其二,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点,即弗朗西丝卡奔放深沉的情感最终服从理智。弗用自己的理智克制欲望,用责任战胜情感,这或许是影片风靡全世界尤其是美国本土根源之所在。从接受美学角度来说,《小》片因特殊的时代背景,其所期待的“观众视野”还未形成,而《廊》片正生逢其时,影片内容在时空维度与观众的期待视野中合而为一,故而形成万人空巷的盛况。
《廊》片既突破理智又止于理智,而《小》片恪守传统礼教游历于“肉”之外,保持着“灵”与“肉”的分离状态,这恰恰说明了影片背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谢遐龄就曾在《社会学研究》里撰文指出:中国是伦理社会,儒家的道德从本质上说是注重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就婚姻关系而言,儒教认为夫妇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与政治礼法制度的基础,即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政教之始’。”[7]而在西方,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形成了“要么对人类进行类的抽象,以理性作为建立道德大厦的基础;要么对个体作‘超越的突破’,将上帝作为个体永世追求的道德目标。”[8]因此西方的道德是建构在对人性的抽象和超越基础之上的,道德本质上追求个性与自我,所以弗与罗的浪漫爱情火花爆发自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然而,美国毕竟又是一个基督教传播及其广泛而深入的国家,“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保持的宗教信仰都是边缘性的。……李普塞特(Lipset)指出:‘没有迹象显示美国的宗教力量正在消弱,盖洛普和其它民意测验表明,在新教教徒中,去教堂最多的是美国人!……1991年,美国成年人中有68%属于一个教会,42%做礼拜,综合比例比其它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都高得多。’”[9]美国社会的宗教背景为我们理解弗朗西丝卡为何最终选择理智和责任提供了一扇缺口,于我们对影片的深入研究更有裨益!
从美国社会60年代“越是革命,越是恋爱”所引发的纵欲主义,到70年代“性自由”,美国尝够了苦果,难怪麦金泰尔说:“当代道德已丧失了人的目的这根主轴,道德理论沦为无社会背景意义‘概念框架的碎片’,失去文化中心首要角色,沦为狭隘边缘地位。”[10]美国自70年代的《克莱默夫妇》开始,《普通人》、《金色池塘》,一直到《母女情深》、《廊桥遗梦》,这些影片“因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朴实无华的艺术风格获得了世界影坛的首肯和观众的普遍欢迎。”[11]这正显示了美国社会伦理道德重构的追求趋势,体现了美国社会对爱情婚姻和家庭问题的深度思考与反省,体现了其对新型人生和人文环境新建的努力和企盼!这一切在《廊》片中都被尽数演绎着,更为全世界尤其是美国人民解读着,《廊》俨然成为一副治疗美国人精神病态的药方,恰如沃尔特在同名小说中所言:“在一个日益麻木不仁的世界里,我们的知觉已生了硬痂,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茧壳之中,伟大的激情和肉麻的温情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我无法确定,但我们往往倾向于对前者的可能性嗤之以鼻,给真挚的深情贴上故作多情的标签,这使我们难以进入那种审美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是理解弗朗西丝卡和罗伯特·金凯故事所必须的……”
当然对于弗朗西丝卡与周玉纹的选择,我们仍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做大胆而又中肯的推测。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出走后爱情的满足感与对儿子、丈夫的愧疚感扭结在一起,终于无法解脱而至精神崩溃。或许安娜就是弗与周玉纹的一面镜子,从中折射出自己出走后的相同命运。根据鲁迅对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分析亦知,由于女性自身经济依附关系,经济上不独立决定了她们即使能够走出原先的家庭,但最终注定要重新回到家里。
五、结语
《小》片用精巧的电影语言成功地营造出了诗意的内蕴;《廊》片用深邃的“镜”语使全片笼罩在理性光彩之下。通过对两部影片多向度的分析,可知两片子不仅有着太多相似处,而且还有诸多差异,但影片带给我们的美的享受和美的体验却是真切的、深刻的,超越了时空界线,尤其是影片本身孕育的哲理精神与审美内涵,分别将两部影片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将显其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