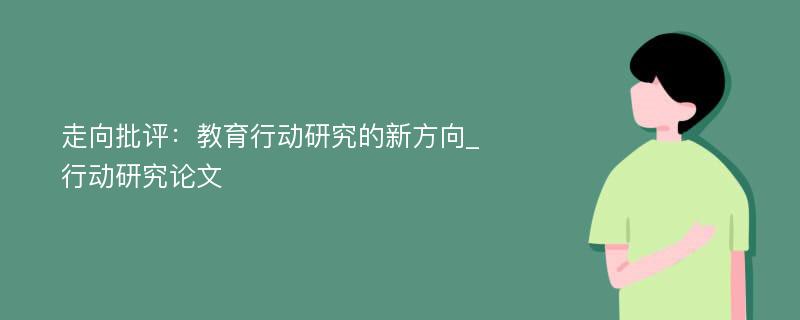
走向批判:教育行动研究的新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行动研究领域中,批判理论被大量地植入教育行动研究,致使“解放的行动研究”或“批判的行动研究”成为行动研究的“新方向”。但在批判的具体方式上,不同的研究者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实质上是在如何对待“教育制度”的问题上出现了某种分歧。
一、意识形态批判
在当代行动研究领域,澳大利亚学者凯米斯、格兰迪和美国学者金切诺等人成为倡导“批判的行动研究”的主将,其中以凯米斯的影响最大。
凯米斯认为,教师对他们的日常实践的理解已经遭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使教师以扭曲和误解的方式理解现实。教师反思的内容以及反思的方式都已经被意识形态控制,教师的自我反思、自我理解本身已经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他们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反思将误解教学和学习过程而复制霸权的合法性。
由于教师受意识形态的遮蔽,如果没有外部的批判理论的辅佐,教师对实践的理解将无法构成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就是说,在没有外部批判理论的帮助下,教师的自我反思将无法使自己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而获得解放。
凯米斯认为,与其他教育研究方式不同,接受了批判理论“启蒙”的行动研究应该坚持以“批判的方法”消减行动研究中的技术控制。行动研究并不反对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问题,但必须抵制那种将教育研究视为实践者接受科学的某些条款,然后将科学的原理应用到教育中的“研究-应用模式”。为此,凯米斯等人就坚持解放的行动研究必须满足5个“要求”:
1.它拒绝关于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实证立场而赞成一种“辩证的理性”。
2.它必须意识到应该由教育行动的执行者对教育实践作出解释。
3.批判性研究者必须努力反思并超越意识形态的曲解。
4.批判性研究者必须揭示那些阻碍教师试图追求理性目标的社会规则的干扰。
5.批判性研究必须意识到它与实践的关系。
这5条要求几乎成为“批判的行动研究”或“解放的行动研究”的宣言。另一位批判的行动研究的倡导者金切诺在《教育成为研究者:通往授权之路的质的研究》一书中对这5个要求重新做了解释。后来在《幕后相见:走向批判的后现代行动研究》一文中,金切诺对英国学者埃利奥特等人的“实践的”行动研究观提出了批评。金切诺认为“实践的”行动研究者缺乏批判意识,他们没有意识到当管理者为教师选择了研究的问题时已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行动。结果,烹饪书式的技术性思维方式受到鼓励,教师则成为依照食谱做菜的技工。这种观念的根本原因在于行动研究不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研究方式。传统的研究向来被认为是收集资料和追求抽象化的实证方式。这种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不受挑战,以致于一些进入了行动研究的教师仍然不认为自己参与了“真正”的研究。即使那些感到自己已经参与了研究的教师也仍然坚持他们所做的研究只是一种低质量的活动。在他们的大学教育中,教育研究被定义为一种有控制的实验设计并充满系统的资料分析。这种定义在暗中破坏了他们选择适合的研究方式的能力,或展开与他们实践生活相关的研究的能力。
根据金切诺的观察,很多教师感到实证研究与他们的期望和需要毫不相关。实证研究既没有使教育问题明确化,也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实证研究追求的精确性和对预设的强调在日常教室生活中几乎没有用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教师越来越感受到教育研究很少有助于改善教师的生活。在传统的专家研究中,“教师被作为学校的土著人被客观地研究”。奇怪的是,“教育世界和它的工作环境几乎视为第三世界文化,教师在教育研究中几乎成为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农民”。由此,金切诺建议人们重新考虑杜威的观念。杜威在《教育科学的资源》一书中认为,教师最重要的角色是通过研究来探明教育学问题,当杜威提出“教师成为探究者”时,他已经将教师视为决定学校成功或失败的最重要的研究者。
二、作为“反思”的批判
埃利奥特作为“实践的行动研究”的热情倡导者一直被抱怨在权利、意识形态的批判等问题上无所作为。这些抱怨是有根据的,因为埃利奥特对“解放的行动研究”一直颇有微词。但埃利奥特并不否认批判理论所揭示的意识形态控制的可能。他在1980年撰写的《课堂研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文章中,已经意识到“行动研究与批判理论”的关系:在福特教学研究中教师们越来越感到理想与现实的分隔,并提出他们缺乏改变现实的自由。他们引证了大量的来自制度、社会和政治背景的教学障碍。如果这些教师想要提升他们的行动自由,那么,他们不仅要理解他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所作所为,还要清楚他们的行动怎样受到制度、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和雕琢。
这样,行动研究就不只是一种课堂教学的活动,它应该超越课堂的界限。埃利奥特认为,“课堂行动研究因而也存在哈贝马斯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其他一些成员所声称的教学情境中的批判理论问题。这种理论将澄清教师的教学如何受到课堂之外的制度、社会和政治等因素的操纵。教学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信仰和价值观的限定。”因此,教师若指望改变课堂教学,他首先得理解限制课堂教学的“制度化结构”。教师的专业发展也必须以理解制度化结构为前提,“他不得不超越课堂中的师生互动的研究,关注那些扭曲教育功能的制度化结构。”
可见,埃利奥特与凯米斯等人一样,也承认批判包括意识形态批判的价值。其区别只在于凯米斯等人坚持用哈贝马斯等人的批判理论使行动研究成为“解放的行动研究”,而埃利奥特等人却认为“反思性实践”已经具有批判的力量,不必节外生枝地以“解放的行动研究”来规范和取代教师已经置身其中的“实践性反思”或“反思性实践”。受埃利奥特的影响,美国学者麦克尔南对凯米斯等人的“批判的行动研究”也提出批判。麦克尔南认为凯米斯等人借用“宏大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而倡导批判的行动研究,以此来使实践者向这种研究范式顶礼膜拜,至少有两个错误:第一,从来没有行动研究可以通过“宏大理论”而带来自由或解放。第二,哈贝马斯、凯米斯、卡尔以及那些赞赏新批判社会科学的人所使用的“语言”对教师、管理者甚至对一些学术中人来说显得陌生而疏远。该学派由于它的抽象而复杂的“语言”而不可能吸引广大的教师。而且,卡尔和凯米斯的“走向批判”模式意在“劫持”行动研究运动以便获得理论控制,这与他们所看到的教育为不公正的力量所控制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一种“学术帝国主义”。
埃利奥特因此更愿意将行动研究理解为“反思性实践”,将斯登豪斯的“教师成为研究者”理解为“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在埃利奥特看来,在行动研究中,教师的“反思性实践”已经内在地包含了“批判”。根据他与教师一起“做”行动研究的经验,埃利奥特相信,“当教师反思他们的行动与其教育价值是否一致时,他们也开始对那些关涉价值的理所当然的信念和假设提出质疑。”
由于埃利奥特坚持行动研究应该成为“合作的行动研究”或“校本行动研究”,而不只是教师个人化的、孤岛式的研究,这种对“合作”的重视使他在自己指导的行动研究中尤其在“师生互动与学习效能研究”中特别关注了“制度化问题”。他提醒人们,“在制度化情境中,教学改革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创造。它总是受到制度的限制,而个人的力量无法超越制度去引起有效的变革。制度总是对个人发生影响,比如选择、排序和组织课程的内容;制定学习方案;组织学生的社会方式;为学生提供学习的时间和资源,等等。”这使得教育行动研究事实上成为一种对课程制度的研究。当教师基于共同关心的问题参与合作性反思时,他们将推动整个制度的发展,因为制度本身也需要教师的集体合作。对制度的反思使行动研究具有“民主参与”的精神。它使教师放弃对课堂教学的控制而将课堂还原为一种师生共同参与的领域,也使学校校长可能因此而放弃对整个学校制度的控制,而将学校还原为教师参与管理的属地。
不过,当埃利奥特希望以合作的行动研究来抵制技术统治或解决制度化问题时,他仍然坚持行动研究是“创造性整合”而不必成为“批判的行动研究”。他认为“合作的行动研究”已经包含了对相关制度的反思。教师要使用自己的权力抵制技术理性对教师专业的控制,但这种抵制不必发展为“反抗”和“阻止”的形式。有效的抵制是一种“创造性整合”。
三、对待“教育制度”的分歧
人类一开始就是以群体的方式在自然界展开种种生存活动(很多动物其实也是以群体的方式展开自己的生存活动)。组织、制度、结构原本是将分散的个体组成有秩序的群体,以群体的方式提高活动效率,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为个体追求幸福提供结构上的保证。没有组织、制度和基本的结构,一盘散沙似的个体行为不但降低了个体活动的效率,甚至连个体的自由也得不到保证。但任何组织、制度和结构在其运作的过程中总容易发生“异化”而对个人的行动和思想构成一种压抑,在极端的状况中可能使个体成为不自由的、不幸福的、不快乐的受奴役者。这就是埃利奥特等人所关注的“制度与个体”的冲突,也是凯米斯所考虑的“社会与个人”的冲突。
实践的行动研究与解放的行动研究显然都以“个人与制度的关系”为思考的焦点,但埃利奥特与凯米斯等人在个人如何理解“制度”的问题上发生分歧。批判性行动研究是对制度的“限制”后果的批判却较少理会它对个休自由的护卫意义(包括法律保护),而实践性行动研究倡导者如埃利奥特接受英国学者吉登斯的“结构理论”而反对“犬儒主义”生活哲学,其目的就在于恢复那些被人们遗忘了的关于制度的某些合理性记忆,要求对制度保持某种“有意的遗忘”,达观自如地从制度中解放出来,并进而倡导一种新的生活理念,设计一套新的生活哲学。
从这里可以看到,对个人与制度的关系的考察,实际上关涉人对自由生活的情感、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对生活理念和生活哲学的建构和选择。教育行动研究的倡议者之所以费尽心机地思虑个人与制度的关系,揭示权力的运作方式,乃因为个人如何“观看”制度,将影响教师的生活态度。教师个人若不接受一种积极的新的生活态度,形成自己新的生活哲学,“教师成为研究者”不过是纸上谈兵。
任何制度总是既保证某些人的某些自由又限制另外一些人的另外一些自由以获得整体的活动效率。埃利奥特等人的目的并不独立特行地将这种状况颠倒过来,只是激励教师在制度面前保持精神自由的理性,在现存制度中利用制度提供的创造空间追求变革、创新的可能或在改变制度的过程中获得变革的自主和自治。批判理论虽然激进一些,但它的根本特征也只是“启蒙”和“解放”。前者使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兴趣和利益,后者使人在反抗不平等和非正义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由。而按照凯米斯等人的设计,批判的或解放的行动研究不过是建议教师在“个人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保持一种积极的、有所作为的辨证理性的态度。凯米斯借用卡尔·马克思的话说,以往的唯物主义只看到了人是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制度)的产物,环境改变了人,却忘了环境也在被人改变,是人改变了环境。这样来看,人与社会、理论与实践就不会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其中空出了大片自由活动的空间。
但埃利奥特认为凯米斯等人的“批判性范式”坚持了一个错误的假设,以为“结构”、“制度”是独立的并存在于教师的个人活动之外。它的根本的错误还在于,它假设了“结构”是社会系统的特权。
埃利奥特借用吉登斯的结构理论对“批判性范式”所坚持的假设表示了不信任。按照吉登斯的解释,系统并不使教师个体活动结构化,因为系统并非独立地、外在地存在。系统不过是不同的个体活动经历时空的变化而形成的结构化权力。这些结构化权力表现为“规则”和“资源”。“规则”是应用于社会实践的抽象程序。在学校中,就有这样一些基本程序来处理“问题行为者”、确立学科、根据学生能力分组、选择和组织课程等等。“资源”则包括“分配”和“权威”两个方面。前者针对一个系统控制物质的能力,后者针对系统控制个人的能力。结构既是实践的中介又是它的成果。它们并不从外部限定个人的行动,因为它们并非存在于个人行动之外。而且,作为社会系统的结构乃由个体行动构成并受个体行动调整。结构是如此内在地根植于个人能动意识之中而不在其外,它也就不能与“限制”等同。结构当然限制个体不能做什么,但同时它也为个体做什么提供便利。结构与其说为社会系统产生权力来控制个体行动,毋宁说它为个体提供资源来引起个体与他人之间发生相互影响。在埃利奥特看来,“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对行动研究的意义在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在限定教师做什么的同时,也为教师的能动活动提供资源。”
总之,“实践的行动研究”与“解放的行动研究”虽然都承认“批判”的价值,但在将批判落实为“制度批判”之后,两者出现了有不同的意见。“解放的行动研究”明显地对政治、权力问题的批判充满热情。但它并非无理地向政治和权力挑衅,其倡导者只是在个人与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较之埃利奥特和萧恩等人更急切地建议个人对制度保持清醒而顽强的抵制意识和反抗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