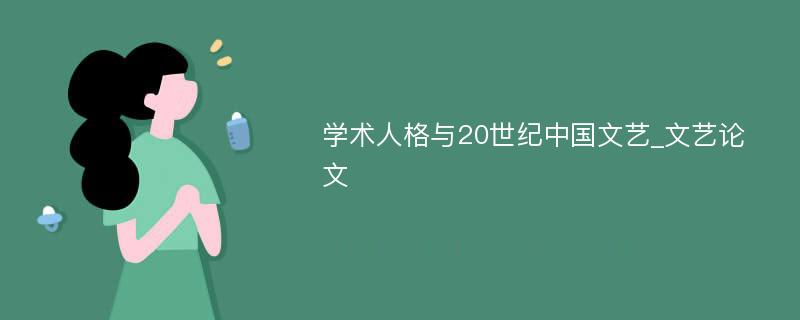
学术人格与20世纪中国文艺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中国论文,人格论文,学术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学,是人类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民族才华与智慧的结晶。但当我们回首20世纪的时候,不能不感到窘迫与尴尬。与思想活跃、流派众多、大家迭出的20世纪西方文论界相比,我们能够摆得上桌面的成果实在不多。对此局面,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更习惯于追究时代战乱、“极左”思潮之类的社会原因,却似乎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在时代背景与社会历程极为相近的同一个世纪里,人口远比我们少得多的前苏联,仍向世界奉献出了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卡冈的“艺术形态学”、维戈茨基等人的“文艺心理学”等重要成果。实际上,本世纪的中国文艺学之所以陷入困境,除了某些社会原因所导致的理论空间的狭窄、文化资源的匮乏之类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这便是:中国文艺学家、美学家学术人格的退化与病变。
一、学术人格的体现
在本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实际上并不缺乏富有理论素养与学术根底的人才,在宗白华、朱光潜、冯雪峰、周扬,胡风、钱钟书、李泽厚等人身上,我们均可以看到这种素养与根底。但遗憾的是,却没有人能够成为堪与同时代西方许多文艺理论家相抗衡的理论大师。即以代表了本世纪中国文论最高成就的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李泽厚等人的著述来看,也是不尽人意的。宗先生对某些美学、文艺学问题的洞察是深邃的,却没有留下一本自成系统的理论专著;朱光潜先生是中国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的开山者,但建国之后,除了在翻译研究西方美学方面的贡献之外,似乎再也没有更多深刻独到的理论创见,其“主客观统一说”,实际上也井没有超出狄德罗与康德;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等。无疑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辉煌高峰,但其中毕竟也缺少原创性的思想体系;李泽厚在美学方面的“实践观”,也主要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进一步阐释,其“积淀说”,在文化视野方面,倒不如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更为宏阔。这种境况,除了外在社会历史原因之外,便不能不说与其学术人格方面的某些局限有关。
学术人格,首先是指能够立足于学术本饨,敢于坚持真理,不为现实得失所扰,不为名纲利索所羁,乃至不惜为之献身的殉道精神。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伟大理论成就,正是源之于这样的主体人格。刘勰是在远离世俗尘嚣的定林寺完成了一代名著《文心雕龙》;李贽是以“头可断而身不可辱”的人格精神,提出了反叛儒家道统,至今仍为人看重的“童心说”;康德是在终生没有离开哥尼斯堡的苦行僧式生涯中,创建了他的学术伟业;叔本华与尼采,亦均是在不为世人理解的孤寂中度过了冥思苦索的一生。在本世纪的学术史上,中国知识分子中当然亦不乏这样的人格。如被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下半叶第一文化良知的马寅初,当“新人口论”遭到批判时,一位领导人曾出面劝他写一份检讨,马寅初的回答则是:“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并公然声明:“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注:参见朱健国《不与水合作》,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年版第251页。)在史学领域奉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格;在文艺学领域敢干向中央直接进言的胡风,以及敢于公开站出来为胡风辩护的美学家吕荧;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顾准,也都表现了这样一种可贵的人格风范。然而,这样刚烈不屈的学者毕竟太少了。
而且,如果以更高的学术人格标准衡量,即使在胡风的人格中,也仍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胡风对当时文艺状况的批评,虽然表现了追求真理的勇气,但其中也分明夹杂着“怀才不遇的怨愤”。贾植芳先生曾分析过胡风悲剧的文化根源:“如果说,中国农民并未摆脱掉封建皇权思想,革命成功有‘杀到东京快活一番’以至轮流做皇帝的念头,那中国知识分子又何尝没有择良木而栖,投向新朝,分得一官半职的思想?连大名鼎鼎的革命诗人柳亚子在建国初期都有‘无车弹铁怨冯驰’之说,何况一些自认为有功于革命的小知识分子?”(注:贾植芳《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9页。)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文化人格局限,使胡风这样一位渴望学术民主、言论自由的文艺理论家,当年也曾以非学术的逼人的态势,指责好友冯雪峰主持的《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向反动的胡适思想投降、向朱光潜这样一个“为蒋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务的人”投降。这样一种局限,自然也使胡风的言论中多了些肤浅的怨愤不平之气,从而影响了更为深速系统的、超越性的学术思想的创建。
真正的学术人格,不仅要独善其身,而且还要有思想锐气,即应从一位知识分子应有的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感出发,不避凶险,敢于抗拒邪恶,勇于探讨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敏感问题。由于文艺与政治及社会现实的密切关联,自然也需要这样一种人格精神。而在我们的文艺学家、美学家中,虽然不乏独善其身者,但却很少马寅初、顾准那样的精神斗士。在批判风潮汹涌的50年代,宗白华先生能够以超然的智慧,固守着心灵的净土,诚然可贵,但这样一位学养深厚的美学大家,自建国一直到1956年,居然不曾公开发表过一篇理论文章,又不免令人为之慨叹。从一些人的回忆中可知,钱钟书先生本是一位客欢特立独行,敢于抨击时世的人,而在建国之后,则深居简出,力避思想锋芒,像是变了一个人,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文革”时所反思的:“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役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注:钱钟书《干校六记·小引》,见《杨绛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版第72页。)在建国后冷峻的学术环境中,洁身自好,避离现实,这也许是知识分子能够找到的最佳生存方式,且做到这一点,已大可敬佩,但这与更高境界的学术人格相比,毕竟还是有距离的。在这样一种人格境界中,要成为伟大的文艺思想家。自然也是很难的。
学术人格,还应体现为学术韧性,即无论在怎样的逆境中,仍能执着求索,在思想创造的天地里安身立命,而不是悲观失望。前苏联的一些文艺理论家,虽与我们有过相似的政治背景,陷入过与我们相同的严酷困境,但他们照样早有建树,在很大程度上,便正是凭依这种学术人格。创建了“复调”理论的巴赫金,曾有过不亚于许多中国学者的不幸:只因参加过一个自发的学术团体,便被关进了集中营并被判处流放6年。后来虽被获允进萨兰斯克师范学院教书,处境却依然十分艰难,不仅政治上一直未获平反,学术成果不能发表,生活条件也极为恶劣,夫妻二人曾不得不栖身于一座废弃的监狱。但这一切并没有磨灭巴赫金的学术雄心,仍坚持埋头著述。终于,这位终生不曾成为教授、不曾成为苏联作协会员的人,却以无法掩灭的理论光辉,成了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形式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由于对十月革命的误解曾经遭到追捕,但在逃亡途中,竟一直未曾停止《情节是一种风格现象》的写作。就是这位有着政治前科、后来再度遭到缉捕的人,出于对学术的赤诚,敢在苏联文坛上公开提出了被视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形式主义见解。卡冈的《艺术形态学》,也是在冒着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风险中写成的。相比之下,我们的理论家,无疑缺乏这样一种能够于逆境中坚持学术探求的精神,故而当寒潮退尽,时代复苏之后,除了控诉历史的过失,或诉说自己的冤屈之外,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出独立思考的学术成果,以填补荒谬时代的理论空白,以证实自己学术人生的价值。
二、学术人格的退化
实际上,本世纪的中国文论史,曾经有过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便是令人向往的“五四”时代。与个性解放的时代浪潮相关,“五四”时代曾经出现过从多角度独立思考文艺问题的局面,如郭沫若、成仿吾等人曾强调文学是非功利的生命反映;茅盾、田汉等人提出过“新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论;许地山则从佛家教义出发,提出文艺要为全人类服务等等。在这些新的思绪中,无疑隐含着文艺理论生长的因子:如郭沫若等人的“生命反映”论,或许有可能衍化为中国的表现主义学派;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论,或许可以发展为中国的人道主义文学观;茅盾等人的主张,或许可以扩展为中国的新浪漫主义学派;许地山富有宇宙意识的文艺观,或许有可能进一步形成现代意识的宗教美学。但遗憾的是,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斗争的日趋尖锐,民族生存危机的爆发,中国的文艺学走向很快发生了转折,即由多角度的探索归拢为一统化的“工具论”主张。与之相关,在文艺学家、美学家那儿,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个性意识的日趋淡漠,学术人格的日渐退化。
其一,由独立的文艺学目的,转向了非学术的政治功利目的。特别是随着革命文学论的高涨,“五四”时代,那些一度思想活跃的文艺学家、美学家们,大多很快放弃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独立思考,而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文艺工具论”。睿智即如鲁迅者,亦未能跳出这种匡拘。关于文艺本身的独立性,鲁迅本来是清醒的,他于1927年的一次演讲中犹这样说过:“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注: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见《集外集》,人民 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长期以来,鲁迅的这类言论,一直被视为转变为马克思士义世界观之前的产物,但恰是在这样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关于文学艺术的独立思考。但同许多人一样,鲁迅并没有能够格守这样一种独立的学术视角,而是发展为后来的绝对化地强调文艺的阶级性等等,从而影响了鲁迅更为阔大的理论视野的形成。
其二,由宽容的学术人格,转向偏激的批判人格。学术思想,本应是在宽容的学术氛围与尊重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中形成发展的,但在本世纪的中国文论史上,我们更多看到的则是一种剑拔弩张、非此即彼的偏激局面。特别是一些自信是从“革命立场”出发的理论家,几乎是容不得任何不同声音的。梁实秋只因主张“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反对将文学仅仅视为革命斗争的工具,即被指斥为“资本家的走狗”。胡秋原在《勿侵略文艺》一文中提出:“无论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自然主义文学,趣味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最近的民主文学,我觉得都不妨让他存在,但也不主张只准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而谁能以最适当的形式,表现最生动的题材,较最能深入事象,最能认识现实把握时代精神之核心者,就是最优秀的作家。”本是不无。道理的,亦被指斥为反对革命的文艺观。胡风所强调的作家要有“主观战斗精神”,即文学创作既要依据现实生活,又要重视主体创造,本是合平马克思主义能动反映论的;他对当时片面强调民族形式的不同意见,也不过意在维护“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传统。但所有这些,亦均被简单化地判定为抗拒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遭到了另外一些革命文艺理论家的严厉指责,并由此埋下了胡风后来人生悲剧的种子。在文艺学领域,为了追求真理,对错误理论予以实事求是的批判当然是必要的,但在我们的历史上,常常见到的不展这样的学术性批判,获胜一方也往往不完全在于是否占有了真理,而在于是否具有政治方面的压倒对手的优势,在于是否得到了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力量的肯定。这样的结果,自然只能导致非学术的批判人饨的膨胀,而使真正的学术人格受到压抑,从而加剧学术人格的退化。
其三,文化视野日趋偏狭。从人类的文化思想史来看,任何一仲有价值的学说创造,往往离不开阔大的文化视野。只有在一个阔大的文化视野中,理论家们才能建立自己的学术人格,才能自由选择思考的切入点。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缘其与酒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它许多学科的密切关联,文艺学的发展,自然更需要文化视野的开阔。中外历史上那些卓有成就的文艺理论家,正是凭依开阔的文化视野,自多角度切入,创建了有价值的文艺学学说的。中国古代的沈约,由语言形式角度切入,创建了诗歌声律论;严羽则是借鉴佛学智慧,创建了禅学诗论;李贺、袁宏道等人则从反道统的人性哲学出发,提出了“童心说”、“性灵说”等。以本世纪的西方文论来看,由特定的哲学观切入,萨特创建了存在主义文论,茵格尔顿等人创建了现象学文论,巴尔特、格雷马斯等人创建了结构主义文论等;由语言学切入,形成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由精神病理学切入,形成了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文论;由人类文化学切入,形成了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等等。显然,正是缘其切人角度的不同,使得这些学者能够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各各不同的文沦见解,丰富和推进了人类对文艺现象及其活动规律的认识。相比之下,反观本世纪的中国文论,我们不能不痛切地感到,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文艺理论家们,日渐丧失了“五四”时代那样一种无所顾忌的文化眼光,而越来越集中统~到了革命的、政沽的,甚至是阶级斗争的现域之内。这般视野拘谨的学术人格,又怎么可能有独特的思想创造?
三、学术人格的病变
至于建国以后,由于文坛上不时出现的政治性批判浪潮,由于随时担心被指责为唯心主义,被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中国的文艺学家、美学家们表现出来的,已不仅仅是独立的学术人格的缺失,而是更为严重的人格病变。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类情况。
第一类:小心翼翼,步趋时势
活跃于新中国文坛上的许多理论家,虽然自信忠诚于革命事业,实际上没有了独立思考。大多理论文章,或小心翼翼地阐释马列文论的某个观点,或设法为某个特定时期的文艺政策、为某位领导人的文艺主张寻找成立的根据。即使探讨某一学术性课题,中国文论家们在著书立说时,也往往广征博引政治方面没什么把柄的前人、名人或革俞领袖人物的言论做挡箭牌,以加强自身的保险系数。在这样的研究中,理论家们付出的只能是缺乏文化增值的重复性、无效性劳动,而很少基于学术人格的独立创造。更有不少人,则习惯于从政治需要出发.响应号召,步趋时势,以批判别人代替了自己的理论思考。而这些人,到头来,大多往往又遭到别人的批判。有人忆及;后来被打成右派的巴人。当年在领导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反胡风运动时,在批判被视为“胡风分子”的聂绀弩时,曾经“格外起劲,大会上动辄声色俱厉地说’反革命分子聂绀弩’如何如何”(注:舒芜《回归“五四”后序》,《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第184页。);陈涌、冯雪峰、丁玲等人后来均饱经了磨难,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中国第一个遭到批判、并导致了终生厄运的萧也牧,正是由陈涌、冯雪峰、丁玲等人首先发起批判的。如冯雪峰曾这样严词指责萧也牧“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认为作者“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注:《雪峰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卷 第468—470页。)。不能否认这些“批评家”当时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真诚,但正是在这真诚中,隐含的正是可怕的学术人格的沦落。
第二类:言不由衷,心态错乱
最常见的情况是:一,违心地宣扬阐释难以自圆其说的文艺主张。加建国后一直主持党的文艺领导工作的周扬,虽曾不断强调作家必须从党性、政治性出发从事创作、并直接组织领导了文艺界的一次次批判运动,但他也曾私下里多次对张光年哀叹:“我们是在夹缝中斗争啊!”(注:参见李辉文集第四卷《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 1998年版第281页。)在政治形势松动的情况下,他也曾表示对以行政命令领导文艺方式的不满,认为正是这种方式“助长了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注: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文艺报》1953年第19期。),甚至排“说到领导,现在当然是党在领导,党有没有领导得好?我看没有领导得好,真正的领导一定要是内行”(注:《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508页。)。从这些言论中不难报知:周扬在公开场合的许多言论,至少与内心世界并不完全一致。建国之初,茅盾在论述文艺为政治服务时曾讲:“如何能使一篇作品完成政治任务而又有高度的艺术性,这是所有的写作者注意追求的问题。如果追求封了,就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如果两者不能得兼,那么,与其牺牲了政治任务,毋宁在艺术性上差一些。当然,严格而言,这句话是不太科学的……”(注:茅盾《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文艺报》第一 卷第9期第8页。)明知不科学,”却又要强调,可见茅盾的心态亦曾陷入怎样的错乱。二是违心地批判别人。在建国后不断兴起的文艺批判浪潮中,积极投身其中的人,虽然绝大多数不明真相,但也确有心里明白是非,只是为了自保,为了表现政治上的进步,而违心服从老。巴金在晚年的《随想录》中即曾担承:在批右派时,就绝不是出于自愿,之所以违心行事,是因政治上的幼稚与自私动机,“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注:巴金《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28页。)蓝翎先生在回忆录《龙卷风》中也曾痛心仟悔:只是为了显示自己进步,即曾歪曲事实,在《文艺报》上发表文审批判自己实际上内心敬佩的老师目荧;后又与李希凡一起,多次奉命写作,违心地批判过白己的老师冯沅君、领受过教益的冯雪峰等人。“五四”时代,鲁迅曾愤怒地揭露中国人是麻木的“看客”,可悲的是,经过多少年的革命之后,活跃于新中国文坛上的一些批评家,已经不止是“看客”了。三是违心地进行自我批判。在50年代,凡来自国统区或海外归来的作家、学者,很少有人不曾有过这样一番脱胎换骨的自责过程。至“反右”及“文革”期间,
迫于压力而违心地进行自我批判,就更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现象了。
第五类:见风使舵,卖友求荣
贾植芳先生在《狱里狱外》中写道:当他因胡风一案牵连被捕受审时,审讯员曾拿出厚厚的三个日记本,“逐条念了几段,包括年、月、日、时和谈话内容。我那时还年轻,他念过几段后,我都会马上对号入座地查找到打小报告的人的姓名。至于他们所记的我的谈话内容,有的是我说的,有的是她们添油加醋地写上的。原来,在我周围有不少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大小‘知识分子’!”(注:贾植芳《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版第45、99页。)贾先生这里写出的只不过是“背后栽赃”的情况,而在我们的历史上,冠冕堂皇地见风使舵,卖友求荣,落井下石者,不是也大有人在吗?当某人被视为有问题,遭到批判时,不是马上就会有人(包括原来的朋友)“反戈一击”,将私人信件、个别场合的谈话等等,当做证据,公之于众,致使被批判者成为“铁证如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吗?而这些人,虽然可以找出诸种理由安慰自己的良心,但在心灵的角落里,又总隐藏着抬高自己、保全自己之类的个人目的,因此又往往要伴随着来自良知的谴责。这种心理病变,显然更不仅仅是一般的学术人格问题了。
四、学术人格的重建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目前的学术生态无疑已大为改观,已为学术人格的建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在文艺学领域,关于学术人格与学术创造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至今仍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从近些年的情况看,许多人的注意力似乎主要集中于这样两个方面:结合自己的实际,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注重民族传统,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研究文艺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将联系实际作为研究文艺学问题的立足点,这当然是必须进一步予以强调的。但如果注重的仅仅是上述具体的文艺学研究方略,而漠视学术人格的建立,将仍然难以真正促进文艺学的发展。
文艺学;就其功能与特性而言,除了与文艺实践有关之外,更为重要的当是人类精神生命空间的不断开拓,是从独立的学术人格出发进行的多方面精神探索。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在文艺学方面,同样创造过历史的辉煌。本世纪中国文艺学局面的困窘,也显然不是由于我们的文艺学家、美学家们缺少才华与勤奋,而主要是因理论空间的日趋缩小、文化资源的不断遭到排斥,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人格的退化与病变所致。相比而言,随着时代的进步,前两者还是容易改变的,而与深层次的思维模式、心理积淀相关的学术人格 的矫正,则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故而在已经过了20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的理论空间虽已相当阔大,文化资源也越来越丰富,而学术人格却仍未走出退化与病变的阴影。因此,为了促进中国文艺学的繁荣与发展,自觉地重建学术人格,便不能不成为当前中国文艺理论家们的首要任务。
就目前情况来看,重建学术人格,需要中国的文艺学家、美学家们,进一步认清文艺学本身的价值所在,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社会职能。近些年来、随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意识形态问题的趋于淡化,文学艺术已极大程度地挣脱了政治的束缚,正在回归自身;随着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其它许多重要学科的迅速崛起,大众的文化兴趣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文艺问题自然也就不可能像原来那样易于惹人视听了。可以想见,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力图仅凭一篇文艺理论文章,使可造成大轰大嗡的声势,便会在一个10多亿人口的国度里掀起波澜的情况,已几乎是不可能了。这种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无疑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饱受压抑的中国人孜孜以求、渴望已久的。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从政治出发、从中心地位出发的思维定势,在这新的时代氛围中,有不少文艺理论家反而感到无所适从了。过去,尽管有着诸多禁忌。但有时仅凭某种胆识或机遇,即可提出某个引起公众关注的话题,而今,在禁忌逐渐消除的情况下,胆识与机遇已不再那么重要了,至于其它富有开创性的艺术命题,也不是轻易就可提出的。于是,许多人灰心丧气了,迷茫彷徨了。实际上,这又正是学术人格匮乏的表现。
文艺学,就其根本特性而言,本来就是人类社会文化与精神生活的一个普通分支,主要是关于文学艺术自身发展规律、价值构成规律的探讨,以及人类精神生命空间的开拓,即既不该被视为祸患之源,也很难凭此即可安邦定国。历史事实正是如此,不论古今中外;那些卓有贡献的文艺学学说;大多并非显赫于一时,也很少直接产生过多大的政治效应。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等,似乎并不曾在历史上造成过什么轰动,也不曾掀起过什么政治波澜。但却正最这些著作,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艺学的重要支柱。在西方历史上。真正建立了重要文艺学、美学体系的。也多是不曾置身于历史舞台中心的康德、黑格尔、克罗齐、泰纳、弗莱这样的学者。因此,在当今的中国文坛上,一切真正有志于文艺事业的理论家,应该认清时势,尽快地走出迷茫,恢复真正的学术心态,在已经进步了的社会文化格局中,找到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
其次,要进一步打破二元对立与一统化的思维指向。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思维中,一直盛行着中与西、新与旧、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之类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对于某种理论主张,往往不是深入分析其中的真理与谬误,而是习惯于从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出发,简单判定其是非。比如在“五四”时代,支持白话文学就是进步的,否则就是反动的;建国之后,只有现实主义理论才是正确的,非现实主义则是离经叛道的,等等。至今,在我们的文坛上,这种思维方式仍在盛行,尤其表现在对西方“后现代”文艺思潮的评价方面。“后现代”文艺思潮本来是复杂的。但在一些推崇者看来,似乎只有唯”后”是从,才够得上观念变革,才够得上思想解放,否则就是落后,就是保守,这实质上仍是排他性的一统化思维方式的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只能助长中国当代文坛盲目的追风逐浪、追新猎奇之风。又正是这种风气,仍在严重地妨碍着中国文艺理论家独立人格的确立。
为了重建学术人格,在学术生态方面,也还要采取措施,进一步改革文化管理体制,鼓励和推崇个人著述精神。目前,在我国,虽然一统化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了,但在文化科研领域,似乎仍在固守着多年形成的计划管理模式。例如,每年一度,都要由主管部门,层层下达科研规划,要求科研人员申报立项。在申报时,又常常要求以课题组的形式。这种计划性与组织形式,对于某些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的自然科学及一些大规模的史学、社会学课题,或许是必耍的。而对于哲学、文艺学之类更具思辨性的理论学科,就值得研究了。且不论这些预定选题的科学性如何,仅从学术规律来看,思辨性成果往往需要一种更具个人创造性的精神劳动,而这样的精神劳动,怎能被动地服从于他人的规划?又如何以课题组的形式进行机械分工?古今中外,那些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学术著作,又有几本是这样多人合作的产物?这样的计划管理体制,显然是不利于形成独立学术人格的;这样的著述形式,怕也是很难产生刘勰的《文心雕龙》、黑格尔的《美学》这样一流的学术成果的。
标签:文艺论文; 胡风论文; 文艺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独立人格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文艺报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