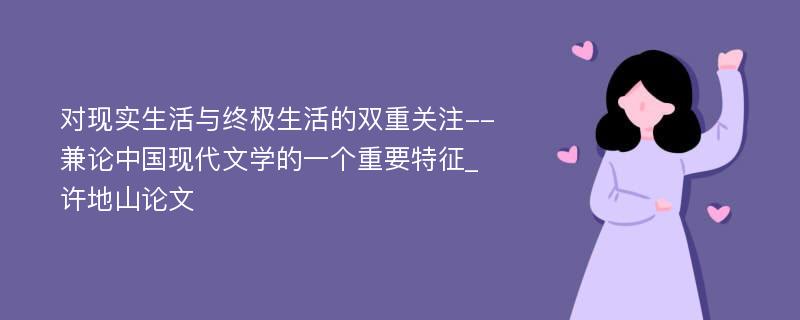
对现实人生与终极人生的双重关注——试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生论文,一个重要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中国现代作家在体验和反映社会人生的过程中,在接受宗教文化思想影响的过程中,既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壤,抓住实际人生的焦点和热点,同时又把眼光投向人生奥秘的阔远之处,积极探求终极人生的无限蕴含,对现实人生的热情探寻始终伴随着对人生根本价值的深沉思考,现实与超现实,急切的时代责任感与悠深的历史使命感,这双重的关注与双重的情怀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种特有的情致和意蕴。
当整整一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人们有理由用总结性的眼光来回顾本世纪从物质到精神在一切方面所发生的重要现象。应该说,宗教文化的不断兴盛和人类社会对宗教文化不断的重新认知正在被这种眼光所深切关注。尤其是人们在对西方文化进行整体性反思的过程中,越来越真切地感到了信仰危机的深重:相信上帝或许是重要的,但坚信实际生活本身似乎更为重要。英国作家康拉德叙述过一个颇富戏剧性的故事:曾有这样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其父告诫他决不要轻信实际生活,且要蔑视一切现实事物。而生活最终把他抛到一个他所完全不能适应的现实境地,他的生命也就在空怀着对上帝的无限信仰之中悲剧性地泯灭了。在行将离开现世之前,他翻然醒悟地对一位年轻朋友说:“多么不幸啊!一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心灵没有学会希望和爱,没有学会相信生活。”这个故事在西方具有相当广泛的反省意味,康拉德警示人们,只有具备对神圣信念和实际生活双重关注的目光,才不至于发生那种由于轻视生活而被生活所抛弃、只懂得信仰而最终被信仰所毁灭的悲剧。这种意识得到普遍加强的结果,是人们把对21世纪的期待更多地投向东方,更加注重探讨东方文化的魅力。
的确,在以基督教精神为主要支点的西方文化里,对上帝的信仰就是人们生活的全部和根本,上帝与人们融为一体,人们的个体存在只有体现在上帝的存在之中才有意义。这个支点影响和决定了整个西方文化的特质。而与此不同,甚至相反,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却体现出一种普遍、顽强的对现实人生的热切关注和执著追求。注重实际生活,注重今生现世,注重人自身的命运,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宗教精神的基本命脉。真正成为传统的东西往往是极富生命力的。因此,当“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发生之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劲冲击,虽然新文化的倡导者和新文学的作家们尽情地吸取了西方文化的素养,包括吸取了大量基督教文化的精髓,上帝及爱的哲学在中国文化面前也前所未有地展现了它的光彩并深深地影响了相当一批正在思考中国文化的前途与民族命运的思想家的思路,极大地感召了无数时代青年的心,然而,正是在外来文化的荡涤和比照之下,注重实际人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伴随着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也同时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加强,只是在传统文化思想机制中对信仰、理想和终极人生的关注被激活了、升华了。因而在反映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学创作中,鲜明地透露出对现实人生与终极人生双重关注的深厚目光。既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壤,紧紧抓住实际人生的热点和焦点,同时又把艺术的视野投向人生奥秘的阔远之处,积极探求终极人生的无限意蕴,这种双重的关注是在更高层次上对一个作家,甚至是对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学的衡量和要求。而在新文学作家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双重关注又在更深的层次上牵动着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的某种深刻的相互影响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特征的重要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和意义上,我们感到,对现实人生与终极人生的双重关注其实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
中国现代文化及现代文学的发生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学的根本性变革与改新,同时还承受着外来文化及文学的冲击和渗透。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使中国现代作家得以在更为开阔的文化空间里思考人生与社会问题。一方面以基督教精神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体系,以其特有的人生价值观念,有力地影响了中国现代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角度,开启了他们新的思维空间;另一方面,此时佛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复兴,也促进现代作家对传统宗教文化产生新的反思和兴趣。许多现代作家,包括一些“足踏大地”、密切关注现实人生的作家,也都不同程度地把思绪拉向悠远、超然的境地,显示出对终极人生的认真探寻和积极关注。
1922年,文学研究会的重要作家朱自清在其著名长诗《毁灭》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深深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然而差不多与此同时,朱自清在思想上却明显受到佛教禅宗的某些影响,他在理智地清除“颓废主义”的过程中,又形成了思想上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刹那主义”。朱自清从中学至大学时代都曾着迷于佛经佛学,他所奉行的“刹那主义”也的确体现出了对佛教禅宗的某种领悟和感发。但朱自清的“刹那主义”深深注入了他自己对人生和世界的坚实理解,与佛教禅宗倡扬的四大皆空、超然出世等观念有着本质的差异。在主张不应沉醉于昨日或明日的虚幻光景,不应徒求佛法佛理,力求把握“今日”的“一刹那”并于此中获得人生真谛这一点上,朱自清的“刹那主义”与佛教禅宗是相通的;不同的是,佛教禅宗的“刹那观”特指对刹那间生活的体悟进入无人无我、无善无恶、无生无灭的“空”的境界,最终归为虚无,而朱自清的“刹那主义”强调的则是透过刹那间生活的感受进而更加真切地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人生的契机以及生命进程的积极发展,最终指向实有。因此,朱自清在《毁灭》中所表露的足踏实地、忠于现实生活的态度,与其“刹那主义”的思想在本质上并不矛盾,而是内在统一的。《毁灭》并不意味着朱自清对“刹那主义”的告别,而是一种有机的升腾。作为现实主义人生派的重要作家,朱自清虽然积极吸取了佛教禅宗的某些思想素养,但这种吸取有一个基点,即更积极地执著于现实人生,执著于人的命运发展,而决不是对虚幻空灵境界的追求。朱自清溶解宗教意识于现实人生的这种基本态度,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具有相当代表性的。
崭露风采于近、现代之交的苏曼殊,是新文学史上较早受到宗教文化思想的影响并以此深切体现在文学创作之中的诗人和作家,这一点近年来已为研究者们所注重。尤其是苏曼殊那些充满爱情悲剧的作品与作家本人极富传奇色彩的身世之间的关系,更是引发了人们独特的兴味。然而我认为,苏曼殊及其创作更为重要的独特意义首先在于:他是一个倾心沉迷宗教情结却又始终无法摆脱现实困扰的典型。苏氏一生之命运差不多都是在出家、还俗、再出家、再还俗的不断轮回中旋转的,可是尽管他从12岁就削发披袈,对佛教文化深有研究和修养,而事实上他又从来未以从一而终的态度来对待宗教佛门。对佛门的皈依在苏曼殊来说从来都是暂时的,甚至带有相当的随意性。究其根本,并非他缺乏对宗教佛门的信仰和虔诚,而是现实生活的多重苦恼以更强的诱惑力把他屡屡从佛门拉回现世。他选择信奉的是大乘佛教,并独有钟情于禅宗南派的“曹洞宗”,因为此宗不仅注重关切民间疾苦,而且主张无拘无束,一蹴成佛,这既符合苏曼殊随时走进佛门的愿望,又顺应了他随时走出佛门的心境。因此我们所看到的苏曼殊,常常为恶浊污秽的社会所激愤,顿然斩断世情,走进深山古刹;可当真来到佛庙静修,却又每每难以忘怀人间风烟进入空灵无我的境界,反而更为现实人生的种种磨难和烦恼牵肠挂肚。对民主新思潮的热情追求,对东西文化的广为吸收,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依托宗教信仰来抚平自己那颗苦难破碎的心,不可能在幽静的佛门之内得到真正的解脱。他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踏入佛门之日亦即忧虑人生现世之时。“天生成佛我何能,幽梦无凭恨不胜。”[①a]“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②a]苏氏的这些诗句正是自己于佛门、于现世痛苦不堪,矛盾重重的心态的写照。苏氏在佛门与现世之间无数次地进出往来,甚至常常“后脚还扎在上海的女闾,前脚却已踏进了杭州的寺庙”[③a],这简直构成了一个奇特的景观,而这一情景决不只是苏曼殊个人命运的遭遇和生活道路的选择,它在更为深广的意义上体现着相当一部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特心态:信仰与现实的不可分割,超然与凡尘的密切融合。
与苏曼殊的奇特人生道路有关,在他的那些自传色彩颇为浓厚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两组深刻的矛盾,其一是爱欲与佛法之间的矛盾:苏氏小说的主人公(如《断鸿零雁记》里很大程度上投入作家身影的三郎)多是历尽人间辛酸凄凉,屡遭世人冷脸白眼,尤其得不到常人家庭的亲情温暖,所以他们特别渴求得到异性的爱抚和温存。然而虚空幻灭,遗恨终天是为根本结局。苏曼殊刻意安排的这种悲苦归宿,使其笔下的主人公往往很自然地选择皈依佛门之路。由宣泄自身命运不平进而反映人间社会的苦难,从这一点出发,苏曼殊的作品与佛学首倡之“苦谛”在精神观念上找到了深深的契合之处。然而无论苏曼殊本人还是其作品的主人公,都远未真正进入佛教“空净寂灭”、根除“我执”的境界,而佛教清规严申戒除的爱欲和情欲,恰恰是苏曼殊及其作品主人公所深深迷恋、难以自拔的,甚至苏氏笔下的那些女性如《绛纱记》中的雪梅、《断鸿零雁记》中的静子等,也都以时代新潮的昂奋,大胆表现出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和坚贞不渝,任其“沧海枯流、顽石尘化”,而“粉身碎骨”、“妾爱不移”、“在所不惜”。显见苏曼殊笔下人物之所以遁入佛门,并非以爱欲爱情为恶,而实以不能得到爱欲爱情为苦。至于苏氏本人,他自己说得明明白白:“我是由于感情上的困境摆脱不了才出家的,虽然出了家,却仍然感到愁闷。”[①b]皈依佛门却并不能得到解脱,反而更加难以忘情忘世,爱欲无法由佛理取代,佛法也丝毫不能减轻爱情的煎熬,这一对实难化解的矛盾深深植根在苏曼殊及其作品人物的心中。其二是情感与理智之间的矛盾:悲凉孤独的私生子身世一直重压在苏曼殊的心头,使他一生都背负着一种极为沉重的“原罪感”。既自恃才高志大,又痛感于人于世甚至于己都是多余的,这种带有点病态的情感驱使他心绪无常,行迹不定,时而狷狂不羁,时而悲鸣绝伦。苏氏一生之浪漫洒脱,创作之浓情厚意都与此紧相关联。但这并不是说苏曼殊对自己及社会缺乏理智的认识,事实上他对自己的身世,对时弊世道都有着冷静清楚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愈是清醒,其自身的“原罪感”愈加深重,对不平世道的愤激也愈加剧烈,进而愈加导致了他的痛苦与绝望。对于苏曼殊来说,皈依佛门既升华了他的理智与慧识,同时却又加剧了他的感情苦恼,使他既不能用宽怀悠远的目光看待终极来世,又无法抛开急近功利、游身当今现世的迫切欲念。因此,在这种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交织中,苏氏本人及作品人物命运结局的悲剧性是无可避免的。也正是在这双重悲剧中,我们更能体悟到苏氏及其创作与宗教文化相互契合的深刻内涵。
苏曼殊35岁的生命是短暂的,其作品也是屈指可数的,加上他生活的时代尚未跨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这些局限多少影响了苏氏及其艺术生命的影响力。然而,作为与宗教文化结缘最早,关系最深的中国近现代作家的代表,苏曼殊及其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含义的模式:悲凉惨痛的身世、动荡不宁的社会以及孤独清苦的心境驱使他信仰佛学、皈依佛门;但佛门的高墙没能隔绝他与现世和现实人生相通的心,佛学经义未能使他超脱悠然,相反,佛教的影响更加深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更强化了他对人生苦难的体验,也更坚定了他对现实人生的执著态度。这个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甚为确切地揭示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基本关系,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其价值是苏曼殊及其创作本身难以相比的。
二
作为中国新文学最初一批现实主义人生派的重要作家,同时又与佛教、基督教和道教等诸种宗教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并发生深刻的关系,许地山是一个少有的特例。
与苏曼殊的创作着重从宗教情结宗教意识来反观现实人生不同,许地山及其创作的独特性和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其坚实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上。他的作品虽然也充溢着宗教情结和宗教氛围,但却始终是以逼视现实人生的态度进而深究人生的终极意义的。
不过,无论许地山对基督教教义究竟采取何种态度,也无论他到底是出于何种原故与基督教结缘[①c]。有一点是肯定的:许地山对基督教文化的透彻了解和卓有成就的研究不可能不对其实际人生及思想发展产生某种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不可能不渗透到他的文学创作之中,尽管他并不一定是个真正信仰基督教的人。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许地山对道教文化也进行过深入系统地研究和探讨,所撰《道教史》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道教文化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和见解,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都相当丰富地体现在许地山的文学创作里。当然,人们普遍注意到许地山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和深刻。在许地山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文学创作之中,佛教文化思想明显占有更为突出的位置,他对佛教文化也有一种更为潜在、更为自觉的兴趣和意识。无论如何,许地山与宗教文化总体上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已成为他区别于其他新文学作家的一个特殊标志,“在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像许地山这样对宗教发生了不止是文学上,而且是学术上的浓厚兴趣,几乎可以说,许地山思想及创作的任何问题,我们都能从宗教中找到解释。”[②c]虽然此说过于强调了宗教文化于许地山的特殊意义,但确实在许地山整个的思想体系和文学创作中,从人物命运、叙述结构到语境氛围,都充满了异常浓郁的宗教情结和宗教意念。尽管许地山的艺术思考也是从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切入的,但是与文学研究会人生派诸作家以至当时绝大多数现实主义作家明显不同,许地山的艺术眼光更多地表现出对终极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特殊关注,而决不仅仅满足于对一般社会现实和人生问题的描写与反映。即使其后期被人们誉之为现实主义力作的《春桃》,看似减弱了其前期作品的某些玄妙虚幻色彩,增强了对普通人物现实遭遇的细腻刻画,但实际上这部作品真正的力度,主要并不在于对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实际命运的反映有所贴近、同情有所增加,而依然在于作者对人之命运的总体思考。命运的偶然性、突发性及其不可捉摸和对命运的迷恋、信念与执著追求,依然是《春桃》真正富有感发力和生命力的所在。那种认为许地山后期创作比前期更富有现实性,更接近社会本质的看法其实是有些偏颇的。我认为许地山对人之命运的双重关注是一以贯之的,而且,人的命运究竟由谁主宰?人生的价值到底体现在何处?什么是人的根本幸福与苦难?这些直迫精神深层的思索一再升腾为许地山作品的核心主题。因此,在许地山的作品中虽然未曾离开日常琐细的现实人生题材,但却总是布满了一种浓厚的说教气氛,借人物之口说教,通过情节说教,以至作者直接站出来说教,那种对人生义理的执著宣扬强烈地透露出作者探索命运之道的痴迷情态;同时他的作品又带有一种玄秘神奇的色彩,故事情节扑朔迷离,人物性格又常常伴随某种程度的偏执与变态,宗教文化的地域背景更加重了作品的虚幻性,这也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许地山其作品却显现出浓重浪漫情调的重要原因,所以有人认为仅仅用现实主义方法和风格的范畴实难揭示许氏创作之根本,因而用“灵异”二字来重新概括许氏创作的总体特征,来指认“许地山同别人截然划清之处的地方。”[③c]
然而“灵异”就是许地山创作的真正本质所在?我认为,作为一种创作的表征和特色,灵透奇异、玄妙空幻确属许地山独有的艺术个性,但作为本质,它还远未体现出许氏创作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在这里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无论是基督教、道教,还是佛教,也不管它们是作为文化修养,还是哲学信仰,对许地山来说首先有一个接受其影响的根本内核,这就是它们与许地山所始终思考的民族命运的关系,“许地山认为,个人的自我修养是拯救民族的‘根本’,这完全符合‘基督教将有助于新伦理道德对民族的拯救’的燕京哲学。”[①d]从许地山的思想发展和文学道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对宗教文化的独有钟情和深深迷恋,并不是或主要不是基于个人命运的悲哀,尽管许氏早年家境窘困,生活流离漂泊,加上原配爱妻的早逝等等,这些也的确强化着他的“人生无常,生本不乐”的宗教意识,但许地山由此生发开来的对宗教文化的兴趣却并没有归向拯救自己的灵魂和命运,时代社会的发展使他有条件把对个人某些不幸的哀叹更明确地升华为对整个人类与社会不幸的沉痛思考,并以宗教文化的某些方式来积极探寻拯救民族与世道的明途良方,这才是许地山走入宗教文化的基本动因。尤其重要的是,“五四”时期的中国,不管激荡着多么复杂的思想交锋,不管涌进了多少各式各样的理论学说,所有这些都基于一个根本的事实:即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国人的现实命运迫切需要得到改新和重造。这一点在当时任何一个有识的知识分子心中都是明白无误的,无论他受到了何种文化思想和哲学理论的影响,忧患意识和进取意识自然地变为时代意识的主潮和标志。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使许地山对宗教文化的选择和投入不可能是盲然的,而分明是以关注现实人生,改造现实社会为出发点和目标的,许地山对宗教文化的极大兴趣,对宗教的精神皈依,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救世意识和一种宽泛的对社会现实的忧患意识,而决不是消沉的、狭隘的个人精神寄托。他在散文《还债》中所精心描写的那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自身却分外清醒的“还债者”,正是这种精神意识的高度象征。与此同时,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还提供了新的条件,使许地山能用冷静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去探究宗教文化的精髓要义,而决不是沉迷于狂热愚昧的宗教情绪之中。因此,一方面是一个热忱的宗教崇拜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现实主义人生派文学的热切倡导者;一方面在创作中表现出大量的宗教情结和神奇浪漫的情调,另一方面又始终投以冷峻深沉的现实主义目光。这是许地山超越苏曼殊的地方,也是在更为深广的层面显现出宗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本质关联的地方。第二,正因为时代所赋予的开放和现实的心态,许地山不仅没有沉醉在自己所选择所投入的宗教情结之中,相反他“渴望更多的是个人的自由和宗教的灵活性。”[②d]这从他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得更为透彻。许地山的作品的确与众不同地、大量地叙述了那些悲哀的人生和屈辱的命运,作品主人公基本上都沉浸在深深的苦难意识之中,并且作品突出渲染了对这种悲苦命运的容忍和认同,“生本不乐”的宗教信念在许地山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和揭示。然而许地山决没有被自己所渲染的宗教气氛所淹没,在认同命运苦难的同时他更强调了与不平命运的决然抗争:《命命鸟》里男女主人公双双从容不迫的死,所换取的决不仅仅是对爱的殉情,而更是对得不到应有爱情的最后反抗,也是对整个不平世道的绝情控诉;《商人妇》里的惜官,虽然对负心的丈夫一再表示了宽大为怀,不计前嫌的胸襟,但作者却又不动声色地为损人者安排了一个极不光彩的狼狈结局,这本身就是愤然有力的道德评判和社会谴责。而且尽管惜官相信丈夫“不忍做”那丧天害理的事,也相信他“终有一天会悔悟过来”,但她毕竟还是发出了“我要知道卖我的到底是谁”这样强烈不平的怒号,她的宽容显然是有限度的,她的超脱也显然是不彻底的;《缀网劳蛛》里再三受到丈夫无端猜疑、凌辱和迫害的尚洁,看似心静如水,随遇而安:“我象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然而整个作品却又自始至终张扬着尚洁那种内在的不屈服命运、毅然果决的刚烈性格:“我虽不信定命的说法,然而事情怎样来,我就怎样对付”,“危险不是顾虑所能闪避的。”“我不管人家怎样批评我,也不管他怎样疑惑我,我只求自己无愧,对得住天上的星辰和地下的蝼蚁便了。”显然,在这位“无论什么事情上头都用一种宗教的精神去安排”的女主人公身上,我们看到的决不只是对命运单纯的顺从和漠然,而更多的是对命运的泰然处之。与其说她是象蜘蛛那样无可奈何地不断修补命运之网,不如说她是顺应命运、把握命运、推动命运,积极地演进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有网就会遭受侵袭,就会损破,只要“向着网的破裂处,一步一步、慢慢补缀”就是了,“是蜘蛛,不得不如此!”是人生亦不得不如此!这种不屈从命运的进取态度才是“蛛网哲学”的根本所在。佛教的生本不乐,基督教的苦难意识,道教的顺应自然,这些使许地山的创作既对人生的无限意义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体悟,同时又以此反观和深省现世人生的平实价值,同样达到了相当程度的慧识。
三
应该看到,象苏曼殊这样数度皈依佛门、许地山这样被“诸教缠身”的中国近现代作家毕竟是不多的,而更多的作家则是在人生及创作的某一阶段、某一方面受到某种宗教文化思想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仅是同样深刻的,而且甚至对某个作家的思想及艺术特质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今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最后一位“五四老人”冰心,其文学创作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然而总观其创作的根本主题却并不复杂,甚至颇为单调,人们往往用一个“爱”字来概括其作品的基调和特质。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现当代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人象冰心那样对“爱的哲学”倾注了如此巨大以至毕生的热情和智慧。但勿庸讳言,这“爱的哲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与冰心所追寻的基督教精神紧紧相连的。一个作家执著地表现和追求某种东西,原因往往不外有二:一是过多地接触到它,感受到它,领悟到它;相反,二是很少感触到它,或者根本就没有得到过它。冰心之于爱显然属于第一种情形。她的人生之旅自起步之初就“一直生活在充满爱的环境中,始终拥有最丰足的爱”,家庭亲情、师恩友谊等等,“她拥有的爱可谓最多、最丰富、最完满。而她也付出了最宽厚、最博大的爱。”[①e]冰心整个生命的价值就是不断地接受与奉献着爱,诚如她自己所言:“有了爱,便有了一切。”可见,冰心生命之源的爱的哲学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原本就有一种天然的默契。值得注意的是,冰心对基督教思想的接受本来或许是不经意的,偶然的,但她对基督教思想特别是爱的精神的追求却是自觉的,必然的。这是因为冰心的爱的意志并非来自纯粹的理念,而是深深植根于其真切的生命体验中的。因此,冰心虽然是以“问题小说”名震文坛的,但她整个的文学创作始终没有脱离过两个内在的本质点:一是对爱的竭力倡扬,二是对人生根本价值的不懈追求。而这两者往往又是相互交合的。冰心在创作初期曾写过一组宗教情绪十分浓郁的诗歌,陆续发表在1920年8月创刊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会刊《生命》上。在现代文学史上最初出现的这些宗教诗里,冰心以她天真、纯洁然而异常执著的声音,热忱地赞美上帝,赞美她所认为的充满宇宙和人类的无限的爱。在一首叫做《清晨》的诗里她动情地欢唱:“晓光破了,/海关上光明了。/我的心思,小鸟般乘风高举,/飞遍了天边,到了海极,/天边,海极,都充满着你的爱。/上帝啊!你的爱随处接着我,/你的左手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的心思,小鸟般乘风高举,/乘风高举,终离不了你无穷的慈爱,/啊们(!)”
冰心的确感受到了太多的爱,爱的哲学已然成为她整个人生价值观念的根本支柱,基督教对人类之爱的虔诚与执著又助燃着她的生命之火。毫无疑问,这种对无处不在的爱的感受以及对它的赞美,对冰心,特别是对当时充满理想、跃动着青春活力的冰心来说,完全是真实的,真诚的。但对于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现实社会,对当时更多的苦不堪言的芸芸众生来说,它就显出了相当的距离,就显得过于空泛、虚幻和理想化了。准确地说,是冰心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爱,而实际上爱决不是无处不在的。其实冰心本人也并非完全沉醉在爱的仙境中,她清醒地意识到社会普遍的不幸、人生广泛的悲哀以及生命极度的脆弱。所以她也苦苦思索着人生的根本价值以及超越苦难现实的奥秘。“生命,是什么呢?”这个终极人生的根本问题一直翻腾在她的心里:“是昙花,/是朝露,/是云彩;/一刹那顷出现了,/一刹那顷吹散了。/上帝啊:你创造世人,/为何使他这般虚幻?/昨天——过去了,/今天——依然?/明天——谁能知道!”(《生命》)而对人生的短暂、惶惑,冰心又发出了沉重的概叹:“这样的人生,/有什么趣味?/纵然抱着极大的愿力,/又有什么用处?/又有什么结果?/到头来也不过归于虚空,/不但我是虚空,/万物也是虚空。”(《“无限之生”的界线》)她还不断扪心自问,苦求人生及世界的本义:“我的心啊!/你昨天告诉我,/世界是欢乐的;/今天又告诉我,/世界是失望的;/明天的言语,/又是什么?/教我如何相信你!”(《繁星·一二三》)
客观地说,人生的终极问题在冰心那里并没有找到准确、理想的答案,但她却有着坚实无比的信念,这就是爱!用爱去溶化一切、消解一切。她的小说《超人》在这方面具有相当深刻的代表性:主人公何彬怀揣一颗冰冷的绝望于世的心,“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凡带有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他对人生根本意义思考的结论是:“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得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然而这样一个心如死灰的人,最终却受到了爱的感化,确切地说,是作者冰心以母爱和童心消解了何彬与世人的一切怨恨,溶化了他那颗绝情绝义的心,重新点燃了他充满爱意的生命之火,并通过何彬之口发出了对整个人类共同之爱的庄严呼吁:“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我认为,《超人》对冰心的思想和创作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它强烈地表现出对终极人生的迷茫、困惑以及对爱的哲学的坚信不移。那么是不是说冰心及其创作仅仅在人生终极价值方面显示了其独特意义?显然不是。事实上如同冰心始终关注终极人生的问题一样,她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对现实人生问题的积极思考。从最初发表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等作品,跨越半个多世纪,直到80年代创作的《万般皆上品……》、《落价》、《干涉》等作品,家庭关系、妇女地位、婚姻恋爱、尊重知识、民主自由等等现实人生的一系列焦点和热点问题,一直是冰心创作的显要主题。在充满爱与理想的心中同时也充满着沉郁悲凉的忧患意识,这是冰心及其创作特有的可贵之处。我们注意到,虽然在对社会与个人的苦难体验方面冰心或许不如许多其他作家,因而她的作品在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与揭示方面也往往缺乏相应的深度和力度;但是冰心对于人生美好信念的执著追求,对爱之精神矢志不移的开掘和推进,则是许多其他作家难以相比的。因此,仅仅用反映现实人生的深度和力度来衡量冰心的创作是难以真正发现其独特价值的。
如果说在终极人生与现实人生之间,冰心更倾注于前者,那么有意思的是,曾经加入过基督教并成为正式教徒的老舍,却把热忱和智慧更多地投向了后者。在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上深受宗教文化思想影响和启迪的作家并不少见,但象老舍这样真正当过宗教徒的作家却不多见。因此,当老舍曾经是个基督教徒这一事实被证实以后,学术界不少人基于老舍本人对这一事实很少提及并一再援引老舍夫人所言:“老舍只是崇尚基督教与人为善和救世的精神,并不拘于形迹”[①f],以此阐明这一事实对老舍似乎并不重要。也有一些学者则反复强调老舍与基督教始终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认为老舍自己绝不相信宗教[②f]。还有的学者忙于判明老舍究竟是何时何地对基督教接受与扬弃的,指出“自1922年加入基督教,到1924年去伦敦前,老舍还可算为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徒。去伦敦后,他已不再是公开的教徒。但这时随着创作的开始,基督教的影响也体现出来了。这种影响,或轻或重,直到抗战胜利后创作著作《四世同堂》时仍有所体现。这之后,便不但不再受基督教影响,而且还对基督教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有所揭露和批判。如小说《正红旗下》、话剧《神拳》等。”[③f]
在我看来,上述这些观点是略有偏颇的。我认为首先应该正视老舍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徒这一事实,并充分认识这一事实对老舍整个人生及创作道路的重要性。事实上,老舍早年的这一经历对其一生所坚持的民主和人道思想,对其一生创作所热衷于反映的平民世界,对其文学艺术风格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30年代中期即有人指出,老舍的创作风格是“幽默和宗教性融合的作品”[④f]。这是极有见地的看法。其次应该看到,宗教影响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精神形态,本来就主要不在于形式,它的影响往往是更为内在、深层和潜隐的。我认为老舍实际上从来没有简单机械地接受基督教的影响,但也从来没有简单地扬弃它。可以说,老舍温文宽厚的一生都是在阐释着宽容、博爱、同情、舍己的宗教精神,以至他最后投湖自沉、以死殉志的悲壮之举,都无不蕴含着某种无可言说的宗教情结。所以我们很难准确地说老舍到底什么时候接受了宗教,接受到了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又开始疏远它,什么时候彻底抛弃了它。再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重老舍究竟是从什么角度接受并切入宗教文化思想的?他又是以何种方式、何种目的来阐发宗教文化思想的?老舍于1922年上半年在北京正式受洗礼加入基督教,时年24岁的老舍正经历着人生的悲观期,他自说“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⑤f]无论老舍当时入教的原因多么复杂,有一点是突出的,这就是惨痛的人生经历。与冰心不同,老舍经历了从物质到精神太多的人生苦难,这使他难以用轻松虚幻的目光去寻求爱和理想。相反,他不能不用沉重凄楚的目光紧紧盯住眼前的现实人生。因此尽管老舍入教的态度是严肃的、虔诚的,但他却没有从根本上与基督教的核心思想上帝及其爱真正契合,而是对基督教舍己牺牲的精神、施善济贫的义举、救世救民的责任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入教后改名“舍予”正是这种心迹的流露。加入基督教,接受宗教文化思想的影响,在老舍来说首先是基于自己深刻痛切的生命体验,而这一点又是与冰心相同的,尽管两人所体验到的内容完全不同。老舍作品中众多的基督教徒的艺术形象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些基督教徒的“入教动机包括:没有工作,只能投靠教会;想占便宜,借洋教赚钱;闲着无事,又没有朋友,故上教会打发时间;为众人众教所弃,只有基督教把他当‘人’看,故入教;认为在基督教里,可寻得平安,故衷心服膺教义;想做好事帮助人,故参加教会活动等等。至于对教义的见解,在这群基督徒身上反映得很少。”[①g]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些教徒入教的具体动机各不相同,但根本动因只有一个:即从现实出发,改变现实的人生境况。所以他们主要都是以各自现实人生的体验去理解和接受基督教思想,而基督教教义本身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实在并非是第一位的。从这层意义上说,其实这些教徒形象的入教动机,何尝不是从一个独特的侧面解释了老舍本人的入教动机及他如何接受宗教文化思想的呢?老舍曾竭力呼唤用宗教精神来开启中国的“灵的文学”,热情赞颂但丁及其《神曲》和《新约》中的《启示录》,认为《神曲》“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的深度。”[②g]老舍深为中国文学缺乏“灵”的感染力而遗憾,因此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着力颂扬甘于“舍己”、勇于“牺牲”的品性与精神,刻意营造惩恶扬善的“地狱”与“天国”等意象,渴望用一种纯净崇高的意念,一种威严的神灵的力量,一种虔诚执著的宗教精神来注入中国文学之中,进而开启现代中国人的良心之门,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老舍所理解、所阐述的宗教精神,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宗教内涵的本义,他把宗教文化精神转化为自己深切体悟到的现代中国社会所急需的献身精神和开拓意志,而这一点一直在很深的层面上左右着老舍创作的思想基调和情感流向。在老舍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中,我们再三感受到一个问题的关键,即老舍虽然一度正式成为基督教徒,但他却始终以自己现实人生的体验,以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去消化和接受基督教的文化思想。基督教的教义经过老舍现实主义目光的过滤,不再是那种空泛的理想化的理念了,而是融化在老舍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之中,转变为一种实实在在的、世俗化和平民化的思想。老舍透过基督教精神体悟到了许多人生的崇高、悲壮、激越、悠远的境界,但他更多地把它们落到了实处。因此,老舍的作品虽然并不具有过于浓郁的宗教色彩,相反都是一些过于朴实的平民世界,但它却能够常常引发人们从宗教的精神境界去思考更为宽阔深刻的人生命题。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作家在体验和反映社会人生的过程之中,在接受宗教文化思想的过程之中,既立足于对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问题的急切追寻,又表现出了对整个人类世界终极意义的积极思考,现实与超现实,信仰与超信仰,这双重的关注和双重的情怀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特有的意蕴和情致。对这一点的深刻领悟和探求,无疑会拓展中国现代文学深层内涵和艺术境地的更大空间。
注释:
①a苏曼殊:《有怀》其二,1905年作。
②b苏曼殊:《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1909年作。
③c李蔚:《苏曼殊评传》,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①b李蔚:《苏曼殊评传》第35页。
①c有一说法认为许地山与基督教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他与教会组织的某种经济关系。参见郑炜明:《许地山的佛教文学》,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6期。
②c郭济访:《论道家思想对许地山的影响》,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1期。
③c《许地山·灵异小说·编者序》(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①d②d[美]路易斯·罗宾逊:《许地山与基督教》,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4期。
①e《冰心·温馨·小说·编者序》(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①f参见赵大年:《老舍的一家人》,载《花城》1986年4月号。
②f朝戈金:《老舍——一个叛逆的基督教徒》,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③f张静民:《老舍与基督教》,载《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3月第19卷第1期。
④f王斤殳:《舒舍予》,载《人间世》1934年第4期。
⑤f老舍:《我的创作经验》。
①g艾华:《试论老舍的宗教观》,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1989年第1期。
②g老舍:《大时代与写家》,收于《老舍研究教学资料》(上)
标签:许地山论文; 苏曼殊论文; 冰心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朱自清论文; 毁灭论文; 宗教论文; 作家论文; 佛门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