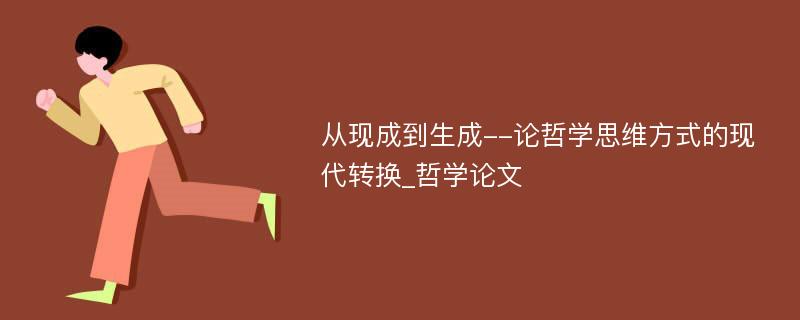
从现成到生成——论哲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方式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3)02-0001-06
一、哲学思维的两种方式
这里所说的哲学思维方式是在最一般意义上讲的,指人们思考哲学问题的基本理路。 与其他思维一样,哲学思维也是建立在一定前提之上的,这些前提在最终意义上决定着 哲学思维的基本走向。因此,从前提入手对哲学思维方式进行考察就成了一条行之有效 的道路。
从理论上看,哲学思维方式的前提可以分为两类,一为进行思维的理性,二为思维所 追问的对象。着眼于前者,根据理性之根源设定的不同,可以将哲学思维方式划分为三 种:世界论、意识论和人类学。[1]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着眼于后者 ,根据思维所追问对象性质的不同,可以将哲学思维方式划分为两种:现成论和生成论 。这是本文要做的工作。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是追根究底之学,这一特点决定了哲学所追问的对象,不是具体 的万事万物,而是万事万物之后、之上、之外的根、底,不同的根、底在最终意义上决 定了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因为特定的思维方式只能用来追问特定的对象,否则必将陷 入歧途。
从根本上看,哲学所追问的对象有且只有两种可能:一为现成的对象,一为非现成的 对象。所谓现成的,简单地讲,就是已完成的。这种已完成性,是在逻辑而非时间意义 上讲的。即从逻辑上讲,一切可(可以、可能)完成的存在都是已完成的。可完成性意味 着已“是其所是”,即可以问它“是什么”,因此我们把追问“是什么”的哲学思维方 式称为现成论的思维方式。在现成论的视野中,一切都是已完成的,都有一个本质,这 个本质决定着对象的“是其所是”。
所谓非现成的,简单地讲,就是未完成的。这一未完成同样是在逻辑而非时间意义上 讲的。即从逻辑上讲,一切不可(可以、可能)完成的存在都是未完成的。未完成性意味 着永处于生成变化的过程之中。对于这样的存在,就不能再问它“是什么”,而只能问 它“如何”、“怎样”了。我们把追问“如何”、“怎样”的思维方式,称之为生成论 的思维方式。在生成论的视野中,一切都是生成的,都处于永恒的变化过程之中,不再 存在一个预定的本质。
以哲学思维方式为标准,可以将哲学划分为两大类别:以现成论为主导思维方式的古 典哲学和以生成论为主导思维方式的现代哲学。
二、现成:古典哲学的阿基米德点
整个西方哲学开端于泰勒斯的一个命题: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提出 了始基问题。追问万物的始基,也就是追问万物之后、之外、之上的根、底,这一追问 开创了一门独特的学问——哲学。泰勒斯之后,希腊哲学家对始基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回 答,如阿那克西曼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等等。巴门尼德对此进行了 反思,认为从具体事物中寻找始基是误入歧途,因为这种探索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 而经验是不可靠的,通过它们只能得到“意见”,而不能得到“真理”。所以,不是任 何具体事物,而是它们共有的存在才是宇宙最普遍的本源。
柏拉图打破了巴门尼德铁板一块的存在,而代之以由不同理念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理 念世界。理念世界是一个思想性、概念性的世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理念是从具体事物 中“归纳”出来的“定义”,它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柏拉图将不能独立存在 的东西当作独立的东西来研究,这就使哲学步入了歧途。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第一 哲学的对象应是独立和不变的实体、第一实体。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开启了近代哲学“主体性转向”的历程,但在笛卡 尔那里,“我思”之“我”乃是一个实体,一个不同于“物质实体”的“心灵实体”, “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2]康德将笛卡尔的实体之我提升为真正意 义上的主体之我,即只能进行“规定”而其自身却不能被“规定”的先验之我。这一先 验之我——“我自体”与“物自体”共同构成了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从根本上看,“ 我自体”和“物自体”一样,都是已被设定了的,不变的现成存在。
黑格尔批判了康德哲学的形式主义,认为“真理不是一种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地 拿过来就用。”[3]“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圆圈,预悬它的终点 为目的并以它的终点为起点,而且只当它实现了并达到了它的终点它才是现实的。”[4 ]这样,运动和变化便进入了哲学,并且成了贯穿黑格尔哲学始终的灵魂。至此,古典 哲学达到了它的极致,一切可能性都实现无遗,所以,我们把黑格尔视为古典哲学的集 大成者。这同时意味着黑格尔哲学依然属于古典哲学。因为尽管黑格尔哲学是一个包含 运动和变化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却是被“前定”了的,其起点和终点都是提前“设定” 了的绝对精神。从理论上看,它是可以完成,也是必定要完成的,因此仍然属于古典哲 学现成论的思维方式。
从泰勒斯到黑格尔,哲学家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阿基米德点,并以此为基石 ,建构自己的哲学大厦。尽管不同哲学家对阿基米德点的认识各不相同,但有一点他们 是毫不怀疑的,即有一个阿基米德点存在,哲学的任务就是去寻求它,去追问它“是什 么”,我们可以将此称为“阿基米德情结”。在“阿基米德情结”的推动下,古典哲学 的历史就成了一个不停变换阿基米德点的历史,从泰勒斯的水、巴门尼德的存在到柏拉 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再到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我自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不管这些阿基米德点彼此多么不同,但从实质上看它们是同一的,即它们都是现成的存 在。所以,现成是古典哲学的阿基米德点。
三、从现成到生成: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古典哲学发展到黑格尔,已经穷尽了一切可能,因此一场哲学革命势为必然。发动这 一革命的是马克思。一般认为,马克思发起了一场哲学革命。但在何种意义上理解这一 革命,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革命,绝不仅仅是具体观 点甚至体系的改变,而必须深入到思维方式的层面,实现思维方式的范式转换。马克思 的哲学革命,恰恰是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一场变革,即由现成论转向了生成论,正是在 此意义上,我们把马克思看作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和现代哲学的奠基人。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之中,前者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 第一个文件”,后者则是“新世界观的第一次系统而具体的阐发”。因此,我们将以它 们为核心文本,通过对其的深度解读,来揭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谛。
马克思的哲学建构是建立在对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这 一批判主要集中于两个基点:自然和人。
(一)自然。在《提纲》第一条,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 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 ]
一般认为马克思在此主要是通过强调实践和主体的重要性,来批判费尔巴哈的自然观 ,这并不错,但还不够。我们认为,必须将其提升到思维方式的高度,才可以理解它的 真正意义。这句话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句是“破”,后半句为“立”。一“破”一“ 立”,相互对应,理解这一对应,是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
那么,这里的“客体、直观”意味着什么呢?“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以及“主体” 又意味着什么呢?
马克思在《形态》中指出:“他(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 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 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 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6]
笔者认为,这句话正是对《提纲》第一条的展开和说明,必须将它们结合起来予以理 解。如果把这两段话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就可以理解“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的自然(对象、现实、感性)恰恰就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 东西”。这里的“直接存在、始终如一”,意味着已经存在、永恒不变,即已完成了, 这样的东西无疑是现成性的存在。而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和“主体”去理 解的自然,就不再是“感性对象”,而变成“感性世界”了。这样的“感性世界”则是 “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而且“其中每一 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 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这就意味着,它们不仅是历史的产物,而且是历史的过程,即 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这里的自然也就不再是现成性的,而是生成性的存在了。
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客体与主体、直观与感性的人的活动和实践这一“破”一“立 ”、交互对应的真正意义了。从根本上看,它蕴含着两种哲学思维方式:现成论和生成 论。所谓“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即从现成论的视野去理解,这种视野中 的自然,无疑是“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现成性存在。所谓从主体、从感性的人的 活动,和实践去理解,即从生成论的视野去理解,这种视野中的自然,就是一种历史的 、变化的、生成性的存在了。
因此,我们认为《提纲》第一条的真正意义不是对“主体性”的强调,而是提出了两 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并试图以生成论取代现成论,这就拉开了由古典哲学向现代哲学转 换的帷幕。
(二)人。在批判了费尔巴哈自然观之后,马克思转向了对其理论硬核:抽象人的批判 。这主要集中在《提纲》第六条。“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 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 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 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本质只 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7]
在马克思之前,对人本质的探讨已是汗牛充栋,如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道德的动物 ,……等等。在这所有探讨中,都蕴含着一个不自觉的前提,即人是……动物。进一步 讲,它们都没有把人当作人,而是把人当作(动)物,用把握物的方式来把握人。因此, 无论他们把人看作什么,都没有也不可能把握住人。因为要认识人,“首先不在于你把 人看成什么,而首先在于你怎样去看人”。[8]古典哲学之所以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屡屡 误入歧途,恰恰是因为它们总是把人看成不同的“什么”,而不去反思一下自己看人的 方式是否正确。当然,这一缺陷并非偶然,而是它们必然的命运。因为在现成论的视野 中,一切都是现成的,都是“物”,都是“什么”,这就决定了它们必然把人也当作一 个“物”、一个“什么”来把握。
对于这种把握的基本方法和途径,马克思予以了深刻的揭示。“撇开历史的进程,把 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通过这 种方式得到的人的本质,只能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 普遍性”,这样的“普遍性”,只能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而绝不是人的本质。 因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那么,如何理解“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呢?马克思在此没有正面论述,但他却从反面 阐述了不应如何理解。即不应“撇开历史……”,不应“固定……”,也不应“假定… …”,这三个不应合在一起,就是不应“现成地”理解。至于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在 《形态》中予以了进一步的阐述。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 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 来。”[9]
这段话同样有两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马克思先从《提纲》后退了一步,承认我们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这里的“意识、宗教或随便 别的什么”相应于《提纲》中的“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 性”或“类”或“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马克思首先承认它们也可以把人与动物区 别开来,但紧接着话锋一转,马克思向前迈进了两步。“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 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
需要注意的是,这句话中的“区别”不同于前一句中的“区别”,前一区别是一般特 性意义上的区别,即通过“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可以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 来,获得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某些特点。但在这里,人仍然是一种动物,一种特殊动物 。后一区别则是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即通过“生产”才最终将人与动物从根本上区分开 来,使人获得了自己的本质,成为了“人本身”,而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动物。
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不同的“区别”呢?进一步讲,“生产”和“意识、宗教或随便别 的什么”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从而导致这一区别呢?
从根本上看,“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都是一些“什么”,即都是“本质先定 、一切既成”现成的概念,从它们出发也即从预先设定的观念出发,这一出发点已经把 人当作了物。而“生产”则根本不同,它绝非一个现成的概念,而是一个实际的生成过 程。为了强调这一点,也为了避免误解,马克思特意在它一前一后加了两个限定成分。 前面加了一个“一当……时候”,表明它不是超时空的,而是居于时空之中的具体存在 ,后面加了一个“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表明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 预定”,而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现实过程。在此过程中,人获得自己的本质,成其为人。 这样,生产就与“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划清了界限。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 ,一个是现成性的,一个是生成性的。
那么,“生产”和《提纲》中“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指出,“以 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0]这就 是说,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社会关系,生产是怎样的,社会关系便是怎样的。因此,把人 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关系与归结为生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生产是生成的,社会关系是 生成的,人的本质也是生成的,这就意味着人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不变的抽象本质 ,而只有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本质。
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在人本质问题上实现的变革,不是在已有观点之外又增 加了一种观点,而是从根本上转变了探索问题的方向,即从统治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现 成论的思维方式转向了生成论的思维方式。在这一全新视野中,不仅自然、不仅人,而 且一切存在、整个世界都不再是等待解释的现成性存在,而是生生不息、变动不已的生 成性存在了。这正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旨趣,也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之所在。
四、生成:现代哲学的主旋律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终结了古典哲学,开创了现代哲学。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理解马克 思在何种意义上终结了古典哲学,但要完整理解马克思对现代哲学的开创之功,还必须 弄清马克思之后哲学的实际走向。这就要求对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西方哲 学进行考察。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现象学和分析哲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思潮,它们代表着现代 西方哲学的基本趋势。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下面将通过 分析他们的“思路”来揭示现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
一般认为,以20世纪30年代为界,海德格尔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探讨Das ein,后期则认为存在的意义在于Ereignis。
(一)Dasein(注:“Dasein”这个词中文一般译为“此在”,此外还有“亲在”、“缘 在”等不同译法,每一种译法都有自己的道理,也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译者的理解。由 于我们这里探讨是海德格尔对“Dasein”的理解,为了避免“望文生义”的简单理解, 我们直接引用德文“Dasein”,不做翻译。)
Dasein在德文中一般为“生活”、“存在”和“生存”的意思,但在海德格尔那里, 它特指人及其存在方式。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存在者(Dasein)的‘本质’在于它去存 在【Zu-sein】”。[11]所谓“去存在”,这里指趋向于存在,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 ,“因为Dasein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12],可能性即意味着未完成性。因此“去存 在”实质上是一种生成活动,Dasein正是在这一生成活动中成为自己的。这样,以“去 存在”为本质的Dasein就不再作为现成意义上的主体而存在,而是作为不断超越当前状 态的“尚未”而存在。所以,Dasein就没有任何现成的属性可资自守,也不能被任何现 成的概念所概括,他只在“去存在”这一生成活动中成为自己,这就意味着,Dasein是 一种生成性的存在。
(二)Ereignis
在德文中,Ereignis的意思是发生的事件,其动词Ereignen为发生的意思。但在海德 格尔那里,它则有其更深的含义。他认为Ereignen一词由er和eignen两部分组成,其中 Eignen为词根,其含义是“为……本身所特有”,“使……成为自身”,前缀“er”则 是“去开始一个行为”和“使(对方和自己)受到此行为的影响而产生相应的结果”的意 思。结合起来,Ereignen的意思就是“在行为的往返发生过程中成为自己本身”。除此 之外,海德格尔还追究过它的词源义“看”,“‘ereignis’这个词取自一个从出的语 言用法。‘ereignen’原本意味着:‘er-aeugen’,即‘去看’或‘使……被看到’ ,以便在这种看中召唤和占有自身。”[13]综合起来看,ereignis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思 想:任何自身—“自己本身”—都不是现成的,而是在一种相互引发、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发生和成为自己的。就其实质而言,这一思想正是一种彻底的生成论思想。总之,生 成论的思维方式作为海德格尔思想的内在灵魂,贯串了其思想的始终,它也在决定意义 上影响了其后的哲学解释学传统。[14]
与海德格尔相同的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同样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 ,这前后两期不再是一脉相承,而是截然相反。从思维方式上看,前期是现成论,后期 则是彻底的生成论。
在现成论哲学中,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在具体的万事万物之后、之外、之上存在 一个不变的本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恰恰是要论证这一本质并不存在。他从游戏这 一日常活动入手,依照现成论的观点,“它们一定有某种共同之处,否则它们不会都叫 做‘游戏’”。[15]这一“共同之处”,就是游戏的本质。维特根斯坦认为,不要从“ 否则它们不会都叫做‘游戏’”就推断出游戏必定存在共同的本质,关键的是“不要想 ,而要看!”。
“例如看看棋类游戏,看看它们的各式各样的亲缘关系。现在转到牌类游戏上:你在 这里发现有很多和第一类游戏相应的东西,但很多共同点不见了,另一些共同点出现了 。再转到球类游戏,有些共同点还在,但很多没有了。”[16]总之,“看不到所有这些 活动有什么共同之处,但你会看到相似之处、亲缘关系,看到一整系列这样的东西。” [17]这就意味着,并不存在一个所有游戏都具有的共同“本质”,而只存在一些“相似 之处”。这些“相似之处”的特性在于家族相似。所谓家族相似,指同一家族的成员之 间一般都有某种相似之处,一成员与另一成员的身材相似,这一成员又与另一成员的相 貌相似,……但这种关系并不一定传递下去,完全可能在两个成员之间找不到任何共同 之处。所以,家族成员之间是靠“相似”而非“相同”的链条来建立联系的。
与家族相似相辅相成的,是语言游戏论。这一学说认为,作为一种游戏的语言,既不 存在不变的本质,也不存在不变的含义。因为“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 [18]在用法之外并不存在一种叫作含义的东西。即含义并非预先设定,而是在使用过程 中不断生成的。进一步言,不仅含义、不仅语言、也不仅游戏,而且一切存在,都是在 “使用”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因为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家族相似”与“语言游戏”都 不仅仅是一个论题,而且是一种视野,这一视野中的一切存在,都是生成性的,所以维 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式乃是生成论的。
维特根斯坦之后,奥斯汀和塞尔沿着“含义即用法”的方向继续前进,掀起了一场声 势浩大的“语用学转向”,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则是这一转向的集大成者。不过,无论是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还是阿佩尔的先验符号学,都不仅仅是语用学影响的结果,它 们同时也在相当程度受到了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和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影响。可以说,它们 代表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的趋势,即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融合。
为什么这两大传统在相互排斥、彼此隔绝多年之后又重新走向了融合呢?根本的原因还 是在于思维方式。早期分析哲学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尽管在所研究的问题上大不同于古 典哲学,但在思维方式层面,则是一致的,即都是现成论的。现象学的思维方式则是生 成论的,这一根本不同导致了二者的隔绝。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所引起的“语用学转向” 之后,分析哲学的主导思维方式开始由现成论转向了生成论,这一转向使分析哲学与现 象学在思维方式上得以相通,这一相通在最终意义上导致了二者的融合,这一融合尚在 进行之中。至此,已经可以说在现代哲学这一多重变奏的交响曲中,生成是它的主旋律 。
收稿日期:2002-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