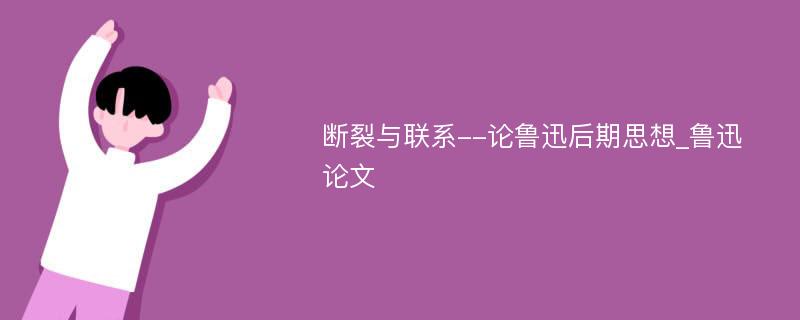
断裂与连接——论鲁迅晚期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晚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4)04-0020-007
鲁迅晚年的思想研究早已从前景渐次退缩到背景以至远景了。时下鲁迅研究的热点与 焦点大多集中在鲁迅早期的思想与作品中。偶有涉及到鲁迅晚期思想的著述,论者的注 意力又大都在关注鲁迅反抗专制的一面,而对于鲁迅与苏俄的集体主义即马列主义的关 系等诸多怎么也回避不了的问题则极力回避或曰逃避之。诚然,这里有太多的顾忌和顾 虑,但是如果不对鲁迅与马列主义的关系进行较为深入、全面的剖析和厘清,那么我们 的研究就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我们所面对的鲁迅就仍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而是一个 被割裂开来的鲁迅,即便这种“割裂”是出于某种目的的“善良”。
本文试图分析探讨鲁迅晚年的思想,重点讨论鲁迅晚年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 困惑与抉择。
一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撰文道:“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两大思想,一曰麦 喀士之社会主义,一曰尼至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 之强者所压伏,尼至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牵制。”[1]在这 里,梁启超是将马克思和尼采二人作为对立的两极介绍给国人的。也就是在这一年三月 ,鲁迅启程东渡日本,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涯。而此时的日本,一股尼采热正在 升温。鲁迅一到日本,扑面而来的就是这股尼采热。可以说,此时鲁迅接触最早、感触 最深、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尼采的思想,以至于他被后人称之为中国的尼采。
应该说,鲁迅对尼采是有相见恨晚的感慨的。我们知道,鲁迅是负着亡国之虞和“我 以我血荐轩辕”之志赴东瀛的。在鲁迅眼里,当时中国是处在“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 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雌安弱,笃于旧习,固无以争雄于天下”[2](P49)的 境地。中国之所以如此,鲁迅以为,与“欧美之强……根柢在人”[2](P50)相较,中国 的病根就出在人身上,就出在国民性上。故此,在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进行启蒙,改 造中国的国民性。在这种忧虑和焦虑的心境中,鲁迅在东瀛与尼采不期而遇了。在尼采 那里,或者说在鲁迅脑中的“个人主义至杰雄”[2](P45)尼采那里,鲁迅看到了他想要 看到的东西,找到了他想要找到的东西,那就是有利于改造中国国民性并为中国固有国 民性所缺乏的“个性和精神”。鲁迅意欲用尼采思想中的“个性与精神”的因子作药方 来拯救“老大之中国”。
“个性和精神”的精神很好地贯穿于鲁迅早期的几篇论文中。相较于当下所倡导的“ 科学救国”和“君主立宪”等口号,鲁迅的思考和思索可以说直抵“人”的底蕴。他提 醒国人严防将人之自我泯灭于国之大群的思想:“聚今人之所主张,理而察之,假名之 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 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寻其立意力,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使 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驸,乃即以大群为鞭箠,攻 击迫拶,俾之靡骋。”[3](P26)“此非独于理至悖也,即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供 献,而考索未用,思虑粗疏,茫未识其所以然,辄皈依于众志,盖无殊疾之人,去药石 摄卫道弗讲,而乞灵于不知之力,拜稽首于祝由之门者哉。”[2](P38)他强调人的个性 :“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3](P2 4)他为“个人”正名:“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人之后 ,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害已之义与欤?夷考其实, 至不然矣。”[2](P43)他一再强调“立人”的重要:“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2](P50);“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议”[2](P39),他试图通过这种立人的努 力以达到“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2](P49)的疗效。一句 话,鲁迅之所以亲近尼采,是缘于中国“因缺失有自由独立人格的、有生命创造力的‘ 个性’和‘个人’,中国传统文化业已钙化或硬结以至全无生命力和创造力可言。故中 国社会要么板结,要么沙化;中国人要么奴隶,要么沙粒”[4](P75-79)的社会现实, 他要用尼采的生命的冲创意志,提升人的个性,拔高人的精神,创生人的自由独立的人 格,改造国民性而将“人”立将起来。他要用文艺的形式唤醒人们“人”的意识,在中 国进行重铸国魂——“立人”的工作。
要“立人”,首先得破,并在“破”中将“人”立起来。新文化运动给了鲁迅以这样 的契机。一篇《狂人日记》,像一道夺目的闪电,撕裂了“天人合一”之天人的“和谐 ”与“同一”,道出了伦理道德的“天”吞噬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天机”。“历史 ——仁义道德——吃人”的剥离和剖析,真可谓石破天惊,振聋发聩。随后他的《呐喊 》、《彷徨》,他的诸多杂文都对旧社会、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和抨击。在“破”和批判的同时,鲁迅在其作品中也试图用“个人和精神”重塑文化精 神。对他笔下的人物,他在哀其不幸的同时,也在恨其不争,恨其不争自己作为“人” 的权利。他积极倡导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他甚至试图将尼采等人的精神直 接注入或移植到中国古人的身上以重释或再创中国传统文化,重塑文化传统。《故事新 编》中最初创作的《补天》和《铸剑》就满蕴了这方面的赤诚和苦心。[4](P75-79)
然而,在1927年后,鲁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也就是说,鲁迅的思想由德国最 占势力之两大思想之一端向另一端倾斜,他由最初的接近和亲近尼采到更多的接触和“ 接受”马列主义。鲁迅的思想和尼采等人的思想发生了“断裂”,而在断裂处“连接” 上了马列主义。
笔者所关注的问题是,鲁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断裂与连接?为什么这种断裂与连接会发 生在1927年?
二
目前还没有资料显示,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研习过马克思主义,尽管那时马克思主义 在日本也异常活跃。这也就是说,鲁迅关注另一“最占势力”的德国人的思想——马克 思主义,还是相对较晚的事情,这种关注最初反映在他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态度和看 法上。
1919年1月,也就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炮响给世界以巨大的震动与震撼后不久,鲁迅接 连发表了两篇随感录《来了》和《圣武》,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成功后的看法 与态度。前一篇随感录《来了》批驳了对苏维埃政权的种种谣言和偏见,他称:“过激 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来了——镇压人民的刀和火。”[5](P53)后一篇《圣武》则直 陈了自己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他说:“看看别国,对抗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 ,他们因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 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5](P62)在这里,鲁迅勾勒 出“镇压(压迫)——对抗(反抗)——主义——牺牲——曙光”的俄国革命的道路。在19 25年发表的《北京通讯》和1926年发表的《<十二个>后记》及《<争自由的皮浪>小引》 等文中,鲁迅也一再重复了这样的想法。可以说,从情感上说,从一开始鲁迅就对俄国 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具体实践——显现出一种亲切感。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兴 趣和关注是由十月革命的胜利触发的,而这种兴趣和关注又是建立在对中国革命的道路 的探寻上的,鲁迅在为国家和民族找寻出路。
然而,鲁迅在当时对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实践虽然有亲切感,但这也是有一定距离的 亲切感;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关注,也是有一定距离的兴趣和关注。换言之,他 当时并未“完全接受”马列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 冷淡,并且怀疑。”[6](P18)秉持着“真”并从“真”的视角来审视大千世界的鲁迅, 对于任何未经证实的东西,是不会轻易地相信的!
但1927年鲁迅为什么就“相信”并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 一是鲁迅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二是社会情势使然。
毫无疑问,立人,改造国民性是鲁迅思想中的关键词。但一如启蒙是作为救亡的一种 方法和路径进入现代中国的视野一样,鲁迅在“立人”、“改造国民性”这些关键词的 背后有一个更为关键的所在,那就是“立人”、“改造国民性”的背景和目的:救亡和 立国。对鲁迅而言,立人与立国这两大任务不是平行的,他那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他对 个人自大的提倡,即隐含着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上来看待个人建设的问题,他要通过个 人的觉醒以求得国家的自救、民族的自强、社会的解放。在鲁迅那里,立人始终是手段 ,立国才是目的。为此,鲁迅着力于先个人再国家,即“把存在从价值中剥离出来而呈 现能再生价值的原初经验,努力将个人从社会存在中剥离出来而呈现出能重组社会的独 立的个人”[7](P69)。然而在他一层一层地清理剥离积淀在国人身上并且包围缠绕国人 的污垢、重负而试图亮出人的本色时,他却与虚无不期而遇。[8](P32-37)换言之,为 了立国,救亡,他致力于追溯人的本真,以期改造国民性、立人。然而使他始料不及的 是,他倾心倾力地追溯的结果最后竟追到了虚无的边缘。立人的地基发生摇晃,大地裂 为深渊,他面临被黑暗和虚无所吞噬的危险。可以说,《彷徨》、《野草》时期的鲁迅 一直在黑暗与虚无的边缘痛苦地挣扎和抗争。在这痛苦地挣扎和抗争的过程中,尽管鲁 迅止住了自己滑向黑暗和虚无深渊的危险[8](P32-37),但通过立人而立国,通过改造 国民性而救亡这条道路无疑遭遇到巨大的障碍!对鲁迅而言,他所感受到的撕心裂肺的 痛苦是:个人尽可以在希望与失望、无望乃至绝望之中驻足彷徨乃至彷徨于无地或无地 的彷徨,但国家和民族却不能在彷徨中驻足,因为驻足彷徨即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和人民 的夭亡,意味着当亡国奴。时代不可能给予鲁迅以从容的时间让他从容地去凿穿前进道 路上的障碍,稳固地基。国家何处去,救国的道路何在,在鲁迅那里已成为当务之急。
内在的驱动力已在驱使鲁迅怀疑自己先前所躬行的从“由立人而立国,由启蒙而救亡 ”的道路,而外在的情势的发展又“自然地”将鲁迅推向了马列主义。本来,五四时期 所倡导的个性解放,大多停留在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层面上,个人性的“个人”并没 有垂直竖立起来,这使鲁迅极为失望,用鲁迅后来的话说,就是自己过去的诸多努力都 如“一箭之入大海”,社会的黑暗依然如故。而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的疯狂大屠杀,则 成为鲁迅思想转换的直接的外在因素,鲁迅的思想开始倾斜,即从尼采这一端走向了马 克思那一端,从个人主义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1927年,正在广州的鲁迅目睹了国民党的清党,这场白色恐怖下遍地殷红的鲜血,给 鲁迅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憾和刺痛,鲁迅在这场大杀戮中每天的所见所闻是:“用斧劈死 ”呀,“乱枪刺死”呀……更为可怕的是,杀人者还在尽情地玩弄血的游戏,以虐杀取 乐。鲁迅以为,如此暴行,即便“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9](P46),为什么 人对人会这么惨烈无情!人类不是已进入到20世纪了吗?皇帝不是已经被推翻了吗?“民 主”、“共和”不是已经讲了好多年了吗?人类不是在进化吗?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惨 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曾惊呼:“为什么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态,而是堕 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10](P1)鲁迅也痛心疾首地呼喊:“我以为20世纪的人群中 是不应该有的。”[9](P47)鲁迅真切地体会到,现在的“黑暗”不仅仅是“如故”,而 且是空前惨烈,国民党的统治较之清政府、袁世凯、北洋军伐更加凶残。这一切不由使 鲁迅陷入更深的思索和反省之中。与二战后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启蒙的内在的逻辑 发展和走向的追问不同,鲁迅首先是怀疑先前所做工作的效用和效果:他感叹他要么在 制造“醉虾”[9](P47),让人吃得高兴;要么自己的努力,做的是无用功。“改革最快 的还是火与剑”[11](P39),掀翻这吃人的筵席,推翻这凶残的社会,是当前首要的任 务。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选择无疑是马列主义的阶级论。有压迫,就要反抗;有反 抗,才会有成功,这与鲁迅先前概括的苏俄革命“压迫——主义——反抗——牺牲—— 曙光”是相同的。正是在这里,鲁迅找到了他与马列主义的契合点。
正是由于这内、外两种力量的驱动和挤压,将鲁迅推向了马克思主义。诚如鲁迅自己 所言的“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了我”[12](P5)。这以后,鲁迅 才认定中国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像苏联那样,“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 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12](P462),才能推翻统治阶级的黑暗统治,“ 惟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12](P191)。故此,鲁迅开始阅读、翻译和研究马列主义 的著作,并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进行论争和战斗。“中国一定要走向共产主义,通过社 会主义来拯救中国,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将来的中国也一定会这样的”[13],可以 说鲁迅是从探究中国社会的出路来接触和接受马列主义的。
鲁迅自觉接触和接受马列主义,他读马列主义的书,翻译介绍马列主义的著作,并与 从前的论敌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率领左联诸成 员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等旧的、保守的文化和文艺进行了坚决而彻底的斗争。一句话, 他希望通过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即十月革命式的革命,推翻旧的黑暗社会的统治,出 现一个迥乎不同的全新的社会。
然而,就在鲁迅以马列主义作武器与黑暗势力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他仍然是心存忐 忑或不安的,那就是,对于推翻旧的黑暗社会的统治,鲁迅认为中国是可以做到的,因 为苏联的革命已经证明;但对于推翻了旧的统治后的新的社会,他“不知道这‘新的’ 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6](P18),因为这未能证 实,可见,他仍然是存有“疑虑”的。我们可以设想,在1931年前后读到林克多《苏联 见闻录》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时,鲁迅的心情该是多么的激动。他不仅花了很 多时间认真地阅读,仔细地校对,而且还为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写了序,对两书大 加赞赏。我以为,鲁迅在这里,赞赏的不仅仅是林、胡二人的著作,更是赞赏自己对中 国应走道路选择的正确,或者说,林克多、胡愈之二人的著作证实了鲁迅选择的正确, 尽管这种证实是间接的。所以,鲁迅才有了情不自禁并“理直气壮”地喊出“我们不再 受骗了!”[12](P429)的狂喜。
试看鲁迅看到的实现了簇新社会制度后的苏联:
1.小麦和煤油的输出——物质生产力的增强。
2.图书馆、博物馆没有被炸掉,西欧东亚都在赞美他们作家的作品,艺术展览异常活 跃——精神生产力的强大。
3.工农都像了个人样,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主人——空前的自由和 自主。[12](P429-431)
不用说,物质上是极度丰厚的,精神产品和精神活动是异常丰富的,个人生活也是空 前的自主和自由。而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自由,这不正是鲁迅所期盼的理想的社会形态 吗,他先前的改造国民性,他先前的抗争和战斗,不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光明的社会的到 来吗!应该说,阅读着林、胡二人的文字,除了激动和激情外,他脚下的大地似乎坚实 了许多,半悬着的心也似乎踏实了许多,他更可以为这光明的未来坚毅与果敢地战斗了 。
本来,林、胡二人未能全面展示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实际情况,至少未能展示出20世 纪30年代苏联的整肃、流放的一面的实际情况,这是其二人著作的一个缺憾;鲁迅因故 未能亲自去看、去感受、去证实苏联的“成就”,也可以说是他的一大遗憾;而鲁迅将 林、胡二人的著作的片面视作全面加以接受,这不能不说是鲁迅的阿基里斯脚踵。事实 上,大量苏俄新解密的档案文件说明鲁迅当时被蒙蔽了,即在他的文章中所赞颂的苏联 政治清明、政局稳定只是一种假象,如“实业党”一案就是冤假错案[14]。终于,鲁迅 感受到了他的脚踵的剧痛。也就是说,他愈来愈嗅到了专制的气息,愈来愈感到了强制 和压制的专横。鲁迅在他所憧憬的光明中似乎也看到了如太阳黑子般的暗影存在。
三
对于鲁迅而言,他一生可以说饱受专制和压迫的痛苦。先是满清和袁世凯、北洋军伐 专制的残暴,而后是国民党政府专制的血醒,而现在在自己倾其热血所从事的崇高事业 中竟也体会到了这种专制的阴冷。对于前两者,鲁迅是有清醒的认识和透悉的了解的, 对于他们吃人、杀人的本质和本性,他曾进行过无情的批判和鞭挞,也曾呐喊和战斗。 而对于后者,他除了不解,更多的是愤怒。“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 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12](P148)我们来看鲁 迅的有关表述:
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 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首先应当扫荡的,倒是拉大 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 君。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 地做,也是打。
《致胡风》,收《书信·350912》
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是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但其实是取了 工头的立场而已。
《致曹靖华》,收《书信·360515》
鲁迅将他所厌恶的专制的代表者称为“革命工头”、“奴隶主管”。然而问题是,以 解放全人类、解放自己自居的人群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工头、主管?又为什么会出现 受工头、主管压迫和压制的感受?我以为这是对待马列主义的两种不同态度使然。
鲁迅试图通过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来达到中国救亡的目的;换句话说,他是把马列 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一种道路。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说过:“在进化的链子上,一 切都是中间物。”[2](P279)在30年代,他又反复强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 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9](P2)“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么样 ,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15](P429)他甚至还说“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 的。”[6](P428)他并不认为也不同意马列主义为一个终极的本体——极境,他要的是 中国通过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而达到救亡、救民的目的,仅此而已。
然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作为一个“极境”进入中国的。在中国的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 者那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运动,他们试图毕 其功于一役,来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既解放全人类,又解放我们自己,最后达至共产 主义天堂。这样一来,马列主义在中国就不仅仅被当作一种救亡的手段、方法和途径, 它更被要求当作一种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实质,依曼海姆的观点来看,就是用一整套不合适的范畴来思考现实并以 此来掩盖现实。[16](P105)而这一整套不合适的来思考现实的范畴即意识形态一旦被人 们所把握和掌握,它就同时把握和掌握了人们。它不但要以这种意识形态统一规范个人 的思想,而且还要求统一规范个人的行为和表达,即作为阶级斗争和文化斗争甚至于社 会生活的中心尺度与基本模式。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由于地处半封建半殖民 地社会,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革命的主体,更要求用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 来保证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要求以其无产阶级党性原则 来统一整合人的思想意识和行动,从而造成强制性的社会运动。这样一来,就由目的高 于一切演变为党性高于一切,手段高于一切。而个人的微不足道,造成了新的专制与压 制。在30年代,虽然左联不是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或党所属的一个文艺团体,但它实 际上被党的地下组织所控制,它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地下党员手里。为了一个“崇高 的目的”,党性原则要求它所属的成员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或同一。 从这种视角观之,左联与鲁迅的矛盾,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组织,一种主 张,一个口号”的提倡,“国防文学”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大张旗鼓的挞 伐,就不仅仅是一个宗派主义的问题,而是关乎党性原则和党的组织性原则的问题。
四
鲁迅觉着了“工头”压迫的苦痛,嗅到了“总管”专制和压制的气息。他在痛苦和愤 怒之余,也在进行深深的思索: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 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鲁迅感到困惑的是,自己殚精竭虑的追寻和追求何以会走向其反面?自己在对光明的拥 抱中何以会抓到那么多的暗影?看来鲁迅没有从追问意识形态入手,而是在“人道主义 和个性主义相互消长”中又拿起了“个人主义”的武器:“自己至今未能牺牲小我。” [13](P103)也就是说,在尼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两极震荡中,鲁迅又有倒向另一端即 “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只可惜,鲁迅先生过早地去世了,没能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深 入的思考。
在第一部分笔者已谈到,鲁迅在日本时就开始强调“个性”与“个人”,中经1927年 的思想上的断裂和与马克思主义的连接,此时则再一次地断裂与连接,只不过这次断裂 的是先前连接的,这次连接的正是先前所断裂的;这也就是说,鲁迅从强调个人与个性 始,也以强调个人与个性终,起点即终点,画了一个圈。走笔至此,笔者不禁深感悲哀 ,鲁迅一生都在警惕这个“圆”字——他为阿Q的“画圆”而哀而怒;他反对“大团圆 ”的结局;他将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一个“圆”:“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 隶而不得的时代”。而他在不经意中竟也画了一个大大的圆!阿Q画了一个不太圆的圆, 鲁迅画的圆是较阿Q“圆”多了;阿Q为他画的圆不太圆而遗憾,然而鲁迅却为了这个“ 圆”而痛心疾首。可以说,鲁迅一生要挣脱的就是这个宿命似的圆圈。
鲁迅没有摆脱画圆的怪圈,尽管我们也可强烈地感觉到鲁迅奋力挣脱“圆”的束缚的 声嘶力竭的呐喊和孤独的背影!时下有学者提出“要接着鲁迅的话往下说”(钱理群语) ,那么我们该如何接着说?该说什么?我们当然不是为了继续画圆——把鲁迅的话再从头 到尾重复一遍(君不见鲁迅之后国人不是还是在不停地画圆吗?),而是要循着鲁迅努力 的方向继续努力地挣脱这个“怪圈”而前行。卡尔·洛维特曾说过:“这两大思想体系 ,即循环的运动和末世论的实现,似乎穷尽了理解历史的各种原则上的可能性。所有那 些阐明历史的各种最新浓度,都不过是这两种原则的各种变体或者他们的各种混合罢了 。”[17](P229)遗憾的是,鲁迅画的圆同时证明了卡尔·洛维特所论断的“圆”——正 确。
不论鲁迅的思想是连接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后的断裂还是断裂后的再度接近或连接苏俄 的集体主义思想即马列主义,其实都一样地渗透着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就是说,鲁 迅是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接触和接受尼采式的个人主义和苏俄式的集体主义的。但显然 ,无论是尼采式的个人主义,还是苏俄式的集体主义,最后都将鲁迅的思想引入到深深 的痛苦与怀疑之中。这诚然表现出鲁迅思想的深刻,但同时也折射出人类所面临的生存 困境与危机。
在鲁迅的断裂与连接处,我们如何断裂与连接?特别是在相对主义恣肆妄为的21世纪, 时代要求我们比鲁迅走得更远,也要求我们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反省和思考。
收稿日期:2004-0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