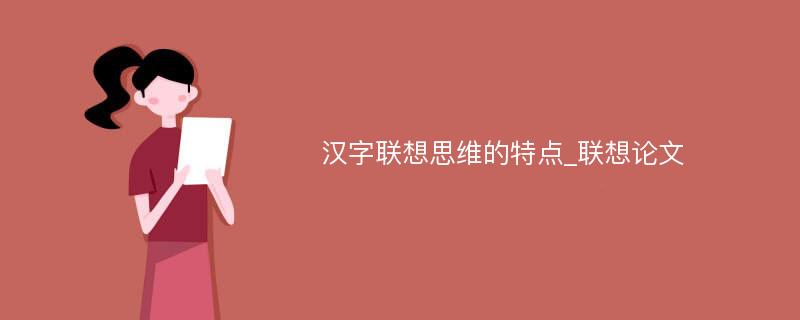
汉字的联想性思维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特质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说文解字》之“六书”,提供了怎样的思维方式?
《说文解字·叙》中写道:“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指示(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无疑是先人用字“直接表意”的写照,或曰是字之本意。而会意字呢?我们从“会意者,此类合谊(同‘义’),以见指撝(同‘挥’)”可以看出,所谓会意字,实际上是在“象形、指事”“直接表意”的基础上,由字义的“引申”而来。它不同于“事物的直映”。在认知层面上,既源自于“直接表意”,却又是经过思维加工而高于“直映事物”的产物,它表明了先人创造文字的表意水平的进步与提高,迈出了建构汉字的联想思维方式的第一步。如,“轰(轟),群车之声。”“从(從)二人相随。”
但是,先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仅仅依靠“象形、指事”直映表意和“会意”引申联想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才有另外两类三种造字法的出现,即一类“假借、转注”、二类“形声”。正如《说文解字·叙》中所写:所谓“本无其字”的假借,通常是说“有些‘词’原先没有为它造过专用字,只是从现成的字中选取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替”,后来习惯了,这个字也就归它使用了。如“莫”字,表示“没有谁,没有什么”意思的否定性无定代词,是借用与之同音的“莫(本义为昏暮)”字。其实,同音的字还有其他,之所以选中“莫”,恐怕还是在于语义表达的联想。因为,古代“语义昏暮的莫,表达的潜在语义就是日落天黑以后,也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没有了)”。
此外,屈伸的“伸”写成“信”;是因为古人屈身可以挟带物品、刀标凶器,而“伸”则目视无藏,表示诚信有加。恐怕也不是仅仅取其“音同”。
飞翔的“飞”写成“蜚”;古人常见飞翔之物当然是蝗虫之类,故假借之。也未必取其音同。
同理,屎尿的“屎”写成“矢”;也是与人身实际感受相关的,古人杂食,且以粮菜冷水充饥,大便会是一泄而就的,畅如放“矢”。
背叛的“叛”写成“畔”;假借之“畔”就是“田的旁边”已不在“田”了,是“界外”了。
抗拒的“拒”写成“距”;古人对抗无论是空手还是兵器相见都是需要保持“距离”的。
凡此种种,就是说明,我们在认识“假借”之法时,不可以简单地解释其为“读音相同或相近”而借,实在是有寓意于其内的,这是中华民族先人造字遵循“以形示意”的基本理念所使然,也是他们造字的出发点与归宿。很明显,“示意”“寓意”“表意”都是先人用以表达思维、沟通情感、交流信息的机制,这种机制的本质就是语义联想的思维方式的拓展,拓展的特征在于超出了“事物实际表象及其直接引申”的程度与范畴,具有明显的“深化推理”性特征,故此先人称作“假借”。
而所谓“转注”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也就是说,某一个字由于意义的变化导致形体的变化,由此衍生出新的字来,是字与字之间的形义关系的一种类型。比如,有文章举例说“考”“老”二字,本义都是长者;“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这些字有着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读音上也是有音转的关系。其实,未必如此,细究起来还在语义方面的差异。“考”“老”虽是长者,但“考”特指“父亲”;“颠”“顶”二字,本义都是“顶”,但是,毕竟“尖顶与非尖顶”是不同的;“窍”“空”二字,本义都是孔,但“有无缝隙”也是相别的。这就说明,先人们造字的“转注”是基于对认知相类而又有异的事物的表意区分,与“音”并没有什么关联。简而言之,是基于对相近事物认知的联想,具有“相似、类比”性特征,完全是表意之需,是语义、形意的联想。
先人们造字从直映的“象形、指事”开始,进而通过直映而联想到“会意”引申;对于不同事物而假借“会意引申”的联想;对于同类、类近事物采用关联性联想的“转注”之法。彼此之间是以表达“认知深化联想”的思维方式进行着的,伴随先人们认知水平的逐步发展,一脉相承地形成了的语义、形意的联想表达机制,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宽泛、提高。一方面,口头语言需要文字作出“超时空”的记录;另一方面,新认知的事物运用“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之法造出的字也需要为口头语言提供表达语义的字音,尤其需要在二者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在这个双向需求面前,先人们从文字是用来“示意”“寓意”“表意”的功能特质出发,将语音依附给用来“示意”“寓意”“表意”的字形,巧妙地将“字形和字音”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形声字”用来表达无限丰富的语义。《说文解字》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这里“以事为名”就是“表意”为干。所采用的方式,正是人类在认知共处于同一范畴的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时,以认知为基点理所当然地使用语义联想为特征的基本思维方式——沟通字形、字音,可以说,形声字是语义联想性思维方式的一个飞跃性创造。几乎所有以“金、木、水、火、土,人、言、目、口、手”为部首的形声字都是“以音附意”“以形示意”的,犹如“字音‘嫁’给了字形而随字意(语义)”,成为具有“形音对立统一”特征的辩证联想性思维。
综上所述,我们有如下的认识序列:首先要明确,先人们造字在先,而后《说文解字》才得以概括出“六书”之法,是对先人造字规律的归纳总结;而今,我们这里揭示“六书”之法所蕴含着的思维特质。即认为,此“六法”恰恰反映了先人们认知世界的逻辑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先人们用他们创造的文字记录了基于认知客观世界的、以形表意的联想思维机制,凭借这样的机制构建了形意文字的基本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以“象形、指事”的“直映表意”为基础,以“会意引申性联想、借意推理性联想、相似类比性联想和形音辩证性联想”,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简到繁地进行,最终用“以形表意、形音辩证”的“六书”之法、建构了包含9335个汉字的字集。如果我们将许慎在《说文解字》结集汉字中反映出来的“汉字整体建构”思想进一步加以归结,那么,我们还会发现,先人们的汉字建构的另一个特有的思维方式,即“系统分类性联想”——这可从大量形声字的偏旁部首的分类中得到启示。比如,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用字的偏旁部首是截然不同的。当然,这是其他文字所无可比拟的。无疑,这是先人们在数以千年计的思维实践中,创造累积而得的,因而也就形成了联想性思维方式的传统,或曰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基因,并由此伴生了绵延五千余年、经久不衰的丰饶文化。由此可见,汉字之所以能够建构悠久、完备的文字系统,其关键在于自始至终贯彻“以形示意性联想”;换言之,当且仅当依凭“以形示意性”建构文字系统之时,才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联想性思维方式。
汉字联想性思维方式的充实、完善与发展
然而,汉字的联想性思维方式成于“六书”而未止于“六书”。
历史上,汉字先后经历了多次外来文化的冲击,这可以由“汉人与非汉人交替掌权”的朝代更迭中管窥一二,最终非汉文化无一例外地被汉字文化所融合,随之,汉字联想性思维方式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其间尤以古代的佛教传人和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这两次最为突出。对此,先人们采取了“以我为主”的文化原则,这个“我”就是文字的“以形表意(而非‘以形表音’)”。其结果,非但没有给汉字以毁灭性影响,反而使汉字获得充实和完善,得到更完备、更良好的发展,充分显示出汉字联想性思维方式的文化活力。这个“活力”在吸纳外来文化的时候,按照“以我为主”的文化原则,一方面,对于汉语、汉字固有的相同、相近、相似的语义,可以用汉语、汉字表述的概念、原理、知识一律予以直译。比如,“代”数、“函”数、“速”度、“化”学、“蕃”茄之类名词用字的选择,都是以“以形示意”为基点的。也正是由于先人们坚持了“以我为主”的文化原则,使得国人对外来文化的认知自然而然地同化于汉字联想性思维方式之中,为外来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并为国人学习运用外来文化创造了极大的便利。相比之下,今人将“fans译为粉丝”、或将“克分子浓度”退译作“摩尔”,真是相形见绌,透着“文化”的缺失,确是无颜示父老、愧对祖宗的!
另一方面,对于原本没有适宜的汉字能够表述的事物和概念,不得不采取了有限度的译音方式处理。即便如此,先人们依然是尽其所能沿着汉字联想性的思维方式进行的,比如,“菩萨”由译音而来,但是,采用的“菩”也是选取与佛教相关的菩提树的“菩”,“萨”也是带有“异域”“异族”的文化联想意味,而没有简单地译音为“仆仨”。而专业名词“铷钾钠钙镁”“氦氖氩氪氡”之类,原本在《康熙字典》中是没有的,完全是现代西方外来文化传入之后创造出来的。显然这是遵循类推联想的思维方式,大量巧妙地运用形声字的造字方法,理所当然地将现代科学技术术语纳入汉字文化之中,也为现代科学分类学所叹为观止。当然,也有极少数“直译不成”“译音不妥”的、世界流行的专业化文字,比如“0123456789”“化学元素符号、分子式”之类,当保留者自然保留,也无妨,正是文化包容的体现。于是,才有现代数学、化学中文教材出现,始终保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原则。在近代,西方工业化社会创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带来了世界性殖民文化浪潮,无数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字体系,甚至文化溃决失散;在中国,也曾出现一批知识分子在强大的科技压力和文化侵略面前,出现对汉字与汉字文化的怀疑与动摇,然而,百余年来的历史证明,唯有汉字力排众难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它没有,也不可能被外来文化所取代,束手退出人类文化的舞台,使得至今依然没有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为汉字所不容,新生文化所不受。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具有巨大的文化包容性、联想性思维方式的吸纳力,以及与时俱进地自我完善的创造性!
我们作出上述论断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分析中得到印证。
一个建立在“数理化生地”等学科基础上、庞大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引进和吸纳,当然不是创造有数的几个汉字就可以胜任得了的。对此,先人们秉承“以我为主”“以形表意”的原则,把汉字联想的思维方式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那就是,大量双音节“词”的创造!所谓“词”是汉字继独体的“文”发展为合体的“字”以后的新创造,这个创造以汉字双音节“词”的“复体”形式为基本特征,并且在两个基本层面展开建构。
其一,基于常态认知规律的形式逻辑法则“种概念+类差”的原理,运用汉字联想的思维特征,建立了无数个(乃至无限个)名词。比如——
电灯、电话、电车、电炉
阴电、阳电、漏电、来电
火车、马车、牛车、汽车
车门、车龄、车锁、车灯
以及例如——
科学—学科、法制—制法、语言—言语等等绝无仅有的复体词。此外,基于语言思维的基本规律,寓基本语法规则于其中,运用汉字联想的思维特征,建构了一系列词语,比如——
主谓结构的:人性、法律、民主、科学
动宾结构的:讲演、纳税、梳理、情人
状补结构的:实验、偶像、恩惠、规则
复意结构的:智慧、羡慕、思想、重复
……
难道这不是汉字体系之语义联想思维方式的里程碑式的创造与飞跃吗!
其二,在运用汉字构词的过程中,因循了自《说文解字》沿袭的“会意引申性联想、借意推理性联想、相似类比性联想、系统分类性联想”,逐步深化、丰富了几乎每一个汉字的义项,使之在建构的不同的“词”中表达不尽全同的语义。比如,一个习以为常的“大”字,尽管最初“大”字源自对人自身的推崇,之后其字义就分别可以从几个层面联想类推,以至于表现出汉字“复体”构词的基本规律,依然是按照汉字造字的几个联想思维的层次进行的——
A.直意为物体占有立体空间的状态,相对于小而言,如:大楼、大象;
B.引申为平面面积的宽广,如:广大、大地、大海;
C.借喻为数量、气力、强度等方面比较的结果,如:大量、大力、大宗;
D.转意为程度、排行、职位等,如:大致、光大、大官、老大;
E.派生为人格特征,如:大气、大度、大方。
我们按照“本意、引申、借喻、转义、派生”等几个基本字义联想层级,将最常用字的500个高频字所构‘词量’(分别构词50~480个),总共45000余个作出层级分类,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样的规律。换言之,如果我们掌握了汉字构词的字义联想性思维方式,那么,既可以准确理解汉字在所在词中所表达的语义,而且有助于正确使用汉字及其所构成的词。当然,依循此法可以与时俱进地吸纳、包容未来出现在汉字面前的所有新事物、新文化。因此,继《说文解字》之后,我们需要运用联想性思维方式著述一部现代的《说字解词》,总结、概括、提升汉字系统规律和基础理论。建立全新的汉语语言学、汉字文字学和汉语中文学。
本文说到这里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汉字联想性思维方式足以包容、吸纳近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社会文明创造的一切文化,因而不仅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作出的最为宝贵的卓越贡献;也可以断言:汉字的联想性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提供的最为珍贵的伟大智慧!德国伟大的科学家莱布尼兹之所以认为汉字是整个世界梦寐以求的最完美的文字,是因为他能够站在高等数学——这个足以代表人类思维最高水准的学科理念之上,以不同凡响的视野和超乎常人的思想高度作出的论断!一些名人之所以预言人类最终将通用汉字,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汉字是建构在最贴近人类基本的联想性思维规律,具有人类认知所需要的直观、简捷特质的思维方式。特别值得兴奋的是,当人类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的新世纪,汉字再次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出乎意料地顺应了数字化技术的需求,融汇了迄今为止人类最为便捷、最为神速、最为绿色的语言文字信息技术。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联想性思维方式与计算机的数字化信息技术原理的吻合。如果说汉字的先进性是与人类联想性思维方式的吻合,那么,汉字与数字化信息技术原理的吻合真真切切是汉字科学性之使然。而所有上述特质集中到一点都是基于汉字的形意性——一个与人类思维最贴近的文字需要。可见,种种语言文字的成熟度,都需要基于人类主体的思维特质层面的研究;语言学、文字学都需要基于文化特质层面的研究;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字学都需要基于科学技术层面的研究;亦即“主体之思维、客体之文化、介体之技术”三者缺一不可。看来,语言文字的认知、应用和研究都需要重新审视与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