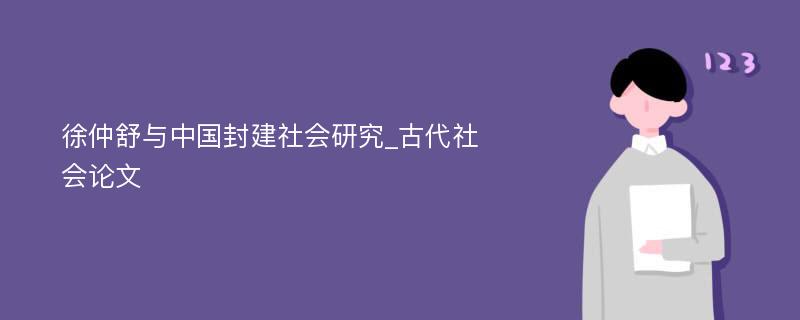
徐中舒与中国前封建社会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建社会论文,中国论文,徐中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3)03-0174-10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大体始于20世纪初。早在1906年,刘师培陆续发表《古政原始论》《古政原论》等著作。其中《古政原始论》讨论的十三个问题,涉及先秦时期的氏族、君长、阶级、礼俗等,刘氏除引用文献外,还利用了金文、钱币等古文字资料。学术界评价刘氏以上两篇文章,“虽仍不脱传统史志的体例,但已开启具备近代意义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端倪”[1]。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社会史论战发生后,中国古代社会问题开始逐步引起中国古史学界的重视。社会史论战加速了中国社会史的成长,但实事求是地说,社会史论战期间,“郭陶两派以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者,人数更多,但有贡献的却甚少,他们不但少有贡献,有的人甚至于反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走入了歧途”[2]99。此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领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然而,由于该重大理论性问题涉及专题繁多,性质复杂,在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学术界对该理论性难题的探索和争鸣一直未停止过。自20世纪30年代起,徐中舒先生即高度关注这一理论性难题的学术进展,并就此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辛勤探索,逐步建立起独到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理论体系。
一、关于氏族组织
中国早期社会中氏族的材料屡见于《左传》《尚书》《国语》《史记》等古代文献及甲骨文资料,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唯班固《白虎通·姓名》、王符《潜夫论·志氏姓》、郑樵《通志·氏族略》及顾炎武《日知录·氏族》等著作或多或少地揭示出先秦社会的部分历史实际外,总体而论,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传入中国之前,由于缺乏科学的历史观念,学术界关于氏族组织与氏族社会的研究,大多尚不具有学术价值。诸如《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近代以来的史学家已较为清晰地意识到,这里的“国”与“诸侯”皆非事实,“夫古国能如是之多者,大抵一族即一国,一国之君,殆一族之长耳”[3]40。又如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殷本纪》中均提到禹、契之后,“其后分封,用国为姓”,并分别列举了不少的氏。金景芳先生指出:“这些血族团体如氏族、胞族、部落等等都是‘自然长成的结构’,并不是如后世的诸侯国,是经过分封才出现的。”[4]唐嘉弘先生亦指出:“司马迁忽略了古代氏族、部落增殖裂变的事实,误以周、汉政体去理解夏商政体,不合历史实际。……这纯粹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现象,夏、商诸氏的出现正是如此,并非出于分封。这在原始社会末期,带有普遍性。”[5]凡此表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初期的社会结构和氏族组织缺乏科学的观念,因而他们对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与特征的不少研究很难准确揭示中国早期社会的历史实际。
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学者对人类社会早期氏族的组织结构与特征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19世纪以前,西方学者对于阶级社会以前的状态和那时的社会组织也基本上一无所知。直到1877年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较早以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发现了氏族的组织结构与本质特征,“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基础”[6]113,“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实根据”[6]114,“从而为上古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7]433。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现代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传播至中国,新时代、新史观、新史料、新方法、新的文化氛围,助推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繁荣局面。1930年,由联合书局出版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较早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概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并结合古代文献和新出甲骨文资料,对商代及其以前的社会生产、氏族组织和婚姻形态等重要理论性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探索。事实上,自《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2]96-97。自20世纪30年代起,徐氏逐步自觉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民族学资料,对上古社会氏族组织与婚姻、继嗣、亲属称谓等问题作较为接近历史实际的考察。
也就在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的同一年,徐氏发表了著名的《耒耜考》一文,文中较早谈到氏族组织问题:
社会学家说原始的人们,不能有个人财产的观念。他们生活在氏族共产之中,氏族内部,一切属于全体,共同消费,非洲波希曼人若是捕获一条野牛,则分割为许多块数以送于其余的人。旱荒的时候,佛爱奇的少年便沿河而跑,若是运气好,遇着一条死在浅滩上的鲸鱼,他们无论饿得要死也不动手,只是迅速地跑回去告知他们的氏族,于是氏族人员立刻跑来,由极年长的人将死鲸平均分割于全体。即是农业发明以后,种族或氏族的共有土地,仍是共同耕作,共同消费的。[8]
徐氏还举证“纪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王时代,尼雅格大将在印度某几处地方,还目击各种族对于共有土地的共有劳动,及收获物之按照户口分配”[8],“一个爱斯基摩人自己只能具两个独木舟,若制造了第三个,便归氏族处置,因为凡自己不使用的物件,便是共同财产”[8]。综上可知,徐氏通过民族学材料较早地了解了氏族组织的概貌和氏族社会的若干特征。
随着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徐氏开始逐渐关注中国古代社会氏族组织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徐氏发表《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一文,文中开篇论及:“氏族社会是奴隶社会的基层组织,而在中国史上关于氏族的资料,还是极端的缺乏或是过于零碎;就是中国四裔的兄弟民族的历史,也都是氏族组织解体以后而以家族谱系为骨干来写成的,所以它的面貌一直是看不清楚的。”[9]他认为,甲骨文资料中王族、子族与多子族“王和王子或许多王子不在一族之内”的现象[9],“必须在原始社会里找出它的类型”[9],“还要从殷、周史料中找出它的嬗蜕之迹”[9]。徐氏指出:“社会发展是要经过一定程序的,而新的阶段里,往往留有旧社会的残余。”[9]徐先生举证“父系而父子不同族”的澳洲土人中阿兰大(Arand)部族的情况:“它的组织有两个分族”[9],“每个分族又分为两个婚族”[9]:
在这两个分族里:彭奴加的男子只能娶蒲儒那的女子,生子为布挞拉;蒲儒那的男子只能娶彭奴加的女子,生子为库马那;同例,布挞拉的男子只能娶库马那的女子,生子为彭奴加;库马那的男子只能娶布挞拉的女子,生子为蒲儒那。[9]
徐氏指出:“在这个分族婚级制下,必是父子不同级、而子孙同级,这个亲族称谓,很像周代的昭穆制。”[9]徐氏同时举证清末保定出土三戈铭文所反映“正是氏族社会兄弟同属于一族的现象”[9]。徐氏推测,每个婚姻级里,是分成大、中、小三个集团的。殷代帝王有两代都以中、外并称,“和大、中、小的划分不同……颇疑为是母系和父系过渡的现象,中为父系,外为母系”[9]。徐氏以上推论,显然和早期史观派学者“氏族社会是以母系为中心的”[10]15、“商代尚未十分脱离母系中心社会,‘彭那鲁亚家族’还有孑遗”[10]20的推论,增加了不少科学理性的分析。尽管近年来有的学者对包括徐氏在内的学者“从甲骨文的个别资料论证商代内婚制的做法”[11]提出质疑和批评,但迄今为止,商代究竟是内婚制抑或是外婚制,仍是学术界争讼不止的话题,以上质疑与批评尚难以从根本上彻底推翻徐氏氏族分族婚级制的推论。
与此同时,徐氏在上文中还论及“氏族与姓”问题。徐氏指出顾炎武《日知录·原姓》关于姓与氏的论述,“实在看不出族和姓究竟有什么分别”[9]。徐氏以为,《左传》定公四年记载鲁、卫分有殷民六个氏族和七个氏族,“这是殷代灭亡之后东方社会还保存了旧的氏族组织的现象”[9],至于晋国,这里原居住的人民有怀姓九宗,“称‘姓’与‘宗’,正是家族或宗法组织的称谓”[9]。徐氏还从夏传子、家天下的记载推测,“夏代西土的氏族组织或者已经解体而成为家族社会了”[9]。徐氏结合古代文献与边裔地区民族学材料推断:“姓是因家族外婚女子从夫居才产生的,在氏族的分族婚级制下,是不需要的,因此,秦汉以前的男子,就从没有称过姓的。”通过以上综合研究,徐氏肯定地说:“家族是氏族社会解体后才建立的,氏族是先于家族的。”[9]徐氏通过对殷代氏族组织解体过程的分析,廓清了中国氏族社会的重重迷雾,揭示不少历史真相。
以后,徐氏在《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一文中继续论及:
姓就是出生的血缘关系。这种出生的血缘关系,最初是以母系计算,称为姓,后来发展到以男性为计算标准时,就出现了“宗”。宗就是祭祀祖先的庙主,是以男系计算血缘关系的。因此,姓和宗的区别:姓原是母系血缘关系,发展到以父系计算血缘关系以后,姓也就转变为父系血缘关系,而宗则完全是父系的血缘关系。[12]
在《巴蜀文化初论》一文,徐氏根据以上研究,结合民族学材料,科学地考察巴、蜀上层建筑的差异:
《世本》说“蜀无姓”,而巴郡、南郡蛮有五姓……这就是巴、蜀上层建筑的差异所在。巴族的姓是大姓的姓,是一种部落组织。每一个大姓,就是一个部落。巴氏统治其余四姓,也不过是一种部落联盟的形式。巴还没有完成国家机构,这也是它的经济基础的反映。蜀所以无姓,它已经超过了部落组织而进入国家形式了。中国历史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没有像汉族这样的姓。他们就没有像周代以后的,百世不通婚姻的,父系外婚制的姓。蜀的无姓,也不例外。[13]
为进一步了解中国早期氏族组织的概貌,徐氏充分关注到广大南方地区少数民族保存的较为原始的氏族社会资料。在《巴蜀文化续论》一文中,徐氏据《新唐书·南蛮传·两爨蛮下》“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复雠云”和《乌蛮下》“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之记载论及:“‘鬼主’是乌蛮的氏族组织,在白蛮中是没有的”[14],“乌蛮部落大鬼主之外,还有百家的小鬼主,正说明乌蛮社会还保存了一套完整的氏族制”[14]。徐氏指出:“血亲复雠是氏族社会对每个成员所承担的神圣义务,氏族的兴衰,完全要看这个任务执行得好坏而定。”[14]徐氏举证解放前西南彝族的情况加以说明:
解放前彝族社会是以家支为主的,这已经是由氏族进入家族社会了。他们的氏族虽然已经解体,他们依然在打冤家,他们还要把血亲复雠的义务交由家族承担。[14]
徐氏还注意到《华阳国志·南中志》“与夷为姓”和檀萃《滇海虞衡志·志蛮》“其同姓者,不必亲种类;或久居相爱,即结为同姓,叙伯仲”的记载,揭示早期“氏族社会虽以血缘纽带为主,但是,如果经过神示结义或氏族成员的同意,也可用继承的关系而为氏族的一员”[14]的若干历史真相。值得注意的是,徐氏并非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西南地区古代氏族资料,他在作出以上推论的同时,强调其所进行比较的边裔民族的氏族社会已“处在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家长制氏族公社的阶段”[14]。显然,徐氏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保存下来的氏族、家族材料推论中国早期氏族社会的概貌,比早期史观派学者简单套用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氏族社会的材料推论中国古代社会,材料更为贴切,所作结论也自然更为接近中国氏族社会的历史实际。
应该强调的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已经进入蓬勃发展的崭新阶段,徐氏所关注的氏族社会的不少重要理论性问题的研究,在不断向前推进。诸如杨希枚先生即对古代文献中出现过的“姓族”和“氏族”进行过严格的区分[15],并提出了“传统所谓氏族(clan)一词不适于先秦时期”[15]的理论。尽管杨氏以上论点仍有继续探讨的余地,但无疑有助于学术界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徐氏氏族社会理论作更为深入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徐氏反复强调:“中国古代社会有自己的特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还需要深入细致地研究,不能简单地按照欧、美社会情况硬套”[16],则与史观派学者“中国的古代发展和马克思的学说不尽相符”[17]109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迄今为止,徐氏提出“图腾并不是人类最原始的产物,而是后起的塗附上去的东西”[14]、图腾“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不显著的”[16]等论点,不断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继徐氏之后,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古籍中并没有像人类学调查所见保存完好的图腾制度”,图腾说的泛滥“必然危害古史研究”[18]。然徐氏之谓“姓在古代就不是最广大的被统治的人民群众所有,也不是中国历史上边裔部族所有”[14],“历史上许多兄弟民族都没有姓”[16]的论点,目前尚未引起中国早期姓氏制度和家族形态的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和关注。综上可见,徐氏对氏族社会组织、结构、特征的研究,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于中国早期社会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二、关于农村公社
农村公社是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形成的、以地域性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二重性为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农村公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农村公社有公有因素又有私有因素;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同时又是向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从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19]450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农村公社,和氏族公社、家长制家庭公社有着实质性的区别,马克思认为,它们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农村公社,则是自由的,没有血缘联系的人们的第一个社会联合组成”[19]268-269。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公社的表述,不难确知,虽然他们并不认为农村公社仅局限于东方社会,但他们屡屡指出,农村公社“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20]220,是“亚洲的专制制度和停滞状态的……更坚实的基础”[21]27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村公社的诸多精辟见解,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上古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中,多数学者均肯定农村公社的存在是东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至于它的性质和作用,学术界则长期存在不同的认识。如有的学者认为,商末周初的基层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到了春秋时代,则逐渐发展成以地区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22]另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整个经济之所以长期地、带有原始性和自然性,“是和农村公社的长期地和顽固地保持,有连带关系的”[23]。一些西周封建论者认为,农村公社的长期保存,并非只是古代东方奴隶社会的特点,它同样是东方诸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如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的农村公社随着商品经济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而瓦解,而东方奴隶社会的农业生产和私有财产虽然不断发展,但公社不但不解体,反而始终强固地保存着,成为东方灌溉国家的最好基础。[24“]在古代东方型的奴隶社会中,是‘古代公社’的继续存在,而不只是被保存一些残余。”[25]与以上意见相反,部分学者则认为古代东方的农村公社只是一种残余形态,不赞成过分强调它的作用。如有的学者认为,任何社会形态的农村公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只能起过渡作用,而不能起独立主导的作用。过分强调村社经济的基础作用,把它看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段,这在基本精神上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26]所谓“农村公社长期存在”、“不解体”以至“日趋强化”的说法,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以此来表述古代东方的特点也是不确切的。[27]总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农村公社的性质和作用的理解,分歧甚远。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村社制度是东方专制制度和亚洲社会停滞状态的基础,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在古史分期讨论过程中,徐氏充分利用历史文献和大量有价值的民族学资料,就农村公社问题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观点,并日渐建立起颇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古史分期讨论中,徐氏较早指出:“古代中国长期保存着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组织,而运河和大规模的人工灌溉排水制度,也是存在的,这都和古代东方相同。”[28]徐氏从文字学角度推论:“农业公社的基本组织是邑和丘”[29],“邑和丘为农业公社的基本结构”[29],以证农业公社是在“低地”[29]建立起来的。在《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一文中,徐氏指出:和家族公社不同,农村公社是“一个相当孤立的组织”[12],它“不是以家族为生产单位,而是以男耕女织相结合的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为生产单位”[12]。徐氏举证宋、明时期南方地区僚“无酋长版籍”及白罗罗“有众数千,无统属”的例证,推论“在农村公社里既无贫富的分化,也不需要军事酋长,仅仅需要一个具有公众办事能力的村长”[12]。根据以上研究,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存在,并初步揭示了农村公社的组织结构与特征。
以后,在《巴蜀文化续论》一文中,徐氏从文字学角度推论:
古代所称的“百濮”和“百越”,就是中国大陆上存在的许许多多的农业公社的总称。[14]
文中徐氏对春秋以后南方地区农业公社的存在形态作了以下论述:
当黄河流域夏、商两代,已经完成了两个奴隶制王朝以后,江、淮以南依然处在这样闭塞的农业公社之中。春秋以后,楚、吴、越在南方相继代兴,接着就是秦、汉王朝完成了封建的统一的帝国,在阶级和部族的双重矛盾中,这些原始公社不断受到中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才逐渐地向阶级社会——奴隶制或封建制过渡,但是,仍然有不少地区的原始形态,还要延续一个很长的时期。魏、晋以来历史家所称道的“宗”和“里”,就是这样孤立的农业公社具体存在的记录。[14]
对以上“魏、晋以来历史家所称道的‘宗’和‘里’”[14],徐氏又作了以下进一步的说明。徐氏注意到《三国志》和《后汉书》分布自长江流域到越南地区这样广大地区的诸族均有与“宗”相关的称谓,并对其性质和演变情况作了如下论述:
他们的社会组织还是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和周代的宗法为近,而与秦、汉以来的家族,还有很大的区别的。宗法有大宗,有小宗;大宗是氏族制度的残余,小宗是家族制度的前驱。……这些“宗部”已有“宗帅”和“宗兵”、“宗伍”的分化,这已经是进入阶级社会了。魏、晋以后这些宗帅成为“方土大姓”,那就更接近于家族制了。[14]
徐氏指出,和以上的“宗”不同,“里是古代农村公社的基本组织”[14]。他举证《孟子》中有关井田制的记载,从孟子教滕文公对被统治的农村公社的野人行“九一”的助法推测:“助法是农村公社中实行的劳役地租。”[14]又综合《孟子》《司马法》《管子·乘马篇》的记载推断:“古代的农村公社,就是计口授田,因田制里,田里都属公有,所以《王制》有‘田里不鬻’之说。”[14]
以后,在《论商於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徐氏结合南方地区民族学资料,以更宏观的视野对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共同体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徐氏指出:
战国时人称当时存在于西南地区的原始形态的村社共同体为黔中。这种共同体因时代和地区的不同,在商代汉中地区则称为於中,在战国时代夜郎的东境则称为黔中,在唐、宋以后的西南地区则通称为洞(溪洞或山洞)。名称虽有不同,所指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村社。它就是以一夫一妻制家庭,在土旷人稀土地公有的条件下,合耦而耕,共同分配生产物的耕作制的社会。
古代原始村社共同体,利用丛生的灌木,如荆榛棘楚之类,构筑外围,既以防御邻敌的侵扰,也避免了野兽的伤害禾稼;春秋以前的楚国,就是从这样环境里发展起来的。[30]
徐氏以资料比较详备的“进步的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与合耦共耕的合亩制相结合的社会”[30]的黎洞合亩制为例,重点考察了唐、宋以后“古代村社共同体发展的最后阶段”的洞的若干情况:
合亩中的家庭,均属父系小家庭,一般包括夫妇和未成年未结婚及已结婚而未另立门户的子女,人数不等,大都为三四口人。……解放前,一个村包括几个合亩,个别仅有一个合亩。[30]
徐氏将黎洞合亩制与古代耦耕进行比较:
古代耦耕,是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进行的,只按合耦的劳动力,包括妻和未成年的子女在内,平均分配生产物。黎洞合亩是在土地私有制下进行的,生产物的分配每户并不相同,出亩多的要多分几成,显示了这里已有贫富的分化和轻微的剥削。[30]
五指山的合亩则和古代的耦耕没有什么区别:
居住在五指山的黎族人民,有一些地区还存在着比较原始的合亩制,这是生产资料(指土地言)共同使用,生产品按户平均分配的原始耕作形式。它是由亲属关系组成的,或以亲属关系为基础吸收外人参加组成的。[30]
徐氏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提供的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古代印度村社共同体的资料,和中国古代村社进行比照:
印度共同体,有一个进步的一夫一妻制父系家庭,有男耕女织固定的家庭分工,这也是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形态……我国古代农村也是以一个进步的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在土地公有的条件下进行耦耕,只是耦耕的组合与生产物的分配,未见记载,现在也从黎族的合亩制得到说明。
印度村社共同体是一个自足的生产整体,其中也有十数人脱离农业生产的公职人员。……这四种公职人员,与秦汉时代县级以下的乡官: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互相对应,十分相似。[30]
徐氏又就以后汉时代乡的组织机构和古代南方地区的洞首、洞官进行比较:
后汉时代乡已直辖于郡县的权力之下,有秩已成为秩禄百石的正式官吏,其地位转处于三老之上,而小乡仅以啬夫一人处理一乡事务,这就和唐、宋以后的洞首、洞官没有什么区别了。[30]
通过对黔中洞的考察,徐氏继续对古代北中国的共同体进行了更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普遍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解放后在黄河流域、江淮流域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星罗棋布,它们就是古代共同体在大陆上的局面。周王朝以农立国,它就是从这样共同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中国古代的共同体,虽经殷、周两代的改造和破坏,在黄河流域也不能蜕变干净。春秋时代齐国还有三老存在,汉、晋时代,从夫余北迁的东沃沮,“邑落渠帅皆自称三老”,他们在共同体中,还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战国时代墨翟、宋牼、老聃、庄周、惠施以及齐国稷下学派的产生,就是以这样共同体作为他们的社会基础。
(4)村社共同体是人类在土旷人稀的年代里,自己走出来一条大路,合耦共耕,共同分配生产物。它的最大的弱点是孤立、闭塞、视野不广,苟安旦夕而不能联合起来,组成有足够的保卫自己的武力。[30]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徐氏强调指出:“中国古代地旷人稀,可以和平发展,形成耕织结合的农村公社,各种不同的文化都是以公社共同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31]由此他对吴越地区的公社组织与吴越兴亡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指出:“吴越在春秋以前虽已建立国家,但农村还广泛存在着村社组织。……这样的社会容易结合成一个大国,遇到变故也容易崩溃。”“吴越的基层组织是公社,征伐物资,动员人民,都要通过公社。公社对人民有一定保护作用,对剥削有相当程度的对抗性。”[31]综上所述,徐氏充分利用文献记载、民族学资料,并自觉结合马克思主经典作家理论,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农村公社的长期存在,并对中国古代农村公社的组织结构与特征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见解,为其长期关注并不断深入探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奴隶制形态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之《序言》中第一次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阶段。”[32]9但是,马克思终其一生,也没有给“亚细亚生产方式”下过定义,更未明确指出这种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的位置,马克思逝世后,“亚细亚生产方式”便成了20世纪世界性的学术难题。
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较早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了简要解释:“‘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会”[10]154,“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10]154。以后至社会史论战中断前夕,郭氏逐渐放弃了以上旧说。他在《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或‘东洋的社会’实等于‘家长制’或‘氏族财产’形态”[33]311,“作为社会发展之一阶段的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奴隶制以前的一个阶段的命名”[33]312。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郭氏“他一方面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在家族中潜在着的奴隶制氏族财产的形态,另一方面又坚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社会以前的原始共产社会阶段,这在理论上不免使自己陷入矛盾”[34]29。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袁林先生举证20世纪中外学术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有原始社会说、奴隶社会说、封建社会说、混合阶段说、东方特有阶级社会形态说、经济形式说等论点[35]。在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下,徐氏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颇为关注,并不断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实际,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论点。
在《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一文中,徐氏较早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只有简略的概念,关于这方面我们期待他日再作进一步的研究。”[9]以后,在《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并批判胡适〈井田辨〉观点和方法的错误》一文,继续论及:“古代中国的社会,依据马克思的论证,是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类型,自古代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都是以公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向有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过渡的。”[29]徐氏认为,经典作家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解答中国古代社会的钥匙”。以后,徐氏继续指出:“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史所以有这样分歧的意见,就是因为‘像在印度一样’、‘像在亚细亚一样’的前封建主义生产形态,我们并没有很好的了解。”[28]随着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徐氏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的认识日渐清晰:“中国社会自阶级社会形成以后,一直到解放后土改之前,都是以共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过渡,因为宗法的普遍存在,象征家族私有制的发展,但是公有制并未完全绝迹,宗祠和土地庙,就是公有制存在的象征。这就是马克思论证的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12]在此之后,徐氏更加关注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和中国奴隶制问题,并不断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其《论商於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一文在对存在于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村社共同体作了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明确指出,这一类型的村社,“是以一夫一妻制父系家庭,在土旷人稀土地公有的条件下,合耦而耕,共同分配生产物的耕作制的社会。这样的村社,自商代以来绵延至十六七世纪的明、清时代,前后将及三千余年……这和十九世纪存在于印度的村社共同体,十分相似,它们都是属于同一类型的社会。这样的村社共同体,就是构成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30];并强调指出:“中国社会,是从村社共同体发展起来的,它与印度有共同的广阔基础,应属于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的奴隶制是从徭役制度上产生的,它与古典的希腊、罗马的类型完全不同。现在我们要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就应当遵循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古代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重新研究中国历史的起点。”[30]在《对古史分期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文,徐氏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了最后论定:“夏、商二代的奴隶制,都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类型,在专制君主政体之下,统治着广大的农村公社,奴隶主不改变当地人民原有的社会职能和生活方式,只要求贡纳一定数量的生产品并负担各种徭役。”[16]至此,徐氏在对村社共同体和夏、商奴隶制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独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应该强调的是,徐氏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点,在激烈的学术争鸣过程中只是一家之言,但最近有的学者继续强调指出,马克思分析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形态的方法论是从分析农村公社开始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在各个时期研究农村公社的动机和方法论,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马克思研究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形态这一方法论的科学性,而且有助于我们走出社会形态划分的争论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困境。[36]从这个意义上讲,徐氏结合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形态探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总体思路是正确的。
四、关于夏商奴隶制形态
自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开始,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是否完全相同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理论界集中探讨的三个重要问题之一。经过长期的争论,到“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争论,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它的上限究竟在什么时代,以及其特点如何等问题了”[34]57。以后,郭沫若先生曾对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对中国奴隶社会的总体认识作如是评论:“中国社会的发展,曾经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制和封建制,和马克思主义所划分的社会发展阶段完全符合。这已经成为一般的常识。四十年前,有人叫嚷的中国社会空白了奴隶制,在原始公社的废墟之上建立起封建社会的议论,早已被吹送到九霄云外去了。”[17]3在长期的学术论争过程中,徐氏长期将夏商奴隶制形态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在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下,不断作逐步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
徐氏对中国奴制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徐氏较早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一文,充分肯定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存在:“奴隶制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在东亚大陆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总是先进的,在中国的周围,没有比它更先进的来影响它,使它超越这一阶段。所以中国的封建制之前,应当有一个奴隶制阶段。不但中国有,就是在中国边区也先后有许多奴隶制的社会和国家出现。”[28]徐氏举证中国历史上先后建立的奴隶制社会和国家的匈奴、鲜卑(北魏解散部族以前的社会)、吐蕃和西夏、南诏、契丹(辽)、蒙古和满洲(入主中国以前的社会)、明代蒙古和现在(按: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彝族的历史“对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资料”[28]。徐氏指出,殷周革命和后来辽金的兴亡,在发展的过程中,“更为相似”[28],“是这两个相先后的朝代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恰好是走在同一阶段上”[28]。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史论战期间即曾有人提出的中国历史空缺了奴隶制阶段的论点被重新提出,当今学术界支持这种论点的学者似乎越来越多。事实上,在我们今天看来,“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学术命题尚有待于学术界在新的学术背景下,继续作更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学术研究的最终结论亦并非仅仅用“越来越多”和“比较一致”作最后“定论”[37]。“无奴学派”学者在“中国无奴隶社会论”的主导下,试图用新的理论对夏、商社会形态进行新的概括,并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无可否认,不少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以上探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若干学理上的疑难或不足,均有待于学术界在新的学术背景下进行更为严谨和科学的补充和深化。[37]显然,由此反过来重新审视,徐氏肯定中国奴隶社会存在的论点,并未过时。
《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一文,徐氏较早将中国奴隶社会和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发生时代作简单比较:“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到铁器时代才出现,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反而在铜器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这个距离是不容易比较说明的。”[9]徐氏研究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正是出于“使中国史上的奴隶社会问题,渐次获得解决的途径”[9]之考虑。此后,随着古史分期问题研究的全面展开,学术界对夏、商、周社会形态的认识相去甚远。徐氏在《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并批判胡适〈井田辨〉观点和方法的错误》一文中指出,诸如“周代社会性质,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在中国现代历史学的阶段上,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论题”[29]。他强调:“我们必须对人类历史有了整体观念,我们才能充分利用这一大批材料(按:田制材料),以阐明古代社会的真相。”[29]他较早地将三代剥削制度的贡、助、彻加以区分:“贡、助是适应于奴隶社会的制度;彻,是适应于封建社会制度。”[29]在徐氏看来,殷、周社会性质是有着实质性差异的。他进一步解释说:“贡,就是奴隶主对奴隶的勒索。奴隶除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以外,他所有的一切,都要贡献于奴隶主。”[29“]助,是奴隶对奴隶主的服役。奴隶除了维持他自己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外,所有的剩余劳动,都要为奴隶主所占有。”[29]同其他新史学家和唯物史观派学者相比,徐氏对殷代侯、甸、男、卫的指定服役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并将其和辽代指定服役的奴隶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比较,初步建立起独到的夏商奴隶制形态理论。以后,徐氏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28]《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的问题》[38]等文中继续阐发殷代指定服役的奴隶制理论,并逐渐建立起完善的论点体系。不少学者认为,徐氏借鉴少数民族的指定服役的制度对殷商时期的外服制提出独到的见解,“为我们指示了一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研究的正确途径”[39]。
在对殷商指定服役制的外服制研究的基础上,徐氏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一文中对殷代奴隶制和奴隶制的特点作了系统论述:“殷代的奴隶社会,是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形式。”[28]“殷代虽已经进入阶级社会,但是它的统治阶级,还长期保存着家长制氏族制度,它就靠了这个家长制氏族制度来奴役其他的部族。”[28]“它的氏族制度业经瓦解之后,它决不能抵抗在它邻近落后的而仍然保存着家长制氏族制度的部族,所以,在统治阶级方面,家长制氏族制度的存在,也是构成奴隶制的条件。”[28]“殷代内服官职是简单得很,它还不能与封建王朝相比拟。”[28]“殷代侯、甸、男、卫四服,只有甸卫二服在邦畿之内。卫服是镇压奴隶的军事贵族,甸服是被俘虏来的生产奴隶。只有这两服才是奴隶制。侯、男两服,前者是没有脱离自己的部族,后者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这两服可能已有封建制的因素了。”[28]20世纪60年代,徐氏还曾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指出,“奴隶制是从氏族社会的废墟上发生发展起来的,它是从氏族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生产出发的,它只能以极为残酷的超经济强制,在简单协作的基础上进行榨取和掠夺”[40],古典奴隶制经济“是在不断掠夺式经济下发展起来的”,“奴隶制经济虽然不属于自然经济范畴”,但“并不排斥奴隶制经济也开始孕育自然经济要素”[41],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奴隶制形态理论。
迄改革开放,徐氏在《对古史分期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文中,从整体上考察了夏商奴隶制的形态,进一步明确了“夏代是我国阶级社会的开端,是最早出现的奴隶制社会。夏人已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贵族可以多妻)。夏代广大的农村公社,是奴隶制君主专制帝国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大奴隶主只有一个,其余都是他的奴隶,所有臣民都要作为他的奴隶为他服役”,“商人虽已进入奴隶社会,但他们的氏族组织还是完整的”,“其后周公东征才摧毁了这一组织,将它分割统治”[16]等论点,并建立起了“中国的奴隶制是从徭役制度上产生的,它与古典的希腊、罗马的类型完全不同”[30],“希腊、罗马类型的奴隶制,中国古代也是没有的。最早的奴隶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了,那是家内奴隶,还算是家庭内的一个成员。进入阶级社会,家内奴隶多了,有些奴隶作为奴隶主的私属,指定一块土地分配他们去生产,向奴隶主交纳一定贡物和负担某些徭役”,“夏商二代的奴隶制都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类型,在专制君主政体之下,统治着广大的农村公社,奴隶主不改变当地人民原有的社会职能和生产方式,只要求贡纳一定数量的生产品并担负各种徭役”[42]等完善的奴隶制形态论点体系。
综上所述,在长期的学术实践过程中,徐氏通过对氏族公社、村社共同体、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夏商奴隶制形态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探索,建立起独到完善的中国前封建社会理论体系。无可否认,徐氏的论点体系仍需要学术界不断完善,其中有的观点,学术界迄今仍存在诸多重大分歧,仍有待于学术界在新的学术背景下作新的审视和进一步深入探讨。但总的来看,徐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充分发掘古代文献、考古学资料,并高度重视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材料的参照作用,在坚实的史料和科学理论基础上,逐步揭示出中国前封建社会的绝大部分历史真相,促进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前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的深入与理论体系的完善,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前封建社会形态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
标签:古代社会论文; 亚细亚论文; 氏族社会论文;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文; 封建社会论文; 文化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读书论文; 民族学论文; 氏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