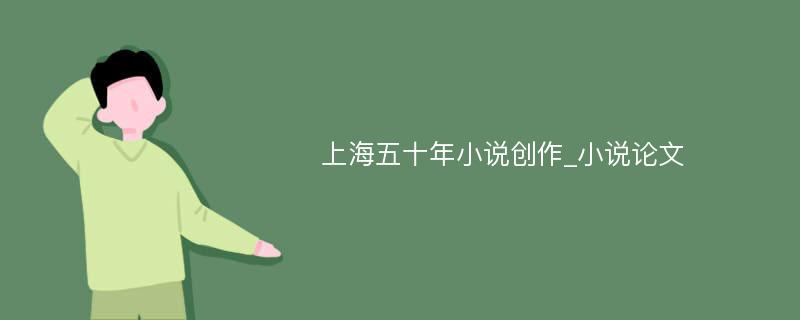
上海小说创作五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五十年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和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自从1921年,当时尚未采用“茅盾”为笔名的沈雁冰接手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并将它改革一新之后,上海就和现代小说的发展结下了难解之缘。几乎在每个历史阶段,上海都向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和重要的内容,文学史上很多重要的小说都诞生于上海,如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巴金的《灭亡》和《家》、《春》、《秋》,茅盾的《子夜》等。而从三十年代那一场“京派”、“海派”之争来说,“海派”作为一大流派而被提出,也说明在上海这块土地上小说创作的引人瞩目。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上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社会风气日益开放,都市文明逐步发达,它不仅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而且这个充满动感的大都市还为现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它不仅成为左翼革命文学的重镇,中国第一个小说创作中的现代派——“新感觉派”也产生于上海。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文学重心迁移大后方,上海形成孤岛时期,在一片肃杀惨淡的氛围中,还顽强地出现了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新海派作家。钱钟书问世于四十年代后期上海的《围城》,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1949年之前,上海在小说创作方面已经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形成了多样化的传统。
1949年,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农兵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为工农兵服务、歌颂工农兵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切文艺创作的目的与内容的中心要求。许多作家欢欣鼓舞地迎接新的生活,努力理解、适应这一新的变化。同时,按照这一全新的要求,发现、培养新的工农兵作家,特别是工人作家,没有比在这个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城市更为合适的了。五十年代出现的工人作家,应该说以上海的几位最具代表性。新、“老”两部分作家的作品构成了当时小说的“主旋律”。但是,一些具有写作经验的作家又不能不对这一狭窄的文艺路线有所质疑。解放后不久,上海就有作家提出了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人物的问题,并进行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而且,不自觉或自觉地企图逾越、冲出这些约束和限定的作品或言论也时有出现,当然,无一例外地都遭受到了迎头痛击,比如“武训传批判”和“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经过一场又一场的批判运动,作家的笔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作品则无论是内容还是所采用的写作方法都越来越单一。然而,如果是一位真正的作家,只要还进行写作,就不可能完全放弃他的独创性,无论在怎样的高压之下,他仍然会谨慎小心却又顽强地突破那些不合理的清规戒律,以自己选择的审美方式表现自己对于生活的独特感受,除非他放下了笔或舍弃了作家的立场。因此,尽管运动一次紧似一次、甚至将一切文艺创作上的不同于现行规定的表现都提到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来进行批判,尽管写工农兵、写工农兵当中的英雄人物的主旋律越来越强,调子也越来越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种规定终究未能一统天下。每逢有所松动的时候,就在狭小的空隙之间,上海仍有一些作家在不脱离革命题材的范围内,写出了一些堪称小说、甚至优秀小说的文学作品。从这一时期——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入选的小说,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方面这种一张一弛的过程和一些作家的执著精神。
谈那个时期的小说,首先得谈老作家巴金的《团圆》。这样一位当时已经在文坛奠定大师地位的作家,也不得不告别他所熟悉的题材,被纳入到重新“深入工农兵生活”的轨道中去。他来到抗美援朝的前线。这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军事题材、战争小说无论在中国小说还是西方小说中都有其较深的传统。人性往往在战争中得到强烈而集中的表现,在残酷的战场上,在“阶级性”之外常常流溢出共通的人性。当然,稍有偏离,被戴上“人性论”、“战争恐怖论”甚至美化敌人丑化英雄之类帽子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而老作家巴金小心翼翼地绕过“地雷”又不失个人风格,以细腻而抒情的笔调,在被圈定的局限之内,小心翼翼地演绎了一出悲欢离合的亲情故事。一出由于革命需要而离散的父女在十几年之后意外地团圆于朝鲜战场的故事。在战争的背景下,小说中既写了亲人牺牲、更多的年青人的伤残、战友之间生离死别的眼泪,又充满着蓬蓬勃勃的青春的活力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小说既未脱离特定的时代氛围,但是,笔触又集中于写人——不是抽象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人,而是活动于特定环境下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也许可以说,巴金大师的这篇小说为在当时条件下如何保存一定程度的艺术性,给一些作家做出了榜样。
战争题材和农村题材是解放区小说的两大重要题材,从战场来到上海的解放区作家对当时倡导的这两方面的题材的写作驾轻就熟。当时上海倒多亏这部分作家支撑了局面。
孙峻青、刘知侠、吴强写的军事小说,在全国范围内也属名噪一时的佼佼者。孙峻青收在《黎明的河边》和《老水牛爷爷》两集中的短篇小说的题材,绝大部分都与战争有关,有的是从正面或侧面表现战争,更多的是写军民关系,写后方根据地老乡和子弟兵的生死攸关、生死与共的关系和感情。他的这些短篇与另一位也是擅长以短篇的形式写战争题材的山东作家王愿坚形成一南一北的对照。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是一部以叙述轻快流畅、故事情节惊险、既符合“大方向”又好看的长篇小说。它不但很快就被改编成电影,而且还开了“畅销”小说的先河,是上海第一部印数最高的小说。吴强的《红日》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战争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写的是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作者视野宽阔,小说气势恢宏。这不仅在于它表现了从军司令部决策到全军行动的全过程,更主要的是着意于刻画从军长、各级指挥员到基层战士一大批人物,形成了一个人物长廊。这得益于他长期部队生活的经验,特别是他的高层领导工作的经验。他熟悉部队中自上至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加以他具有来自三十年代的写作训练,他力图表现不同的人物在面对战场的生死考验时的不同反应,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心理上。他想写不同的人,还想写人的复杂的真情实感。《红日》中出现了一个被胜利的狂欢冲昏头脑,打了胜仗之后喝醉了酒摇着帽子骑马招摇过市的解放军连长的形象。这位连长石东根自然在所难逃“歪曲解放军英雄形象”的指责,但是这个形象倒是书中最生动可感令人历久难忘的。小说还出现了敌方高级将领张灵甫,也看得出作者竭力避免使之概念化小丑化的企图。尽管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受到约束,但他们都透露出生活的气息,具有或强或弱的艺术性和打动人的力量。
尽管上海是中国开埠最早、最大的现代都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上海大多数作家还是来自农村,熟悉农村。城市题材小说一直比较薄弱。1949年之后虽大力倡导让工人阶级登上文艺舞台当主人,但一时也未能改变这种局面(这一点下面再说),卓有成绩、且能独树一帜的倒在写农村生活的方面。老作家在这方面虽勉力为之,却存在困难,童少年记忆中的农村生活已不符合当时号召描写翻身当主人的新农民生活的要求,而以“深入生活”作家采访方式得到的素材难以得心应手。比如王西彦也曾以土改为题写了《春回地暖》,毕竟似乎隔了一层,而不如他那些写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我们这里所选的两位女作家菡子和茹志鹃的两个短篇《万妞》和《百合花》,可以算得个中翘楚。是不是大多数女作家在观察与感受方面都格外敏感细致,而且对政治和阶级斗争缺少兴趣,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疏离回避的态度,所以她们能够处于战争中心漩涡的农村,在残酷而紧张的战争间隙中寻找到一些温馨的故事和相濡以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菡子的《万妞》以很短的篇幅描绘了一幅老解放区军民之情的恬美的图画。这篇小说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的语言功力。短篇小说更加需要语言的凝练。菡子不愧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欣赏她的文字都是一种很好的享受。茹志鹃的作品则是值得特别提出的。她的成名作《百合花》曾在文坛引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篇以解放战争中军民关系为题,又是发表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的作品,却完全摒除了狂热浮躁之气,甚至将烽火硝烟都推至幕后,而是以“清新俊逸”的笔致细细地刻画了一段军民之情。战争打响之前,一个尚未成年的腼腆的小战士向村上新娘子来借被,但是战争结束之后,惊鸿一瞥的小战士已经牺牲,曾经调侃过他的新娘子泪水涟涟地用陪嫁的新棉被包裹他已经流尽鲜血的年轻躯体。我之将它归入写农村的小说(其实不该做这种什么战争、农村题材的划分,只不过是为了论述行文的方便),只不过是它们(也包括菡子的小说)都略去了残酷激烈的战争场面,她们实在写的是农村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包括在生死面前所流露的人情人性。写这样普通的人普通的事普通的喜怒哀乐,这就与当时流行的豪言壮语以及后来进一步发展的“假大空”大相径庭。这篇小说遭到非议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没有当时身居文化部长的前辈作家茅盾慧眼识英雄,给予鼎力支持,这篇小说很可能会夭折。尽管它幸免于难,而贬斥它对抗“重大题材”专写“儿女情家务事”的责难却也一直不绝于耳。茹志鹃的可贵之处在于她的坚持,她既未停笔,也没有顺从时尚改变自己的写法。她仍然坚持以小见大的写法,仍然坚持抒情的写法,仍然写大时代的小浪花。不但表现战争年代的题材如此,写当时正高歌猛进的公社化大跃进的题材也如此。她避免诠释、宣传、歌颂什么运动,她只是写大变动背景下的凡人小事,写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在变动中的生活变化和感受。这种坚持不仅使她的作品免于急速地被淘汰,而且那种摒除流行的宏大叙事、专注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取材、视角和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的独立不羁的精神,还对后来以迄于今的上海一些作家的小说写作,发生了重大影响。
这里选了两篇当时上海最有代表性的两位工人作家胡万春和唐克新的小说《骨肉》和《沙桂英》。按照当时的文艺指导思想培养教导出来的作者,难免带有当时规定模式的痕迹。不过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中,还不时闪现出他们的艺术感应能力。胡万春可惜后来越来越热心于配合、演绎政策。我们选了他一篇早期的作品《骨肉》,虽嫌单薄但还较朴实。《沙桂英》写技术革新的红旗手倒别具一格。从作品看得出作家不肯拘泥于人物对技术的钻研改进(尽管从中也看出了作者对纺织机器的熟悉),他力图将焦点放在人的身上,围绕沙桂英、邵顺宝和新嫂子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来突现人物的性格。小说的前半有很不错的表现,可惜结尾显得牵强而乏力。这两篇作品可以作为反映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那一群体的生活的见证。
尽管五十至六十年代对于文艺方面的控制日益加强,但是在一次次的运动当中总还有松动的间隙。一些作家总是千方百计企图突破限制,表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表现解放之后的资产阶级生存状态的《上海的早晨》,就是在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声中诞生的。由于作者周而复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熟谙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小心掌握笔下人物的进退,未致翻船。倒是写革命知识分子的婚姻爱情悲剧的两个短篇小说丰村的《美丽》和阿章的《寒夜的别离》被打成了大毒草。尽管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非常革命,都在革命利益面前牺牲了个人的爱情,但是,这不仅未能使它们免除厄运,而且从此爱情成为写作的禁区,战争造成的夫妻失散成为对于革命的控诉。虽然后来三十年代名斐一时的老作家师陀,又迂回曲折地写了一个历史小说《西门豹的故事》,但也不能幸免被批判的命运。至此,能够发表作品的作家已寥寥无几,“文化大革命”的鼓噪声已隐隐可闻了。
及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之后十年,虽然全国文艺界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由于历史和当时现实的种种原因,上海似乎受灾最重,可以说是落得个茫茫大地真干净。如果说,有的地方或者还有手抄本于地下悄悄流传,或者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还有个别可以称得上是文学作品的小说出现,而上海则只有《朝霞》、《虹南作战史》作为反面典型留下来了。
承受压力最大的地方,往往反弹也会更强。七十年代末,文艺方面的“拨乱反正”还阻力重重的时候,后来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开端的“伤痕文学”却诞生于“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最重的上海。除去据以命名为“伤痕文学”的同名小说、卢新华的《伤痕》之外,作为“伤痕文学”代表作的《枫》(短篇小说,郑义作)、《于无声处》(话剧本,宗福先作),几乎同时集中发表于上海。今天重读《伤痕》,不免感到它浅显粗糙,但在当年它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是由于它一反“假大空”的模式,首先站出来揭开人们身上和心里的累累伤痕,直接了当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血泪斑斑的控诉。特别是它通过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母女情的纠葛来体现“文化大革命”对于人性的戕害和扼杀,引起读者的共鸣更为强烈。
如果说这篇出自年轻作者之手的处女作还未免有嫌稚嫩,那么接踵而来的戴厚英的《人啊,人》和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就成熟多了。他们为上海的小说写作开创出一个新局面。她们不仅展示了上海作家对于历史的深刻的思考能力和严肃的思考态度,而且还表现了她们在表现形式上的创新精神。《人啊,人》是以长篇的篇幅描绘了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一群知识分子的痛苦的生活和思想经历,反思了人性和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由于作者长期从事评论工作,小说也偏重理性思考。虽然对于她在小说中所表露的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与诠释,读者之间有不同的评价,但它毕竟是第一部正面表现人道主义这一关系人的根本命运的主题,因而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茹志鹃个人写作上的一次大解放,而且为后来的上海小说的发展开创了新路。她在这篇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解放是双重的:思想上和手法上的双重解放。小说围绕着一个农民和一个干部长达五十年的关系,提出了过去为老百姓出生入死的干部、共产党员怎么会变得置农民生死于不顾了?她寻找演变的轨迹。她认为问题不仅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随着她的思考,她的笔触在时间上大幅度跳跃,从当前到大跃进时期,再到战争年代。它几乎是最早穿越“文化大革命”,反思到更早以前的某些历史教训的作品。以“清新、俊逸”著称的她怎么会变得如此沉重?其实不难理解,她原来不是就具有那样一种独立不羁的精神吗?在压力重重的五十年代,她还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始终保持自己的艺术见解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一旦闸门半开(当时还处于“两个凡是”没有完全解决的时候),她自然会更加放开手脚地表现她对于生活的感受、体验、认识和思考。这篇小说不仅在突破思想禁区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它从“文化大革命”朝更前面的历史进行反思;而且它所采用的时间交错的叙述方式也是对现实主义写作规范的突破。在上海的小说发展中,茹志鹃贯穿了前十七年和后二十二年两个时期,成为承转两个时期的重要作家。
与“伤痕”文学几乎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还兴起了所谓“知青”文学。这类作品既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上山下乡的年青人所写,写的又都是他们各自的经历。由于“知青”人数众多,几乎囊括了整整一代人。他们分布的领域广阔,遭遇又各异,因而这些凭真情实感写出来的小说色彩斑斓。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代“知青”又不断要面对新的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因而“知青”小说形成历久不衰的局面。不少后来成为上海创作中坚力量的作家,几乎也都是由此起步、脱颖而出。首先要提及的是竹林。她的《生活的路》是第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这部作品的命运和小说主人公的命运一样地坎坷,在茅盾和韦君宜的大力支持下才得问世。这位作家二十年来坚持在上海郊区生活,最近发表了具有上海附近农村的文化历史和风俗特点的长篇小说《女巫》。后来以长篇小说《丹青引》获得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的王小鹰的写作生涯也是从写黄山茶林场的知青生活开始的。以文体著称的陈村也是以他的《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引起人们关注的。叶辛的《蹉跎岁月》作为一部细致地描写了上海知青在边远地区的生活遭遇的小说,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成为“知青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在“知青”题材的小说中,似乎是一部“迟到”之作,它出现的时间较迟。它的主人公的“知青”生涯已接近尾声,正坐在火车上回到他从小生长的城市。应当说,这部作品在众多的“知青”小说中并不特别厚重,但它却为“知青”小说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从某种意义来说,八十年代以后,经久不息的“知青”或“后知青”小说,反反复复抒写的其实正是王安忆在这里提出的问题。返城以后怎么办?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知青的生活已成历史,而作为这场运动中的亲历者,他们的故事,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以及过去经历的后遗症等等,还远远没有结束。王安忆以她“69届初中生”和并不长久的知青经历,却率先敏感到了这一点。这似乎再一次印证了我们的看法:上海作家由于天时地利的原因——即由于上海处于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上海的文化传统对于作家的眼界的影响,往往能在有意无意之间对现实生活做出敏锐和具有个性的反应。这种品性与才能在王安忆身上体现得特别鲜明,并且在这之后一再表现出来。八十年代中期,在文坛一片创新声中,她不动声色地连续发表了《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岗上的世纪》,在寻根热中,她的《小鲍庄》更是后鸣惊人,成为寻根小说的压轴之作。
除去对于时代变化和社会变迁做出敏感并独具个性的反应之外,上海作家的另一大贡献则是对于都市生活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的关注和表现。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城市文化自然相应不够发达,直至三十年代才有表现现代城市的小说在上海出现。也许可以说,三十、四十年代那一批描写现代城市生活的小说,是上海作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贡献。1949年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之后,人们本当期望这类小说有更大的发展和收获,但它却随着“大上海的沉没”而衰落了。整整三十年间,写上海这个城市的小说,除去《上海的早晨》、《春风化雨》、《火种》等寥寥可数的几部之外(《火种》还主要是写二七大罢工的),剩下的只有工厂、车间、技术革命、劳动竞赛……总之,只有一片机器声。幸亏还有一部《上海的早晨》,它以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上海解放时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情节线索,多方面展现了上海工商业的几大巨头及其家庭在剧烈变化中的社会各个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它在描绘社会新气象的同时,为历史留下了关于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的记忆,这几乎是惟一的“正面”描写城市,称得上有城市意蕴的作品。“城市”虽然在小说中“退场”,但并没有从人们、从后来成为作家的人们的记忆中消失。随着王安忆笔下知青的返城,它们开始逐步浮出地面。说是逐步,因为几十年来,不但资产阶级被宣布为反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之,凡是产业工人之外的市民一律被排斥于表现范围之外,所以他们再度出场必然是谨慎地审势度时,小说中先出现的是以里弄为背景的城市生活,然后再是花园洋房,再是宾馆、酒店、咖啡厅、证券交易所……
在《本次列车终点》之后,王安忆一系列的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都是依托于里弄的。对于上海这个城市,王安忆有她独特的感受、理解和发现。她认为这个城市的性别应该是女性。她认为里弄是这个城市的象征和“中流砥柱”。它营造着这个城市的氛围,并且是这个城市的规则和传统的承传者。在她眼中,里弄之于上海似乎正如四合院之于北京一样。《墙基》、《好婆与李同志》、《雀巢鸠占》、《逐鹿中原》、《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等等,都是以女性为中心,写的是发生于里弄的婆婆妈妈叽叽喳喳的故事,自不必说。就是《流逝》写的虽然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抄了家的资本家儿媳妇的对家庭挽狂澜于即倒的故事,《长恨歌》写的是曾经当过国民党官僚外室的末代上海小姐在解放后的辗转生涯,她也没让她们进入上海的所谓上层生活。她们仍然属于小家碧玉。即使她们曾经偶然地攀龙附凤得过几个遗产,但她们一生的活动中心仍在里弄。《文革轶事》最能体现王安忆对于里弄的理解与诠释。她一反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通常写法,她描述的不是政治暴力对于既成文化的彻底的横扫,而是表现它所未能扫及的角落里的“小人物”——包括“资本家”的不起眼的家庭,如何在风暴边缘千方百计地保全自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固有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说,依照王安忆的理解,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不同阶层、不同社区都各自形成一套为人处世的规范和生活习俗,这些看来无形的准则却十分柔韧,远比政治力量坚实而顽强,远非一场风暴就能如数瓦解的。这大概也就是民间社会的生命力。
八十年代之后新起的作家中,不少人将目光转向城市中的普通人甚至最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以赵长天的《不是忏悔》来说,它的主人公的身份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工厂的厂长,其实它所表现的还是上海这个城市里的普通人的家务事,儿女情。如果说,王安忆的“里弄”和赵长天作品中的场景大多数还属于“上只角”,那么,还有更多作家的作品背景则是“下只角”的老旧破败的石库门,甚至是棚户区。生活其中的人物当然都是体力劳动者和他们的后代。其中不乏特色鲜明的作品,比如沈善增的《正常人》、王晓玉的《阿花》、殷慧芬的《屋檐下的河流》等。这些作品所展示的人物生存空间极为仄逼,生存条件极为艰窘,但是它们都不让人感到沉闷。这还不仅在于作品的语言生动、细节丰富,更主要的在于作者着重表现了这些辗转困境的人物身上充满了一种生存的智慧,他们大都泼辣、有生气,而且具有幽默感。这里顺便提出,我们在这个选本中选入了殷慧芬的《厂医梅芳》,她所讲述的上海工厂中的女性的故事,迥然不同于过去的所谓工人创作。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上海的迅速发展,上海的疆域不断向外延伸,彭瑞高的表现这些城郊结合部城镇生活的小说别具一格,语言特别生动。这些作品都从各自的角度,在小说领域中拓展了“上海”的空间,丰富了“上海”的内涵。
如果石库门无形中成为上海的指称,略去了都市的繁华与喧嚣,那就不能完整地体现作为金融、工商业中心的现代大都市的上海。程乃珊是最早缅怀寻找旧上海作为大都会的流风遗俗的一个。她的《蓝屋》、《女儿经》,通过对于资本家的后代的命运衍变的描述,隐约透示出这座现代城市的历史变迁。她的另一部长篇《金融家》则在塑造上海第一代现代金融企业家的同时,连带更为丰富地表现了上海这个都市发展的侧影。另一位作家孙颙更熟悉和更有兴趣的则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另一个重要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上海的知识分子与北京及其他内地的知识分子阶层有所不同,他们除去出身世家与传统文化有着血缘关系之外,往往又接受了西洋文化并且参与现代文明的创建。因之,他们的命运与上海的发展与变化常常有着密切的关联。孙颙的《雪庐》和《烟尘》描写的就是这个阶层的昨天和今天、前辈和后代,以及他们中间不同的人在历史急速变化转折中的迷惘、失落和追求。这两部家族史式的小说并非为我们提供多姿多彩的都市的声光色影,而是企图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了解上海的今昔。
发表于八十年代末的俞天白的《大上海的沉没》,这个标题就振聋发聩,它抓住金融这一大都市的命脉,通过它的兴衰评说上海的浮沉。小说的艺术质地还比较粗糙,但是它气势宏伟,展示了一大批大大小小的敢想敢干的“冒险家”的跃动着的野心,它预示了正是这一批人的呼风唤雨会使大都市上海重新浮出海面再现辉煌。不过,吴荪甫式的人物,除去俞天白在写他们的发家史的系列,在其他小说中还很少见,倒是随着社会转型而出现的所谓“新市民”在一些评论者和小说家联手倡导下纷纷登场。何谓“新市民”?似乎各说纷纭没有统一的界定,洋行小姐?白领阶层?正在向发家致富奋进的个体户私营业主?总之大概是那些有别于作为“老上海”的“基石”的、繁衍于石库门里弄的“旧市民”,是那种对于现代都市文明最敏感、接受最快、物质欲望最强烈、将要成为大城市的中坚力量的弄潮儿。由于这一人群刚刚崛起,还处于“暴发”阶段,因此,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也还未规范。套用作家格非一部小说的题目,他(她)们高高竖起了“欲望的旗帜”。但是,有的人在急急地追求着官能享受的同时,内心还存在着纠缠不清的矛盾与惘然——或者为自己的自尊心受到某种伤害而感到委屈,比如陈丹燕的《吧女琳达》,或者沉浸于酒红灯绿的包围中却感到某种填不满的空虚,比如唐颖的以《丽人公寓》为代表的系列。而更年青一代的作者笔下的这类人物,则表现得更为迫不及待和直接了当。他们在金钱、物欲的驱赶下,几乎心无旁骛,不择手段,不惜付出任何代价,飞蛾扑火一般直奔目标。他(她)们对于“目标”的专心致志,不免让人想到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蓝天绿海》,只不过后者在当年表现的是奋力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争取个性解放的精神追求,而前者则只剩下对物的追求。它们呈现了物质匮乏过久的年青人面临花花世界的疯狂状态,他(她)们还来不及思考过度的物欲对于人性层面的影响。不过,呈现这种现象本身也可让读者思考。
此外,走出了国门的王周生和彭小莲的小说又给我们带来了在异国的生活体验,特别是彭小莲的小说,无论是写于国外还是国内,都从骨子里溢散出一种现代人的紧张、焦虑情绪,和对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所感到的绝望。
除去“写什么”之外,在“怎么写”方面,上海作家也多有建树。也许由于上海是新小说的发源地,小说的传统源远流长,因而尽管自五十年代以来,不断地对原有的小说观念进行“摧枯拉朽”的整肃,但是,上海作家始终未能忘怀“创新”是文学的生命这一原则,总有一股压抑不住的跃跃欲动之势。1962年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稍有松动之势的时候,电影理论家瞿白音就公开发表了《创新独白》,大声疾呼改变创作萎缩状况的关键在于“陈言之务去”。茹志鹃当时的一系列小说正是创作方面的例证。它们之所以至今还有生命力,正在于她不甘于流俗,敢于寻找独特的视角,以独特的方式表达独特的感受。在万马齐喑的禁锢时期尚且如此,及至进入新时期之后,上海作家在“怎么写”方面的探索立即为之活跃。首先应该提及的是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曹冠龙的《锁》和陈村的《一天》。新时期文学复苏伊始,大多数作者急于揭示“伤痕”,进行控诉,还顾不上考虑艺术技巧,但是这几位作者在叙述方式、风格、语言上都显示出了与众不同。《剪辑错了的故事》不仅在“反思”的内容方面大大深刻于当时的同类作品,而且作者所采用的时空交错的方法更有力地传达了她所要表达的内容。新起的年青作者曹冠龙和陈村不同凡响之处不仅在于构思巧妙、描写精致,更为主要的是他们所采用的叙述方式、文体和语言和他们作品的内容恰相契合、相得益彰。特别是陈村的《一天》,作者以一种堪称单调、不断重复的句式,絮絮叨叨地记叙了主人公琐碎、暗淡而沉闷的一天的生活。而这一天也就是他、也是最最普通的人的单调而无限重复的一生的日子的概括。陈村在这篇小说中显示出了他有意识地在文体上的新探求和对旧有模式的突破。结构的单纯和叙述的沉闷都是他为了夸张地表现“庸常之辈”的几近卑微的生存状态,而经过匠心经营的结果。这篇不足万字的作品可以称得上当代短篇小说的经典。从琐碎处入手,以一种幽默甚至带有自嘲意味的态度观察周围的人包括自己的生活,并且不断地打破原有的叙述方法成为他写作的一贯追求。他的长篇小说《鲜花和》正是他这种追求的结果。在这部小说中,他以一种随笔的形式进行结构,又是对于传统小说作法的一次突破。
1985年方法论的讨论在全国铺天盖地而来,文体、叙述方法的革命也掀起热潮。其始作俑者应属马原,他在以《冈底斯的诱惑》等为代表的小说中所运用的“叙述圈套”,是最早的对传统小说叙述方式的颠覆。具有三十年代现代派传统的上海作家,自不会落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应属格非和孙甘露。他们的名字和余华、苏童一起进入读者的视野,随后又归入同一流派,成为新时期文学中十分瞩目、也非常重要的流派——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如果说异峰突起的先锋小说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对小说文体进行各种极端的试验和对传统进行大胆挑战,那么,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则是其中最为极端的作品。小说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写法,置人物、情节等传统小说的基本要素于不顾,甚至放弃了对语言常规的遵循。通篇由五十多个“信是……”的句子以及变幻莫测的诗意描写和意象所组成,表现了小说家奇特的想像并构成了小说写作中一个前所未有的奇特的景观。如果说,以几近“决绝”的姿态反常规是孙甘露小说的基本写法,那么,同样以先锋小说著称的格非的作品则仍有一定的故事性,只不过他的小说情节扑朔迷离,在引人入胜的同时也将人引入迷阵。《迷舟》、《青黄》无不如此。在《青黄》中,对“九姓渔户”如烟往事的兴趣和追寻似乎是推动情节发展的线索,而其实那不过只是一个“契机”,小说不断地从一个事件引向另一个事件,从一个故事过渡到另一个故事,“结果”始终在延宕之中。因此,小说成了一个叙事的迷宫。不难看出,这里有着博尔赫斯式的“交叉小径”的痕迹或影响。而从孙甘露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从卡夫卡、巴思到巴塞尔姆那一派作家的流韵。可以理解,过去闭关锁国几十年,一旦国门打开,西方几十年所经历的文学流变、形式更新一涌而入,加以许多作家渴望“让世界走近我们,让我们走向世界”,因而,有些作家的文学实验受到间接或直接的影响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或者还应指出,形式革命从来不限于形式的意义,往往也是意识革命的一个表现。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在当代中国的语境和条件下也是如此,这是无须赘言的。
在这一借鉴西方现代派的热潮中,上海作家中还有一位也颇引人注目,那就是“后知青”作家李晓。李晓写作开始较迟,而且最初写的也不是当年的知青生活。他先写的是知青返城后在新的环境里遭遇到的人和事,然后才回溯既往。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从不以控诉的情绪和姿态去写既往的历史包括上山下乡的生活,而是将感情隐去,以夸张的手法、揶揄的笔调去表现时代的荒谬,将笔力集中于那一代人身不由己地卷入的、以及至今仍在不断遭遇到而且无以摆脱的种种荒谬境况。《机关轶事》、《继续操练》无不如是。由于他对所表现的对象极其熟悉,因此写来喜怒笑骂,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从容不迫。李晓不属于那类以颠覆传统小说形式为主要特征的先锋小说家,他对西方现代派的借鉴更多的兴趣在于“黑色幽默”。他的作品的别具一格之处也正在于他对幽默的独到的领会和运用。沉重而苦难的岁月,荒谬的事物,以他所描写的那种可笑的面目出现,就更见其荒诞不经了。
与这些先锋小说家相比,从表面上看来,王安忆的小说无论在语言还是文体方面,都比较传统。其实,她对小说形式的探索和试验是始终不懈的。从《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小鲍庄》到《长恨歌》,从内容到形式一变再变。这种变化不仅由于她对世道人心的独到的发现,而且也是她艺术创新的结果。最能体现她这一特点的是《叔叔的故事》。在这部写于一个历史时期终结之后,意图给那一时代作一反思总结的中篇小说里,王安忆一改以往对描写的倾心,而代之以明显的主观叙述,并采取了一种不断地“自我解构”的结构方式,来不断地对已写下的故事提出质疑和否定。由此,小说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历史反思,将对于头罩光环的“叔叔”的讲述过程,变成了一个不断打破虚幻,显示真相的解读神话的过程。正是她这种再再出新的不断变化,使她成为贯穿新时期的重要作家。
当然,这些小说家的文体革命、形式革新也并非完美无缺,还有着诸多不足。随着时间的推进,有些不足表现得愈益明显。于是,作家对于小说写作又寻求新的变革的可能性。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除个别作家仍坚持先锋试验之外,先锋小说作为整体可以说已全线隐退。不过,先锋小说家那种勇于探索、大胆革新的精神并未就此消失。这种精神不仅对当代小说的发展已经产生了而且将继续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九十年代之后从“新生代”到“私人写作”更加层出不穷的求新求变,正是这种变革精神的继续。而它们之所以获得如此的宽容和接纳,也正是由于先此的小说变革家已经冲破了固有的小说模式,使得人们见怪不怪了。
回顾上海五十年来小说的发展过程,令人感到高兴的是上海的小说家始终保持了不断为中国新文学史输送新的内容的传统。在政治压倒艺术的年代,上海仍有作家执著地坚持艺术家的立场,而到了小说可以回归本体的时候,他们又和全国的同行们一起不断探索小说的“本质”和新形式,承担起探路者的责任。
最后我们要说明的是,在编这本选集时,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包容上海五十年来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由于篇幅、也由于我们的阅读范围或眼光的限制,很可能有所疏漏。特别应该说明的是,长篇小说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只能以选目的方式编入,还请作者和读者共谅。
(本文系作者为选《上海小说五十年》所作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