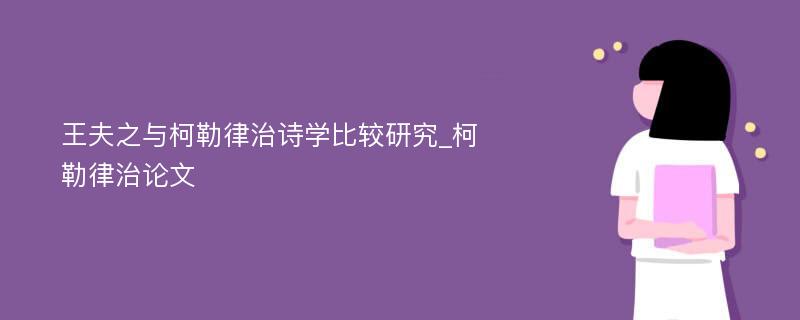
王夫之和柯勒律治诗学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柯勒律治论文,诗学论文,王夫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人孙联奎解说《二十四诗品》说的一段话有耐人寻味之处:他先是因司空氏以“谈诗小技”而“论及天地”而不无嗟讶,继而又感叹道:“谈诗岂小技哉!”〔1〕显然,在孙氏心中, 诗学既是“小技”又可以是关乎天地之道的学问。这一嗟一叹之间划出了诗学的不同层次:技巧的和形而上学的层次。刘若愚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曾以最大篇幅讨论了中国文论的后一层次。因为他相信:“在与西方理论比较中”,此一层次将“展示最有兴味的观念”〔2〕。 这也恰是我选择两位深具哲学背景的中西诗论家进行比较的原因:这一比较将最有兴味地展示中国传统诗学的文化意义。
王夫之(1619—1692)仅就其诗论成就而言,恐已堪称中国诗论史上著述至丰的巨擘了,然诗论究非其最著意之领域。其于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首先须从其哲学、思想贡献中发现之。而诗学仅为其哲学体系之一层次。如此有深厚形而上学背景之诗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中实属罕见。有的读者或许会联想到刘勰和司空图文论中的玄思意味,但刘氏和司空氏究竟不是哲学家;人们还会想到写了《清邃阁论诗》的朱熹,但朱氏论诗却远无船山那份精采,而船山作为哲人其思辨性却不逊于朱氏。这样,船山诗学就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多见的以论诗体现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模本。事实上亦如此。船山在学问上最心折关学的张横渠,而“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像张载一样,王氏从《周易》中引申出姻缊生化之宇宙论。而这“无定体观”之宇宙论,唐君毅以为乃是“将部分与全体交融互摄”之“中国文化根本之精神”的首要体现:“中国人心目中宇宙只为一种流行,一种动态;一切宇宙中之事物均只为一种过程,此过程以外别无固定之体以为其支持者。”〔3〕以下的论述中我们将看到这一宇宙论正是其论诗之出发点。
山姆·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却主要是诗人和批评家。他在英国湖畔派三诗人中,诗名略逊于渥兹渥斯,却远胜于骚塞。他的诗不像渥兹渥斯那样以平易自然见长,而是以奇诡幽深著称。提起他的名字,人们永远会记得令人毛骨悚然的《老舟子吟》中的惨绿愁红。在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他是受到德国形而上学——谢林哲学浸淫最深的批评家。而西欧浪漫主义哲学、文学的主要主题,甚至文论的许多命题,都是基于对基督教观念之重新阐释,后者则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渊源和文化的“语法”(诺兹诺普·弗莱语)。由此我们也就看到柯勒律治诗学之体现其文化根本精神的意义了。
这样两位形而上学背景截然不同的批评家却面对着相近的诗学问题,即通过审美活动克服和自然的异化问题。心物或情景或审美主客体的关系是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王夫之一再强调诗是心、物之邂逅中所产生的宁馨儿:
情景一合,自成妙语。〔4〕
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5〕
天壤之景物,作者之心目……磕著即凑。〔6〕
柯勒律治曾以如下文句描述他的诗的孕育过程:
当我思索时我又在观察自然界的一个对象,如同透过露水濡湿的窗玻璃望着远处朦胧的月亮。
我似乎在寻求,而月亮也仿佛在要求一种象征的语言以表达我心中所有而且永远存在的什么东西,而不是我在观察什么新的事物。〔7〕
诗的构思过程被柯氏描述为“寻求的心灵”和“要求着象征语言的月亮”在雾色溟濛的玻璃窗上的幽会。 这个主题也正是他的主要批评著作《文学生涯》(Biographic Literaria)的核心内容。
而且,这两位诗论家又都声言或暗示心灵和自然对象能遇合于诗是由二者的“共质性”(consubstantiality)所决定。
然而以上的契合仅呈现在最肤浅的层次上。它仅仅为我们的比较提供了根据而已,而决非我们比较的结论。我们的比较将以二者面对的共同问题为根据,首先转向对其形而上学背景的讨论。
生活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一位无神论哲学家。上文已谈到他从《周易》中抽绎出的姻缊生化的宇宙论。这宇宙是:“至虚之中,阴阳之撰具焉,姻缊不息,必无止机。故一物去而一物生,一事已而一事兴,一念息而一念起,以生生无穷……皆吞虚之和气,必动之几也。”〔8〕对王氏而言,六合之中的万象万物, 万事万念皆起于气的姻缊动荡,甚至人也只是那屈伸变化的太和之气的部分而已,所以是“空无非气……其聚而出为人、物则形”〔9〕。整个宇宙因此只是一个无始无终,不被人格化的力量启动、 操作的气的运作过程。这是一个典型的非创造的,“无固定之体以为支持”的宇宙!
在王氏的哲学中,气的永无休止的屈伸聚散之中,也确有其内在的运动规律——“理”。然船山并不排除宇宙中神秘和不可知的现象。在姻缊生化之中这种现象被他称作“神”:“盖气之未分而能变合者即神,自其合一不测而谓之神尔。”〔10〕由“神”构成二元对立之统一体;阴和阳,天和地,自然和人等等。美国学者阿列森·哈莱·布莱克(Alison Harley Black)认为:神一方面联系着变化, 另一方面又与“化”相对而暗示出某种统一性。因此,“神”是一种容许变化的统一。“神”在王氏哲学中,因上述特征,几乎被视为阴阳二元之外的第三元〔11〕。然而,从整体上看,“神”又是不与阴阳二气分离的。即所谓:“神者,气之灵,不离乎气而相与为体。”〔12〕
值得注意的是,“神”也被王夫之用以指称人类的精神活动,特别是难以测知的直觉和灵感活动,所谓“知几合神”,“自其变化不测,则谓之神……人得其秀而最灵者也”。“神”在这里成为主、客体之间的中介,因为它是天致美于人而生,而与天同质:
天,致美于万物而为精,致美于人而为神,一而已矣。〔13〕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一自然哲学如何影响了他的诗学。船山既视宇宙为一姻缊生化之过程,诗——其本质是心、物之间的邂逅妙合,就只能发生在这大化之中倏然一瞬间的统一里。这种心物情景间之妙合,也就是“神”,所谓“合内外者,化之神也。”这是一种在姻缊聚散之中不可测知亦不可理解的统一,也是人思维中不可解说的神秘直接性:
言情则于往来动止,缥缈有无之中得灵蠁,而执之有象,取景则于击目惊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落笔之先,匠意之始,有不可知者存焉……。〔14〕
在天地间的奕奕流光之中,诗人在注盼间会突然触到“神”,正所谓“磕著即凑”。“神”带来一种转瞬即逝的心物间的“凑泊”。在这“动止”、“有无”之中和“分合”之际的刹那间,心灵和对象间的界限消失了: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15〕
一首绝妙好诗就体现了情景于恍惚之中的凑泊——“神”。“神”又是人中之天,是诗人心理活动中不可测知的直觉:
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如“物在人亡无见期”,捉煞了也;如宋人咏河鲀云:“春洲在荻芽,春岸飞杨花”,饶他有理,终是于河鲀没交涉。“青青河畔草”与“绵绵思远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16〕
这里“神理”又是诗人心理活动中的不可知的必然,即所谓“意中之神理”,也就是“势”了〔17〕。因为是“势”,也就是人中之天,是在灵感勃发、诗情涌动之际意象间或意和象间恍惚之中的逻辑,正是皎然所谓“语与兴趋,势逐情起,不由作意”〔18〕。由势和直觉、灵感的关系使人想起谢林所说的“直觉的客观性”。其实,在柏拉图那里,灵感也是客观的。然而,由“意中之神理”和流于两间的“神理”的相关连,王夫之的灵感(即他所谓偶发之“天巧”,“数觏”)成为一种感觉型的灵感,其客观性也就不止于“不以力构,须其自来”的意义了。此一感觉型灵感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是以“兴”这一术语表达的,它不同于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中所说只诉诸深层心理和“纯绵延的时间”的直觉灵感。伫兴而发首先要“触物以起情”。对“物感”的强调使王夫之从因明学中拈出“现量”一术语以论诗。“现量”依其本人的解释为:
现者有现在义,现成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前五根于尘境与根合时,即时如实觉。知是现在本等色法,不待忖度,更无疑妄。〔19〕
要诗“因现量而出之”,无疑是强调感觉型直觉是此道的秘要〔2 0〕。以“现量”论诗的例子很多,我们且看他下面这段议论: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就作他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情因景,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21〕
这一种“即景会心”“不劳拟议”的心理状态,王氏称为“现量”,它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与感觉相联系的直觉、灵感。尽管有人表示过不同意见〔22〕,我仍然以为这种与感觉联系的灵感而不是想象才是王夫之艺术论的核心。我们在了解了主张想象的柯勒律治的诗学的形而上学背景会更相信这一点。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在其新著《中国文学思想》中以现量之景为非杜撰或非发明之景(non-invented scene), 并以此呼应他过去强调的中国诗歌的“非虚构性”(non-fictionality)。 这与我本人过去由王船山诗论推导出的中国诗歌强调即目即景,强调感觉的结论不无共通之处〔23〕。欧文写道:王氏的观点:“不仅排除了诗人为其未曾感受过的心情杜撰的境况那样一种传统的西方虚构性,而且也排除了容许诗人为其真实心情杜撰出外在环境那样一种由浪漫主义修正了的虚构性”〔24〕。欧文以为西方最早的文学理论是基于对戏剧的讨论,所以虚构性也就成为文学理论的基础;而抒情诗传统却把“非虚构性”嵌入中国文学意识〔25〕。而我们现在则从王夫之诗学与其形而上学背景的联系处也看到这种“非虚构性”的根据。天、人之间由“神理”圆成的“凑泊”是无法在“非量”(“情有理无之妄想”)中找到的。这又是船山何以在诗境中推崇“小景”:
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柳叶开时任好风”,“花覆千官淑景移”,及“风正一帆悬”,“青霭入看无”,皆以小景传大景之神。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张皇使大,反令落拓不亲。〔26〕
船山推崇的诗境是正常视域中被感触之景,而非由想象创造出的恢宏阔大之景——这实在是其形而上-诗学合乎逻辑的演绎!
在将王氏的逻辑继续完成以前,且让我们看看柯勒律治如何从他的形而上学背景中发展出他的诗学。
柯氏的思想是复杂的。一方面, 恰如罗伯特·巴特(J .RobertBarth)所言, 人们不难从柯勒律治“所有事物的共质性”原则中发现从抽象思辨返还人类经验世界的倾向,柯氏强调宗教感性即具形呈现的神性正是这一倾向的结果〔27〕。正是这种泛神论情绪使柯勒律治将精神感觉与理念等同起来。宗教象征因而是“重述式的(tautological)而非寓言式的(allegorical), 象征与被象征是在同一层面而非不同层面之上不同地表述同一主题而不是相似地述说不同主题”〔28〕。根据同样的逻辑,人类的原初想象(primary imagination)遂成为有限生命的心灵之中重复着的无限存在的神的创世活动〔29〕。
然而,另一方面,正如保罗·汉弥尔顿(Paul Hamilton)论证的,柯勒律治又呼吁将精神活动例如想象从休谟的经验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他声言哲学意识和想象的首要条件是一种导向自我意识的人类直觉:“我们从‘认识我自己’开始,以便以绝对的〔神性的〕IAM 〔我在〕结束……自我意识可能是更高形式存在的变化形态,或许是一种更高的意识,一种更高却向无限的回归。”〔30〕在这里,柯氏虽然承认主体和客体是“同质的”,却又把与神相关的内在自我意识置于外在的经验知识之上了。把发现自我视作通往神之路是一个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宗教心理学”的思想。圣奥古斯丁说:“哪里是你的上帝?你的上帝恰在你心中。不通过自身,灵魂是无法发现他的。”这也正是柯氏始自“认识自己”而结束于神的绝对存在的逻辑。
柯勒律治诗学的宗教形而上学背景可以综述如下:在柯氏心目中上帝创世和诗人创作诗歌是在同一层面上的活动。上帝是用语词来创世的,圣奥古斯丁说:“上帝啊,你说而他们被造就。在你的话语里你创造了他们。”〔31〕上帝的话语是“我在”(IAM)——在上帝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里,世界才存在。现在诗人在想象中重复着神的创世活动,诗人也是以语词来创造,他是从自我意识走向上帝的绝对存在。柯氏的诗学鲜明地体现出基督教文明被创造的宇宙的观念。
“创造”(creation)也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才被从神学引进文艺领域。仅从词源学的角度人们也不难窥到近代西方文艺学的宗教形而上学背景,而柯勒律治的诗学则是很典型的以人文主义对基督教观念的重新阐释。
这样,虽然柯勒律治同样以为人和自然是同质的(consubstantial),但这种同质性并不意味二者是同等的,而只是表明人和自然都是神在和神的永恒创造的体现。然而,只有人能凭自我意识沉思他之被创造并意识到他和自然的关连:
心灵……四处谛视着自然,它发现它自身的自然一直在探索外在的自然,而自然本身不过是一面更大的镜子,在其中他可观察他自己现在和过去的存在……而他感觉到那伟大存在的必然性,其永恒理性乃心灵中理念之根据和绝对条件,更是自然中所有相应现实的根据和绝对原因。〔32〕
这里,心灵把人引向自然,而不是自然触动了心灵。自然是一面既供他端详自己又供他端详上帝的镜子——因为上帝就具形呈现在自然中,上帝又以自身的形象塑造了这个端详的人。而把外在自然和内在自我意识整合起来的就是心灵的想象力。从其中介于主客体之间的意义而言,它对应着船山诗学中的“神”。然而“神”却是姻缊生化过程之中的现象,是不为任何人格化力量所操纵的。而想象却是人格上帝的创造活动在人心灵中的重复。上帝无时不在,无刻不在的绝对存在与个体的我思我在在想象中溶合起来,体现上帝存在和创造的外在自然也就和内在心灵整合起来。 想象力是靠象征实现了这一整合,象征(symbol)是想象(imagination)基本的工作:
一切心灵必须以象征来思索——最强有力的心灵在想象中具有鲜明的象征……象征里具有那些外在事物,那些外在性(outness)的特征。〔33〕
通过象征,想象力成为了心灵和对象间中介。自然成为心灵的象征,成为上帝无限存在的象征, 所有象征都并非是在寓言(allegorical)的平行层次之上,而是在重述(tautological)的同一层面之上呈现。
柯勒律治曾把他所说的创造的想象和“机械的记忆”区别开来。但心理学告诉我们:想象总是以记忆为基础的。而且,即使从柯氏自身逻辑而言,“自我意识”也依赖于记忆。基督教的拯救(redemption)观念把过去、现在、未来三时间的互渗原则嵌入西方文化,而这恰恰提升了个体意识。本世纪最大的比较学者艾瑞克·阿厄巴赫说:“由于肯定了末日审判之时世俗个体形象的存在,拯救观念引导出一种个体无可摧毁的永恒意识。”〔34〕而在末日审判号角吹起之时,每一个体还须面对他的过去。这一宗教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基督教理念再阐释的浪漫主义文化中的记忆主题。渥兹渥斯认为诗应当是“从平静记忆中自然涌流的情感”。他的脍炙人口的名诗《丁登寺》(Tintern Abbey)则被哈罗德·布鲁姆称为“记忆的神话”。 他的另一长诗《序曲》(Prelude)则咏叹着回忆如何拯救人类于自然。在这里,诗成为了元诗(metalyric),成为对其诗学的评注。 这个文化主题推动柯勒律治在自然中“观察自己的过去”。记忆是他的自我意识之基础:
人们只有不再以柔情蜜意回顾以往的自我之时,才会对他人负情。他们因此破碎地存在着。消灭了过去,他们对于未来而言也就死了。否则他们就是到处寻找未来存在的根据,只不在他们本身去寻找。〔35〕
帕那修斯山上的西方缪斯从来都是回忆的女儿。回忆也是中国诗人的母题之一,却鲜能成为中国诗学的命题。这是因为回忆在中国诗中主要不在于展现个人和民族历史,诗中呈示的并非线性的时间,而往往是现在这一瞬刻与以往某一瞬刻间的联想。在这以“点”呈现的时间里历史观中的线性时间和自然观中的循环时间相交而相互“妥协”〔36〕。诗人感叹自然的周而复始的青翠不谢和人的青春、生命的一掷不还。正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种时间结构在怀古诗中尤为显著。斯蒂芬·欧文在《追忆》一书中谈到的羊祜岘山堕泪和孟浩然、欧阳修等登岘山追怀羊祜就是个绝佳的例子。如欧文所说:羊祜和杜预的名字和岘山已分不开了。岘山本身已变成一座铭刻着羊祜、杜预名字的碑石〔37〕。换而言之,过往一段时间已转化为一段空间。后人走进这段空间的那段时间就与历史一段时间连系起来。这里,现在时态的感觉依然凸显。这也就是王夫之在谈到皇甫涍一首怀古诗时所强调的“现量情景”:
乃当时现量情景。不尔,预拟一诗入庙粘上,饶伊议论英卓,只是措大灯窗下钻故纸物事。〔38〕
怀古该是凸现记忆的极端例子,王夫之却仍然强调“现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王夫之诗学中的与感觉相联系的直觉如何对立于柯氏诗学中以记忆为基础的想象而成为其诗学的核心。
而柯勒律治则号召诗人们起来打倒经验主义所建立的“眼睛的专制”〔39〕。显然,那些“不可见的事物”和“形而上的真理”比知觉印象于他更有价值,因为它们直接与上帝相关。他对于荷拉斯(Horace)的讥嘲语“易感的天才”(genus irritable)这样评说:
想象力的萎弱和迟钝,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感官的直接印象的必然依赖,使心灵易染有迷信和狂热。由于缺少内在的适度的温热,这类心灵们才聚在一起凑热。而他们的本性像湿稻草一样,堆在一起才会发热发烧,要不然他们就像是蜜蜂,蜂拥一群而增高的温度使他们敏感而不安。……〔40〕
过度的感觉对于这位崇尚想象的理论家而言甚至是诗人的不幸。想象,特别是“第二想象”(secondary imagination)才是真正天才的标志。柯氏所谓的“第二想象”“与自觉意志共存……它溶解、混合、挥霍着〔感觉和记忆〕以便再创造”〔41〕,它成为“绝对自我”和“自由意志”最充分的表达:
人类语言的最美妙部分……是心灵自身活动的反映。它是在随意志移用的内在活动的固有象征里形成……。〔42〕
正是这种对于自由意志的强调使他的诗学最终走向移情论。李斯托威尔伯爵说:移情论者主张情感的外射,所以,诗“不仅是主观的感受,而且是把真正的心灵中的情感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和事中去。一句话,它不是(Einempfindung)(感受), 而是(Einfahlung)(移情),外射的动作是紧接着知觉而来的,并且把我们的人格融和到对象中去”〔43〕。柯勒律治下面的话几乎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的美学史学者的描述完全一致。他心目中的诗人——
必须将他们先已有的情怀铭印给外在世界,以便以令人满意的清晰、鲜明和个别性在他们的观照之前再呈现出来。〔44〕
一旦诗人将其人格外射到自然,自然也就逃脱不了成为“情感误置”(pathetic fallacy)或拟人化对象的命运了。此中的逻辑是:既然神按照神的模样创造了人,人在重复神的创造的想象中也就按自己的模样创造自然。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拟人主义(anthropomorphism)〔45〕。阿伯拉姆注意到柯勒律治在说明想象的作用时“最经常引用的是诗人将其生命和激情溶入感觉对象从而激活和人化自然的例子。自然‘在本质上是呆板和无生命的’,而想象则‘把人性和人类感情的标记印上自然’”〔46〕。
但这种anthropomorphism却不见容于王船山的审美观。陶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一诗中的一联“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引得他说出如下的讥嘲,其中还连带上写了“花柳更无私”、“水流心不竞”等佳句的杜子美:
“良苗亦怀新”乃生入语,杜陵得此遂以无私之德横被花鸟,不竞之心武断流水,不知两间景物关至极者如其涯量亦何限,而以己所偏得非分相推。良苗有知,不笑人之曲谀哉?〔47〕
或许柯勒律治眼中“太描述化的”法朗士诗句也比陶潜的这两句诗更拟人化些。但王夫之仍然以诗人不当“以己所偏得非分相推”,即将人性转移给了自然而责怪之。他的话无疑是偏激之语,因为他欣赏的司马彪所作《杂诗》“秋蓬独何辜……搔首望故株”〔48〕,又何尝没有此嫌?然而这种偏激却无悖于他诗学的逻辑〔49〕。
船山的现量之景已肯定了心灵的开放状态。在心物关系上,他虽未像杨万里仅执一端地强调“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50〕,却力主心物间感应的同步性而非因果性:
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絜天下之物,与吾情相当者不乏矣。天地不匮其产,阴阳不失其情,斯不亦至足而无俟他求者乎?〔51〕
这里所谓“至足而无俟他求”即已拒绝了欧文所说的“杜撰之景”(invented scene)。船山力主取景须“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52〕,反对“以頳色言情”,“于情上布景”〔53〕。然而,他也承认,诗人言情之际,既有“不谋之物相值而生其心者”,亦有“识之心而推诸物者”〔54〕。如果是后者,却又如何使诗人貌物之本荣呢?王夫之下面的话说明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他已注意到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多重联系,由此产生了兴象所包孕的多义性:
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天情物理,可哀而可乐,用之无穷,流而不滞,穷且滞者不知尔……当知“倬彼云汉”,颂作人者增其辉光,忧旱甚者益其炎赫,无适而无不适也。〔55〕
船山借“倬彼云汉”在《大雅》之《棫朴》和《云汉》所引发的不同情感说明同一之景“可哀而可乐,用之无穷”。他并未如吴乔那样简单化地推论“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因为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人们不难找到如少陵的“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啼”,或者“夙昔所娇儿……望爷背面啼”,那样的反例。船山对这样例子的解释让人感到他于诗歌艺术确是独具慧眼: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知此,则“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与“唯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情之深浅宏隘见矣。〔56〕
船山在这里已克服了囿于“物感说”论诗者的一些偏执,他已接触到瑞查兹所说到的诗的“张力”(tension)问题。 但我总感到他的种种命题都在精致地辩说诗人在言情时何以能“不敛天物之荣凋,以益己之悲愉”〔57〕,即建造一个移情论者所不曾梦到的诗学体系或王国。
我的以上比较分析旨在勾勒出中西两位诗论家的诗学与其形而上学背景的联系,因为其形而上学背景恰正体现出其文化之根本精神。船山诗学是从他的非创造的宇宙论中演绎出来,他对于诗人审美心理的理论描述严格说来不应以“创作论”名之〔58〕。正如斯蒂芬·欧文所说:在中国文化的“这个非创造的世界中,意志驱使下的制作是不适当的,是一种欺瞒:诗人关注的是真实呈现出世界的面貌,内在经验和外在感觉世界的面貌。诗人的作用在于观察出世界的条理,观察出世界的无限分化背后的模式。正如孔子一样,诗人‘述而不作’”〔59〕。我认为王夫之诗学的主要命题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对创作的非创作性解释,对表现的非表现理论。王氏的言情诗学,其实并不基于主体的表现,而基于阿列森·哈莱·布莱克所说的“有表现意味的自然”(an expressivenature)〔60〕,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个“有表现意味的自然”其实是从中国文化之传统中获得了表现性。人和自然的整一性掩盖着个体和社会文化的整一性。
而柯勒律治的诗学则是浪漫主义对于基督教观念重新阐释的延伸。当他把诗人的想象和上帝创世活动放在同一层面的时候,他是在以宗教语言表达着新的人文主义的审美理想。
阿伯拉姆曾以一对“原型比喻”(arehetypal analogies),“镜与灯”,描述西方文学思想从古典向浪漫主义的转变。现在,柯勒律治和王夫之诗学的比较使我想到中西文化中两则寓言,它们的主人公恰可以成为另一对“原型比喻”以代表柯氏和王氏诗论中的诗人。我想到的两则寓言是拉康的理论虚构“镜子阶段”和庄周的“庄周梦蝶”。拉康说,无论个体或〔西方〕文化的本体化结构都形成于这样一个时刻中:当婴儿第一次面对镜中影像时,他通过把“自我”投射为他人而得到了虚幻的自我概念。这个童稚时代的发现使人们历尽艰辛去寻找这个想象的实体——自我以及“它”对世界的主宰。对于文艺复兴特别是浪漫主义时代的西方文化而言,拉康的虚构化的理论故事确有其理论意义上的真实。
而庄周则以他的寓言暗示人们:自由不在于个体对自我的执著,而在于自我超越于一切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上。作为儒家学者,王夫之自然是承认人与物“各正性命而不可齐”的。但无可否认,王氏的诗学却继承了魏晋玄学兴起以后的审美诗学的主要成就。于是,在他以通于天人的“神理”论诗兴,反对移情拟人,和肯定一个“有表现意味的自然”的说法里,我们还是可以联想起庄周的那个美丽寓言。
注释:
〔1〕《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济南:齐鲁书社,1980), 页22。
〔2〕Liu ,Jamcs J.Y.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p.16.
〔3〕见唐君毅《中西哲学思想比较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页9。
〔4〕《明诗评选》卷五,页36,沈明臣《渡峡江》评, 《船山遗书》(上海:太平洋书店版)。
〔5〕〔55〕〔56〕《诗绎》,《薑斋诗话笺注》戴鸿森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1),页33,页33,页10。
〔6〕《古诗评选》卷五,页3,谢灵运《游南亭》评。
〔7〕〔33〕The Notebooks of Samucl Taylor Coleridge ,ed .Kathleen Cobur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Ⅱ,p.2426,Ⅲ,p.3325.
〔8〕〔9〕〔10〕〔12〕《张子正蒙注》(北京:中华书局,1975),页326,页9,页65,页8。
〔11〕〔60〕Black,Alison Harley ,Men and Nature i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Wang Fu-chih (Seattle: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1989),p.74,p.33—34.
〔13〕〔51〕〔54〕〔57〕《诗广传》(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72,页20,页68,页75。
〔14〕《古诗评选》卷五,页5上,谢灵运《登戎鼓上诗》评。
〔15〕〔16〕〔17〕《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见《薑斋诗话笺注》,页72,页63,页48。
〔18〕皎然《诗式》,见《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上册,页29。
〔19〕《相宗络索·三量条》,见《船山遗书全集》(台北:自由出版社,1972),十八册,页10454—10455。
〔20〕十几年前,我曾以“直接对象前的审美直觉果实”说明此感觉型灵感,同时亦对非量、比量进行了讨论。参看拙文《王夫之的诗歌创作论——中国诗歌艺术传统的美学标本》,见《中国社会科学》, 1984年第3期,页143—168。
〔21〕〔26〕《薑斋诗话笺注》,页52,页92。
〔22〕见黄葆真等《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四册,页184—186。
〔23〕见拙文《王夫之的诗歌创作论》及《中国诗画创作比较观》中“背拟作画与即目吟诗”一节,载《中国诗歌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页194—201。
〔24〕〔25〕Owen,Stephen,Reading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463,p.466.
〔27〕Barth,J.Robert,The Symbolic Imagina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135.
〔28〕Hamilton ,Paul,Coleridge's Poetics ( London: BasilBlackwell,1983),p.198.
〔29〕〔30〕〔39〕〔40〕〔41〕〔42〕〔44〕Coleridge,Samuel Taylor,Biographic Literaria,ed.James Engell and W.Jackson
Bat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vol.Ⅰ,p.301,p.273,p.107,p.30,p.304,vol.Ⅱ,p.54,vol.Ⅰ,p.32.
〔31〕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Trans.R.S. PineCoffin( NewYork:Penguin Books,1964),p.258.
〔32〕The Philosophical Lecture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ed.KatheleenCoburn(London,1949),vol.Ⅱ,p.2456.
〔34〕Auerback,Erich,Mimesis,trans.Willard R.Trask(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27.
〔35〕Coleridge,Friends,ed.Barbara E.Rooke (London,1966).
〔36〕此观念在拙文"Lyric Arch-occasion:Co- existence of'Now'and Then"中有详细讨论,见CLEAR(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15)1993,pp.17-35.
〔37〕见Owen ,Stephen,Rememberences: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86),pp.26-27.
〔38〕《明诗评选》卷四,页34下-35上。 皇甫涍《谒伍子胥庙》评。
〔43〕《近代美学史评述》,蒋孔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页43。
〔45〕笔者在十多年前讨论中国诗时即使用“拟物主义”与“拟人主义”相区别。但其实anthropomorphism在西方文论中已是通行术语,而我在当时并不清楚。可参见W.K.Wimsatt 和C.Brooks 的Literary Criticism:A Short History,vol.Ⅱ,p.400(Chicago:The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1983).
〔46〕Abrams,M.H.The Mirror and the Lamp:The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London:Oxford UniversityPress,1952),p.792.
〔47〕《古诗评选》卷四,页33下。
〔48〕《古诗评选》卷五,页13上。
〔49〕十多年前我曾以“拟物主义”说明王氏此一倾向。现在我知道陈世骧先生也以“physiomorphism”(相对anthromorphism)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见《陈世骧文存》(Taipei:1972),p.120。
〔50〕《答建康府大军康监门徐达书》,《诚斋集》(上海:商务影印宋写本,1919),卷六七,页5下-6上。
〔52〕《古诗评选》卷五,页12下,谢庄《北宅秘园》评。
〔53〕《唐诗评选》卷一,页9下,李白《乌夜啼》评。
〔58〕这里也包含对笔者本人十几年前对王氏“创作论”研究的批评。
〔59〕Owen ,Steph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p.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