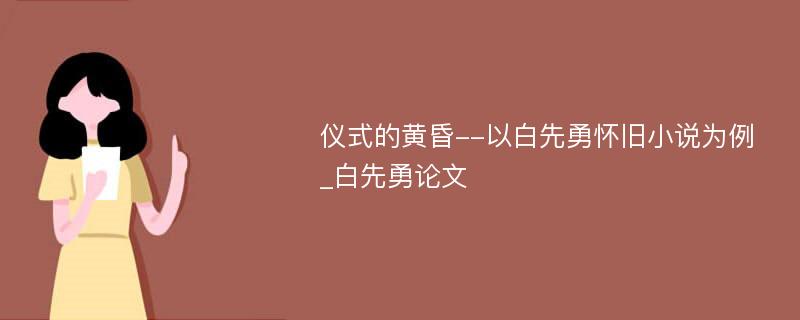
仪式的黄昏:以白先勇的怀旧小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仪式论文,黄昏论文,小说论文,白先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仪式作为历史延续的黏合剂 白先勇小说的一个核心线索,是中国历史在20世纪中期的沧海桑田巨大变迁,给各种人带来的身份危机与悲剧命运。历史的洪流周折回旋,人的生存就出现了强力的扭曲。但是人的生存必须有一个人格的延续性,因此他必须找到一个挽救历史和自我线性延续的办法,那就是仪式。生活中有意无意采用的各种仪式,是特殊的行为符号,它们具有回归意义原点的能力:仪式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复,具有修复意义错位与畸变的功能。 仪式旨在重构一种情境以连接过去与今日。一个文化中的符号与其意义解释方式(符码)的延续,可以保证文化表意方式(编码)与解释方式(解码)的稳定,尤其在社会文化发生巨变的时代。只是文化符号学中,这个关键性的储存并复制文化的元素,称为“模因”(meme),这是符号学的文化研究模仿“基因”(gene)而生造的词。是希腊语mimema(模仿)的缩短,又让人想起英文词“记忆”(memory),法文词“相同”(meme)”。①模因是携带了各种意义能够在社群文化中延续意义的“单元”,它可以是反复进行的行为和风格。 这种带着文化基因的重复,就是广义的仪式。它是某种体现社会规范的、意义再三积累的象征行为。②它能阐释日常活动中传统与变异的动力关系,同时又帮助个人主体经验与社会力量交互影响,沟通个人命运与社会环境的关联。仪式借助重复演示标准程序,遵循已经先定的时空间布局,维护历史的既有意义。因此它是世界经验的持续、稳固的保证。借此,人们得以悬置时间变化带来的各种焦虑、各种异化,从而解除文化与人格在变迁中的困惑。 虽然我们对此不一定自觉,大至整个文化社群,小至社会上每个人,都无法摆脱对广义仪式的依赖。从小事说,如果我们早晨起来,不重复某个习惯行为,喝某种饮料,我们这一天就会不对劲。这无关于身体的生理状况,而是不习惯生活被打乱。从大处说,在社会动荡个人失位的历史剧变时期,某些特殊需要的重复,是减轻我们的生存困惑的一个意义提供者。仪式,是人类为保留过去的重大遗迹,把某些曾经的过程象征化,也就是在重复中让这些实践行为获得超越畸变,而保留历史的所谓“不变的规律性”的魔力。 不仅是白先勇笔下的人物情节,他的写作本身,也就是他的生活本身,都充满了仪式感。白先勇自己说:“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了。”写作就是挽救传统的仪式。因此它的小说常用标题《思旧赋》《梁父吟》等,用古人说今日之象,拿诗赋名,作为小说题目,取其意而象征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秩序的瓦解,影射传统的日渐式微。 《永远的尹雪艳》中写道:“尹雪艳公馆一直维持它的气派,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水平”。而这种“追昔”效果是惊人的:“出入的人士,纵然有些是过了时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身份,有他们的派头,因此一进到尹公馆,大家都觉得自己重要,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的头衔,经过尹雪艳较亲切地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诰封一般,心理上恢复了不少优越感。”这是对仪式效用的最精准描述,靠某些形式(排场、派头、头衔、做派)的精心重复,历史会回归,命运的损伤可以修复。 因此,仪式是通向过去,连接现在,并且意图伸向未来的桥梁,仪式连接的点是否具有文化史的意义,就变得很重要。《游园惊梦》本是汤显祖《牡丹亭》中的一出。杜丽娘梦中和从未谋面的书生柳梦梅春风一度,醒来就相思缠绵而死。书生柳梦梅跨越生死爱恋追求,杜丽娘复活,两人结为夫妇。白先勇的《游园惊梦》则让这出昆曲成为一种文化仪式:名伶蓝田玉钱夫人赶到台北赴昔日姐妹窦夫人家宴,故旧重逢,照例戏码上演。一曲《游园惊梦》,勾起钱夫人对往事的满腹辛酸。此时钱夫人仿佛杜丽娘,在遥望隔世之情。此情此景,却又让人联想到《红楼梦》,“葬花”之后,黛玉经过梨香院,听到里面有人正唱《游园惊梦》。因此,此小说中的场面,是中国文化最精美景观的仪式性重复。虽然此一梦非彼一梦,世事无常,华日不再,只能靠仪式挽回余韵,保持回忆。 因此,仪式强调了人类的图式思维,仪式的形象再现,正是顺应强化了社会文化的图式系统:选择并加强符合图式的经验。文化意义方式的维持,正是仪式对构建图式的争夺。仪式形象的生动,携带情感氛围,使意义方式延续成行为的一致。③ 二 个人在仪式中的角色扮演 希腊语中,仪式称为dromenon,意为“所为之事”,与戏剧(drama)一词同根。④仪式确实是一种模式化的扮演活动,但与戏剧表演不同的是,它的目的在于取效,而不在于娱乐,它是具有预期价值的实践活动的再现。谢克纳指出仪式与表演的区别:“戏剧与仪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功能。仪式须有效,它要求说出话后直接且可测量的效果。戏剧在于娱乐。在仪式中动作引起动作;在戏剧中,行动产生思想。但是,仪式与戏剧这两套系统经常是很难区分,于是,凡戏剧的表演均会影响行动,而仪式则企图借娱乐激发思想。”⑤ 仪式文本与戏剧演出文本之间,可能在表现方式上几乎没有差异:二者都是用身体与情景讲故事。但是细看它们的执行者与参与者,演员与观众的关系,就会明白功能极不相同:戏剧是娱乐,而仪式追求文化延续。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游移不定,根据每次“演出”的具体情况,以及参与者的解释而定。在戏剧家日奈看来,戏剧本来就是没有内容的礼拜仪式。⑥ 白先勇小说的主人公,都曾经有过无法忘怀、也回不去的过去,现在只剩下不堪回首的记忆,人物在悲思之中,只有借助仪式才能在想象中复得乐园。究竟这种仪式是什么,其实每个人是不同的。有些仪式虽然对每个人意义不同,却是民族化、社群化的;而对于潦倒落魄的人,这种复旧的仪式感或许不起眼。但首先的条件是个人必须参与这个仪式,参与这个仪式戏剧的表演。孔子说,“吾不与祭,如不祭”,是对仪式作用的深刻理解。 《国葬》一篇说了李浩然将军的“国葬”仪式,小说主角是死者的一个老副官秦义方。他自己年事已高,想再演副官的角色也不可得。主角已死,他想参加跟随了一辈子的长官的葬礼,左右新换的年轻人,把他赶了下来。白先勇自己说:“我写这篇时,自己也很感动,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了,里面有象征性的,好像整个传统社会文化都瓦解了。” 《岁除》选取了中国人除夕夜这一特定的中国文化仪式时间,写赖鸣升到刘营长夫妇家吃“团圆饭”。赖鸣升一生有过辉煌。但时光流逝,今日穷愁潦倒,衰老而孤独,只能在老部下刘营长家的团圆饭桌上过除夕。虚幻的满足感也变成了他生活下去的支撑点。除夕是送旧迎新之时,而《岁除》的主角对“过去”固执专情,对现实本能抵触。新年虽然迫近,但这不过是别人的新年,与赖鸣升似乎离得很远,其结果,是这个悲剧人物无法跨越“新旧交替”的门槛。 本来,个人的心灵必然是孤独的,每个人的观念必然与别人不同。仪式的共同性,给了人和他人在心灵上回到过去时刻重建沟通的可能,个人的意识会随着特殊的程序,与这些文化符号携带的意义认同,产生交托感与归属感。人需要仪式,是因为我们需要在世界和意识之间建立联系。因此,个人的直接参与感至关重要,在回不得老家的情况下,围坐吃“团圆饭”代替团圆:仪式时节,只有仪式的替代,用别人的团圆,代替自己的团圆,替代的仪式参与,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三 仪式在于细节形式 在讨论白先勇的小说时,我们看到两种形式:一是小说的形式,叙述本身是一种充满形式意味的小说;二是被叙述的形式,小说中的人物,执着于形式地做每一件事,哪怕这些形式本身已经“过时”,也就是说与当前的生活形式已经不相配,也必须一丝不苟地进行。对于仪式,形式就是一切,内容倒是可真真假假,因为它是次要的成分。 《游园惊梦》中的昆曲作为一种参与仪式,聚集了一帮共享这种表演的昔日文化精英。表演是他们生命记忆的重要仪式。在这一文化社群中,表演,而且是一丝不苟重复久远年代传下的表演形式,就成为象征意义的“必要的重复”,追回昔日时光的努力,寻找这一群体的身份标识。所以一旦钱夫人唱的时候出现了“失声”,她“觉得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泉涌到头上来了似的”。自己不能参与的仪式,实际上斩断了个人与这个文化社群的联系,也失去了自我与自己生命史的联系。 仪式表演与文化记忆之间是一种互文与“重写”的关系,这体现了文化的重复与创造、延续性与不延续性,每一次的仪式表演都是对仪式内涵意义的深化。洛特曼在其《文化的符号学机制》一文中将文化分为主要面向表达的文化和主要面向内容的文化,前者以仪式为代表,后者以符号为代表。面向表达的文化……有着严格的规则和系统。⑦所谓“表达”,就是以形式为最重要的元素。 而形式的要义,在于细节。重复的细节可能表面上缺乏意义,但是借助历史的回顾,再无所谓的细节都有重大意义。《梁父吟》在描写朴公书房时,有如下几乎是过于细腻的描写:“靠窗的右边,有一个几案,案头搁着一部《大藏金刚经》,经旁有一只饕餮纹三脚鼎的古铜香炉,炉内积满了香灰,中间还插着一把烧剩了的香棍……朴公抬头瞥见几案的香炉里,香早已烧尽,他又立了起来,走到几案那里,把残余的香棍拔掉,点了一把龙涎香,插到那只鼎炉内。一会儿工夫,整个书房便散着一股浓郁的龙涎香味了。”重要的不是不厌其烦躬行本身的意义,细节的重复才形成跨越时间之桥。 再例如小说《Tea for Two》对同志酒吧的描述:“酒吧的装饰一律古色古香,四周的墙壁都嵌上了沉重的桃花心木,一面壁上挂满了百老汇歌舞剧的剧照《画舫》、《花鼓歌》和好几个版本的《南太平洋》,另一面却悬着好莱坞早起电影明星的放大黑白照,中间最大那张是‘欢乐女皇’嘉宝的玉照,一双半睡半醒的眼睛,冷冷地俯视着吧里的芸芸众生。酒吧中央那张吧台也是有讲究的,吧台呈心形,沿着台边镶嵌了一圈古铜镂着极细致的换温暖。” 为什么细节是如此重要呢?难道仪式的威力如此强大,能把任何细节都“再语义化”?卢卡契说过“在原始思维中,类比要比因果性和规律性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由类比形成的普遍化在此构成了原始思维的出发点”⑧。仪式的“思维方式”却是人类最古老的思维方式。方式不变,内容也就不变。细节的重复对于达到类比效果,其重要性超过一切。 四 仪式的黄昏 仪式本身是一个意义聚合体,整合了一系列不同意义,绝对不可能只表达单一的意义。仪式是一个“开放文本”,它的多义性和模糊性正是它的力量所在,也正是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仪式效果的一致性、持续性与稳定性。仪式意义的多面,更在于它是一种“行动方式”,它依赖的是参与者各自代入的情感,而不强加特定的解释。所以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之在,只是一种拟想,需要参与者用“如在”的态度把它唤出,让已经不在场的重新变得在场。 这一点能否做到,参与者能否从仪式中解释出相关意义,关系到仪式究竟是否有效。这是一场灵魂的冒险,但是参与者往往已经没有选择,只能固执地遵循仪式,努力争取他需要的意义。我们从白先勇小说中许多生动的例子可以看到,这一点越来越难做到,因为对参与者来说,要召回的时空越来越遥远。仪式原本应当扮演的作用,即回复生命的丰满性,把纯粹的时间空间变成社会化的时空。当仪式成为纯粹形式的“模因”时,这种意义丰满性就被掏空,被虚化,只剩下一种假定,成为无对象的象征。但这样的仪式,或许形式上就更加纯粹,因为它们是被剥夺了内容的形式,被剥夺了回溯源头可能的凝固记忆。 《骨灰》这篇小说情节的时空跨度很大,地点横跨大陆、台湾、美国,时间延续从抗战、内战直到“文革”结束,如此长的历史,需要一个合适的具有震撼力的仪式才能搭起桥梁,这就是骨灰墓葬。一个留美学人归国,参加亡父平反的骨灰安葬礼,碰见一位从大陆来到美国的老者,竟向他打听纽约墓地的价格。作者没有苛责任何人,然而老来宁愿埋骨他乡,甚至把妻子的骨灰也带来了,那么,安葬仪式还能起什么作用呢?当仪式解决不了两位老人死无葬身之地的窘况,如果安葬仪式无法解释出“入土为安”的意义,就成了一曲哀歌,悲剧意味也就不言而喻了。 由于仪式,小说《游园惊梦》中主人公蓝田玉钱夫人一生的命运,与演唱昆曲《游园惊梦》相连:她的演唱赢得了钱将军的爱情,从而娶她为夫人。而发现自己爱恋的情人郑参谋与她亲妹妹的私情,也恰好在南京的一场清唱聚会上,正在演唱《游园惊梦》时。急怒之下,顿失嗓音,而在窦夫人的宴会上演唱《游园惊梦》时,不仅再次勾起她的各种回忆,而且再度失声,无法再唱“惊梦”。对她来说,梦已醒来。因此,《游园惊梦》实际上是一曲往日不可挽回失落的象征,对昔日美好时光的无奈留恋,也只能是注定走向黄昏的仪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仪式在无法延续的时候,如果参与者们再坚持延续,只能是一种文化错位。这时候仪式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异,文化符号学上称为“转码”(trandcoding)。每一个物种的基因都有保持不被侵犯、不被改变的功能,这是“基因稳定”。文化上的配合,却是一种主观可控过程:文化有保持纯洁的本能,因为一个文化的元语言(即意识形态),拒绝或无能力解释或欣赏某些异文化的元素,不得不给予排斥。但是一个完全排外的文化,又是一个僵化的文化,因为文化之间的异系统碰撞与互渗随时随地在进行。 在没有共同一致信仰的情况下,仪式用行为界定了我们,这是一种悬而未决的符号,因为解释意义不在场而暂时团结了社群,但终究要归结于每个参与者的解释。记忆的联系,要靠个人化的解释,当社群的集体记忆越来越乏力时,个人的解释也越来越难维持。这时就出现了仪式本身降解为悲剧,甚至喜剧,最后变成反讽的可能。 另一种仪式坠落的可能,出现于仪式意义的偷换。仪式本来具有模糊多义的意义,这是对一个社会文化中各种人物获得合法连续性的途径,让他们纷纷借用原有的传统。人们明白,完全创造新仪式不可能,他们自己生命有限,只能从原有仪式借用、移植、沿袭。仪式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重复性、周期性,每一次的重复就是对前文本的引用。但仪式的规则化机制也不是坚不可摧的,每一次的仪式化表演既有正向的对前仪式文本的遵循,又有逆向的对前仪式文本的偏离,这种偏离是对仪式进行转码的努力,但是很多文化史是不能忍受转码,尤其是转码不成功反而产生畸变。《一把青》中的歌曲无法再延续,唱歌的人已经从昔日的纯情女子,变成今日醉生梦死的堕落女,而这也是《一把青》从“思无邪”的纯情民歌,变成浪荡淫曲的过程。 这就是仪式令人心惊的坠落。弗洛伊德详细讨论过这种焦虑心理,他称之为“unheimlish”(非家幻觉),此词直接对应英文的“unhomely”,虽然许多英语学者译成uncanny(中文“诡异”、“恐惑”、“暗恐”),实际上“非家”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术语。弗洛伊德说得很清楚:恰恰是因为你害怕某种恐惧,你就会不断碰到它。内心的恐惧会造成似乎客观出现的强迫性重复。每次重复或许各自有其原因,却越来越成为焦虑的根源,“非家”的原因就是仪式失效,人在世界上找不到归宿。而“非家感觉”在白先勇作品中,却不纯是幻觉,仪式对他们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漂泊离家,而仪式之所以渐渐失效,也正是因为非家感觉超过了仪式的复原力量。 克里斯蒂娃在其著作中进一步推进弗洛伊德的“非家幻觉”,她称之为“自我陌生人”⑨:自己对自己感到陌生了。克里斯蒂娃提出:每个人都会在自己身上找到令人恐怖的“非我”因素。主体性可以不稳定到这种程度,我变得不认识自己:我们经常会发现,存在于自我内心深处,是与自我相反的异质,是让我无法控制的经验。白先勇的《纽约人》中其他各篇中的留学生,是“双重离散”(double diaspora)的人物:他们从文化之根被迫两度放逐。他们可能在尘世的意义上成功,例如《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终于得到了英文文学的博士学位,面临大好前程。但他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恐怖的“非家”状态。他无爱的能力,甚至无法为母亲的死亡悲哀。到酒吧买醉的仪式,完全无法让他找到自我,他发现自己变成一个自己都无法辨认的陌生人。 所以仪式不得不强调一丝不苟,目的就是在汹涌而来的变化潮水中,显示文化的延续力量,显示人类符号表意的稳定性。现代人的一般历史倾向,是重视创新与“进步”。诚然,创新是现代文化的推进力,但是一味踩油门会带来倾覆的危险。重复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的作用,被远远低估了。应当说,在重复与创新这二元对立中,重复是恒常的,“非标出的”(unmarked),作为背景出现的;而创新是作为前推(foregrounded)出现的,标出的。重复的垫底作用,往往被人忽视,但是没有仪式重复,文化无法存在,创新就没有起飞的跳板。 白先勇小说最大的震撼力,是仪式的不再可能,更是知仪式之不可能而为之:仪式本身如落日一般,任何重复最后会走向不重复,因为任何重复本质上包含了变异的因素。由此,与主人公的命运一样,仪式也走向了黄昏。《国葬》是《台北人》的最后一篇,这篇描写小人物(副官)坚持仪式的简朴小说,意义深长。如果说整部《台北人》是一首安魂仪式,《国葬》便是这首曲子的终曲。白先勇自己说,他写完《国葬》感到一种逼人的凄凉,传统文化可能到此就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天读来依然感动,正是因为他在接受无可奈何的结局,同时又在坚持。 或许重复仪式最惨痛的演述,是“西西弗斯神话”。人类历史上不乏没有结果的劳作,辛苦万状而似乎一切白费。加缪为这本书写的序中尖锐地指出:如果人生存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真相,没有价值的世界中,他的生存只是无益的重复努力。只有当重复形成“演进”时,重复才有意义。加缪坚持存在的荒谬,在全书最后,他却给出一个高昂的乐观调子:“迈向高处的挣扎足够填充一个人的心灵。人们应当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⑩ 是的,坚持仪式,终将突破其有效性不可避免的流失,由此延续了人类的“文明”。中文称人类的这种集体意义为“文明”,“文”字并非中文用词错误,因为人类社群的进步必须靠仪式符号,籍仪式符号之“明”,意义的累积才是演进的。我们也像加缪想象西西弗斯一样,想象白先勇是幸福的,因为他明知其不可为还是在他的作品中,用仪式的写作坚持意义的延续。 ①Richard Dawkin,The Selfish Gen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192. ②③参见[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④Jane Ellen Harrison,The Transition from Ritual to Art:The Drome non and the Drama,Kessington Legacy Reprints,2010. ⑤Richard Schechner,The Future of Ritual.Journal of Ritual Studies,1987(1). ⑥Ronald Hayman,Theater and Anti-theater,London:Martin Secker & Warbury,1979,p.93. ⑦Lotman,On the semiotic mechanism of culture,Soviet Semiotics and Criticism:An Antholog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217. ⑧[匈]卢卡契:《审美特性》,徐恒醇译,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7页。 ⑨Julia Kristeva,Strangers to Ourselv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210. ⑩[法]阿尔贝·加缪:《西西弗斯神话》,闫正坤、赖丽薇译,新星出版社20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