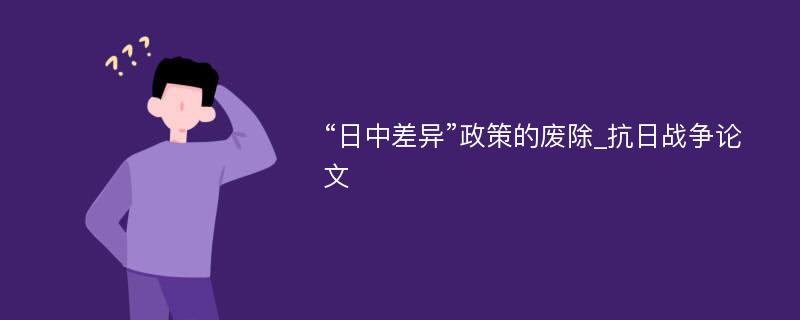
日本与“中国差别”政策的废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国论文,差别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6)02—0218—06
艾森豪威尔上台之后,对杜鲁门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进行了修改,其主要特征是缓和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管制,但在对华禁运上,仍然继承并在实际上加强了杜鲁门政府的“中国差别”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并没执行太长时间,由于遭到巴统各成员国的反对而于1957年被废除。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艾森豪威尔时期“中国差别”政策废除过程中的日本因素。笔者认为,日本在“中国差别”政策的废除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影响表现在三方面:首先,作为东亚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差别”政策与美国对日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矛盾,这为它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其次,在“中国差别”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日本通过内部侵蚀的方式一点点削弱了“中国差别”政策的基础。最后,在废除“中国差别”的谈判过程中,日本以一种谨慎而又坚决的方式,与其它巴统成员国一起努力,最终导致了“中国差别”政策的废除。
一
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保留并加强“中国差别”政策的那天起,有关这一政策的争论就从未停止。争论的起源在于“中国差别”政策与美国对日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
朝鲜战争停战之后,西欧国家强调,全面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自由世界在与共产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应该把“经济发展优先作为长期战略”,缓和东西方贸易管制。与这一要求相应,1953年5月25日,美国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了《经济防卫政策考察报告》,即NSC152号报告,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了 NSC152/1、NSC152/2,直至1954年6月18日的NCS152/3号文件,标志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基本完成了对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其基本特点就是缓和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管制,加强对共产主义中国的贸易管制。NSC152/3号文件提出:第一,“我们专注于对苏联战争潜力有重大意义的物资和设备,不再要求管制那些次要战略物资”;第二,“新政策认为,我们面临着长期紧张而无战争的局面”,“美国允许自由世界同苏联集团之间的非战略物资贸易,但是承认自由世界在非战略物资和基本原材料方面依赖苏联市场和苏联资源的实际风险”;第三,“新政策要求维持现行对共产党中国和北朝鲜的管制水平”①。
1954年8月,巴统第一次大幅度调整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巴统贸易管制清单的总数从474种下降到252种,其中禁运物品的总数从270种下降到167种。而“中国委员会”贸易管制物品仍然有472种之多。这样,巴统与“中国委员会”之间的贸易管制水平实际上差距是扩大了。
为什么要继续保留“中国差别”?这是由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的东亚政策决定的。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美国仍然把苏联视为心腹之患和竞争对手,但美国军事战略的重心却越来越从准备对苏联的全面核战争转向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局部有限战争,认为对东亚非共产党国家而言,“主要而且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共产党中国的进攻态势和正在增长的军事力量”②。1953年11月6日批准的NSC166号中明确指出,在东亚地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敌人,美国必须使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确保它在亚洲的目标得以实现。中共政权的崛起改变了“远东力量结构”,而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问题是要应付这种已经改变了的力量结构,美国的政策是通过“发展非共产主义的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通过“削弱或至少是阻碍中共力量在中国的增长”,通过“破坏中苏关系”来“削弱共产党中国的相对实力地位”③。之所以保持“中国差别”政策,是因为“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管制,不仅要阻碍其战争潜力本身的发展,而且还要阻碍其现代化,对欧洲苏联集团的贸易管制,则只是要阻碍其在欧洲战争潜力的增长”④。
因此,可以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中国威胁观”和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东亚遏制战略的确立是美国保留“中国差别”政策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尽管“中国差别”政策被保留下来并在实际上得以加强,美国政府内部关于这个问题却始终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而矛盾的核心就在于关于中日贸易对于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重要性的不同认识上。
出于对中日贸易在日本经济恢复过程中重要性的考虑,我们可以看到,艾森豪威尔本人在对华禁运问题上的看法是极其复杂的。战前日本对外出口的18%,进口的25%是在对华贸易中实现的,如果日本取消对华贸易控制(不包括对战略物资的控制),中日双边贸易在两三年内即可达到4—6亿美元的水平,这对于改善日本的外汇短缺,产品出口等方面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而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虽然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但他并不认为美国的贸易禁运是对付中国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在他眼里,即使中国的经济有所发展,但短时期内并不能造成对美国的真正威胁,而贸易禁运的真正受害者是日本,美国也会为此付出代价。因此,艾森豪威尔总统赞同对华贸易禁运必须限制在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范围内的观点,认为缓和对华禁运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须的。如果美国亚洲政策的长期目标是“削弱中苏同盟”,“贸易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可能是很有用的工具。”这“将有助于减轻共产党中国对苏联的依赖和日本对我们国库的依赖”⑤。1953年4月8日的NSC125/4文件表明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中日贸易的支持态度:“除非从满洲里和北中国获得市场和原材料,否则日本的经济没有前途”。即使在目前对华实施完全禁运的状况下,中日之间适量的贸易也是应该被允许的⑥。1954年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变得更加支持,他不仅使用了“允许”,还使用了“鼓励”的字眼,他甚至认为任何“试图永远堵塞贸易自然流向的努力,都将归于失败”[1](第581页)。
可是,以杜勒斯为首的禁运强硬派却担心如果日本过分依赖中国市场,会使它对西方产生离心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日本同亚洲大陆的传统联系,在影响日本的发展方向方面仍然有着巨大的力量,日本严重的经济问题在决定其国际联盟方面仍然是关键因素。日本对华贸易如发展到一定规模,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政治与战略目标的实现。1955年1月1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发给美国驻日大使馆一份政策性电报中指出:“自从共产党贸易的政策服务于政治性地诱导以造成自由世界分裂的目的以来,日本希望把它同中国的贸易恢复到战前水平是一种错觉,日本依靠中国作为其原材料的主要来源的做法也是危险的。依靠与共产党中国发展贸易的前景也会大大影响日本与韩国、台湾,可能还有泰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严重影响日本通过赔偿协定而刚刚建立起的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纽带,影响日本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和贸易推广。”⑦ 杜勒斯认为缓和对中国的禁运,同北京发展贸易关系之类的措施,都无助于促成中共政权消亡这一最终目标,美国还是应该通过帮助日本发展同东南亚的贸易,推动其经济复兴。
可见,在对华采取和维持什么禁运水平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存在分歧,而分歧的焦点就在于“中国差别”政策对于日本可以产生的影响。反对放松对华禁运的当然不止是杜勒斯一人,国务院、国防部、共同安全署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表示反对放松贸易控制。面对这样“一个敌对的、甚至反叛的国会和一个分裂的政府”[2](第46页),艾森豪威尔也无可奈何。
因此,尽管美国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保留“中国差别”政策,但这同时也造成了美国东亚遏制战略自身的一种矛盾:为了遏制中国,就必须实施严格的对华禁运,保留“中国差别”政策,但严格的对华禁运又可能损害到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进程,这显然又妨碍了美国对日政策目标的实现。这种矛盾为“中国差别”政策的最终被废除埋下了一个根源。
二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尽管日本被迫接受了“中国差别”政策,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日本从未放弃发展对华贸易关系的努力,并随着中日民间贸易关系的发展,不断地以内部侵蚀的方式谋求“中国差别”政策的削弱。
在旧金山和会结束后,美国以参议院批准媾和条约为要挟,迫使日本与台湾签订了《日华和平条约》,中日官方贸易被迫中止。同时,美国指示日本加入巴统组织,并签订日美秘密备忘录,保证只要中国仍然在“侵略”,日本就将实行严格的对华贸易控制,并且把各种控制的水平维持得高于一般的欧洲国家,而仅低于美国和加拿大⑧。日本同意对巴统贸易管制清单中的所有物品、美国贸易管制清单中的所有物品、根据美日秘密备忘录确定增加的所有物品一律实行管制。
然而,日本国内上下对此强烈不满,并且这种不满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后经济面临的严峻困难而激化。朝鲜战争带来的大量美国军用订单使日本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开始复苏,日本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繁荣,但这种繁荣缺乏稳定的基础,而且,从某种程度上使一些问题甚至变得更为严重了。外贸是日本经济的命脉。当日本工业生产已经大大超出战前水平的时候,对外贸易仍然处于严重萎缩之中。如以1934年至1936年的工业生产年平均指数为100,1952年日本的工业生产指数已达到140,而1952年的外贸出口只占1938年的1/3,进口只占50%。朝鲜战争的结束,使得日本依赖特需而迅速增长的出口贸易出现了停滞,由于进口过多,日本外贸入超严重,酿成了严重的外汇危机。外汇储备由1952年底的11.4亿美元跌至1953年的9.76亿美元,1954年日本实际外汇储备不足5亿美元,而且出现了生产过剩危机[3](第6页)。
在巨额的外贸赤字面前,日本急需扩大对外出口。日本虽然试图将贸易重点转向欧美各国,但是作为经济命脉的重化工产品成本高、技术水平低,缺乏竞争力,无法在欧美市场上立足,而且战后由于冷战对峙,世界市场相对缩小,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再加上美国凭借自己对日本的优越地位向日本大量倾销过剩产品,使得日本除了巨额贸易逆差之外,几乎什么也得不到。而在美国战略规划中被作为中国的替代市场的东南亚,其贸易前景也不被日本人看好。这不仅是因为从东南亚进口资源成本偏高,更在于该地区尚未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资源开发和物资集散体系,多数国家又属于英镑集团[4](第623页)。
在危机面前,日本更加指望美国提供纯粹经济援助,但池田-罗伯逊会谈(1953年10月)和《日美相互防卫援助协定》(MSA协定)(1954年3月)并未满足日本要求。事实上,同期美国对外援助总额也在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1952年美国全部对外援助计划为7284.4百万美元,1953年为6001.9百万美元,到1954年便减少为4531.5百万美元,而1955和1956年则进一步减少为2781.5百万美元和2703.3百万美元[5](第222页)。
在强大的经济压力面前,日本人认为经济之所以造成如此窘境,恰恰在于中国贸易所占比例太小,因此,“一部分经济界人士和劳动团体等要求重新恢复中日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6](第805页)。
1952年6月,日本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一行三人前往中国,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贸易额虽不大,但却在中日官方贸易被迫中止之后开创了民间贸易的形式,打开了对华禁运政策的缺口。之后,在1953年10月29日和1955年5月4日,中日分别签订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三次贸易协定之后,中日两国的贸易额由1953年的3500万美元增长到15000万美元。两国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由此带动了政治关系的发展。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中规定了中日互设准官方的贸易办事处和中日直接结汇(即不再通过中日在伦敦的银行结汇)。1955年11月日本前首相片山哲访华,同年12月中国副总理郭沫若访日,这两次访问虽然都是以民间身份进行,却标志着二战后中日官方接触规格的升高。
随着中日民间贸易关系的升温,日本开始直接向美要求降低对华禁运的水平。1953年10月日本大藏大臣同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逊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中,日方要求美国将COCOM和CHINCOM中的禁运物质降到同东欧国家的水平,美国最终于1954年8月批准了这一要求。同时,日本直接提出修改“中国差别”政策。在1954年7月巴统会议上,日本代表首先提出,如果只缓和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管制,经由苏联的转口贸易势必增加,对华贸易管制的实效将减低。因此,应当在适当时机重新讨论中国问题。日本政府保留提出具体方案的权利⑨。
1955年2月,日本明确提出要求修改巴统“例外程序”的规定。根据1951年巴统第4711号文件规定,巴统成员国如果不出口禁运物资就不能从苏联集团国家获得本国急需的物资时,经巴统委员会事前同意,可以出口禁运物资。这就是所谓“补偿原则”下的例外程序。同年巴统第782号文件规定:只要属于民用而不是用来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可以向中国出口巴统管制清单内的禁运物资,但事后要向中国委员会申报备案。这就是所谓“第782号文件的例外程序”。 日本要求的就是广泛利用这种“782方式”。据英国方面统计,1952年,巴统成员国中还没有一个国家利用“例外程序”对华出口,1953年,巴统成员国利用“例外程序”的对华贸易额中,西德120万美元,英国8万美元,日本为0美元。1954年,西德为100万美元,意大利和日本奋起直追,分别为7.5万美元和4.5万美元,英国则下降到只有4.2万美元。到1955年上半年,日本跃居第一位,达到135万美元,英国和西德则只有6.1万美元和4.9万美元。另据美国方面统计,巴统成员国利用“例外程序”的对华贸易额,1954年只有300万美元,1956年则高达7900万美元⑩。
通过中日民间贸易和广泛地利用“例外程序”来扩大对华出口,是日本从内部侵蚀“中国差别”政策的主要策略。
三
到1955年末,美国与其盟国在“中国差别”政策问题上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在关于“中国差别”政策问题的谈判过程中,日本采取了一种谨慎而又坚决的方式,既避免了日美关系的紧张化,又与其他国家一起,取得了废除“中国差别”政策的胜利。
1955年12月,英国警告美国说,如果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的话,英国将单方面宣布废除中国差别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此时才开始显露出缓和对华贸易管制的意向。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此问题举行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认为,认为禁运可以打败中国的想法是“幼稚的”,这样做只会损害自由世界的利益,禁运将使得中国更加依赖苏联,并损害到与中国具有传统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经济利益。他进一步指出,与中国的贸易将是互利的,美国目前的政治气氛只会阻碍中苏分离的计划。“我们的麻烦,在于我们国内的政治环境迫使我们在对中国和苏联贸易问题上采取一种绝对的僵化的政策。”(11) 杜勒斯也表示,“要避免多国贸易管制的彻底崩溃,美国就必须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12) 1955年12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设立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负责起草、制定对共产党国家贸易管制政策的具体方案。1956年1月26日,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称:“自由世界国家应该加强而不是缓和对中国大陆的管制。”倘若为了维护多边主义而必须做出让步,可以从日本最近提出的“例外程序”物资清单中选择出19种,作为最低限度的缓和措施(13)。这表明,美国政府的底线是在继续维持“中国差别”的前提下,尽可能将对华贸易管制缓和限定在最低限度之内,这也预示了美国同其盟国谈判的不可避免破裂的结局。
1956年1月31日,艾森豪威尔与英国首相艾登举行会谈,拉开了美国与其盟国讨论“中国差别”政策问题的序幕。在美英就废除“中国差别”政策问题在进行外交交涉的过程中,正在日本的道奇责成经济防卫咨询委员会就三个问题作出评估:(1)西方国家的何种物资最能增强中国的军事潜力;(2)中国出口物资中何种物资能使除日美两国以外的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受益;(3)中国出口物资中何种物资主要使日本受益(14)。同时,美国政府也对美日关系进行了仔细的评估。这说明美国似乎更关心“中国差别”对日本,而非英国或其他国家所带来的影响。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指出:“在美国政策中有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遭到了所有阶层的日本人的一致强烈抵制……日本人强烈希望加强对华贸易关系并最终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日本人正在测试美国人关于贸易问题的耐心的底线,对华贸易问题很有可能成为美日关系中一个严重的导火索。美国驻日大使亚里松也从东京发回了类似的报告,强调加强对日协商的重要性,认为华盛顿在中国差别问题上的举措是危险的,尽管贸易和对华关系目前仍未成为两国间最重要的问题,但日本人对此的愤恨是显而易见的。
1957年5月,巴统成员国会议在巴黎开会。这次会议一开始就充满对立气氛。法国代表提议:除IL/II中的25种物资以外,其他现行对华禁运物资一律在6个月内解除管制。而美国准备只放松控制,但要求保持明显的中国差别,英国、法国、日本和比利时等成员国对美国的提案表示极度不满,与会的16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支持法国方案。5月23日,谈判陷入僵局无法继续进行,一周之后,英国率先声明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独立行动,缓和了对华贸易管制水平,7月,绝大多数巴统成员国,包括意大利、挪威和西德很快也紧随其后。
焦急的日本此时却没有急于表态。1957年6月19日,岸信介首相访问美国,在与杜勒斯的会谈中提出了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问题,他表示对华贸易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日本寻求对华贸易额的“合理增长”。为了实现日本对华贸易利益,日本政府打算承认共产党中国或与中国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杜勒斯对此坚决表示反对。他说,美国一直认为日本应与共产党中国开展适当的贸易,但美国关心的是这种贸易能否迅速增强中国的战争潜力。中国的军事工业在现阶段仍处于低级阶段,并几乎全部依赖于苏联的军事战争备用物品的供应。如果中国获得独立的战争供应源,在这一地区战争的危险将会大大增加。杜勒斯告诫日本:政治责任远比商业利益更重要。为了弥补日本限制对华贸易而承受的损失,杜勒斯鼓励日本加速发展与东南亚自由国家的贸易,并承诺世界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将在资金方面给予大力帮助。(15)
然而,巨大的外贸赤字和来自国内的政治、经济压力使得日本再也不能遵循美国的警告。1957年7月,巴统委员会成员国关于贸易禁运的谈判重新开始。16日,日本政府即发表声明宣布废除“中国差别”:从即日起,解除272种物资的对华贸易管制;从8月1日起,解除13种物资的对华贸易管制;从8月3日起,解除10种物资的对华贸易管制。日本人最终做出了选择。
对于美国而言,巴统成员国纷纷废除“中国差别”,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一次失败,而这次失败的根源是深埋于“中国差别”政策自身的。日本正是利用了“中国差别”政策与美国对日政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来作为进行内部侵蚀的借口。“中国差别”政策的废除使得美国开始“重新审查美国对共产党中国贸易政策的全部问题”[7](第106页)。
注释:
①④⑥ 参见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hereafter FRUS),1952—1954.Vol.1.Washington,1983:p1241,1252,1401—1408.
② 参见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2—1954.Vol.12:pp421—422.
③⑤⑧ 参见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2—1954.Vol.14:pp283—287,268,1332.
⑦(15) 参见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5—1957.Vol.23:pp5—7,387—414.
⑨ 参见Public Record Office.COCOM Documents,No.1650B,June 28,1954:ppM346/45,F0371/111213.
⑩ 参见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5—1957.Vol.10:pp420—421.
(11) 参见“Discussion at the 27lst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Thursday,December 22,1955”.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hereafter DDRS)(81):p497B.
(12) 参见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5—1957.Vol.3:p209.
(13) 参见Joseph M.Dodge to CFEP.January 26,1956,CFEP Records,Policy Papers Series.Dwight D.Eisenhower Library:Box 2.
(14) 参见Briefing Paper for CFEP,Paul H.Cullen to CFEP,March 2,1956,CFEP Records,Policy Papers Series.Dwight D.Eisenhower Library:Box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