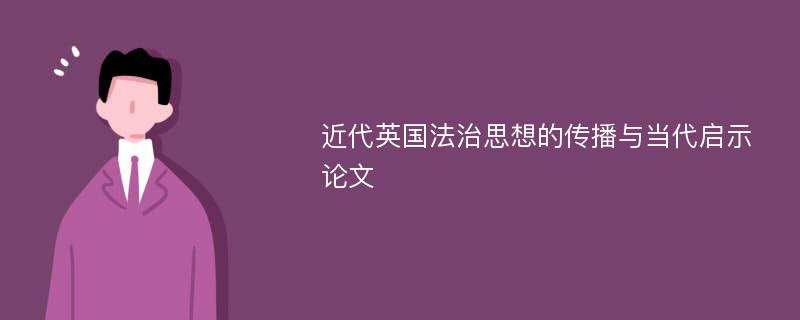
新闻传播与法治
近代英国法治思想的传播与当代启示
叶海涛,方 正
(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1187)
摘 要 :英国法治理念肇始于近代社会政治变革。17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土地贵族的矛盾不断激化,传统政治体制的瓦解,印刷媒介的发展以及阅读型的形成,为以权利为核心的法治、平等、自由等现代政治价值的广泛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旧价值理念的激烈碰撞启发和塑造了近代英国公众的理性精神,凝聚起了现代化进程。当代中国正处于“大国”向“强国”的转型期,合理吸收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可为新时代培养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维护法律尊严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英国;法治;传播;启示
16世纪至18世纪初,这种管治主义下的治理,意味着对个体活动的规范到了最细微之处,管治的对象也几乎是一个无限的对象[1]。在近代英国,君主集权化倾向于16世纪末达到顶峰,破坏了自诺曼征服以来的传统法治秩序,因而英国传统法治思想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两个基本目标,即限制国王权力与维持议会的相对独立。17世纪以后,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与传统政治体系的崩溃,法治、平等、自由等现代价值理念借助印刷媒介得到广泛传播,逐渐凝聚为社会价值共识,并在“光荣革命”后转化为制度实践,英国由此开启了政治现代化进程。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正处于由“大国”向“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时代必须坚持的十四个基本方略之一,并提出在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战略目标。合理吸收其他国家法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新时代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形成遵法守法与崇法敬法的社会氛围提供有益借鉴。
一 、近代英国法治思想的发轫
现代自由与法治理念大体能够追溯至17世纪的英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的遗产与现代自由毫无关联”[2]。事实上,法治一直在英国社会中扮演着调和权力与自由之间关系的角色,而其有资格限制的主体是传统贵族与骑士阶层,这种封建法治秩序下的限制实则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关系调整。17世纪以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法治思想承袭了英国传统法治要求限制权力主体的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基于公民权利的现代意义的法治观。
(一)“法治”概念溯源
在欧洲两大法律体系中,“法治”概念均起源于古希腊城邦时代。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了法治概念,及至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理论化。政治哲学家多用“isonomia”一词指代“法律下的平等”(equality of law),此外,还有一些以“iso”为词根的专门术语用于指代某种具体的平等权,如“isegoria”即指在政治集会平等发言的权利(equal right to address the political assemblies),“isopsephos”则意指平等投票的权利(equality of vote)[3]。在法治传统的继承发展过程中,英国各个时期的学者对“法治”概念均有过不同的英文表述。根据哈耶克的考证,16世纪末已有英国人从意大利引入了“isonomia”这一术语,意指“法律平等地适用于各种人等”。1600年,英国人费尔蒙·霍兰德(Philemon Holland)在翻译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著作《罗马史》时,用“isonomy”代替了“isonomia”,该词“在17世纪初的英国得到了广泛使用”[2]206,主要是指法律平等地适用所有人以及行政长官也负有责任的状况。虽说这不能完全概括“法治”的全部内涵,但其对“法律平等”的界说却构成了法治始终如一的基本内核[4]。
检测大鼠摄取D-木糖后其血清D-木糖的水平,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大鼠血清D-木糖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显著(P<0.01)。而给药组大鼠与模型组大鼠相比,血清D-木糖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显著(P<0.05、0.01)。其中熟地黄II、熟地黄III以及熟地黄IV组与熟地黄I组相比,血清D-木糖水平降低,表明九蒸九晒熟地黄中缺少黄酒或砂仁或二者都缺影响了九蒸九晒熟地黄的药效。同时熟地黄V和熟地黄VI组与熟地黄I组相比,血清D-木糖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显著(P<0.05),表明清蒸或酒炖熟地黄对模型大鼠消化吸收能力的改善作用比九蒸九晒熟地黄差。结果见表4。
17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英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发生,关于“法治”的理解与表述又有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出现了诸如“equality before the law”(法律面前人人平等)、“the supremacy of the law”(法律至上)、“Lex,Rex”(法律即王)、“dominion under law”(依据法律统治)等表述。其中以“rule of law”(法律之治)一词在当时的影响最大,使用也最为广泛。18世纪初,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其著作中强调,英国历史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从意志的统治到法律之治”(a government of will to a government of law)的演化,最终确立了“government of law”这一表述的用法。“rule of law”与“government of law”逐渐成为现代“法治”概念的最普遍表述方式,但即便如此,这种概括性较强的表述也不能完全涵盖不同时期“法治”所阐发的具体意义,仍需要在不同历史时段的考察中进行实体性分析。
(二)中古英国的法治传统
欧洲的法治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时代,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明确表达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的观点:由于城邦决议不可能针对普遍事理,故而法律是城邦不可或缺的治理规范,“在法律失去其权威的地方,政体也就不复存在了,法律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5]。罗马共和国时期,西塞罗发展了希腊化时代斯多葛派的自然法思想,提出自然法是宇宙“最高的理性”与“正确的规则”[6],是一切人类成文法的基础,人类因自然法而联结为一个整体,并且“不管对人作怎样的界定,它必定对所有人同样适用,(因而)人类不存在任何的差异”[7],即自然法之下,人人平等。中世纪以后,基督教在欧洲大陆确立了神权统治,并垄断了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以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为代表的古典思想被视为“异教”文化,遭遇灭顶之灾。但在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国,西方传统法治理念得以延续,并获得了里程碑式的转型发展,其标志性事件是1215年《大宪章》的签署。
《大宪章》被视为奠定英国法治基础的第一个制度性文件,内容主要为界定君主与臣民在自由、纳贡、土地、婚嫁、诉讼等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其目的虽是为捍卫贵族的基本权利,“却为不了解贵族且惧怕国王的后代人提供了捍卫自由的保障”[8]33。13世纪中叶,英国著名大法官布雷克顿发表了《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他在书中着重阐发了国王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提出“国王不在任何人之下, 而只是在上帝和法律之下”[9]的著名论断,被视为中世纪英国传统法治理念的光荣与梦想。但彼时王之决定即有法治效力,国王的决定是法律的重要来源。因此,17世纪前的英国虽一度盛行由习惯法、封建法与神法等共同构成的“王在法下”的传统,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传统并不能真正限制不断集权化的国王。被视为体现这种“法治传统”的议会,虽偶有限制君主权威, 但传统土地贵族的利益具有整体一致性,贵族把控的议会仍旧是国王的议会,在本质上是支持王权的,“尤其是在封建君权强大的时期,‘王在法上’的专制独裁更是让这一所谓的法治传统沦为虚幻的政治图景”[10]。大贵族集团与国王的政治权力博弈,不应该被视为具有宪政意义的“革命”和“实验”。
(三)现代法治思想的渊薮
中世纪宗教政治共同体下,世俗权力与宗教神权实现了某种结合。近代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出现后,宗教神权虽为欧洲各国的世俗王权所压制,但神意依旧是国王政治权力最重要的法理性依据。国王不仅先于法律而存在,亦可以凭借宗教赋予的权威制定法律并对国家进行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对民众的管治。这一时期,集权化的君主成为国家的象征,所谓“法治”更多地体现为以国王为代表的传统封建贵族的“牧民”手段。现代意义的法治理念形成于英国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激烈政治思想交锋之中。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英国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的不相匹配,使其对传统土地贵族独揽政治权力的局面日益不满,其中的政治精英以议会为平台, 通过阐发“法治”理想来抗争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土地贵族。为了追溯政治权力的来源,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们通过思想实验建构出一种“自然状态”,并借助社会契约这一理论工具为政治社会的产生提供佐证。
②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企业在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给予内部该段人才和紧缺型人才奖励时,可对照中关村的做法实行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政策。
在资产阶级的理论建构中,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自然状态下无法存续的个人权利,因而政府的权力源于人民的同意,而非虚构的神意。在政治社会中掌握公权力的机构,不能按照个人意志随意行事,其一切命令以保护人民的权利与实现其幸福为目的。法律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是一种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它并不在受法律约束的人们的一般福利之外作任何规定[11]53。因此,资产阶级法治理念的核心在于保护以自由为根本的人的基本权利,它为现代法治政府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种鼓吹公民权利至上与限制王权的理论模式, 不久就随着政治冲突的深入与传播革命的发生而日益拓展, 为英国理想“法治传统”的重构融入了“自由权利”与“议会主权”的思想底蕴,英国社会的法治秩序由此开启了现代性转型发展历程。
二 、英国法治思想的社会传播机制
综上所述,城市建筑的中水回用系统,往往需要依托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和中水资源利用来完成;对于中水就地水源就地使用的直接使用系统,需要开发商或建设方首先在观念上提升,当前环保及绿色建筑的要求,都需要中水系统与主体建筑同时设计、施工及使用,并且应把中水日回用量统计纳入绿建环保考核指标,通过合理设置城市建筑的中水系统,认真规划中水资源的主要来源,能够尽可能多地提高中水资源的应用范围,从而促进中水资源的回用价值提高,中水使用范围的扩大,让中水利用成为常态,消除社会公众对于中水回用产生过多的误解,灌输民众对节约用水与中水回用是绿色环保和建设美好家园的行动措施。
(一)传播主体:社会政治力量的多元化
这些价值共识亦对英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诸多实质性影响,公众意见得到了权力阶层前所未有的重视。如在内战爆发后,议会为争得社会民众的支持,开创了一项新的制度。“从1641年开始,议会每个月都会确定一个公共开放日,在这一天,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公共人物请到议会并倾听他们的意见,上议院与下议院都会时常派人将他们的意见印刷成册,这是议会派了解公共意见的重要渠道之一。”[16]22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政治论战中的思想成果也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巩固并保存下来:17世纪末,英国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如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国家, 而且“从中产生出来的是有关法律至上、人民的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威的民主基础的一系列原则”[8]3。近代英国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以法治、自由、平等为核心的现代价值理念的广泛传播,型塑了公众的启蒙精神,建构了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政治体制,在思想与实践两个维度开启了英国现代性的转型发展进程。
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综合前述研究,形成了消费者无现金支付使用意愿模型。该模型从消费者感知价值角度入手探讨影响无现金支付使用意愿的因素,把感知价值作为中介变量,而感知价值取决于感知收益和感知损失两方面,感知收益主要体现在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优惠补贴方面,感知损失主要是感知风险。研究模型如图1。
1642年,英国内战爆发后,传统政治体系彻底崩溃,国王下的高压管制消失。政治语境的变化为信息传播敞开了新的社会环境,极具争议的政治议题不断出现,不同政治派别蜂拥而出。“掘地派”(Diggers)、“平等派”(Levellers)、“喧嚣者派”(Ranters)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派别,他们借由各种传播媒介发表对国王政治的看法,并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批判。1647年,平等派运动领袖李尔本(John Lilburne)在狱中起草了题为《千万自由公民的抗议书》的小册子,提出“人民应该是最高主权者,反对一切暴政,废除君主和上院,倡导民选议会,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主张[13];掘地派领袖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以《自由法》为旗帜,批判了私有制的不公与破坏性,认为私有制是使人民陷入一切贫困之中的一切战争、流血和奴役性法律的原因,并提出现实的法律制度只是为了维护财产私有制而存在的,法官也只是富有者财富的看守者,繁杂的法律对下层民众只是一种镣铐与枷锁,谁的口袋里装的钱多,谁就可以打赢官司[14]。此外,一些影响较大的自由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如弥尔顿、洛克等,出版了多部政论性小册子,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意义的法治思想的传播。
(二)传播媒介:印刷媒介的重大发展
其次,要打造一支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一方面,要打造集理论阐释、图文设计、视频制作、实践调查为一体的内容设计团队,只有专业化的媒介团队才能充分掌握互联网传播规律,在内容设计上满足互联网用户的文化需求,增强公民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要注重媒体工作者的法治思维培育,坚定其马克思主义信仰,确保新媒体传播的正确价值导向。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领域的相关法规政策也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因此在新媒体内容的制作过程中,必须遵守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在内容创新的同时始终坚守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
据英国学者雷蒙德(Joad Raymond)考证,1588年~1639年之间,英国国内和在海外发行的出版刊物种类数量只维持在勉强生存的水平,每年的出版刊物种类约在211-695种,平均每年为495种,其中,1588年~1599年间平均每年约为260种,1630年~1639年间平均每年约为624种,有了小幅度的增长。但这一数据到了1640年,突破到了800种,1641年则达到了2042种,到1642年时,英国每年出版的印刷书刊种类上升至4038种,实现了印刷出版刊物的几何倍数增长[16]161。小册子是印刷刊物的主要构成,仅1640年~1660年这二十年间,英国便一共出版了超过25000种以上的小册子,平均每年超过1200种,“英国历史上从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时期像这二十年一般出现了如此多的抨击性小册子”[17]。作为现代报纸的最初形式,时效性、周期性较强的新闻书在内战爆发后同样取得了较大增长。据统计,内战期间,仅伦敦一个地区的新闻书就超过了7000种[12]。印刷媒介的大发展,拓展了社会信息渠道,因此,有学者“直到17世纪中期, 英国社会才具备让大众知晓信息的条件, 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1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新闻书的政治议题同步性与小册子所展现的思想贯序性实现了有机结合,为现代法治理念的有效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媒介环境。
(三)传播受众:现代阅读公众的形成
“人们在话语的互动中形成了公共舆论并发挥作用。”[23]公共舆论并非在公共领域内被某个力量团体所主导的舆论,亦非卢梭口中凌驾于个人意见之上无可分割之“公意”,而是包含了几个力量团体相互冲突的观点,强烈、清晰和统一的大众认同是不存在的[24]。英国政治大变革中,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多元政治主体为信息的传递提供了不同的话语“版本”,使得针对同一政治议题的评判出现争议。随着政治军事斗争的不断深化,这种价值冲突更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社会公共舆论始终呈现跌宕起伏的态势。在法治思想的传播中,罗伯特·菲尔麦(Robert Filmer)与洛克关于“国王与法”的辩论是近代英国最著名的政治论战。
近代英国自由主义法治传统以及“王在法下”的法治文化,为现代法治理念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建立同样离不开法治文化的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合理借助现代传播媒介,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法治文化宣传,不断增强全体社会成员对法治文化的认同,从而将法治内化为一种社会文化自觉。
2.协整检验。为检验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接下来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通过协整检验发现,人民币汇率预期(DNDF)、境内外利差(DLC)与经常账户跨境资金流入(DLIJC)、经常账户跨境资金流出(DLOJC)、金融账户跨境资金流入(DIJR)、金融账户跨境资金流出(DOJR)以及资本账户跨境资金流入(DLIZB)等五项跨境资金流动指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而在分析人民币汇率预期(DNDF)、境内外利差(DLC)与资本账户跨境资金流出(DLOZB)之间的协整关系时,得出它们之间存在至少一个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如表2所示)。
(四)传播话语:公共舆论中的多元价值碰撞
媒介革命不仅带来了信息传播的规模化发展,同时促进了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变革,施拉姆曾以“文化爆炸”(explosion of culture)与社会变迁的“洪流”(flood)[15]190来形容这一时期文化的重大发展。在教育领域,机印书的廉价与规模化,改善了教学用书严重不足的状况,“不仅使得勾勒老师职责的图书得以出版,且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分别设计的教材从最初级知识到高级知识均能循序展开……于是儿童受影响的发展阶段就不同于中世纪的学徒、耕童、新手或侍从了”[19]267。印刷书的出现,使得中世纪以来欧洲普罗大众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普遍提升,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甚至夸张地形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有学问的人,很能干的老师,宏大的图书馆……柏拉图与西塞罗时代都没有这样好的学习机会。”[19]72在文字文本方面,机印书促进了文字文本标准的统一化。中世纪以来,“抄写时出现的拼写标准混乱与语法的准确性表达问题并没有受到高度重视”[20],加之文字种类的不固定,导致公众在阅读中出现诸多障碍。16世纪以后,多样化的书写风格逐渐消失,印刷的样板书(specimen book)在语法、分类、编订、校对等方面形成了统一样式,结束了社会语言分割对整个欧洲的影响,促成了欧洲文化与学术一体化的形成。
1948年,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发表了《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奠定了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范式,即“5W”模式, 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 (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此后的传播学研究多遵循这一范式。本文亦采用“5W”要素分析法,对近代英国法治思想的社会传播机制进行解构分析。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保皇派的代表人物,菲尔麦于1680年付梓出版论文型小册子《父权制:论国王的自然权力》,为国王政治进行辩护。在小册子中,他系统阐述了“君权神授”理论,竭力鼓吹“王大于法”的观点,声称上帝的“神法”造就了王权,因此没有任何世俗法律可以限制它,立法权从来就只从属于一个人(国王),法律是国王意志的延伸,议员们应当“将自己约束在效忠与服从的范围内[25]43,议会只是国王的法庭而已,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法律的共和国无法存在,而没有法律的君主制却可以长存[25]41。为了驳斥菲尔麦“王在法上”的论断,洛克于1689年、1690年分别发表了《政府论》上下两篇。洛克在《政府论》中建构了一个所有人都完全平等的“自然状态”,否认了国王权力的“神意”来源,并提出所有人生而具有不可剥夺、不可让与的自然权利。人们放弃自己的部分自然权利,授权成立一个共同的社会管理机构,把所有不排斥他可以向社会所建立的法律请求保护的事项都交由社会处理[11]53。因此国王制定法律的权力源于人民的同意与委托,他没有意志,没有权力,有的只是法律的意志,法律的权力[11]95。洛克关于“王在法下”的阐述,建立了基于公民权利的现代意义的法治观,也为英国君主立宪制提供了法理依据。菲尔麦与洛克的法律观在当时都颇具代表性,他们基于不同政治立场,就“王与法”的问题进行论战,本质是对争夺政治话语通过种种社会传播形式(公之于众),其最终目的就在于对意见的控制[26]。英国内战期间,多元化的政治理念见诸报端,公共舆论因此呈现出多元价值交锋碰撞、跌宕起伏之势。在此过程中,政论家们实现了与普通民众的思想交流、意见沟通,论战中所展现的思维模式、逻辑方法与论证技巧逐渐为公众所熟知,由此启发了社会公众的理性思维,催生了公民个人理性精神的诞生。
(五)传播效果:价值共识与制度建构
信息传播效果大致体现在两个层面,即对受众思想、认知、情感的影响程度以及信息传播意图的实现程度[27]。近代英国政治制度崩溃、社会体系撕裂,导致各种政治派别粉墨登场,各类政治主张层出不穷,保皇派、议会派、长老派等各种政治力量纷纷发声,竞相阐述本派别的政治价值与理想社会形态;温和改良主义、极端保守主义、激进平民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激荡碰撞。近代英国公众对理性的运用,正在于对各类政治主张之思辨与求真,通过去伪存真、淘汰陈旧观念,摆脱“自己加诸于自身的不成熟与缺乏理智的状态”[28]。驱散“神圣瘟疫”,实现中世纪以来专制主义政治下的自我解放,成为近代英国的社会主题。在这一批判与推陈出新的过程中,旧思想旧制度常有胶着与反复,新旧交替在异常激烈的论辩中进行,民众思想得到前所未有之涤荡,理性之启蒙成为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汤因比曾把人类历史发展分成黑暗时代、中世纪、现代时代、后现代时代四个阶段[29],启蒙运动是现代时代的重要标志,它建构了一个民族整个的道德和智慧的思维习惯和心灵习惯,是走向现代性的重要途径[30]。法治思想的传播是英国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它使英国公众摆脱了中世纪以来国王政治的枷锁,形塑了英国公众关于个人基本权利的思想意识,凝聚了现代意义的社会价值共识。
传播主体是信息传播的源头,也是政治传播系统的首要环节。17世纪以前,英国处于都铎王朝兴盛时期,国王权力膨胀,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这一时期,王权对舆论的控制达到了巅峰,书报审查制度与残酷的司法惩罚制度使政治信息流通几乎绝迹。其时,关于法治的传播内容多半是一些违背封建法律的具体判例,有些会被装订成册,钉在公示板上供民众观看,旨在震慑社会不同声音,维持传统贵族统治权威。17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崛起,英国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分裂,这些新兴政治力量与传统土地贵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政治上的决裂使得一元发生根本性变化,催生了不同意见的产生。信息传播主体二元化的过程中,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亦逐渐走向公开,中央和宫廷的政治不断透明化,引发民众对于国王政治的担心,促成地方公众形成了较为激烈的意见和两极化的政治态度[12]。
在电池组件中,隔膜一般是聚乙烯、聚丙烯等高聚物,分子结构中存在大量的碳氢键,同时电池中的电解液是有机溶剂,也属于可燃物,因此锂离子电池在热失控后主要是隔膜和电解液在发生燃烧反应,产生大量的烟气。
三 、对当代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启示
法治思想的传播是英国现代性转变的重要内容,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英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及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制度基础。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法治文化的培育、法治精神的形成、法律尊严的维护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强国建设的重要维度。合理吸收英国法治思想的传播经验,可以为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提供有益借鉴。
(一)建立现代传播体系,培育法治文化
在市场领域,现代商业性印刷所的出现实现了知识向固态商品的转换,它通过复制的形式,将信息与知识转变为一种可以经过包装售卖的商品,并通过明码标价的方式进入普通家庭。中世纪的抄本时代,复制和传播他人的书籍会被视为一种恩赐,知识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仅掌握在宫廷贵族、教会以及少量的银行家手中,而机印书籍的统一性和可复制性,在近代建立起了书面文化和工业所不可缺少的市场与价格体系,实现了信息由上流社会的横向流通向普通公众垂直流通的转变。社会文化领域的诸多变革,提升了英国普通民众的阅读率,亦使之形成了现代阅读型公民群体。一方面,机印书的规模化生产效能不断提升,增强了普通民众的书籍购买能力。17世纪中期,一个普通工人完成一个小册子制作的时间大约为6天左右,而印刷书商则可以将制作效率提升一倍,生产效率的提高降低了印刷刊物的成本,“17世纪,小册子零售价格接近1便士1开,一本小册子的价格仅为1先令左右”[21]。另一方面,英国普通家庭藏书率大为增加。17世纪末,英国拥有藏书的普通家庭的比例约为五分之一,而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大陆,这一比例甚至不及万分之一[22]。阅读型公民群体的形成,带动了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增强了普通民众在政治论战中的信息理解能力,构筑了接受现代法治理念的受众基础。
大数据时代下在数据开放共享的同时,也面临数据安全的威胁,我国目前信息安全制度还不健全,对数据资源采集、存储、利用等方面的管理不规范,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随着数据应用越来越频繁以及解读技术的提高,网络数据安全风险不断加大,使得公民个人隐私、国家机密的保护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决策依据是合同立项的根本依据,主要包括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纪要、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纪要、请示批复、投资或费用计划、采购中标文件等,根据企业性质不一一列举。
从普法媒介来看,当前社会公众接受普法信息的渠道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普法传播渠道的影响力急剧衰减。新媒体时代,要善于利用“微传播”,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宏大叙事主题与厚重文化内涵以社会成员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出来:在话语风格上,应当摆脱传统媒体平铺直叙的灌输模式,借助新媒体灵活多样的语言形式、现实生活化的语言风格,增强法治文化的感染力、渗透力;在话语内容上,适当减少冗长繁杂、系统宏观的说教式宣传内容,借助互联网热点巧妙设置话语主题,科学合理的安排话语内容,以增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教育内容的吸引力;在传播方式上,不仅要整合广播、电视、报刊、文化展板等传统媒介资源,还要充分利用微信推送、微博转发等新媒体功能,创作契合网络用户心理、蕴含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深刻内涵的微视频、微段子,通过“微言大义”、春风化雨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入脑、入心、入言、入行,提升法治文化的宣传效率。
媒介是政治传播的基本介质,是信息扩散与接受的重要载体。15世纪中期,欧洲人口超过一亿,但包括宫廷图书馆、修道院图书室在内,所有藏书加在一起不过几万册[15]205。这几万册书籍大部分为手抄本,且多为宫廷贵族与教会所有,藏于民间银行家、大商人手中的数量极少,因而不具备广泛传播的媒介条件。15世纪末,莱茵河畔的古登堡(John Gutenberg)发明了包括铅锡合金字模、新型油墨、机械印刷机在内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拉开了近代传播革命的序幕。16世纪末,较为成熟的金属活字与机械并用的印刷技术传入了英国,使得口耳、手书式的传播形态逐渐向油墨印刷式信息载体转变。英国内战爆发后,国王政治下的高压管制消失、书报审查制度废弛,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英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盛况,以新闻书(News-book)与小册子(Pamphlet)为主要类型的印刷刊物出版呈现出“爆炸式”发展的局面。
最后,还要注重传播对象分众化与传播策略精细化,提升传播效率。新媒体舆论场生态复杂、受众规模庞大与传播对象分众化等要求在法治文化传播过程中,要合理利用大数据技术,依据不同年龄层次、学历背景、行为习惯的受众,制定不同的传播内容并进行精准投放,做到有的放矢、高效传播;传播策略精细化,旨在对法治文化宣传的内容选择、平台建设、传播频率、修辞应用、回应期望等各个环节进行设计包装,根据受众的群体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区分处理,提升宣传策略的有效性[31]。
“首先是人员素质的提升。”张伟强调,其后才是工具的使用。自2014年起,伴随医改攻坚的深入,规避医疗风险,提质增效成为医院发展的新主题,质量管理的多个闭环形成,成为时势所需。“例如PDCA循环管理。制度在先,落实在行动,反馈和检查、督导跟进,才能形成闭环。”
(二)借助两个舆论场,传播法治精神
在英国,大多数人服从法律不是因为害怕惩罚, 而只因为它是法律。“他们觉得没有义务服从那些不是法律的规定。”[2]209近代英国法治思想的传播,在意识层面树立起了英国公众的法治精神。十八世纪中叶,“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格言成为英国民众权利意识与法治精神最鲜明的写照。我国自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方略至今二十余载,法治中国建设已初具规模,民众已具备基本的法律意识,但法治精神却远远落后于国家层面的法治建设步伐,传统观念中畏惧权力和畏惧法律的倾向依然存在,这也直接导致了民众法律素养普遍不高、法治精神严重缺失的现状。新时代提升全民法律意识,必须加强民间舆论场中的理性公民培育,优化官方舆论场的引导规范功能,在法治舆情的话语实践中,重塑社会成员的法治精神。
民间舆论场的话语生产主体是普通民众,主要传播内容是社会公众的所见所闻所感, 是社会感性认知和情感的集成[32]。因其依托网络平台,故具有反应迅速、感染性强,扩散范围广等特点。近年来频频出现的社会法治热点事件,常常引爆民间舆论场,形成网络全民大讨论。“江歌案”“山东辱母案”“昆山持刀伤人案”等都是轰动一时的网络法治舆情热点,道德情感与法治价值的冲突成为这些热点舆情的共性问题。但司法信息的公开往往具有一定的迟滞性,网民群体会依据感性立场对法治事件产生道德先判,在网络谣言、猜疑、煽动话语的推动下陷入“众意的螺旋”,形成“偏见共同体”[33],法治精神被群体式情感宣泄所替代。社会主义法治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原则,在个体情绪的侵蚀之下,社会成员往往失去理性判断能力,致使法治意识失守、法治精神缺失。因此,弘扬法治精神,要在民间舆论场中培育起理性的公民群体。一方面,社会成员要在网络法治舆情的话语实践中,不断锤炼成熟理性的思考方式,提升理性判断能力,逐步强化自身法治思维;另一方面,要在学校与社会教育中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认知与了解,树立网络责任意识。
官方舆论场以党政机关主导的传统媒体为支撑,反映了社会政治系统的态度、立场与观点。面对网络法治舆情事件,官方舆论要提升对法治舆情的敏感性,增强法治信息的有效供给,合理引导法治舆情热点的走向,规范法治舆情中的谣言与煽动性话语,建构以理性讨论为基础的舆情氛围;此外,官方舆论须摆脱话语姿态上的俯视心理, 积极研究和吸纳民间话语,以语言形式的共通带动思想层面的共鸣,合理引入民间声音,让社会各界都有表述自身观点和诉求的机会,强化传统媒体于民间舆论场的亲和度、影响力,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提供强有力的媒介保障。
(三)加强立法执法规范,维护法律尊严
“法者,治之端也。”[34]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制度依托。近代英国社会的法治转型,伴随着基于“公民权利”的现代法治理念的传播,实现于“法律至上”“议会主权”等条款载入《权利法案》等纲领性文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含了保障人权、制约公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35],法治核心价值的实现,最终须体现于具体的立法与执法层面。在当代中国,人权的保障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正当性的体现,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二元割裂,文化、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同步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个体权利的充分有效实现。
新时代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改革发展成果,一方面要在立法层面补齐民生的制度短板,紧抓人民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利益问题,完善利益分配与社会保障领域的法律体系,在保障社会成员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基础上,尽快将公民生态权益的保护纳入到现行法律体系中;另一方面,要在立法层面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格权。党的十九大首次将“人格权”写入报告中,充分显示了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维护公民的人格尊严,是使人民生活幸福的重要前提。在保障公民各项民生权利的基础上,于立法层面切实维护好公民的人格权,才能够让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其次,维护法律尊严,必须严格制约公权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处于网络舆论聚光灯的时刻关注中,各级机关干部若不能严格依法行政,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产生极大破坏。在治理主体层面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完善防腐法律体系、严格执行治腐制度,保证领导干部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依法履职履责,杜绝不作为与乱作为现象;此外,要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建设,增强机关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与法治能力,改善执法质量与执法效率,使之善于运用法治方式解决行政执法中的利益纠纷问题,树立治理主体的行政执法权威,增强政府服务的群众满意度。
最后,要保障司法公正,维护法律权威。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 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 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法律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平正义具有正向引领作用,一旦司法防线失守,社会公平正义必然受到公众质疑,法律尊严必将荡然无存。维护司法公正,需要执法者面对社会群体性事件不纵容退让,承担舆论的汹汹压力不变更妥协,紧守法治底线,保证司法活动的专业性;在执法过程中,执法者还要积极接受舆论与社会监督,做到司法信息与司法过程公开透明,以客观公正的司法执法树立法律权威,建立起国家党政机关的公信力。JS
参考文献 :
[1]汪民安.从国家理性到生命政治:福柯论治理术[J].文化研究,2014(01):100-118.
[2]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Mogens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M]. OxfordBlackwell Pub,1991:81-84.
[4]郑永流.英国法治思想和制度的起源与变迁[J].清华法治论衡,2002(00):295-350.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7.
[6]西塞罗.论共和国[M].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20.
[7]西塞罗.论法律[M].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95.
[8]詹宁斯.法与宪法[M].龚祥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9]爱德华·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M].强世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21.
[10]孟广林.“王在法下”的浪漫想象:中世纪英国“法治传统”再认识[J].中国社会科学,2014(04):182-203,208.
[11]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翟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2]蒋焰.16、17世纪英国新闻文化的兴起[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67(04).
[13]阎照祥.英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2.
[14]温斯坦莱.温斯坦莱文集[M].任国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0.
[15]施拉姆.人类传播史[M].游梓翔,吴韵仪,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94.
[16]JoadRaymond. Pamphlets and Pamphleteering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17]维诺格拉多夫.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M].何清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5.
[18]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6.
[19]伊丽莎白·艾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20]H.haytor.From Script to Print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Literature[M].Cambridgh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1.
[21]T.Watt.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1550-1640[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12.
[22]L.Weatherill. Consumer Behaviour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Britain,1660 -1760.London:Routledge,1988:107.
[23]荆学民,苏颖.论政治传播的公共性[J].天津社会科学,2014(04):62-66.
[24]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5]Robert Filmer. Partriacha and Other Writings.ed.by Johann P.Sommervill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26]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M].张洁,田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2.
[27]罗莹,刘冰.网络信息传播效果研究[J].情报科学,2009,27(10):1487-1491.
[28]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3.
[29]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M].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1-42.
[30]格特鲁德·西美尔法布.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M].齐安儒,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8.
[31]叶海涛,方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媒体传播研究述评[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05):29-47.
[32]文新良.“两个舆论场”的融合路径探析[J].新闻界,2018(07):82-86.
[33]李彪.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与治理范式新转向[J].新闻记者,2018(05):28-34.
[34]荀况.荀子[M].杨倞,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47.
[35]张文显.法治中国的理论建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08.
[36]培根.培根论说文集[M].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216.
The Transmiss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Ruling -by -Law Thought of Modern Britain
YE Hai -tao ,FANG Zheng
(College of Marx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7, China)
Abstract :The ruling-by-law thought originated from the social reformation in modern Britain. In early 17th century, the conflict between British bourgeoisie and feudal nobility quick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syste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int media and the increasing of the amount of readers, the modern political values centered on rights, such as ruling-by-law, equality, freedom etc., were offered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be widely transmitted.
Key Words : Britain; ruling-by-law; transmission; enlightenment
中图分类号 :DF49
文献标志码: 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9.01.10
文章编号 :1008-4355(2019)01-0114-10
收稿日期 :2018-11-14
基金项目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的中国生态政治学逻辑建构研究”(16BKS062);2017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线开放课程资源库建设”(201702023023);2018 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研究”(18ZDL23)
作者简介 :叶海涛(1973),男,山东曹县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方正(1991),男,安徽芜湖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任编辑 :陈笑春
标签:英国论文; 法治论文; 传播论文; 启示论文;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