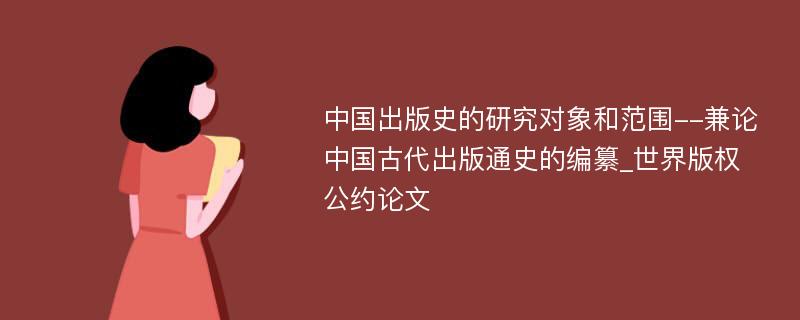
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关于编撰中国古代出版通史的基本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史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中国论文,研究对象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08)03-0083-05
一般说,古代出版史就是书籍出版史。古代研究书籍的学问称书志学。在书志学中,出版史与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文献学相比,与书籍史、刻书史相比,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众所周知,建设新学科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学科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研究对象、范围的任何不科学或不恰当,都将妨碍学科建设。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有了文字就一定有书籍,也不是有了书籍就一定有出版。最早的出版,本是书籍传播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里,涉及如何理解出版概念。科学界定出版概念,是界定出版史研究对象、范围的出发点。出版活动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出版活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社会环境对出版的存在方式、发展演变以及成就与不足等,常常有重大影响或决定性影响。鉴于此,出版史的研究范围除了历史上出版的基本过程、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外,还必须包括社会历史环境,特别是给出版以重大影响的经济、文化、技术等社会因素。确定了出版史的研究对象、范围,才能有的放矢地搜集资料,避免事倍功半。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出版的产生发展与历史演变。再根据出版自身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做历史分期的工作。本文历史分期的主要根据并非社会发展阶段或朝代更替,而是出版自身的阶段性特征,以体现出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过程。
1 关于出版概念——两要素说与三要素说
出版概念是考察出版史的出发点,有什么样的出版概念,大致就有什么样的出版史。学术界提出的出版概念很多。然而,就出版概念如何表述出版过程看,当今世界上的出版概念主要是两大类:一类为两要素说;另一类为三要素说。
所谓两要素说,是根据复制与发行这两项来界定出版概念。例如,《世界版权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之第六条:“本公约所用的‘出版’一词,系指以一定有形方式复制某作品,并将复制本在公众中分销,以供阅读,或以其他方式观赏。”① 《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之第三条第三款:“就作品的性质而言,无论复制本以何种方式制作,只要可以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即构成出版。”② 上面两个国际公认的版权公约都认为,将作品复制了,并且发行了,就是“出版”。换言之,兼具复制、发行这两项就是出版。这就是两要素说。世界上许多工具书都以两要素说界定出版,具体表述不同,恕不一一列举。
所谓三要素说,是根据编辑、复制、发行这三项来界定出版概念。例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73年)“出版”条说:“出版是对书写的著作物的选择、复制与发行。尽管它在现代依赖于印刷与纸张,但它的产生比两者都要早。”③ 上面所说“选择”,代表出版过程中的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五款:“出版,指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以上两例都认为,兼具编辑、复制、发行这三项就是出版。这就是三要素说。世界上许多工具书都以三要素说界定出版,具体表述不同,恕不一一列举。
中国古代的出版概念,是两要素说。最早,宋代出版物上的新词如“刊行”“印行”“板行”“梓行”等④,现在看来都是“出版”的意思。这些宋代新出现的词语中,“刊”“印”“板”“梓”等,系指印刷,就是复制;“行”,为行布,大致相当于发行。不过,古人经常略去“行”字,单以“刊”“梓”“雕印”“镂版”等代表出版。略去“行”字的原因,主要是受观念上重刊刻而轻发行的影响,也是社会观念中轻商或贱商的一种表现。观念上轻视发行,不等于不存在发行。略去“行”字,仅以“刊”“梓”“雕印”等表示出版,并不说明在完整的出版概念中完全没有发行的地位。
将两要素说与三要素说做比较,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有无编辑这一项。在现代社会,编辑、复制、发行是出版过程中最重要的三个基本环节。此外,出版过程还存在其他环节,如管理、物流、科研、教育等。从历史上考察,各国古代最早的出版活动大都没有编辑这一环节;在现代出版中,编辑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编辑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出版诞生的标志,它是出版成熟或趋于成熟的标志。没有编辑的出版活动普遍存在于古代。而《世界版权公约》与《伯尔尼公约》都根据两要素说界定出版,说明现代社会同样存在没有编辑的出版活动。一般说,两要素说代表早期的或起码的出版活动;三要素说代表成熟的出版活动。研究出版史需以三要素说作为出发点,考察历史上包括两要素在内的所有出版现象,进而探讨出版活动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这里要说明,出版概念中的编辑,理所当然是出版编辑,不能是别的什么编辑。当今学术界所说编辑有两种:一是作为出版工作一部分的编辑(或出版以外其他媒体工作一部分的编辑),另一是作为著作方式之一的编辑。前一种编辑为出版编辑,它是出版过程中三个重要环节之一,其作用是为下一步的复制准备合格的文本。后一种编辑不属于出版过程中三个重要环节之一,与出版编辑是两回事。出版史若将作为著作方式之一的编辑视为出版编辑,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必然导致逻辑混乱,损害科学性。
与出版概念直接相关的重要概念,是书籍概念。古代出版史基本上是书籍出版史,因此书籍概念的混乱,必定造成出版概念的混乱,进而造成出版史内容的混乱。今天,国外常以超过若干页的非连续性出版物,称为书籍。这样界定书籍,仅可用于册页装的书籍,不可用于古代常见的非册页装书籍,因而不适用于出版史。书史学家刘国钧教授强调将书籍“专用材料”,作为区别古代书籍与非书籍的根据。他说,“正式的书籍,就是指用文字写在或印在具有一定形态的专用材料上以借(供)人阅读为目的的著作物。甲骨、青铜都不是专门作为书写用的材料。专门作为书写用的材料在我国最早的是经过整治的竹片与木板。”⑤ 刘国钧认为,凡书籍必须使用可以书写的“专用材料”。古代的青铜器或甲骨,都是文字载体而不是书籍“专用材料”,因此凡以青铜与甲骨为载体的作品都不是“书籍”。这种见解至今具有价值。此外,刘国钧又将是否“以传播知识为目的”去界定书籍概念,如说:“图书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而用文字或图画记录于一定形式的材料之上的著作物。”⑥ 强调“以传播知识为目的”,本意是借此区别书籍与古代官府的文书档案。问题在于,并非只有书籍才“以传播知识为目的”。有些铜器铭文也“以传播知识为目的”,像孔子在周太庙见过的《金人铭》等⑦。铜器并非书籍“专用材料”,这样未免陷入自相矛盾。将“以传播知识为目的”界定书籍概念,并不妥当。书籍与文书档案的区别,可以用是否向公众传播来界定。
著名出版学家林穗芳提出这样的书籍概念:“书籍是用文字、图画、声音或其他符号按一定的主题和结构系统组成一个独立的整体,以印刷或非印刷的方式复制在供携带的载体上以向公众传播的作品。”⑧ 林穗芳认为,书籍是以某种方式复制在某种载体(书籍材料)上的作品,这是多数书籍概念的共同内容。此外,林穗芳强调两点。其一,书籍材料(载体)必须是既能“以印刷与非印刷的方式复制”,又可以“供携带”。书籍材料可以“供携带”,书籍才可以流通。出版学认为,凡书籍都是可以流通的,可以流通是书籍的固有特征;不能流通者不能成为书籍,更不能成为出版物。认为书籍材料(载体)除了可以复制,还必须可以携带(流通),是颇为深刻的见解。其二,可以“向公众传播”。凡书籍都可以向公众传播,不能用于公众传播者不能成为书籍。在古代,书籍可以公众传播,但不一定已经实现公众传播,这也是要注意的。
比较上面两个书籍概念,我们以为林穗芳的概念可以包括刘国钧的概念,又可以避免其不足,更为可取。
2 出版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兼谈方法问题
古代出版大致就是书籍出版,所以出版史的对象以书籍出版为根据,又不与报纸杂志的出版相抵触为限。不论古代或现代的出版,无不表现为一个过程,不论两要素还是三要素的出版都表现为一个过程。再从传播学看,书籍出版的过程就是书籍传播的过程;所有书籍传播的过程,都以作者为起点,以读者为终点。从书籍传播过程看,出版与非出版的区别,关键在于是否进行公众传播。凡有公众传播,必有公众读者。如前面所引出版概念中,或说“将复制本在公众中分销”,或说“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或说“向公众发行”,意思都是公众传播。可见,不论两要素还是三要素的出版,都以公众传播作为目的与归宿。反过来看,有书籍而不向公众传播,就不算是出版。因此,出版概念也可以这样界定:以公众传播为宗旨的,以作者为起点、读者为终点的书籍传播。这样界定出版概念,包括了两要素说与三要素说而不与两者相矛盾,又可以避免在研究中遭遇不同出版概念的困扰。
据此,我们可以界定出版史的对象是:历史上以公众传播为宗旨,以作者为起点、读者为终点的书籍传播。如此界定出版史对象,要点有二。其一,以书籍是否公众传播,区别出版与非出版。其二,以作者为起点、读者为终点,借以代表出版过程,既包括两要素与三要素的出版过程,也包括其他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的出版过程。就前一点而言,重在考察古代书籍如何实现公众传播,以及书籍公众传播在历史上的进步与发展。如今的出版史研究,往往不管书籍是否公众传播,因而在书籍尚未公众传播的时代,就认为有出版编辑,有书籍发行,甚至断言出现了大编辑家。社会上书籍尚未公众传播,就是出版尚未诞生。在出版尚未诞生的社会上,怎能有出版编辑?又怎能产生为出版工作的大编辑家?如此违背逻辑,岂非笑话?所以,古代出版史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探讨古代书籍如何走向公众传播?何时开始公众传播?就后一点而言,旨在考察历史上以作者为起点、读者为终点的书籍传播过程的发展演变状况,其中重点弄清楚三个问题:作者的作品如何问世?读者如何获得读物?联系作者与读者的中间环节的地位作用如何?这也是为了避免将现成的出版概念当作条条框框,生搬硬套,便于使出版史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历史资料与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在中国古代,由于受社会环境中重农抑商与贱商主义的压制,汉唐书商无法自己建立书籍作坊,也无法建立发行业,因此面向公众的读者传写成为自汉至唐上千年间书籍流通的主要方式。通过读者传写实现公众传播,它集中体现了汉唐出版的特殊表现形式,独具一格,与众不同。再进一步看,中国古代出版与欧洲古代出版的具体形式不完全一样,与现代出版的差别更大。凡此,就是出版的历史多样性。出版的历史多样性乃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管你承认与否,它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今天,需以清醒的科学态度,尊重出版的历史多样性,研究出版的历史多样性。如果不是这样,不问青红皂白,拿了某个既定概念作为条条框框,乱套数千年历史,或者玩弄编辑、复制、发行三者的魔方组合,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结果必定歪曲历史真相。在我看来,不承认出版的历史多样性,中国出版史不可能走上科学之路。
从出版史的研究对象出发,进而可以确定出版史的研究范围大致是:历史上书籍传播过程与在这过程中出现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以及影响、制约书籍传播的社会历史环境。按照对象、范围、方法三者统一的道理,有怎样的对象、范围,就应有怎样的研究方法。将社会环境列入出版史范围,本身就具有方法论意义。将出版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乃是出版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影响、制约出版活动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人口、地理、交通等诸多因素,其中以文化、经济、技术这三方面因素最具经常的重要意义。兹说明于下。
第一,文化因素,包括文化政策与文化教育事业等。
出版活动是一种文化活动。集中体现国家意志与政治意图的文化政策,为书籍传播或出版活动设定规范、纪律、自由度等。以先秦到两汉的文化政策为例。春秋以前,如章学诚说是“学在官府”,官府对社会文化实行铁桶般的全面垄断,民间没有学校,私家没有著作。在这种垄断政策统治下产生了所谓“书在官府”,书籍由官府垄断,不准随便复制而公诸于众。春秋后期至战国年间,官府文化垄断在私学与诸子的不断冲击下,节节败退,渐趋瓦解。而它的最后一次垂死挣扎是,秦代禁止私学,“行挟书律”,焚书坑儒。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官方第一次宣布允许书籍自由流通。从汉初开始,放松文化管制,逐渐结束了官府垄断文化的漫长历史,最后形成以儒学为主的多元文化。两汉实施文化教育向民间开放的新政策,在这种文化政策影响下,逐步完善了书籍公众传播的条件,促使抄本出版(古典出版)迅速成熟起来。可见考察古代文化政策,对弄清出版史上一些重大问题,颇为有益。
社会上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衰成败,经常成为影响出版兴衰的一个直接因素。自汉以来,文化教育的发展进步对出版繁荣的推动作用,特别重要。在古代,文化教育掌握在士阶层手里,而书籍的作者与读者又都是士大夫。因此,士阶层的价值观念、兴趣爱好、风俗习尚等对出版的影响,常常比书商更大,更重要。研究者不可不察。
第二,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制度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等。
出版活动并非仅仅是文化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将出版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就必须联系社会经济制度进行考察。从经济学看,书是书籍生产的最终产品;书可以是商品,也可以不是商品。书一旦成为商品,就产生了书籍市场与书商。我国的书籍市场与书商,最早产生于西汉后期。在此以前,书籍不能买卖,原因主要是礼乐制度与官书垄断。有书籍市场,才有书商。书籍市场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分,不能不与社会经济制度保持一致。所以考察历史上的书籍市场与书商,必须联系社会历史环境,特别是社会经济制度。
西汉以来,由于推行重农抑商的缘故,社会上形成了无所不在的自给自足经济。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书籍经济不可能不走自给自足的道路。今天,有人以为书籍经济可以脱离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独自走市场化的道路,无非是脱离历史环境的一种想入非非而已。西汉以后,一方面是书籍市场发展缓慢,另一方面是自给自足的书籍经济,随着书籍事业的繁荣而迅速发展起来,它的具体表现就是读者传写风行全国。出版学中读者的含义,包括官府、寺观等机构单位,也包括官员、藏书家等个人。读者传写的意思是,读者通过“传写”复制作品,进而制成供自己使用的书卷。在这个过程中,制作书籍的原材料如纸笔等,都是市场上的商品;抄写(复制)的劳动力也可以是商品,就是古人所说“佣书”。“传写”的最终产品——书卷只供读者自己使用,它不是商品。从最终产品——书卷看,读者传写以自给自足为目的,不以商品交换为目的,所以是典型的自给自足书籍经济。公元3世纪因“传写”《三都赋》而引起“洛阳纸贵”,最能说明读者传写对公众传播的巨大作用。从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看,出版活动中出现读者传写盛行,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
历史上书商做什么与怎么做,归根结蒂地说不决定于书商自己,首先决定于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经济制度为书商提供的条件是什么,提供的舞台有多大。自汉至唐的书商,都生活在自给自足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必须面对无所不在的读者传写。读者传写愈是盛行,书商的地盘就愈小。此外,还存在制约书商活动的两大社会因素。其一,秦汉至唐,国家实施将商人权利剥夺殆尽的“市籍”制。商人因“市籍”而沦为贱民,地位与奴婢相似。汉唐书商都是“入籍”贱民,无有例外。其二,书商所面对的作者与读者是士大夫,而士大夫是重农抑商的坚定倡导者,无不奉行贱商主义。从社会阶层分析,士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尊士而贱商,早已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在士人看来,市场为藏污纳垢的场所,书商与所有商人都是没有道德、没有文化之徒。西汉扬雄讥称书商为卖书市肆而不懂书中意思⑨,唐代的《北史》作者在《阳尼传》中故意记载书商如何弄虚作假,欺骗读者,这两例都说明士大夫心里瞧不起书商。上面两个客观因素决定汉唐书商,在作者、读者面前岂止是低人一等!完全不具平等相处的起码条件。因此,书商没有办法也没有可能将复制与流通这两大环节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进而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充分发挥桥梁作用。从资料看,汉唐书商的工作主要是买卖旧书,汉唐书肆其实是旧书店。与现代书商相比,汉唐书商以买卖旧书为主,这就是所谓“书商边缘化”。结合社会历史环境考察,“书商边缘化”是合乎逻辑的一种必然现象。到宋代,“市籍”取消了,市场宵禁也解除了,社会上商品经济比唐代发达,市场比唐代繁荣。与此相适应,宋代书籍市场的规模与水平都超过唐代,书商边缘化现象随之逐渐缓解(不是完全消失)。凡此说明,书籍市场与书商跟随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制度的变革而变革。脱离社会历史环境孤立地考察书商或书籍市场,结果往往是以今例古,用空想代替事实。
第三,科技因素,指直接应用于出版的科学技术。
在传播学看来,书籍是一种传播媒介或媒介工具。制作媒介工具要靠科学技术;制作先进的媒介工具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众所周知,出版依赖于三大发明,即文字、纸张、印刷。”⑩ 在古代,造纸与印刷这两项最重要的出版技术都是中国发明的,它们对中国出版乃至世界出版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在出版学中,纸是一种书籍材料,造纸是制作书籍材料的一种技术。而书籍作为媒介工具的作用如何,首先取决于书籍材料是否优良,取决于制作书籍材料的技术是否先进。在世界古代史上,纸是最佳书籍材料,纸书是最先进的媒介工具。纸,是中国汉代发明的。自东汉蔡伦成功制作“蔡侯纸”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推广纸书的时代。中国是最早使用纸与纸书的国家。与其他书籍媒介相比,纸书制作容易,使用方便,价格便宜,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其他书籍媒介都望尘莫及。在历史上,使用纸书是书籍媒介的第一次革命,为我国书籍出版开创了新时代。印刷,是一种复制技术,就是将作品复制到书籍材料上的一种技术。书籍生产的两件大事就是制作书籍材料与复制作品。在印刷出现以前,世界各国复制作品的方法都是手抄,或以手抄为主。与手抄复制相比,印刷复制可以使书籍生产从单体制作变为批量生产,从而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将纸书与印刷结合起来,极大地提高了书籍媒介的传播功能与效率。印刷大约发明于隋唐之际。自五代开始,雕版印刷被大规模引入出版,从而引发了书籍媒介的另一次革命。不论古代还是现代,先进的出版技术都是促进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有时是关键因素。不断应用先进技术是中国出版史引以为豪的传统作风。从方法论看,出版史关心的重点并不是科技本身,而是科技进步对出版进步的作用与影响。
从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看,中国古代出版的发展进步,受文化因素与技术因素这两方面的推动作用最大,可以称为文化推动型与技术推动型。毋庸讳言,流通与发行是中国古代出版最薄弱的环节。自五代开始,我国书籍发行业逐步发展,书籍市场迅速走上繁荣之路。但总的看来,书籍发行的进步因受重农抑商的制约而困难重重,市场动力不足始终是困扰晚清以前出版业的基本问题。
(收稿日期:2008-02-14)
注释:
① 林穗芳来信指出,《世界版权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第六条中“分销”一词,英文为distribution,中文译文以“发行”为是。从中文词义看,发行可以包括分销,分销不可包括发行。
② 林穗芳《有关出版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出版史料》,2003年第3期)认为(《伯尔尼公约》这段话是对“已出版的作品”的解释,并不是直接给出版下定义,可参考。
③⑧ 林穗芳.中外编辑出版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5,39。
④ 林书清编著《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出版)所录宋刻牌记如:(《三苏文粹》:“婺州义乌青口吴宅桂堂刊行”;《唐书》:“建安魏仲立宅刊行”;《文选五臣注》:“杭州猫儿桥东岸开笺纸马铺锺家印行”;《钜宋广韵》:“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印行”;《画继》:“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等。
⑤⑥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20,2。
⑦ 刘向.说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8。
⑨ 扬雄《法言·吾子》(《诸子集成》本):“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晋人李轨注:“书肆为卖书于市,不能释义。”“说铃为铃喻小声,犹小说不合大雅。”按:“书肆”“说铃”皆为比喻。扬雄的原意大致是:爱好读书而不能折中于孔子,就像是卖书于市肆而不能释义的书商;好发议论而不能折中于孔子,就像只能敲出小声而不合乎大雅之音的铃铛。如今,常将扬雄的话解释为书商读书不限于孔子儒家,理解为书商读书广泛,以致博学。如此理解,与原意大相径庭。
⑩ P.S.昂温著;陈生铮译.外国出版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