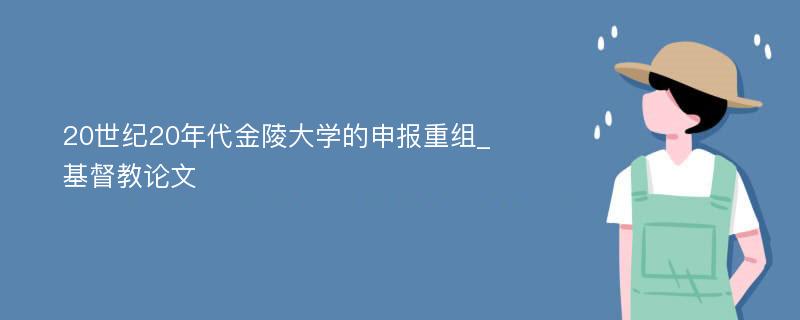
20世纪20年代金陵大学的立案与改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陵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陵大学(简称“金大”)由南京的三所基督教书院合并而成。其一是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由美国的美以美会(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创办于1888年。其二是基督书院(The Christian College),由美国基督会(Foreign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创办于1891年。还有一个是益智书院(The Presbyterian Academy),由美国长老会(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创办于1894年。1906年,益智书院与基督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The Union Christian College)。1910年,宏育书院与汇文书院合并,建立新的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金大于1911年获得美国纽约州教育局和纽约大学的认可,其毕业生由纽约大学校董会授予学士学位。①金大是中国第一所由基督教各差会联合办学的高等教育机构。②20世纪20年代初掀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与“收回教育权运动”,以及1927年政权鼎革对金大外部属性与内部治理体系造成重大冲击。该校在美国的决策群体、校方和中国籍教师群体被动或主动地做出各种回应,直至学校的治理结构完成根本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陈裕光由参与校内变革的重要一员而成为改组后的第一任中国籍校长,并推动金大向南京国民政府完成立案。 金大校史研究已有一定基础。张宪文主编的《金陵大学史》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专门以金大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③英语学界的中国教会大学个案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启动,但以笔者目力所及,尚无以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为研究主题的英文论文。 研究金大校史,有两种最主要的档案史料。一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私立金陵大学档案”;二是“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第四系列“中国教会大学资料”(Series IV China College Files)中的“金陵大学档案”。④以上两种档案中英文并举,除小部分内容交叉重叠,余者可参照互补。不过,由于档案开放以及语言等问题,这两种档案未得到充分利用。金大内部诸多史实重建有赖于英文档案,特别是对英文会议档案的条理贯通,若只靠中文档案及报刊、回忆录等,往往使许多史实模糊不清、似是而非。此外,学界对教会大学立案问题也有充分的个案研究。⑤然而,既有研究对北京政府的立案措置及教会大学的应对重视不足。其实,这一问题应与教会大学内部的权力调整、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案措置进行通盘考量。本文在利用档案及其他史料的基础上,全面考察20世纪20年代金陵大学的两次立案的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权力结构改组,以呈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与革命运动中,教会大学如何应对政府政策与政局变动以保持继续办学,并迈向“中国化”。 一、北京政府的立案法令与金陵大学的应对 金大的首任院长包文(A.J.Bowen),美国伊利诺伊州人,1897年来华,是南京汇文书院的第二任院长,他力主将南京的基督教书院合并成一所大学。从金大建校到1927年,包文长期担任校长,是校内最高行政首脑。不过,在法理上,校长并不负金大的最高责任。 金大是美国几个基督教差会在中国合作的教育事业,具“派出性”,其本部仍在美国。在美国纽约设有金陵大学的“托事部”(Board of Trustees,中文亦有译作“托管会”、“托事会”或“美国董事会”),成员由创校的美以美会、基督会与长老会派员组成,此后北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参与金大的办学,其成员亦有加入托事部。 托事部的职责之一是持有金大拥有或借来的财产,投资和管理基本金。⑥换言之,金大的校产所有者是金大托事部,托事部对校产有充分的所有权和处置权。托事部的另一项职责是批准或否决在南京的理事会(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的成员、提名理事会成员和任命校长、罢免不称职的校长。⑦1925年修正的《金陵大学细则》明确规定托事部对金大的经济和行政负全责。⑧ 在金大的相关英文文件中,在美国的托事部称Home,在中国的金陵大学称Field,这对指称很形象地说明金大“西人治校”和“教会治校”的治理特征。不过,从实际办学情形而言,Home毕竟和Field遥隔万里,托事部“遥领”的实效性有时可能较弱,而在地设置的另一个决策机构正好弥补此缺憾。这一机构即设于南京的理事会(Board of Managers)⑨。 根据并校前的制度设计,金大同时设置理事会和托事部。理事会是在地(Field)的“校董会”,对校政的决策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对托事部而言,理事会是其在南京的执行机构;而对金大而言,理事会又是其决策机构。理事会成立之初,其成员均系在华的美籍差会传教士。1915年后,理事会开始有中国籍人士加入(由理事会自行选任)。⑩此后,理事会又渐次有同学会代表(即校友)与差会中的中国籍人士加入。金大理事会屡次增加中国籍成员。据校长包文言,在理事会中,中国籍理事将逐年增加,直至“中西各半”。(11) 托事部和理事会共同构成金大治理结构的“顶端”。托事部授权理事会处理校务,但选聘校长及教授必须得到托事部的最后同意。(12)在托事部和理事会之下,校长包文是具体校务的最高执行者,同时是理事会的主席,掌握了在地的最高治理权。副校长文怀恩(John E.Williams)的主要职责是沟通南京学校与美国托事部及各合作差会的关系,并负责在美国为学校募款。文怀恩长期以“休假”的名义在美国,最长的一次是连续三年在美国休假后才返回南京。(13)而大学和各院系的绝大部分行政权力均掌握在西籍教师之手,可以说是“西教士独掌校权”。(14) 金大在建校初期全然由西人所办所治,基督化是其根本性质。在当时,这是所有中国教会大学的共性。在清末民初,教会学校是一股独特的力量,基本游离于中国的教育体制之外。从1924年起,中国教育界提出“收回教育权”的口号,即在国内提倡民族性的教育,反对教会教育,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将教会学校(包括其他外国人在华办理的教育事业)收归中国人之手,掀起轰轰烈烈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这场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延续,之后又因1925年五卅运动引发的全国性反帝民族主义运动及国民革命而声势更为壮大。(15) 无疑,“收回教育权运动”对中国各教会大学造成极大的影响,它们被迫回应这一“政治正确”的民族主义浪潮。这涉及两个方面:对内,教会大学是否应将更多的学校行政权力开放给中国人;对外,教会大学是否应向中国政府注册成为“私立大学”,即立案。就后者而言,教会学校从清末起就面临这一问题。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国家对教会学校并无一以贯之的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实质性管理或规范。清末全国兴办新式学堂,各级教会教育也陆续进入中国。关于外国人设学堂,学部称,清廷的学堂章程并无允许办理的条文,但并不要求此类学堂向政府登记,“除已设各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均无庸立案,所有学生,概不给予奖励”。(16)可以说,在清末时期,国家对教会学校实施的是放任政策,这与当时朝野上下急切兴学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在进入民国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教会学校的办学依然游离于国家教育体制外。关于高等教育部分,北京政府曾对私立大学有一系列的规定,教育部于1912年10月颁布《大学令》,其中第21条规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17),即承认私立大学的合法性。翌年1月16日,教育部颁布《私立大学规程》。从条文看,教育部仅规定私立大学设立时须将设立之目的、名称、位置、学则、学生定额、地基房舍之所有者及其平面图、经费及维持之方法和开校年月等“呈请教育总长认可”,而对于私立大学的内部组织和科系课程没有特别规范。(18)1月23日,教育部又颁布《私立大学立案办法》,要求3个月之内所有私立大学遵照《私立大学规程》报部备查,一年后由部派员视察,如果成绩良好,准予正式备案。(19)当然,民初私立大学认可、立案的相关规定的约束力并不强。 不过,在当时的政策语境中,教会大学并不算作国家规定的“私立大学”,而是单列为“外人设立学校”。北京政府对于此类学校有专门规定者始于1917年。该年5月,教育部以第8号布告的形式颁布《中外人士设专门以上同等学校考核待遇办法》(20),其中规定“此项学校办理确有成绩者,经本部派员视察后得认为大学同等学校或专门学校同等学校”,这类学校呈请教育部认定时要将具体办学情况造册上报。1919年3月,教育部颁布第6号布告,规定“凡外国人在内地所设专门以上学校,不以传布宗教为目的,且不列宗教科者,准其援照私立专门学校规程或大学规程及专门以上同等学校待遇法,呈请本部核查办理”。此条显系针对各级教会学校。当时中国的此类学校概由外国教会创办,是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各校均开设宗教科目,这是其实现教育宗旨的重要手段。如果依照1919年教育部第6号布告的规定,各教会学校向政府立案,教会学校的基督教性质便荡然无存。1920年11月,教育部又颁布第11号布告,称近年来外国人士在各地设立专门以上学校较多,但大部分未经教育部认可,要求“外国人之在国内设立高等以上学校者,许其援照大学令、专门学校令以及大学专门学校各项规程办法,呈请本部查核办理,以泯畛域,而期一致”。(21) 教育部的几则官方法令表明国家对教会大学办学的基本态度,教会大学方面对此确实有一定反应。1917年,之江大学曾考虑过向北京政府申请立案,未果。(22)金大的立案情况则比较复杂。1920年教育部第11号布告颁布后,金大即向教育部提出其大学部(colleges,含文科、农林科与预科)立案的请求。(23)翌年2月,教育部派员视察该校。视察委员向部方报告,认为金大农科“成绩既有可观,办法亦属得宜,应许暂准备案”,而文科和林科“内容既未充实,办法亦欠妥善”,应该加以整顿,另外还要求必修的宗教科目改为选修。(24)1921年8月,金大农林科(25)在北京政府教育部立案。(26)在同年10月13日召开的理事会会议上,校长包文通报此消息。他表示,当初向教育部呈请立案时并不得知须将宗教科目改为选修的要求,既然教育部提出这一要求,金大今后不再谋求立案。(27)11月1日,托事部召开非正式会议,称收到教育部关于金大立案的公文,托事部将在收到南京的意见后再做出决定。(28)此时,托事部应该尚未收到10月13日理事会会议记录。12月20日,托事部召开年会,会议宣读校长报告。该报告指出,在文理科设置宗教必修科目成为立案的障碍。托事部对于立案问题进行讨论,并参考理事会会议记录,决定由执行委员会在下一次托事部会议中宣布声明。(29) 托事部自然不同意以牺牲宗教必修科目为代价而立案,如此就意味着学校基督教性质的丧失,但金大又接受了农林科立案的部令,所以这是一种“部分立案”的特殊状况,在当时的各教会大学中绝无仅有。这同时也体现金大办学者在向政府立案和保持基督教性之间的复杂心态。不过,从整体而言,在1925年前教育部的立案政策及条件对于教会大学没有实质性触动,除了金大,没有一所教会大学向政府立案。 1925年11月1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设立学校认可办法》6条: (一)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遵照教育部所颁布之各等学校法令规程办理者,得依照教育部所颁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二)学校名称上,应冠以私立字样。(三)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四)学校设有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过半数。(五)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六)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科。 该办法公布后,此前教育部公布所有同类法令均作废。(30)此案似一颗深水炸弹,在中国基督教教育界迅速引爆,并彻底改变了各教会大学对立案的态度。从条文内容看,相较此前教育部公布的立案法令,“1925年办法”各条更为明确、严苛。例如,“校长须为中国人”之条,对于当时各教会大学校长均为西人的现实情形,无疑是极大的挑战;而第五条更使教会大学无法接受。两个多月后,教育部又规定:“国内私立学校及外人捐资所立学校,关于一切课程训育管理事项,须按照部章,如有违反者,应即停办。”(31)这个规定亦颇严格,彰显教育部的权威。 在这些条文的背后的大语境是五卅运动引发的全国性反帝民族主义高潮,对教会大学在华的合法性构成巨大威胁。这就使得教会大学不仅要正面“1925年办法”,又要借助是否立案或如何立案之法,以克服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教会学校在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中的困境,除了合法性问题外,还涉及实际利益。一般而言,当时教会大学的收入除了基本金利息收益和合作差会拨款外,学生缴费是其大宗。但在中国民族主义高昂之际,很多国人以子弟入外人学校为耻,教会学校面临生源不足的生存危机。例如1926年春季学期,因受“非基督教运动”影响,金陵大学有100—120名学生转学到同城的国立东南大学。(32) 在“1925年办法”颁布之前,中国基督教教育界已有较为充分的心理和行动准备。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华人基督教领袖和政学两界的基督教徒名人较主动对此进行正面回应,普遍要求在教会大学内停止强迫的宗教信仰仪式和宗教科目,并向中国政府立案。如燕京大学中国籍教授吴雷川就较早提出要改良现有的教会教育,他称:“教会的保守性太重,自从国家遍设学校之后,教会学校的进步,反而迟滞……一般非难基督教的人,以为基督教不应将传道事业与教育事业,并为一谈,更不当以学校为传道机关。”他指出教会中学应该“删去圣经”、“废去早晚祷”。(33)另一位中国教育界的教徒、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董事朱经农说得更为直白:“教会大学对于宗教事项,应该任人自由选择,不可加以强迫”,主张任何教会学校都要向中国政府注册。(34)相较而言,外籍传教士和教会大学管理者的回应要保守得多(35),他们坚持教会大学的基督教特性和外国性,上述1926年前各教会大学拒绝立案即是例证。然而,在激烈的民族主义浪潮中,他们的态度不可能一成不变。(36) 1925年4月召开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董事会年会做出“学校注册案”决议:“基督教学校应即速向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注册立案;惟须顾及基督教之特殊功用,不受注册之限制。”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副总干事程湘帆拟就《基督教学校注册之意义》的意见书,作为会议的官方文件。(37) 曾任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宗教教育参事会干事的缪秋笙回忆,1923年吴哲夫(Edward W.Wallace)就任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代理总干事,他倾向于接受中国政府的立案要求,并在教育会内增加华人教徒的参与。吴哲夫向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董事会提议成立“基督教学校注册委员会”,以刘廷芳、程湘帆(38)、赵运文等为委员,到北京去活动。1925年9月间,刘廷芳、程湘帆与赵运文三人草拟“基督教教育近年来进步情况”的说帖,呈送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次长、参议、司长等重要人物。1925年11月16日,教育部公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教育部承认教会学校为私立学校,吴哲夫认为这是重大胜利。(39)照缪秋笙之意,教育部颁布“1925年办法”前,教会方面已经和政府方面做过相当多的沟通,教育部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其实,“1925年办法”颁布后,教育部在舆论环境中也颇显尴尬。当时《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一篇未署名文章,认为“北京政府教育部关于教会学校立案的六条规定,态度是友善的”,这些规定已比之前宽松。但教育部正处在夹缝之中,一面是中国的激进主义者大肆批判这个条例,要求颁布更加严格的条例以迫使教会学校关门;另一面是基督教徒和自由主义者恳请教育部落实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立案。(40) 1926年2月,中华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41)隔年会在上海沪江学院举行,会议的焦点议题就是立案。该会议有两场关于教会大学立案问题的专门讨论会,但会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会议也未做出任何相关决议,未采纳任何调查结果,但接受了立案的原则,并支持1925年4月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董事会年会“学校注册案”决议。(42) 与下属的高等教育参事会相比,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对教会学校立案推进力度更大。1926年5月,该会董事会召开第二次年会,吴哲夫做干事报告。他指出,1925年11月16日教育部颁布的《外人设立学校认可办法》,“颇使基督教教育界大大的失望,但是较之从前的注册条例确有极大进步”,原来教会学校被单列为一类,后经过基督教教育同仁的请求,政府允许按照私立学校注册条例办理,“基督教学校既在中国设立,则教育中当然应含有中国的性质;不但不能与中华民国的愿望相反,而且必须至少能代表一部分中国人的意旨。此外,我们更要承认中国政府有管辖我们学校之实权。至于讲到基督教教育与政府怎样接近而发生联络关系,则更为我们不可推委[诿]的责任”。(43)吴哲夫的意思很明确,教会学校若想在中国继续办学,非立案不可。此次会议作出关于立案的3项决议: (一)特派一委员会进京,与教育部作非正式之接洽,说明其基督教学校请求政府注册之诚意,与当前之阻碍,并希望当局有以解决之。(二)催请全国基督教学校,即请实行注册办法第一,二,三,四条及第六条之首项。(三)凡基督教学校,愿照颁布之条例注册者听之。(44) 这一决议表达得十分直白,即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对于教会学校的立案态度是接受教育部所规定的大部分要求,“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与“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科”两条予以保留,但会继续与教育部保持沟通,协商解决;如果有教会学校完全接受教育部办法立案,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也不会阻拦。据缪秋笙称,这个决议是董事会根据三个参事会的意见,重新斟酌一番,经过吴哲夫的最后修正。决议中的代表,仍由刘廷芳、程湘帆与赵运文等人充任,并委托刘廷芳先在北京布置,使代表团有与教育部人员谈话的机会。因为交通和时局的关系,程、赵未入京,1926年夏,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会长刘廷芳以个人身份向教育部请求解释原第五条疑义。(45)1926年7月6日,北京教育部第188号部批,解释第五条: 据呈,称:“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第五条,是否专就宗旨立言,与信仰及传教自由,不相抵触?请求解释”等情。查该项办法第五条,系言设立学校,当以部定教育宗旨为宗旨;在校内,不应有强迫学生信仰任何宗教,或参加宗教仪式之举,于信仰及传教之自由,并无限制。此批。(46) 从教育部的解释文意看,教会学校向政府立案并不影响校内信教师生的信仰和传教自由,部方已作出很大妥协。即便如此,各教会大学仍采观望态度。之所以如此,胡卫清认为有几个原因:教会大学受西方差会本部控制,在华传教士不能擅作主张;向中国政府立案,教会大学也担心其绝大部分来自西方的经费受到影响;而立案要中国人担任校长,这也是当时传教士不能放心的;传教士也担心学校立案后自己原有的地位受到影响。(47) 教育部颁布“1925年办法”,又于翌年颁布态度软化的“部批第五条解释”,而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和华人教会要人也推动各教会大学立案,但此后究竟有几所大学遵此令立案?以笔者目力所及,卢茨、胡卫清、杨天宏、杨思信和郭淑兰诸著均未言明。(48)此后真正向北京政府教育部立案的只有燕京大学,燕大于1926年冬向北京政府教育部呈请认可,1927年春获准。(49)同一时期,广东岭南大学亦向政府立案获准(1927年3月),不过申请对象是广州国民政府。(50)还有一所教会大学被教育部认可,情况很特殊,这就是金陵大学。前述金大农林科于1921年在北京政府教育部立案,1925年底北京政府教育部援引1915年《私立专门以上学校认可条例》,以民国大学、平民大学、华北大学、金陵大学和协和大学虽经批准立案,但无“认可”字样,一律改为正式认可。(51)如此一来,金陵大学(其实是农林科)被认可为私立大学。有意思的是,金大校方对外公开宣称:“本校为私立大学,所有行政组织一律遵守教育部规定之私立学校规程”;还表示:“本校虽为教会设立,但不强迫任何学生皈依教门,但愿尽吾人义务,使学生明了各种教谛,庶将来作自由的选择。”(52)承认金大是私立大学,言下之意是已经向政府立案,服从政府的规定;而不强制学生的宗教信仰,亦符合教育部“1925年办法”的规定。若如此,金大和教育部两厢情愿,该校立案应该没问题。不过,现实情况要比所宣称者复杂纠结得多。 1926年3月18日,金大理事会召开第22次会议。(53)此会恰是教育部颁布“1925年办法”后金大理事会召集的首次会议,会中应该对立案问题有所讨论。不过,从会议记录看,关于是否立案并无决议。但会中形成两个相关决议,一是组织“立案委员会”(Committee on Registration),由5名委员组成,其中3名中国人,2名外国人,该委员会将研究金大立案的所有问题,并将报告递交执行与经济委员会(54);二是组织“宗教教育委员会”(Committee on Religious Education),同样由5名委员组成,其中3名中国人,2名外国人,该委员会将研究金大的宗教教育问题。显然,此时金大对于立案与否尚未定案,“1925年办法”中的关于取消宗教必修科目的决定是金大考虑立案所涉及的关键问题之一。同样,当时托事部亦未形成立案的决议,不过在1926年4月21日的会议上,专门就教育部“1925年办法”进行讨论,但“因为缺少包文校长明确意见,托事部未形成决议”。(55) 虽然,1926年3月18日金大理事会年会未对立案与否表态,但另一项议程与立案问题息息相关。校长包文在会议上称:“目前学校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比这更严重的是‘华人领导层问题’。我们都知道此问题的急迫性,这也代表了一个进步的方向,即本校既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是各合作差会的一部分。”包文公布了前一天(3月17日)各外籍行政主管的集体辞职书,内称:“我们相信是时候让更多的中国人担任校内行政职务,理事会应郑重考虑此事……以扩大学校的合作基础。我们自愿辞去行政职务,并听从理事会的任何安排。”该辞职书签署者为校长包文、副校长文怀恩、文理科科长夏伟师(Guy W.Sarvis)、农林科共同科长(Co-Dean)芮思娄(J.H.Reisner)、图书馆馆长克乃文(Harry Clemons)和鼓楼医院院长赫济生(A.C.Hutcheson)。辞职书于3月17日递交理事会执行与经济委员会。执行与经济委员会遂任命一个委员会向理事会起草报告,程湘帆代表该委员会在3月18日的会议上进行报告。经过讨论,理事会做出3项决议:1.理事会向校行政主管表示谢意,他们能在短时间内将职位开放给中国人;2.当有充分能力的中国人服务于学校时,理事会将宣布遴选中国人担任行政主管的政策;3.任命一个五人委员会充分研究必要的步骤,该委员会须向执行与经济委员会报告。此次会议任命中国籍教员过探先与芮思娄担任农林科共同科长(Co-Dean)。 1926年3月金大外籍行政主管宣布集体辞职,向中国籍教员开放学校高级行政职位,这从侧面显示该校对立案的态度。教育部“1925年办法”第三条规定:“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包文和文怀恩同时宣布辞职,意味着校长与副校长之职均可让渡给中国人。当然,此次“辞职”仅是一种姿态。因各行政主管辞职须理事会和托事部批准,而物色中国籍接替者又须经过专门委员会的研究,即使有中国籍接替者,也须经过理事会和托事部的任命,特别是接任校长和副校长;即便三个步骤均顺利完成,所费时日也颇多。值得注意的是,向中国人开放行政权,外籍传教士和教师未必能达成一致意见。签署了总辞职书的夏伟师在一个月前代表金大出席中华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隔年会,上海沪江学院校长魏馥兰(F.J.White)在会上报告教会大学向中国籍教员开放行政权问题,在讨论中,夏伟师明确表示:“大部分外国人对任何中国人担任华人行政主管均表示十分担忧。征求几位中国人的意见,回答是任命中国人担任科长是不可行的。真正的问题是,是否有既是基督徒又有能力的中国人?这样的人几乎没有,而且这样的竞争对他们来说太激烈了。”(56) 当然,金大的治理权已逐步向中国人开放,这种趋向已不可逆转。从1915年开始,金大理事会增加多名中国籍理事的固定名额,差会派出理事中的中国人也逐渐增多,至1925年时中国籍理事在理事会已占半数。另一方面,金大的中国籍教员人数不断增多,从1912年创校之初的外籍教员17人、中国籍教员20人,到1922年外籍教员34人、中国籍教员64人。(57)由外籍传教士和教师包揽行政的架构也终将被打破。在1925年3月16日的第21次理事会年会上,包文称“将保证经费聘请优秀的中国籍教师,他们也将分担学校的行政责任”。(58)所以,1926年金大外籍行政主管宣布集体辞职并非突然。 1926年夏,金大又聘陈裕光担任文理科科长、过探先为农林科科长、胡小石和陈钟凡任国文系主任、张信孚为体育系主任。包文还对外透露,时任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最适合继任金大校长。(59)郭秉文是一名基督教徒,也是当时中国教育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60)据理事会一位“重要人”说:“接收困难,不在人材,而在经济。一俟经济方面筹划妥当,即正式允许辞职,收归华人办理云。”(61)可见,一来西人辞职与华人接替需要按程序进行;二来学校受“经济问题”掣肘,所以,实现行政主管大换班“延宕不决”。但是,随着一年后国民革命浪潮的汹涌袭来,金大行政权迅即由中国人接收,并且完成多年悬而未决的立案问题,该校治理结构从而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籍教师群体成为推动这个进程的重要力量。 二、“南京事件”后金陵大学校内行政权的让渡 1927年3月23日,北伐军攻抵南京,直鲁联军败退城内。次日北伐军入城,南京局势极度混乱。这期间,南京城内发生大规模由“乱兵”发动的排外暴力活动,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教堂、教会学校及商店遭抢劫,并有外国人遭殴打甚至被杀,英美两国军舰炮击南京,又造成人员死伤,酿成“南京事件”。(62)南京事件对金大几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副校长文怀恩被杀,学校科学楼的设备小部受损,部分学生宿舍财物被抢劫,附属中学损失严重,华言科的大楼遭大规模抢劫,有5幢教员住宅被烧并遭劫。(63)国民党军队进驻校园和鼓楼医院,所有外籍教员离开学校,学生回家,学校就此关闭。当时有报章称美国准备“完全抛弃”金大。(64)事件后,金大面临两大困境:一为绝大部分外籍教员离校回国,金大原有的行政和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二为金大在当时仍标举“打倒帝国主义”和“收回教育权”的国民党政权统治区域内,作为教会大学,前途未卜。 1927年4月19—20日,金大理事会第23次会议在上海传教大楼举行。(65)校长包文报告了外籍教员请假的情况,并表示自己也将于4月23日回国。他针对目前的局势表示:外籍教员和在美人员要求金陵大学保持明确和强烈的基督教性质而不被限制,美国人不会允许金大被政党驱使或被学生控制,否则学校不可能获得美方资助。就此,理事会决议继续办理大学,维持到1927年春季学期结束。这就意味着,金陵大学可能因政局变动而停办。不过,在此紧急时刻,金大有一套临时维持的方案。农林科科长过探先介绍了包文任命的一个由9位中国籍教员组织的委员会主持校政的情况。这个“九人委员会”的前身是1926年包文提出辞呈后为应对金大改组问题组成的“四人委员会”(过探先、陈裕光、刘国钧和刘靖夫),不过这个问题之后搁置了,直到南京事件后“四人委员会”出面应付政局变动,之后又补充5人,组成“九人委员会”。理事会决议,授权包文、过探先和陈裕光组织“学院行政委员会”(Colleg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委员为过探先、陈裕光、刘国钧、李德毅、陈嵘、李汉生和陈钟凡,该委员会与理事会进行协商后代表理事会管理学校。在5月下旬召集的理事会执行与经济委员会会议上,学院行政委员会委员和金大附属中学行政委员会两位委员及鼓楼医院两位职员组成“校务委员会”(University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校务委员会对理事会负责,承担学校的行政职责,并负责与政府打交道,过探先为召集人。(66) 以上措置,或早有准备。据《申报》称:在北伐军攻占两湖之际,金大校方就对时局有所研判,当时外籍领导层对将行政权交予华人的决心更加坚定,副校长文怀恩曾到汉口与国民党商量金大善后事宜,当直鲁联军占据南京对抗北伐军时,校长包文即准备当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外籍教员全体辞职,校务交给“临时教育委员会”(即“四人委员会”)。(67)不过,理事会和包文还任命了芮思娄为校务顾问(Advisor to the Administration)。芮思娄的角色类似校长的代表。他在上海博物院路20号526室设立临时办公室,作为金大教职员总部(68);同时,理事会的执行与经济委员会仍在上海召集会议,芮思娄任执行秘书。校务委员会在南京,芮思娄及其控制的教职员总部临时办公室和理事会执行与经济委员会在上海,芮氏代表外籍教员和外国的利益(69),他对校务委员会的职权起到牵制作用。在非常时期,校务委员会和芮思娄共同维持金大,双方虽同舟共济,但亦有龃齬之时。如校务委员会决定免考及毕业典礼日期,芮思娄在沪表示不满,校务委员会去函表明此是不得已的办法,并希望芮“以后认清权限,勿任意发言”。(70) 校务委员会接管金大,负责日常事务,前述“南京事件”后金大面临的第一重困难,即外籍教员离校,已基本克服。而且金大校友愿意出资帮助学校渡过难关,使1927-1928年度预算得以成立。(71)即在1927年夏的学期结束后,下一学年能正常开学。不过,在当时的政局下,金大未来是办是停,如何办理,并不完全取决于该校的行政、教学和经费状况,以及美国托事部和外籍教员的态度,还要看金大如何跨越第二重困难,即应对国民党的政策措施,这一点更具决定意义。 早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对教会学校实行严格限制的政策,严令教会学校立案。而北伐兵锋所指,各地教会学校又受到严重冲击,其中也包括金陵大学。虽然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实行“清党”,随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逐渐淡化“反帝”色彩,但在南京政府初期,其教育政策依旧体现较强的“革命性”,同时国民党地方党部对包括教会学校在内的各类学校持激进的“党化”态度。但之后情况慢慢发生变化,教会学校得以继续生存。 在金大第23次理事会会议上,负责在宁维持局面的过探先报告说,激进的国民党南京市政府欲接管金大的财产和校舍,由于过探先和李德毅与国民党高层的沟通才作罢。江苏省政府成立后,情形稍好转,金大得以开学。金大“九人委员会”还向蒋介石递交申请书,说明金大目前由中国人主持,并不设宗教必修科目,请求蒋撤掉驻军。与包文的态度明显不同,过探先强调金大应继续办理,“一旦道路更为光明清澈,我们就能把握其方向,这比我们让它停办更好”。(72)显然,过探先对金大前途的态度坚定,但学校能否继续生存,一个老问题又重新摆在眼前,即立案。不像前一两年,金大对北京政府的立案法令可以延宕不决,此次绝无可能绕过南京政府的立案政策。 1926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私立学校规程》和《私立学校校董会设立规程》,规定外国人设立的教会学校也属于私立学校,私立学校须受教育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宗教科目不得为必修科,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由校董会选任校长,外国人不得担任校董,如果有特殊情形可以充任,但本国董事名额须占多数,外国人不得任董事长。(7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7月成立的大学院是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对其前身教育行政委员会所议决的法令,采取继承的态度。(74)大学院重新公布1926年《私立学校规程》和《私立学校校董会设立规程》。(75)而在金陵大学一方,校务委员会清晰地认识到现实,学校已到非立案不可的境地。 在1927年6月13日的金大校务会议上,陈钟凡称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对金大“态度颇为不妥”,并鉴于浙江省限期收回教育权之举,他提议修改金大组织大纲草案中关于校董会组成的条款。言下之意,他担心国民政府接管金大。同时,会议决议邀请国民党政要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和刘文岛参加金大的毕业典礼并训词。此决议表明校务委员会主动释放对国民政府的服从诚意。(76)6月16日,金陵大学理事会在上海召开第24次会议,过探先指出江苏省教育厅颁布新的教育体系,每一个省只设一所公立大学。此即“大学区制”。6月9日南京政府决定在江苏省试行大学区制,任命张乃燕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长;7月8日江苏省实行大学区制,裁撤省教育厅,第四中山大学既是该省(大学区)最高学府,又是大学区内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区内所有公立学校及教育机构均隶属于第四中山大学。(77)为此,过探先很担心江苏省的大学区制会对教会学校的地位造成影响,教会学校会被东南大学(此时已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引者注)控制,所以“有必要考虑尽早向政府立案的问题,以应对紧急情况”。显然,过探先主张立案。会议接下去讨论立案问题,有人称南京政府有官员提出,如果金大没有在1927年前向政府申请立案,就很难继续办学,故立案很有必要,如果拖延,事态将复杂化。 出席此次会议的理事葛德基(E.H.Cressy)称,上海沪江学院正在申请立案,但所涉及的问题远超过他们之前所想到的,立案的时间可能很长,还涉及校产问题。他还提到一个关键问题,各校在华的董事会必须有明确的权力来处理立案问题。葛德基的发言其实代表当时外籍教会人士对立案的摇摆心态。不过,沪江学院的先例促使金陵大学的决心更加坚定。讨论之后,理事会表决:赞成采取各种申请立案的措施;任命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金大改组计划,交由托事部批准;授权大学立案委员会准备立案事宜,这将得到理事会和托事部的批准,这个委员会有6位成员,其中芮思娄为会议召集人,过探先为当然委员。(78)就此,金大立案的大原则确立。原则确立之后就需要具体办法。归根到底,金大立案要从三方面努力:一是尽快与政府接洽,办理立案手续,以免学校有变;二是建立新的校董会,重新划分校董会与托事部的权责关系,后者要把若干权力让渡予前者;三是选任一名中国籍校长。三个方面问题同时解决,立案才有可能实现。 三、陈裕光担任校长与金陵大学立案 在当时的局势下,金大校方很害怕学校成为国民党的“革命对象”,故只有通过立案,即被现政权认可,才能继续办学。6月29日,金大改组和立案委员会(Committee on Reorganization and Registration)召开会议,程湘帆和陈裕光指出目前形势已很急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键已有政府接管金大之意,所以金大必须及早立案。(79)金大为申请立案有两个基本前提:一个符合规定的校董会,一名中国籍校长。这两点的落实,需要托事部和理事会的讨论和决议,时间耗费就在所难免。改组和立案委员会决定在8月1日前向托事部通报立案的必要性。同时,金陵大学同学会也呼吁母校尽早立案。(80)而此时的校务委员会对此更加急迫,7月6日的校务委员会会议决定致函理事会,“声明倘八月一日不将立案手续办妥,如因此发生困难,全体委员不负维持责任”。(81)陈裕光回忆,自己曾主动向即将成立的大学院联系有关学校前途与立案事宜。(82)然而,8月1日已至,金大却未完成立案手续,校务会只得派过探先和陈裕光到第四中山大学区汇送缓期立案的呈文。(83)10月,校务会又托芮思娄催请托事部考虑立案问题。(84)此后,托事部托人视察金大以便立案。(85) 改组和立案委员会在6月29日专门讨论了改组问题。因为根据国民政府1926年《私立学校规程》和《私立学校校董会设立规程》的规定,私立学校的校董不得是外国人,如果有外籍校董,名额数也不得超过校董会人数的一半。芮思娄提出要修改金大的现有章程,使中国人在理事会中占多数,但尽量以现有章程为基础进行改组。这就意味着外籍传教士和教师不希望金大大幅度改组,校董会构成只要符合政府规定即可。校友吴东初认为,理事会的权力范围应该扩大,托事部的一些固有权力应该交给理事会。最后,会议形成3个决议,根据会议精神,理事会发电报给托事部,请求批准:(1)理事会更名为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2)董事会有权选举校长;(3)托事部将校产出租给董事会,为期5年;(4)托事部将所有校内事务管理权移交给董事会。(86)7月12日召开的理事会第25次会议通过修订的《校董会章程》和《托事部章程》。其中托事部章程有许多重大修改:办学宗旨由原先“培养教徒领导人,为我们基督教的后代提供高等教育,并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与上帝保持一致”,改为“在充分的宗教自由中保持教会主办本校,这将确保高等级的教育质量,促进社会福利和公民社会和公共服务的典范,发展创办人所秉持的理想人格”。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托事部改为“创始人委员会”(Board of Founders),废除托事部任命校长和提名理事会成员、批准理事会改选两项权力。另外,理事会改组为校董会,原本理事会中3个完全合作差会即美以美会、基督会和长老会各拥有4个固定成员名额,这4个名额中西籍不论;而在新的校董会中,3个完全合作差会各拥有5个固定成员名额,其中3名中国人,2名美国人;北浸礼会原在理事会中有3个成员名额,现在校董会中有4个成员名额,中美籍成员各半;由同学会推举4名成员,理事会(校董会)推举5名成员,以及校长作为当然成员不变,校长不再担任校董会主席,教职员不能担任校董。新的校董会将主导学校大政方针及其他校务大权,校董会和创始人委员会签订校产租赁协议,即金大校产仍归创始人委员会(托事部)所有,但校董会有使用权。(87) 两个月后,托事部会议召开,讨论理事会提出的改组计划,形成7项决议。第一,同意并承认理事会所提请求:(1)理事会更名为董事会;(2)董事会有权选举中国籍校长;(3)托事部将金陵大学校产在5年内租予董事会;(4)托事部将所有校内管理权移交给董事会。第二,托事部将选举新校长的全权交由校董会;所有有关立案和校内行政、财务等问题交由校董会。第三,托事部正在准备理事会章程基础部分的草拟,理事会的宗旨是保持学校的基督教性和完全的宗教自由。第四,托事部大致同意由理事会提出的校董会和托事部(创始人会)关系的文件……第七,托事部劝说各差会继续资助金陵大学目前所申请的现金经费,并尽可能不削减。(88)如此,金大改组在校内和美国两方面的制度障碍基本扫清,金大所有立案手续均由新校董会办理。(89) 11月29日,金大理事会在沪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自行休会(adjourned since die)。同日,金陵大学董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告校董会正式成立。(90) 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任中国籍校长成为最关键、最急迫的问题。在1927年6月29日的金大改组与立案委员会会议上,吴东初提出要选出一位中国籍校长,标准是“既能与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又是一位杰出的基督徒”。(91)这是金大各种正式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选任一位中国籍校长及其标准。紧接着,7月12日召开的理事会第25次会议决议组织一个校长提名委员会以提名新校长人选。不过,此次会议所修订包括校董会有任命校长之权的各项章程有待托事部通过,所以产生的提名委员会及校长提名人选均是非正式的。(92)尽管如此,校长提名委员会的工作进展得十分快捷高效。9天之后,校长提名委员会召开会议,正式提名陈裕光博士为金陵大学校长。从此次的会议记录看,与会委员未提及其他人选。(93)翌日,提名委员会以书面形式通知陈裕光的提名决定,称陈是提名委员会的首选,是中国各教会、各差会、校友和教员都对其抱有信心的人。(94) 陈裕光,祖籍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1893年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基督教家庭,1905年进入金陵大学的前身之一汇文书院附属中学读书,之后进入金陵大学学习,1915年毕业。1916年,陈裕光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克司工业大学(Case School of Applied Science)和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化学,1922年毕业获博士学位。毕业后陈裕光即回国,先受聘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1924年曾任该校总务长和代理校长。1925年秋,陈裕光回母校金陵大学任教。(95) 关于被提名为校长,陈裕光回忆说:“同年(1927年——引者注)11月,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突然作出决议,推选我为校长。电报发来,局面已成,难以推辞。”(96)不过,陈裕光的回忆有误。前述,7月份他已经得到提名的通知。而11月的理事会会议正式任命他任校长,他当时并不在南京,而在上海的会场。(97)彼时提名陈裕光为校长,似乎很突然。可是,他自己回忆说,北伐时包文就有意请他出任新校长,被他婉拒了,在形势突变之际,包文又对他提及此事,他的态度“一如既往”。(98)照此说,陈裕光在提名宣布前,自己应有心理准备。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陈裕光担任校长?在校长提名委员会给陈裕光的通知函中,提及原因,即他受各方面的信任。不过,这种表述还比较含蓄,读起来庶几冠冕之词。陈正式就任后,金大学生会对他能够当选校长的原因有过分析:“本校校长须兼备下列四种资格始克胜任:(A)与本校有长久历史并对于本校情形熟悉者,(B)有学识经验者,(C)为西人信仰者,(D)与同学会及各方感情融洽者,上列四者之中,独具一项者,校中固不乏人,但能备而有之者,则舍陈博士外实无其他最合宜之人。”(99)此言至当。 陈裕光是金陵大学的毕业生,这一身份是他当选校长的重要原因。纵观近代中国13所基督教新教大学,在1949年前,历任的中国籍校长特别是首任的中国籍校长绝大部分为毕业于本校者。例外情况有岭南大学首任中国籍校长钟荣光,不过钟氏从岭南学堂时期起即任该校中文教习;圣约翰大学第二任校长涂羽卿(1946-1948)非校友出身;齐鲁大学校长更替频繁,部分中国籍校长非校友出身;燕京大学校长(及代理校长)吴雷川、刘廷芳、陆志韦和梅贻宝等均非校友出身。(100)中国早先的本土大学教授一般来源于有科举功名的士人,随着清末民初第一批大学生的毕业,大学教授开始来源于大学毕业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学国外,后又回国任教;一部分未留学者直接留校任教,或通过从事其他职业后进人大学任教,这种情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大量出现。大学毕业生留校或留学后回本校任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校方似乎也乐意并信任校友任教。陈裕光自己就称当时他回校任教,颇受包文信任。 另外,陈裕光是留美博士,任职教授,学识当可服众。他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行政职务,现任金大文理科科长和校务委员会委员,负责实际事务。在非常时期,金大需要一位有行政经验的校长。还有更关键的一点,陈裕光于1925年秋回金大执教,1926年3月18日即以理事的身份参加理事会会议,他是金大三个完全合作差会之一的长老会派出的代表(101),可见他在教会和学校中的地位。 1927年8月24日,已回美国的包文致函托事部主席史密尔(Robert E.Speer),正式提出辞去金陵大学校长职位,这样,“金大才可以由中国人继任校长”。(102)9月14日,托事部会议批准包文辞职。(103)如此,从法理上讲,之前金大理事会提名陈裕光继任校长才真正有效,接下去的任命步骤才合法。 在9月13日的理事会执行与经济委员会会议上,校务委员会首次明确表示希望确定一位中国籍校长,认为由校长领导行政工作比校务委员会有效率得多,而且要立案也必须有中国籍校长,所以恳请理事会任命新校长。(104)这显示了校内中国籍教员的态度。 11月9—11日,金大理事会在沪召开第26次会议。会议讨论校长提名问题,校长提名委员会提名陈裕光为校长。随后,陈即席发言,做了一番推辞。紧接着,校务顾问芮思娄转达包文对陈裕光的信任;校务委员会主席过探先代表中国籍教员支持陈当选校长。最后,理事会推举陈裕光为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即发表当选感言,表示自己将在这一职位上尽力,任职主要是为了便于金大立案,希望只担任代理校长至立案完成,并要求设立名誉校长和副校长之职。理事会否决陈裕光只担任代理校长与设副校长之请,设立名誉校长待以后考虑。理事会还决定,校务委员会即自行解散,由新校长负责校务;同时,改组与立案委员会终止,其所处理的事务交予执行与经济委员会,立案手续由新校长负责。(105)11月29日,金陵大学校董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任命陈裕光为金陵大学校长。(106)自此,金陵大学校长更替问题完全解决。陈裕光回忆说自己担任校长的条件是理事会要同意他在金大立案事务上“采取主动”。(107) 就在金陵大学完成学校改组(设校董会)并任命中国籍校长之后不久,大学院于1927年12月20日颁布《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1928年2月6日颁布《私立学校条例》,核心精神即私立学校要受教育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私立学校必须组织校董会“负经营学校之全责”,校长须对校董会“完全负责执行校务”,并规定私立学校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不得在课内做宗教宣传,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108)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最早颁布的有关私立学校立案的法令。对此,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态度如旧,建议教会大学从速进行立案。(109) 1928年2月21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复函陈裕光,称收到陈的手书,得知金大正在筹备立案,发给私立大学立案表样式一册。(110)从时间看,政府有法可循,金陵大学即照此规定正式准备立案,节奏紧凑,颇为主动。5月中旬,金陵大学正式呈请立案。6月,校董会设立一个新的立案委员会处理立案事宜。8月6日,大学院核准金大校董会之设立,并准予其立案。经大学院派员实地调查,于9月20日与大同大学、复旦大学和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同一批获准立案,成为南京政府时期最早立案的私立大学之一和第一所立案的基督教新教大学。(111)陈裕光向托事部宣称,立案意味着金大得到公众与官方的认可,金大的事业将得到中国人民更好的评价。(112)包文向托事部称赞陈裕光任校长后,在立案问题上,对保持金陵大学基督教性质的态度十分坚定和积极。(113) 1928年,金陵大学实现校董会设立、中国人出任校长和完成立案的全方位转变,由此进入新时代。这项转变与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的民族主义风潮、国民革命风暴和政权鼎革有直接关联。金陵大学对民族主义与革命运动的回应,既体现教会大学“中国化”趋势以及内部治理结构调整的整体共性,又有其独特性。金大校方在北京政府时期就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与中国政府、社会的关系,努力融入国家教育体制之中,游走于“中国化”与基督教宗教性之间,完成特殊的“部分立案”,拥有了“本国私立大学”的政治标签。而在五卅运动与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强硬的立案政策的冲击下,金大校方主动释出向中国籍教职员开放校内中高级行政职位的善意,学校改组已是大势所趋。 1927年的“南京事件”对金大几乎造成毁灭性的冲击,外籍教职员出走,学校陷入混乱和困顿,进而由中国籍教职员执掌校务,学校得以维持。正是事件前校方主导的渐变性改组,才使得事件发生后中国籍教职员能够牢固掌握校政,并主导学校未来的走向。由此,陈裕光脱颖而出,成为新的校长,进而打破“托事部—理事会”的权力结构,成立新的校董会。陈裕光力主金大迅速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请立案,将学校带入南京国民政府规划的方向。上述各个环节紧密相扣,金大的立案与改组是一个持续几年的渐进过程。金大成为南京政府时期最积极谋求立案同时也是第一个成功立案的教会大学,与此有莫大关联。 立案之后,与同时期的国立大学相比,教会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中既有一个代表教会和西方利益的校董会(尽管与之前相比,校董会已有相当程度的“中国化”),校董会对校长的权力无疑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时,中国籍校长在校内外也受到外籍教职员和教会势力的掣肘,与国立大学校长在校内事务上能握有绝对权力不等同。在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是能协调教会与中国世俗教育界、金大与政府间关系的绝佳人选。他担任校长不仅是教会方面应对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必须遴选中国人担任校长的结果,也缘于金大校方主动践行“中国化”的努力。在金大校内,相对于教会与外籍教职员,陈裕光担任校长不仅体现的是个体意义,更代表着中国籍教职员的群体力量。正是这股力量推动着金陵大学迈向本土化与自主性。 本文初稿提交由《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和浙江省历史学会、宁波市鄞州区方志办共同举办的第五期中国近代史论坛“涵育与超越:文化传统与鄞州近代人物”学术研讨会(宁波,2015年10月),承点评人桑兵教授及徐秀丽、项义华教授指点,谨致谢忱! ①《成长时期概况》,《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②Nanking Stand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Its Church Work,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私立金陵大学档案(下文简称“金大档”),649/2296。 ③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该档原藏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已全部制成缩微胶卷。该资料原档50余盒(Box),制成胶卷43盘(Reel),绝大部分为英文文件,包括各种会议记录、各学院文件、教职员论著、各方函电、财务资料与学校期刊。 ⑤如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第4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章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研究》第2章,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1909 Proposed Co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5.Box 188,Hereafter "UBCHEA Archives". ⑦1909 Proposed Co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5.Box 188. ⑧By-laws; Minut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February 25,1925,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5.Box 188.Folder 3316. ⑨亦译作“校董会”,为区别1927年后的校董会(Board of Directors),本文统一称“理事会”。 ⑩The Semi-annual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March 30,1915,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5.Box 188.Folder 3316. (11)包文:《金陵大学之近况》,《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4期,1925年12月,第33页。 (12)刘廷芳:《教会大学办学之困难》,《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3期,1939年9月,第18页。 (13)Twenty-first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March 16,1925,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38. (14)吴哲夫著,于华龙译:《教会学校移交行政职权之问题》,《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4卷第2期,1928年6月,第44页。 (15)关于“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详见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6)《学部咨各省督抚为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1906)》,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077页。 (17)《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公布大学令》,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18)《1913年1月16日教育部公布私立大学规程》,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册,第17—18页。 (19)《1913年1月23日教育部私立大学立案办法布告》,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册,第18页。 (20)“专门以上学校”即“专科以上学校”。 (21)教育部各布告文转引自杨思信、郭淑兰《教育权与国权:1920年代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59—60页。 (22)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9页。 (23)Registration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60.Box 196.Folder 3379. (24)《教育部视察金陵大学报告》,《南大百年实录》中卷,第25—27页。原引文句读有误,已更正。 (25)金陵大学于1914年创办农科,1915年创办林科,1916年两科合并,称农林科,1928年改称农学院。 (26)《教育部对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调查一览表金陵大学部分(民国15年5月13日)》,《南大百年实录》中卷,第31页。 (27)The Eighteenth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October 13,1921,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35. (28)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November 1,1921,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5.Box 188.Folder 3316. (29)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December 20,1921,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5.Box 188.Folder 3316. (30)《教育部最近公布外人设立学校认可办法》,《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4期,1925年12月,第1—2页。 (31)《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23卷第6号,1926年3月25日,第147页。 (32)Twenty-secon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March 18,1926,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38. (33)吴雷川:《对于教会中学校改良的我见》,《真理》第1年第16期,1923年7月15日,转引自杨思信、郭淑兰《教育权与国权:1920年代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研究》,第227页。 (34)朱经农:《中国教会学校改良谭——在南方大学讲演》,《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l卷第2期,1925年6月,第8—9页。 (35)详见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第271—273页。 (36)卢茨(Jessie Lutz)认为教会大学的西方行政当局倾向于渐进主义,慢慢改变了对教会大学管理权开放给中国人和立案条件的态度。杰西·格·卢茨著,曾炬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234—235页。 (37)《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董事会年会决议案(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至二日)》,《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3期,1925年9月,第82—83页。 (38)在1926年2月召开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高等教育参事会隔年会上,齐鲁大学校长瑞恩培(J.D.MacRae)称程湘帆在过去数月间与教育部有过接触。见J.D.MacRae,"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ference",The Christian College in the New China:The Report of the 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Shanghai,1926,pp.2—3。 (39)缪秋笙:《教会学校“立案运动”中的见闻》,政协上海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2—201页。 (40)"Shall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Register with Peking Government?" The China Weekly Review,36:1,March 6,1926,p.4. (41)1924年全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改组为中华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与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高等教育参事会(The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合为一体。 (42)"Government Registration",The Christian College in the New China:The Report of the 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p.76. (43)吴哲夫:《干事报告》,《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2期,1926年6月,第74页。 (44)《董事会第二次年会纪要》,《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2期,1926年6月,第81页。 (45)缪秋笙:《教会学校“立案运动”中的见闻》,第212—213页;程湘帆:《注册问题之经过及解决的焦点》,《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26年9月,第60—61页。 (46)转见刘廷芳:《会长通函第三号》,《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26年9月,第10页。 (47)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第382—383页。 (48)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述及此问题,也是一段空白,从“收回教育权运动”直接过渡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后的立案问题。 (49)《〈燕京大学一览〉记燕京大学校史》,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页。 (50)高冠天:《岭南大学接回国人自办之经过及发展之计划》,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第570—573页。 (51)《教部正式认可五大学》,《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4期,1925年12月,第77页。 (52)包文:《金陵大学之近况》,《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4期,1925年12月,第37页。 (53)Twenty-secon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March 18,1926,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38.下文所引此次会议内容,均见此。 (54)理事会下设若干常设委员会,最重要的机构是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负责在理事会会议前拟定议案,是理事会的代表,在紧急情况时可代表理事会作出决议。从1924年起,执行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合并,称“执行与经济委员会”(Executive-Finance Committee)。 (55)Minutes of the Semi-annual Meeting of the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April 21,1926,金大档,649/2317. (56)F.J.White,"Making the Christian College more Chinese",The Christian College in the New China:The Report of the 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p.39. (57)包文:《金陵大学近十年的发达》,《兴华报》第19卷第18期,1922年5月17日,第5页。 (58)Twenty-first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March 16,1925,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38. (59)《金陵大学当局总辞职》,《申报》,1926年7月5日,第3张第11版。 (60)详见许小青《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教育学报》2014年第5期。 (61)《金陵大学当局总辞职》,《申报》,1926年7月5日,第3张第11版。 (62)1927年“南京事件”的焦点是谁是制造者和参与者,此问题目前尚无定论,参见杨天宏《北伐期间反教暴力事件及其责任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陈谦平《关于1927年南京事件的几个问题》、《1927年南京事件中外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考订》,《民国对外关系史论:1927-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63)《H.G.罗伯逊先生向美国托事部报告金陵大学在“南京事件”中的遭遇》,《南大百年实录》中卷,第39页。 (64)《华北警备问题》,《申报》,1927年4月7日,第2张第7版。 (65)下文引用该次会议内容,均见Twenty-thir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April 19,20,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39。 (66)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May 20—25,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39. (67)《金陵大学收归华人办理经过》,《申报》,1927年6月13日,第3张第10版。 (68)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June 9,1927; John H.Reisner to Friends,April 28,1927,金大档,649/2317。 (69)"The Revolution and Christian Colleges",The Chinese Recorder,58:7,July,1927,pp.456—457. (70)《六月八日第十三次校务会议记录》,1927年6月8日,金大档,649/225。 (71)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May 20—25,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39. (72)Twenty-thir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April 19—20,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39. (73)《国民政府取缔私立学校》,《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26年9月,第77—80页。 (74)《大学院教育行政处处务会议记录(第一次会议,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2期,1928年2月,第49页。 (75)《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1期,1928年1月,第39—44页。 (76)《六月十三日第十五次校务会议记录》,1927年6月13日,金大档,649/225。 (77)详见蒋宝麟《“党国元老”、学界派系与校园政治——中央大学首任校长张乃燕辞职事件述论(1928-1930)》,《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67—168页。 (78)Twenty-fourth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June 16,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39. (79)Meeting of Committee on Reorganization and Registration,Board of Man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June 29,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39. (80)《金陵大学第十七届毕业礼纪》,《申报》,1927年6月22日,第2张第7版。 (81)《七月六日第十九次校务会议记录》,1927年7月6日,金大档,649/225。 (82)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83)《八月二十六日临时校务会议记录》,1927年8月26日,金大档,649/225。 (84)《十月六日第三十二次校务会议记录》,1927年10月6日,金大档,649/225。 (85)《十月十七日第三十四次校务会议记录》,1927年10月17日,金大档,649/225。 (86)Meeting of Committee on Reorganization and Registration,Board of Man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June 29,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39. (87)Twenty-fifth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July 12,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40,另见附件A Proposed Amendments to Constitution of Board of Directors和附件D Proposed Amendments to Constitution of Board of Trustees。《修订校董会章程》中的大部分内容体现于《修订托事部章程》中。 (88)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September 14,1927,金大档,649/2317。 (89)《十月二十日第三十五次校务会议记录》,1927年10月20日,金大档,649/225。 (90)First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November 29,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43. (91)Meeting of Committee on Reorganization and Registration,Board of Man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June 29,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39. (92)会议记录中在组织校长提名委员会的决议后有一个说明:“在未得到托事部批准前,任命提名者是几乎不合适的。在立案生效后举行新校长就职典礼是明智的,这样他会感到在位稳固。”见Twenty-fifth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July 12,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40。 (93)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July 21,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40. (94)Secretary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to Dr.Y.G.Chen,July 22,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40. (95)陈裕光生平,详见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第1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96)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第13页。 (97)Twenty-sixth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November 9—11,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41. (98)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编:《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第12—13页。 (99)矫如:《本校学生会招待沪宁各报记者纪》,《金陵周刊》第1期,1927年12月2日,第67页。 (100)各教会大学历任校长情况,综合参考各校校史资料,不一一标注出处。 (101)Twenty-secon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March 18,1926,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38. (102)A .J.Bowen to Robert E.Speer,August 24,1927,金大档,649/2327。 (103)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September 14,1927,金大档,649/2317。 (104)Twenty-secon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March 18,1926,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38. (105)Twenty-sixth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November 9—11,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41. (106)First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November 29,1927,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43. (107)陈裕光1958年《自传》,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藏,转引自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第106页。 (108)《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布)》,《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1期,1928年1月,第26页;《私立学校条例(十七年二月六日大学院公布)》,《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3期,1928年3月,第8页。 (109)《本会十二届年会纪要》,《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4卷第3期,1928年9月,第91页。 (110)《蔡元培致陈裕光函》,1928年2月21日,金大档,649/62。 (111)《改进时期概况》,《南大百年实录》中卷,第38页;Minutes of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June 28—29,1928,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58.Box 192.Folder 3343。最早立案的私立大学是厦门大学(1928年3月28日)。金陵大学立案后,除圣约翰大学(1947年10月立案)外,其他基督教新教大学相继立案成功,最晚立案的是华西协和大学(1933年6月)。 (112)Y.G.Chen to B.A.Garside,October 5,1928,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72.Box 209.Folder 3354. (113)A.J.Bowe to B.A.Garside,November 30,1928,UBCHEA Archives,Microfilm,Reel 72.Box 209.Folder 3354.标签:基督教论文; 北京的大学论文; 大学论文; 金陵大学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金大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教育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