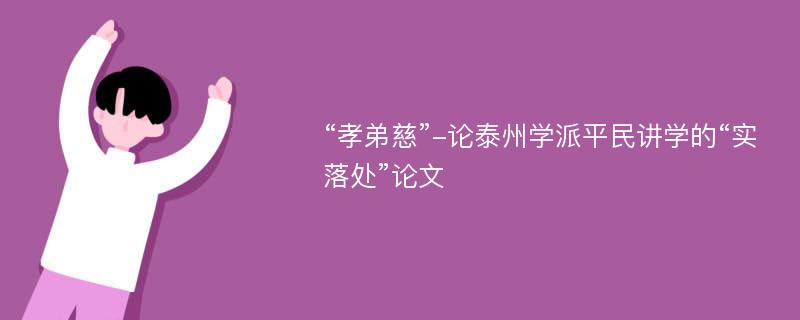
“孝弟慈”
——论泰州学派平民讲学的“实落处”
唐东辉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02)
摘 要 :泰州学派的平民讲学活动以近溪的“孝弟慈”思想为“实落处”。王艮的身本孝道观为其“孝弟慈”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颜钧对“圣谕六条”的阐释为其“孝弟慈”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近溪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泰州学派独树一帜的“孝弟慈”思想:在理论上,以本末观贯串“孝弟慈”,既以“孝弟慈”修己立本,又以“孝弟慈”率人达末;在实践上,则以乡约为载体,着力阐发“圣谕六条”。近溪的“孝弟慈”思想,最大的实践意义在于,为泰州学派的平民讲学找到了落脚点;理论意义在于,一方面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方式,另一方面也为“四民异业而同道”找到了更加坚实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孝弟慈”;泰州学派;平民讲学;“实落处”
《明儒学案》记载:“先生(指王心斋,笔者注)拟上世庙书,数千言佥言孝弟也。江陵阅其遗稿,谓人曰:‘世多称王心斋,此书数千言,单言孝弟,何迂阔也。’罗近溪曰:‘嘻!孝弟可谓迂阔乎’?”[1]718心斋所拟上嘉靖皇帝书,洋洋数千言而佥言孝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心斋思想重视孝弟的特色。其实不止心斋,其所开创的泰州学派,都表现出重视孝弟的思想风貌,呈现出一种重视孝弟的家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泰州学派认为,孝弟或者说“孝弟慈”(近溪称为“孝弟慈”)乃是平民讲学的“实落处”[2]188。所谓“实落处”,即是切实处,与普罗大众切实相关之处。因为人生在世,人人都有家有室,有妻子可慈,有父母可孝,有兄长可悌,从“孝弟慈”入手,才能贴近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才能使高明而又精微之道显现于庸常而又广大的生活之中。
柳红也不知自己在苏秋琴家的门口呆了多久,突然听到里面有开门声,她下意识地拔腿就跑。她听到白天明打开院门,朝小路上张张,问是柳红吗?柳红没有理他,她突然非常非常讨厌白天明和苏秋琴,不想见到她们俩;她边往家跑,边没头没脑地对自己说:“有什么了不起!”但不知为什么,她的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
一、从王艮到颜钧:“孝弟慈”的理论奠基与实践探索
从学术传承的角度看,从王艮到颜钧,再从颜钧到罗近溪,重视孝悌可谓一脉相承。其中,王艮的身本孝道观为近溪“孝弟慈”的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而颜钧对“圣谕六条”的阐释则为近溪“孝弟慈”的思想开拓了实践探索。
(一)理论奠基:王艮的身本孝道观
如引言所论,王艮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重视孝弟。不过,王艮的孝道思想,有一个从传统孝道观到身本孝道观的转变。前者以《孝弟箴》为代表,后者以《孝箴》为转变,而以《与南都诸友》一书为代表。
王艮的《孝弟箴》曰:
事亲从兄,本有其则。孝弟为心,其理自识。爱之敬之,务至其极。爱之深者,和颜悦色。敬之笃者,怡怡侍侧。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所为若是,终身践迹。所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若善,尽心竭力。所命未善,反复思绎。敷陈义理,譬喻端的。陷之不义,于心何择?父兄之愆,子弟之责。尧舜所为,无过此职。[3]54
全《箴》分为三个部分:首句为第一部分,以“事亲从兄,本有其则”总领全《箴》;第二至第五句为第二部分,讲孝悌之道当以爱敬存心;第六至第十五句为第三部分,讲孝悌之道不是盲目顺从,规谏也是应有之义。可见,王艮在此箴中阐述的孝弟之道,不外乎以爱敬之道事亲从兄,及对父兄所为应当有所规谏。这两点其实是儒家传统孝道思想的题中之义,并没有新的理论建构,故笔者将其称之为传统孝道观。
一次在大学里举办“高端培训班”,参加者都是地、市一级的领导,我去讲清史,在讲课中,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问:“碰到小人怎么办?”我当时真没有料想到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思考了一下说:“感谢!”底下沉默了二三十秒后,全场长时间鼓掌。
王艮的孝道观,在《孝箴》中开始由传统孝道观向身本孝道观转变。《孝箴》曰:
父母生我,形气俱全。形属乎地,气本乎天。中涵太极,号人之天。此人之天,即天之天。此天不昧,万理森然。动则俱动,静则同焉。天人感应,因体同然。天人一理,无大小焉。一有所昧,自暴弃焉。惟念此天,无时不见。告我同志,勿为勿迁。外全形气,内保其天。苟不得已,杀身成天。古有此辈,殷三仁焉。断发文身,泰伯之天。采薇饿死,夷齐之天。不逃待烹,申生之天。启手启足,曾子之全。敬身为大,孔圣之言。孔曾斯道,吾辈当传。一日克复,曾孔同源。[3]54
《孝箴》分为三大部分:第一至第七句为第一部分,重点阐述的是“天人感应,因体同然”;第八至第十二句为第二部分,着重论述的是要“外全形气,内保其天”;第十三句至最后为第三部分,举了大量的古代事例以证成“苟不得已,杀身成天”。《孝箴》虽然没有出现一个孝字,但却把“外全形气,内保其天”的孝道观诠释得淋漓尽致且通俗易懂。所谓“外全形气,内保其天”,就是曾子所说的“全生全归”。从“全生全归”的角度看,王艮的《孝箴》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孝道观,但此《孝箴》引人注意的是倒数第三句“敬身为大,孔圣之言”一语。王艮所谓的“身”是本末一贯的身,以己身为本,天下国家为末,所谓“敬身”就是进不危身,退不遗末,必至于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后已。由此可知,王艮在《孝箴》当中所表达的孝道观开始由传统孝道观向身本孝道观转变。
狼剩儿低声抽噎着,像只受伤的小兽。他哽出几句话,还是哇啦哇啦的,却不带一丝戾气,倒透着拳拳的温情。我分明看见了,我的狼剩儿好像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王艮在《与南都诸友》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这种身本孝道观。王艮认为:“尧舜君民之道,必有至简、至易、至乐存焉,使上下乐而行之,无所烦难也。”[3]50
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明原因的偏倚;此外,纳入的病例是单中心的前列腺癌患者,且样本量有限。因此,此研究结论有待后续多中心的大样本量的研究进一步证实。
王艮指出,在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中,具根源意义的乃是仁、义二德,他引用孟子的话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在他看来,仁即是事亲之孝,义即是从兄之悌,所以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黄伟语气和缓地说:“你们当然有抗议的权利,不过呢,这会儿先认识一下行不?我叫黄伟,哈尔滨知青,老高二,他叫傅正,也是我们哈尔滨那嘎哒的,和我一样,老高二。”说完,向赵天亮伸出一只手。
“坦率他说,我虽然并不了解您,但我觉得您绝不是罗马那些无聊透顶的有钱人可比的,您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气质吸引我。
春天的田野是美丽的:蔚蓝的天空中,慢悠悠地飘过一朵朵洁白无瑕的云,它们没有线条,就像只用白色颜料泼出来一般,随意而自由。山路两旁有成片的野酸枣树、桃树、山楂、野荆,这个时节有些果木正好开花,成群的蜜蜂嗡嗡地在花丛间飞来飞去,一刻不闲地忙碌着。纵横交错的河支细干在小山村中纵情蜿蜒,河水清澈甘冽,调皮的鱼儿在纤柔的水草间来回穿行,时不时吐出一串串晶莹的水泡。这真是一幅美丽的春景图。
无诸己而求诸人,是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有诸己而不求诸人,是独善其身者也。[3]50
阳明之后,心学一系最为重视孝弟,进而大力弘扬“圣谕六条”的,莫过于泰州学派。王艮对“圣谕六条”推崇备至,甚而将其提到“万世至训”的高度。心斋之后,泰州学派极为重视“圣谕六条”的则是颜钧。[注] 除颜钧外,王栋也非常重视“圣谕六条”,并作有《乡约谕俗诗六首》和《又乡约六歌》。其中,《乡约谕俗诗六首》缺第一条“孝顺父母”的诗文,只保存了后五首;《又乡约六歌》散佚更多,只保留了“孝顺父母”和“尊敬长上”这两条的诗文,其余四条的诗文不存。 颜钧著有《箴言六章》阐发“圣谕六条”。由于《箴言六章》较长,此处只举“孝顺父母”一条为例进行说明:
王艮又指出,孝悌不仅是家庭伦理,还可以治国平天下,若在上位者能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则可以使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在下位者若能事父孝,就可以以孝事君,移孝作忠。因此,王艮得出结论说,“上下皆当以孝弟为本也”[3]50。而以孝悌之道来尧舜君民,关键在于把握好人己、本末关系:
求诸人而天下之有不孝者,未能尽其术者也。不取天下之孝者立乎高位治其事,是未能尽其术也。取之在位,所以劝天下以孝也。立乎高位,所以尊天下之孝也;使之治事,所以教天下以孝也。[3]50-51
一是以“圣谕六条”为核心。我国最早的成文乡约是《吕氏乡约》,但它在两宋之际并未取得太大的实践效果,[注] 吕氏兄弟在自己的家乡蓝田推行该乡约,并一度取得良好的效果,可惜在当时就遭到一些士大夫的反对,加之北宋灭亡,《吕氏乡约》也就随之湮没无闻。南宋时期,朱子重新发现了这个乡约,并编写整理成《增损吕氏乡约》,可惜朱学一度被禁,故其实践也就无从谈起。 直到明代它才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出作用。明太祖非常重视乡村治理,并为此颁布了“圣谕六条”。明成祖则将《吕氏乡约》颁行天下,使之成为全国推行乡约的蓝本。阳明制订《南赣乡约》时,首次将“圣谕六条”与《吕氏乡约》结合起来。及至“嘉靖间,部檄天下,举行乡约,大抵增损王文成公之教”[7]。而近溪的《宁国府乡约训语》则是“第一部明确地以《圣谕》为思想指导而制定的《乡约》”[8]。不仅如此,近溪还很好地处理了“圣谕六条”与《吕氏乡约》的关系,以“圣谕六条”为核心,而以《吕氏乡约》发明“圣谕六条”,为明代以“圣谕六条”为核心的乡约实践作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说明。
在上者果能以是取之,在下者则必以是举之,父兄以是教之,子弟以是学之,师保以是勉之,乡党以是荣之,是上下皆趋于孝矣。然必时时如此,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岁岁如此,在上者不失其操纵鼓舞之机,在下者不失其承流宣化之职,遂至穷乡下邑愚夫愚妇皆可与知与能,所以为至简至易之道,然而不至于人人君子、比屋可封者,未之有也。[3]51
将前文所述纠偏算法录入竖井掘进机控制系统,模拟工程可能遇到的偏斜情况(表2),并进行现场试验。试验现场如图9所示。
据此可知,王艮所说的尧舜君民之道,其实就是孔孟所说的孝弟之道,而孝弟之道就是此书开篇所说的尧舜君民的至易、至简、至乐之道。“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若“在上者不失其操纵鼓舞之机,在下者不失其承流宣化之职”,使父兄、子弟、乡党皆知当以孝弟为本,则必至于“穷乡下邑愚夫愚妇皆可与知与能”,从而实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尧舜之治。
(二)实践奠基:颜钧阐发“圣谕六条”
王艮的身本孝道观虽然为泰州学派的平民讲学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他在《与南都诸友》一书中所探讨的外王路线,却仍然走的是“得君行道”的传统路线,观其书中所言“今闻主上有纯孝之心,斯有纯孝之行,何不陈一言为尽孝道而安天下之心,使人人君子,比屋可封”[3]50,即可知其心目中论述的理想对象乃是刚即位的嘉靖皇帝,他这是要“出则必为帝者师”,为嘉靖皇帝提供平治天下的治国纲领。然而明代的政治生态环境极为恶劣,并不存在“得君行道”的良好君臣关系[注] 关于此点,具体可参看余英时所著《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六章第一节“明代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的相关论述,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60—175页。 ,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注] 明世宗即位后,坚持要尊称生父兴献王为皇考,230余名官员集体伏跪于皇宫左顺门以示抗议,世宗一怒之下竟将134人逮捕入狱,杖五品以下180余人,死者多达17人。这是明史上仅有的集体官员被杖事件,惨烈程度可谓空前绝后。 ,正式宣告了王艮这一传统外王路线的失败。
近溪之所以提出以“孝弟慈”为宗旨来修己率人平治天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家学渊源的启发。近溪曾向其孙辈转述其父罗锦之言说,人的家业想要兴旺,需要培养“三条大根”:“盖我此身,父母分胎,父母其一也;此身兄弟同胞,兄弟其一也;此身妻子传后,妻子又其一也。若能孝父母,和兄弟,善妻子,三根得培,而身家产业有不发越者哉!”[2]423其中,善事父母为孝,善处兄弟为悌,善待妻子为慈。因此,近溪以“孝弟慈”立宗,可谓渊源有自。近溪承其父“孝弟慈”之说而予以发越曰:“我此人身,从何所出?岂不根着父母,连着兄弟,而带着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个人身为仁,又指此个人身所根、所连、所带以尽仁,而曰:仁者人也,亲亲长长幼幼,而天下可运之掌也。”[2]65-66认为“孝弟慈”不仅仅可以兴旺家业,更能平治天下,使治天下可运于掌。
这里提到的本、末,涉及到王艮的格物论。王艮指出,身与家国天下本为一物,惟其为一物,才有本末之别,其中,身为本,家国天下为末,故要修身以立天下国家之大本。因此在王艮看来,若自己不孝不悌,无诸己而求诸人,就是《大学》所说的“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若自己已孝已悌,有诸己却不求诸人,就是孟子所说的“独善其身”,退而遗末。王艮尧舜君民的孝悌之道正是以其身本论为关捩,既要自己孝悌,修身以立本,又要人人都孝弟,而非独善其身。而若要天下皆入于孝弟,在上位者则须“尽其术”:
孝顺父母
天地生民,人各有身。身从何来,父母精神。形化母腹,十月艰辛。儿生下地,万般殷勤。儿饥啼食,儿冷啼衣。乳抱缝浣,惕惕时时。儿渐长大,择师教儿。儿长大矣,求妇配儿。人有此身,谁不赖亲。幼赖养育,长赖教成。
儿幼赖亲,儿幼恋亲。娶妻生子,何忍忘亲!父母衰老,舍儿谁亲?儿不孝顺,亲靠谁人?亲不忍我,我忍忍亲。忍亲饥寒,饥寒我身。亲不逆我,我忍逆亲。我逆亲心,天逆我心。我若不孝,子孙效行。阳受忤逆,阴受零丁。
1)随着压力机技术的发展,使用伺服压力机代替传统机械压力机,可以将冲压的噪声控制在75dB以下,达到非常理想的效果。
儿幼亲怜,施德施恩。亲老儿痛,报德报恩。摩痛搔痒,喘息忧惊。老人多病,顺志体情。思之痛之,泪血淋淋。孝顺父母,圣谕化民。
附诗曰:
孝顺父母好到老,孝顺父母神鬼保。孝顺父母寿命长,孝顺父母穷也好。
父母贫穷莫怨嗟,儿孙命好自成家。勤求不遂大家命,孝顺父母福禄加。[6]
颜钧对“孝顺父母”一条的阐释,主体部分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人身得于父母精神说起,历述父母养儿教儿的艰辛,以此说明人有此身,全赖双亲“养育”“教成”的道理;第二部分从儿女幼时“赖亲”“恋亲”说起,指出即使娶妻生子了,也不能忘了生养自己的父母,若不孝顺父母,就会“子孙效行”,“阳受忤逆,阴受零丁”;第三部分从儿女幼小时父母“施德施恩”说起,讲父母年老时,儿女要“报德报恩”“顺志体情”。附录部分为两首七言古诗,再次强化本条的主题,极有可能是在举乡约时供童子歌诗所用。不过这两首诗掺杂了佛教的因果报应,带有明显的劝善意味。由此可见,颜钧对“孝顺父母”一条的阐释,诉诸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很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而采用诗歌的形式,则朗朗上口,易于传颂。
二、罗近溪:以“孝弟慈”为平民讲学的“实落处”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王艮对身本孝弟观的阐发,为罗近溪的“孝弟慈”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而颜钧对“圣谕六条”的阐发,则为罗近溪以“圣谕六条”为核心的乡约实践奠定了实践基础。因此,罗近溪“孝弟慈”思想的形成以及乡约实践,可谓水到渠成。
(一)“孝弟慈”理论——修己率人的挈矩之道
近溪的平民讲学,“纯以孝弟慈立教”[2]389,“夫孩提之爱亲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学养子而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爱敬之所自生者也”[2]108。可见,近溪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将“慈”与“孝弟”联系在一起的,认为父母之慈是孩提之孝弟之所由生,父母以慈心保赤子,赤子才能以孝弟之心爱亲敬兄。
近溪指出:“孝、弟、慈三事,是古今第一件大道、第一件善缘、第一件大功德,在吾身可以报答天地父母生育之恩;在天下可以救活万物万民万事之命。”[2]152不过近溪对“孝弟慈”的理解,却有一个从“寻常人情”到“归会孝弟”的深化过程。他在早年只把孝弟当作寻常人情,以为并不紧要,直到后来在省中逢着大会,与闻同志师友发挥,才幡然醒悟,孝弟才是做好人的路径。他从此回头,将《论语》细细再读,真觉字字句句重于至宝,又看《孟子》《大学》《中庸》,更无一字一句不相照映,哪怕是五经之源的《易经》,也只是究极孝弟的本源而已。自此以后,“一切经书皆必归会孔孟,孔孟之言皆必归会孝弟”[2]53。
近溪的“孝弟慈”思想,一言以蔽之,即以本末观贯穿“孝弟慈”,修己立本,率人达末,从而实现平治天下的理想。具体而言:一方面,是以“孝弟慈”修己立本。近溪指出,孔门宗旨,惟在求仁,而“孔子自己说仁,平生只有‘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是他正解”[2]102。所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人以仁修身,人亦以仁而立,而仁道之大端,则在“亲亲”即孝弟。故孝弟是修身立本之要;另一方面,是以“孝弟慈”率人达末。近溪指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故大人联属家、国、天下以成其身”[2]8。在近溪看来,仅仅以孝弟修身立本是不够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故大人还能以“孝弟慈”率人达末,使家、国、天下都归于孝弟,以实现天下太平的社会理想。而治平的机栝则在以挈矩之道修己率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莫不兴孝,长吾长以及人之长,而莫不兴弟,即明德达之天下,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治且平焉者也”[2]213-214。
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悲观,王艮在该书中还提道,“钦惟我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以孝弟为先,诚万世之至训也。”[3]50所谓“以孝弟为先”,就是教民榜文中著名的“圣谕六条”。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地方基层的治理,并为此颁布了一系列诏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有洪武三十年(1397年)九月颁布的“圣谕六条”:“上命户部下令,天下民每乡里各置木铎一,内选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太祖实录》卷第255,洪武三十年辛亥条,见《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版,第3677页。 “圣谕六条”对有明一代的地方基层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明代基层教化的指导思想”[4]。上至皇帝,下至各级官员,都极为重视“圣谕六条”在基层教化中的作用。王阳明最早将“圣谕六条”与乡约相结合,他在《南贛乡约》中提出要以“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5]665这十条乡约来协和乡民。其中,前四条明显是从“圣谕六条”化用而来,后六条则是从《吕氏乡约》中化出。
二是个人见闻坚定了他以“孝弟慈”为论学宗旨。近溪说:“予叨仕进,自极北边陲,率海而南,历涉吴、越、闽、广,直踰夜郎、金齿,其深山穷谷,岁时伏腊之所由为,未有一方一人而非孝弟慈和以行乎其间者,则其习虽殊,而其性固未甚相远也。”[2]316这就使近溪更加坚定地相信,性之所以善者,即在于孩提之爱亲敬兄,而善之所以同者,也惟在此“孝弟慈”三者。“民间一家只有三样人,父母、兄弟、妻子;民间一日只有三场事,奉父母、处兄弟、养妻子。家家日日,能尽力干此三场事,以去安顿此三样人,得个停当,如做子的,便与父母一般的心;做弟的,便与哥哥一般的心;做妻的,便与丈夫一般的心,恭敬和美,此便是民三件好德行”[2]151。因此,只要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以至于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之父子兄弟自法之,便可天下太平。
三是悟《大学》“格物”宗旨以兼贯本末。《大学》“格物”之说,历来聚讼纷纭,近溪早年时也曾苦于格物之旨,直到38岁时才忽悟格物之旨,认为“格物者,物有本末,于本末而先后之,是所以格乎物者也”[2]28。意、心、身、家、国、天下,本是一个大物,但物有本末,以身为本,而以家、国、天下为末。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是一件大事,但了结这件大事,却有个先后,以诚意、正心、修身为始,而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欲明明德于天下,究竟这场物、事,只是以挈矩之道挈度于物之本末,“故《大学》虽有许多功夫,然实落处,只是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故上老老、上长长,便是修身以立天下之本;民兴孝、民兴弟,便是齐、治、平而毕修身之用也”[2]188。只要人人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则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能家齐、国治而天下平。
(二)“孝弟慈”实践——《宁国府乡约训语》
近溪不仅坐而论道,提出“孝弟慈”的理论,而且起而行之,大力实践“孝弟慈”的思想。近溪居官期间,常以乡约为载体,实践自己“孝弟慈”的思想。
《宁国府乡约训语》集中对“圣谕六条”进行了阐释,可以看作是近溪对自己“孝弟慈”思想的集中实践,故笔者以该乡约为中心,探讨近溪“孝弟慈”思想的实践。由于该乡约训语原文颇长,故此处只举“孝顺父母”一条为例进行说明:
臣罗汝芳演曰:“人生世间,谁不由于父母,亦谁不晓得孝顺父母。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是说人初生之时,百事不知,而个个会争着父母抱养,顷刻也离不得,盖由此身原系父母一体分下,形虽有二,气血只是一个,喘息呼吸,无不相通。况父母未曾有子,求天告地,日夜惶惶。一遇有孕,父亲百般护持,母受万般辛苦,十月将临,身如山重,分胎之际,死隔一尘。得一子在怀,便如获个至宝,稍有疾病,心肠如割,见儿能言能走,便喜欢不胜。人子受亲之恩,真是罔极无比,故曰‘父即是天,母即是地’。人若不知孝顺,即是逆了天地,绝了根本,岂有人逆了天地,树绝了根本而能复生者哉?故凡为人子,当常如幼年时一心恋恋,生怕离了父母,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则必告,反则必面,远游则必有方。又当常如幼年时一心嬉嬉,生怕恼了父母,好衣与穿,好饭与吃,好屋与住,好饭与吃,好兄弟姊妹同时过活。又要常如幼年时一心争气,生怕羞辱了父母,读书发愤,中举做好官,治家发愤生殖,置产业。间或命运不扶,亦小心安分,啜茶饮水,也尽其允,也留个好名声在世上。凡此许多孝顺,皆只要不失了原日孩提的一念良心,便用之不尽,即如树木,只培养那个下地的一些种子,后日千枝万叶,千花万果,皆从那个果子仁儿发将出来。”[2]752-753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在这种社会情形下,刑事诉讼案件激增与司法资源短缺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所以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追求效率价值就显得更加迫切,庭前会议制度的设置乃是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诉讼效率最大化的最好途径。
在近溪看来,孝顺父母乃是人的良知良能,正所谓“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具体而言:一是子女与父母有天然的血缘纽带,所谓“此身原系父母一体分下,形虽有二,气血只是一个”;二是子女受亲之恩,罔极无比,父母从“未曾有子”到“一遇有孕”,再到“得一子在怀”,可谓备尝艰辛,子女若不知孝顺父母,便是“逆了天地,绝了根本”。子女要孝顺父母,“当常如幼年时一心恋恋,生怕离了父母”;“又当常如幼年时一心嬉嬉,生怕恼了父母”;“又要常如幼年时一心争气,生怕羞辱了父母”。这许多的孝顺,都只从“原日孩提的那一念良心”发端而来,只要不失了赤子良心,便可用之不尽。
在演绎完圣谕后,近溪又概括说,“圣谕六条”不过是欲人“为善事,戒恶事”[2]755。基于此,近溪又将“圣谕六条”与《吕氏乡约》打并一块,认为“善恶得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四句言语,虽则与圣谕不同,其实互相发明”[2]755。所谓“德业相劝”,是说同族、同乡、同会之人,都要以“圣谕六条”互相劝勉;所谓“过失相规”,是说在践行“圣谕六条”的过程中,遇有过失,大家应互相规讽;所谓“礼俗相交”,是说平常时节和睦乡里,大抵期于不失古礼,不悖时俗;所谓“患难相恤”,是说患难之际和睦乡里,只有患难周急,才是彻底的好人。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近溪的《宁国府乡约训语》有以下三个特点:
在王艮看来,“盖孝者,人之性也,天之命也,国家之元气也”[3]51,而要培植元气,就必须“尽其术”,即取天下之孝者立乎高位、使之治事,以劝天下之孝、尊天下之孝、教天下以孝。而取天下之孝者又须“取之有道”,即取之以专、取之以渐。所谓取之以渐,即一月颁取天下之孝者,二月颁取在各司之次位,三月颁赏爵禄,四月任以官事,五月颁以举之司徒,六月颁取进诸朝廷,颁诸天下。所谓取之以专,即要月月颁诏,使天下皆听其谆谆之教,而知在上者用心之专也,又得以宣畅其孝心,使无间断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作为国家元气的六阳之孝壮盛起来,才能使六阴之不孝渐渐转化,如此则天下之不孝者鲜矣。在王艮看来:
EFpsize,j为j类土地的足迹广度,EFpsize,reg为区域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所组成的生态足迹广度。
近溪之所以在举乡约时以“圣谕六条”为核心,第一,继承泰州学派重视孝弟的家风。如前所论,王艮特别推崇“圣谕六条”;颜钧著有《箴言六章》,专门阐发“圣谕六条”;近溪在此基础上,着力阐扬“圣谕六条”,可谓渊源有自;第二,顺应明廷推行乡约的时势。明廷于嘉靖八年(1529)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乡约,并很快与“圣谕六条”结合在一起。近溪在任内推行以“圣谕六条”为核心的乡约,即是积极响应朝廷的号召,也为讲学找到了合法的前提。此外最为重要的则是,“圣谕六条”与近溪自己的论学宗旨不谋而合。近溪思想归宗“孝弟慈”,而“圣谕六条”首之以孝弟,故近溪认为“高皇帝真是挺生圣神,承尧舜之统,契孔孟之传,而开太平于兹天下,万万世无疆者也”[2]5。有学者指出,“罗汝芳将太祖六谕提升到道统的地位上,与泰州学派师道自任的取向是矛盾的,这标志着泰州学派师道自任思想的终结”[注] 陈时龙:《师道的终结——论罗汝芳对明太祖<六谕>的推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明史研究论丛(第十辑)》,2012年3月1日。 ,这种论断未免偏激,完全忽视了近溪自己的学术旨趣即“孝弟慈”。
二是以俗语训导,侧重说理教化。陈时龙研究员曾概括嘉靖年间士大夫对“圣谕六条”的三种诠释方式,即纲目式、歌诗式、说理式。[4]其中,纲目式是分条设目诠释六谕,列举同约之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乃是受《吕氏乡约》疏之为目的诠释方式的影响;歌诗式是以诗歌诠释六谕,如前举颜钧的《箴言六章》,既朗朗上口,又易于传诵;说理式则是以浅近俗语诠释六谕,《宁国府乡约训语》“可以说是说理式六谕诠解之经典”[4]。从上举“孝顺父母”一条的演绎来看,近溪的用语可谓通俗易懂,既将抽象的良知观念用浅显直白的语言传达出来,又将何以要孝顺父母以及如何孝顺父母的大道理讲得生动感人,无怪乎黄宗羲评论说:“近溪舌胜笔。顾盻呿欠,微谈剧论,所触若春行雷动,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现前。”[1]762
近溪之所以用白话俗语进行说理:一是因为说理的对象大都是不识文字的乡里村民,因此语言不得不通俗易懂;二是近溪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坚持为政以德,他在该乡约序语中说,易俗之机,惟在“敦德礼以洁治源”“萃人心以端趋向”[2]750,而章程与讥察则在有所略,故他在举乡约时,必然以说理的方式感发人心,引人向善。
三是具有强烈的复兴礼乐的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举行乡约的过程中注重乡饮酒礼与歌诗这两点。乡饮酒礼是周代乡人聚会宴饮的礼仪,具有尊贤与尊长养老两种功能。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乡饮酒礼。及至明代,朱元璋又将乡饮酒礼与宣读“圣谕六条”结合在一起,突出了其在地方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不过在近溪这里,“酌酒”改为了“敬茶”,这或许是因为酒可致人迷乱,茶则醒人心神。此外,近溪还特别重视歌诗,在乡约中引入诗教乐教。在该乡约中,歌唱的是《诗经·南山有台》。进讲者每演讲完两条圣谕,歌生班首就吟唱其中的一至两章。近溪之所以选取此诗,乃是希望会众通过对“圣谕六条”的学习实践,成为有德君子,就像南山之下的有台、有桑等一样,都长成有用之材。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通过复兴礼乐,以实现尧舜三代之治,是儒士群体共同的社会理想,近溪亦莫能外,故他特别重视通过乡约来复兴礼乐,以期实现移风易俗、安上治民的理想。
近溪在宁国府任上,“诚以讲会、乡约治郡”[2]922,竭力表彰“圣谕六条”“凡士民入府,则训以孝顺父母,尊敬长上”[2]407。当时就有人质疑,仅凭“圣谕六条”能否治理好宁国府,而事实证明,近溪的乡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及经月,而鞭朴不闻,数月后,而教化大行,远迩向风。不仅如此,近溪在宁国府的乡约实践,还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徽州知府何东序在全府倡立乡约,其做法如选年高有德者为约正,通礼文者为约赞,童子歌诗等,都借鉴了近溪的乡约实践;又如隆庆时的一些宗族乡约,像徽州府休宁县的乡绅,对“圣谕六条”的解释,甚至直接引自近溪的乡约训语。[注] 关于此点,具体可参看董建辉教授所著《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213页。
三、“孝弟慈”思想的实践与理论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近溪的“孝弟慈”思想,在晚明乃至整个儒学发展史上,都可谓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约翰·奥哈拉先生:从企业运营角度讲,麦格纳之所以不惧市场起伏的原因在于:第一,我们的定位非常清晰;第二,麦格纳有强大的资产负债表,充裕的现金流完全可以支撑我们克服市场周期性。
“孝弟慈”思想最大的实践意义在于,为泰州学派的平民讲学找到了落脚点。近溪将阳明心学抽象理性的良知观念发展成为具体感性的“孝弟慈”,从而使圣人之道更加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我们知道,阳明从百死千难中悟得良知,正是为治儒门支离之病,极有功于圣门。阳明指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5]7可见阳明所说的良知,乃是指本体而言。这种本体良知对于不识文墨的普罗大众而言,未免显得过于抽象,虽然在指点良知的过程中可以深入浅出,事实上阳明确实也做到了,但不免离百姓日用还隔着一层。近溪正是有见于此,所以才评价阳明的良知之学说:“阳明先生乘宋儒穷致事物之后,直指心体,说个良知,极是有功不小。但其时止要解释《大学》,而于孟子所言良知,却无暇照管,故只单说个良知;而此说良知,则即人之爱亲敬长处言之,其理便自实落,而其工夫便好下手。”[2]86近溪提出的“孝弟慈”思想,正是接续孟子良知良能之爱亲(孝)敬长(悌)而来,把阳明本体层面抽象理性的良知观念发展成为贴近百姓日用的具体感性的“孝弟慈”,不仅使良知在百姓日用中有了“实落”处,还揭示了百姓实践良知的“下手”处,“民间一家只有三样人,父母、兄弟、妻子;民间一日只有三场事,奉父母、处兄弟、养妻子。家家日日,能尽力干此三场事,以去安顿此三样人,得个停当,如做子的,便与父母一般的心;做弟的,便与哥哥一般的心;做妻的,便与丈夫一般的心,恭敬和美,此便是民三件好德行”[2]151。
其理论意义则在于:一方面,以“孝弟慈”贯通四书五经,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方式。孝是否具有形而上的本体意义,可以孝与仁的关系为例进行探讨,具体表现为对“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一语的阐释。有子虽然首先提出孝弟“为仁之本”的论断,但此语究竟何解,后儒却有不同的理解。汉唐儒者的主流观点认为,孝弟是仁的根本。皇侃指出:“此更以孝弟解本,以仁释道也。言孝是仁之本。若以孝为本,则仁乃生也。”[9]而宋明理学家的主流观点则认为,仁才是孝弟的根本。朱子指出:“论仁,则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则当自孝弟始。”[10]可见,汉唐儒虽然也说“本”,但“本”之所指,则是根基、基础之意,并无形上的意义,且根基意义上的孝悌,已被宋明理学家所谓的“行仁,则当自孝弟始”所涵摄;而宋明理学家所说的“本”,则是体用意义上的本体之义,仁是形上本体,而孝悌则是形下之用。不过,居于形下层面的孝悌,在晚明则实现了向本体的升越。这其中,近溪可谓代表。在近溪看来,“孝弟慈”就是《大学》的“明德”,就是《中庸》的“天命”,就是《论语》的“为仁之本”,就是《孟子》的“良知”“良能”,就是《周易》的“生生”之道,就是《尚书》的“峻德”,就是《诗经》的“懿德”,就是《春秋》《礼记》的经礼。因此,“孝弟慈”作为一种普通的家庭伦理原则与伦理情感,在近溪这里,获得了内圣层面的形上意义,如明德、天命、良知良能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是学者志学修身的头脑所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从事传统民居保护工作的研究,各级政府也都划拨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扶持,但传统民居形式上的丰富多彩,造成了其保护难度较大。以往,传统民居的保护多侧重于基于测绘的二维平面图档的保存,这已不符合如今三维动态保护的需求。因此,亟须引入新技术解决传统民居二维图纸与三维表达之间的矛盾。
不仅如此,近溪在大悟格物之旨后,还指出“孝弟慈”具有外王层面的意义,即不仅以“孝弟慈”修身立本,还要以“孝弟慈”率人达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明明德(明德即是“孝弟慈”)于天下。在儒学史上,对孝道最为推崇的莫过于孝道派及其理论著作《孝经》。《孝经》指出:“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经·开宗明义章》),对孝弟之道的外王功能推崇备至。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孝弟的风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孝治天下。如前所论,近溪在中年大悟格物之旨,以为意、心、身、家、国、天下本是一物,但以身为本,家、国、天下为末,而欲明明德于天下,只是以挈矩之道挈度于物之本末,而挈矩之矩,就是“孝弟慈”,而挈矩之道,就是以“孝弟慈”挈度于上下左右,正所谓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悖,只是以“孝弟慈”的矩修身立本,自然能够率人而达末,正己而物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则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能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社会理想。
另一方面,泰州学派的“孝弟慈”思想,也为“四民异业而同道”找到了更加坚实的理论依据。中晚明时期,随着四民的流通尤其是商人与士人的融合,士阶层对四民在社会中的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最著者为王阳明所提出的“四民异业而同道”之论。王阳明指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5]1036阳明主要是从“尽心”的角度来论述“四民异业而同道”的。在他看来,士、农、工、商只要尽心于修治、具养、利器、通货,就都有益于“生人之道”。可见,这是从整个社会运转的角度对“尽心”的客观效果进行的一种抽象概括。问题在于,四民“尽心”于四民自身有何“同道”之处?这不能仅以“尽心”这一从业精神状态来简单概括,而应深究“尽心”这一精神状态背后的动机。关于此,近溪恰恰给出了完满的答案,那就是尽心四业以求尽此“孝弟慈”。近溪指出:“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家,一家之中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国,一国之中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国之孝弟慈而观之天下,天下之大,亦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缙绅士夫,以推之群黎百姓,缙绅士夫,固是要立身行道,以显亲扬名,光大门户,而尽此孝弟慈矣,而群黎百姓,虽职业之高下不同,而供养父母,抚育子孙,其求尽此孝弟慈,亦未尝有不同者也。”[2]232-233在近溪看来,“孝弟慈”才是通之家国天下的“同道”,无论是“缙绅士夫”,还是“群黎百姓”,虽职业有高低不同,但尽心本业以求尽此“孝弟慈”则无有两样,“总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结维系,所以勤谨生涯,保护躯体,而自有不能已者”[2]233。诚如吴震所指出的,“孝弟慈作为一种伦理学说,可以打通‘缙绅士人’与‘群黎百姓’的界限,也不受家族/社会、道德/政治的局限,而成为普遍性的道德法则”[11]。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近溪的“孝弟慈”思想,为泰州学派的平民讲学实践找到了真正的“实落处”,“民间一家只有三样人,父母、兄弟、妻子;民间一日只有三场事,奉父母、处兄弟、养妻子。家家日日,能尽力干此三场事,以去安顿此三样人,得个停当,如做子的,便与父母一般的心;做弟的,便与哥哥一般的心;做妻的,便与丈夫一般的心,恭敬和美,此便是民三件好德行”[2]151。平民讲学的关键之处,在于将极高明而又尽精微之道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给愚夫愚妇,同时使普罗大众将这种高明、精微之道实践于庸常而又广大的日常生活当中。“孝弟慈”正是具备这种特性,极高明而又道中庸,尽精微而又致广大,可以高明到天命之性,但又落实到百姓日用,可以精微至生生之易,但又达致天下而莫不尊亲。因此以“孝弟慈”讲学,既能贴近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又能为愚夫愚妇所乐于接受与践行。
参考文献 :
[1]黄宗羲.明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
[2]罗汝芳集[M].方祖猷,梁一群,李庆龙,等,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3]王艮.王心斋全集[M].陈祝生,等,校点.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54.
[4]陈时龙.圣谕的演绎:明代士大夫对太祖六谕的诠释[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3(5):611-621.
[5]王阳明全集[M].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颜钧集[M].黄宣民,点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9.
[7]叶春及.石洞集卷七·惠安政书九·乡约篇[M]//备忘集(石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489.
[8]吴震.明末清初劝善思想研究(修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89.
[9]论语集解义疏[M].何晏,集解.皇侃,义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4.
[10]朱子语类:第二册[M].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463.
[11]吴震.泰州学派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40.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The “Foothold” of the Folk Lecture of Taizhou School
TANG Dong-hui
(Confuc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02,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folk lectures of Taizhou School regards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as “foothold”. Wang Gen’s view of filial piety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t, and Yan Jun’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x oracles” laid a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it. On this basis, Luo Jinxi developed the unique “filial piety and kindness” thought of Taizhou School. In theory, he pointed out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not only to achieve themselves, but also to achieve others. In practice, he taked the rural covenant as the carrier to elaborated and practiced the “Six Oracles”. The bigges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ought of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of Taizhou School lies in finding a “foothold” for the folk lecture of this school;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lies in that on the one hand, providing a new way of interpreting 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inner sanctity and external kingship, on the other hand, also establishing a more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our groups with different occupation but the same way”.
Key words :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Taizhou school; folk lecture; “foothold”
中图分类号 :B24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6133(2019)02-0009-08
[收稿日期 ]2018-02-13
[作者简介 ]唐东辉(1987-),男,广西全州人,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
[责任编辑 刘昶 王建蕊]
标签:“孝弟慈”论文; 泰州学派论文; 平民讲学论文; “实落处”论文;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