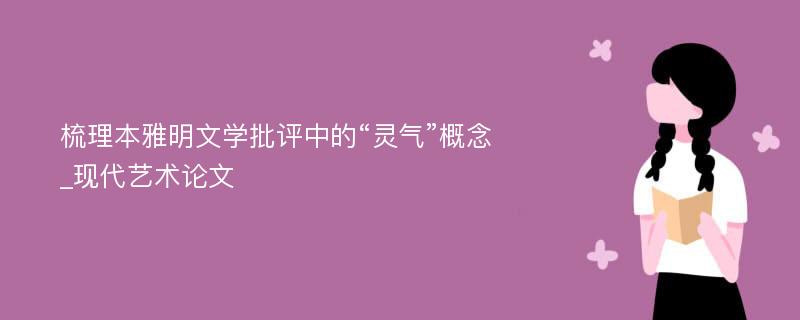
对本雅明文艺批评中“Aura”概念的梳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文论文,批评论文,概念论文,Aura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4)01-0124-05
本雅明同很多现代思想家一样,更强调现象自身的重要性,这直接可从他在文艺批评中对概念的运用上体现出来。概念,在本雅明的文艺批评中成了始终不脱离具体体验的个体思想的庇护者,他所运用的一些批评术语,往往也带有含混模糊的特征,对其具体概念的分析,也就成了把握本雅明思想的一个契入点。
在本雅明的文艺批评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绕不过去的,即“Aura”。此词在中译本中有多种译法,如:“韵味”、“灵晕”、“光晕”、“气息”等[1],下面我们通过对涉及到此概念的具体批评文本的分析,从多个角度来对此概念进行界定与梳理,以获得一个较清晰的认识。
在《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4-1935)中,本雅明谈到由于机械复制而导致艺术品“本真性”(Echtheit)的消失,进而导致其“权威性”也难以维系。在这里,本雅明提出了他的“Aura”概念:“复制过程中所缺乏的,可以用Aura这一概念来概括”[2](P264)。在此著作中,我们把本雅明关于这一概念的论述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Aura”是与“独一无二”性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复制技术可重复生产复制品,这样,被复制品的独一无二的诞生便被大量出现所取代”[2](P264))。第二,“Aura”是与“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复制技术使被复制品脱离了传统范围”[2](P264),“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性与它植根于传统的关联是一致的。这一传统本身当然非常活跃、特别易变”[2](P266))。第三,“Aura”是与“礼仪”、“膜拜”联系在一起的(“艺术作品的氛围(Aura)浓郁的生存方式从来就不能完全脱离礼仪功能。也就是说:‘本真的’的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的价值以礼仪为根基,它的独特的、最初的使用价值正在于此”[2](PP.266-267);“把Aura定义为‘一定距离外的独一无二显现,无论它有多近’,这无非是用时空感知范畴来表述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远是近的对立面,本质上的远是不可接近的。事实上,不可接近性是膜拜画的主要性质”[2](P267);“随着绘画的膜拜价值的世俗化,对其独一无二基质的设想也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在观赏者的想象中,在膜拜画中占主导地位的显现的独一无二性不断被画家或他的绘画成就的切实可感的独一无二性排斥掉了……随着艺术的世俗化,真实性(Authentizitaet)取代了膜拜价值”[2](P267))。
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1939)中,“Aura”则同绵延、非意愿记忆、震惊、通感等几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本雅明在这篇论文中一开始就提到了柏格森的《物质与记忆》,并进而谈到:“自上世纪末以来,哲学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以图把握一种‘真实’经验,这种经验同文明大众的标准化、非自然化了的生活所表明的经验是对立的”[3](P126)。《物质与记忆》是用时间的绵延说明经验的本质,我们要进入以往的某个时刻,获得对那逝去世界的完全把握,单纯凭借理性的记忆是不可能的,因为理性本身就带有析取过滤的特征,本雅明由此提到普鲁斯特所说的“非意愿记忆”,它区别于“意愿记忆”即“理性记忆”。普鲁斯特对于在孔布莱镇度过的童年时光一直难以回忆起来,而在一天下午一种叫玛德兰小点心的滋味却把他带到了过去。本雅明进而引入波德莱尔的“通感”,“通感”的意义在于寻求在危机中把自己建立起的经验,在所有的感性印象中,只有与同样的气息结盟,本雅明说:“辨出一种气息的光晕能比任何其它的回忆都更具有提供安慰的优越性,因为它极度麻醉了时间感。一种气息的光晕能够在它唤来的气息中引回岁月”。在此,本雅明把“Aura”定义为“在非意愿回忆中自然地围绕起感知对象的联想”[3](P159),这个结论的得出也有佛罗伊德的启发,佛罗伊德的阐述是:“进入意识和留下一个记忆的踪迹在同一个系统中是不能兼容的两个过程”;“意识怎么也得不到记忆踪迹,但却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抑制兴奋”[3](P131),它抵制外部世界过度能量的影响,以免给人不断的震惊。另外,在《讲故事的人》(1936)中,“Aura”还可以比作与发达大工业相对照的在小作坊的悠闲时间里手艺人所完成的陶罐上手的痕迹。
那么,本雅明对“Aura”(韵味)以及现代艺术中“Aura”的消失所持的是怎样的态度呢?研究者对此意见不一。如Chandra Mukerji和Michael Schudson在为《流行文化反思》(Rethinking Popular Culture,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撰写的序言中提到:“(本雅明)对于流行艺术和新技术所具有的革命性潜力,持乐观态度,但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学者则不对此表现乐观。这种乐观态度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很明显,他指出,由于形象的批量生产,形象创造者在创作中需要追求群体支持,而不是个人表现。因此,批量生产必然而根本地把传播政治化。它把‘他者’(作者)从受众的直观中消除,而只有在大批人可以被说服成为受众时才能进行批量生产”。刘象愚先生在《本雅明文集》所作的序中认为,在其前期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是对失去“韵味”(Aura)的现代艺术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而在其他的一些批评文本中则对富有“韵味”(Aura)的传统艺术有一种怀恋的倾向。[4]刘北成先生认为:“尽管本雅明本人对‘灵晕’(Aura)艺术有一种怀恋情愫,但是他不以线性的‘进步’或‘倒退’观念为衡量标准,而是基于他的革命辩证法,对后‘灵晕’艺术(机械复制艺术)也抱着积极的态度”[5](P180)。
下面我们结合文本来做一个具体的分析。首先,我们来看《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4-1935)。此书的第六、七节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地方,因为他对现代艺术“韵味”(Aura)的消失还未透露出明显的态度,下面我们来仔细考察这个文本空隙前后的论述。
在第七节及后面的几节里,本雅明指出为像摄影这样的现代艺术赋予意义与价值的困难,一些理论家确实也把电影之类的现代艺术归入艺术领域,但是,他们其实没有看到这类艺术的特征所在,而只是硬把属于传统艺术的膜拜因素注解到电影中去,“武断地硬从电影中阐释出膜拜因素”[6](P272);恰恰相反,现代艺术的特征是“展览价值开始全面排挤膜拜价值”[6](P270)。正是由于艺术的“膜拜价值”被抑制、被排挤,与其相连的权威性也就消弱了,这样,大众可以直接占有艺术品的复制物,而且,人们可以直接参与进去,创造者与接受者的界限模糊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演员。面对当代人希望自己被复现的正当要求,在西欧对电影的资本主义开发制止了对谁进行特殊的满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工业所感兴趣的只是通过虚构的想象和双关性的思辨来刺激大众的参与”[6](P279)。这些似乎在肯定现代艺术的进步意义,因为这正是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所要求的东西所得到的实现。电影抑制“膜拜价值”,不要求观众“凝神专注”,而只是一种“消遭”,“电影通过震惊效果来迎合这种接受方式。电影排挤膜拜价值,因为它不仅让观众持鉴定者的态度,而且电影院中的鉴定者的态度不要求全神贯注”[6](P290)。
以上这些是第七节后面的论述,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本雅明欲赋予现代艺术以意义的努力,又如在第十二、十三节中,本雅明把现代艺术称之为“进步”的:“进步状态的标志是,观赏和经历的乐趣与专业评判者的态度直接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种结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标志。……而在电影院里,观众的这两种态度已融为一体”[6](P282);“……我们的办公室和塞满家具的房间、我们的火车站和工厂,似乎把我们圈死在里面了。这时电影出现了,它以十分之一秒的炸药摧毁了这个牢笼世界,从此,我们便可以在四处飞散的废墟间从容地进行历险旅行。特写镜头延伸了空间,慢镜头则延伸了运动”[6](P284);“摄影机凭借它的辅助手段——俯冲与上升、中断与孤立、对过程的延伸与压缩、放大与缩小,介入进来了。通过摄影机,我们才知晓了视觉无意识,就如同通过心理分析学,我们才了解了本能无意识”[6](P285)。带有“韵味”(Aura)的传统艺术始终同人们保持着距离,保持着它的“权威性”,不允许人们以消遣的眼光来看,而是要把“自我”沉入到“艺术品”之中:“消遣与定心安神相对立,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艺术作品前,定心安神者沉入了作品中:他走进了作品”,与此相反,在现代艺术中,“心情涣散的大众让艺术作品沉入自身中……消遣在所有艺术领域中都越来越受推崇,崭露头角,它显示了统觉所经历的深刻变化,消遣中的接受在电影中找到了真正的练习工具。电影通过震惊效果来迎合这种接受方式”[6](PP.288-290)。
在《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第十四节中,本雅明把对有韵味(Aura)的传统艺术所持的“凝神观照”与“静观玄想”这种意识看作是帮助资产阶级摆脱教会监督的“只与上帝同在”的意识[6](P287),而资产阶级同时是伴随着工业技术的运用兴起的,到了他们的衰落阶段,如果仍持原来的态度,就会陷入孤立之中,这种意识使他们必须要考虑”个人在与上帝交往时投入的力量可能会使他逃避公众事物”[6](P287),因此只能借助技术来使“大众获得表达”,这样,现代艺术好像争取到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赋予了大众,使他们能以一种非崇拜的眼光来看,原来是以“艺术品”为中心,而现在是以“自我”为中心。
但本雅明在此书的第六节中写道:“在人脸转瞬即逝的表情中,氛围(Aura)最后一次——在初期照相术中——起着作用。这便是照相的忧伤、无以伦比的美之所在”[6](P270),“它(摄影)要求某种特定的接受,对此,神游八极的冥思已行不通;照片使观看者不安,使它感到:要看懂它们,就得找一条特定的路。画报立即开始为他提供路牌。不管路牌是对是错……观众由文字说明获得指导,不久,文字说明在电影中变得更为精确、更具强制性,因为对任何一幅画面的理解都已由之前的所有画面规定得明明白白了”[6](P271)。
此处的文字在描述一种大工业生产时代现代人的命运,即,尽管大众争取到了那种可以进行“批判”、“鉴赏”的“权力”,但是,现代电影制造出了一种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由规定好了的所有先行展现的画面向大众传输的。大众获得了“权力”,但是面对“愈趋精密和愈趋强制”的现代文化,只能是沉于“消遣”。正如本稚明在这部著作的最后所写的:“观众是主考人,不过是心神涣散的主考人”[6](P290)。
下面,我们再来考察他的另外一部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在此部著作中,我们参看的主要是第二部分:《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在这一部分里,本雅明主要提到了两个人,他们是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提到这两个人的时候,不是把这二者放在同一个层次上论述的,本雅明在这两个人中间是有所倾向的。
普鲁斯特是有意识地把握柏格森理论中“纯粹记忆”,即他自己归纳的“非意愿记忆”的作家,如上面所提到的关于玛德兰小点心的滋味把他带到过去的例子,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本雅明认为普鲁斯特“要在现在一代人面前重新树立讲故事的人的形象”[7](P129)。而“讲故事的人”的叙述在本雅明看来是一种“老式的叙事艺术”,是与现代媒体的叙事方式不同的,“它带着叙述人特有的记号,一如陶罐带着陶工的手的记号”[7](PP.156-157),而这也就是本雅明所提到的同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相区别的传统艺术所特有的“Aura”(韵味),普鲁斯特“以无比的坚韧”从事这种有“韵味”艺术的创作,着力于回忆。
但本雅明提到:“‘在波德莱尔那里……这种怀旧甚至为数更多。’……但如果《恶之花》包含的一切只不过是这个成功,那么它也就不成为其本来面目了。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能从同样的安慰的无效、同样的热情的毁灭,和同样的努力的失败里获得诗。这种诗无论从哪方面说也不比那些通感在其中大获成功的诗更低级。‘忧郁与理想’是‘恶之花’组诗的第一首。‘理想’提供了回忆的力量;而‘忧郁’则召集了大批第二性的来反对它。它是它们的指挥官,一如邪恶是苍蝇的主子一样。一首‘忧郁’诗‘虚无的滋味’(Le Gout du neant)写道:‘春天,爱人,失去了芳香’。在这里波德莱尔极其谨慎地表达了一种极端的东西;这毫无疑问是他特有的。Perdu(失去)一词宣告了他曾享有的经验目前正处于崩溃的境地。气息的光晕无疑是非意愿记忆的庇护所。……一种气息的光晕能够在它唤来的气息中引回岁月。……然而一种强烈的感情(如狂怒)的核心正是这种经验的极度无能。……愤怒的暴发是用分分秒秒来记录的,而忧郁的人是这种计时的奴隶。……在‘忧郁’中,对时间的理解是超自然地确切的。每一秒都能找到准备插入到它的震惊中去的意识”[7](P164)。
显然,波德莱尔同普鲁斯特是不一样的,他并不致力于“Aura”的唤回,相反,在波德莱尔的诗歌当中,更多的是“震惊”。因为他面对的是大众的“盯视”,是“未回报他注目的眼睛”[7](P164),他因而不去幻想,波德莱尔写道:“我更喜欢看舞台的布景画,在那儿我看到我酷爱的梦被交给完美无缺的技巧和可悲的简洁去处理”[8](P165);对波德莱尔说来,“头戴光环的抒情诗人早成了老古董”[9](P166)。
虽然波德莱尔的观点未必是本雅明自己的观点,但是,从此文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本雅明在普鲁斯特与波德莱尔之间,还是倾向于波德莱尔的。本雅明称波德莱尔的诗歌是“一颗没有氛围的星星”,“气息的光晕(Aura)在震惊经验中四散”[9](P168)了。去掉了那种让人腻烦的“尊严”,即,与传统艺术独一无二的“韵味”紧密相连的“权威性”。
可以看出,本雅明对“韵味”(Aura)持有一种相当复杂的感情,怀恋与厌弃混杂叠加,正如他在《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中所引用的居斯塔法·热弗鲁瓦的一句诗:“这里坐落着旧新桥的,一模一样的仿制品;根据当前的法令,它已被装修一新”[9](P108)。复制技术打碎了古典艺术所拥有的“权威”,而创造出了一系列的“震惊”,使人从那种“凝视”所滋长的“压抑”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本雅明在这里肯定了启蒙精神所要求的正当性——人人都有权鉴赏,人人都可以参与,人人都可以占有:“它那‘视万物皆同’的意识已如此强烈,以致它借助复制从独一无二的事物中获取同类事物”[10](P266),那种“神秘的距离应被冲破”[11](P165)。但是,本雅明并没有为“韵味”(Aura)的消散而欢欣,这位敏感的哲学家注意到,在大众用巨大的代价争取到自己的权力之后,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思想,观赏者通过文字说明从画报中直接获知的意旨,在电影中就愈趋精密和愈趋强制,“因为对任何一幅画面的理解都已由之前的所有画面规定得明明白白了”[12](P271),因而,大众不必去思考,只须在“消遣”中接受这些“所规定好了的”东西,做一个心不在焉的主考官;本雅明看到了现代复制技术既使人们获得占有艺术品的权力,又有另外的一面,即现代艺术借助机械复制从对“仪式”的依附中摆脱出来后,开始建立在另一种实践的基础上,即政治基础上,而法西斯主义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把其政治进一步美学化,甚至把战争美学化:“战争是美的,因为它借助防毒面具、令人生畏的扩音器、喷火器和小型坦克建立了人对他所征服的机器的统治。战争是美的,因为它实现了人所梦想的躯体金属化。战争是美的,因为它在机关枪兰花般的火焰周围缀满了绚烂的草坪”[12](P291),本雅明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是技术所发动的起义,毒气战争是“技术摧毁氛围(Aura)的新方法”[12](P292)。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本雅明提出应该以艺术政治化的途径来消解法西斯主义美学和资本主义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