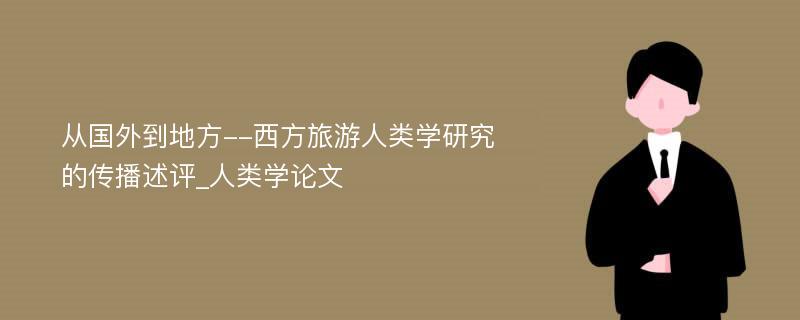
从异域到本土——旅游人类学的西学东渐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东渐论文,人类学论文,述评论文,异域论文,本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遥远的他乡,人类学家有一种天然的向往,他们渴望了解异域未知的神秘世界,到处追寻已不存在的真实的种种痕迹,以此反观自身的文化,或者从异域他乡的文化世界中建立人类文化的普遍模式,达成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是人类学家的文化抱负。”[1] 当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名著《忧郁的热带》中发出人类学家试图参与到对旅游活动进行观察与研究的诉求之时,在西方,事实上人们仍然关注的是旅游能给当地带来多少经济利益。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二战之后,严格地说由人类学家所进行的严肃的有关旅游方面的研究是在20世纪的60年代初期。“1963年,人类学学者努尼斯(Nun is)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述了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西方的旅游人类学学者一般将其当作人类学学者加入旅游研究的标志。”[2]
事实上,人类学家对旅游的早期关注与研究常常是描述性的,理论研究相当少,他们倾向考虑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到底是益是害这一简单化的价值判断。人类学家之所以持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态度,主要是由于当时许多人类学家对于西方社会制度中的权力机构的不信任,特别是对那些在旅游目的地带有“文化帝国主义”性质的行为的憎恶。随着现代旅游规模前所未有的扩大,使旅游人类学对旅游事项的研究着眼点,渐渐从揭露事实的真相转变为对旅游负面影响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评论上。而由于旅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到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涉及的是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影响方面的问题,因此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也相应集中到了这个领域,并已经和正在取得重要成果;同时,旅游人类学的主要突破点也集中在这里。
旅游人类学认为,现代旅游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充满了矛盾和各种利益冲突;接待地社会文化商品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衰退问题,“伪民俗文化”的泛滥;在一些市场经济不发达地区,大量来自发达国家旅游者带来的异质文化的冲击,使当地传统伦理观念、社会和家庭的传统凝聚力减弱;与此同时,由于旅游者的大量涌入造成接待地环境和生态遭到破坏,动摇着接待地社会的整个基础;由此而引发了旅游人类学对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激烈争论。如“哈莱尔·邦德(harrell bord1978)在《面向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户:冈比亚的旅游和发展》一文中,对由外界刺激和外界导向引发的经济发展提出疑问。卢基西斯(loukissons1978)在《旅游和环境的冲突:以希腊马可纳斯岛为例》中指出,旅游使该地区环境急剧恶化。皮·桑亚(P·Sunyer1977)研究了布拉瓦海岸地区的大众旅游,认为它强化了陈规陋习。努尼斯(Nunis1977)对外来因素导致旅游目的地文化发生“可口快乐化”现象感到失望。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在《切开零售的文化》中提出的,他认为旅游使巴期克地区阿拉德节日仪式商品化了。这一节日仪式深受当地人们喜爱,凝聚了许多当地传统文化。人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市场机制中的一个元素是他无法忍受的。[3]
与上述论点针锋相对的是“麦基恩(MCKEAN1976)对巴厘岛,科恩(Cohen1979)对泰国,波斯维恩(Boissenvain1987)对马耳他和曼斯浦格(Mansperger1981)对布拉瓦海岸的研究,他们认为旅游是良性或者有益的发展途径”。[4]
旅游人类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成果终于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了,这就是1977年史密斯主编的《旅游者与东道主:旅游人类学研究》(《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人类学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领域内的研究开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提出了“旅游人类学”的概念。虽然这个概念在以前和后来都有人提到,但是首先以一本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包括15篇文献,分别讲座了旅游人类学理论的架构问题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行为的个案,以反映可能成为旅游学科中第一个学科分支的构想和框架的,就是该书。“该书被旅游学术届的权威期刊《旅游研究年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称为旅游人类学的里程碑。”[5]
史密斯“里程碑”式的著作成就了旅游人类学的学术地位,也使得新兴的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更加明确:即其重点研究的内容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旅游者及旅游本身的研究;一是旅游业的出现和发展给东道国地区带来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影响和研究。后者显然不定期包括了旅游主体和客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对前者的研究主要包括:什么是旅游者?他们的旅游行为和动机是什么?不同的需求产生了哪些不同的旅游方式?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到人类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如文化变迁、文化拒斥、文化互动、族群性、全球化、地方化、迁移、现代性、宗教、法律等等。人类学家认为这些都是跨文化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旅游的意义以及旅游给社会物文化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变迁。
旅游人类学对后者的研究即旅游业给东道国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文化上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旅游与文化涵化;旅游与文化传统;旅游与商品文化;旅游与民族工艺品的开发问题;旅游与民族文化重建问题;旅游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旅游与宗教的关系;旅游与性别角色问题;旅游与人口流动问题等。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随着应用人类学的迅速发展,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者也在不断壮大和成熟,以美国加州大学为代表的教授群体成为了旅游人类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格雷本(Nelson Graburn):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教授,著名旅游人类学家。他在分析旅游现象时,提出了首先要了解与人类学有关的概念和方法体系。他在对旅游业的研究中,以旅游者的身份,结合自己对土著民族长期的田野调查,提出了民族志旅游。即旅游者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深入村寨部落,调查研究他们的社会与文化,发现他们的社会文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的巨大变迁,格雷本为《无包装文化》一书所写的序言,《民族旅游艺术品的再思考》等论文中,深刻分析了现代旅游给东道国与接待地区的艺术品发展带来的变化、转型及新的整合。他的另一篇论文《亚洲及大洋洲地区旅游与文化发展》,深刻地阐述了现代化与地方文化产生的碰撞、涵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文化转型;阐明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产生以及保持地方文化的重要性。此外,格雷本在其他的论著和论文如《旅游人类学》、《旅游:神圣的旅程》、《旅游,现代化和怀旧》、《旅游、休闲以及博物馆》等论文当中,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人类从事旅游业的目的、动机、行为,以及旅游业与现代化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其论点十分深刻、精辟。
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另一先驱是史密斯(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其代表作便是前文所提到的《旅游者与东道主:旅游人类学研究》,事实上这本书已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者的必读书本。该著作论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现代化与旅游业在文化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具体内容分为四大部分:(1)旅游本质的定义;(2)旅游业所产生的影响;(3)旅游业在不同社会中的发展;(4)从理论角度对旅游业进行研究。史密斯所编著的另外一些论文如《旅游:神圣的旅程》、《旅游业:一种帝国形式》、《从人类学角度谈旅游商品化》、《朝着理论的方向研究旅游业:巴利的经济又重性及文化的进化》等,成为旅游人类学的经典文章。
另外一位同样值得我们敬重的旅游人类学家,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系教授马康柰,他编撰了不少有关旅游人类学的文章和著作,其代表作为《旅游者:休闲阶层的新理论》。该书分析了作为中产阶级的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旅游目的和行为,即他们去旅游,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一种文化经历,而在这种寻求过程当中碰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关于传统文化的真实性问题。东道地区为吸引旅游者而设计了“舞台真实”,即设计所谓的旅游文化产品,以此来迎合各国游客,这对传统文化是破坏呢?还是保护?马康柰从社会、文化、经济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浓厚兴趣和注意。该书体现了这样一种主题思想,不同的旅游者对文化的真实性存在不同的要求;因此“舞台真实”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引起了许多后来研究者的争论。马康柰对“舞台真实”的深刻批判有着独创的理论和观点。
马格丽特·丝旺:(Margair B·S wain)美国人类学家,专门从事旅游业与旅游艺术品,旅游与性别的关系等研究。她曾长期在中国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重点研究游工艺品及人们性别在旅游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如论文《民族旅游在中国云南石林彝族地区的发展》,《民族艺术品开发中的女性角色》、《国家主义:石林的旅游和少数民族政策》等,这些论文涉及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与保护;当地居民的态度及价值认同;女性在旅游商品生产中的角色;国家主义对民族政策的影响及国家力量与民族文化间的冲突等。
与格雷本、史密斯以及丝旺相比,纳什(Nash1996)则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更加客观地审视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领域。他在其代表作《旅游人类学》一书中,从旅游作为发展和文化趋同,旅游作为个人转型以及旅游作为上层建筑的形式等三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旅游现象作出理论解释,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纳什结合田野研究事例,分析和阐述了“商品化”、“模仿效应”、“内在化和社会化”、“社会矛盾与冲突”、“文化调适”、“文化瓦解与文化重建”等等社会文化现象在世界旅游发展中的表现。
在东方旅游学术界,对旅游人类学研究造诣较深的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山下晋司教授。1996年和1998年,山下晋司教授分别出版了《观光人类学》和《巴厘岛:文化人类学的教训》等两本重要的人类学著作。《观光人类学》一书从旅游的产生、旅游的构成、旅游民族志以及旅游文化等四个方面分析旅游的本质和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巴厘岛:文化人类学的教训》一书,则是对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旅游发展的田野研究成果。该书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与观点,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旅游与巴厘岛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
在中国,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引进与介绍得益于已故的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王筑生教授,王筑生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不仅发表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论文,他还是首先提议在中国——昆明召开关于旅游人类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人,也因为有了王筑生教授生前的这一提议,1999年9月在云南大学召开了由云南大学人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联合举办,美国伊利诺大学人类学系协办的“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看似平常的学术会议,在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不平常的足迹。这是因为此次会议在中国旅游人类学界所起到的不容忽视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之后,由云南大学人类系的杨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志明教授等把会议高质量的论文编著成了一部名为《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的论文集,并在翌年正式出版。事实上,这本书是开启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先河之作。
此后,中央民族大学的宗晓莲教授对西方的旅游人类学理论成功引介到中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宗晓莲于2001年发表在《民族研究》第3期的《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一文,无疑成为了当时中国寂静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一声春雷。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是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理论进行简单的罗列与推演,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多向度全方位立体式地向我们展开了一幅西方旅游人类学理论研究的路径图,文章把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分门别类,将其中的理论交叉系统以及相互的关联与差异梳理得非常清晰。文章认为西方旅游人类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旅游。第一,从旅游目的地社会出发来研究旅游,即研究旅游业给东道国或旅游接待地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从这一角度研究旅游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史密斯(V.Smith)、格林伍德(Greenwood)、奥格尔索普(Oglethrope)等。他们认为从旅游目的地社会民众的影响的角度出发,旅游实际上是一种涵化和发展形式,它使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发生变化。第二,从旅游者角度来研究旅游,即从旅游者这一视角出发,研究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旅游体验,并分析旅游对旅游者的影响。因此,这些学者主要探究的是旅游文化和符号内涵。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格雷本(Nelson Graburn)和丹尼逊·纳什(Dennison Nash)然而二者在其学术角度上又不尽相同。前者热衷于探索旅游的本质,分析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如在其代表作《旅游:神圣的旅程》中,格氏从历史上的旅游行为分析到今天的旅游活动,从旅游对人们的行为表现分析到旅游对个人的心理意义,认为旅游活动与日常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旅游对人们的精神状态达到一种神圣的“高点”,由此,格氏断定旅游是一种有着丰富的符号内涵的人类活动,旅游活动是一种仪式行为。
与格氏的理论观点针尖麦芒的是纳什,他在题为《作为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的旅游》的文章中指出,“以前的帝国主义以‘强迫,强加’为主要特点,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人们已经‘自愿’甚至‘积极’地接受外来影响,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旅游接待地人们把发展旅游当作一种获取经济济利益的方法,故尔,他们按照游客的好恶来进行开发”,纳什进一步指出以这种“旅游服务”来满足游客们的需要的客观存在,实际上是一种非公平的现实,因此,纳什认为当今的旅游必定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第三,从客源地角度来研究旅游,即从这一角度出发,西方旅游人类学家研究的是旅游产生的原因,也就是产生旅游和旅游者的条件(研究原因在任何学科中都是被当作主要研究任务的)。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Sahlins)、马康柰(Maclanell)、科恩和吉登斯。
萨氏认为旅游是“与经济动态适应的上层建筑”。萨氏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思维方法去研究社会活动的习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分析方法较为接近。然而,萨林斯这一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在现代语境下我们既要关注和分析社会的物质基础,更要注意多种社会文化的因素和条件。比如客源地的文化基础及人文资源等。
马康柰认为现代商业社会固有的残酷,使得现代中产阶级满世界地到处寻觅现代物质条件的家中不能得到的“真实”,需要到宁静安详的乡村社会去寄放精神,去返归真。以此出发,马氏认为现代旅游产生的真正动因在于现代社会的压力。然而马氏理论同样存在着致命弱点,即忽略了现代人对于异质文化的向往,以及旅游者自身文化资本等因素。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旅游人类学是一门晚近的学科,旅游人类学在我国的引进更是迟来的学问。除宗晓莲博士将这门学科理论向中国学术界进行成功的推介外,云南大学商旅学院的张晓萍教授无疑是这门迟疑学问的极其重要的引介者。张晓萍在美国师从格雷本等旅游人类学一代宗师,回国即刻将老师的名作《旅游:神圣的旅程》译成了中文,同时还翻译收集有这篇文章的在旅游人类学发展道路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史密斯主编的《东道主与旅游者——旅游人类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氏不啻是一个西方旅游人类学单纯的传声筒,她在其后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旅游人类学的论文:如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旅游人类学在美国》、《用人类学眼光看旅游》、《旅游是一种现代朝圣“诌议”》、《旅游业与“舞台真实”——一种西方旅游人类学的观点》等,更值得我们惊喜的是张氏与杨慧教授共同于2005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这部集数十篇有关旅游人类学论文的著作,可以说是张晓萍教授十几年对旅游人类学的东渐孜孜以求的明证。
为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提出理论纲领的人物应该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彭兆荣教授,彭凭借着对文化人类学的高深造诣,凭借着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与格雷本教授近距离的接触,彭氏在回国不久便出版了中国式的《旅游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这部著作的内容基本涵盖了旅游人类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内容,同时,提出了现代语境下旅游人类学需要研究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这部著作应该是集编译、介绍、译述和作者独立见解为一体的《旅游人类学》。由于在此以前,中国还没有一部由中国学者独立撰写的旅游人类学的专著问世,于是这部著作理所当然地成为旅游人类学十几年西学东渐富含学术和实践指导意义的成果。
如果我们把旅游人类学近半个世纪的演进过程作一个小结的话,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是从研究旅游活动的经济现象开始的,而以研究旅游的文化内涵是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发端,并延续至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二战前的数十年是把旅游活动作为经济现象研究的时期,即是现代旅游刚刚起步的时期。而二战以后则是文化内涵逐渐成为研究中心的时期。作为以文化视野关注旅游人类学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是在旅游经济现象研究的发展势头上,把旅游作为经济现象来研究都远远逊于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的研究。如我们从旅游活动的形态结构上考察,就可以发现,经济现象仅仅只是旅游的一个外壳,而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关系才是其内涵本质。前者只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而后者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与许多方面发生错综复杂的联系。所以,在旅游活动的研究中,人类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现象学、行为学已日益成为国外旅游研究中的主导学科,而人类学,尤其是旅游人类学的重要性正在逐渐超越经济性,成为旅游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段里,旅游人类学经历了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播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中国也经历从西学到东移,并不断拓展学科自身研究空间的过程,但笔者还是非常赞同旅游人类学的先行者纳什所指出的那样:“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理论还须深化,方法还须提高。虽然已经形成一些较为完整的理论,如商品化理论、依附理论、官僚主义化理论等,但他们只是一些中期理论,有一定的适应范围,但应该作进一步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