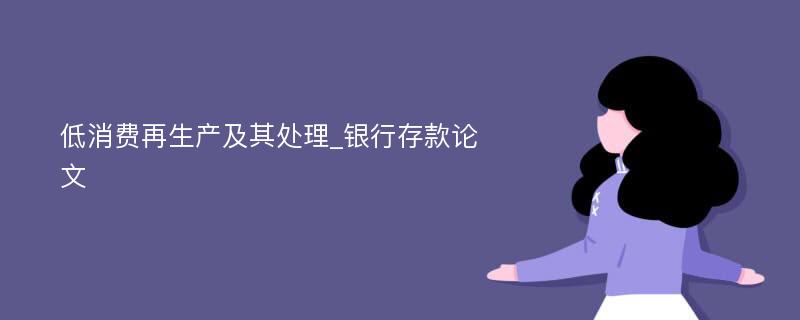
低消费再现及其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当前出现的低消费问题,很值得关注。
二十多年前,改革开放伊始,经济界异口同声批判和声讨低消费、高积累问题。当时的所谓高积累,其二十年(1958-1978年)平均积累率也不过33%左右,相应的低消费率在67%左右。最后得出的几乎一致的结论认为,适度的或科学合理的积累率为25%左右,而消费率为75%左右。
二十年后的今天,对上述的认识应做出如何评价?是真理佐见,还是谬种误传!且看事实。从1978年至2001年的24年间,平均最终消费率为62.3%,资本形成率为37.0%。这同1958-1978年二十年期间的高积累、低消费相比,难道不是出现了更高积累、更低消费的问题吗?具体情况请见下表。
最终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
年份 1978 1979 1980 “六五”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消费率
62.1 64.3 65.4
66.1
67.5 66.3
66.2
65.5 65.7
资本率 38.2 36.2 34.9
34.5
32.3 32.1
33.0
34.7 38.5
年份
“七五”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八五” 1991 1992
消费率 63.4 64.6 63.2
63.7
64.1 62.0
58.7
61.8 61.7
资本率 36.7 38.0 36.7
37.4
37.0 35.2
40.3
35.3 37.3
年份 1993 1994 1995 “九五”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消费率 58.5 57.4 57.5
59.5
58.5 58.2
58.7
60.1 61.3
资本率 43.5 41.3 40.8
37.5
39.3 38.0
37.4
37.1 36.2
年份
“十五” 2001
消费率
60.6
资本率
37.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2年)。
上表的资料说明了什么?说明消费是适度、还是膨胀,或不足?是低消费,还是高消费?毫无疑问,肯定是低消费或消费不足。原因很简单,从1978年的低消费率62.1%经过曲折过程降至2001年的更低消费率60.6%。当然,这是相对于生产发展速度、积累率、资本形成率而言的相对水平,不是绝对水平。就绝对数表示的消费水平而论,二十多年提高很多。这个时期是历史上中国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时期。在做出这个肯定之后,又不能怀疑如下的假定。如果消费与投资(积累)的关系更协调一些,消费尤其是农民的消费就可以增长更快一些,生活改善更多一些。
判断消费是否适度最好参照一些发展水平大体相同国家的情况,或者说,找一个国际参照系。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之初做得较好。近来,也有人注意了国际比较。有的文章写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年中,世界平均的最终消费率为78%-79%。其中美国1997年为86.6%,英国都在80%以上,印度、巴西为80%。由此可见,中国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了近20个百分点。用剔除掉政府消费后的居民消费数据,更加能够反映消费需求的实际情况。1997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为47.5%,同期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为68%,就连被世界公认的国内消费严重不足的日本,这一数据也达到59.8%”。(注:参见《上海商业》2002年第9期第7页。)这样的对比目前实在太少了,故引出供参考。我国同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可比性较小。最好找一些发展中的大国进行对比。
根据目前国家统计局的规定,在我国的“最终消费”中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两部分。这二者的比例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里呈现出极其明显的差别。以2000年政府消费所占比重(政府消费率)来看,前五名分别是新疆(34.9%)、北京(33.8%)、宁夏(32.6%)、天津(30.7%)和青海(30.2%);后五名分别是安徽(17.1%)、四川(18.4%)、湖北(20.8%)、上海(21.9%)和江西(22.1%),高低相差一倍以上。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很值得研究。如果说边远的新疆、青海、宁夏等地广人稀、交通费用庞大,可以理解;那么北京与上海同为大城市,为什么也相差达十几个百分点呢?是否在某些省市自治区也存在政府的高消费,而居民的低消费呢?
在居民消费中,又划分为农村居民消费与城镇居民消费。随着城市化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必然呈下降趋势,而城镇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必然出现上升趋势。2000年比1978年,农村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由62.1%下降到45.2%,而城镇居民消费的比重则由37.9%上升到54.8%。如上所述,这种升降有其合理的成份。但是,其中也隐藏着农民消费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严重问题。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8年和1999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仅比上年分别增长19元和32元,或者说增长1%和1.7%。而有的文章指出,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分别下降26.8元和12.9元,或者说分别下降1.7%和0.8%(注:参见《现代经济探讨》2002年第5期第9页。)。不管是微升,还是下降,相对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相对于畸高的资本形成率,不能不承认,这是低消费的再现。
二
低消费为什么再现?主要原因有:
(一)重生产、轻生活。在生产建设上,近十年来,超大型工程接连上马。像三峡工程、京九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三北防护林、青藏铁路、核电站以及遍布全国的高速公路网等等,哪一项不耗费巨资。这些举措从根本上从长远上看,肯定有利于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但从目前说,它们将占用巨额资金,且短期内又难以收回。因此,在资金一定的前提下,改善生活的钱就显得不足了,许多县乡发不出去工资,医疗费无着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一定比例。上述的许多有益于子孙后代的大工程,不是不应搞,而是上马太集中,国力一时难以支撑,在一定程度上挤了生活。在生活与生产关系上,我们既不主张先生产、后生活,也不同意先生活、后生产,而必须将二者同时并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使生产发展与生活改善协调起来。
(二)重城市、轻农村。我国目前并没有出现一些国家的“城市繁荣、农村偏枯”的问题。但是,城镇发展快,而农业和农村发展慢,则是值得注意的。一定要防止出现城市繁荣、农村偏枯问题。近几年,县乡小型企业不太景气,农民从这些企业取得的收入相对减少。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经济作物、水果、蔬菜、水产品等增加很多,但供过于求,价格相对下降,农民获得的效益并不理想。农民外出到城市打工,又受到种种限制和歧视,收入增长不多。再加之屡禁不止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以及农民教育、医疗等支出增加,使得农民收入与支出的关系似有愈加不协调之现象。在改善生活问题上,不能仅限于城市职工和城市人口,而必须同时关注农民问题。农民改善生活更难。为使城乡消费关系协调,必须实行城乡并举,使二者的增长速度大体同步,甚至农民消费增长速度稍高一点,以便将来消除城乡差别,达到全国城乡共同富裕目标。
(三)重外需、轻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一靠内需,二靠外需。所谓外需者,是指国家的净出口,即满足国外的需求。我国的外贸出口额由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2661.6亿美元,增长达26.3倍。真可谓高速度!即使在1997-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在这三年的净出口(出口-进口)也分别达到404.2、434.7、292.3亿美元。这三年的净出口折合人民币计算达9300亿元以上。由此可见,外需对我国经济推动的作用多么巨大。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但是,启动内需的政策则是1998年作为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措施而出台的,似乎有点晚矣!如上所述,在启动内需上,也是把更多的资金和项目用在生产建设,尤其是大型工程上,而对亿万居民消费需求启动不够有力。居民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这是拉动经济前进的三驾马车。其中最重要最根本者是居民消费需求。这个需求启动不力,是低消费再现的根本原因。
(四)重收入、轻消费。以往经常有人将收入当成消费,认为收入增长很快,就是消费提高很多,收入膨胀就是消费膨胀,因而在报刊上连续几年痛斥所谓“消费膨胀”。其实,在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间,始终不存在消费膨胀问题。(注:参见本人拙文:《“消费膨胀论”质疑》,《财贸经济》1989年第11期。)当然,有时有地区有行业存在收入增长过快的问题。收入=消费+储蓄。如果收入=消费,那么储蓄必然等于零。在我国,储蓄不仅不为零,反而以极高的速度增加。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由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73762.4亿元,增长349倍。这样高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储蓄不是现实消费,能否转换成未来消费尚需一定条件。条件不具备,它将永远是积累,而不是消费。储蓄在当前就是积累,转换成投资,用于生产建设上。近二十年的高储蓄是形成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的重要机理。这同世界上著名的高投资、低消费国(日本)有类似之处。在储蓄问题上,早有人研究如何将储蓄转化成投资,可惜至今未见如何将储蓄转化成消费的研究论著。如果一味鼓励储蓄而不研究如何将它转化成消费,其结果必然是低消费的一现再现而已。对于收入也应当这样说。如果仅仅满足于收入增加,而不研究如何将收入转化成消费,也可能出现高收入、低消费的局面。不能仅重视收入、储蓄,而轻视消费,必须把三者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使它们协调发展。
(五)重预期、轻现实。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尤其是消费体制改革的大力推进,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消费逐渐由供给型向自理型转化,这就迫使人们既要安排好当前的生活消费,更要谋划和筹备未来一生的生活消费。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加强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因此,存钱防老、存钱防病、存钱买房以及供子女升学等等大量增加。这就必然促使储蓄迅速增加。即使利息一降再降,储蓄增势仍然不减。这说明消费预期多么强劲。宁肯眼前的生活差一点,甚至受点苦,也要为子女未来的升学、前途安排好,也要使自己老年生活有个着落。这既是储蓄猛增的动因,又是目前低消费再现的动因。
(六)重共性、轻差别。在由温饱向小康转变的过程中,居民生活也由雷同型向多样型转化。过去,大家的收入、生活都差不多,可谓雷同也!如今,差别扩大了,生活多样化了。主要差别有三种,一是城乡差别,二是地区差别,三是社会阶层的高低差别。目前,广大的乡村、贫困地区以及贫困的社会阶层收入太低,刚刚解决了温饱,甚至温饱尚未完全解决,对于更高的消费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反之,高收入者,富裕者,即使有了大量收入,因其各项生活都已满足,也无需再把更多的钱用于目前的生活消费。真是,想消费者无收入,有收入者不愿消费。故低消费必然矣!
三
既然找出了低消费形成的种种原因,也就容易对症下药进行治理了。根本的措施或药方当然是解决上述的“六重”与“六轻”,正确处理生产建设与生活消费的关系、农村居民消费与城镇居民消费的关系、外需与内需的关系、收入与消费的关系、预期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共性与差别的关系。除此之外,当前似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民消费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消费领域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针对农民收入低、负担重的问题,既要多方增加农民收入,又要大力减轻农民负担。在增加收入方面,继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创汇农业、特色农业;大力扶植县乡企业尤其是服务类企业,使之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大力组织和培训农村智能型劳动力,使之成为农村致富的带头人;积极推动小额扶贫贷款,帮助贫困户创业脱贫;组织好外出打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减轻负担方面,除了坚决刹住“三乱”之外,实行农用工业生产资料的退税制,即在购置时交税、年终凭发票向农民退还其中包含的各种税款,或者说,实行农用工业生产资料的零税制,以减轻农民的税负;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免减费制度,尤其在边远贫困地区一律实行免费教育,其教育经费的不足部分由县省中央三级财政分担,以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在中西部地区,减免农业税,可否先试行二三年,然后再决定是否推广;大力精简县乡村的机构,减少“官”,减少行政经费。
(二)切实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困难问题。除了确保退休金按时发放和坚持最低生活保障线之外,在住房方面,实行低价廉租房。在城镇不同地区由政府出资盖一批供贫困生活家庭使用的住房。据德国的经验,这种房子要分散建造,不宜太集中,以免形成“贫民区”,最好与其他住房搭配组合,共同组成某个社区。在子女受教育方面,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减免费制度,高等教育阶段实行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办法。在饮食方面,可实行低价食品券,在指定的商店中购买便宜的食品,而政府则给予这类商品一定补助。总之,在城镇居民消费方面,应实行“上不封顶,下要保底”的政策。对于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的生活一定要切实解决,绝对不能出现“街头居民”,更不能形成“贫民区”或“赤贫群”。要不断进行反贫困斗争!
(三)加大区域间转移支付的力度,遏制地区差别扩大的势头。解决地区间收入、消费方面的差距,固然要从发展后进地区经济入手,但从宏观上通过国家财政政策进行适当的转移支付,先富帮后富,也不失为重要手段。在转移支付过程中,一定要提高效益,把资金用在刀刃上,坚决防止“跑冒滴漏”。
(四)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如,扩大就业人数的投资,按比例抵扣所得税;向贫困地区的投资,按比例减免税收;银行存款的利息税专门用于扶贫解困,不准移作他用等等。在调节分配关系方面,税收杠杆确有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