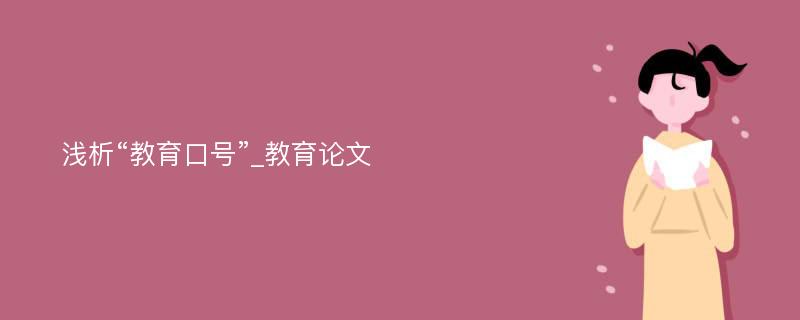
“教育口号”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口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口号”是教育语言的基本形式之一,在教育活动中颇为常见。以往我们总有意无意地认为,“教育口号”只是一种“政府的行为”,与教育实践者个人关系不大,更与教育理论研究无涉,不必将其单独提取出来加以甄别、考究。其实不然,“教育口号”作为描述教育现象的语言形式,以其独有的方式影响着参与教育活动的每一个人,影响着教育理论的建构。
一
按照英国分析教育哲学家谢弗勒(Scheffler,I)的分析, 教育语言主要由三种形式构成:教育术语、教育口号、教育隐喻。教育术语应有着较为清晰的涵义和明确的规定;而教育口号一般是非系统化的,在表述方式上也不严谨;由于它通俗易懂,常被人们不加思索地加以接受和传诵;与术语、口号相比,隐喻并不用标准或规定的方式来表述词语的意义,只是借助于对比、类似和相近来论述问题,它与口号一样,也没有标准的陈述形式,缺乏系统(注:Scheffter ,I.,The LanguageorEducation,1963,p.36.)。
但我们似乎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对教育语言这三种形式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说区别。
教育术语主要以概念、范畴形式出现,是人们对教育现象的概括性反映,它是人们理性思维的产物,通过将感性认识不断进行加工、提炼而成。教育口号虽然可能会以人们的理性分析、判断为基础,但毕竟是以一种情绪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激起的是人们的情绪化反应(当然并不仅限于此)。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教育口号是“主情”的,而教育术语是“主知”的。前者唤起的是人们的情感、情绪的相应反应;后者建立在理性分析之上,给人的是教育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一般性认识。大概也正因如此,教育术语采用一种“冷冰冰”的形式,不轻易随时势而更迭,依社会条件而变迁;而教育口号则采用一种“活跃”的姿态,因时而动,因势而更。在“动”与“静”这架天平上,教育隐喻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它来源于感性认识,而又尚未脱离感性的樊篱;它试图借助理性达到抽象概括的水平,而又苦于没有适当的语词来表达。处此情形,它总是暂且就范于其他学科或其他事物的旗帜之下,藉着它们所提供的语词来表达自己所包括的含义。
三者还有一个区别需要提及,那就是它们所属的群体不同。“教育口号”这种语言形式,多属于教育实践工作者,那些在教育实践中影响较大、传播较广的教育口号,一般地是属于某一政党、政府或在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的个人。而“教育术语”,是属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他们凭藉概念、范畴阐述问题,表述的是一般的、抽象的知识。“教育隐喻”,多属于教育理论—实践工作者,他们既熟知实际,又多少了解些理论,常通过类比来说明问题。当然,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就一般情形而言的,为了丰富自己的语言表达形式,不同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着这些语言。认识到这点至关重要,它提示我们,不同的群体话语形式不同,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亦成问题,一不留神,三个群体之间的对话就成了“鸡同鸭讲”。如此,若教育理论工作者将“素质教育”的口号,作理论的阐释,将其转化为教育上的种种术语,是不当的;同样,一些人将“素质教育”诉诸理性,斥之为学理上“荒谬”、“伪劣”,也是可笑的。如此,“第二课堂”的隐喻有其存在价值,只是这种隐喻不必一定要提升为教育术语,教育理论工作者也不必将其当作术语来看待。
其次谈联系。联系之一在于三者间的相互依存上。无论是教育口号的“主情”,还是教育术语的“主知”,抑或是教育隐喻的“情、知杂合”,反映的都是人类对教育的不同程度、方面、形式的认识。它们是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的,三者共同结成了教育语言的整体。口号中有时会包含有隐喻的形式,如“全社会行动起来,努力打好‘普九’战役”,此处的战役即是一种“隐喻”。同时,口号中也会将教育术语中阐述的一些理性的认识外显出来,唤起人们的关注,如“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实际上就是将“教育先行”的观念用口号性语言表达出来了。
联系之二在于三者间的相互转化上。术语、口号、隐喻不是各安本位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就拿教育隐喻来说,隐喻的长期运用,因没有更为严谨、精当的词语来代替它,久而久之就有可能演化成为约定俗成的术语。“上层建筑”这个词语,最初并不是一个表示社会结构的学术概念,不能精确地概括与经济基础相对的生产关系,但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学说的确立,它逐渐摆脱初始的隐喻形态,而成为哲学、经济学等学科中的重要术语。
二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只要教育在国家政治经济的制约之下,只要教育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只要人们还关注教育,就会有教育口号的市场。
“教育口号”的特点至少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简约性
任何教育口号,几乎都使用的是简单明了的语句。它将一些复杂的有着丰富含义的问题,用短小精悍的词语表达出来,真正是言简意赅。就拿希望工程的代表性口号“为了托起明天的太阳”来说,其寓意是深刻的,背后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样的。它包容了众多的信息与含义在内:儿童是明天的太阳,我们的世界靠他们来创造,我们的事业要靠他们来继承;然而,在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孩子由于贫困却不能入学,不能接受基本的教育。为了孩子,为了明天,为了人类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伸出你的援助之手。
(二)情绪化
口号并不排斥概念、术语的认知意义,但更重视的是概念的情绪意义,亦即强调其情绪感染力。为了能打动人、鼓舞人,引起人心理上的共鸣,口号有时会夸大其辞,使人不由自主地受到情绪上的感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超越了教育术语的咬文嚼字的论述,而倾向于实际赞成或对抗的行动。就此,谢弗勒说,教育口号是为教育运动的主要观念和态度提供鼓励性的符号(注:Scheffter,I.,The Language orEducation,1963,p.36.)。同理,作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您不会对“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无动于衷。
教育口号将教育术语的含义情绪化、表面化了,它不重视词语含义的清晰程度,高喊教育口号的人,一般是“拿来主义者”,是“实用主义者”,只要词语能为我所用,就可以拿来用上。如“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此处除“教书育人”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外,其他两者更属于自然影响,而非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也就是说,这些根本就不是教育。所以,要想给教育口号加以明确的界定,几乎是徒劳的。口号无助于教育术语的厘定,“若批评一个口号的表达形式不够恰当,或者用词不够精确,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注:Scheffter,I.,The Language or Education,1963,p.36.)。
也正是由于教育口号的这种情绪色彩,有时也会使得它走向极端,在表述上趋于极端化。它不肩负有严格规定术语的职责,是以影响人的情意心理为己任的,因而,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问题的陈述推向极端。
(三)导向性
教育口号表述的意思,一般都有着明确的指向性,它规定的是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将教育发展的未来前景用口号的形式外化出来。从这点来说,教育口号有时颇具理想化的色彩,不一定着眼于现时现地,如“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表述的就是我国教育的性质与发展的远景。这样的口号常是由政党、政府提出的,与教育目的等密切相关。
(四)明显的价值倾向性
对教育口号来说,重要的不是客观描述,而是如何将一定的价值倾向借助于适当的语言表述出来。似乎我们还没有看到只有事实描述而不含价值倾向的“口号”。这样的语言即使有的话,与其称之为“口号”,倒不如称之为“术语”。
对于教育口号的作用,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在教育理论发展中的作用。教育口号的语言形式,虽然与教育理论的陈述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它对于某一教育理论问题的“通俗化”,将教育理论由学府的殿堂深入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与行动,不无助益。诚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教育理论揭示的是教育的一般现象,使用的是脱离了经验形式的抽象化、概括化了的语言。正因如此,理论常显得高深莫测,教育实践者常对其敬而远之。而教育口号则可能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经过传媒的“狂轰滥炸”,很快为人们所熟知。它虽然有使理论简单化的危险,但却在理论与实践间铺设起了一座桥梁。比如“教育要先行”这短短的五个字,实际上反映出的是教育理论研究者对教育本质、功能的认识,是教育理论界沸沸扬扬争论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取得的一些共识。这个口号背后,隐藏的是教育本质论争中“教育是生产力”的本质观,教育功能讨论中“经济决定论”的功能观。
二是在教育实践中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唤起人们对一些教育活动或方面的关注。对于人们关注较少、认识不定的事物,通过教育口号来提升它的重要性,可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电子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句口号一下子使得全国上下都来关心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电子计算机的教育问题,开始注意让学生掌握电子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环境保护,教育为本”,则使教育界意识到自己的担子又至少加重了许多。其二,对实际开展教育活动具有强烈的鼓舞、推动作用。那些带有导向性的教育口号,对教育实践干预甚大,它促使人们作出抉择,摒弃其他的一些杂念,向着某一特定的方向迈进。“五四”时期的“打碎孔家店”,就为教育上倡导废除封建礼教、引进新思想大开方便之门;“文革”时期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造反有理”等,就使得红卫兵小将们豪情冲天,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似乎更注意教育口号,人们也多少有些信奉教育口号,这与建国后政治运动不断不无关联。可以说,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有着一些激动人心的口号作“先锋”,它导引着运动的方向,制约着人们的行动。实践工作者一般并不会去认真地阅读、领会某一政府文件,哪怕是至关重要的文件,而是大多借助于口号性语言对政策、法规、文件等有所了解。大多数教师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可能知之不多,但大都知道“教育要为提高全民族素质而努力”这一口号;大多数教师可能不太明了《义务教育法》的具体条款,但大都知道“要积极、稳妥、扎实地开展‘普九’工作”这一口号。鉴于此,善用教育口号在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
在教育活动中,教育口号是多种多样的,几乎涉及教育的每一方面。这些口号,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分类。例如,从其来源上,可分为政府的教育口号、社区的教育口号、社会团体的教育口号、学校的口号乃至个人的口号;从其指向上,可分为教育理论的口号与教育实践的口号;从其涉及范围上,可分为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口号,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文化组织教育、职业组织教育的口号,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的口号,如此等等。在这里,我们暂且撇开上述分类,仅从教育口号的语言表现形式上对各类别加以分析。
从语词结构上来讲,教育口号可划分为两个大的类别:一是短语式,一是语句式。其中语句式教育口号,还可具体分为带有陈述某种教育事实色彩的陈述句式的教育口号,带有更为明显的价值倾向性的表情句式和表意句式的教育口号。
短语式教育口号,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语句,而是将一些关键性的词语汇合成一个短语。这种教育口号简洁、缩略,较为引人注目,“教育学中国化”、“素质教育”、“教育先行”,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也正因为短语式教育口号形式上不完整,使得它所反映的含义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甚至人们往往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这样的口号容易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但有时由于其含义的不确定性等,难以在教育实践中得到落实。
语句式陈述句式的教育口号,一般并不常见,因为口号若采用句式,较多地是以感叹句、祈使句等形式来表现的。陈述句式的教育口号,看上去像是陈述一个事实或说明一个道理,如“教育一代人,影响三代人”,说的就是通过对一代人进行教育,可使得这代人的知识、态度、行动、价值等影响到与他们共同生活的另外两代人。这种教育口号用语平和,给人的感觉是在谆谆说理,引发的人的情绪反应相对较小。对于那些善于理性思维、感情不易冲动的人来说,这类口号更易于接受。
语句式教育口号中的表情式,与陈述句式不同,它用语中的情绪色彩甚为明显,这种句式无论是采用感叹句,还是祈使句,总是把“情”放在首位,是以情动人,以情感人的。“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就是这类教育口号中的一个典型。表意式教育口号,同样富含价值倾向,但表述方式与表情式教育口号不同,它以“一定要”、“坚决要”之类的形式来表达对教育某一方面或问题的信心和决心。“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让经历“文革”的人们记忆犹新的口号,以及“坚持执行某某方针、政策”之类,都属此类。
教育口号的存在是正常的,它与一个国家的体制、社会发展的要求等密切相联。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可怕的不是存在教育口号,而是教育口号的滥用、混用、错用。认清教育口号的性质,对于我们把握它在教育语言中的位置、作用等都不无助益。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标签:教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