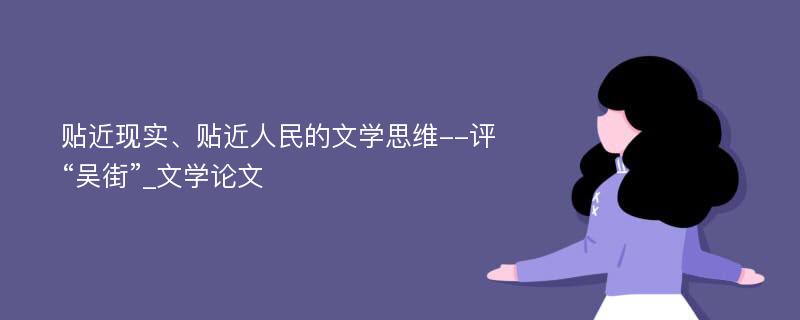
贴近现实贴近百姓的文学思维——漫评《五爱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现实论文,百姓论文,文学论文,五爱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木青写下两句话,作为长篇小说《五爱街》的题记:“办一方市场,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集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摇篮。”请注意,这完全不是文学语言,不是小说语言,没有文学味道、小说味道,它是纯粹的司政者话语、经济学话语。它又不是泛泛的司政者话语,而是和我们党兴国富民的基本方略相关,凝铸着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人民办实事的公仆精神的话语;它又不是泛泛的经济学话语,而是深涵着我国当代社会转型和历史变动主流的话语。作者不但把它作为小说的题记,而且在小说实际描写中体现为全部生活故事与人物故事的题旨。这说明,作者的文学思考与当前的世相社情、与当政者和老百姓心之所想、行之所趋,是融为一体的。或许有些主张玄而又玄的“文学本体论”者,会以为这是“非文学思考”,然而,剥离了文学与现实生活、与庶民百姓的血肉联系去别寻“文学本体”,那会是能活在生活中、活在民心里的文学么?
在《五爱街》中,作者以集贸市场个体户们为自己文学描写的对象主体,他是自觉地为他们竖牌立传的。个体户既是我国社会转型中新生成的经济人群,也是新生成的社会人群。由于种种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他们迅速崛起,膨胀,人数极多,社会辐射面极广,他们自身的社会成分和素质也极其庞杂。他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对社会经济生活、对全社会的日常生活,有巨大的影响,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一般人对他们的社会评价不高。这是由他们中许多人的经营活动违背市场经济应有的规范,个人品质良莠不齐——或许是莠多于良造成的。当然,也有我国市场经济发育并未成熟的客观原因,也有人们市场经济意识尚未发育成熟所产生所形成的社会成见。作家木青不是把市场个体户引入文学、使之成为文学主人公的第一人,在他写沈阳五爱街个体户之前,早已有写武汉汉正街个体户以及其他许多以市场个体户为主角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了。但可以说木青是把这一创作潮流有力地推向前进的最近一位作家。木青写个体户有自己的视域和视点,他有自己的明确的社会经济眼光、社会历史眼光、社会人性眼光。他把个体户看成支持社会发展的一种纳税人阶层,认为应当“鼓励更多的人成为纳税者”,认为“纳税者是社会的真正主人,真正脊梁”。他看到最早把握改革开放先机,投入市场经济的个体弄潮儿中,确有不少“不三不四的人”,他把他们与当年土改运动中以“土改先锋”面貌出身的“二八月庄稼人”相比,他认为正如只有正经庄稼人投入,土改才能胜利一样,当前这场经济革命,必须有更多的正经个体户投入。木青写《五爱街》,实际上是怀着一种社会经济理想和历史观的,他描写了五爱人从集贸经济的一个社区,一步步走向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他描写了随着市场经济从无序到逐渐有序,五爱人的思想面貌也在变化,获得改造,获得提高。这是作家木青对“经济与人”“市场与人”的思考。木青对他笔下的个体户,投注了充沛的热情,这是基于理性热情的感性热情。究其实,这种热情不仅是给予个体户的,也是给予当前这个历史时代、这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现实的。《五爱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在同类作品之后,有力地表明了文学对个体户这一社会经济、社会历史新成员的积极关注,更在于它表明了文学对发展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的积极参与。作家的这种文学思维,与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以回避责任和使命、消解崇高和激情为共同特征的诸色文学新品文学讨论,不可同日而语。
木青自言,他这个“眼镜先生”,为了写作《五爱街》,可谓吃尽苦头。不是别的苦头,而是生活底子薄的苦头。他从商业ABC学起,向书本学,更向“业户”学。很长时间,他天不亮就骑上自行车赶赴五爱街,去感受生活,去熟悉人物。辛苦不说,还曾被人怀疑、盯梢,甚至要加害。因为他要探悉业户们的商业机密,包括正当的与不正当的经营技巧商战技巧,因为他要探索业户们的心灵,包括商业心灵与社会心灵。为了能看到真相,听到真话,学到真经,他谢绝有关部门的协助,扮演着五爱生活圈中普通一员的角色。他又以真实的身份为业户们奔走呼号,不仅用作家的眼睛去观察,而且以业户的心思去体验,并且躬行实践亲身参与。他因此交了不少个体户朋友,进入了个体户的生活世界和内心世界,懂得了他们的真诚与狡诈、义气与争斗,创业的艰辛与生活的沉溺,欲望与理想,情爱与家庭,以及他们经商与做人的一切。他也和市、区党政干部、工商干部交了朋友,了解了他们创办、管理集贸市场的思路与日常操作,以及他们为民操劳也挨骂也受人爱戴的种种。熟悉木青的文学界友人说,木青是严肃对待生活的人,他不写自己不懂不熟悉的东西,他不赞成一味表现自我,而遵循“写生活”的原则。确实,木青深入五爱一年,才写出了《五爱街》,作品后记着重谈的就是体验生活的体会。这是自然的,贴近现实、贴近百姓的文学思维,不可能是作家住在宾馆里向壁虚构的思维,不可能是作家与小圈子中人啜酒品茗神聊海侃产生的思维。
坚持到生活中去,到基层中去,到人民大众中去,获取第一手素材,获取思想与灵感,是不是太陈旧的话题了?木青的回答是否定的。对于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遵循创作规律应当有多种方式,应当有自己的个性形式。木青在做人与作文上都并不保守也不古板。他写作《五爱街》就有对长篇小说样式的突破。《五爱街》是小说,但作者融进了纪实性和纪实成分,书中所写的五爱市场发展的基本过程、背景和大事件,都是与实际生活相符的。《五爱街》中还融进了报告性和报告文学成分,以及经济调查报告成分。《五爱街》还融进了论辩性和论文成分,作者每每在情节行进中,加入对发展集贸市场和个体户经济的论理见解。作品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它塑造的不是典型个体而是典型群体,它讲述的不是五爱街上几个人的故事而是五爱街上众多百姓的故事。这部小说的语言,也不都是文学语言,还有非文学语言。它的文学语言,无论人物语言、叙述语言,大众性、地方性、市井性都很突出,特别是作者掌握了一套个体户语言,包括行业语言与生活语言。从作品的结构到语言,作者不避俗但不媚俗,既不媚某些大众文学的低俗,也不媚某些新潮文学的“雅”俗。正如所谓雅文学之“雅”有端正与否的区别,所谓俗文学之“俗”也有端正与否的区别。正雅正俗的文学都可归入严肃文学,《五爱街》作者的创作思维,属于俗而端正端庄的文学思维。
《五爱街》的艺术表现,或许还有粗糙不圆满之处,但它所传达出来的时代主旋律,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贴近现实贴近百姓的文学思维,是一切关心生活前进、文学发展的人们,都应当为之思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