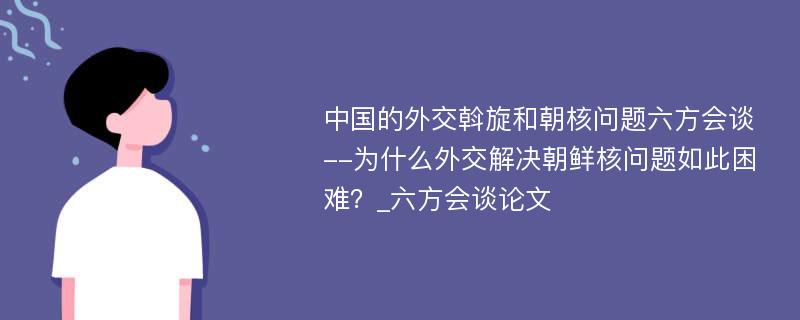
中国的外交斡旋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什么外交解决朝核问题这么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朝核问题论文,中国论文,六方会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6)02—0023—08
自2003年8月以来, 以“六方会谈”机制为基础的外交与政治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谈判已经进行了5轮,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突破。虽然2005年9月第四轮六方会谈发表了各方签署的《共同声明》,但声明并没有为谈判的持续深入带来决定性的转机。2005年11月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之后,新的一轮后继会议究竟什么时间恢复至今还很难确定。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了美国和朝鲜的观点依然对立、互不信任的坚冰依然难以融化之外,也与各方难以形成有效的共识来推进多边会谈进程以及彼此之间在朝鲜问题上隐含的战略性利益分歧无法缩小等诸多因素有关。其中,中国和美国对外交斡旋(mediation)的角色认知差异和由此引发“斡旋”努力的有限性,客观上是六方会谈难以打破僵局的又一重要因素。从国际斡旋的理论上和六方会谈的实践这两个层次分析和把握外交斡旋的意义和作用,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外交在朝核问题上的贡献和局限、并进而更好地澄清未来我们在六方会谈中的角色,是必要而又具有启示性的。
外交斡旋理论与六方会谈中的外交斡旋
外交斡旋、或者说对冲突的国际斡旋的本质是通过第三方的介入为冲突各方寻找到妥协的道路,从而管理冲突、并逐步发展出谈判解决冲突的办法[1](p.4)。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外交斡旋俯拾皆是,经常是国际关系与各国外交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冷战结束后,外交斡旋在国际冲突防止与解决进程中更是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因为在意识形态对峙全球退潮、军事冲突的灾难性后果严重以及安全利益的相关性发散的情况下,一方面外交斡旋赢得了各种比冷战时期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引进斡旋机制解决总是难以避免的冲突,符合全球化时代国家的根本利益。不管斡旋的结果如何,外交斡旋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冲突管理的过程,本身能为危机的解决奠定必要的基础①。
朝核问题的外交斡旋进程是一个复杂的冲突解决程序中的外交斡旋问题。它既不同于为了停止直接军事冲突、建立和平秩序而进行的以维和为目的的军事外交斡旋,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地区冲突进程中的第三方强行介入的政治外交斡旋。上述两种类型国际斡旋的重要基础是“斡旋者”的中立身份、单纯的和平动机、斡旋的方案设计和过程执行的能力建设②。在这两种斡旋过程中,斡旋者可以诉诸国际组织的强制力或者发挥全部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来形成“力量介入”的态势,并通过动用各种国际辅助力量来保证被斡旋者缺乏固执己见的资源。在这样的军事外交斡旋或者政治外交斡旋中,斡旋者的道德义务以及利益取向不受怀疑,斡旋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其斡旋的能力与决心。在这样的斡旋过程中,斡旋者的地位、受斡旋事态的性质常常决定斡旋的进程和斡旋的结果。
从国际斡旋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来看,朝核问题这样的外交斡旋过程是难度最大的、也是斡旋效果最不容易发挥的问题。因为朝核问题由来已久,不仅涉及时间长,而且包括了美朝之间长期的不信任以及依然严峻的意识形态对立。例如美国在冷战后长期将朝鲜视为“流氓国家”(rogue state),2002年2月布什总统的国情咨文又将朝鲜与伊拉克和伊朗并列,称为“邪恶轴心”(Axis of Evil)。1993—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时克林顿政府曾很认真地考虑过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框架协定》签署以来,双方的猜疑和争执从来没有停止过。朝鲜则长期指责美国对平壤实行敌视与扼杀政策,而美国则始终没有真正改变过朝鲜“欺骗”和“非法”方式进行核努力的怀疑③。布什政府上台后,更是在很长时间内中断了和朝鲜的直接对话。更严重的是,朝核问题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这不单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全球安全的首要关注,对朝鲜来说也是“高位政治”(High politics)中最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朝核问题无论从那方面来讲,都符合国际斡旋问题分类中“级别最高”、最难解决的问题④。
然而,最困难的斡旋问题和斡旋对象恰恰也是最需要、也是最值得进行斡旋的。外交斡旋的启动与进展首先取决于在什么时机介入斡旋和由谁来进行斡旋。从时间的选择上,危机开始连续出现新的对抗性事态、或者危机达到第一个“波峰”高度之后应该是斡旋介入的“最佳时机”(optimal time);而能对当事方同时具有影响力的第三方应该是介入斡旋的最好“人选”[2](pp.121—135)。传统的国际斡旋理论常常认为,斡旋国际冲突、即便不是直接的军事冲突也需要等到其自身爆发、难以收拾残局的时候,外交斡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冲突自身进程的有限性会遏止冲突当事方真正下定决心寻求妥协。而斡旋理论新的发展则认为,从斡旋介入的条件来看,最有可能、也是最应该出现外交斡旋的情景是冲突双方形成了全面僵局、危机性质严重而又无法由当事方自身寻找到直接对话途径的时候[3](pp.249—266)。
当然,对所需要斡旋的问题不仅事关性质是否严重,还涉及到该问题是否具有危机损害的多重效应。如果一个冲突问题可能失控而导致的麻烦种类越多,那么,外交斡旋的可能性越大,由此而带来的成功斡旋的难度也就越大。但相对应的是,此时外交斡旋介入的“理性程度”就越高[4](pp.563—570)。换句话说,斡旋越值得进行。对斡旋的这一相关变量关系的建立,也反映了冷战后国际斡旋的基本现状:即便是地区性的军事冲突,也只有大约35%涉及到国际斡旋。这说明国际斡旋是常见、但并不普及的事实。
在这个过程中,成功的外交斡旋还取决于“斡旋的类型”(mediation style),或者说,斡旋行为本身。一项良好的、有针对性的外交斡旋行为常常取决于三个要素:一是能够便于冲突双方直接沟通和协商;二是能够引导形成相关的解决问题的原则、并设定解决冲突方案的坚实基础;三是斡旋者能够主控会谈与磋商进程;即“便利”(facilitation)、“成型”(formulation)和“主控”(manipulation)[5](pp.58—87)。其中,斡旋者是否能主控冲突重要当时人之间的谈判进程,是斡旋效果最强有力的制约因素。
朝鲜核问题具有典型的危机损害的多重性。因为朝核问题如果持续核化,不但可能会激发朝鲜半岛出现新的军事冲突,危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能触发东亚地区新的核军备竞赛,从而大大恶化东亚的区域地缘战略环境,并因为“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作用而导致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发展的安全成本大大上升;甚至可能造成区域安全结构退化到冷战时期那样的新的地缘政治分裂。即便这样消极的安全后果不那么明显,但朝核危机一旦进入军事冲突、或者对抗升级的情景,朝鲜境内的经济状况将会持续紧张,即便难民危机也将给周边国家造成沉重的经济与社会压力。如果局势失控,核材料的走私等可能性甚至会造成核恐怖主义。这些后果都不堪设想。
外交斡旋在六方会谈机制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作用
中国积极对朝核问题进行外交斡旋,不仅在时机的掌握以及问题的选择上及时、果断,而且通过中国自身的地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对美国和朝鲜拥有外交影响力——为六方会谈机制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社会目前的共识是:六方会谈机制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好形式”。
2002年10月初新一轮朝核危机爆发后,美朝双方在核问题上的对峙迅速升级。朝鲜很可能是利用承认其有核计划的方式逼迫美国加大与朝鲜对话的投入,并希望利用“核牌”为美朝之间关系正常化谈判以及压美国取消对朝经济制裁能一系列安全与经济要求服务。当然,针对美国2002年2月有关将朝鲜列入“邪恶轴心”国家战略压力,朝鲜争取核能力普遍被视为是朝鲜为了改善安全状况而作出的举动⑤。但布什政府拒绝和朝鲜直接对话,采取停止《框架协议》中重油供应等方式力压朝鲜公开起全部核计划。2002年12月底到2003年1月,朝鲜宣布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武器核查人员、重启5兆瓦石墨反应堆、并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 布什政府则坚持“不会放弃任何政策手段”迫使朝鲜放弃核设施和核计划,暗示存在着军事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的可能性。而朝鲜则采取“战争边缘政策”(brinksmanship)来对抗美国的军事压力⑥。到2003年1月,第二次朝核危机出现了升级的趋势,朝鲜半岛爆发新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上升。再者,一个核武化的朝鲜半岛也是东亚地区安全的重大隐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迅速启动了朝核问题外交斡旋进程,经由2003年4月的北京“三方会谈”迅速扩展为了2003年8月的第一轮北京六方会谈。截止到2005年11月的第五轮六方会谈,外交斡旋对于推动朝核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了以下突出作用。
首先,中国主导的外交斡旋促成了六方会谈机制的建立和发展。这是中国外交斡旋朝核危机、进而在各方支持下形成多边对话平台以启动多边谈判进程富有历史意义的成果,代表了解决东亚重大地区安全问题的多边合作架构的首度正式启动。为了促成多边会谈,中国不仅进行了繁重的“穿梭外交”,在各方之间“穿针引线”、及时沟通信息,力陈进行多边磋商的各种好处以及尽快举行会谈的利害,并一直热情地提供多边会谈的对话场合;更重要的是,中方努力秉持客观、公正和积极的原则,在将近3年的对话进程中始终是牵引多边会谈不断打破各种障碍、能让六方会谈“谈下去”的强大动力。没有中国的外交斡旋,建立六方会谈机制以及已有的五轮多边磋商都是难以想像的。中国对朝核问题的外交斡旋以及领导六方会谈的努力,被评价为是中国争取承担“负责任的大国作用”的生动体现,是中国谋求“有所作为”“新外交”的具体标志[6]。
其次,中国主导的外交斡旋创造性地发展了多边谈判的性质和内涵,通过多边框架内安排双边会晤等一系列方式,为满足有关各方各自坚持的会谈需求打开了便利之门,显示了中国外交人员为政治解决朝核问题的坚定决心与把控外交斡旋角色的出色外交技巧。布什政府不愿意与朝鲜双边会谈,朝鲜一开始也难以接受多边会谈。为此,在六方会谈的架构中穿插双边会晤,不仅自然、而且符合各方的政策底线。这种将双边与多边结合的创举,充分展示了中国在介入朝核这样“高难度”冲突问题时所具有的出色的斡旋能力。
从第一轮六方会谈到第五轮六方会谈,中间的进程起伏跌宕。每次在出现美朝意见对峙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和外交官员总是挺身而出,坚持公正意见,才得以使得六方会谈迄今能一轮又一轮地进行下去。例如,第二轮六方会谈之前朝鲜要求落实的美国“书面安全保证”,第三轮六方会谈之前美国要求朝鲜必须“坦白”秘密浓缩铀问题,第四轮会谈之前朝鲜要求美国“道歉”才能复会,第五轮会谈前朝鲜则坚持先解决轻水反应堆再“弃核”。每次新一轮会谈酝酿和举行前的“卡壳”时期,都是中国外交官员和其他有关国家一起共同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让美朝双方都有所松动之后才得以渡过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顶住了来自美国的外交压力、也承受住了美国官员多次强调朝核问题“考验”中美关系性质这样的软硬兼施的手法。六方会谈机制的存在凝聚了中国外交官员的心血。
第三,中国主导的外交斡旋兼顾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原则性的核不扩散国际规制以及现实中的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平衡了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固执与其他各方意见背后的苦衷,避免了单纯“压力和孤立战略”有可能引发的冲突升级,同时也努力阻止了朝鲜想要通过核试验等进一步的对抗性举动来激化核僵局态势的冒险举动。
美国在第三和第四轮会谈中出现了因立场僵硬而被“孤立”的局面,因而在美国国内也饱受批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中国外交斡旋的积极努力,在六方会谈中态度僵硬、保守,谈判代表授权有限的布什政府不得不开始收敛一贯的“政权更替”(regime change)战略,转而公开强调美国的朝鲜政策是旨在促成平壤的“政权转型”(regime transformation)。第三轮会谈中美国所坚持的从“冻核”到“弃核”三个月过渡期的强硬立场,在第四轮会谈中有所改变。美国原来坚持不在“冻核”开始后给予朝鲜任何援助的方针因签署了《共同声明》而有所灵活。与此同时,中方对于要求朝鲜弃核的决心是坚定的和严肃的。中国和韩国一起说服朝鲜改变了2005年2月10日声明中所提出对六方会谈的参与无限期延期的偏激态度,这才有了9月的《共同声明》。为了声明的通过,中国外交官员又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草案六易其稿,从全面代表各方意见的斡旋者的立场出发,要求各方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因而大大简化了声明通过的程序,确立了今后会谈可以依据的白纸黑字载明的原则。这一幕显示了中国在朝核斡旋上“刚柔相济”的精彩一面。中国的外交斡旋与积极参与,以行动和能力证明了中国对衷心希望解决朝核争议、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义不容辞所承担的责任。中国主导六方会谈进程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第四、中国主导的外交斡旋在保持六方会谈机制的同时,正在不断地探讨和追求将对边对话解决地区安全议题的制度化进程。在六方会谈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和扩大多边安全合作架构,有可能为东亚地区安全摸索出更富有建设性的地区安全新机制⑦。自2005年2月以来,朝核问题总的来说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发展轨迹。尽管尚未实现突破性的进展,但在中国政府和外交人员的努力下,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危机事态没有进一步加剧,军事冲突的威胁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
六方会谈机制中“外交斡旋”的困境
然而,随着六方会谈进程的深入,通过六方会谈机制促成朝核问题的解决已经不是单纯中国的“外交斡旋”努力可以解决的。在六方会谈的多边架构中,一系列因素的存在,从内外两个方面限制了中国外交斡旋作用的发挥。单纯依靠中国外交斡旋只能尽可能地保持六方会谈机制,但并不能保证决定性进展能够尽快实现。
首先,无论是中国在对朝核危机以及六方会谈进程的外交斡旋时都难以避免做到完全的价值和立场中立。即便中国政府是依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我们的立场,但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是基于自己的利益、历史传统的中朝友谊以及未来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考虑而拒绝对朝鲜采取压力政策。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基于利益估算对中国斡旋角色的判断,也不能忽视在这种判断基础上六方会谈进程中各方相关利益主张协调与平衡的难度⑧。六方会谈进程中各方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有碰撞削弱了多边机制在共同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凝聚力。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坚定地表明了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基本原则,同时重申朝鲜正当的安全与经济发展需要应该得到必要的尊重,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这样的原则总是难以避免地会被视为有某种中、韩自身的利益导向。原因很简单,因为中、韩两国不仅是朝核问题的斡旋者也是朝核事态发展的直接当事人。“朝核问题”以及背后更为重要的“朝鲜问题”的演变方式都直接牵涉到中、韩双方的利益估算⑨。例如,中国之所以拒绝向朝鲜施压,不仅是我们认为“孤立和压力”政策只会激化冲突、恶化六方会谈的气愤和环境,更会导致危机新的升级。而朝核危机如果升级到军事冲突或者引发朝鲜内部局势的激烈动荡,中国都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这是我们必须避免看到的灾难性的前景。而韩国卢武铉政府也深受国内政治的影响,韩国国民近年来对朝鲜的“同胞认同”不断上升,首尔更愿意对朝鲜采取和解性的、而不是孤立性的“和平与繁荣政策”⑩。而这一利益的联系反过来也在六方会谈的外交斡旋过程中限制了中国和韩国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眼中“相对中立”的地位和影响,从而在六方会谈的多边架构中,客观上形成了中、韩、俄立场相近、而美日共同语言较多的情景。对于这种多边架构中因为利益原则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并非是能够通过斡旋得以弥补的。从多边斡旋的理论与实践来看,要么通过多边机制的制度力量,要么通过实力最强的大国的权威性压力[8],这两点在六方会谈架构中短期内都无法实现。
在国际外交斡旋的个案经验中,凡是利益直接相关的外交斡旋者的努力,都常常容易受到诟病,并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斡旋成果。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政府自80年代初以来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解的外交斡旋。虽然从卡特政府开始,斡旋巴以冲突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环节,但成功的事例太少。伊拉克战争后,布什政府加大了调停力度,但巴以和平进程依然困难重重。美国的斡旋行动甚至从来没有得到过阿拉伯人民的真正信赖和支持。对这一案例研究的结论就是美国的利益卷入太深。斡旋进程的成功首先取决于谁在斡旋[8](pp.310—330)。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与朝鲜半岛从历史到现实、从经济到地缘都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个稳定的、无核化的朝鲜半岛对我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至少在六方会谈架构中美国和中国之间对究竟实行什么样的利益估算基础上的政策的争议,使得中美之间无法形成驱动朝鲜尽快“弃核”的合力。为此,有学者提出,就六方会谈需要达到朝鲜弃核的目的来看,北京和华盛顿需要一项共同的朝鲜政策[9](pp.75—89)。这在目前是没有可能性的。中美有共同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政策,但没有共同的朝鲜政策。
中国在六方会谈中进行外交斡旋的第二个困境是无论是我们缺乏对美国政策的实际影响能力,也相对缺乏对朝鲜政策在不触动其关系基本性质前提下的强制性影响能力,因而六方会谈进程中的外交斡旋常常停留在撮合谈判、维持谈判进程等形式上,而不是在推动各方做出实质性妥协的操作能力上。
布什政府是否愿意通过对等原则基础上的外交让步来解决朝核问题,其决心和意图都是值得怀疑的。在朝核问题上,布什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过“大谈判”的决心[10](pp.7—8)。任何外交斡旋重在通过谈判和磋商解决问题,而谈判和磋商不管是在双边还是在多边层次上都必须有妥协、有让步。但布什政府目前在朝核问题上对朝鲜作出让步的可能性非常微弱。其基本原因,一是布什政府依然强硬的对朝战略主张;二是对朝鲜人权状况等问题的对美国国内政治的消极影响,妥协性的政策举措事实上难以在美国国会和公众中得到充分的支持;三是朝核僵局的拖延,能够继续对布什政府的东亚安全战略发挥“鲇鱼效应”,刺激日本政府和公众进一步加强美日军事同盟。
布什政府对中国积极斡旋朝核危机以及引领六方会谈的谈判进程表示感谢,但美国对中国在解决朝核危机中所扮演角色的期待并非仅仅是“斡旋者”、而更希望中国是一个“施压者”。中方认为,美国和朝鲜是六方会谈中两个最重要的“当事方”,但美国看来,中国同样也是要使得六方会谈有突破性进展需要更有“抉择”和“勇气”的当事方。在美国的逻辑中,中国更多地目前不是斡旋,而应该是“挑边”来协助美国“压服”朝鲜。美国国务卿赖斯2005年两度访问中国,中国之行前后都曾公开用强硬的语言要求北京对平壤施压,要求中国让朝鲜尽快拿出弃核的决心。在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之后,赖斯很坦率地表达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不满[11]。2004年11月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金融制裁。虽然美国否认是“制裁”,而只是对朝鲜的相关公司采取调查和查处措施,但目前成为了朝鲜拒绝重回六方会谈进程的理由。在中方来看,美国在人权、金融以及东亚增强军事部署和军事合作等一系列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硬姿态,只会加剧朝鲜是否回归六方会谈的疑虑。与此相对应的是,平壤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与中国合作、下决心通过弃核多边谈判进程来实质性地缓和与美日之间的关系、通过改革开放来改善国家经济和安全状况,依然还是一个“迷”。历来重视中朝传统友谊的中国不愿意、也不会以减少援助、或者威胁使用制裁等手段迫使平壤就范。但中国又缺乏实质性的手段推动美国在六方会谈中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作为霸权国家,美国欢迎中国在六方会谈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但由于中国缺乏足够的“杠杆”改变布什政府目前依然强硬的对朝政策,中国的斡旋外交无法实质性地“掌控”六方会谈进程,通过斡旋来实现弃核的实现自然是有限的。
结论
显然,解决朝核问题的外交进程想要获得实质性的突破,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外交斡旋、而是有关各方在核武器、国家安全、经济收益、外交正常化等一系列问题上是否有足够的政治决心来做出重大的政策转型和政策选择。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所主导的外交斡旋不重要了。未来六方会谈的延续需要、并且不可或缺地需要中国继续发挥积极的斡旋者的作用,但突破性的进展还需要各方充分的政治决断。中国的外交斡旋将会继续引领六方会谈前进,但六方会谈是否能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需要有关各方共同努力。
从目前来看,中国所能扮演的外交斡旋的角色是基于东北亚区域和平与繁荣的中国责任所能承担的贡献。我们没有必要去为了某个国家的利益标准和战略意图充当“权力掮客”(power broker)这样的角色。事实上,即便中国更多地按照美国的意志在朝核问题上去发挥“权力掮客”的作用,美国也不会给予中国足够的战略信任来让“授权”中国成为美朝解决朝核问题的“经纪人”。英国可以在利比亚弃核问题上通过10个月的秘密谈判做到这一点,但中国不是英国。即便中国愿意,中国不可能在美国充分信任的前提下去“客串”这一角色[12](p.146)。所以,六方会谈中的中国只能用我们自己的诚意和责任去担当我们作为区域国家的和平使命。目前,对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斡旋角色究竟能走多远,国际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论。有人认为中国基于文化与历史的联系,对朝核问题的政策永远是以稳定为主;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将会最终让中国对朝鲜实行“强制性接触”(coercive engagement)政策[13](pp.234—248)。面对未来东北亚局势的变化,中国斡旋角色的适时调整、在动态中把握我们对区域和平与繁荣的最大贡献,应该是指引中国的外交斡旋使命的基本思路。
收稿日期:2006—03—28
注释:
① 有关后冷战时代国际斡旋在解决国际性冲突中的意义和作用,参见Jacob Bercovitch,ed.,Resolv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diation,Boulder:Lynne Rienner Bublishers,1996,pp.11—35。有关冷战后国际外交斡旋的回顾与总结,参见Saadia Touval and I.William Zartman,“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in Chester A Crocker,Fen Osler Hampson,and Pamela Aall,eds.,Turbulent Peace:The Challenges of Manag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Washington,D.C.:United State Institute of Peace,2001.
② 有关国际关系中外交斡旋在冲突解决中的理论总结,请参见Jacob Bercovitch,ed.,Resolv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diation,Boulder:Lynne Rienner Bublishers,1996; J.A.Wall and A.Lynn,“Mediation:A Current Review,”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7,No.1(1993),pp.225—229; C.R.Mitchell and K.Webb,New Approach for Conflict International Mediation,New York:Greenwood,1988.
③ 有关第一次朝核危机以及克林顿政府的朝鲜政策,参见Michael J.Mazarr,North Korea and the Bomb:A Case Study in Nonprolifera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6; Leon V.Sigal,Disarming Strangers:Nuclear Diplomacy with North Kore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Joel S.Wit,Daniel B.Poneman,and Robert L.Gallucci,Going Critical:The First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4.
④ 按照Chester A.Crocker,Fen Osier Hampson,and Pamela Aall的分类,最难解决的斡旋问题是那些冲突时间长、性质严重和存在着对立意识形态的问题。参见Taming Intractable Conflicts:Mediation in the Hardest Cases,pp.7—9.
⑤ 有关2002年10月朝鲜在与美国当时的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的会谈中承认有“核计划”的原因分析,请参见Victor D.Cha and David C.Kang,Nuclear North Korea:A Debate on Engagement Strateg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 Michael O'Hanlon and Mike Mochizuki,Crisi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How to Deal With A Nuclear North Korea,Washington: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ook,2003;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军控与裁军研究中心刘沛主编:《朝鲜核危机透视——美俄日韩专家论朝核危机》,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3年版。
⑥ 有关对朝鲜、美国及相关各方对朝核问题基本政策的跟踪与分析,参见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trategy,The Strategic Balance in Northeast Asia:2003—2005,Seoul: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trategy,2003—2005;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of Japan,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2003—2005,Tokyo:NIDSJ,2003—2005; CSIS Comparative Policy Quarterly of East Asia,CSIS Pacific Forum E-Journal,2003—2005.
⑦ 在朝核六方会谈的基础上扩大、并建立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呼声目前已经成为政策与学术界的共识。而这一地区安全多边机制的建立很有可能进一步带动朝核问题的解决。有关这两者相互关系的探讨,请参见Joseph R.Cerami,“From the Six Party Talks to A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Regime? 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The Korea Economic Institute of America:The North Korea Nuclear Issue,2004,pp.59—76.
⑧ 对中国外交斡旋角色与中朝关系问题上“美国式”解读,请参见Andrew Scobell,“China and North Korea:From Comrades-in-Arms to Allies at Arm's Length,”March 2004,www.carlistle.army.mil/ssi/pdffiles/00364.pdf; Anne Wu,“What China Whispers to North Kore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8,No.2(Spring 2005),pp.35—48.
⑨ 有关“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之间的联系,为什么更需要首先解决“朝鲜问题”才能解决“朝核问题”的具体分析,请参见朱锋,“六方会谈:朝鲜问题还是朝核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第28—38页。
⑩ 韩国在六方会谈中这一对朝立场背离了美韩同盟协调一致的对朝鲜政策的传统,被视为是美韩同盟“漂流”的重要因素。有关这方面的分析,请参见Norman D.Levin,Do the Ties Still Bind? The U.S.-ROK Security Relations after“9·11”Rand:Project Air Force,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