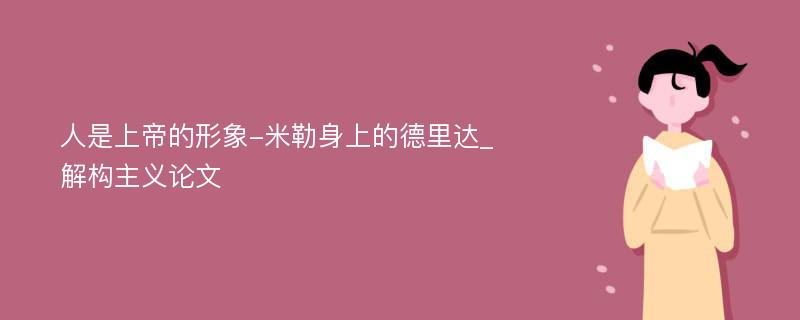
人是上帝的映像①——德里达论米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勒论文,人是论文,映像论文,上帝论文,德里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4月18-19日,在美国厄湾加州大学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研讨的对象是J.希利斯·米勒其人与其学术。参会的有不同国家的学者,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是米勒过去或现在的学生或朋友。米勒和他的密友——已故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主旨发言。德里达的发言题为“论正义”(Justices)。该演说后来发表在《批评探索》春之卷,又收Provocations to Reading一书。②他以其一贯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演说风格,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米勒的人格、学术的敬仰和钦佩之情,同时对米勒与他三十多年的真诚友谊进行了回顾。雅意勤勤,殊为感人。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哲学家,德里达并未停留在一般性对朋友、对其成就的评论,而是借机做了对诸如正义、友谊、孤独等问题作了哲学上的思考与表达。仔细阅读,我们能发现他在演说中以他与米勒在不同时期的交往和对米勒不同时期著作的评论为经,以“正义”、“孤独”、“友谊”、“米勒学术成就”为纬,既对米勒做了深刻的评价,又借题做哲思的发挥,评论与哲思并妙。德里达和米勒同为大思想家、理论家,可谓大家评大家,精彩处俯拾皆是。而此演说思想密度极高,涉及面极广,又不是本文所能概全的。下文仅按以上所提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对德里达论述中的某些隐晦处提出管见。
论“正义”
文章开篇,德里达便提出一个问题:他与J.希里斯·米勒友情甚笃,对他钦佩有加。而结交三十五年来,德里达却一直在问自己,J.希里斯·米勒到底是何等样人?德里达认为,米勒首先是一个“正义者”。他说:“正义者,这是我今天要送给米勒的一个雅名。这雅名出于我对他的感觉,出于我对他在意识自我和体味自我方面的认知。其实,“正义者”这个名字我一直悄悄地留着要送给米勒。这是美德之名。在他人面前,在作品面前,在文本面前,在他人的签名面前,它具有承担责任的楷模意义”(230)。
德里达认为,正义不是一种后天可以获得的品质,而是一种先天的自然禀赋。“正义之光会闪耀出去,辐射开来。正义者亦然。”他借霍普金斯的话说,这种禀赋仅能来自上帝,但上帝却允许我们在需要正义时以“我”的名义自由发挥。有着这种禀赋的正义者,能温文尔雅,又坚强有力。正义来自其外部而又发自其自身。他能做到正义就是正义。正义将正义交付给正义者,使正义者能赋予自己以力量,使正义得以伸张(230)。
以解构主义者所擅长之追根究底的方式,德里达考察了“正义”(Justice)一词的词源,指出它有着拉丁词根,兼带着希腊语的记忆。它指的是一种观念、一种价值、一种品质、一种判断方式,一种永远与法律相关的司法形象。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行事方法。他指出,这个词常常有着言语行为中的“践行力量”,有“使正义发生,普及”的意思,但是这种动作并不带有及物意义。德里达认为有着“正义之心”的人本质上是正义的,正如呼吸之于他的存在一般自然。行使正义,对他来说是一种天性的流露。这种“自然而然”意味着正义从它的发源地自由地流淌,散播。因此这种正义是内在的,与正义者本人不可分离(231)。对于德里达来说,米勒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正义者”。而他作为一个正义者所表现出来的正义之心,尤其让德里达深怀敬意。
有意思的是,德里达把正义归属于上帝和人的共同品质。上帝和人都是正义的,都是正义者。……“正义”正是上帝的特质(232)。他特别评价了米勒在《上帝的消失》(The Disappearance of God)一书结尾时对霍普金斯的几行诗的分析:Wert thou my enemy,Oh,thou my friend/How wouldst thou worse,I wonder,than thou dost/Defeat,thwart me?③诗中的主人公对上帝似乎愤懑不平。他对上帝百般顺从,却不得上帝眷顾。有德者事无所成,有罪者反飞黄腾达;年复一年,辛勤耕耘,却一无所获。《圣经》中约伯有此怨言,《哀失明》中的叙述者(或者也就是密尔顿自己)也有此怨言。那么怎么解释上帝的公正或正义呢?
在谈到这首诗的阐释的时候,德里达对当时的听众说:那时(指米勒在书中阐释霍普金斯的这首诗的时候)你们中很多人都还没有出生呢!出生了的,也还都是些初出茅庐的学生娃。至于我,当时还不认识这么个人(指米勒),以及他写的任何著作。而这个人和他的著作却在我日后的生活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早在1963年,米勒就对霍普金斯的这几行诗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全新阐释。他对“正确”与“正义”的双重关注,对阐释的伦理关注,对其他文本的负责任的忠诚,对文学认识论的、本体论的问题的深刻认识,都让德里达“非常钦敬”。而最令德里达佩服的地方是,在米勒对这首诗进行阐释时,还没有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还没有所谓“陈述”与“践行”的语言范畴。而米勒的阐释却涉及到了哲学家奥斯汀后来的哲学理论,即言语行为理论。德里达认为这是对正义本身所持的勇气,是对阅读伦理,写作伦理,教学伦理的勇气,对此,正义的学者都该肃然起敬。
正义与阐释、回应的真实性、必要性和忠实性在德里达文中时时提起却语焉不详,似乎有难言之隐。而说到米勒,说到解构,这却是一个不能不提的问题。这一段非常有趣,不妨多引用一些:
米勒的著作,新意繁多,不可胜数。而我最想提及的、最具米勒个性的,是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对那些声称最为契合、最为接近、最为相似的种种臭名昭著的景观的清晰的疏离。那些署了米勒的名字的,或称之为米勒的作品的,都可能需要进行无休无止的回应。那些回应,当然都是以他的名,并为了他的名而进行的,是负责任的举动。但也是为了责任本身。为责任而回应,或因与正义相关,责任使然,就要想想让回应的可能性成为回应的具体形式,想想其中的种种难处。伦理的责任不仅体现在生活或生存中,还体现在解密、阐释和写作当中。作为教师、作者,也是作为公民,甚至是世界公民,米勒都把他的才干整个投入进去了。没有谁对应答的必要性——即使不是在真实性的问题上,比他说的更好的了。关于必要性与真实性问题,他在《阅读的伦理》一书中讲到了。米勒从卡夫卡的《审判》中引用了一段话,说明真实与必要之间的张力。牧师对约瑟夫·K说了心里话,对方一言不发。牧师感叹地说,“不必把一切都当成真的,只把它看成是一种必要就行了。”……米勒象法律面前的约瑟夫一样,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他必须在法律面前为他人的文本进行应答,并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冒撒谎的危险,哪怕他自己是极为正直而诚实的人。(254-255)
我们不知道德里达想要通过这段话表达怎样的意图,但这不妨碍我们对这段话作一个试探性的阐释。德里达在美国、在世界,都是以解构主义的创立者而闻名的。而解构主义的核心力量除了在耶鲁大学执教的德里达外,还有所谓耶鲁“四人帮”,即保罗.德曼,J.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1966年德里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宣读了题为“人文学科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嬉戏”的论文,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提出种种质疑。接着于1967年发表了三部奠基之作:《言语与现象》、《书写与差异》和《论文字学》,从此成为20世纪哲学话语的中心人物,也开始了他作为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生涯,并与法国的罗兰·巴特、福科、美国的耶鲁学派理论家彼此呼应,推动了解构主义思潮。1987年,保罗·德曼被揭发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1-1942)在比利时一份学生刊物和两份纳粹报纸上发表文章,解构主义也因此遭遇严重危机。很多人不仅对德曼以解构思想撰写的文章提出种种质疑,而且还对整个解构主义发难。而解构主义也奋起抗争,一时间硝烟弥漫。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维纳(Jon Wiener)的质疑信和米勒致维纳的公开信。维纳的信对德曼的为自己的纳粹写作和整个解构主义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米勒的回信可谓义正词严,环环相扣,锋芒所向,势不可挡。他一方面为德曼辩护,一方面为解构主义辩护,所表现出的正义和修辞上的说服力,都令人叹为观止。下面选几段共赏:
约翰·维纳教授,
我本不想写信,但想到我俩都该对更大的学术群体和更多的人负责,而同事间的争论可能愈演愈烈,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不得已写此公开信。我本想再等待一阵,我也建议你这样做,直到德曼所有的有关文章都找到了为止。我也在等着看你能否收回那篇文章,改正文中的错误和那些含沙射影之词。我知道这些问题已经有其他人也向你指出了。
我认为你关于德曼的文章毫无根据,歪曲事实,丝毫不负责任,是关于德曼问题最为糟糕的报道。你说你在文章中是让双方说话的,并让读者自己去作判断,但你文章所给的“证据”却很清楚你会得出怎样的结论,读者会被引导得出什么结论。你允许发表的东西已经在美国和欧洲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使得理性地、有根有据地讨论德曼的文章问题没了可能。这个国家和欧洲成千上万的人将读到你的文章,并把它作为事实的精确报道。如果德曼得对他所写的东西和由此产生的影响负责,我相信你也要对你所写的东西所产生的影响负责。你说你戴着两顶帽子:一顶是记者的帽子,一顶是历史学家的帽子,但我想,不管作为哪一种人,你的首要职责应该是负责任地、正确地陈述事实。你的文章很有分量,很有权威性,因为你是历史学教授啊!当然啦,向所有其他人一样,你大有对德曼和解构主义随意判断的自由,但是这种判断应该以对文件的仔细阅读,对事实的细心甄别为基础,对如此严肃的问题更应如此。(Miller,Theory Now and Then 369-370)
米勒指出,维纳文章中的错误太多,不胜枚举。择其要者,他列举了14大问题19个小问题逐一批驳,其力似泰山压顶,其势如摧枯拉朽,令对手无招架之力。如第13条是这样的:你关于海德格尔和“解构主义”的话中,最为糟糕、最为玷污清名的,是关于解构主义的那一段了,这实际上是你文章中的实质部分。文中所隐论点的逻辑顺序是这样的:从其早期文章里,可以看出德曼是一个地道的法西斯分子,在其晚期文章里,德曼是一个“解构主义者。”他的结构主义作品与他的“早期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所有的解构主义者,包括我和德里达,都是法西斯分子。更有甚者,德里达承认海德格尔——一个法西斯哲学家,是解构主义的鼻祖。因此,我们又回到前面的结论,即所有的解构主义者都是法西斯分子。你在发表了这种东西之后,还希望我能坐下来,两人好好聊聊你那篇文章。你真会开玩笑!(Miller,Theory Now and Then 378)
从上述文字的口气,我们可以看出米勒是正气凛然的。这种凛然之气不仅出于对他的好友的忠诚友谊,更出于要对事情真相进行辩白的正义。事实上,德曼事件发生后,“耶鲁四人帮”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各种压力之下,哈特曼遁身耶鲁大学图书馆,潜心搞他的犹太研究中心;而此时的布鲁姆,则从先前为德曼出谋划策④到现在与德曼划清界限,说自己是怎样痛恨德曼的为人了。只有米勒,耿直的米勒,坚持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而不是单凭当时发现的几篇文章就草率地下结论。他要据理为自己辩,为朋友辩,为解构辩。因为心怀坦荡,正义在胸,所以才能大气凛然。这种辩护是必要的,在事实未能确定前怎么能随便给人下定义呢?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也是值得钦佩的,具有人格的魅力。
但是,“必要”和“真实”不一定吻合。在一定时间里有必要做的事情,最后可能没有“真”的价值。这就使这种有“必要”做而未必有“真”的价值的事情最后染上悲壮的色彩。这种事情史有前例。1923年10月,康有为到陕西讲学,发生了康氏换经、盗经风波,康圣人“树上开花”,瞒天过海的韬略得售,而友人马凌甫等人竟浑然不觉,还为之慷慨申辩,可谓“君子可以欺以其方”(夏晓虹441-442)。德曼当时著文,也许只是幼稚草率,也许出于无知,也许真有政治倾向,这现在还是悬案。而米勒为其辩护,难免有马氏为康圣人辩护之虞。
怎么评论米勒这一“义举”?应答的必要性与应答最终的“真实性”往往有不一致之处。但从正义者身上流露出来的“正义”很自然地让正义者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只是事实或有令人懊丧之处。这也许是德里达要提到米勒早已在阐释霍普金斯诗歌时,就提出了“正义”与“真实”的两面性的原因?是他既要阐明米勒的“正义”,又要说明“正义”并非时时“真实”这一重要命题的原因?
论“孤独”
法国思想家卢梭因为身处难以承受的外力,以至其“自我”被残酷地异化,变得非常孤独。在《漫步之五》中,他表达了强烈的追求自由的愿望。他写道:
假如有这样一种境界,心灵无需瞻前顾后,就能找到它可以寄托、可以凝聚它全部力量的牢固的基础;时间对它来说已不起作用,现在这一时刻可以永远持续下去,既不显示出它的绵延,又不留下任何更替的痕迹;心中既无匮乏之感也无享受之感,既不觉苦也不觉乐,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到自己的存在,同时单凭这个感觉就足以充实我们的心灵:只要这种境界持续下去,处于这种境界的人就可以自称为幸福,而这不是一种人们从生活乐趣中取得的不完全的、可怜的、相对的幸福,而是一种在心灵中不会留下空虚之感的充分的、完全的、圆满的幸福。(卢梭76)
卢梭崇尚自我,不受羁绊。《漫步遐想录》是他跟自己的心灵亲切交谈的产物,是对自己的心灵的分析和解剖,也是一个思想者生存状态的写照。对于思想者来说,“孤独”是幸福的,也是必然的。
从哲学上看,孤独并不是一种贬义的东西,它是一种生存状态,与“自我”(selfhood)紧密相关。德里达认为,孑然一身,离群索居,与外界隔离,这是一种“自我存在”(selfbeing),是“自我”(selfhood)和“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得以实现的经历。孤独的过程,也是自我旨趣(the taste of self)得以细心品尝的过程。迪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孤独状态,因为一个人只有处于“自我”状态的时候,才能真正进行“思”的活动。米勒给出了“我思故我在”的霍普金斯版本:“我品味自我,故我在。在品味自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与任何一个别的人都迥然有别”(Miller,The Disappearance of God 271)。这种自我旨趣,用霍普金斯的话来说,是“不可模仿的,”用米勒的话来说是“难以言说的。”
德里达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他说,他脑子里经常萦绕着一个这样的问题:一个朋友,无论怎么亲密,仍是一个“他者”。米勒是他的密友,那么希利斯·米勒的自我品味究为何样?何为希利斯·米勒?他对这件事或那件事有何看法?他都干些什么?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在问:一个人的内心感觉是个什么样子?一个人如果是J.希利斯·米勒的话,他在与自己接触时,其独特的孤寂感是个什么样子?为什么一个人只会是自己而不是他的朋友?这种自我中的孤独难以言表、不可与外人道。中世纪苏格兰经院哲学家,唯名论者邓斯·司各脱[John(或Johannes)Duns Scotus,约1265-1308],称其为人类的“终极孤独”(the ultima solitude of man)。在自我的最深处,人类是孤独的。在这里,有自我品味意识的群体中的任何一员都彻底地与他人隔离。“按照这个意义,上帝是最具个别特征的、最为与众不同的人。他最为孤独。他是一把钥匙,最终开不了任何一把锁”(238)。这样,德里达方便地由人的孤独转到对神性的孤独的讨论。在这里,神与人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孤寂具有一种神性:即上帝也有神秘、可怕的孤独。上帝是孤独的。人作为上帝形象的投射,其孤独当然就在上帝孤独的形象之中。但与其所有的创造物相比,上帝又是最为孤独的。我们每次身感孤独时,就与上帝有所相似了。但上帝的孤独远甚于我们,因为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特立独行。上帝就是上帝,因此上帝是孤独的。上帝孤独,我们每个人在“自我”的意义上也是孤独的,因此我们爱他。我们爱他不是因为他全知全能,君临万物;我们爱他,因为他也孤独,可怜!上帝是所有存在中之最为孤独者!因此尽管有神性,但也易受伤害。这当然不见得是基督徒的想法。特立独行者的孤独,是无法形容的。他像一个稚童,被遗弃,受伤害,却又口不能言。我们所爱的很多朋友,爱人,情况也大抵如此。(241-242)
人与神比邻,哲人生就孤独,这在丁尼生的诗歌里也有体现。丁尼生在《鹰》中把好朋友哈拉姆(Arthur H.Hallam)比作长空中的一只孤鹰,孤居高峰,近日而栖,以山为壁,蓝天为顶,睥睨万世,纵横红尘。滔天江海,不过微澜;自天俯冲,势如惊雷。这是一个孤独的形象,也是一个力量的形象。它不屑红尘琐事,自由翱翔于天地之间。在丁尼生的眼中,哈拉姆本来就是一个超凡脱俗的智者,思想深刻,智慧超人。孤独,让他享受思想的快乐;孤独,使他享受自由。两相比较,德里达以哲学的语言,探讨孤独与崇高;丁尼生以形象的语言探讨同样的主题,实在异曲而同工。人与神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孤独的。孤独是一种境界,是一种生存方式。孤独是智者的知性生活达到超出常人境界时的独特感受。在德里达的眼里,米勒便是这种具有哲思,享受孤独的人。
论友谊
在德里达的演说中,上帝已被人化,或者说,他已把特定的人神化。因此他说:“上帝是爱,上帝是朋友。这个朋友有着强大的力量,如果他要害我,他可以比任何其他人都厉害,但是他却不会害我”(Derrida 233)。对他与米勒之间的友谊,德里达有如下深情而理性的回忆——用德里达的话来说,是用理论的、哲学的、甚至体制性分析的中性语气来表达敬佩与情感。
给予我这样的公开机会,回忆与米勒的交往,简直是一种恩赐。三十五年多来,我能执教鞭于米勒左右,并在美国各大学广受欢迎,由霍普金斯大学(1968-74)而耶鲁大学(1975-86),而厄湾加州大学(1987至今),何其荣幸!更能有幸与米勒一同周游各国,讲学、开会,种种学术活动打上了我们共同生活的烙印。此时,我们一起呼吸的空气,是宁静的友谊,是不渝的忠诚。所有熟谙世事的人,熟谙世事中之学术圈的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这实在难能可贵,不同一般,是例外中的例外。三十五年里,我们各自在语言、历史、风格、姿态、性格,乃至各自的用语特色,自我品味等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非常明显,尽人皆知,我们两人更是明白不过。但从来没有争执的阴影将我们包围,从来没有不和的乌云将我们笼罩。之所以能如此,要归功于希利斯的“正义”和他的友谊伦理。(Derrida 251-252)
确实,米勒是诚挚友好的,德里达是领情感恩的。如果德里达只是利用米勒的善意,过河便拆桥,德里达不会这么深情地致谢;米勒和德里达是互相欣赏的,在为人行事方面也有很多的契合。米勒和德里达是互相包容的。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互相尊重对方,而不以己见为圭臬,排斥异见,继以挞伐。他们都是学界泰斗,在很多学人眼里他们似乎有着神圣的光辉。凭着他们的强大力量,如要加害于他人,那也非同小可,但是他们坚守正义,让世人懂得什么是高尚。诚如德里达所言,“米勒的友谊是正义的,如同他阐释文本、撰写文章时所表现出的正义一样”(Derrida 234)。尽管在演说中德里达没有把友谊论述得像《友谊的政治》中那样深透⑤,但是友谊与“正义”却又是德里达关于友谊的新阐发。
论卓见
德里达对米勒的博学与深思表现了深深的钦佩之情。在演讲中他涉及了米勒的《上帝的消失》,《阅读的伦理》,《黑洞》等数部著作,指出了每部著作中米勒表现出的卓见。这里略举数例。在《上帝的消失》中,德里达认为米勒关于“上帝隐身”的思想最令他着迷,信服,印象深刻。米勒的这一思想不只是一种学识、一种哲学、甚至一种神学,它关乎思维、经历和文学写作等的问题。在这一书中,米勒通过对五位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之作品的分析,清晰而忠实地阐释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确”。米勒认为,上帝隐身,不仅因为他从未被人看到,而且还因为他从不亲自回应人的问题。米勒以高屋建瓴的方式描述了19世纪直至当代文学中的“宗教情形”。他指出,在这段时间里,宗教实质上被废弃了,上帝从这里隐退了,离去了。
德里达评论说,米勒在这里论述的“存在”,或者说“不可能的存在”等概念,很明显在1963年“解构”这个词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有人说米勒在一天之内皈依了解构主义,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解构”的思想在他的第一部著作里就存在了。只要读他的著作,我们就能看出他说的“品味的独特”是怎么回事,什么是语言的局限,什么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尤其知道什么是对存在的超越和切分(246)。米勒在《上帝的消失中》说
上帝并不以显现的方式存在,他只存在于那些关于创造的书中。当我问我此身来自何方时,没有谁能回答我。我转而自省,只发现自己不可被他人效仿的自我品味。不管在我之外还是之内,上帝都没有直接出现在我之前。他的存在只不过是我由“自我发现”推论而来。创造了我和世界的其他万物后,他就退隐了,住在我们之上、之外的什么地方,忙他自己不为人窥见的事情去了。上帝隐身藏行,这便是19世纪很多人发现的宗教情形。(Miller,The Disappearance of God 272-273)
19世纪乃至当代文学中的“上帝隐形”现象,是米勒的卓见之一。而他对于修辞解读的社会功能,同样见人之所未见。在阐释霍桑的《牧师的黑面纱》时,米勒认为,修辞解读同样关心阐释的社会功能,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功能。
又如,德里达指出,米勒对政治、政治体制、地缘政治、技术政治的关心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他希望人们能够从米勒的文章中获益,了解地缘政治的转变,认清其对大学体制和民主的影响,以及其对大学里文化研究的意义。他认为米勒的探讨,在文学、哲学、心理分析、绘画与建筑等领域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述论述在他的《黑洞》里表现得很清楚。而在《阅读的伦理》中,米勒向人们说明了,由于读者有责任作出反应,因此阅读一方面超越了人们所假定的属于纯粹的文本内部阅读的“内在性”,比如认为这仅仅属于文本的“内在性”,或认为这仅仅属于学术体制内的“内在性”。另一方面,它又在政治、社会和司法等方面超越了伦理的界限。因此,《阅读的伦理》一书讨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阅读的伦理”。用米勒的话来说就是,阅读行为,由于涉及到对文本的反应,因此既是强制性的又是自由的。说它是强制性的,是因为阅读不可避免地要求你做出反应;说它是自由的,是因为我必须对我的反应承担责任,对进一步的影响承担责任——比如对我的阅读在“人际”、体制、社会、政治和历史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负责任,因为阅读行为可能以教学或对某一特定文本发表评论的形式呈现(Miller,The Ethics of Reading 43)。
德里达认为,作为一个思想家,米勒思想敏锐,眼光犀利。德里达说,如果有人认为《阅读伦理》一书的作者希利斯·米勒是一位温和的,宁静的,满口仁义道德的保守思想家,那就错了。解构主义常常遭受愚蠢的指责,说成是刚愎自用的,不道德的,愤世嫉俗的,怀疑主义的,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的。米勒总要起而辩护。对他来说,关于伦理的无休无止的争辩是一场斗争,必得要有耐心,要冒险,要勇敢。因此,米勒不能只是呆在图书馆,呆在《圣经》里,呆在那些成为文学的书中,尤其是呆在大学校园(257)。而J.希利斯·米勒全然不是这样一个书呆子。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备受尊敬的大教授,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位挚友,一位和蔼的同事。他学识宏富,著述等身,研究领域包括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文学理论、修辞学、语言学,也研究教学、大学体制、经典的变化与发展问题,文化研究、新技术、伦理学、政治学、绘画,以及这一切与神学、哲学、语言学、研究言语行为的语用学等等。在所有这些领域里,他都取得了令人景仰的成就。德里达以《新约》和《旧约》中的两个约瑟来评价米勒。一位是《新约》中圣母玛丽亚的丈夫约瑟(Matt 1∶19)。另一个是《旧约·创世记》中的约瑟,雅各的爱子,一位解梦者(Gen 37∶23-28)。德里达以这两个约瑟表示对米勒的敬佩与感激:前一个约瑟是个义人,后一个约瑟是个解码大师,而米勒对文学之谜的独到见解和解码技能、其理论与批评的建树,实在世罕有俦。
有鉴于此,德里达用解构主义哲学的语言,在对米勒进行评价的时候,有意模糊了神与人、具体与抽象的二元对立,创造了一个可爱的神,和一个可敬的米勒。这里的神有了更多的人性,甚至有了常人的弱点——易受伤害,给人一种“我们中间的一个”的感觉,因而可爱;而这个人却具有了相当的神性,让人肃然起敬。这种模糊,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人是上帝的映像。他在确认自身身份的同时,也将上帝的形象映照出来。”
注释:
①此说源于《圣经·创世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米尔顿在《国王与行政官权利的来源》一书中也写道:all men were naturally born free,being the image and resemblance of God himself.德里达在论米勒时用此语,有画龙点睛之妙。
②Critical Inquiry 31(2005)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689-721; Provocations to Reading,ed.Barbara Cohen and Dragan Kujundzic(New York:Fordham UP,2005).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标明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③霍普金斯全诗如下:“Thou art indeed just,Lord,if I contend/With thee;but,sir,so what I plead is just./Why do sinners' ways prosper? and why must/Disappointment all I endeavour end?/Wert thou my enemy,O thou my friend,/How wouldst thou worse,I wonder,than thou dost/Defeat,thwart me? Oh,the sots and thralls of lust/Do in spare hours more thrive than I that spend,/Sir,life upon thy cause.See,banks and brakes/Now,leaved how thick! laced they are again/With fretty chervil,look,and fresh wind shakes/Them; birds build—but not I build; no,but strain,/Time' s eunuch,and not breed one work that wakes./Mine,O thou lord of life,send my roots rain.”
④2007年我在耶鲁大学做研究时,专门对此事做过调查。有耶鲁大学教授告诉我,德曼出事后,向布鲁姆讨教,布鲁姆跟他说,你可以说这是我爸爸让我写的,我叔叔让我写的呀!“it’s the daddy,it’s the uncle.”姑为一说。
⑤德里达在《友谊的政治》[Politics of Friendship,trans.George Collins(London & New York:Verso,1997)]中,对什么是友谊,友谊的类型,友谊如何塑造着人格和气质,友谊的私人性和社会性的界限,友谊和战争的关系,私人友谊和集体之间和国家友谊之间的差异等作了深入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