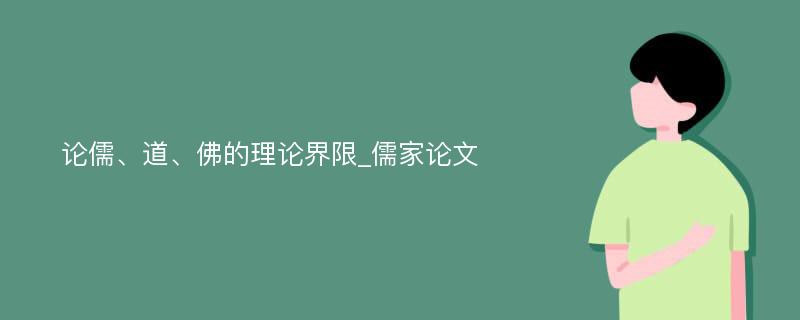
关于儒、道、佛三家的理论极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家论文,极限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儒、道、 佛(禅宗)三家理论构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从理论“终极关怀”的视角看,三家皆有自身的理论极限:在儒为“天命”,在道为“无极”,在佛为“拈花之境”。三家理论既有纵向的衔续性,又有横向的涵纳性。道家以“无限”实现了对儒家的超越,佛家以“心法”实现了对道家的超越,最后由宋明理学完成了对三家的综合性超越。准确地找到这三个极限,对于在宏观上重新认识儒、道、佛三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或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几乎每一个学说,都有其理论所难以阐释和证明的最高限度。这个最高限度,我们称之为“理论极限”。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均有自己无法逾越的理论极限,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儒家、道家和佛学。东晋大和尚慧远,《高僧传》说他“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但抚今追昔,慧远却每每对儒、道两家颇多贬抑:“每寻畴昔,游心世典(指儒家经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这一心得,除了证明他悟道境界之不断提升外,却也说出了儒、道两家在思想理论上各存极限的客观事实。实际上,佛教,尤其是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其本身亦存在着类似的极限。准确地找到这三个极限,对于重新认识儒、道、佛三家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或许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天命”——先秦儒家的理论极限
先秦时期有一个特殊的理论现象,即:争鸣的诸学派几乎无一例外地均把“道”视为本学派理论的最高范畴。但“道”的内涵显然是千差万别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的讲法,道出了这一事实。那么,儒家的“道”是什么呢?
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理论发轫,“孔孟之道”包含着儒家关于“道”的全部萌芽和终极属性。儒家虽也重视世界万物存在本体和天地运行变化大规律意义上的“道”,即“天道”,但它更重视的则是社会发展之根本目标和最高准则意义上的“王道”与个人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并由此而优入圣域的途径方法。因而从实际上讲,该“道”乃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和永恒原则。《孟子·滕文公下》即把“道”的目标瞄准了“天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而“道”之所以具有公正的意义,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天下的“民”为尺度而量得的结果:“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孟子·尽心下》)、“道也者,治之经理也”(《荀子·正名》)、“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荀子·天论》)。不难看出,这种“道”,带有相当浓重的人本色彩,这可以从“人”、“仁”、“道”三者间的互训关系中明察:“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说明“人道”即“仁道”,亦即“王道”。所谓“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是也。看来,《论语》所谓“士志于道”(《里仁》)也好,“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也好,《荀子》的“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修身》)也罢,其“道”之所指,均未尝逾此。就连心理上的耻感反应,亦未离其大旨:“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显然,此“道”已成为儒家士子的“终极关怀”。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堪称为“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中国哲学关于终极关怀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其实,说到这里, 结论性的东西已经露呈,即:先秦时代的儒家之“道”,更多的只通用于天地之间的人类社会。就是说,与人生无关的,或离人生稍远的抽象存在,一般不在讨论和探究之列。孔子弟子子贡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对此,荀子有一段比较达意的发挥和总结:
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天论》)就是说,这样的“道”是不离人世的,也是不离人事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礼记·中庸》)可是,儒者在知行活动中,却实实在在感觉到有一种高于此“道”并指导和决定此“道”的大规律客观地存在着。孔子说:“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论语·宪问》)这表明,孔子已意识到,在儒家的“道”之上,还应有一个特殊的存在,这就是“命”。可究竟什么是“命”,却又很难说清,只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东西,它决定人事的发展变化,却又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使人们在它面前无可奈何。《孟子·万章上》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庄子·人间世》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达生》篇释“命”:“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儒家的“命”,有时就是“天”,“天”亦常常被称作“命”。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中的“命”与“天”之互训关系等,故“天命”每每连用。《左传》宣公三年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论语·为政》篇亦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说。而且,孔子对于“天命”是常怀敬畏之心的。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有学者认为,“命,作为儒家历史哲学的重要范畴,与‘天’、‘天意’属同一层次,天与命可以相合成‘天命’。”(方同义:《儒家道势关系论》,《孔子研究》1993年第1 期)而人类的主体之道与历史发展不可预知的内在必然性之间所发生的矛盾,使“孔孟之道”的有效范围也只能局限在人世间而已。“尽人事而待天命”等说法表明,人事尽处即是“命”。说明儒家之“道”已无力解释虽在人世之外却能决定和制约人间事务的更高层次的规律。显然,“天命”已成为先秦儒家的理论极限。
理论极限意味着无话可说。好像有一种预感,当孔子发现了这个极限后,就已经意识到了它的危险走向,即流布于民间的“天命论”可能会染上浓重的先验迷信色彩。所以他才竭力防范和阻止之,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是也。荀子亦曾对“天命”讹滥成“宿命”后的卜知祷求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认为这些行径,“学者不为也”(《荀子·非相》)。可是,理论极限所形成的诠释真空,事实上是无法阻止异端邪说的乘势填充的。历史上,这种染上了迷信色彩的“天命观”,早已散入民间,甚或在某些权势者口中,也每每成为无可奈何时的最高安慰和推卸责任的唯一借口。殷商将灭,纣王喊道:“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项羽兵败乌江,不自忖过失,末了却仰天长叹:“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史记·项羽本纪》)迨至东汉,此风非但未衰,反发展成较完备的理论说教。如王充在《论衡·命禄》篇中所云者。它最终凝结成一句先验论格言,叫做“否泰有命,通塞听天”(《抱扑子·外篇·应嘲》)。这显然是儒家理论极限的负效应,它导致了迷信。
二、对“天命”超越与“无极而太极”
荀子曾非议道家,说它“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可是,反向的思考亦同步成立,即道家的天论,又何尝不是对“蔽于人而不知天”之儒家理论及其极限的一大超越呢?如果说,儒家的“命”就是“天”,那么,它的层次则刚好处于“老庄之道”的下面,即孔孟与老庄之间的关系实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中的“天”与“道”的关系。“大道废,有仁义”(《老子·十八章》)一语,已至为明确地披露了这一关系。因此,可以说,儒家抛出的理论极限,刚好是道家哲学的出发点。即:道家所喋喋不休的,正儒家之所阙如者。日后互补的原因,盖存乎此。
儒家之所以推出“天命论”这一理论极限,某种意义上,实出于对瞬息万变之社会现实的无可奈何。雅斯贝尔斯认为,在“轴心期”时代,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使人们经常不断地面临着现实性的丧失(参见《智慧之路——哲学导论》第十三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不过,不确定性也好,不断丧失的现实性也罢,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即儒家所遵奉的伦常道德和社会秩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讲,都不过是一种有限的存在,唯其有限,因而才无法对超出这一范围的事物做出准确的判断。特别是当现实的实际状况与按正常价值尺度之要求所产生的结果每每相左时,人们便只好对天长叹,把这最高裁决权拱手让与老天,让与命运了。“老庄之道”的意义在于,它要求人类在大规律、大背景下,来寻找终极和永恒,即把人放进宇宙世界中以后,再去抓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和无限合一,才有永恒可言,才不致患得患失,更不会软弱到将生命前程寄托给命运和鬼神的程度。
为了突破儒家的理论极限,庄子曾设计过一个反差极为悬殊的大、小之境。《庄子·秋水》篇云:
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小,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
这一大一小的强烈对比告诉世人,当人感受到无限并回视人间时,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该是如何渺小和不值一提!社会既已如此,于其间往来运作的人生价值标准又何足道哉!而面对这不值一提的“人间世”,还有什么是非曲直看不开呢?又何苦“为轩冕肆志”、“为穷约趋俗”,甚至慨叹命运、怨天尤人呢?显然,这里的“小”,是指有限,而“大”则是无限的存在。可以说,“老庄之道”的理论体系,便依此而立,即:无限审视有限,有限化解于无限。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叫做“以道观之”和“道通为一”。
那么,究竟是哪些不确定性事物促成了儒家理论极限的形成呢?庄子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庄子·德充符》)这里,有时间上的概念,亦有空间上的概念,更有人事上的纠葛。可这一切,在无限的“道”面前,显然都是稍纵即逝的有限,即:“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空间);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时间);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人事)。”(《庄子·秋水》)结果,无限的“老庄之道”既破了这个“虚”,也破了这个“时”,更破了这个“教”,它实现了“至大无外”的理想,也实现了“道通为一”的夙愿。于是乎,有限世界中形成的理论极限,在无限的世界里便再也无“极”可言。就连儒家“天命论”在民间所造成的迷信,在“老庄之道”的纵横捭阖下,也全部烟消云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老子·六十章》);“夫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
无限,在《老子》、《庄子》和《列子》书中,每每被称作“无极”或“无穷”。《老子·二十八章》说:天下万物,“复归于无极”。有人说,“广成子”即老子,广成子云:“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有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故余将去汝,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庄子·在宥》)在这个意义上,“道”的别称——“无”,则径被解释成“无穷”或“无极”。《庄子·则阳》篇:“无穷无止,言之无也,与物同理”;《列子·汤问》篇载:“殷汤问:‘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不知也。’汤固问,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显然,“无”,作为“无限”的代名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物质实存。程明道说:“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语录》四)可是,对这个无边无际的存在,究竟怎样做才能把握得了,这却难坏了所有的先哲。王弼“圣人体无,无又不可训”(《世说新语·文学》)云者,说的正是这份苦恼。我以为,这与道家哲学物质无限论所产生的新的理论极限,密不可分。如果说,“天命”是儒家诸子宥于“有限”而形成的理论极限,那么,宇宙无限论的难以把握(“大道不称”)这一事实本身,则构成了道家诸子的新的理论极限,这便是后世周敦颐和朱熹所经常讨论的重要命题——“无极而太极”。
如前所述,“无极”一词,出自《老子》第二十八章。而“太极”的名称,则最先始于《易·系辞上》,即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卷八称:“太极,道之极也。”朱子释“太极”,谓“太极”“是无之极”。然此“无”却并非空无,因为“至无之中,乃至有存焉”、“至无之中,乃万物之至有也”。“只是极至更无去处了”、“太极者如屋之有极,天之有极,到这里更没去处。”(均见《语类》卷九十四)这个“没去处”,显然不是行走之穷途,而是逻辑之穷途。庄子在《大宗师》篇中,曾把“道”列诸“太极”之先。对此,朱子门人陈淳之于《北溪字义》中论云:“庄子谓道在太极之先。所谓太极,亦是三才未判浑沦底物,而道又是一个悬空底物,在太极之先,则道与太极分为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极。”邵雍亦称:“道为太极”(《皇极经世书》卷七)而“谓道为太极者,言道即太极,无二理也。”(《北溪字义》)既然“道”就是“太极”,而且如前所述,“道”也是“无极”,那么,由周敦颐最早提出的“无极而太极”的命题,便颇让人费些解释上的周折。有人说,“无极而太极”,是指“太极”之前“复有“无极”,其顺序自应是“无极”在先,“太极”在后。但朱子认为,这不过是对庄子“道”在“太极之先”之记述谬误的一种放大。其实,“无极而太极,不是太极之外,别是无极,……‘无极而太极’此‘而’字轻,无次序故也。”(《语类》卷九十四)此亦如冯友兰所说:“无极、太极,及无极而太极,……统而言之,我们名之曰道。”(《新理学》第九十七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可见,“无极”就是“太极”,无限就是极限。就是“无极”,道家之理论极限,就是“无极”,就是“道”本身。因为无限的“道”也只能以自我为极,故曰“道法自然”。
“无极”之所以就是“太极”,就是道家的理论极限,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是由于对“无限”的无法说明。因为古往今来,任何一位试图对“无限”作出说明的人,恐怕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表述上的巨大困难。困难的原因在于,“无限”(雅斯贝尔斯称为“统摄”,冯友兰称为“全”),指的其实是某种非对象的存在。可当你去思考它时,它就成了你思想的对象。于是,主、客对立产生了,因为这是认识的前提。而一旦它已成为你思想的物,那就必然是分裂之中的存在物。由于分裂是一个本来统一的东西被撕裂开的状态,因此,在这种状态下获得的认识,便肯定不再是囫囵一体的无限。道理很简单,假如这是包容一切的“一”,那么,当我要研究这个“一”的时候,“一”与我便成了相互对待的存在,而“一”与“我”一旦成了相互对待的存在,那么,此时的“一”,便决不再是包容一切意义上的“一”了,因为至少我已经不再包括在此“一”中。与此同理,当你去说明“一”的时候,说明本身便成了“一”的对待物。“一”的无所不包性,自然也要包括你的语言才行,而你若说明它,那么,被说明的对象便也肯定不再是无所不包的“一”了。即:“无限”变成了“有限”,“无”转化成了“有”。
显然,老庄的无限论,亦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以上的苦恼。《老子·一章》就向世人披露了这一苦恼:“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给“无限”起的名字,如果用这个概念来说明,并且可以说明那无所不包的“无限”,那么,这个无限便不成其为“无限”了。因为既然无限无所不包,那就应该包括这个“道”字,而一旦用“道”来说明“无限”,“道”与“无限”便成了相互对待的存在。正因为如此,老子才讲,“道”,说得出的,便不是永恒的“道”;“名”,叫得出的,便不是永恒的“名”。老子为什么要说“道常无名”、“道隐无名”,为什么要强调“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和“希言自然”,恐怕也都是基于以上的苦恼。对此,庄子在认真总结老子思想的同时,更给后人留下了一道最大的难题:“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能知之,此之谓天府。”(《庄子·齐物论》)形成于唐朝中叶的禅宗哲学,历史地承载起这至为艰巨的理论任务。
三、“心法”——禅宗对道家理论极限的超越与被超越
道家的理论极限,实源于把握上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用经验去感受超经验的存在;用语言去陈述超语言的东西。要破除这个悖论,只有一个办法,即抛却感受和陈述的经验、语言前提而直入肯綮。禅宗及其“心法”要妙,即存乎此。
依禅宗的说法,释迦牟尼有一种秘密传道法,称为“密意”或“心法”。这个“密意”或“心法”,在印度经过了二十七代的传授,到梁武帝时,始由达摩传至中国。又经五代传人,始衣钵慧能,是为“六祖”。慧能生前传道的方法,被弟子记录下来,辑成《六祖坛经》。任继愈先生认为,“禅宗在西方的传法世系,恍惚迷离,完全是中国禅学者补造的,不足信。”(《农民禅与文人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九九五年第一期)实际上也确乎如此。一定意义上说,禅宗基本上是由中国人自创的,因为其理论本身乃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顺势发展和继续,这种发展和继续形式中所呈现的突破或超越,也是对前一种哲学所遇到的理论极限而进行的突破与超越。外来哲学的影响,充其量只是助力,而非主力。范文澜先生说:“(慧能)的始祖实际是庄周”(《唐代佛教》第六十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说甚确。
禅宗的立意本旨是“即心即佛”。慧能说:“故知万法,尽在自心”、“识心见性,自成佛道”、“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味。”唯其如此,其传授的方法,也只能是“以心传心”的“心法”。当年慧能受法时,五祖弘忍对他说:“法以心传心,当令自悟。”慧能也说:“迷人口念,智者心行。”(以上均见《六祖坛经》)慧能的弟子神会亦道:“一念相应,便成正觉。”(《神会语录》)它至少道出了禅宗的以下三大特征:1.废止语言,不立文字;2.追求顿悟,废止渐教;3.但求体道,不拘仪式。
道家的最高困惑,是如何以非语言形式来状摹“道”或“无限”。而禅宗的理论,便刚好从这里起步。据《楞伽人法志》载,弘忍大师不喜言说,亦不喜为文,平素总是“萧然静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生不瞩文,而义符玄旨”。所谓“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云者,正得其旨。北宋大师契嵩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中说:“默传,传之至也。……《涅槃》曰:始从鹿野苑,终至跋提河,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谓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义不依语者,以义实而语假也。曰依智不依识者,以智至而识妄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传也。”(《镡津文集》卷三)相传,慧能生来不识文字。可是他极高的悟性,不但使不识文字无法构成他体道的障碍,反倒成了一大天然长处。据《曹溪大师别传》载:“尼将经与读,大师曰:‘不识文字。’尼曰:‘既不识字,如何解释其义?’大师曰:‘佛性之理,非关文字;能解,今不识文字何怪?’”(《续藏经》第二编乙》)甚至有人认为,慧能自谓不识文字,非不识也,乃有意为之。契嵩即谓:“夫至人者,始起于微,自谓不识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说而显道救世,与乎大圣人之云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将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识乎?”(《镡津文集》卷三)同时,历史上,也每每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废止语言,不立文字,可是,禅经所见,又安之而非语言、非文字耶?元朝宗宝云:“或曰:达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卢祖六叶正传,又安用是文字哉?余曰:此经非文字也,达磨单传直指之指也。”(见《普慧大藏经》四本《坛经》合刊本)实际上,如果把禅宗的发展大致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话,那么,前期的弘忍、慧能等创立成长时期的确是主张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而《灯录》、《语录》等文字记录在悟道时的渐居主位,则是化为“五宗”后的后期情形。因此,从体道水平而论,后期往往不及前期。当然,这也并非绝对,临济宗的许多做法,常常可视为反例。
“以心传心”的最高境界,便是禅宗大师们所津津乐道的“拈花”之境了:“妙道虚玄,不可思议,忘言得旨,端可悟明,故世尊分座于多子塔前,拈花于灵山会上。似火与火,以心见心。”(见《普慧大藏经》四本《坛经》合刊本)禅宗自称,佛陀在灵山会上对着百万人众,默然不语,只自轻轻地手拈一枝花,对大众环视一周,人皆不解,唯大弟子迦叶会心,展颜一笑,于是佛祖便肯定只有他获得了佛说的主旨,并当众宣布:“我有无上正法,悉已付嘱摩诃迦叶矣!”(见《镡津文集》卷三)
那么,禅宗最高境界之“心境”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呢?《曹溪大师别传》中有下面一段话:
其年四月八日,大师为大众初开法门曰:“我有法,无名无字,无眼无耳,无身无意,无言无示,无头无尾,无内无外,亦无中间,不去不来,非青黄赤白黑,非有非无,非因非果。”大师问众人:“此是何物?”(《续藏经》第二编乙)
一望便知,这乃是“不可称”、“不可名”的“道”和不能视、不能闻的“混沌”,是“统摄”、“大全”和“一”。在这个“无限”面前,任何语言文字都是不能达意的(“第一义不可说”),任何外在的体道方法和手段都因其有限而无法与无限冥通为一。经验和语言这些道家在体道过程中所欲舍而不可、欲罢而不能的前提条件,却在禅宗的“默传”与“微笑”中得到了化解。而“默传”与“微笑”的凭藉,则是由外在世界的无限内化与内在世界的无限外化之相互交融所形成的“真心一元”。慧能说:“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既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六祖坛经》)禅宗通过“心法”,把道家的“游心于物之初”变成了佛教的“万法归心”。《坛经》说:“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心法”,实现了佛教对道家理论极限的超越。
由以上可见,在无限的意义上,佛、道境界是一致的。但道家的体道过程,却颇费时日,亦非常人之力所及。如庄子曾叙述道:
吾犹守而告之,叁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庄子·大宗师》)
这种对“无限”的思维把握显然是直觉式的,然而,其对永恒的接近却是渐进式的。它与禅宗的体认方法,可谓大相径庭。“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说法表明,禅宗是主张“因缘渐修,佛性顿见”的“顿悟”的。即超越所有过程,达到“瞬间——永恒”。一般认为,禅宗中“北宗”、“南宗”之不同,主要是以了悟之迟速分界,即所谓“南顿北渐”。其实,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弘忍、神秀也都主张顿悟。神秀《观心论》即谓:“悟在须臾,何烦皓首?”《大乘无生方便门》亦云:“一念净心,顿超佛地。”禅宗的这种体认方法,把道家的“过程”变成了佛教的“瞬间”,把道家的“不守即失”的“无限”感受,变成了佛教之“一旦了悟,即为永恒”的终极存在。显然,这是佛教对道家的又一超越。
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才可能对禅宗不拘一格且多彩离奇的悟道方式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首先看“棒喝”。
禅门悟道时,师傅往往对将悟而未悟者当头棒喝,据说这样做可以促其顿悟,达到“心佛一体”之境界。《五灯会元》:“枉费精神施棒喝”;《碧岩八则评唱》:“德山棒,临济喝”;《禅林句集·坤》:“喝大地震动,一棒须弥粉碎”。但是,学界却每每以为此乃禅宗之堕落和低俗化表现,实则不然。理由是:既然第一义不可以语言文字言说,那么,便只好凭借其他语言形式来传递了。拈花会意是心理语言,而这种对肉体的击打与喝斥,则属于促人顿悟的物理语言。它适用于、也只能适用于禅宗式的悟道。尤其当悟得“平常心是道”的时候,则问道者本身,即属该打之列。临济曾经说过:“我二十年在黄檗先师处,三度问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后于大愚处大悟,云:元来黄檗佛法无多子。”(《古尊宿语录》卷四)
其次看所答非所问。
谜语式的“机锋”问答,是禅宗僧徒间经常出现的对话方式。由于很多问题原本就不需要回答,所以,以何作答,便是件无所谓的事。僧问马祖:“‘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曰:‘为止小儿啼’。”(《古尊宿语录》卷一)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这样的对话呢?我以为,这也正是语言文字对禅宗不再具有意义的缘故。既已无意义,那么,答非所问甚至信口胡诌,都不犯教规。语言,在禅宗那里,实成为一种做语言游戏的玩具。
第三看“担水砍柴,无非妙道”。
参禅打坐,是禅宗悟道方法之一种,是有限。既然连语言文字都可弃置不理,那么,经典自然无用,削发为僧、双掌合什又何用之有?慧能说:“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六祖坛经》)其实,由于“即心即佛”,内在的“心”才是一切,因此,无论什么外在形式,都变得无足轻重。“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的意思,实际上是说,既然干什么都对悟道无妨,那么,干什么亦都可以悟道。弘忍即说过:“四仪(行、住、坐、卧)皆是道场,三业(身、口、意)咸为佛事。”(《楞伽人法志》)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但终日吃饭,未曾咬著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终日说事,未曾挂著唇齿,未曾道著一字;终日著衣吃饭,未曾触著一粒米,挂著一缕丝。”(《古尊宿语录》卷三、卷十五)显然,悟道者已进入了灵肉分离的状态:“直向那边会了,却来这里行履”(《古尊宿语录》卷十二)这也是少林禅僧“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之俗令所由以产生的理论根据。既然干什么都不妨碍悟道,那么,自己养活自己的农事劳作,显然是生存下去的最实际选择。这也是对任继愈先生把禅宗归结为“农民禅”的我的解释。
禅宗常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冯友兰先生解释说:“一个人爬竿子,竿子的长有一百尺,爬到了百尺,就是到头了,还怎么往上爬呢?这就需要转语。”(《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第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如果说,禅宗“心法”实现了对道家之“道”的理论极限的超越,那么,超越后的“相对无语”和“拈花而笑”,便成了禅宗爬到了尽头的“百尺竿”,这就是禅宗哲学所难以逾越的理论极限。“更进一步”,只不过体现了它超越自身的愿望而已。然而实际上,禅宗的理论极限,在它形成的一刹那,就已经被其废弃语言、不立文字原则所导致的正常反应所超越,所突破,尽管这是不自觉的。这一切,均体现在必然要下的那个转语上,体现在“出圣入凡”的行为中。因为既然“担水砍柴”无非妙道,那么,出家与否又有何别?既不出家,则“事君事父”又安非妙道?这个转语由宋明理学所完成。在那里,最终实现了对儒、道、佛三家的超越与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