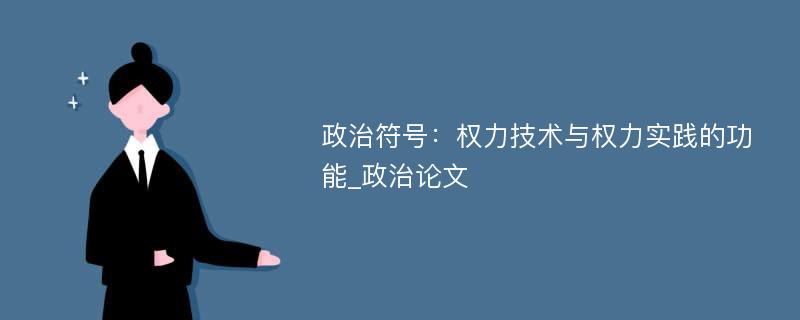
政治象征:作为权力技术和权力实践的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象征论文,政治论文,功能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政治象征的历史性观察表明,几乎所有的政治系统都依赖于一些象征符号、仪式行为或特殊话语的采行来维持其运转。哈罗德·拉斯韦尔曾指出,对政治象征的操纵是各种权力精英驾驭环境、实现其政治目标的4种主要途径之一。反对派群体、尤其是革命精英,由于缺乏物资、制度性暴力和实际措施,则更依赖于象征操纵来进行政治动员(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页)。各类精英使用政治象征的共同目标就是要使其政治行为合理化、权力合法化并试图长久持续。因而,政治象征是权力精英建构权力结构和秩序的一套技术策略,而对它们的运用,则构成一种普遍性的权力实践,其主要的工具性价值表现在4个方面。
政治身份的确定与区分
政治活动是人与人在政治领域中的互动作用,其显著特征在于它的社会性。因而,个人一旦参与政治生活,就不再是其自然之身,而是被赋予了某些政治属性的政治之身。同样,政治团体也必须界定它的组织与活动的边界。而在国际舞台上,每个国家也要创造出专属于自己的特殊符号以标识自己。所有的政治象征表现形式,如被神化的人、圣物、政治仪式、特化的政治语言或阐释方式等等,都作为政治身份确定与区分的重要标准而被广泛地运用。
有关群体起源的神话和传说是各类政治系统中有着强势影响的群体分殊方法。比如,中国人是以“龙的传人”、“炎黄子孙”的神话与传说来表达群体的同一性。多数起源性神话按照继嗣原则来建构,即强调血统的一脉相承和系谱的秩序。通过这种“拟制血亲”机制,政治群体就演变为血缘上的世系群,群体成员由此获得某些共同的身份与特质。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则主要通过对领袖人物的态度来确定其政治身份。支持里根或撒切尔夫人的,通常被认为是现代保守主义者。投票给社会党人密特朗总统的,一般属于左派阵营。而极权主义政体则更偏爱简单的两分法,拥护、忠诚或是反对、疏离元首、领袖,就是识别政治敌友的标准,而且一般是终极性标准。
政治象征物是更易于达成识别和区分目的的另一类标准,因为它们非常直观。在英国十五世纪的王室战争中,交战双方各自佩戴象征两个皇室家族的族徽(红、白两种玫瑰)作为政治忠诚分殊的标志。特定的颜色在被赋予某种政治意义后,也能成为政治象征物。例如,自从法国大革命把最贫穷的农民戴的小红帽作为象征物后,红色就成为世人公认的革命的颜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黄色一直被视为“吉色”或官方钦定的“贵色”,但革命以后,红色取代了这种尊贵位置。
使用某种特定风格的语言,或者宣称接受或信仰某种政治意识形态,也是政治区分的途径。共同的语言往往成为说这种语言的人群政治团结的象征,因而很多民族都努力保持自己语言的独立性。有些非正式组织,如秘密团体则发展出一套只有自己成员才能听懂的行话、暗语。同样,相信某种政治信念的人成为某种主义者,而革命群众的显著特征就是依赖于他们所追随的领袖话语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之身。
当然,有关起源的神话传说和政治意识形态信念,其实都依靠各种仪式活动来维持活力。正如爱弥尔·涂尔干所言,信仰、思想体系并不能单独地存在,唯有依赖于社会仪式才得以表现。仪式是集人、物、语言、行为等多种要素于一体的意义“综合表述”,因而它的表现力最为集中和强烈。通常,不同的政治群体会组织专属于己的仪式,并排斥其它成员的参与。仪式的发动者一般握有大多数人的重要资源,因而能否参与和是否参与仪式就成为性命攸关的事情。这在国家仪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且,在所有的仪式中,参与者的身份地位都被严格地界定。正是通过仪式的重复演练,人们的身份地位得到了反复确认、强化和区分。比如,在义和团中,拳首通过收徒仪式确定了成员之间的身份地位和秩序;通过上法仪式,使团民实现了“人神合一”的身份转换和身份再确认,并使团民意识到自己与其他人的差别。
在上述的各类象征形式中,有时候人们仅仅使用其中之一就足以达到区分的目的。但在多数情况下,则必须采用一组象征办法或其它更精细的标准。
政治沟通
卡尔·多伊奇指出,“沟通是政治的神经。”在政治过程中,个人或团体的政治身份界定只是采取行动的基础,但还不足以使一个政治团体进行有效运作。一个团体的生存和发展是要靠成员之间发展及维系一套正式的且日常化的沟通办法。
通常,政治沟通主要发生在群体内部。一方面是因为成员拥有共同的沟通中介,如共同的象征符号、共同的语言和行为模式,使他们能够沟通;另一方面,群体内沟通旨在加强成员之间在情感上的亲近程度,强化成员间利益一致的共同感觉和增强成员对团体的忠诚,以便群体能在政治系统中采取一致性的行动。对于很多秘密组织而言,比如中国的洪帮、义和团,早期的同盟会,内部沟通就比外部沟通重要得多。只有团体在获得了合法身份后,才更可能转而关注群体外的沟通。
几乎所有的用于界定政治身份的象征办法,同时也是政治沟通的办法。这些沟通交流的象征策略可分为两大类别:言语性沟通方式和非言语性沟通方式。言语性沟通方式主要指成员共同使用的某种特定话语,在现代社会则常常表现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它们通常是由群体内的精英人物所建构并被其追随者所普遍使用,最典型的如无产阶级的导师们所创造的革命性阶级话语、极权主义领袖所发明的那些不允许被违反的原则和命令等。作为沟通的政治话语,不仅担负着政治信息传递的功能,而且也是激励或抑制群体成员情绪的手段。因而,具有特定风格的政治语言和文字可以变成一种高效的政治手段。在雅各宾主义者的法令中,在列宁的革命宣传小册子中都能窥见一斑。
各种象征物品、仪式行为、人的表情、手势和姿态等等都是非言语性沟通手段。其中,政治仪式因常常涉及多种沟通手段的卷入而成为最能激发情感和采取行动的沟通与交往途径。拉斯韦尔就此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政治可以被看成是仪式和神话的堆积。通过仪式和神话,政治实现了它的目标界定、社会整合和问题客观化的功能。”
确立、演示与强化权力和权威
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转依赖于一套明确清晰的权力结构。在权力结构的建构中,关键的是要明确谁是领导者、谁拥有权力,即确立权威。一个政治系统在运用各种象征办法确立权威的同时,也是在向其成员或外界演示和强化权力与权威。
权威一般是由哪些人充任呢?最常见的,是把权威集中在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在有关权威的观念里,高高在上的位置总是附带一些神秘的力量,权威也由此而生。苏联共产党的会场布局是个明显的例子。会场被分隔为主席台和普通参会者的就坐区。领袖总是坐在主席台的第一排正中,其他重要官员分坐在他的两旁和后排;他们面对的就是他们的支持者和崇拜者。“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成为表达领袖崇拜的基本形式。会场仪式确立和强化了权力等级,也进一步强化了政治领袖及他们所拥有的权力。
由于权威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关联,有时候它看起来就显得极为抽象。这时,权威就惟有透过它的象征符号和各种典礼仪式才能看到。像王冠、权杖、玉玺、徽章或巡幸、出访等,就履行着这类功能。文化大革命是使用政治象征符号和仪式行为的登峰造极时期,其功能无疑主要在于建立、演示和强化权力与权威。在效忠性仪式(如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或集体朗读最高指示)中,仪式的中心目标和意义联想都指向政治权威者。这些精心、持久和重复的政治行为被不断模式化,其政治功能的实现过程就是政治权力的实践过程。
政治决策的合法化
通常,一个政治系统确立了内部的权力结构和秩序后,成员就比较清楚权在何处,政出何方。但是,在复杂的政治系统中,政治决策与权力和权威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而常常是一种相互论证的辩证关系:决策所需的是权力,但它的实施则更依赖于权威;错误的政策尽管能够凭藉权力而施行,但会遇到抵制从而削弱权力,而正确的决策往往形成权威,并可能增加权力的份量。因为,权威意指一种合法的权力。政治权力只有在同意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权威。如此,以权力为基础的政治决策只有获得了一种认同后,它才具有被普遍遵守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在大多数政治系统中,政治决策通常是由一个小范围的核心领导层做出。因而要使领导者个别人的意志和见解转化为一种要求人们普遍认同并一体遵守的政治决策,就需要一套有效的合法化途径和手段。各种政治象征形式在寻求决策合法化和权威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一些程式化的语言(通常是官方特定的政治话语)、一些仪式化的政治行为成为这一转化过程的必备要件。
例如,在中国,最明显和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开会”。基于会议代表是由人民选举并代表人民意志的认知前提建构,通过代表对领导层提出的政策的确认,领导层的意志就能合法地被转化为“人民的意志”并由此获得普遍的权威性。虽然外行的公众常常把实现这种转化的会议机制视为是“空洞”的、无意义的“形式”,但政治分析表明,开会尽管是一种仪式化行为,但它并非空洞或无意义,而是传递和展现了仪式所隐含的象征意义,其核心就是使决策合法化和权威化。因而,会议仪式在显示和强化权威的同时,它也是将政治合法性象征归因于“人民”的关键制度。
政治象征作为一种权力技术,在政治过程中主要具有上述4种工具性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功能彼此之间是重叠、交叉的,存在一种互相依存、补充和强化的关系。各种象征形式在实现其功能方面也有强有弱。而且,象征符号和仪式行为等,并不是“一箭定江山”的工具,它们必须在不断的重复运用和演练中,才能达成其主要功能。因此,政治象征不仅是一套权力技术,更重要的,也是权力精英用于演示、强化权力和权威的政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