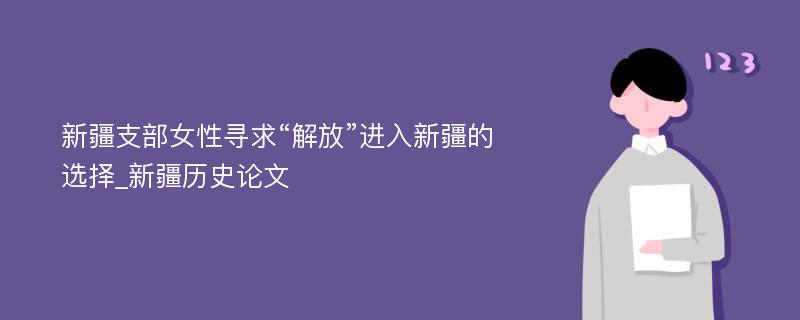
新疆支边妇女寻求“解放”的进疆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277/j.cnki.jcwu.2014.04.014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4)04-0084-05 在新疆石河子军垦博物馆,有这样一段话:“新疆解放后,王震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率领数十万将士建设新疆,屯垦戍边。为使广大官兵扎根边疆,王震上书中央,组织大批妇女进疆,参加边疆建设。1949年从陕西、甘肃青年女学生中征兵。1951年从华北野战军医院征调未婚山东籍女医护军人120人。1950-1952年从湖南征青年女兵8千人;1952-1954年从山东、湖南等地征青年女兵2万人。这些早期进疆的青年妇女,在兵团各条战线发挥聪明才智,奉献着青春和热血,并光荣地成为新疆兵团第一代军垦母亲。” 从1949年开始,湖南、山东等省的青年妇女,成为参军和支边妇女的主体。随后,1954年10月7日,毛泽东发布主席令:“驻新疆的部队官兵奉命集体就地转业,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他们由进疆的原一野一兵团第二、第六军及新疆三区民族军改编的第五军大部,和陶峙岳起义部队改编的第22兵团组成。命令要求基本保持军队的组织形式,执行屯垦戍边任务。”这些以参军、支边等身份进入新疆的妇女,随着部队转业,重新进入新的工作岗位,开始了建设边疆的生产、生活。 长期以来,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这一群特殊的支边妇女处于失语的状态。随着第一代军垦母亲逐渐进入老年,这段历史被遗忘甚至逐渐消逝。本文运用口述史的方法,从妇女经验和视角出发,探究支边妇女所经历的国家政治动员下的进疆选择。本文的新疆支边妇女,指从1949年开始,主要来自山东、湖南等地的女青年、女知识分子。其中,部分妇女是以参军方式进疆的,有军籍;部分妇女则以支边的身份进疆,进入新疆各条劳动战线;还有一部分人,则被安排持家,进入家属队,没有正式工作。 作为妇女解放的呈现面,妇女进疆参军、工作,体现了新中国建设中妇女“半边天”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伴随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成为社会主流话语,人人皆知;妇女被最广泛地动员起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都完成了从家庭领域走向社会化生产的过程。”[1]在革命热情高涨的年代,军人身份、读书、工作等符号,无疑成为巨大的力量,吸引着寻求“解放”的妇女进疆。但是,通过历史史料的呈现,我们可以看到国家20世纪50年代对于妇女大规模进疆的政治动员,无法不与解决部队的婚姻问题相联系。在国家意志影响下,支边妇女选择进疆,然而这一行为并未有效地实现其个体的自我解放。 一、文献回顾 学术界对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运动及妇女生活的分析,多见于延安妇女、知青、农村妇女尤其是“铁姑娘”、城市女工等主体的相关研究,内容涉及妇女身份的变化、社会性别关系、妇女社会角色、妇女解放、妇女劳动等。 学者关于革命时期的妇女叙事,集中于从革命史角度阐释延安时期的“妇女解放”、“革命战争中的革命女人”等宏大的革命叙事。[2]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政治动员在城市和乡村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李从娜的研究指出,新中国建立初期,政府通过思想教育、一齐发动、培养女干部等措施,动员妇女参加土改运动,从而使妇女获得了解放和地位的提高。[3]陈雁以上海宝兴里经历过1958年“大跃进”的妇女为研究对象,提出通过“大跃进”的矫枉过正,在经历了从话语到意识形态的平等后,国家倡导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政策使妇女解放伴随着国家运动的开展而深入人心。[4]但是,一些学者提出,国家权威对于妇女日常生活的渗透,使得以“国家人”身份参加社会生产的妇女并未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何平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分析提出,国家作为形塑的主要力量,推动了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通过改造传统婚姻家庭实现了对家庭中个人的整合控制,动员和整合妇女生产力,将妇女纳入政治生活,动员妇女参政,实现了女性从家庭人到社会人、再到国家人的转变,从而实现了国家权威的被认同和对整个社会的整合和渗透。[5]左际平认为,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城市推行男女平等、男性和女性都是“国家人”的背景下,妇女实现了就业方面的解放和两性义务平等。但是,“国家人”的身份,使男性和女性都无法获得完全的个体意义的解放。[6] 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贺萧等人的研究发现,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劳动动员和行政干预,使农村妇女裹挟到集体的农田劳作中。[7][8]张志永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华北村庄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在革命余波和社会改造的冲击下,妇女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权,提高了家庭地位,父权意识和男权支配地位弱化,传统家庭关系向现代家庭关系过渡。但他同样强调,这个时期妇女地位的提高,主要是党和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妇女政治性解放,因此妇女家庭地位的上升具有不彻底性和不平衡性。[9]高小贤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在“银花赛”的劳动竞赛中农村妇女如何被动员参与棉田管理劳动这一过程,分析在社会动员的背后,国家经济政策和妇女解放策略交织,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制造并维持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1]郭于华以中国农村集体化过程中的一个村庄中的妇女生活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妇女口述的集体化经历、感受和记忆,来探讨这一革命性变迁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践形态。[10]贺萧对陕西农村妇女的口述史研究,发现很多妇女并不把外出劳动当作“解放”,相反,她们通常提得更多的是艰辛和危险。[8] 目前,学者的研究着重考察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而从妇女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的感受和经验叙事出发的研究较少;学者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妇女在革命中是否获得了解放,却忽视了妇女的解放是嵌入在国家政治和历史背景下的。同时,相关支边群体的研究或缺。在国家大规模政治动员背景下的妇女进疆行为及其动员背后的国家意涵,将是本文试图探讨的议题。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口述史的方法对新疆支边妇女进行研究。口述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女性主义者用以提取被忽视的女性的生活经验和故事,希望通过口述故事的补充,将女性的声音引介到历史的中心。学者们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为研究共和国妇女史提供了妇女自己的声音。口述历史可以保存女性的声音,同时,因为独特的资料收集和演绎方法,口述历史更可以“有效地开发不同的女性议题和展示其中的复杂性”。[11] 本文共访谈了12位支边妇女,其年龄均为70岁以上。①这些妇女进疆后的工作包括担当拖拉机手、招待员和进入家属队等。本文将12位受访者分别编码为XJ1至XJ12。尽管这些接受口述访问的支边妇女,属于“历史边缘的人物,他们所陈述的内容大多不存在于既有的文献中”[12],但是,笔者通过查阅历史档案、刊物、书籍、补访相关人员及与受访者内容互相佐证等方式,力求还原真相。而口述历史作为强调主体建构的方法,通过受访者的陈述,我们可以管窥妇女群体自身对于历史的建构性叙事。 三、妇女寻求“解放”的进疆选择 在劳动光荣、走出家庭、妇女解放等成为社会主流话语的20世纪50年代,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动员,使妇女成为劳动力,加入到新中国的生产和建设中来。而这一系列的社会主流话语在国家的宣传和动员下,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积极寻求进步和解放的妇女。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热情高涨的年代,军人身份、读书、工作等符号,无疑成为巨大的力量,吸引着寻求“解放”的妇女进疆。 “参加新疆的支边,参军的事情,我觉得主要当时是与年代有关系,当时国家解放,这个很多地方有自由啊。整个社会,整个学校就是爱国主义、积极主义,就是说搞的轰轰烈烈。我当时就不想上学了,就想工作,想工作这个要有机会啊!当时参军,学校就动员。我们那时候要上初中一年级了。我们就去报名。”(XJ5) 此外,特殊年代下的“不问成分论”的支边,成为经历过土地改革、被划为地富子女等出身不好的妇女“去除出身”的出路。 “1952年我就那时都19岁了,52年要招人,招女兵,就是18岁到25岁未婚青年。我们只知道参加光荣,参加解放军光荣。那旧社会,社会上的这些工作都不叫这些地富子女的人员去做。你看我19岁了,我在城市里连个工作都没有。一个大姑娘家,当时家里要给我找个婆家,我根本不想,我不愿意。哎呀,听说了要招兵团来了,不问成分论。我们的亲戚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一看不问成分论,我嫂子的妹妹、侄女,我们三个都一起报名,就说参军吧,那当然只有这个出路,你再没有什么出路了。……当时招兵的说,新疆需要些女兵,是干啥不知道。我们想女同志当兵去建设边疆,那可以呀,那很高兴呀,所以就报名参加。……一个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再一个呢,就是在家里真是过不下去,真是把你排斥得没有办法。”(XJ3) “地富子女”的政治身份,使这些妇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真正获得“解放”。受访者提及的“出身不好”,使其丧失了“妇女解放”下的工作机会。“不问成分论”的参军则成为妇女寻求自我解放的出路。此外,在重男轻女的农村,妇女很小就作为家庭劳动力种地劳作或操持家务。受访者提及,来新疆参军支边,是为了读书或者改变只能种地嫁人没有未来的命运。 “当时我就在家里干活,后来16岁了新疆来招人。也不用说啥,问了你多大,太小了不要。第二次又去了报的18岁,一听还不行,最后又去了报到20岁,说是20岁也不行。最后一次报的22岁,就要了。他就看名单嘛,一看是22岁,那就可以收。当时家里面不同意,但是我想我这样一直在家里种地,我那时间就想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就背着我的父亲母亲家里人自己悄悄地去报。……因为当时去招人,我们也不知咋回事,就听说像我们这个年龄来了以后可以叫上学。最后才弄清楚了,什么样的让上学呢,我们那儿不是有战争时间牺牲了的战士的一些寡妇,还有的(丈夫)到台湾去的,这些结过婚的有孩子,他们的孩子可以上学,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能上学。招这些结过婚的,这个招不够的话再招大龄的这个女青年。……来了以后我们就上不成学了,因为你是在册的都不属于学生了。但是当时招的时候说是像你们年龄小的可以上学,我们都高兴,说一心都要来。”(XJ1)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妇女解放意识的提高,妇女对于传统的性别角色的反抗意识和意愿逐渐增强。支边动员的参军、上学、工作等许诺,成为妇女摆脱传统家庭角色的出路。在热烈的建设年代,去新疆支边是光荣的事情,也是为人民服务。 “我当时要到新疆来,想法就是建设边疆,就是你让我干啥都可以,总比在家强。”(XJ1) “当时新疆军区下去的人招兵,军区派下去人领队的。当时我们巷里有妇女干部,告诉我们招兵,我们就赶快去跑去报名参军,就这样家里还不知道。报名完,学习完,我才说我要到新疆当兵去了,就这样我妈就哭了不愿意,我爹说你走了家里生产谁来干,我说我不管谁来干。我说我出去以后我挣钱给你们寄回家,我搁家我也不挣钱,我出去挣钱我寄回家来养活你们还不行吗。……我当时想到新疆啊,当兵了,就这个我要为人民服务啊,建设祖国边疆啊,就这么个心。他们再讲得不好我都不动摇,说是新疆找对象瘸子瞎子给你们,都是复员军人转业的残废的。当时就这么说我们,我们都没动摇就到新疆了。一心一意地就觉得出来干公家的事好,那个时候叫公家的事,当兵家里也是军属了,动员时说就是军属了。”(XJ5) 进疆作为妇女寻求解放的主动选择,冲击了传统的家庭格局和两性关系。但是,通过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关于进疆的国家大规模的政治动员,缘起于新疆部队官兵较难解决的婚姻问题。 四、政治动员的进疆缘起——部队婚姻问题 20世纪50年代,地方部队和政府动员妇女参加祖国边疆的经济建设,或以军政干部学校招生等名义,吸引妇女进疆支边。当时的口号包括:“新中国的优秀妇女们,为了祖国富强和人民的利益到祖国边疆去,和新疆人民共同建设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社会!”“妇女们,打破乡土观念、家庭观念,英勇向前到祖国边疆去,积极地参加祖国建设,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奋斗!”等等。 1949年新疆总人口为433.34万人,其中汉族人口29.1万人。新中国建立初期,新疆的性别比是107.4,1953年开始提高并上升到110.2。1950年进驻新疆的解放军官兵有11万人,他们创办军垦农场,兴办现代化工矿企业,后来复员转业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地方工作。当时新疆部队的男女比例是160∶1,而30岁以上未婚男女比例却是300∶1,个别师团的男女比例达到500∶1。[13]新疆起义部队,“平均年龄38岁,98%以上官兵家在内地,96%以上士兵尚未成家。”[14]126、127“为了不影响新疆的稳定和保持少数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惯,王震又给部队下了死命令:‘汉族军人不准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15]21 当时新疆军区解决部队婚姻问题的办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让广大官兵通过写家信的形式自己解决婚姻问题。老家有配偶的可以直接来新疆,使离别多年的夫妻得以团圆;家里没有配偶的,可以让父母、兄弟姐妹、亲戚帮忙介绍一个来新疆,费用由国家负担。《新疆军区政治部关于保障革命军人婚姻的通知》(1951年5月7日)中写道:1950年6月,新疆部队根据总政与内务部的通令,要求全体军人写一封家信,并以师(独立团)为单位,报告本单位的婚姻情况统计数字,其目的就是具体掌握部队婚姻的真实情况。②二是由军委和西北军区往新疆调拨妇女。三是由新疆军区和新疆人民政府出面到内地大量招收妇女进疆。[15]29历史数据显示,1952年进疆的部队家属只有3148人,1952年军委和西北军区调拨和介绍来新疆的有4155人,新疆自己招聘的则有10137人。③姚勇提出,上述三种解决婚姻的办法,第一种只能小范围地解决官兵的婚姻问题,第二种和第三种才是解决的根本办法。尤其是第三种,更能有效解决部队的婚姻问题。[15]29至此,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下的妇女进疆拉开帷幕,进疆的妇女主要来自甘肃、湖南、山东、上海等地。 通过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在国家把新疆的妇女问题列为“先立业,后立家”,将解决新疆部队官兵婚姻问题上升为政治任务的背景下,动员大量妇女进疆。从甘肃、湖南和山东等地以参军和参加经济建设等名义进疆的妇女,成为解决新疆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的承接载体。在寻求“解放”的诉求下,妇女选择进疆。而进疆路上的无军籍、进疆后的家属工、甚至持家,都使部分妇女所寻求的“解放”,成为一种政治动员下的口号。这种政治动员,并没有将解放妇女、争取妇女权利予以优先考虑。国家政治动员下的进疆,赋予了妇女国家和集体革命者和建设者的身份,与此同时,却使其囿于传统的性别角色下。一定程度上而言,妇女进疆并未实现其个体的自我解放。 国家在动员妇女参与生产和劳动建设的同时,以“解放”作为口号来进行政治动员。但是,在“解放”话语背景下的国家建设和边疆建设,并没有将“妇女解放”作为国家的主要目标,在一切为国家的集体主义时期,性别被隐匿在政治动员下。虽然妇女选择进疆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学习、工作的机会而摆脱传统的依附男性的生活,但是国家政治动员下的进疆,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个体意义上的妇女解放。 在国家政治动员下的新疆支边妇女,在妇女解放的话语背景下,部分参加社会劳动,拥有工作,获得了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传统性别文化下的性别关系和地位有所改变。对于参加工作的支边妇女而言,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独立,使其对妇女自身的价值有较高的评价。但是,妇女的角色从“家庭人”到“国家人”的转变,并没有使妇女获得真正的个体意义上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在可能的最大限度内解放了妇女,帮助妇女走出传统家庭,从而跨越了一个旧时代。但它并没有将妇女交还给妇女自己,而是交给了国家,即国家通过‘解放妇女’完成了对妇女的整合控制。”[5]同时,部分妇女进疆,并没有获得参加社会劳动和生产的机会,而是进入家属队和下放持家,原本为“妇女解放”口号下的国家动员的支边和参军行为,却在国家父权制的框架下延续了传统的男性的特权。支边妇女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却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性别等级秩序得到了进一步的固化。 新疆支边,改变了妇女的日常生活,形塑了妇女自身的性别意识,也形成了支边妇女独特的记忆和叙事。而关于妇女解放,更重要的是其个体解放与集体解放的张力,及妇女能动性地寻求和获取的自我解放,希望随着研究的继续和深入,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历史答案。 ①本文访谈为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女性图书馆口述历史项目。 ②参见新疆军区档案馆:《新疆军区政治部关于保障革命军人婚姻的通知》,1951年5月7日。 ③参见新疆军区档案馆:《新疆军区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接收进疆学生、妇女统计》,新疆军区政治部,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