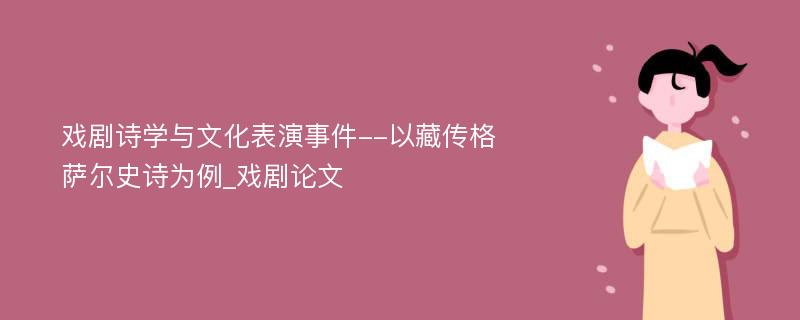
迈向戏剧与文化表演事件的诗学——以藏族《格萨尔》史诗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诗学论文,为例论文,史诗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0-05 文献标识码:A
戏剧家郑正秋认为“戏剧能移人性情,有裨风化”,是指戏剧的教化功能;布莱希特说“只要是好的戏剧就是娱乐的”,是对戏剧娱乐功能的肯定;皮斯卡托创立的“文献纪实剧”,则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具有社会功能。
实际上,格萨尔戏剧似乎是一部“文献纪实剧”,它是由一些事件而生发出来的艺术作品,即纪实性戏剧。这些事件和作品似乎可以说明表演与现实是如何相互贯通渗透的,同时,也可证明表演中所潜在的阐释力,即以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格萨尔》史诗,反映了藏族古代社会交织着的对立性矛盾、竞争性、论争性等因素。同时,史诗还提供了各类社会叙事内容,诸如社会结构的、政治性的、心理的、哲学的和宗教的,甚至方法论方面、物质承载方面的形式。但是它的支配性话语并不仅仅是讲故事和加以回味,它是对崇拜对象的扮演,这种扮演或许是非戏剧的,或许是模仿性质的,但是有助于了解社会生活,具有社会功能。在某些特别情况中,社会生活与戏剧表演具备了一些认同感,并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知识的美学模式。因此,格萨尔史诗是一个特殊的事例,它存在于戏剧性与表演性,而且在诗性叙事中扮演重要角色,从而迈向戏剧与文化表演事件的诗学。
一、角色、象征及其表演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以讲述格萨尔这一理想中的民族英雄人物的坎坷经历和他克敌制胜的非凡业绩而构成了宏大的叙事结构,《天岭卜筮》、《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降伏魔国》、《霍岭大战》、《地狱救母》等许多部故事,虽然独立成篇,但就史诗的整体结构来说,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叙事链条,那就是格萨尔这一天神之子应岭国百姓的祈盼,投胎转世,来到人间,成为岭国国王后,征战四方,在与各种敌对势力的较量和角逐中,靠神力和勇武取胜,造福百姓,最后重返天国的神话故事。格萨尔史诗植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沃土,不仅概括了藏族历史发展的重大阶段和进程,揭示了深邃而广阔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格萨尔剧把这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情节内容重塑为完整的艺术整体,以戏剧表演展示了格萨尔除暴安良、征战四方的事件。这一事件,是以角色扮演并阐释其象征意义。
扮演即表演,“表演”所涵盖的范围很宽,不同的学者在使用上也各有侧重。一般西方学者将其置于“戏剧”的范畴,如特纳强调“社会剧”,包含了社会的多样性和多重性,诸如“世俗的礼仪”和“神圣的礼仪”;戈夫曼把重点置于人们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上;而奥斯汀、斯伯尔等人则侧重于分析表演中的“演说行为”。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彭兆荣教授在《遗产反思与阐释》著述中,则认为“表演”是人类学仪式研究中的重要方面,“表演”的特性具有更为宽广的解释空间,在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宗教学、戏剧学、政治学、文学批评、现代传媒等领域都会涉及。早在1957年,詹森就开始使用“表演”这个概念,并以民俗案例,从民俗理论上讨论“表演”。此后,“表演”呈现出多种阐释。在当代的文化研究中,辛格则使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表演文化”,以概括人类社会文化在演变过程中的诸多历史形态和传统,如部落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以及各类文化主题的表述类型。在辛格的“文化表演”的概念中,包括了他称之为“文化中介”,即一种交流方式,不仅包括人类的语言交流,而且包括非语言性的交流,如歌舞、行为、书法及造型艺术等,或融合了多种艺术要素的交流性民族、族群文化,如印第安文化等。当代最负盛名的仪式研究者,表演人类学家特纳则使用了“社会剧”,以强调仪式的表演性。鲍曼在《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中认为,“表演”的本质是“一种言说的方式”,是“一种交流模式”。
此外,表演还标志着通过对表达行为本身内在品质的现场享受而使经验得以升华的可能性。因此,表演会引起表演行为的特别关注和高度自觉,并允许观众对表述行为和表演者予以特别强烈的关注。
其实,从这个意义上看,“表演”事实上是一种社会空间中的实践,是强调戏剧表演是一种特殊的叙事。
无论表演理论在不同学科和学者那里所阐发的意思和意义有什么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前提,即认可作为表演的仪式具有其交流与交通的特质。换言之,交流与交通构成了仪式的一个基本功能,并通过这一功能作用于社会现实。在西方,表演理论有几个发展脉络,其中有一条脉络来自于语言文学,即诗学的影响。这一学派认为,诗性语言与日常生活的语言不一样,表演属于特殊的语言形式,而且也重视表演与其他的言语方式的差异。格萨尔戏剧表演恰好属于这一类型,它既是诗性语言,又是一种与藏族日常生活语言不同的韵文体。
表演的另一条脉络与仪式更为接近,即强调于“文化表演”,这一脉络发展的学理依据和学术背景直接来自于文化人类学,尤其是法国人类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认为仪式是社会关系的扮演或者说戏剧性的“出演”。
简单地说,格萨尔戏剧就是通过一系列象征符号和一系列象征性行为聚集在一起,戏剧化地展示了藏族部落的社会关系,并达到对社会关系的理解。所以,这些事件就变成了社会力量的象征化力量的象征化展示。《格萨尔》史诗的主题是战争,它的全部内容展示了一场场世俗与神魔的战争场面,它犹如一台回顾历史画面的系列戏剧,英雄、美人、圣哲、魔王、暴君、奸臣等等纷纷登场,形成了一幅幅感人的战争画卷。而史诗中的部落战争场景主要为两个群体:一是天神,以英雄和正直的角色出现;另一个是邪恶的,或者说是非道德的群体,魔王、暴君参与其中,它是前者摧毁的对象。一场场战争成了两个阵营的对峙,这就是善与恶、正确与谬误、正义与非正义永恒冲突的宇宙观在《格萨尔》中的表现。比如,从《降伏魔国》、《霍岭大战》、《降服霍尔》、《岭与姜国》的战争起因看,这几部应该是属于保卫物质财富的战争,从整个史诗的结构上看,这类战争处于全部史诗的前部,为社会关系的变化铺垫了话语权,因此产生了岭国和格萨尔保卫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物质资料之上的远征和讨伐。如北方魔王鲁赞抢走格萨尔的王妃梅萨而爆发了《降伏魔国》的战争,霍尔王趁格萨尔远在北方,举兵犯境并掠夺财宝而爆发了《霍岭大战》等战争。所以,这些事件就变成了社会力量的象征化力量的象征行为展示,成为一种戏剧表演的性质和特征的仪式行为。
这个群体象征善与美,其使命是与丑恶的魔道作斗争,从而向观众表示和表现自己独特的意蕴。这一文化表演事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升华和强化人的情感,所以它具有仪式功能,因为格萨尔戏剧表演的目的既在于功效,又在于娱乐,这就是戏剧。毫无疑问,仪式的表演性质是一种外在形态,这是人们很容易看到和感受到的。同时,从格萨尔剧案例来看,也可以说是从现代人的眼光和知识分类体系去看待格萨尔剧反映了古代或原始民族的行为,即人类祖先的“表演行为”或“表演活动”可能或可以在“仪式/戏剧”之间互相转换的,具有诗学审美特质的。因为,戏剧应当发生于戏剧的目的之外,从“演”的形式形态发生角度说,它来自于摹仿,要“演”就必须摹仿;从本体的动力学发生角度说,“演”本体形成的动力因是本体之外的巫术目的,也即人类实际生存的实用目的。只有巫术目的才是“演”的原发性起因,而摹仿并非是“演”的原发性起因,它也从属于巫术这个原发性动力因。
这就是说,“演”的发生是双线的:一方面是“演”的形态本体由源头、萌芽生长的线索,一方面是本体之外的人类实际生存急迫需求(在此为巫术)的线索。双线发生原理的具体表述形式是:本体形态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历史演进即形态本体发生论,和人类需求的历史演进也即功能本体发生论。其中功能发生论是形态发生论的内在灵魂,因为第一,人类功能需求作为艺术形态本体发生的原因,永远具有动力型的决定力量;第二,只有在确定了功能需求性质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确定艺术的形态本体性质。例如格萨尔剧中的战争,如果我们确定不了格萨尔征战的动机和目的,也就确定不了格萨尔和剧中“扮演”的形态性质。也即是说,在事物的发生阶段,“功能”总是“形态”的主导和灵魂,只有判定它“干什么”,才能确定它“是什么”。格萨尔剧或格萨尔神舞,只从其形貌上看,它似乎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艺术品的那种东西,然而它就不是!因为它当初担负着不是艺术的而是另外的意义和功能;只不过那意义和功能被历史和文化的变迁而淹没,使今人难以查寻却易于误解罢了。“当我们按时间和发展顺序向上溯而按人类进步水平向下看的时候,人类的发明是越早越简单,越早越同人类的基本欲望直接相关。”
乔治·汤姆森在《希腊悲剧诗人与雅典》一书中说:“在原始社会中,所有事物都是神圣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与宗教无关的。所有的活动——吃、喝、耕作、战斗都有着它们适当的程序,就连这种程序也被规定为是神圣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圣的,但最神圣的莫过于“形象”和“替身”;因为它们是实现巫术目的的直接工具和实体,是原始人与超人力量之间的媒介和桥梁,是满足基本欲求的保证。“摹仿”、“扮演”、“戏剧”、“艺术”在本质上是通神的,格萨尔戏剧的发生,就是与通神人的巫术活动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在格萨尔戏剧的产生一节中得到了合理的揭示和解释。恰恰是在于艺术的巫术目的和外在于艺术的生存实用功能,才使得格萨尔戏剧具有了仪式性和宗教性,戏剧扮演实际上成了原始宗教的一种“符号”、“工具”和“手段”。在藏族古代社会,既然巫术效应或神性效应是高于一切的,那么为神圣目的服务的手段就绝不能满足于粗糙的形式。形象的制作越生动、越精确、越逼真、越完美,其通神功能与控制、等值、交感的力量也就越强大。恰恰是艺术之外的力量促使艺术在形式上由粗糙走向完美,使艺术本体,即格萨尔戏剧的扮演、形象和仪式由稚嫩走向成熟。在格萨尔艺术发生阶段,外在功能的力量大于本体自身发展的力量,“功能”大于“本体”,所以格萨尔戏剧的仪式功效是清晰可辨的。实际上,无论是神圣性、程序性、程式性,还是“功能”大于“本体”,在中国古代的“礼”“乐”关系中都可以得到最好地解释与说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礼”不是别的,正是为原始宗教、为巫术、为神、为帝王服务的一整套文化程序。史前艺术的一系列特征正是“礼”的特征。“礼”起于对神的献祭,目的在于神赐。事实上,音乐的发展史也正是从事巫、事神、事君到事人的过程,而中国古代也完全是走的这条路径。原始艺术在本质上正是“以乐礼之”,且“礼”大于“乐”。“礼”的精确性、完美性、程式性,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越来越得到强化,它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宗教性的“礼”的观念越来越精致精细,与之相适应的“乐”(艺术)也变得越来越多样;二是程式性、因袭性、神圣性使“形象”得以完好地接续与保存。格萨尔戏剧不仅如此,而且其形象得以延续。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宗教的神性渐渐消散之后,“形象”得以在神性的控制下独立、游离出来,真正的艺术诞生了。形象、摹仿、扮演逐渐摆脱神性控制,艺术自身之外的功能渐渐消退,形象、摹仿、扮演与“原型”之间的关系由合一、互替、混合、混淆开始分界、分离直到泾渭分明。对于格萨尔戏剧而言,其人物形象的转化过程是角色的扮演——角色象征——“形象”由为神造型向进入了娱人的世俗扮演。因此,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彻底独立了,真正的戏剧的发生学正是人类学,因为每块“标记”都隐藏着一段极其复杂、极其深刻的人类生存史话。
二、格萨尔剧的角色扮演与象征功能
萨尔戏剧的角色扮演是具有象征性的——英雄崇拜,其原型只是由单一的崇尚英武的原始勇士赞歌所构成,这种勇士赞歌亦是诗、乐、舞(浓厚的祭祀仪式)的错综并存的组合形态,其后经过相当漫长的扩充演绎、兼收并蓄的艺术层积累的嬗化,才逐渐达到了史诗在内容上的丰富、厚重、多元化,且日臻完美。
《格萨尔》史诗角色扮演及其象征功能,可从善道与魔道两方面来分析:善道,包含有正义感、为百姓带来安全和美满生活的;魔道,是代表恶势力。莲花生是格萨尔史诗的保护主,其中的英雄为其化身或使者。因此,格萨尔是莲花生的化身——百姓的保护神——英雄人物(主角人物)——神的象征,是代表善道的。在史诗扮演中,其行为模式是神圣保护主传授一种帽子,由一顶特殊帽子具体化了的奥义——解救苦难者。在说唱艺人扮演时,一般头戴这种帽子,这就意味着说唱艺人接受一顶帽子,传授奥义的内容已被启示神强加给了未来的说唱艺人,这便是说唱艺人和普通的歌手之间的区别。史诗的演唱人(使者一类),同时也是因为他将会解释说唱艺人与他表现的史诗中的英雄人物之间的相似关系,因此在格萨尔戏剧中还保留着说唱艺人的说唱扮演形态,也就是说唱艺人用各种不同声音、语气、语调来扮演剧中所有的人物角色。这是一种保护神的象征,因此,他的使命就是消除魔道,解除苦难。善道中还有一些勇士角色扮演,他们一般都是神灵,即护法者、护道者,是英雄格萨尔的将士和随从。还有喇嘛和女性角色扮演,喇嘛一般是启悟者,女性主要是指度母化身。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通灵者,史诗中的通灵者实际上是萨满,他与天地、神灵鬼怪交通,这在格萨尔史诗中贯穿始终。
据考察,在说唱艺人与萨满之间的比较,已经得到明确证实。萨满们是口头英雄文学的卫道士,他们熟悉世系谱、传说和宇宙志,他们都是说唱艺人,其神通性出自神灵在他们耳边低声细语的事实。他们的词汇非常丰富,特别包括作为史诗典型特点的多种隐喻或譬喻,说唱史诗和萨满教赞歌具有同样的特征。“说唱艺人”往往也是萨满,他是自上部(天神或山神)接受其史诗的。至于民间通俗史诗,布里雅特人的萨满文献既包括大量口传内容又包括成文的、土著的和密教的内容。《格萨尔史诗》中的英雄人物(主角人物)变成了萨满文学中的神。我们还将看到,格萨尔和西藏那些神通说唱艺人为了更好地听到声音而都以把一只手伸向耳朵的手姿为特征,他们的帽子和服装也可以与萨满们的这一切相比较。
格萨尔这种古老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藏族部落原始艺术的各种特征,也充分说明说唱艺人的起源。他们的乐器是带有藏式鼓柄和镰刀状鼓槌的铃鼓,说唱艺人完全如同萨满一样,也是从神灵那里接受其知识的人。唱段是向他启示的,他经过了一种秘传的过程。最能引起我们注意的却是他们的奇装异服,他们戴着一种五彩缤纷的锥型帽,上面似乎缀有一些小铃。他们的耳朵上挂有呈展开的扇子状和彩色奇特的装饰,我们在藏地跳神的假面具舞蹈中也常看见此类人物,因此格萨尔说唱人的装饰与跳神这种相似性并非是偶然的。据考察,魔道角色扮演,主要指恶势力的化身,象征违背教义仪轨的暴君、魔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格萨尔》的角色的象征性,还表现在人物形象面具与服饰两方面:
一方面格萨尔的面具造型主要为黄色,在藏传佛教艺术理论中,由于不同的颜色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如白色象征慈祥,像观音、文殊、普贤菩萨的面具多白色;红色象征权势,一般如阎王、司命主、阿弥陀佛的面具都具有这种颜色;蓝色象征威猛、愤怒、杀戮,密宗一些威猛神如金刚手菩萨、马头明王、大威德金刚都以蓝色为其面具的主要颜色。格萨尔面具是金色和黄色的,金色象征财富,黄色代表宗教、教法、佛陀、活佛,法王的面具颜色就有黄色,黄色有时也象征财富。
另一方面,在青海果洛地区,关于格萨尔的帽子形状、装饰和服饰独具特色,蕴含着相关的象征性,典型的格萨尔的帽子的形状是基部为菱形,上面有一个颠倒的顶圆锥状,象征佛塔;左右有两个分开的尖锥,像耳朵形,被称为“驴耳朵”。耳朵尖垂着四色彩带(红、白、黄、蓝),帽尖向后也垂着各种布片与彩带。象征格萨尔的本命神的生命的旗帜,白色象征大白梵天神(即因陀罗),黄色是身体之神格错(年神),红色是岭地的战神,蓝色是龙神祖拉仁钦,花斑色为岭地的杂色居民。帽顶有孔雀翎毛或白腹鹰的羽毛,象征一名英雄。帽子中心有一个白色的铜镜,象征格萨尔是金刚手的化身。其上边有由小铜镜与野猪牙构成的日月符号,象征格萨尔统治世界的力量。左边是一张拉开上弦的弓箭,为格萨尔的铁弓与铁箭。镜子的右边是木马鞍,象征格萨尔对霍尔国王的胜利。无论是格萨尔史诗说唱还是戏剧扮演,格萨尔艺人都摇头带起帽子,因为扮演者以会讲述格萨尔故事为荣。藏民族把会说格萨尔故事的视为神人,是有至高德行的文化人,把表演看成一种特殊的、艺术的交流方式,认为是神授予讲述人才智和表演才能的。讲述人的口头表演,是通过展演荣誉来展示交流能力——特殊技巧和效果成为表演者的具体行动。讲述人在讲述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他们朝着被艺术性地叙述和赞颂的目标,艺术性地展示自己的行为。同时,帮助人们追忆往昔的光荣和荣耀,强化历史的自豪感,起到凝聚族群历史记忆的作用。
正如罗素曾经指出的,在希腊时代“任何地方的原始宗教都是部族的,而非个人的。人们举行一定的仪式,通过交感的魔力以增进部族的利益,尤其是促进植物、动物与人口的繁殖。冬至的时候,一定要祈求太阳不要再减少威力;春天与收获季节也要举行适当的祭礼”。这就是说,巫术式的原始宗教在柏拉图的时代还残留着,巫术式的摹仿也残留着。摹仿或扮演的神性遗留的一个最重要的例证,也许要算作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时代的酒神颂了,而这正是后来戏剧史家所谓的戏剧的母体或希腊悲剧的母体。其实,格萨尔英雄崇拜在本质上也仍然是巫术性的,只是这种仪式“在外观形式上是戏剧性的,那么,它们实质上却是巫术性的。”也就是说,根据巫术的交感原理,其意图是为了确保植物春天再生、动物繁殖,而这些都象征着财富。那么格萨尔的服饰、帽饰……甚至他的骏马都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如同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或巴科克斯是我们最熟知的葡萄树以及葡萄酒的人格化,“对他的狂热的崇奉,通过纵情的舞蹈、激动的音乐和极度的醉酒而表现出来。”可以说,史诗是戏剧(或人类戏剧)发生的源头,只是史诗中未加入对话,是一种戏剧扮演而已。
综上言之,格萨尔史诗故事是关乎于藏族部落安康或者说对社会的某一部族有重要意义,这些部族就是一部分观众,这一事件就是引起观众的注意力,或者说得到收益的。因此,格萨尔故事或者说神话传说、或者说仪式,很明显是将事件以史诗形式叙事的一种戏剧表演行为,让人能够从人物和情节的角度去领会。更重要的是,格萨尔这些事件通过戏剧结构来激发其所表现的社会中的批判性和伦理性的想象。
从格萨尔事件情节、人物和戏剧表演中,不难看出它是一部纪实性戏剧,其题材来源本身就是社会事件,与当时社会紧密相连,并利用史诗这一独特美学手段来诠释古代藏族社会,而这种清晰的表现手法在当下又能帮助公众对格萨尔史诗的认知和理解,因此可以提供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因为格萨尔戏剧表演可以凝聚族群,起到惩戒、凝聚、赋予人们以生命力和欢娱的仪式功能。藏族《格萨尔》史诗是一部藏族社会发展史,或者说是藏族族群的生活画卷。在格萨尔戏剧表演中,它既具有凝聚族群生存与繁衍的特点,又有娱神喻人的仪式功能。
本文正是通过对格萨尔史诗的考察,阐述了藏族戏剧自产生乃至发展至今,对藏族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凝聚族群的作用,这都说明了戏剧叙事与文化表演的关系。因此,格萨尔史诗这一事件迈向了戏剧表演,决定了其史诗口头传统表演所具有的诗学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