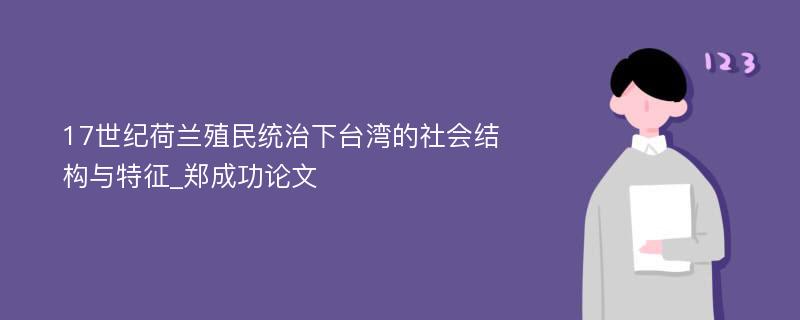
17世纪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结构和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荷兰论文,台湾论文,特征论文,殖民统治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1)03-0085-10
一、前言
荷兰人殖民台湾之前,台湾住民以原住民为主,也有少数汉人居住。例如,明天启初年,颜思齐等人已经在台湾居住。① 1623年11月,荷兰入据台湾之前,两个荷兰商务员(J.Constant和B.Pessaert)奉荷兰舰队司令官莱尔森(C.Reyersen)之命到大员附近萧垄村社探查时,听说有超过1000个汉人居住在台湾各地,跟原住民交换商品为生。② 荷兰人占据大员后,进驻台湾的荷兰人中,虽然公司员工为主,但是家眷和奴隶人数也不少。以1661年5月初被郑成功围困的热兰遮城为例,城内员工为968人,奴隶及其子女为547人,为员工的56.5%;妇女和小儿为218人,为员工的22.5%。③ 由于荷兰官方资料中以公司业务为主,女性和婚姻的资料几乎没有,相关的研究也很少。为了筹划2003年台北故宫举办“十七世纪的台湾、东亚与荷兰”特展,欧兰英(Everlyn Oranje)女士偶然发现保存于雅加达的印度尼西亚国家档案馆的两份资料,《热兰遮城婚姻(1650—1661)登录簿》和《热兰遮城洗礼(1655—1661)登录簿》。韩家宝和郑维中将这些史料编译,于2005年8月出版,使得本文得以利用这些弥足珍贵的数据,将女性和奴隶的讨论纳入文中。④ 17世纪荷兰以基督教立国,规定基督徒不得与异教徒通婚,鼓励基督徒的子女出生后受洗成为基督徒。在台荷兰社会成员的婚姻申请和登记由公司的婚姻家事督导官负责审核、认可和登记。热兰遮城婚姻登记簿中只限于记载热兰遮城市民、公司员工和奴隶基督徒间婚配的记录,没有非基督徒的婚姻资料。由于汉人没有基督徒,因此婚姻登记簿中没有汉人的记录。⑤
台湾原住民、汉人和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不同群体在殖民地构成一个由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组成的社会。本文依次讨论荷据台湾殖民地社会的各类成员,包括公司员工、自由市民、员工眷属、奴隶、台湾原住民和汉人,说明群体间的关系,并分析荷据台湾社会的特性。
二、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
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是在台荷兰社会的主要成员,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类别:商务(包括台湾长官、商务员、会计)、军人、教师和其他职位(包括传教士、医护、技工、仓储、行政等)。由于雇员异动频繁,因此官方文书中并没有总人数的确切统计。驻军的人数记载较多,大致是逐渐增加的:1628年有330人,1636年11月讨伐麻豆社时派出500名白人士兵,1649年为984人,1658年在1000人上下。⑥ 1661年郑成功攻台前后,在台驻军得到巴达维亚补充援军,包括1661年2月樊德朗留下600名士兵,和8月考乌带去的700名士兵,⑦ 最高峰时,台湾荷军可能接近2000人。除了驻军之外,在台其他各类雇员人数也不少。根据1650年—1661年婚姻登记资料分析,军人登记共有62人次,商务、教师和其他职位雇员登记共有96人次,⑧ 超过军人登记次数的一倍半,可见军人之外的公司雇员人数也不少。估计1661年高峰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驻台湾人员(都是男性)应该超过2000人。
从婚姻登录簿的出生地分析,男性181人中,以欧洲出生154人为最多,占85%,其余有印度出生的6人、东南亚出生的3人及台湾出生的4人。⑨ 欧洲出生的男性中,也有很多男性出生在荷兰以外的国家。例如跟台湾原住民女性结婚的德国和比利时裔男性超过20人,大约占台湾原住民女性婚配对象的三分之一。17世纪时荷兰国力强盛,经济繁荣,阿姆斯特丹可能是全世界最好过日子的地方。当时驻荷兰的一个英国领事馆的员工夸张地形容,阿姆斯特丹“穷人收容所像是王子的住家”。即使穷人也很少有人愿意离开荷兰,到远方的殖民地工作。荷兰因此欢迎信奉新教的其他欧洲人加入,宣誓效忠,就等同荷兰公民,可以被派到海外工作。⑩ 欧洲裔的外国人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受到相当的重视,升迁似乎没有受到限制,原籍瑞典的揆一能够升任台湾最后一任长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1)
当时荷兰社会按照官职、血统、法律地位和财产划分社会位阶,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也是如此。(12) 以薪资区分,大约可以将公司雇员分为下列四级:
·最高级:月薪大约在200到300荷盾之间,如最高长官勃尔格(van der Burg)月薪300荷盾,揆一任台湾副长官时月薪200荷盾;(13)
·次高级:月薪在100荷盾左右,如上尉约100荷盾,(14) 牧师约80~140荷盾,(15) 上席商务员、地方官和牧师月薪相当;
·中级:月薪50荷盾左右,如下席商务员约40荷盾,商务员约70荷盾;(16)
·下级:月薪在10到30荷盾间,如士兵8~10荷盾,(17) 1637年麻豆的学校教师比德松(J.Pieterzoon)月薪16荷盾,目加溜湾的西门斯(L.Simons)月薪10荷盾,萧垄的探访传道欧霍福(H.Olhoff)月薪为26荷盾。(18)
公司的最高治理机构是大员议会,基本成员是5名公司的最高级职员,包括台湾长官、副长官、最高阶军官和两名上席商务员。(19) 士兵在公司雇员中阶级最低,薪水只有最高级职员的三十分之一,可是面对汉人居民时则以统治者的姿态出现。例如1646年士兵在赤崁乡下以粗暴的手段检查汉人居民的人头税单,并借机勒索,带走汉人的山羊。官员得知后设法改善,(20) 但是士兵骚扰汉人居民的情况并没有改进。1651年10月10日,几个汉人长老再次到大员议会抱怨此事。(21) 派驻原住民村社的学校教师也时常欺负原住民。1654年一份东印度事务报告中谴责教师的恶劣行径,对于原住民能够忍受这样的虐待而不起而反抗感到吃惊。(22) 虽然荷兰士兵和学校教师在荷兰社会中地位不高,风评不佳,可是因为他们代表统治阶级驻扎在原住民村社中,因此跟台湾原住民通婚的案例很多。
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驻台湾的员工位阶和薪资上下差异很大。由于公司员工都是殖民地的统治阶层,因此即使公司最下级员工也可以肆意地欺负身居被统治阶层的汉人居民和原住民。
三、自由市民
台湾的男性自由市民人数很少,从荷兰文件零星的记载推测,至多只有数十人。荷兰自由市民娶原住民为妻有6个案例,比传教士还多。所谓的“自由市民”(burghers),简称“市民”,是在殖民地中生活,但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的荷兰人。台湾的自由市民多半是跟公司合约期满后,留在台湾生活的前公司雇员,从事贸易,或者提供服务,例如,1624年有个喇叭手自由人高义肯斯(Meeus Goijkens),计划回到巴达维亚去,高义肯斯同意留下他的奴隶在台,由公司付费,为公司工作一年;(23) 商人瑟基门(Direk Segerman)于1644年5月曾经乘他的舢板到台湾南部贸易;商人费尔玫尔(Nicholas Vermeer),1655年11月派一条戎克船到马六甲交易;(24) 自由人泥水匠西努(Willem Cnoop)于1643年3月10日,跟随公司的上席商务员到新港视察牧师待修的房子。(25) 这几个例子说明台湾的自由市民从事不同职业,拥有奴仆,有权决定留在台湾,或者离开。由于自由市民时常到台湾各地贸易,因此接触到原住民的机会较多,增加了跟原住民妇女的通婚机会。
自由市民在殖民地的地位很高。大员议会辖下有四个议会,分别掌理婚姻家事、孤寡、教务和法务,由公司官员和自由市民合组,(26) 可见自由市民的地位相当于公司的中高级官员。台湾的自由市民人数很少,却得以参与殖民地政府工作。相较之下,汉人居民在荷据末期超过三万人,负担绝大部分税捐,但是却没有参政权,只有少数汉人“头家”得以为殖民地提供咨询,地位明显低于自由市民。汉人居民是不折不扣的被统治者,将在第七节讨论。
台湾另外一类自由市民是从小被荷兰人收养教育的台湾原住民孩童,多半是公司讨伐原住民之后带回的孤儿。例如1645年公司到北部的大肚王(Quataongh)讨伐,捉获15个儿童,连同先前在麻里麻仑(Varorolangh)捉获的3个儿童,都被分配到荷兰人家中做童仆。(27) 在荷兰家庭中成长人数最多的是小琉球的孤儿,总共有30多人,接受荷兰文化,成为基督徒,被公司称为“福尔摩莎裔荷兰自由市民”。(28) 这将于第六节讨论。
总之,荷据台湾的自由市民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在荷兰社会中地位高,可以参与治理殖民地,是荷兰社会中重要的成员。
四、员工的眷属
荷据末期荷兰驻台员工眷属人数估计在300人以上,包括1661年5月初,被郑成功围困的热兰遮城内眷属218人。另外一批荷兰人包括30个妇女从北部乘船逃亡,于6月抵达长崎。(29) 员工眷属来自不同的地方,参考1650年—1661年婚姻记录中的171个妇女,以台湾出生的最多,占39.8%(68人),这将于第六节讨论;其他依次为欧洲出生占21%(36人),印度出生占16.4%(28人),和东南亚出生的占14.6%(25人)。(30)
绝大多数欧洲裔的女性应该是以员工眷属的身份抵台。例如海伦娜(Helena Hambroex)于1659年1月5日跟公司首席助理柏区(J.Burch)结婚,他们的女儿安玛丽亚(Anne-Maria)于1660年2月8日受洗时,揆一女士(Helena Coijets)见证。(31) 从姓氏判断,揆一女士应该是揆一长官的家属,而海伦娜应该是牧师汉布洛克(A.Hambroek,1648年—1661年驻台)的女儿。1661年,汉布洛克牧师及妻儿被郑成功俘虏后,受命到热兰遮城劝降,揆一要他留在城堡中,他住在城堡中两个女儿也苦苦哀求他留下,但是汉布洛克牧师还是返回郑成功处,告知荷兰人拒降,因此被害。据说,汉布洛克另外有一个女儿被郑成功纳入后宫。(32)
有些长期在台工作的欧洲裔雇员的子女在台湾出生成婚。例如,在台湾服务25年的佩德尔上尉(Thomas Pedel)有三个女儿都是在台湾出生。佩德尔1636年已经在魍港担任队长,1645年升任上尉,(33) 1654年代表军方出任大员议会议员。(34) 1661年4月郑军围困热兰遮城时,佩德尔出城迎战阵亡,《从征实录》中也有记载。(35) 根据婚姻登记簿资料,佩德尔三个出生在大员的女儿萨拉(Sara)、伊莉萨白(Elisabeth)和法兰西娜(Francina),分别在1655年8月12日、1659年11月7日和1660年9月2日在台湾出嫁。前两个女儿的新生儿受洗时,都是长官揆一做见证。第三个女儿的孩子在1661年7月3日受洗时,热兰遮堡已经被郑成功军队围困了两个多月,佩德尔上尉已经阵亡,揆一没有出席见证。见证人是佩督的儿子威廉(Willem)和女儿萨拉。(36) 威廉华语流利(可能是闽南语),在热兰遮城被郑军围困后,于1661年5月3日随同两位荷兰谈判代表去面见郑成功,担任翻译工作。(37) 威廉可能也是出生在台湾。
印度和东南亚妇女占结婚登记女性30%以上,居台人数可能比欧洲妇女还多,大部分应该是以员工家属身份抵台。由于当时荷兰社会以男性为中心,女性没有谋生能力,只能在家负担家务,依赖父亲或丈夫生活,丈夫去世后,需要再嫁。1651年之中就有5个印度或东南亚孀妇登记再婚,其中有些可能是以员工妻子身份抵台。也有新婚妇女身份为初婚的“少女”,可能是员工的子女。婚姻登录簿中有9个印度或东南亚男性,其中职位较高的是任会计的印度普利卡人莫里纽斯(Pieter Molineus),和任下席商务员的印度马苏利帕南人米尔(J.Meere),米尔娶佩德尔上尉女儿伊莉萨白为妻,是少有的欧洲裔妇女嫁给亚洲人的案例。(38)
1655年—1661年洗礼登录簿中,在不到六年内,热兰遮城附近荷兰社会出生婴儿总计139人,平均每年约24人。荷兰人统治台湾总共38年,如果只计算荷据后期的30年,在台湾出生的荷兰人后代应该超过700人,其中包括相当比例的台湾原住民和欧洲混血后代。台湾原住民中有荷兰后裔应该是没有疑问的。(39) 到荷据后期,应该已经有接近成年的混血后代,可是相关记载却很少。1657年5月6日有一个混血少年詹斯(I.Janss)悔罪并宣誓恪遵戒律生活后,接受洗礼,被指派为理发师。记录中说明因为詹斯是“荷兰人父亲与爪哇人母亲所产下的孩子,应在此受教育”,(40) 说明荷兰人觉得有责任教育荷兰人混血后裔。台湾原住民女性、荷兰人混血后裔的教育和生活的资料则尚待发掘。
眷属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对长期驻台的荷兰人是一个重要的精神依持,是在台荷兰人社会一个重要的群体。
五、奴隶
1661年5月初,热兰遮城被郑成功围困时,城内人员共有1733人,其中奴隶及其子女547人,占31.6%。(41) 可见奴隶是当时荷兰社会重要的组成分子。有些奴隶属于公司,例如,1622年巴城议会决定派一支12艘船的舰队前往对岸大陆打开贸易,“配备1000名荷兰人,和150名奴仆”。(42) 地位较高的官员也有相当多的私人奴隶。例如,普罗文萨城堡投降郑军的荷兰人主管于1661年10月28日被郑成功遣送到大陆。同行的共有四个家庭,包括地方官法兰廷、牧师李奥纳、两个测量师,总计23人,随行的奴隶和他们的孩子高达13人,比例相当高。(43) 驻守在原住民村社的一些荷兰人也拥有奴隶,1661年5月12日,一批驻在原住民村社的白人(计140人)带了他们的男女奴隶投降郑成功。荷兰人投降后,长官揆一想将赤崁、新港等地的奴隶一并带到巴达维亚,郑成功只允许带走热兰遮城中的奴隶。(44) 由此可见荷兰人相当重视奴隶,可能视为他们重要的资产。
当时荷兰虽然已经开始在非洲介入黑奴买卖,但是在亚洲奴隶的来源多半掳获自敌对的所谓“异教徒”。例如1623年莱尔森率舰队在中国沿海胁迫打开贸易时,到处捕捉无辜的百姓。1623年4月17日截获3条帆船,捉获800名中国人,5月11日,截夺一条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再俘虏200名中国人。这次行动一共捕捉了1150名中国百姓,送到澎湖修筑城堡,其中一半因水土不服和劳累过度而死亡,幸存的571人被送到巴城,到达巴城时只有98人存活,65人又因饮水中毒丧生,最后留在巴达维亚存活的只剩下33人。(45) 也有不服荷兰人的台湾原住民被俘为奴。例如,1640年3月台湾长官给巴城总督的报告中,提到驻扎在台湾东部的荷兰人韦斯林(Wesselingh)带了士兵和卑南原住民盟友,到里漏(Linauw,今花莲的吉安)探寻金矿。由于双方语言不通,发生冲突,荷兰一方开火,杀死所有四五百名里漏村民,只俘虏9个妇女和孩童,向他们学习当地语言。(46)
奴隶地位低下,类似公司的家畜。由于对奴隶罚款或劳役都没有意义,因此公司对奴隶的惩罚都是加诸肉体的痛苦,并公开执行。1643年4月6日布告,规定逃走的奴隶被捉回后需接受鞭刑、烙刑、削去双耳、终身系锁链服劳役等惩罚。(47)
在台湾的奴隶也有受洗的记录。例如阿尔凡女士(Van Alphen)的女奴玛丽亚于1657年7月12日受洗成为基督徒。男女奴隶都有登记结婚的案例。例如1661年3月24日,公司助理西比尔(Hans Sibeers)的两个奴隶弗朗西斯(Francis Nonnes,男,出生于鸡笼)和玛格丽塔(Margrita,女,马六甲人)登记结婚。(48) 玛格丽塔可能来自敌对的马来部落,而弗朗西斯出生于鸡笼,应该是荷兰人带到台湾的奴隶之子。
按照当时荷兰社会习惯,一旦成为奴隶则世代为奴,不得翻身,只有成为基督徒后才有可能成为自由人,因为奴役“异教徒”理所当然,奴役基督徒则不符基督教义。为了解脱枷锁,成为自由人,17世纪荷兰的纽约殖民地的黑奴都极力争取成为基督徒。(49) 但是从台湾的记录看来,弗朗西斯和玛格丽塔和其他几个案例,登记结婚时必定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仍然维持奴隶的身份。由此看来,在台的奴隶信奉基督教以后,依然不能获得自由,进入荷兰人社会。
六、台湾原住民
台湾原住民是荷据时期人数最多的族群。根据荷兰人的调查,1650年高峰时期原住民人口总数达到68657人。(50) 如果加上居住在荷兰人控制以外地区的人口,荷据时期原住民人数可能超过10万人。荷兰人据台之初,曾经于1625年1月以15匹坎甘布(cangan)的代价向新港村购买一块赤崁的土地。(51) 但是1635年11月荷兰人将武力强大的麻豆社打败后,麻豆社同意“转让麻豆社及其附近土地给荷兰政府”后,(52) 正式改变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土地政策,要求每一个归顺的原住民村庄承认荷兰政府对台湾土地的主权。1636年2月22日,22个原住民村社长老到新港,将他们的土地“奉献”给荷兰政府。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为台湾原住民的统治者。(53)
荷兰人积极向原住民传教,大员附近的新港、萧垄、麻豆、目加溜、大目降和大武垄等西拉雅族原住民,是荷兰人传教的重点地区。1636年—1638年,荷兰人陆续在这些村社开办学校,教导男女童基督教义,1643年培养了50名原住民教师,驻扎该六村社。(54) 为了强行传播基督教,1641年12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牧师的请求下将大员附近原住民村社的女祭司放逐至诸罗山地区。(55) 1652年荷兰人才同意被放逐的女祭司回到原村社,原先被放逐的250名女祭司中,只有48名活着回去。(56) 1643年台湾宗教议会报告阿姆斯特丹教区,传教成果丰硕,尤罗伯牧师(R.Junius)已经为6个村落的5400人洗礼。(57)
1627年8月,甘治士牧师(G.Candidius)抵台传教,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后,就发现未婚牧师能够娶台湾原住民为妻更好。1629年2月1日,甘治士致函巴达维亚总督,要求回国,建议总督指派一位有能力的牧师接替,“要终身住在这里,并与新港妇女结婚”。(58) 驻巴达维亚的荷兰统治当局也广泛支持跟原住民通婚,于1629年指示大员评议会:“如果公司雇员愿意跟新港或者其他原住民结婚,不要反对,让他们结婚,希望这样上帝会给我们越来越多的祝福”。(59) 其原因是荷兰人观察到在葡萄牙统治时期安汶出生的欧洲人混血儿对欧洲殖民当局忠诚,可以增进公司的安全保障。(60)
在台荷兰人男多女少,殖民地当局又鼓励荷兰人跟原住民通婚,台湾原住民改信基督教的人数相当多,成为基督徒的原住民女性应该是荷兰人就近的婚配对象。可是荷据后期11年之间,嫁给荷兰人的原住民女性只有60人次。除了小琉球人的27人次(45%)居首,是特殊案例之外,大员附近西拉雅六村社居次,共19人次。(61) 西拉雅六村社是荷兰人的重点传教地区,在荷据末期跟荷兰人通婚案例平均一年不到两起,而且目加溜湾社连一个婚配的案例都没有,说明两个事实:第一,两个族群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隔阂,通婚只是极为少数的例外;第二,荷兰人报告的传教成果可能过分夸大。
小琉球是一个很特别的族群,在荷据台湾结束以后,就从历史中消失。原因是1636年荷兰人大举进攻小琉球,将岛民自小琉球岛迁出,男性岛民被送到巴达维亚做苦工,女性岛民被分配居住到新港村。此外,还前后两次将38个小琉球孩童分配到荷兰人家庭中做仆人,以荷兰方式养育,被荷兰人接受为“优秀的国民”。(62) 小琉球妇女除外,约三分之二的台湾原住民妇女婚配对象是低阶的士兵或教师(33人次中的21人次)。小琉球妇女婚配对象的职位较高,大约三分之二职位比士兵或教师为高。原住民妇女婚配对象中职位最高的可能是南区政务官欧拉留斯(J.Olarios),他的妻子是小琉球人。(63) 可见这些小琉球妇女融入荷兰社会的程度最高。
台湾原住民男性在婚姻登录簿登记的三个案例中,都是小琉球人。其中一个是公司士兵克罗克(P.Klock),于1661年跟新港少女丽投(M.Littouw)结婚,两人都是配偶去世后再婚。另外两个案例都是公司士兵法其奥(Vagiauw),他于1658年2月17日,跟印度(克罗曼德尔)人凯瑟琳娜(Catharina)结婚,丧妻后,于1661年1月30日娶来自孟加拉湾的安妮卡(Annica)为妻。(64) 法其奥在1636年荷兰人大举进攻小琉球时是个青年,被捕后很快学会了新港语,于1636年9月随荷兰军队到小琉球协助围捕余下的岛民。(65) 可能由于法其奥学习能力强,得以被公司雇用为士兵,融入荷兰社会。
根据高登(Milton Gordon)提出的族群融合的观点,同化包含了七个层面:文化的、心理的(认同)、社会的(结构)、态度的(没有偏见)、行为的(没有歧视)、公民的(没有价值和权力的冲突)和生物的(通婚),其中通婚最难达到,是“同化的最后阶段”。根据这个观点,这群在荷兰家庭生长的小琉球人是跟荷兰人同化程度最高的台湾原住民。(66)
台湾原住民跟荷兰人通婚后被接受为荷兰社会成员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原住民,即使成为基督徒,仍然是被统治者,只能留在原村社中,(67) 遵守荷兰人立下的重重限制。欧洲人的种族歧视在15世纪西、葡向欧洲以外扩张时就开始形成。当时有欧洲学者根据柏拉图的人性优劣论和天然奴隶论,证明美洲原住民是天生的劣等人,优等的西班牙人享有天然的“宗主权”和“征服权”,有义务去征服印第安人。(68) 其他西欧国家,包括荷兰,为了掠夺世界各地的资源,也乐于沿用种族歧视的论述,以合理化对原住民的压榨行为。
七、汉人居民
汉人居民对大员商馆很重要,荷据末期人数估计超过三万人,仅次于原住民。(69) 荷兰人无论在农渔业、转口贸易、市镇建设和驻台荷兰人的衣食住行等,都需要依赖汉人。荷兰人非常了解汉人对大员商馆的重要性。例如,台湾长官普特曼斯于1629年9月15日写信给阿姆斯特丹商会(chamber),建议“从爪哇、巴厘岛等地送20到30个女奴隶到台湾,卖给中国人”,以吸引汉人移居大员。(70) 随着汉人移民增加,台湾开垦收到成效,荷兰人陆续强征各种税捐,如人头税、渔捞税、稻米十一税、屠宰税等项目。这些内地诸税在17世纪40年代逐渐增加,到1650年达到接近40万盾的高峰,其后虽然下降,依然维持在20万~30万盾的水平,对殖民地当局是一个比贸易稳定的收入,到了1655年甚至超过贸易收入,成为殖民地政府非常重要的财源。(71) 可以说没有汉人居民的协助,荷兰人不可能成功地将台湾建设成为一个获利的贸易基地。
美国的安德瑞德(Tonio Andrade)提出17世纪荷兰人和汉人“共同殖民”(co-colonization)台湾的说法。安德瑞德的理由是东印度公司建立行政机构,提供免费土地、税捐减免和其他的补助,制服原住民,阻挡海盗,建立民政和警察机构,将台湾打造成为一个更合适的经商环境,吸引拓荒者渡海前去;汉人移民则为殖民地政府提供开荒、打渔、猎鹿、伐木、造屋、修路、劳务等,繁荣台湾的经济。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经营为汉人统治台湾铺路。(72) 比利时的韩家宝(Pol Heyns)也附和“共同殖民”的说法,认为“当时的汉人不一定居于被剥削者的地位,反而可能成为该合作关系下的共同受益者”。(73) 本文认为这个“共同殖民”的说法是错误的,荷据时期汉人居民明显地被荷兰人统治和受到剥削。试举几个例子说明如下:
荷据末期内地诸税收入日益重要,其中人头税是最重要的税收来源,1656年、1657年均占内地诸税的一半以上。(74) 根据殖民政府规定,台湾居民中只有“我方辖下所有中国人”需要缴纳人头税。欧洲裔自由市民及员工家眷均不需缴纳,明显地剥削汉人居民。再如,1636年3月31日规定:“所有中国人不得拒绝公司征用舢板执勤出航”;1641年6月5日规定:“未经我方发放许可证,所有中国人均不得与任何地方、港口或海湾与本岛当地居民从事交易”。(75) 汉人居民的婚姻也受到限制。殖民地规定,只有基督徒,或者至少需要接受基督教育,才可以跟原住民妇女结婚。(76) 在1650年—1661年热兰遮城的婚姻登记簿中,完全没有汉人。(77)
所谓“提供免费土地”更是谬误。荷据台湾以前,本来就有许多无主土地,可以免费开垦,荷兰人本没有台湾土地的所有权,哪里有资格提供土地给汉人。所谓“税捐减免”一说也难以令人信服,税捐是荷据台湾以后强加给汉人的,本来不需缴纳任何税捐的汉人在荷据后被迫纳税,哪里谈得上是好处。在收成不好的时期,汉人农人和承包人亏损累累,濒临破产,荷兰人减少本来不应征收的税捐,为的是怕杀鸡取卵,断了日后的财源,而不是为了汉人居民利益着想。
汉人居民也没有参政权。殖民地法令由荷兰人订立,汉人唯有遵行。以村社包税制度为例,首先,无论制度的设计、建立、实施和监督都是荷兰人一手主导,汉人没有机会参与法令制定,贡献意见,维护自己的权益。其次,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武力压制,汉人和原住民都没有不参加村社包税制度的权利。为了在殖民地生存,汉人和原住民只有加入,让荷兰人坐享厚利。
由于汉人在大员和赤崁人口占绝大多数,为了管理方便,公司指定10个左右汉人长老(Cabessa)跟汉人居民沟通。长老没有清楚的任期和职权,不是一个正式的职位,只是作为双方沟通的桥梁。(78) 1644年殖民政府指定3位汉人长老和4位荷兰人参加市政法庭审理跟汉人有关的民事小案件,是汉人在殖民地政府中担任的唯一比较正式的职位。(79) 这个法庭实际组成后只有两名汉人委员Joctaij和Chako。(80) 1647年12月底法庭重组,荷兰人增加为7人,汉人维持2人,为商人Boyko和Lacco。(81) 1653年在首任地方官(Landdrost)胡格兰(Albert Hoogland)的建议下,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在赤崁设立一座法庭,(82) 由两名高级市政委员会成员轮流担任法官,仍然只有两名汉人长老参加。(83) 汉人代表居于少数,只参与审理民事小案件,提供咨询意见,参与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说明虽然荷兰人将汉人视为重要的事业伙伴,但是荷兰人绝对处于统治者的地位,压榨汉人居民,“共同殖民”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殖民地内歧视汉人的做法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主张普世的一神论,基督教是全人类唯一的真正宗教,全人类都应该接受基督信仰,因此以“我们基督徒”对“他们异教徒”的“二分法”看世界。(84) 他们的逻辑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比“他们异教徒”优越,因此有权享受更好的待遇;汉人是“异教徒”,没有受到神的眷顾,因此不能成为“自由市民”,不必尊重他们的权益,压榨他们为基督徒或公司谋利是合理的。这种“二分法”的世界观,反映的是荷兰殖民社会对非基督徒的宗教歧视。
八、小结
综合以上所述,17世纪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首先,它是一个阶级不平等的社会,统治阶层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员工、“自由市民”和眷属,以荷兰人为主,欧洲人占绝大多数。被统治阶层有汉人、台湾原住民和荷兰人的奴隶。其次,它是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女性不能出外工作,没有谋生能力,一辈子只能做男性的家属。再者,它是一个宗教不平等的社会,独尊基督教,唯有基督徒才能进入荷兰人社会。基督徒享有政治和生活上的特权,中国有自己悠长深厚的文化,没有人接受基督信仰,因此不能得到等同荷兰人的地位,只能处于被压榨和被统治的阶层。最后,它是一个种族不平等的社会,由于台湾原住民不是欧洲人,即使成为基督徒,还是不能得到等同基督徒的地位,大多数原住民仍然属于被统治阶级,受到荷兰人的重重限制。只有极少数跟荷兰人通婚,或者在荷兰家庭中成长的原住民才被接受成为“自由市民”,进入荷兰人社会。
注释:
① “台湾在支那东南海中,古无闻焉。明天启初,海澄人颜振泉聚众据之”。见市村赞次郎编:《郑氏关系文书》,附录“海外异传”,台湾文献丛刊第69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第73页。
②(51)(59)(70) L.Blusse,N.Everts & E.Frech.The Formosan Encounter Vol.I,台北:顺益原住民博物馆,1999年,第21页,第39—42页,第149页,第158—159页。
③(41) 村上直次郎编译:《巴达维亚城日记(三)》,程大学译,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0年,第291页。
④ 韩家宝,郑维中译著:《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曹永和序”,台北:曹永和文教基金会,2005年,第xvi页。
⑤⑧(19)(30)(40)(63)(77) 韩家宝,郑维中译著:《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第64—67页,第61—63页,第57页,第269—315页,第373页,第269—315页,第65页。
⑥ 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1624—1662》,台北:联经出版社,2000年,第77页,第173页,第509页。
⑦ C.E.S.:《被忽视的福尔摩莎》,见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0—141、168—171页。
⑨ 韩家宝,郑维中译著:《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第61—64页,第269—315页。
⑩ Russell Shorto.The Island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New York:Random House,2004,pp.40-41.
(11)(22)(42) 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1624—1662》,第554页,第393页,第7页。
(12) 郑维中:《荷兰时代台湾社会》,台北:前卫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第312页。
(13) 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1624—1662》,第177页,第491页。
(14)(17)(71)(74) 中村孝志:《荷兰时代台湾史研究(上)》,吴密察、翁佳音、许贤瑶编译,台北:稻乡出版社,1997年,第335页,第335页,第322—326页,第319页。
(15) 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编译:《荷据下的福尔摩莎》,李雄辉中译,台北:前卫出版社,2003年,第111页,第141页。1630年甘治士牧师的月薪是84荷盾,1641年尤罗伯(R.Junius)月薪140荷盾。
(16) Tonio Andrade.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Dutch,Spanish,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ovember 2008,Appendix A.
(18)(34)(57) 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编译:《荷据下的福尔摩莎》,第233页,第428—429页,第279页。
(20)(25)(81) 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二)》,台南:台南市政府,2002年,第509页,第53页,第700页。
(21) 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三)》,台南:台南市政府,2003年,第268页。
(23) 江树生译注:《荷兰台湾长官致巴达维亚总督书信集》,台北:南天书局,2007年,第99页。
(24) 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三)》,第267页,第313页。
(26) 韩家宝、郑维中译著:《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第52页,第56—59页。大员议会拥有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由台湾长官、副长官、最高阶军官和两位上级商务员等5人组成。
(27)(46)(53)(55)(65) L.Blusse,N.Everts.The Formosan Encounter Vol.II,台北:顺益原住民博物馆,2000年,第542页,第253页,第37页,第276页,第96—97页。
(28)(60) Chiu,Hsin-hui.The Colonial“Civilizing Process”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The Netherland:Leiden University,2007,p.147,pp.145-146.
(29) 村上直次郎编译:《巴达维亚城日记(三)》,程大学译,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0年,第291页,第324页。热兰遮城被郑成功围困时城内人员共有1733人。乘船逃到日本共有300个荷兰人。
(31) 韩家宝、郑维中译著:《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第306页,第383页。
(32) 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编译:《荷据下的福尔摩莎》,第115—119页,第476页,第567页。
(33)(52) 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一)》,台南:台南市政府,1999年,2002年,第273页,第222页。
(35) 杨英撰:《从征实录》,台湾文献丛刊第32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年,第187页。佩德尔上尉被称为“拔鬼仔”。“初三日,宣毅前镇□官兵札营北线尾,夷长揆一城上见我北线尾官兵未备,遣战将拔鬼仔率鸟铳兵数百前来冲□,被宣毅前镇督率向敌一鼓而歼,夷将拔鬼仔战死阵中,余夷被杀殆尽”。
(36) 韩家宝、郑维中译著:《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第289页,第308页,第313页,第370页,第386页,第389页。
(37) C.E.S.:《被忽视的福尔摩莎》,第151页,第207页。
(38) 韩家宝、郑维中译著:《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第272—274页,第281页,第296页,第308页。
(39) 韩家宝、郑维中译著:《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第365—389页。登记日期自1655年10月24日到1661年7月14日。
(43) 江树生译注:《梅氏日记》,台北:汉声杂志社出版,2003年,第60页。包括:地方官法兰廷,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主任医生(L.Bollekens)的孩子,孩子的老师(A.Gravenbroeck),翻译员(M.Visch),三个士兵,两个男奴,两个女奴。牧师(Leonaerts),他的妻子、岳母、两个孩子,两个男奴,三个女奴,三个女奴的孩子,和一个士兵。土地测量师(J.Brommer),他的妻子,和一个女奴。土地测量师(D.Cotenbergh),他的妻子,儿子,和一个士兵。
(44) 江树生译注:《梅氏日记》,第43页,第76页。
(45) 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1624—1662》,第29—30页。1623年12月25日东印度事务报告,有些文章误以为这1150名汉人是在澎湖捉到,其实是由在澎湖的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捉到的。当时澎湖只有少数渔民居住,远少于被捉获的汉人数。
(47)(76) 郑维中:《荷兰时代台湾社会》,第314—315页,第346页。
(48) 韩家宝、郑维中译著:《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第314页,第373页。
(49) John Franklin Jameson(Editor).Narratives of New Netherland,1609-1664,New York:Scribner,1909,p.330,pp.408-409.
(50) 中村孝志:《荷兰时代台湾史研究(下)》,吴密察、翁佳音、许贤瑶编译,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第36—37页。
(54) 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编译:《荷据下的福尔摩莎》,第196页,第198页,第230—234页,第276页。
(56) L.Blusse,N.Everts.The Formosan Encounter Vol.III,台北:顺益原住民博物馆,2006年,第429页,第451—452页。包括麻豆、萧垄、新港、目加溜湾和大目降村社的女祭司。
(58) 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编译:《荷据下的福尔摩莎》,第126页,第135页。
(61) 包括新港(9)、萧垄(4)、大目降(2)和麻豆(2)、大武垄(2)。
(62)(82) L.Blusse,N.Everts.The Formosan Encounter Vol.III,第255页,第469页。
(64) 韩家宝、郑维中译著:《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第299页,第313—314页。
(66) 王甫昌:《省籍融合的本质——一个理论和经验的探讨》,收录于《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台北:业强出版社,1994年,第60页,第78页。
(67) 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二)》,第500页。例如,1646年2月28日北部村社会议中规定原住民未得荷兰殖民者许可不得迁徙。
(68) 严中平:《老殖民主义史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195页。该学者是Peito Pomponazzi(1462—1525)的弟子。
(69) 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年,第169—170页。
(72) Tonio Andrade,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Dutch,Spoanish,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onclusion p.6.
(73) 韩家宝(Pol Heyns):《荷兰时代台湾的经济、土地与税务》,郑维中译,台北:播种者文化有限公司,2002年,第74页。
(75) 韩家宝、郑维中译著:《荷兰时代台湾告令集、婚姻与洗礼登录簿》,第147页,第160页,第163页。
(78) 郑维中:《荷兰时代台湾社会》,第258页,第262页。
(79) 村上直次郎编译:《巴达维亚城日记(二)》,郭辉中译,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9年再版,第428页。
(80) 郑维中:《荷兰时代台湾社会》,第246页,第249页。
(83) 程绍刚译注:《荷兰人在福尔摩莎1624—1662》,“1654年1月19日东印度事务报告”,第394页。
(84) 杭亭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黄裕美译,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