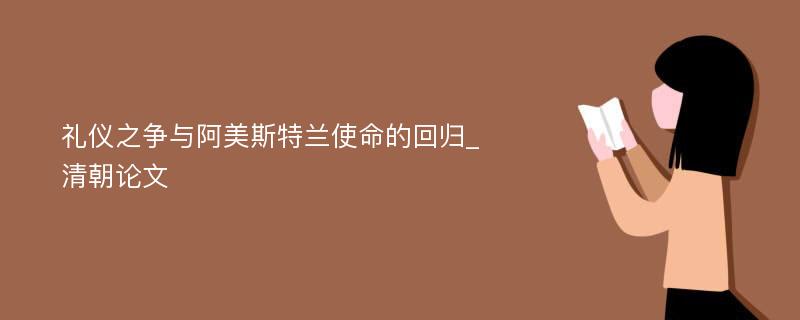
礼仪之争与阿美士德使团徒劳而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团论文,之争论文,徒劳论文,而返论文,礼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译者按:本文摘译自克拉克·艾贝尔的《1816和1817年中国内地旅行与往返航行记事》(Clarke Abel:Narrative of A.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一书的第三、第四章。艾贝尔是英国地质学会成员,阿美士德使团的首席医官和博物学家。这部著作于使团返英的第二年即1818年出版,其中包含有“最有趣的阿美士德使团到达北京朝廷的记载和对所访问国家的观察”。
离开白河口后的第三天,即(1816年)8月12日的下午4点钟,使团抵达天津。我们到达不久就得到通知,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将于第二天与清朝使臣和一位高级别的官员苏大人举行会议,① 会议之后赐宴,勋爵的随行人员也被邀请赴宴。因此,第二天上午10点钟,我们列队出发,前往会议大厅。正副使和随行人员乘坐轿子,侍者、卫队、乐队则步行作为先导。
将近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目的地,并立即被引进一间极为宽敞的房间。阿美士德勋爵、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依里斯先生(Mr.Ellis)和马礼逊先生(Mr.Morrison)被引进里屋与清朝使臣及其他官员商议事情;② 勋爵的随行人员则留在原地欣赏周围的物品。
大概过了两个小时,阁下重新出现在宴会厅。③ 毫无疑问,他过了这么久才回来,是因为在争辩礼仪问题。当中国人指着地毯再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跪地叩头时,我们怀着不祥的预兆注视着隔板。大使终于来了,他告诉我们他打算遵行的礼仪,性质类似于他有时在自己的君主宝座前施行的那一种,即他应该鞠躬,次数与清朝官员们叩头的次数相同。然后,他走向牌位,与乔治·斯当东爵士、依里斯先生和马礼逊先生一起很快到了牌位跟前站好,使6位清朝官员站在了他的右边,他的随行人员则站在他的身后。一个官员给出信号,这个官员提高嗓门,唱似的说了几个字,④ 官员们就双膝跪地,低下头,叩头碰地3次,然后起身。第二次、第三次,信号重复发出,他们第二次、第三次地跪下,每次都叩头碰地3次。使团的使臣与随行人员则各自鞠躬9次。
礼毕,阁下、乔治·斯当东爵士、依里斯先生被引导至为他们准备的设在右边的桌子就坐。同时,主要的清朝官员们在左边的桌子就坐,把他们自己安排在所谓的上位。⑤
第二天黎明,我们起锚开航,溯白河而上。
我们的船队走得很慢,因为清朝官员一再来拜访阁下,目的是为了迫使他遵行跪叩之礼。
8月16日早上,大使与清朝使臣的会议结束后,我们的船队非但不前进,反而顺流而下,停在了一个叫做蔡村的村庄前。早饭时,阿美士德勋爵告诉随行人员,他拒绝行跪叩礼,所以,使团很可能立即返回。我们因此得出结论,船队顺流而下是为返回作准备。我们很高兴地知道,中国方面得到了我们的船舰已驶离直隶湾的情报,因为这样一来,中国人就不得不陪同我们穿过大陆到广州。
17日上午,大使与清朝使臣又一次举行会议。会后船队离开锚地,再次将船头朝向北京开航。第二天(8月19日)一早,我们继续朝北京进发,下午4点钟,抵达距离北京12英里的通州。
使团中的非官方人员得到了消息,跪叩礼问题将在通州作最后决断,他们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将迅速决定他们命运的这件事情。21日下午,几位拜访阁下的清朝官员说有很高级别的钦差要来。我们吃晚饭时,得知来人了,大使立即准备迎接。卫队集合整队,乐队奉命在他们进来时奏乐。乔治·斯当东爵士、依里斯先生和海恩先生(Mr.Hayne)在院门外迎候,与此同时,阁下则在他的房间门前几步远的地方迎候。等了不长时间,他们就来了,共6位官员,都戴着或浅蓝或深蓝色顶子的帽子,其中3位的帽子上还有孔雀翎。他们带着一派无法形容的傲慢气度很快进入。他们急匆匆地走过在院门外迎候的先生们,不向他们回礼;也几乎不在意爵爷的存在,快步走进他的房间,不等爵爷进屋,他们就在上座落座。会议前的这一序幕预示着会议长不了。会议只持续了10分钟,结束时,清朝官员能被怎么轻蔑就被怎么打发。乐队不奏乐,卫队已撤离,原计划在他们返回时向他们敬礼也被取消。这些人的可鄙和专横给出了一种信号,也就是他们的皇上将怎样对待英王特使可想而知。
钦差确实是地位很高的人物,他们是和(世泰)与穆(克登额)。⑥ 这些人来教导大使演习正确的鞑靼之礼,不仅在觐见皇上时,而且在每次见到象征中国皇上的黄色布片时都要行这种礼。公爵看来倾向于用强烈的威胁性的态度来达到他的目的。
他们的使臣无礼貌地拜访我们之后的第二天上午,阁下由其他使臣和随行人员陪同,前往通州城中心的一个不大的官衙去拜访和世泰和穆克登额。
公爵在一个不大的厅里接见使臣和马礼逊先生,厅前是一个院子。作为惯例,不接待其他人员。他们可自行选择,或在院子里淋大雨,或在满屋难缠的中国人的难闻的气味中闷死。所幸会见很快就结束了。公爵坚持要行跪叩礼,而大使断然地加以拒绝。公爵于是威胁不让大使面见天颜就送他离开中国,阁下则表示已经作好离开的准备。不过,阁下拿出一封写给中国皇上的信递到公爵手中,信中说明他拒绝行跪叩礼的理由。公爵没有迟疑就接受了这封信,他好像愿意有这么一个台阶好让他降低他原先的声调。现在我们是否能访问北京的唯一机会似乎就看这封信了。在会议期间,公爵的说话声很高很果断,响彻整个院子。
我们访问之后的两三天里,阁下和公爵之间一直有联络,联络的结果怎样只有使团中的外交人员知道。但是,中国士兵的动作,以及关于使团里某个人的报告使中国政府感到不快,这两件事让我们一直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我们住处周围的士兵增加了一倍,并有告示贴出,警告中国人不要与陌生人讲话。中国人采取这些手段旨在影响爵爷的决定,想让他遵行对他们有利的跪叩之礼。几乎不必加以评论,这些手段是徒劳无效的。
27日上午,阁下给公爵送去一份照会,斩钉截铁地声明他决意不行跪叩礼,并要求为他的离开作必要的准备。于是我们等着立即返回;同一天下午,我们亲眼见到了公爵来拜访大使,通知大使说,皇上有变通一下跪叩礼之意,按照他提出的条件办,在圆明园的宫殿里接见他。这真叫我们又惊讶又感到满意。公爵现在满脸微笑和举止优雅,并且催着要我们赶紧出发前往宫殿,而以前他是不想让我们去那里的。礼物和行李装车的命令立即就下达了,并明确了我们第二天起程。
一切终于准备就绪,下午4点钟,我们出发了。清朝官员骑马走在四轮马车之前,马车之后是轿子,然后是二轮马车,再后面是侍者、乐队、卫队乘坐的运货车,殿后的是我们的行李。清朝官员和士兵,或乘轿子,或乘马车,或骑马,或步行全程随同。全体人马以一般的步行速度前进。
大约9点钟,队伍停在距离北京5英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大使被引导至一所更像棚子而不像房子的建筑里,进了一间大房间,就是这间房间供使团所有人员和他们的马匹使用。房间尽里头,有一张长桌,供大使和他的随行人员使用;房间中央有长凳、桌子,供侍者、卫兵和乐手使用;就在不远处,马在那里吃饲料。我们这顿饭,有整只的鸡鸭,但是没有刀叉来切割,最后我们只好用手撕了吃,让一旁站着的人看着挺可乐。我们喝的是水和很上口的烈性酒。
吃饭耽误了大概1小时,阁下很乐意地接受了陪同的清朝官员提出的赶紧上路进京的请求。那些清朝官员,以广(惠)和苏(楞额)为首,⑦ 是他俩催促阿美士德勋爵,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很焦虑,解释为什么催促赶紧上路时,说因为九门提督在城门口迎候阁下。
大概12点钟,我们抵达北京城郊,发现这么晚了,真奇怪,中国人都没有睡意,路上挤满了人,人人手里提着小小的卵形灯笼,都想看一眼这队人马。
队伍前行了一段时间,我们急着想快到城门口,但是却看到马车前进的方向不是朝着城门,心被猛地一击,我们的带路人在说谎,说什么九门提督在迎候我们,这不过是中国人说谎的一个例子罢了。
黎明时分,马车到达了著名的圆明园。
书本上描写的中国花园如伊甸园般的美景一一浮现在脑海,我在想象中尽情地享受。但是一想到欺骗、专横和亵渎,刚刚开始的好心情就全没了。
快到宫殿跟前时,见有一大群官员,其中几位身穿礼服的官员前来迎接大使,马车就停下了。前来的这几位官员中有苏大人和陪同我们的向导广惠,他们要阁下立即进宫殿。阁下一开始拒绝了,理由是太疲劳和病了,要求带他去为他准备的住处。但经他们三番五次地请求和保证,说只是留阁下用点茶点,阁下就下了马车,由他的儿子、乔治·斯当东爵士、依里斯先生和不多几位刚好在他身边的随行人员陪同,在大群官员的夹道中走向宫殿。这个过程中,他们多次企图将阁下与他的同行人员隔开,手段就是带着阁下走得很快,而其他人要赶上阁下,则不得不费劲地在人群中挤过去。最后,全部人员进了宫殿,都被塞进一间房间里,要是其他地方也都像这间房间的话,那真会令人猜想中国皇帝不过是个破烂王……这间房间长约12英尺,宽约7英尺,四面都有窗户,更确切地说,窗户上都装有窗板,就像船上的舷窗那样。屋顶上有纸质的已经破了的天窗。四周的窗板打开了,以满足低级别中国人员的好奇心,与此同时,一群官员和亲王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好奇心涌进了房间里,几乎使人窒息。
阁下一进屋就一屁股坐到长凳上,一路劳累、整夜等待和心情焦虑,真叫人筋疲力尽。所有的人都照他的样子假装闭眼睡觉,想摆脱中国人的无休止纠缠,但是他们根本不理会我们需要休息。我们到达后没几分钟,苏大人来了,对大使说,皇上要见他和其他使臣。阿美士德勋爵回答说,因为劳累、有病,和必须的礼服还没到,使他真的不可能按照皇上的要求办,并且要求中国皇上允许他那天休息,同时请求带他去指定给他的下榻处。爵爷的理由不被接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以皇上的意愿来催促,好像没有被拒绝过似的,阁下则坚持一开始就说明了的理由。苏大人的做法受到广惠的强有力的支持。不过,发现他们的恳求无效后,他们退出去了。但是紧接着,和世泰公爵带着一股决断的气势进来了,他走到大使跟前,重复皇上要见使臣,并补充说,只要求使臣们按英国的礼仪行礼。当他得到与苏楞额和广惠所得到的同样的回答之后,竟粗鲁地抓住勋爵的胳膊,同时召唤身边的清朝官员帮他一把。清朝官员听从他的召唤,起身向前。为了让大使摆脱他的粗野的突然袭击,不等清朝官员们接近大使,我们就行动起来,向大使靠拢。这一突然的行动阻止了公爵,也警告了他的随员。公爵松了手,他的随员们也一脸惊愕地后退了。爵爷摆脱了公爵的强抓之后,以最坚定和尊严的态度抗议他所受到的侮辱,声明必须把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独立的君主的代表来对待;宣布休想用强制手段把他带到皇上面前。公爵立即变了说法,尽力把我们认为是强迫大使离开房间的企图,说成只是中国人对一个不能行走的人给予的帮助,并补充说,一个病人自己哪有主意。还极力用劝导的态度,恳求爵爷觐见皇上。他说,皇上只是想看见他到了,不会扣留他的。劝导,如果说一开始用或许能奏效的话,现在也太晚了。公爵的目的没有达到,极不高兴地离开了房间。
于是阁下对我们这些亲眼见到他的遭遇的人提出要求,说这样的事情可能还会发生,告诫那些携带武器的人,不能使用武器来制止。我们的反应在这一时刻不是很乐意的。我们不能不意识到,我们落到了一个专横的、反复无常的政府手里,这个政府的大臣们占有最有利于他们的制高点的企图被挫败了,他们显然不再受什么礼貌、谦恭的约束。尽管我们满腔义愤,但是当大群的太监、官员、亲王出没房间不断地烦扰我们时,我们还是克制住了。尽管马礼逊先生最强烈地要求他们讲礼貌、讲礼仪,他们还是逼近我们,最无礼地站到我们跟前,盯着我们看,他们甚至想要斜倚在长凳上的大使站起来,好让他们看得更清楚些。显然,他们把我们看成是一种没见过的动物,好奇地对我们进行观察,并不把我们作为应给予文明待遇的人。他们看起来还猜想我们可能完全不会伤害他们,而如果他们再次企图达到他们先前的目的,他们就会发现英国人并未被训练得不反抗专横的侮辱。
我们的沉思被来自公爵的信函打断了,公爵通知爵爷,觐见皇上的安排已取消,并邀请爵爷到他的房间去,那样可以摆脱拥挤的人群。爵爷看着这封邀请函,心想邀请是假,把他拖到皇上面前是真,立即就拒绝了。很明白,如果他能去公爵那里,那么他的身体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见皇上了。当得到拒绝的回答时,和世泰失去了耐心,又来见阁下。这一次他非常有礼貌,并用尽了他所能想到的一切说法来引诱大使迎合他的意愿。他的纠缠太叫人怀疑了,不能照他说的办。他未能达到目的,再次离开房间。之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给阁下递送信息,烦恼阁下,而他得到的回答总是“大使愿意前往为他准备的房子”。过了一段时间,信息来得不那么频繁了,然后就完全没有了。原来聚集在宫殿前的清朝官员和士兵奉命解散。很快大使得到通知,他可以去他自己的房间了,并且将有御医去给他诊治。
爵爷立即离开宫殿,挣扎着前往他的马车,马车是停在我们下车的地方的。起初,最大的困难是穿过包围着我们的中国人。几个士兵,挥舞着鞭子,企图开出一条通道,但是因为他们的鞭子只朝地甩,他们的努力白费劲。不过,我们身边有更有效的援助,公爵就在离我们不远处,见我们受阻,抓起一条鞭子,狂怒地朝他跟前的中国人抽去,迅速地为我们开辟出通道。身穿礼服的三六九等的贵族们,使劲地相互推搡着尽力逃离他。于是我们很快到了为使团准备的住处,在海淀的一个村子里。⑧ 在那里,见到了我们的同伴,他们是被人故意地与我们隔开的,对于我们的失踪,他们感到困惑。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承诺的御医很快就来为大使诊疗。这位先生,看起来已过了中年,穿着官服。他在爵爷的双腕上把了脉,说可能是吃了中国饭,胃里不舒服,建议休息并服用催吐剂。然后他就退出了。此人向皇上的报告,起了实质性的作用,这可以从以后我们所受的待遇看出。
供使臣们下榻的房子相当舒适,房子本身和周围环境都很好,是马戛尔尼使团的可尊敬的陪同人员之一乔大人的邸宅,乔大人现在在中俄边境。
吃了一顿丰盛美味的早餐,我们出去寻找可供我们欣赏周围景致的休息地。我们一夜赶路,实在太累,不等我们的帆布床卸下,就倒在长凳上或椅子上,沉沉地睡着了。但是几乎还没有开始做圆明园美景的好梦,我们就被赶紧准备的吵声喊醒了。这次是要我们立即准备回通州。因为大使拒绝觐见,皇上发怒了,下令我们立即离去。张(Chang的音译)来传达谕旨,很快又来了一个官员,他的语调很高,手势很专横,叫喊着要见主要的翻译。马礼逊先生出来了,那位神气活现的人说:“我是信使,从九门提督那里来,九门提督是北京九个门的总管,帝国最高的军事长官,统率一百万人。他下令立即离开他管辖的地区。”⑨ 这样一道命令没有被完全拒绝,我们于是准备离开,但是不能如中国人所愿,因为使团中的远征队不都走。中国人提出来,让我们先动身,他们随后为我们押运行李。但是他们无法诱使阁下立即出发,直至阁下对每一件从车上卸下的物品再装上车感到满意之后,我们才起程。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到达北京。
大约(半夜)12点钟,使团的很多人淋着大雨停在一所房子前,前一夜,就是在这所房子里,我们受到过怪怪的招待。现在我们既无遮挡,也无食物,只好躲在马车里。车停了约一个小时,我们睡了一会,然后又起程赶路。凌晨4点钟,我们到达通州,回到船上感到很高兴。船,在我们当时的境遇中,就像家一样吸引着我们。原先供使臣们下榻的房子都闭门拒绝我们……
我们多少恢复了一点体力之后,回想起过去两天里发生的事情,我们真觉得像大梦初醒一样,而不是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什么。无法用任何可能的因果线索把这些事情串联起来。我们只能推测,我们被这样赶着来去匆匆地往返圆明园,并受尽侮辱和不便,只是为了遂那个反复无常的暴君之愿。估计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是徒劳的,还是这个暴君,可能再一次凌辱我们,或许也可能要我们觐见。
入夜前,我们的担心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因为有可靠消息说,皇上从他的大臣那里得到了大使拒绝觐见的真实原因,对自己草率地打发了使团有悔意。第二天一早,这一传说因苏和广的到来而被证实了,他们带来了皇上给摄政王的礼物,包括一柄白里透点绿的玉如意,一盘玛瑙朝珠和一些别的珠子,还有几个刺绣的丝质荷包。作为回礼,他们从英国的礼物中挑选了英王和王后的肖像画,汤卡斯特(Doncaster)的赛马图,几件铜版印刷品,几幅中国地图。这真是符合之后的一道谕旨所说明的“厚往薄来”之意。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马礼逊先生得到了相关的书面信息,上面说皇上并不知道我们整夜赶路的情况,也不知道我们没有觐见皇上穿的礼服;只知道英使拒绝觐见的唯一借口是大使生病了。对此,有理由推测中国医生把大使生病说成是装的。还说,与使团有关的所有中国官员都被降了级。降级的事之后被证实了。
我们在通州,从8月20日待到9月2日。
[收稿日期]2009-2-20
注释:
① 阿美士德勋爵,英国使团正使;“苏大人”即苏楞额,工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译者
② 乔治·斯当东,英国使团第一副使;依里斯,英国使团第二副使;马礼逊,英国使团翻译。——译者
③ 阁下(His Excellency),指阿美士德。原作者称呼阿美士德时,还用大使(Ambassador)、爵爷(His Lordship)、勋爵(Lord)等。——译者
④ 贝尔先生(Mr.Bell)说到在北京的俄国使节在皇帝面前行礼时说,礼仪官站在一旁,用鞑靼语“Morgu”和“Boss”发出指令,第一个字的意思是“跪”,另一个字的意思是“起”。这两个字,他补充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⑤ 迪·圭讷司(De Guignes)说:“关于座位,汉人以右为上,而满人以左为上。”我们没有机会来证实此说。我们在中国时,在礼仪场合所观察到的,每次都是以左为上。
⑥ 和世泰,皇舅,理藩院尚书,原作者常以“公爵”称呼之;穆克登额,礼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译者
⑦ 广惠,长芦盐政。英国使团船舰抵达天津口外时,他奉旨至大沽照料。——译者
⑧ 原文为“in the village of Hai-tcen”。“Hai-tcen”在其他相关英文著作中有拼为“Hai-teen”的,故译为海淀,而从地理位置来看,也应为海淀。——译者
⑨ 这位传令官没有严格地按照命令是什么就传达什么,而是趁机对大使的行为表达了一番自己的看法,他说:“大使太无礼了,你们的王是可敬的和恭顺的,你们的大使可不是,他的言语大不敬。皇上将写信给英王指责他。”当告诉他大使只是请求中国皇上仁慈地延迟一下觐见时间时,他声称:“天国礼仪,岂可擅改!”“现在没时间谈礼仪”。他冲着马礼逊先生说:“我被派来这里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就是叫你们离开。”说完就和其他人一起走了。
